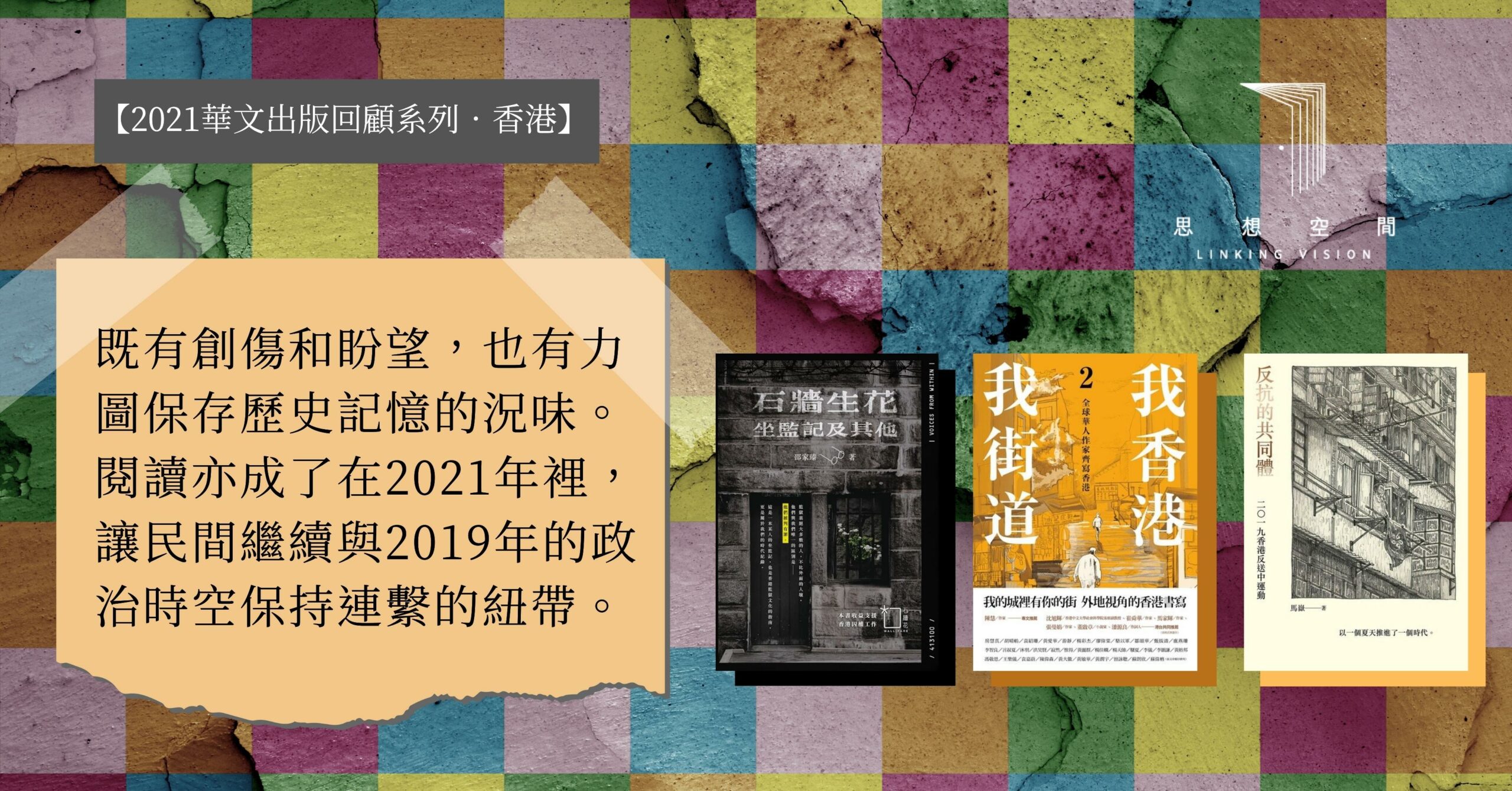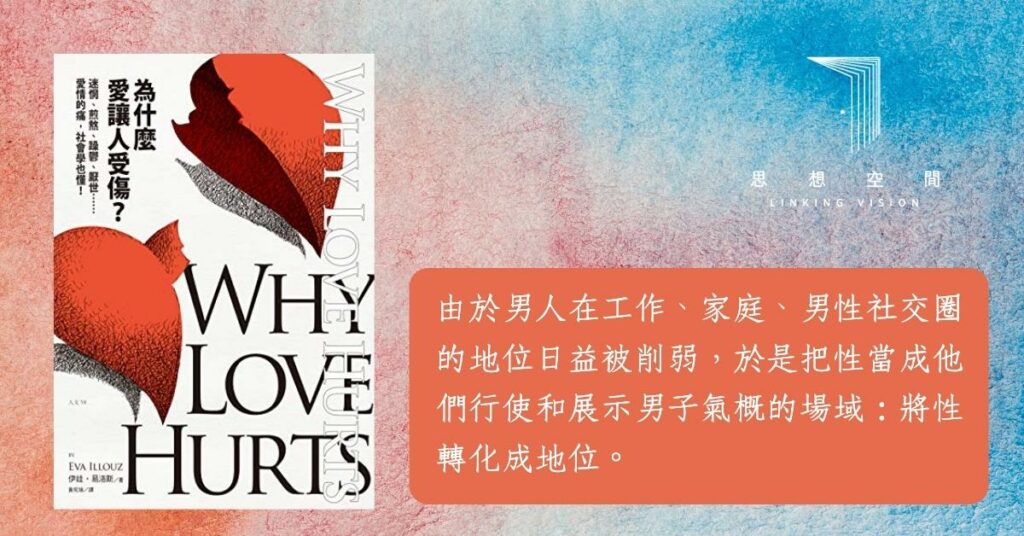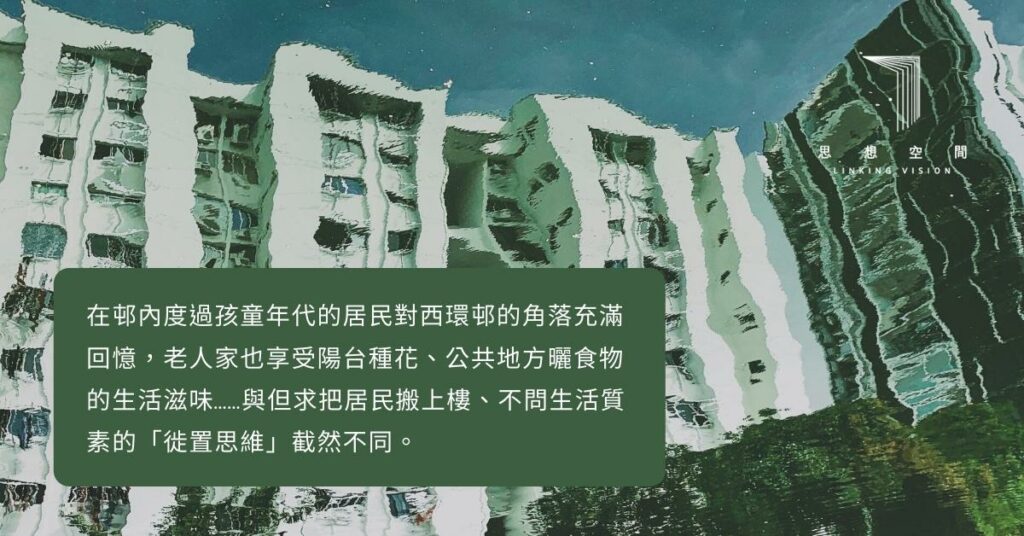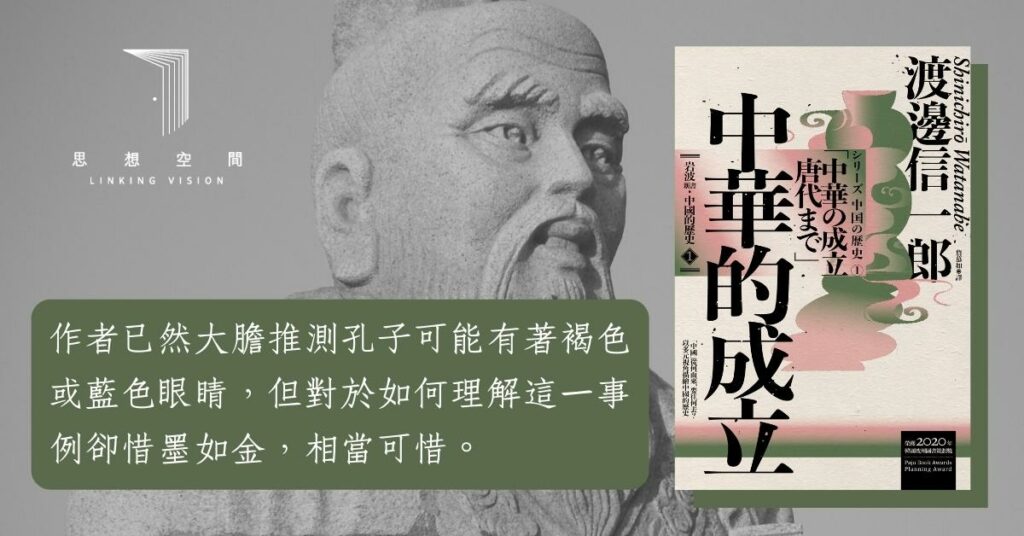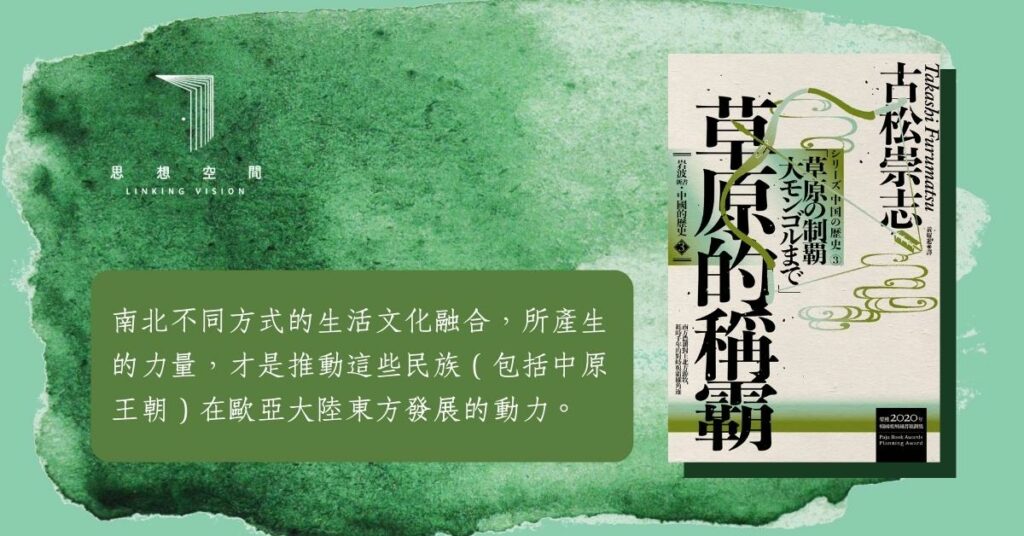文/白立丁(中國書評人)
編按:2021年將盡,思想空間邀請來自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及星馬的評論人,分別對本年度四地華文出版作出全貌觀察,並為該地區年度出版生態提煉出一個關鍵詞。本文邀請了中國書評人白立丁,談談這一年中國書業在政治審查之外,還面對著哪些不容忽視的問題與困境。
文章原題為:〈在焦慮和徘徊中的大陸出版〉,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擬。
對於大陸出版和閱讀而言,2021年既不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不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但一定是一個焦慮和徘徊的時代。任何時代都有人會期待出版成為一項純粹知識傳播的事業,但是事實卻是:自從出版誕生以來,就被政治、資本和社會權力所左右。
中國出版業的弔詭與困境
中國的出版業呈現出一種弔詭的現象:一方面,因為政治審查的原因,導致某些書的出版週期延長或者不能夠出版,要獲取書號(ISBN)和圖書在版編目(CIP)十分困難;另一方面,卻是大量資本所推動的民營出版品牌,塑造著人們的閱讀習慣。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果麥文化。在2019年前,公版經典著作是果麥出版的重要盈利來源之一,如四大名著、《小王子》、陀思妥耶夫作品等一些外國經典名著的重譯。與傳統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和譯林出版社不同,果麥的選題並不是書籍本身的重要性,或如同商務印書館的經典譯叢那樣有明確的思想史脈絡作為基礎,而是單純的市場導向。
果麥在2021年出版的「經典重譯系列」,其翻譯品質未必勝於過去一些老的版本,但是從裝幀、到市場行銷都針對都市中產階級的品味。這種資本的優勢,也能夠讓果麥抓住一些本土的熱門IP。通過視頻傳播「出圈」的刑法學家羅翔、文學教授戴建業都是果麥的簽約作者,而以礦工出身的作家陳年喜,也通過果麥出版了最新的作品《微塵》。無論是精裝出版公版書,還是出版童書,科幻題材,以及推出熱門作者,毫無疑問,果麥模式可能是目前民營出版能夠存活並且盈利的少數可行的模式。而對於同行業和讀者而言,卻可能是毀譽參半。
2020年發佈的「全球出版五十強」,表明出版業已經被跨國大型出版巨頭所壟斷,其中有四家中國出版集團入圍,即:鳳凰出版傳媒、中南出版傳媒、中國出版集團和中國科技出版傳媒。
鳳凰出版傳媒旗下的江蘇人民和譯林等幾家出版社,中南出版傳媒旗下的浦睿文化等因為資金的充足,相比果麥模式而言,能夠更長期出版一些短期收益較低的系列叢書。比如海外中國研究(蘇人社)、以及譯林社的人文與社會譯叢,不可忽視的還有類似中信出版社。目前在中國出版界,對於海外書籍版權的購買,因為這些資本雄厚的大社的參與,不僅提高了版權代理競價的成本,也造成了一些熱門外文IP的壟斷。當然,去政治化和不觸及敏感議題仍舊是任何出版社的前提法則。
三輝這些獨立出版機構,不僅規模和受眾較小,且這些偏重學術、思想類的獨立出版機構在未來,特別是在資金方面,還是會面臨不小的挑戰。
市場與審查雙重壓力下的民間出版
傳統的出版社如商務和三聯(北京、上海),仍舊延續著長期打造的名著和譯著系列,而華夏出版社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六點圖書)也成為劉小楓主編的《經典與解釋》各種系列的出版管道。長久以來學術界不乏對劉小楓及其立場的批評,但是在目前思想界這套叢書還是有其獨特的聲音和意義,今年從《胡克與保守主義主義》、地緣政治學叢編《地緣政治學的世界》,《卡爾 · 施米特的國際政治思想》,人們可以感受到其背後具有的思想框架和問題意識。
與之相類似的,還有民營出版的代表,如三輝圖書。其出版的圖書種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創辦人的學術品位,讀者們也可以感受到,最近幾年三輝具有了更為多元對話的出版理念:從早期偏重於政治自由主義的脈絡,到如今既有激進左翼思想如阿甘本、巴迪歐,也有對於女性主義、後技術時代、第三世界聲音等多元立場和議題的關注。
相比於《經典與解釋》有國家課題和出版社資金的支援,對於三輝這些獨立出版機構,不僅規模和受眾較小,且這些偏重學術、思想類的獨立出版機構在未來,特別是在資金方面,還是會面臨不小的挑戰。書號和CIP的審核,都左右著這些獨立出版機構的運營成本和出書的可能。它們也必須通過和國營出版社的合作,才能獲得書號出版,從而導致無法形成規模效應和建立品牌的長期影響力。
我們仍以三輝為例,儘管其出版了不少品質內容都俱佳的書,但是這些書散落在南京大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信、華僑等各大出版社。除了一些資深讀者外,很難有人意識到三輝這個出版機構。儘管如此,這些獨立出版機構的堅守還是值得尊重的。今年值得關注的是三輝的「現代人小叢書」系列:這系列書提供不同思想立場的學者對當下日常生活的反思和批判。還有一些小眾的獨立出版社,如以出版詩歌和先鋒寫作、本土化為主的「51人」,今年出版的《每日的工人階級史》也為讀者提供了獨特面向。
當下的中國出版界和思想界,也都陷入一種非此即彼的矛盾中——要麼以某種歐美中心主義的視角出發;要麼就以有著同樣問題根源的中國中心主義,來理解世界和自我。
在體制中謀求自由的大學出版
既區別於果麥的市場模式,也和三輝這些獨立出版生存境遇不同的,是大學出版社。
除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這些以中小學教材盈利而補貼學術出版的個例外,目前大學出版社也在市場和體制需要之間掙扎,其既限制於自身的定位也需要有市場利潤的要求。畢竟國家課題的補貼,也會左右大學出版社策略。
而國家的干預事實上是雙刃劍,並非只有消極的一面(即政治審查和出版國家政治思想導向的書籍)。對於出版而言,其積極的方面就是能夠不完全考慮市場盈利的影響,而出版一些經典卻冷門的書籍。例如過去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康德全集》,《亞里斯多德全集》,以及黑龍江大學出版社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文庫」,此類規模的出版都必須依靠國家課題方式資助才能夠實現。
2021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謝林著作集》、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守望者」系列和由南京大學出版社主要承擔出版的「當代學術棱鏡譯叢」系列。這些出版系列囊括了一些英美之外的當代歐陸思想的著作,例如:目前謝林著作的中文翻譯,甚至遠超過目前英語世界紐約州大學出版社的當代歐陸哲學(Suny Series in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系列的數量。
前些年,採取市場化策略比較成功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也是「理想國」叢書的主要合作者——因為管制和整頓,在近兩年的出版趨勢更偏重於文學藝術類、偵探推理虛構類。其在思想方面的出版,目前主要就以「新民說」系列和部分「理想國」系列的品作為維持。而「理想國」叢書也和其他國營出版社合作,如中譯出版社、上海三聯、海南出版社等。
就「理想國譯叢」而言,它表現出這些出版人和叢書編委的特有品味,在於對社會轉型的關注。一方面,這套譯叢推出了不少英美學者和作家的著作,例如《福山作品集》;另一方面,可能受限於編委的眼界和品味,該叢書選題遠比以上談到的幾個大型譯叢要狹窄,過度關注於英美世界當下流行的一些作家和作品,遠非這套譯叢自身期待那樣,要求具有經典性和思想深度。當然,目前看來,這套叢書還是提供了一個視角,供讀者思考當下的社會處境。
其他大學出版社,因為缺乏行銷和宣傳的管道,而不太為大眾所知。但是我認為今年有必要提到西北大學出版社的「精神譯叢」、重慶大學出版社的「拜德雅」系列,以及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的「人類經濟社會思想探索前沿叢書」。這幾套叢書有的關注於當代和後現代的問題,有的關注歐陸和第三世界的人文、藝術、思想,也有以專業學科視角關注社會轉型,都各具特色,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框架和多元的視角。
事實上,當下的中國出版界和思想界,也都陷入一種非此即彼的矛盾中——要麼以某種歐美中心主義的視角出發;要麼就以有著同樣問題根源的中國中心主義,來理解世界和自我。正如上面提到的「理想國譯叢」那樣,目前不少出版社的關注都過度集中在英美世界的文化中,對於英美世界以外的關注遠遠不夠。例如今年坦尚尼亞作家古爾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文世界卻鮮有該作家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後浪」出版社的「華語文學」系列中推出了馬來華人張貴興、黃錦樹、臺灣袁哲生、童偉格等作家的文學作品,可能會給大陸讀者提供一個更多元、寬廣的視野,認識「華人」這個群體。而人民文學出版社在2021年重新出版的肯亞作家恩古吉 · 瓦 · 提安哥的作品,同樣也是讓我們打破歐美中心主義,更多瞭解其他世界的一個視窗。
普遍的焦慮迫使出版業更追求同一化的熱點,跟風和「爆款」。各種版本的氾濫,也反映了出版社選題的單一化和趨同化背後的急功近利。
流量至上與直播帶書引發的「焦慮」
上面概述了2021年的一些出版狀況,接下來,我會談到一些這個時代出版和閱讀的精神狀況——「焦慮」。
無論是出版界對官方審查和市場競爭,無疑都具有不確定和張力中的「焦慮」。但是更多還是我們這個單一化、同質化的時代所帶來的。
社交媒體和娛樂行業的發展,讓一些原本局限在學術界和學科內部的人能夠被公眾所知。思想史學者劉擎在參加了「奇葩說」之後,通過「得到圖書」出版的《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成為現象級的暢銷書,在豆瓣1萬多人打出了9.1分的高分;有趣的是,劉擎在2006年通過三輝圖書出版的思想史論著《懸而未決的時刻》,評分人數200多人,其中還有一些是今年參與打分的人,但就內容,三輝的這本書可能更反映了劉擎的思考深度。
學者進入公共視野為人所知本身無遺是件好事,也是對學者思想的肯定。但是,從「得到圖書」和其他媒體更深入介入到出版業時,我們也需要意識到某些危機。一方面,「得到」和類似的「知識付費」形式,還是反映出這個時代的焦慮:讀書被作為「使用」的技能和途徑,而不是一種生活的「享受」。
「得到」所製造的幻想,就是閱讀和知識是可以通過簡約化的步驟、逾越那曲折經驗的過程。這種風尚造就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出版和閱讀的習慣,成就了各種知識付費的公司,也是我們單薄和同質化生命最直接的寫照。一切以「快」、「直接」為目的,五分鐘可以講完電影,十分鐘可以理解一本書,我們生命的經驗已經被成為了流水線的平面畫,「焦慮」成為了生命的狀態。我們知道一切,卻一無所知。
此外,讓人遺憾的是,無論在學術還是公共領域中,與出版最為息息相關的書評,卻喪失了自身作為評論反思的功能:有些因為審查原因而被關閉,有些要麼淪為軟廣告,要麼無人問津。對於一本書的好壞和優缺點,人們已經無法在通過閱讀客觀深刻的書評,而做出自己的評價。相對好的,還會參考一些嚴肅的書評雜誌和公眾號,以及豆瓣上的評價。然而大數據和僱傭「水軍」已經深深影響到人們的閱讀。不論是出版還是後續評論,都是以流量和粉絲作為導向基礎,人們真正獲得的是不再是知識,而是短暫的熱鬧。
追求「快」和「流量」,對於出版社的長期發展而言,並不一定是有益的。傳統出版業相較於新媒體行業,更像是一種夕陽產業。然而出版業對於人力資本的要求卻更高,更看重學歷和經驗;而新媒體相比之下門檻就很低,收入卻是傳統出版業的數倍甚至幾十倍。這種差距也讓很多出版社的年輕編輯頻繁跳槽,流入到新媒體行業。相比於隨時可以註冊公眾號「換馬甲」的新媒體行業,傳統出版和書評仍舊還恪守著品牌和專業操守。這種矛盾更進一步加深了焦慮感。
普遍的焦慮迫使出版業更追求同一化的熱點,跟風和「爆款」。如同十多年前,在領導人的推薦下,一年中不下有10個版本的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出版。今年相同的例子,是霍夫施塔特在1960年代所寫的《美國反智主義傳統》一下就出版了5個版本。從積極方面說,出版社的競爭給讀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而從消極的方面看,畢竟這本著作寫於上個世紀60年代,儘管經典,但已經有了新研究作為補充。各種版本的氾濫,也反映了出版社選題的單一化和趨同化背後的急功近利。
比起審查本身,我們時代的精神焦慮對於出版和閱讀習慣的改變更為強烈,技術和社交媒體也強化了這點。
閱讀出版,勿忘初衷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基本上所談的出版更偏重了外文作品的譯介;而相對的,有關本土著作出版談及較少。真正原因在於,儘管今年不乏優秀的虛構和非虛構作品、以及本土原創出版物,但是我們仍舊可以發現一個並不樂觀的趨勢——對於虛構作品,很大程度上人們關注的仍舊是流量IP,許多作品並非本身的優秀,而是因為它們被轉換為了影視作品,成為話題。非虛構作品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需要補充的是,在現今學術評價體系的約束下,真正願意專心寫一部整體性專著的學者愈來愈少。近年來被各大年終好書排行榜選出的作品,大多數都是將作者早已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文章集合成冊。
儘管在英美學術界專著出版也常常如此,但是兩者有一個很大的區別——英美專著很大程度上都是圍繞單一主題論述,或所發表的論文本身就是從自身專著中抽取出來,最終成書時仍舊需要修改,讓主題連貫。然而,目前的中文界不良的風氣,就是所謂一些專著,不過是作者已經發表的文章集合,除了序言之外,幾乎一字不改。儘管這可能有利於知識的傳播,但是這種草率之作,卻常常成為各大年終書籍榜單的首選。有趣的是,這些榜單的書幾乎都千篇一律,也許就是本土思想界貧瘠的一種隱喻。
每年年底,各大媒體又都會推出各種書籍榜單、獲獎作品。然而在這些熱鬧的背後,我們已經喪失了專業性、犀利、更為客觀的書評體系,而是以媒體、大眾打分、水軍刷分、甚至是社會關係網絡,來評價書的好壞,或者來選擇閱讀一本書。一些自媒體「網紅」,即便不理解書的內容及其真正價值,也能左右大眾對書的選擇和評價。如今,我們很少思考一本好書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而任由一本壞書敗壞我們的品味。無利益地認真閱讀一本書、評論一本書,也成了這個焦慮時代的奢侈品。
很多人會將如今的出版問題、閱讀問題,都單一的歸咎於政治的管制和出版的審查。顯然這些都會有影響,然而並非全部的原因。比起審查本身,我們時代的精神焦慮對於出版和閱讀習慣的改變更為強烈,技術和社交媒體也強化了這點。英國作家切爾斯頓談論現代社會的病徵時,認為部分是因為「沒有能力在做事的時候不做的過分」,對於出版和閱讀也是如此。我們過度依賴了外在,卻忘記了出版的初衷,是將有價值的知識呈現出來;而閱讀只是隨時隨地,一個人拿著一本書安靜地坐下來,其實就這麼簡單。但對於當下的我們而言,卻稀缺而彌足珍貴。
延伸閱讀:
【2021華文出版回顧 · 香港】鄧正健:政治紅線當前,低調進行文化「戰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