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娃 ‧ 易洛斯 Eva Illouz(社會學家)
譯/黃宛瑜
編按:近幾日來,台灣藝人王力宏與李靚蕾的離婚風波,引發不少討論。李靚蕾在網絡上發佈數篇長文,揭露兩人婚姻中的不平等關係,也引起了不少女性的共鳴。近年來男性公共人物捲入情色風波者不在少數,我們藉此機會與讀者一同思考,這些事件和現象為何會發生?2019年聯經出版的《為什麼愛讓人受傷?》一書,就從社會學角度進行詳盡分析。
本文摘選自伊娃 ‧ 易洛斯(Eva Illouz)著:《為什麼愛讓人受傷?:迷惘、煎熬、躁鬱、厭世……愛情的痛,社會學也懂!》一書第二章,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
歷史學家約翰.托許(John Tosh)說,在西方社會,男子氣概主要在家庭、工作、純男性社團這三個領域內展現。[1] 家庭中享有權威;不當奴隸,有能力獨立賺取薪資;能在志願性質的協會、酒館、俱樂部等女性禁入的場所內形成有意義關係;這是男子氣概的傳統三大支柱。
然而,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崛起,標誌這三足鼎立的結構出現了重大改變:從二十世紀開始,女性主義運動風起雲湧,劇烈衝擊著政治、經濟、性等諸多領域,有效且持續地挑戰和侵蝕家庭中的男性權威。同時,官僚組織和薪資工作也削弱了男性的獨立自主性,如今多數男性必須在其他男性和(或)女性監督下工作,純男性社交場所業已式微(除體育賽事外),正規社交休閒活動泰半歡迎任何人參加,沒有性別上的限制。
假使,男子氣概真的如托許所言,是種「社會地位,必須在特定社交脈絡下展現」,[2] 那麼,顯然構成那地位與脈絡的基本元素已經隨著現代性的到來而遭受嚴重侵蝕。眼看獨立自主、家庭權威、男性團結通通被削弱了,傳統男子氣概不再是地位的表徵,它成了反指標,成了文化符碼,與勞動階級緊密扣連。
正是在此脈絡下,「性」取而代之,成為彰顯男子氣概的地位標誌。誠如我在第一章論證的那樣,「性」可以授與地位。性魅力和性慾,成了性別認同的內涵和依據,認同又以地位的形式向外展現。[3]
畢竟以前還可透過家庭權威、工作自主、男性團結等等,來彰顯地位、展現男子氣概,現在這三樣東西全部融匯成了「性」,用「性」來表達和展現。
通過「性」來成就的「男性地位」
在某種程度上,性向來跟男子氣概密不可分;可是在很多社會,男人必須先掌握社會權力才有機會接近女性。男性藉由性征服,跟無數女性發生性關係,來肯定自己,證明自己比別的男人、乃至於所有女人掌握更多社會權力。也就是說,「性」若是鬥爭場域,那麼在傳統社會裡,能夠在性競技場內叱吒風雲的人顯然就是權勢較大的男人,因為男性權力通常被轉換成性支配,有機會接觸到更多類型的女人。
按照法蘭西斯.福山的說法:「古往今來,唯有權高位重、富甲一方的男性才有機會接近眾多女性(即在婚姻框架下與人發生非正式的性關係)。」 [4] 換言之,性是社經地位的直接指標,反映一個人的社經資源。但享受多重關係的同時,勢必也要承擔相對的義務,以各種方式支持女性,要麼最後跟她們結婚,要麼提供經濟好處。
「性」之所以跟男人的地位扣得那麼緊,我在這裡提出三種解釋。
以前,性在某種程度上,其實跟男人的社經地位密不可分,男人掌握權力,似乎也就意味他跟不同女人性交的機會增加,所以性與權力地位的關聯迄今仍保留,儘管現在薄弱許多,不若以前強大。假使說,跟不同女人性交的機會是有限的,並非人人唾手可得,那麼,任何階級的男人都會被系列型性關係(serial sexuality)所吸引,因為性是男性地位的表徵,代表他擊敗了其他男人,獲得女人的青睞。男性競爭、驗證程序、社會地位,都是經由性範疇來傳達。對男人來說,性是地位的象徵,表示他有能力跟別的男人競爭並獲得女性的青睞:「異性戀男子傾向把跟女人性交的機會當成驗證的手段,為此激烈競爭。」[5]
第二點,男人也把以前握有的家庭控制權轉移到性和性慾上,性成了他們表達、展現權威與自主性的場域。感情疏離——剔除性裡頭的感情因素——後來成了一項比喻,且寓意擴大了,它隱含了獨立自主、控制權、男子氣概等意思。所以,應將「感情疏離」視為一種譬喻的手法,它象徵男性獨立自主,當然前提是性和婚姻徹底切割。
第三點,男人雖然因為性而存在著競爭的關係,但彼此之間也錘鍊出堅韌無比的紐帶,將女人的身體當作一件物品,促使他們團結一致。[6] 換言之,既然性自由被認可了,取得合法地位,男人由於他們在工作、家庭、男性社交圈的地位日益被削弱,於是把性當成他們行使和展示男子氣概的場域:將性轉化成地位。
假使性對男人而言是他們展示地位、跟其他男人建立紐帶的方式,那麼,眼看自己在家中失去掌控權,工作領域又被剝奪自主權,性自然成了他們依託的對象,膨脹它的重要性;畢竟以前還可透過家庭權威、工作自主、男性團結等等,來彰顯地位、展現男子氣概,現在這三樣東西全部融匯成了「性」,用「性」來表達和展現。
男子氣概如何被重新定義
性之所以那麼重要、在男子氣概的重新界定上扮演那麼核心的角色,關鍵主因就在所有人,不管男也好女也罷,都面臨了急遽情色化轉變。情色化的意思是說,兩性關係徹底擺脫了道德框架的控管,性吸引力——性感——成為性別認同的基礎,跟自我(self)的道德展演完全畫清界線。情色化是段漫長的過程,橫跨整個二十世紀,它不僅催生了、更加速了男子氣概被重新定義的進程。[7] 前面第一章我說性成了鬥爭的場域。
現在讓我再講得更精確一點:由於男人必須透過性來取得並維持社會地位,性成了一座競技場,男人為了確認他們的性地位,不得不下場展開激烈競爭。
我們不妨做個假設,如果說一九六〇年代以後,性和性慾成了女性行使跟展現自由的據點,這很可能是因為系列型性關係跟男性權力扣合得很緊。性邂逅的環境與條件高度情色化,且性不管對男女而言都是一種地位的指標,但儘管如此,男女情色化的路徑還是不一樣。
人類學家布雷克伍德(Evelyn Blackwood)便指出,「面對性,男女所處的位置不同」,「不同」之處在於「掌控行動(acts)的能力不同,替行動命名的能力不同;對特定實踐(practices)主張權利的能力不同;最後,貼標籤的能力也不同,即把某些實踐貼上准許,某些貼上不准許」。[8]
社會學家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則以「性的階序系統」形容兩造的不同。[9] 然而,最能道盡兩性差異的其實是性策略;也因此,我們現在要轉向,開始探索女性的婚配策略。
大量證據顯示,由於女性進入勞動市場,接受高等教育,使得她們婚嫁和生育的時間雙雙推遲(而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只有結婚時間推遲,生育時間未見延後)。
為何女性更願意給出承諾?
女性承諾的意願顯然比男性高,但這無疑是我們所謂的「專一配對策略」所造成的結果。
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認為專一策略深受女性青睞的理由是,依照男女雙方訂定的契約,男性負有保護女性的責任,避免她們遭受強暴,以此換取她的忠誠和依賴,所以女性的專一策略屬於契約的一部分。[10] 她這裡認為,專一策略是女性依賴性、性別不平等、不對等權力關係所導致的結果。艾莉絲.羅西(Alice Rossi )則以另一種觀點解釋女性的專一策略,她說女性具有「先天雙重」——「趨向男性取向性」和「趨向家中子女」。[11]
不過我認為,與其說異性戀女子先天趨向男性,倒不如說她們實際上基於生育的理由而選擇了排他性策略。也就是說,我們比較容易在那些渴望在一夫一妻家庭框架下為人母的女性身上看到排他式性關係。這些女性其實是將尋覓伴侶這件事放在她們生育角色的構建和認知底下。[12]
在前現代傳統父權社會,男人跟女人一樣,迫於成規和文化的壓力,必須生兒育女,成為一家之長,傳承香火。活在傳統父權體制下的男子,需要組個家庭證明自己,證明自己具備男子氣概,足以統率管理子女、女人、僕從和土地。可是在一些父權體制多所爭議的社會(例如我們的社會),男性迫於習俗倫常生兒育女的情況少得多,因為家庭已經不再是男人能夠掌控跟支配的據點了。
支撐男子氣概的最主要的文化要件是心理層面獨立自主、向上流動以及在經濟組織內取得經濟上的成功。所以現在換女人擔當起渴望生兒育女的社會角色。在此過程中,她們所處的選擇生態及選擇架構都發生劇烈的變化。而今,生物時鐘尤其在形塑女性怎麼認知自己的身體從而提出相對應的婚配策略上,也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女人若是選擇要孩子,選擇以婚姻(或異性同居家庭)作為撫養孩子的框架,那麼就很容易被身體認知所侷限,這種身體認知是把身體視為在特定時間內起作用、並聽憑時間安排的生物單位。兩個因素造成這樣的身體認知。
大量證據顯示,由於女性進入勞動市場,接受高等教育,使得她們婚嫁和生育的時間雙雙推遲(而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只有結婚時間推遲,生育時間未見延後)。[13] 現代女性決定比二十世紀中葉的前輩更晚進入婚姻市場,只是絕大多數的異性戀女子仍選擇為人母;所以相較於一九六〇年代以前的女性,當代女子面臨更加緊迫的時間壓力。[14]
請容我模仿海德格(Heidegger)的語氣,我們可以說,現代中產女性只要踏進婚姻市場,就不再是從死亡的角度思考時間,而是從「生育能力」的角度思考時間。在愛情領域中,女人的侷限是由生育視野來界定的。舉個例子,英國《獨立報》兩性專欄作家凱瑟琳.陶珊(Catherine Townsend )寫道:
我剛剛跨過三十歲大關,我已經準備好將我狂野的閨房術,保留給某位(非常幸運的)男士;而且我很有信心,性愛探險使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伴侶,無論在臥室內還是臥室外。我從來不曾如此穩健、自信、開心。只是現在約會比較難,因為要考慮的事情更多了。我還沒決定要不要生孩子,但我必須面對現實,正視生物時鐘,我感覺浪費在錯誤對象身上的時間愈來愈少了,以防哪天我真的決定生孩子。[15]
女性當前的處境十分不利,而她們所面對的,是結構性不利:女性被養育孩子的責任給緊緊束縛著(泰半在異性伴侶框架內),認為生理條件限制了她們,迫使她們不得不在時間有限這一框架下來思考和安排擇偶事宜。
短暫的「性感」與持續的「懼老」
人對時間更加敏感的第二個原因是美容產業,及坊間隨處可見的女性生育「窄」門知識,這些資訊都將女性身體(很少針對男性身體)建構成一個由時間界定的小單元(因而面臨衰老的威脅)。
隨著「性感」的觀念日益普及,美麗的標準漸趨苛刻,現在人主觀上愈來愈重視青春,從而對老化提高警覺,女人對此尤其敏感。在十九世紀之前,「熟齡」女性(特指年近三十歲的女性),憑恃她們多年累積的雄厚財力,在婚姻市場上仍保有炙手可熱的地位;反觀現代社會,一個人性感與否,取決於青春和容貌,這也使得女性對年歲增長格外敏感,更強化其將女性特質放在「時間」此一文化類別下運作的傾向(分析前現代歐洲平均結婚年齡,發現男少女長的比例高達25%)。
女性當前的處境十分不利,而她們所面對的,是結構性不利:女性被養育孩子的責任給緊緊束縛著(泰半在異性伴侶框架內),認為生理條件限制了她們,迫使她們不得不在時間有限這一框架下來思考和安排擇偶事宜。尤其到了三、四十歲,女性更容易感覺時間有限,選擇愈來愈少,所以想趕緊找個男人安定下來。
套句海倫.菲爾丁(Helen Fielding)在《BJ單身日記》裡頭的三十多歲女主角布麗姬.瓊斯的話:「當女人悄悄從二十多歲滑向三十多歲……,權力平衡出現了微妙轉移。即令是最放浪形骸的輕佻女子,恐怕也將膽怯、畏懼,與生存焦慮的初次陣痛奮力拚搏:她害怕孤伶伶死去,生怕死後三週才被人發現,而遺體早已被德國牧羊犬啃去大半。」 [16]
近年來更有研究顯示,女性生育力隨著年歲增長而逐年下降,不過她們對性的興致卻不減反增,性幻想的頻率益發密集而頻繁,性交的意願也提升,性交的次數遠比其他年齡層的女性高出許多[17], 顯見性愛追求跟女人自認生育年限將屆有關。[18]
在這樣一個因為時間認知不同而造成感情供需不平衡的市場裡,男人又是怎樣看待自己?我們從網路論壇上這篇忠告可略知一二:
假使她年長你許多,身邊又有孩子,那麼,你大可放心,她的小孩估計已經長大成人,根本不會在乎你出現。但假使對方僅大你五歲,那麼,你可要仔細聽聽她腦袋裡的滴答時鐘聲,就像《洩密之心》(The Tell-Tale Heart)寫的那樣。畢竟年屆三十歲,如果她還在你身上投資任何時間的話,那麼,她的最後通牒已經像魚雷一樣,悄悄上膛。趕快想好應變措施吧。她發出結婚通牒以後,緊接著是生孩子的要求。整個情況就像天主教徒接到教宗諭令一般。如果你可以接受比你年長的女性,也確定她孩子都上大學了,那麼,祝你旅途愉快。否則的話,趁你現在還有機會脫身,儘早分手吧。[19]
這則呼籲奉勸全天下男性切莫落入婚姻、感情糾葛、養兒育女的陷阱裡,通篇邏輯基本上是建立在某個不證自明的假設上:女人比男人更渴望結婚,更期盼承諾,因為她們的時間框架比男人侷促、緊迫許多。[20]
生理時間,是現代社會特有的文化範疇(cultural category),它關乎個體怎麼認知時間、理解時間,從而影響他們做抉擇;因此,生理時間不僅是女性選擇架構的基礎,更是女性做選擇時所仰賴的認知機制和情感機制,然而,女人卻也被生理時間給牢牢牽絆住了,少了談判的籌碼,畢竟男性關注時間因素的程度遠較女性低,所以每當做選擇時,男性的時間認知顯然遠比女性來得寬廣。
男性傾向把婚姻市場當作性市場,渴望在裡頭逗留久一點,而女性卻把性市場當作婚姻市場,逗留時間比較短。
人口結構如何讓男人患上「承諾恐懼症」
還有一個原因令中產及上層中產階級女性感覺她們選擇變少了,那就是新興選擇生態的人口結構。從歷史上看來,在資本主義發軔的前兩百年,女性面臨了雙重隔離:
一是困在低薪工作上,二是陷在性行動者(sexual actors)和性別行動者(gendered actors)這兩個角色裡。[21] 在此情況下,婚姻成了女性爭取社會地位、確保自身經濟存活的關鍵據點。而通往婚姻的途徑便是依附在某個男人身上——也就是愛情——於是乎,性對女性的經濟存在、對她們的社會存在,起了關鍵作用,而女人也傾向把婚姻視為情感範疇,投入過多資源。總體而言,女性的婚配策略以同質婚(homogamy)或高攀婚(hypergamy)占大宗,也就是說,女性傾向挑選教育程度比她們高、或一樣高的男性(連帶社會地位也比她們高或相當)。[22]
然而一九八〇年代以降,男人教育水平提升的速度其實不若女人快,[23] 且男人賺錢的能力,跟女性比起來,平均而言是呈現下降的趨勢,所以,女性若想找個教育程度相當、錢又賺得比她們多或一樣多的男性,機會恐怕會比以前降低許多。[24] 這就意味,如今有愈來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及上層中產女性,正在競爭同一批富裕且受過良好教育的男性,因而造成後者短缺。[25]
表面上看起來,婚姻市場陰盛陽衰,女人恐將面臨僧多粥少的局面,[26] 但礙於年齡主義——即對年齡的歧視——所以男人在找對象時,依照往例,最好(或應該)挑選比他們年輕的女性,職是之故,男性伴侶的樣本總數整體而言,還是比女性多。但反常的是,從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男大女小的機率增加了,而女大男小的機率卻減少。[27] 這是因為當今男性的經濟存活比以前更直接仰賴市場機制,他們現在單憑一己之力便可達到經濟獨立,毋須再仰仗女方累積的資產和財富。是以,只要男性願意接受較年輕、不富裕、教育程度不高的伴侶,這就意味他們可以選擇的數量比以前多得多。
上述因素加總起來,造成男女選擇的樣本數出現巨大分歧,雙方差距愈來愈懸殊,致使現在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所能選擇的對象遠比以前少。[28]
這回過頭來又再度印證承諾恐懼症確實跟選擇生態有關;正因為選擇生態出現根本性的改變,男性才有條件在這場性角力中掌握主導權。
如今他們接觸到愈來愈多女性,與之發生性關係的機會也增加了,並積極藉由系列性關係(一段又一段的性關係)來肯定自己的社會地位;加之,由於婚配策略不同,致使男女雙方所能挑選的樣本數出現十分懸殊的差距,且在時間這一文化範疇上,男女所認知的侷限又不一樣。以上種種改變,皆使得男性可以選擇的樣本數遠遠超過女性,而男性所處的選擇環境,也較女性來得豐富多樣。倘若要我換個說法,我會說,男性傾向把婚姻市場當作性市場,渴望在裡頭逗留久一點,而女性卻把性市場當作婚姻市場,逗留時間比較短。
[1] J. Tosh, Manliness and Masculin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Essays on Gender, Family and Empire (London: Pearson Longman, 2005), p. 35.
[2] Ibid., p. 35.
[3] 這裡我想澄清一下,我說性提高男性地位,並不表示性已經成為某種社會區分手段(a process of social distinction),完全取代傳統男性區分機制。相反地,我認為文化矩陣(matrix)是由兩條平行的歷史進 程共同創造出來的:一條是象徵男性地位的傳統符號遭到弱化,另一條,「性即是地位」的概念更集中、更受重視。
[4] F. Fukuyama,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Glencoe, IL: Free Press, p. 121).
[5] M. Donaldson, “What is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22(5) (1993), 643-57 (p. 645).
[6] S. Hite, The Hite Report on Male Sexuality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1), p. 479.
[7] F. Attwood, Mainstreaming Sex: The Sexualiz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London: I.B. Tauris, 2009); A.C. Hall and M.J. Bishop, Pop-Porn: Pornography in American Culture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7); B. McNair, Striptease Culture: Sex, Media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Desi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8] E. Blackwood, “The Specter of the Patriarchal Man,” American Ethnologist, 32(1) (2005), 42-5 (p. 44).
[9] R. Collins, “A Confl ict Theory of Sexual Stratifi cation,” Social Problems, 19(1) (1971), 3-21 (p. 3).
[10] S. Brownmiller,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6); Chodorow, “Oedipal Asymmetries and Heterosexual Knot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11] A. Rossi, “Children and Work in the Lives of Women” (paper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February 1976) cited in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p. 631.
[12] Rosanna Hertz 的研究顯示,中產階級女性教育程度高,經濟獨立, 她們為了解決此問題,另謀策略,將婚姻(或別種兩性關係)跟生兒育女做切割,選擇「自己」當母親,顯然是女性不甘受選擇生態約 束而想出的可行因應方案。參閱:R. Hertz, Single by Chance, Mothers by Choice: How Women Are Choosing Parenthood Without Marriage and Creating the New American Fami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 Elwood and Jencks, “The Spread of Single-Paren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60.”
[14] 這論點顯然需要更細緻的釐清,西班牙和義大利的女性選擇不生,而美國女性傾向生兒育女。
[15]http://sleeping-around.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in=2008-01-01T00%3A00%3A00Z&updated-max=2009-01-01T00%3A00%3A00Z&max-results=50, last accessed October 11, 2011 (no longer online).
[16] H. Fielding, Bridget Jones’s Diary (London: Thorndike Press, 1998), p. 34.
[17] J. Easton, J. Confer, C. Goetz, and D. Buss, “Reproduction Expediting: Sexual Motivations, Fantasies, and the Ticking Biological Clock,”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9(5) (2010), 516-20.
[18] 生殖技術突飛猛進,確實將生育年齡與極限不斷往後推。不過總的來說,進展仍微乎其微。
[19] http://seductiontutor.blogspot.com/2006/09/4-women-to-avoid.html, last accessed October 11, 2011.
[20] 當然,這裡指的承諾是跟對方締結連理,養兒育女,而不只是跟對方談談戀愛,承諾當對方的愛侶。
[21] C.A. MacKinnon, 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 A Case of Sex Discrim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2] 然而,羅伯特.施恩(Robert Schoen)與羅賓.威尼克(Robin Weinick)(《婚姻與同居伴侶的選擇》)證實同居關係稍微傾向「女高男低」(或男性高攀〔male hypergamy〕),這也印證「同居關係,女性教育程度跟男性教育程度同等重要」的說法。
[23] K. Peter and L. Horn,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ticipation and Completion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How They Have Changed Over Time (NCES 2005-169)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 ce, 2005); A. Sum, N. Fogg, and P. Harrington, with I. Khatiwada, S. Palma, N. Pond, and P. Tobar, “The Growing Gender Gaps in College Enrollment and Degree Attainment in the US and Their Potenti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prepared for the Business Roundtabl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Labor Market Studies, 2003).
[24] 利維士(S.K. Lewis)和歐本海默(V.K. Oppenheimer)的研究顯示, 女性若處在較不重視教育的婚姻市場,比較有可能跟教育程度比她們低的男性結婚,年紀越大,這樣做的機率越大。
[25] 顧爾德(Eric D. Gould)和帕斯曼(M. Daniele Paserman)的研究顯示,城市有薪資不平等的問題,男人的薪水比女人高,造成女性結婚率下降,她們必須花更長的時間尋找第一任或第二任的丈夫。參見:
E.D. Gould and M.D. Paserman, “Waiting for Mr Right: Rising Inequality and Declining Marriage Rat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3 (2003), 257-81.
[26] 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自1980 年代以來,妻子教育程度比丈夫高的對數出現增長,一改傳統女性教育程度普遍比丈夫低。參見:Z. Qian, “Changes in Assortative Mating: The Impact of Age and Education, 1970- 1990,” Demography, 35(3) (1998), 279-92 。誠如錢其琛所言,女性配對策略會有年齡上的差異:早婚女性傾向遵照傳統「男高女低」模式, 晚婚女性(年過30 歲才結婚)則往往挑選教育程度相當的男性(頁291)。
[27] 錢其琛還指出,1990 年代男大女小的配對,結婚的機率比同居高,若是女大男小,則兩人同居的機率是結婚的兩倍(同上,頁283)。
[28] Lewis and Oppenheimer,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cross Marriage Markets,” p. 36.
延伸閱讀:
| 閱讀更多 |

社會學家,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教授。著作有《冷親密》(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消費浪漫的烏托邦》(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痛苦的魅力》(Oprah Winfrey and the Glamour of Misery)等,其中《痛苦的魅力》獲美國社會學聯盟圖書獎。2018年,易洛斯獲得了EMET獎,是以色列最高的科學榮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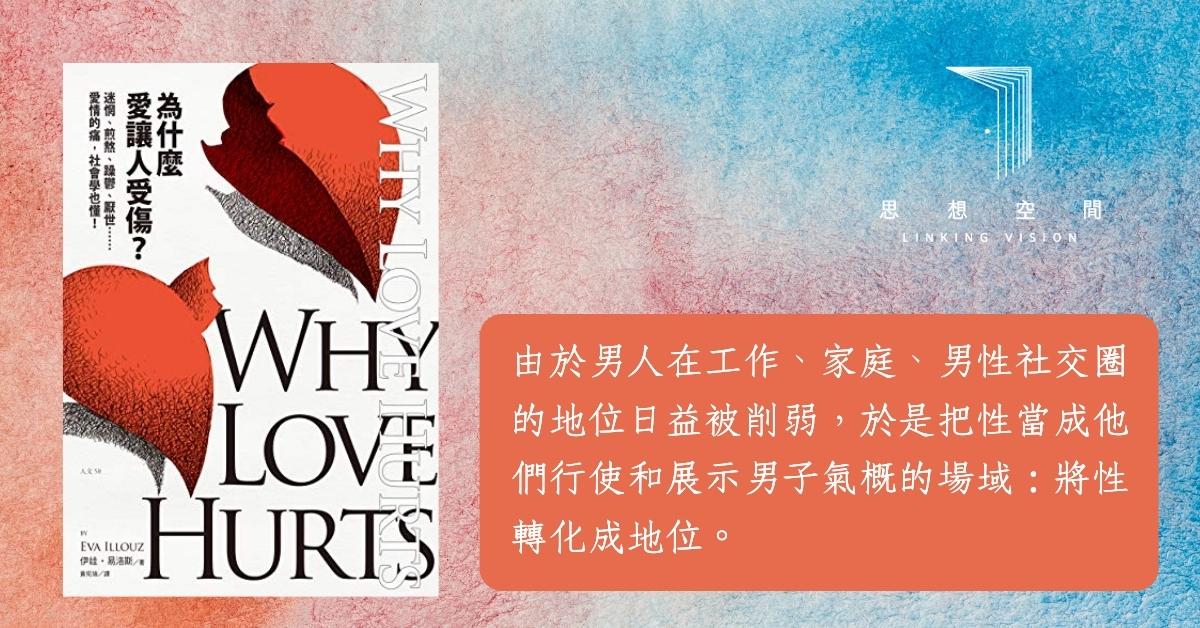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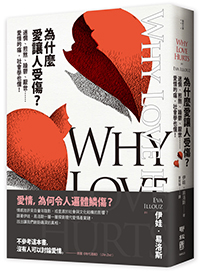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