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隨著COVID-19疫苗的普及,新一輪反疫苗運動也在世界各地成形。2021年12月7日,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世界史研究室主辦了一場演講,主題為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Anti-Vaccination: Re-Considering the Lübeck Disaster(全球史視角下的反疫苗運動:對呂北克災難的再思考),邀請到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孟軒,就其在書寫計畫 Medicine and Mistrust in Modern Germany:A Global History,1880-1960(暫名)中有關反疫苗運動的歷史追溯與複雜關係梳理進行發表。同所副研究員張谷銘、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副教授吳易叡,亦分別以主持及對談嘉賓身份出席是此活動。
吳孟軒(Albert Wu)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興趣在世界史、宗教史、醫療史。他的研究從歐洲傳教史出發,近年來擴展到醫學的跨國史。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學士,2013年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學位。曾在巴黎美國大學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Paris) 任教,在柏林自由大學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擔任博士後研究學者。
本次講題原想透過回顧德國另類醫學(Alternative Medicine)的發展,進行一個全球醫療史研究,過程恰逢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目睹德國乃至全球各地興起各種反疫苗示威,包括在世人眼中高度工業化、崇尚理性與科學、擁有豐富醫療資源的西方國家。吳孟軒試圖以全球史的角度,從1930年的Lübeck disaster(呂北克災難)出發去理解這些世人眼中反理性、反科學的反疫苗運動。
歷史回顧
The Lübeck disaster(呂北克災難)是1930年發生在德國呂北克(Hansestadt Lübeck)的一次疫苗施打後造成新生嬰兒死亡的歷史悲劇。
在事發前兩年,巴黎的巴仕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在國際聯盟(Leage of Nations)的組織下進行了一次對於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érin,簡稱BCG)安全性與效益的評估。根據會議的結果,國聯決議將在歐洲進行大規模人體實驗以評估疫苗的長遠效果;同時,指派當時巴仕德研究所副主任、疫苗學家,也是卡介苗的研發者之一的阿爾貝·卡爾梅特(Albert Calmette)與同事卡米爾·介蘭(Camille Guérin)致力推廣卡介苗用於新生嬰兒以對抗上世紀對公共衛生最嚴重的威脅——結核病(Tuberculosis)。
儘管當時卡介苗在歐洲各國飽受質疑,包括德國內部各種反對聲浪(比如納粹支持者認為疫苗是「法國毒藥」),德國北部的呂北克公衛部門為展示其醫療現代化的雄心,還是決定引入疫苗並對新生兒施打,但一週後,接受疫苗施打的嬰兒開始出現嚴重副作用以及結核病的病徵,最終導致三分之一接種疫苗的新生兒死亡。
反疫苗運動的歷史脈絡
此事引發大規模的抗議,以及興起各式各樣的反疫苗團體,包括各種另類醫學(Alternative Medicine)的支持者、社會民主黨(主張改善工作環境以對抗結核病)以及納粹。
一年後,德國當局件的調查報告表示:疫苗的技術本身沒有問題,此事乃肇因於人為操作的失誤導致嬰兒施打的疫苗受到未稀釋的病毒污染,並起訴此事件中呂北克當地公衛部門的相關人員;卡爾梅特本人雖然並未受到法律追訴,但他所代表的的疫苗安全性也受到公眾的質疑。
但最終,卡介苗的安全性還是受到科學證據的支持,並在整個20世紀運用在全世界,最終我們得到的,是一個關於疫苗如何拯救世界的故事。
另類醫學其實不斷地試圖驗證其自身的「科學性」,比如設立研究機構,並且形成政治組織以對抗各種國家法律的規範,隨著反疫苗運動的國際化轉向,另類醫學的版圖也得以向外擴張。
不同歷史行動者的論述策略
過往史學家對於由呂北克災難引發之反疫苗運動的看法在於:這些反疫苗團體受德國奇特、怪誕的自然醫學(Naturheilkunde)啟發,其思想根植於19世紀的浪漫主義傳統,是威瑪共和時期展現的一種反理性、反科學的精神展現;呂北克事件純粹是人為操作失誤的後果,只是疫苗技術史上的一次實驗意外。
20世紀初的德國仍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界之處,當時在公共衛生的問題上,存在兩大觀點:一是技術解決(techno-political),二是社會改革(social tranformation);前者以疫苗作為解決方法,由國際聯盟以及學院醫學(Academic Medicine)為擁護者;後者由反疫苗團體,以及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主張一種社會性的解方(Social Medicine)。
其中以社民黨人Julius Moses為代表,他認為應該要注意到疾病背後的社會起因,以結核病為例,真正應該改變的,是工人階級的工作環境、更合理的報酬、溫暖的衣物、陽光以及乾淨的水。同時Moses也對學院醫學提出批判,認為國聯,以及國聯代表的技術官僚主義壟斷了醫學論述的知識權威,將傳統的、地方脈絡下產生的醫學知識斥為「Quackery」(庸醫)。Moses與這些各式各樣的另類醫學(Alternative Medicine)支持者結盟,甚至發展國際組織;這與學院醫學陣營之策略一致,都強調以國際主義為精神(Internationalism),跨國連帶(solidarity)為目標,對自身主張進行合理化論述。
為了取代疫苗技術,這些另類的醫學支持者也發展自己的結核病療法,比如各種草藥製的藥丸,直至今日,德國許多地方還存在這樣的草藥傳統。史學對這些另類療法的評論通常是將之視為未現代的產物,但這些另類醫學其實不斷地試圖驗證其自身的「科學性」,比如設立研究機構,並且形成政治組織以對抗各種國家法律的規範,隨著反疫苗運動的國際化轉向,另類醫學的版圖也得以向外擴張。
反疫苗運動在跨國連結的過程,認識到國際組織與網絡的政治效益,不斷地以結盟及擴張的方式將此運動「國際化」,它如同一把「傘」,將各式各樣政治光譜的團體收合,集中在同一訴求之中。
結論及回應:為何檢視反疫苗運動?
本研究的重點不在於去幫「歷史失敗者」平反或正名,疫苗確實救命無數,但檢視反疫苗運動的歷史,也有助於我們了解個人身體、國家以及醫療實踐者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們可以看到,國家行動者對疫苗安全性的脆弱治理,以及人對入侵物(疫苗)的抗拒、人如何在身體與信念的層面拒絕被馴服。
另一個層面,1920至1930年間反疫苗運動映照出的,是當時德國民眾對國際聯盟的幻滅:國聯被視為是細菌學家以及巴仕德追隨者們(Pastorians)的利益代言,這些人相信可以「技術」解決一切問題;反之,人們渴望傳統的醫學方法能被融入國家的公共衛生計劃中,並反對這種國聯代表的跨國技術官僚主義。
反疫苗運動在跨國連結的過程,認識到國際組織與網絡的政治效益,不斷地以結盟及擴張的方式將此運動「國際化」,它如同一把「傘」,將各式各樣政治光譜的團體收合,集中在同一訴求之中。
最後,1930年代的國際主義,特別是關於國際聯盟的描述中,在過去史學研究傾向將國際主義與心胸寬廣的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劃上等號;而反對國際聯盟的聲浪,則是來自於保守的國家主義者。但在反疫苗運動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中的歷史行動者們非常熟練的吸收國際主義的話語及主張,包括不同意識型態的團體,都以這種策略去賦予自身合法性。這是我們今日可以重新理解1930至40年代國際組織互動的一種新視角。
而若從社會史的角度去理解,不管是支持疫苗或是反對疫苗的行動,似乎都可以置於一種現代視角下的人體觀(什麼是健康的人體?)去理解,以及人與社會對微生物這種「不可視之物」的反應,這也呼應演講中提到對於人體、微生物與國家之間的關聯。
| 新書快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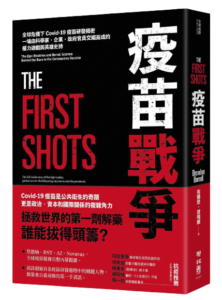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