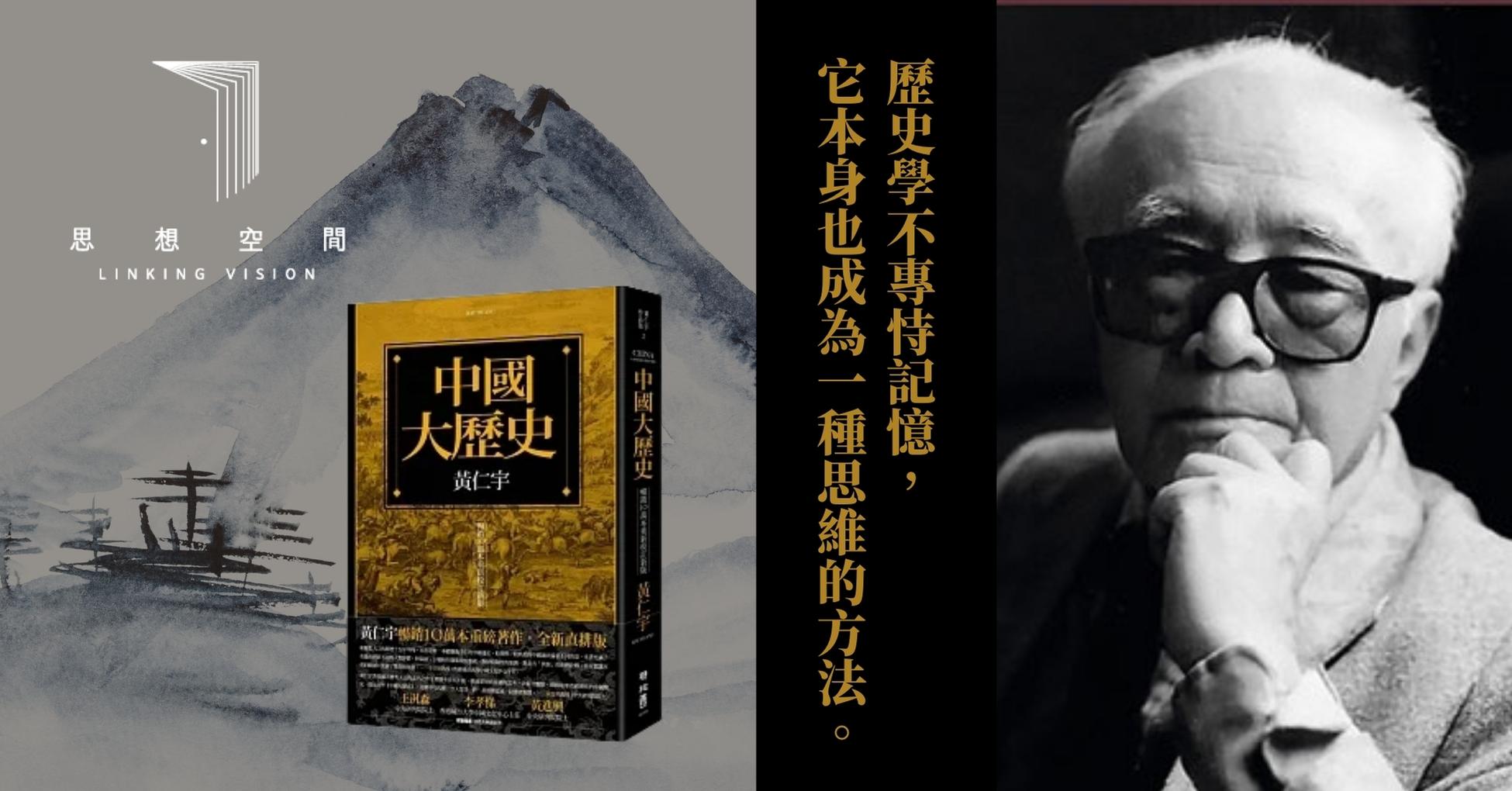
黃仁宇:我的「中國大歷史」研究,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捩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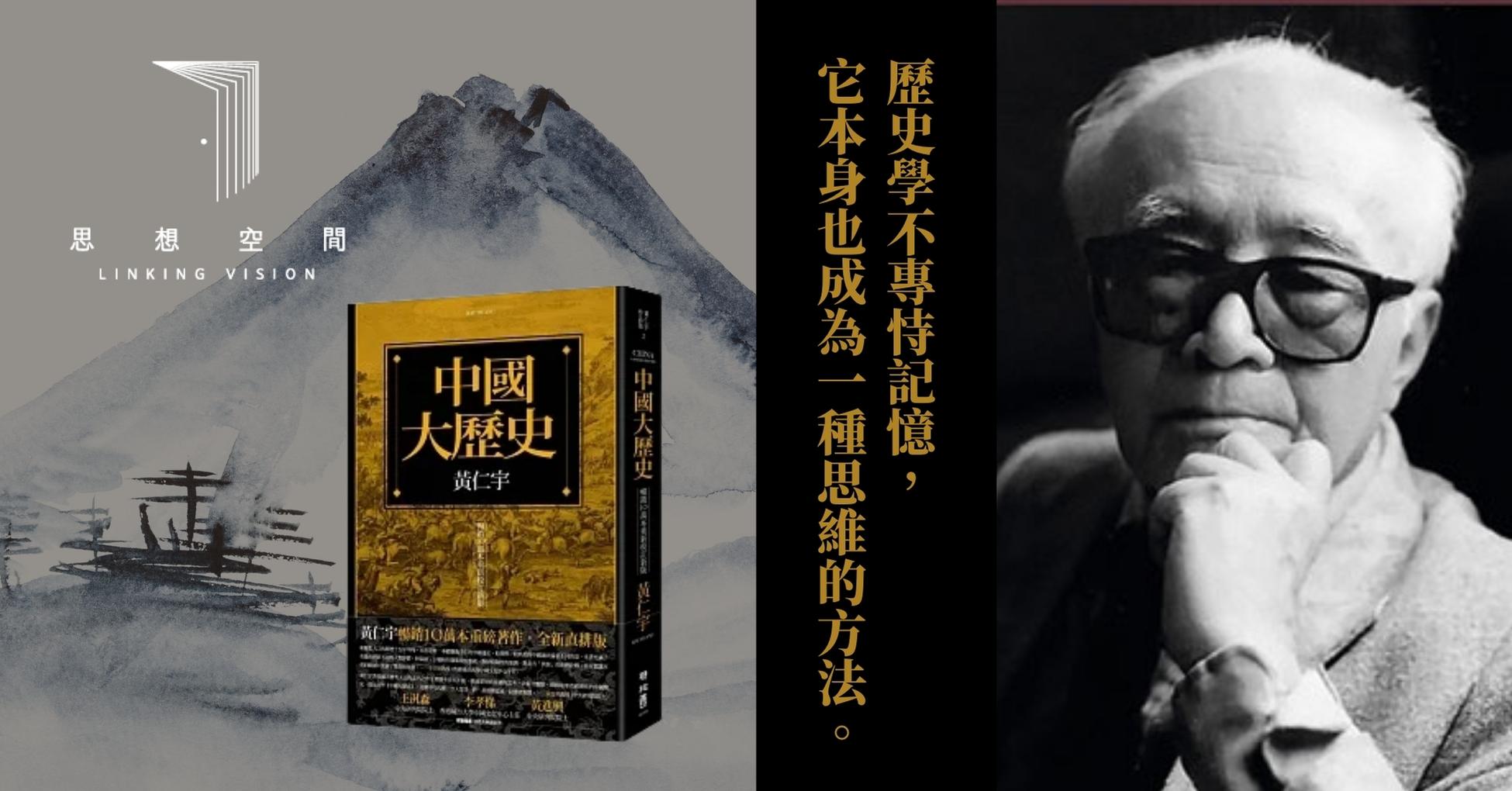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捩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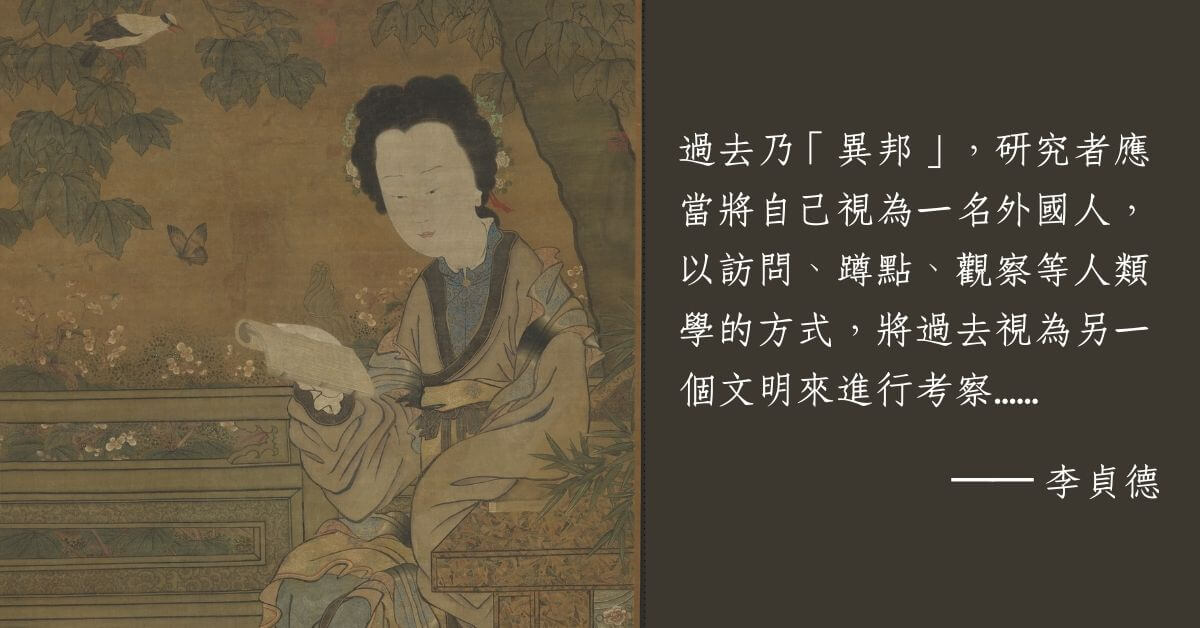
由性別與當歸的歷史,我們可以窺見,基於女性與血的關係確立,造成後人對於藥物看法的改變。李教授由此衍伸指出,人的「觀念改變」會影響我們對於中立科學的看法,「觀念」會影響人對待物的方式,而本草的物質文化史正是在探討藥物、知識和人之間的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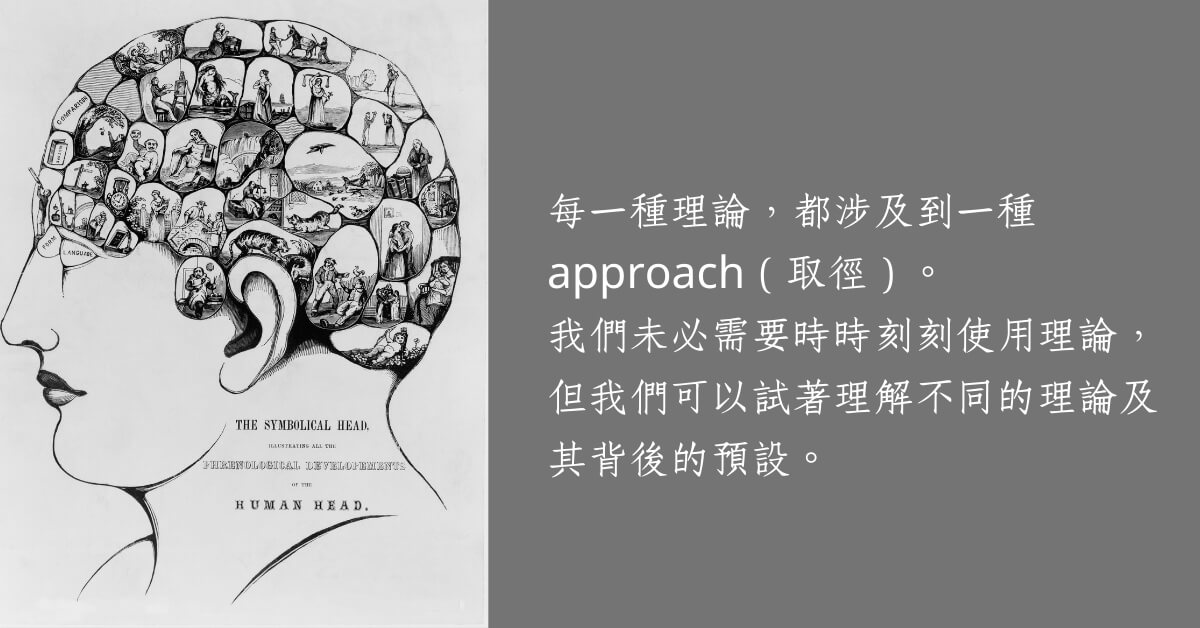
陳教授認為,每一種理論,都涉及到一種approach(取徑)。我們未必需要時時刻刻使用理論,但我們可以試著理解不同的理論及其背後的預設,這就涉及到一種個別研究的取徑。性別史有性別史的理論(取徑),政治軍事史有政治軍事史的理論(取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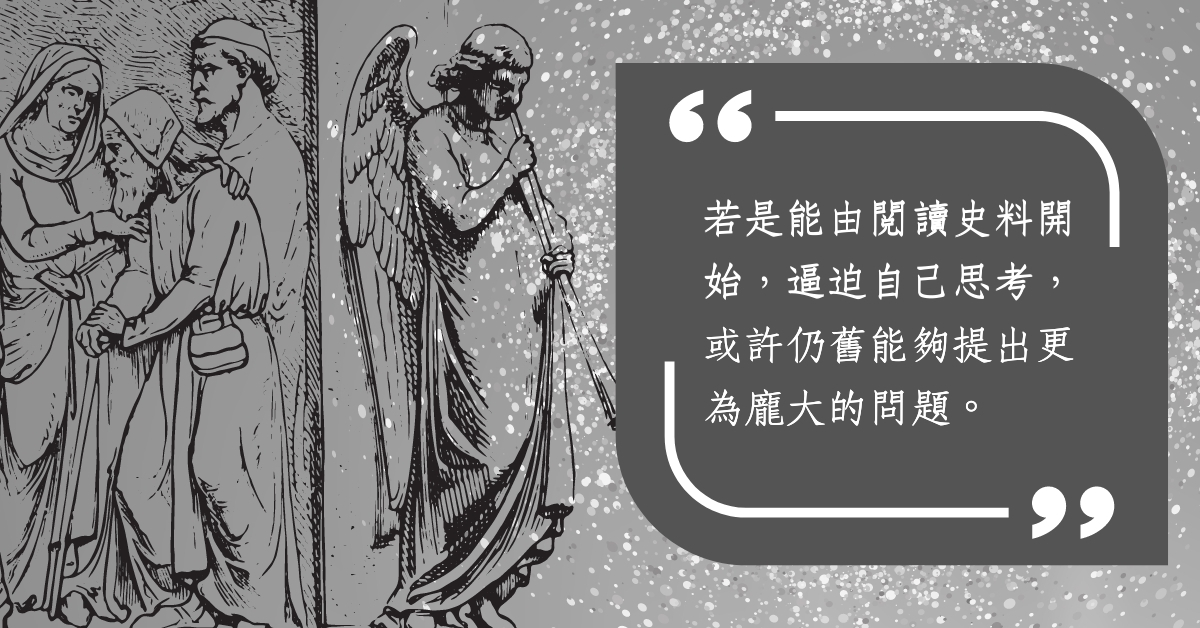
王教授指出,1950年代臺灣的史學界尚缺乏思想史研究,主流的研究大抵聚焦於制度史的討論,以及考據和義理等議題。直至1962年,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正式出版,替史學界帶來改變的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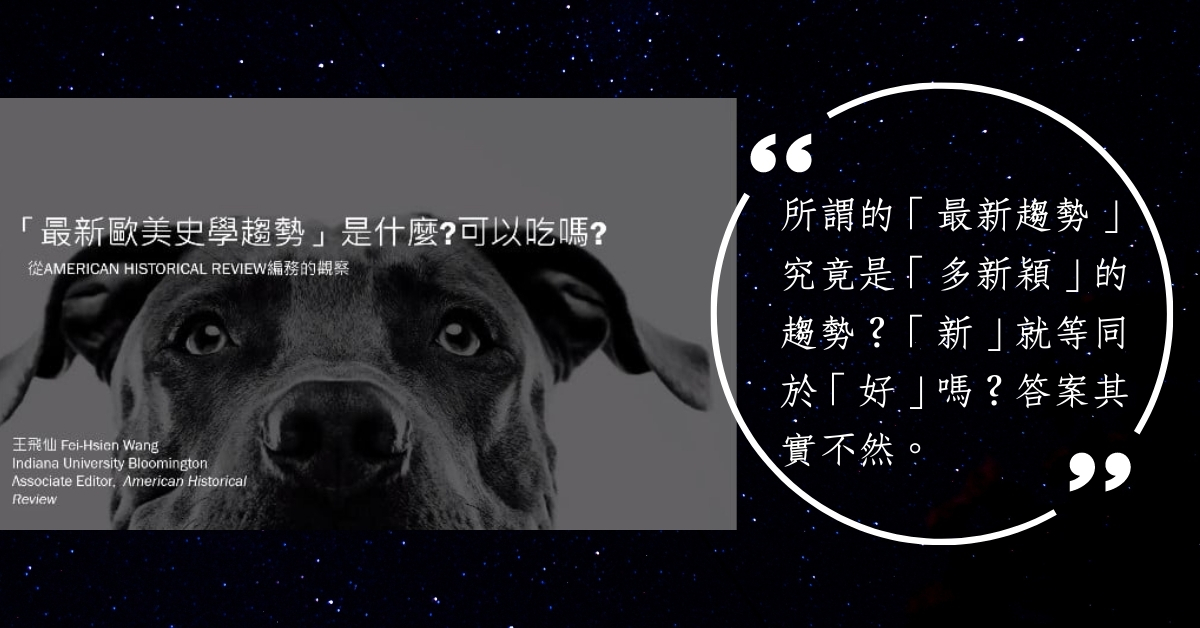
,研究者選擇的討論議題,大多和現實社會正在發生的問題有關,如難民和離散、移民與多元文化、global south等。現今的研究題目越來越趨近現代,專史的分野漸漸弱化,研究取徑也更以「問題導向」而非「專史導向」為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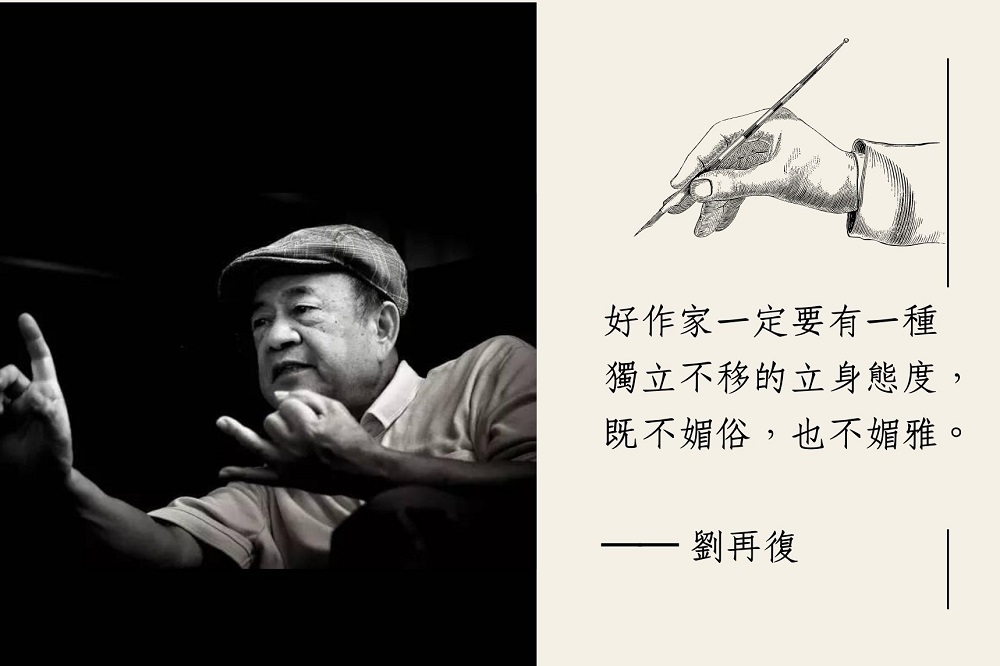
不媚,才有文學的尊嚴與自由;不媚,才有作家的主權與獨立;不媚,才有作品的格調與境界。我早已提出,好作家一定要有一種獨立不移的立身態度,既不媚俗,也不媚雅。順從大眾的胃口固然不對,順從小眾的胃口也不對;刻意取悅「下里巴人」不對,刻意取悅「陽春白雪」也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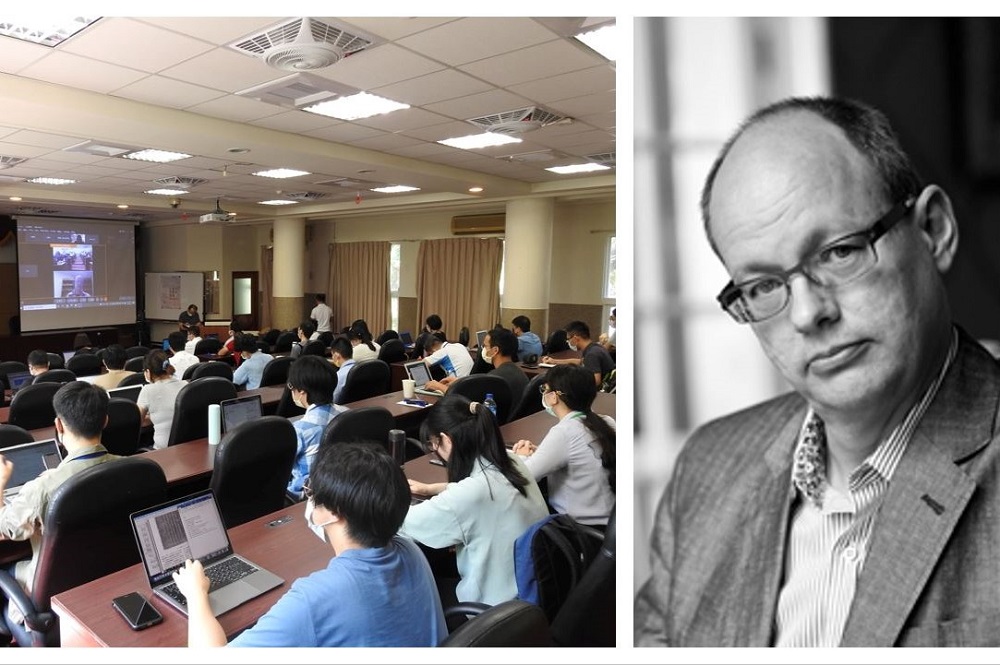
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馮客以「什麼是好的寫作?」拉起整場演講的序幕。他指出,一名良好的學術研究者,首先必須對於寫作具有「熱情」(passion),這份熱情會促使你以紀律(discipline)「持續地」寫作,進而思索精進自身的寫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