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仁宇(歷史學家)
編按:2000年1月8日,歷史學家黃仁宇與世長辭,至今已過22年。然而黃仁宇留給我們的研究方法與視野開拓,仍在史學研究範疇流動並幻化生機。如今,我們回看先生從1984年開始撰寫《中國大歷史》之序言,了解學者是如何對中國的歷史與文明進行系統的分析與解釋,而這一研究動機及熱忱又緣何而來。(本文摘錄自《中國大歷史》自序,原文題為〈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標題為編者擬。)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週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為始作俑者。宏觀與微視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歷史,顯係模仿而非發明。
至於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裡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在國軍服務十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於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蹟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複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需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 Fei Tzu同受業者有Li Ssu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焚書,後又為宦官Chao Kao所構殺?Empress Wu的一生事蹟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千年的歷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合的重要。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
在一九六〇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捩點了。
一九七〇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裡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二十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志三十九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時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里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係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千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二百七十六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產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歷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裡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於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並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
一九七二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裡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踐而去,使我緊隨在後也只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八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啟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採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馬克思和韋伯的忠實信徒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於一九七〇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閒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一九七〇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七萬六千餘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五十頁,也要四、五年,並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係。《資治通鑑》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鑑》英譯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捲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歷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係。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並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亙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復興前之標準,尚未進入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鑑》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己了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一九六〇年間我曾在教書之餘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一百三十三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十二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六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註,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誇的「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捨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歷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髮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誌。
一九八〇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干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亙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覆,我在稿中只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歷史上之演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歷、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見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閒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於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台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書評者報刊裡寫出:不論我寫的歷史是否涉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森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麼能使中國改觀,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這邊那裡稍微扭轉一子罷了!」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歷史從業員的工作只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於籌畫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中國大歷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一九八一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我稱他們為XYZ領導集團,取各人名字中之首一字母)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於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誌裡出現。這種趨勢和徵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歷史和西洋文化匯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系,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於英國研究十七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 George N. 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家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隱喻:等於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而能使銀行開設於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十七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只因為日子久了,我們以為英國歷來如此,想像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本書有十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這境界的程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於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回頭,一九八〇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社不復成為生產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轉,才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將事了。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十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可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著哥倫布航行四次,親歷牙買加、宏都拉斯諸地,回到西班牙,說及確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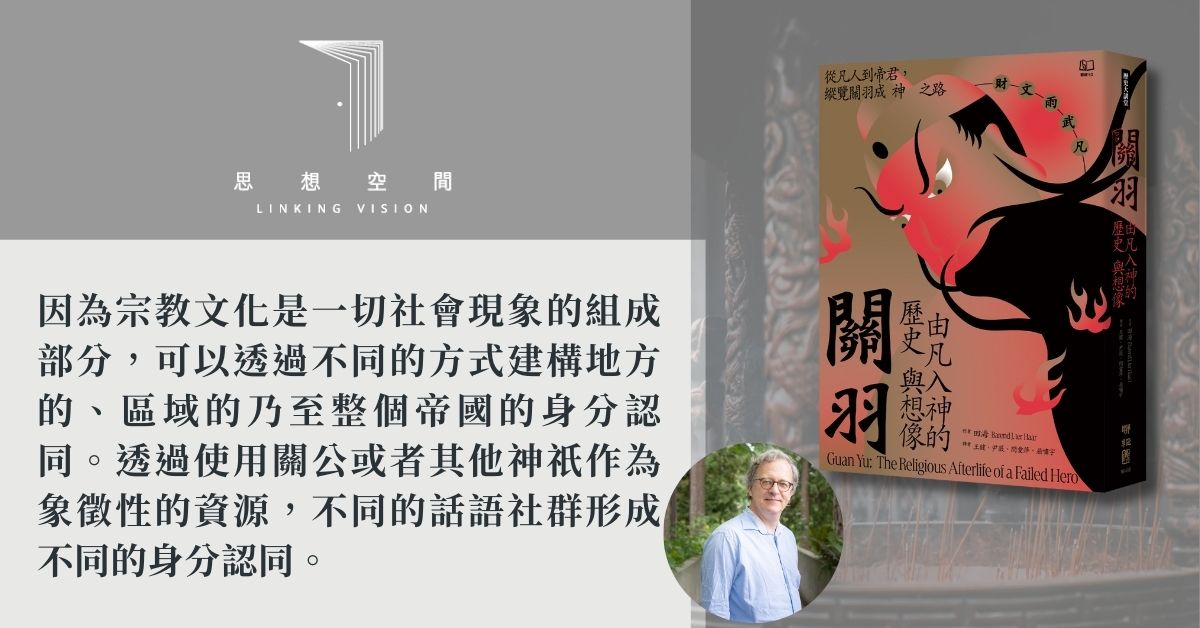
來自地方社會的體驗——《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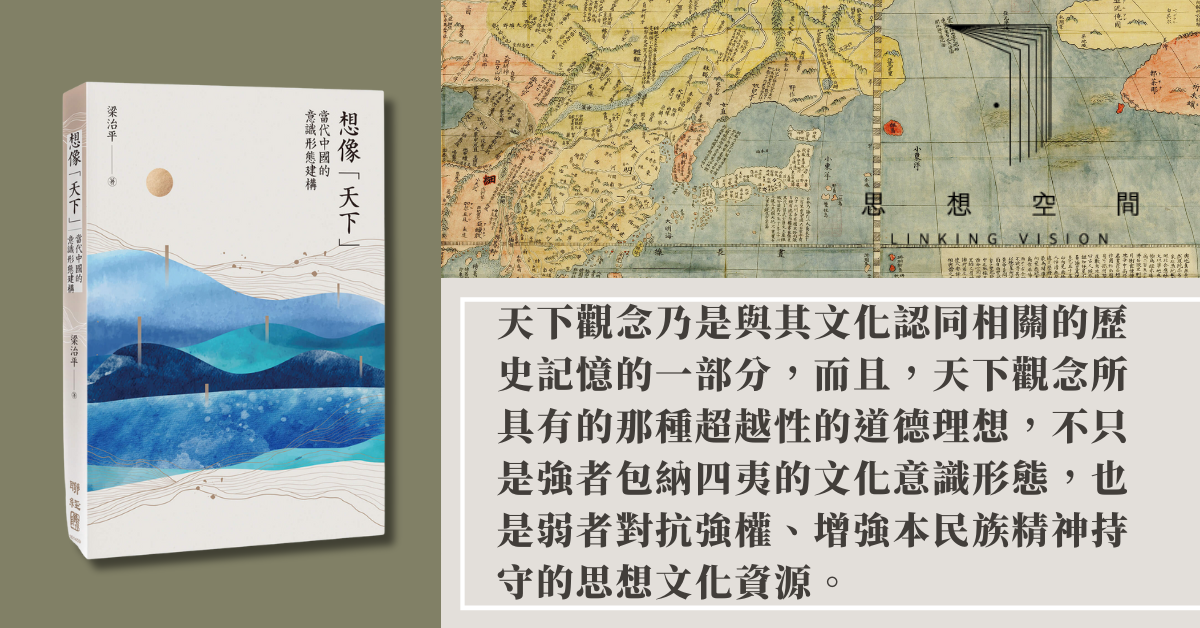
梁治平:天下因文明而立,其範圍伸縮無定,漫無際涯

蒲慕州:漢武帝個人的精神狀態和信仰造成了宮廷派系鬥爭和社會動盪,終至引爆了慘烈的巫蠱之禍
| 新書速遞 |

191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2001年1月8日逝世於美國紐約。天津南開大學肄業(1936-1938),成都中央陸軍官校畢業,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陸軍少尉排長、中尉參謀、駐印新一軍司令部上尉參謀、少校參謀、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New Paltz)分校教授。主要著作有《緬北之戰》、《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萬曆十五年》、《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近代中國的出路》、《關係千萬重》、《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大歷史不會萎縮》、《明代的漕運:1368-1644》、《黃仁宇的大歷史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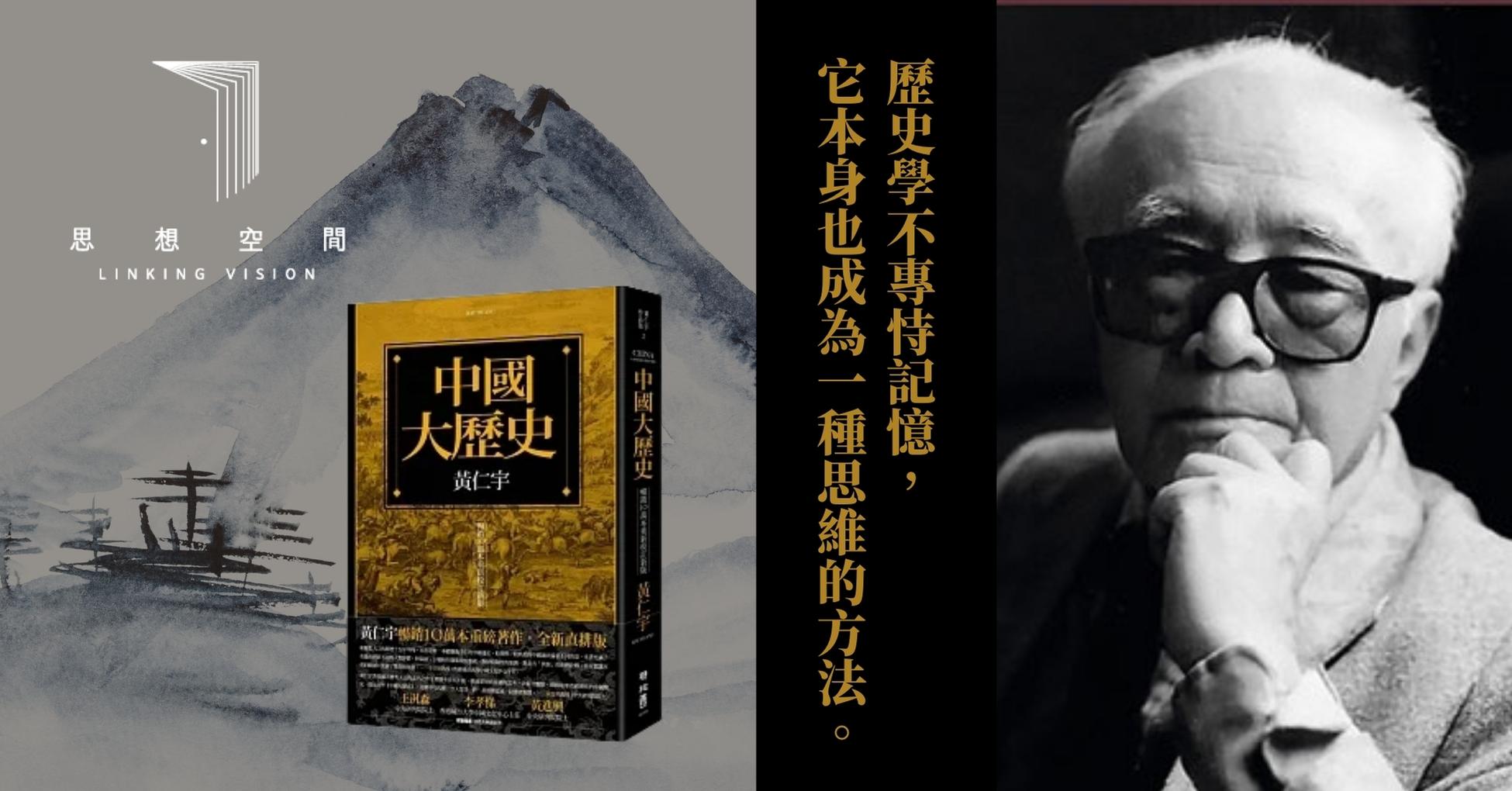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