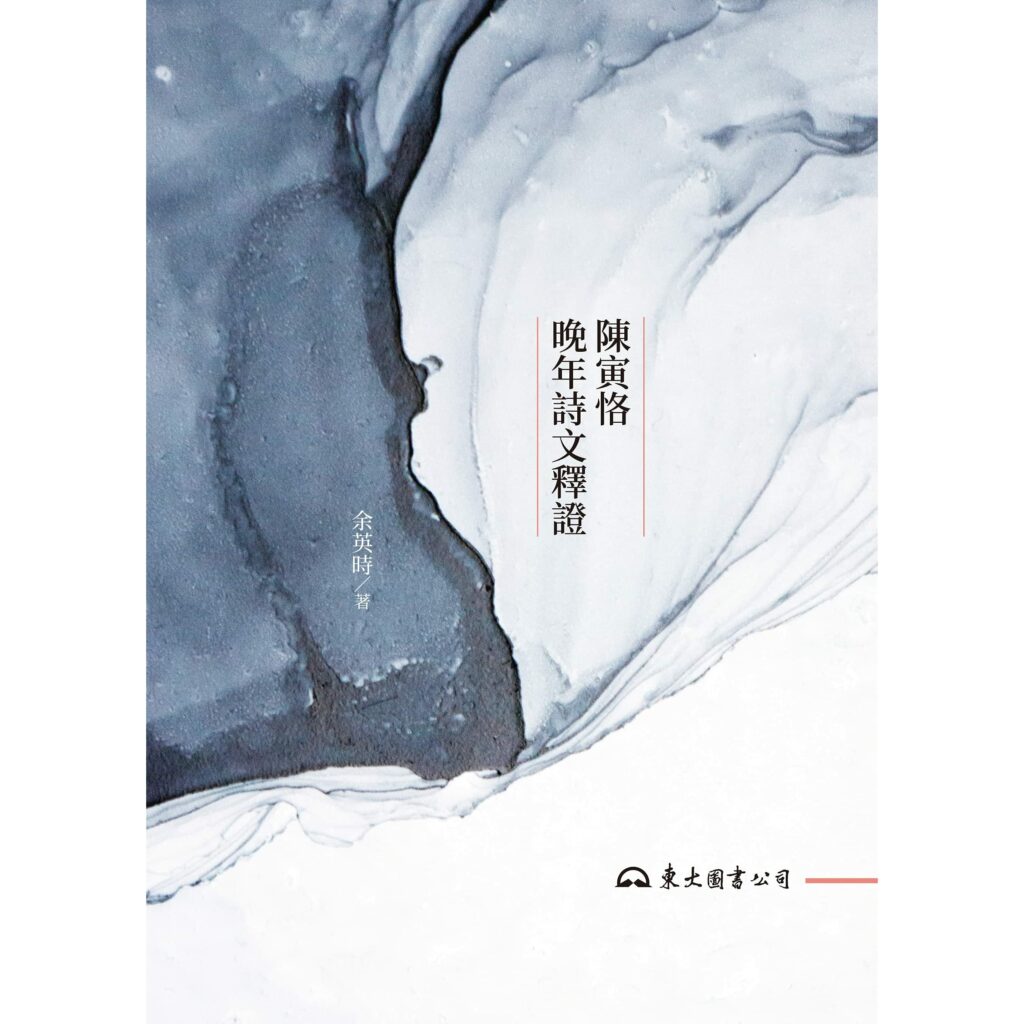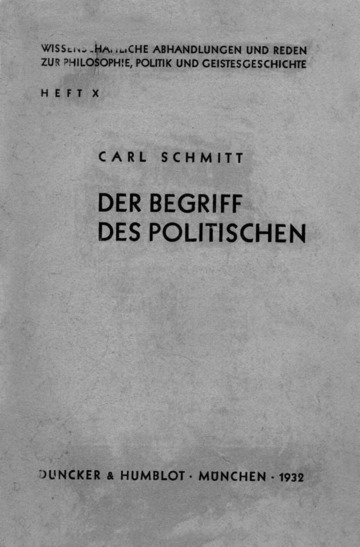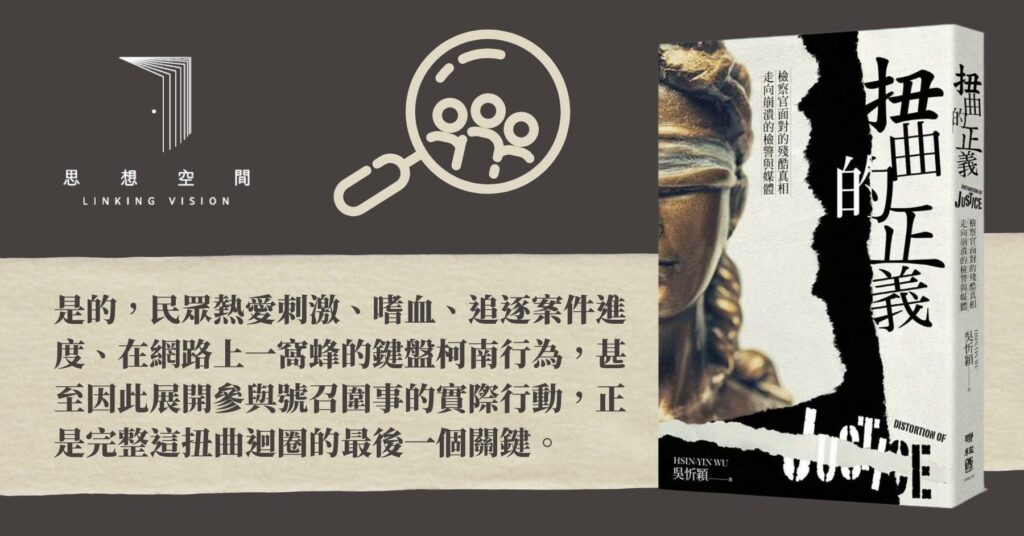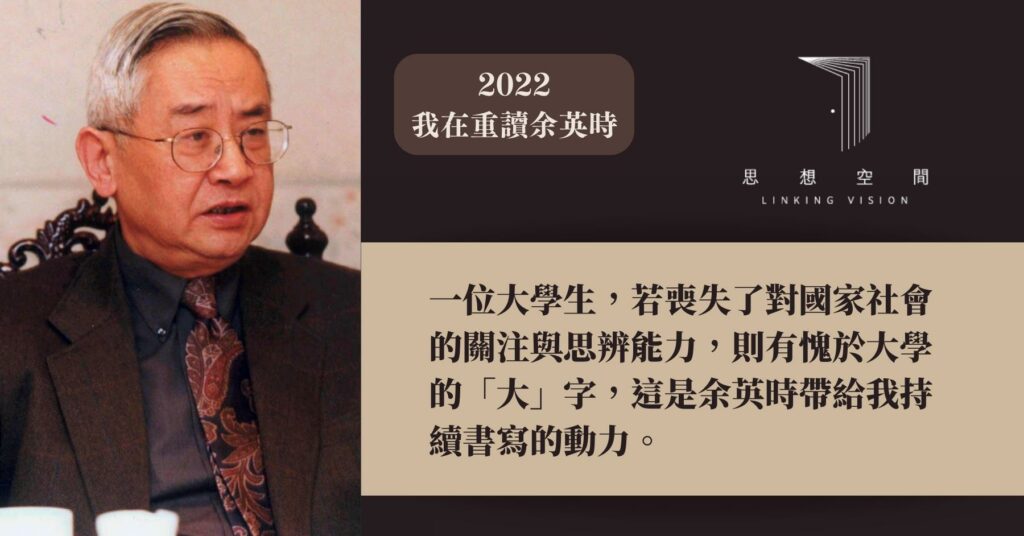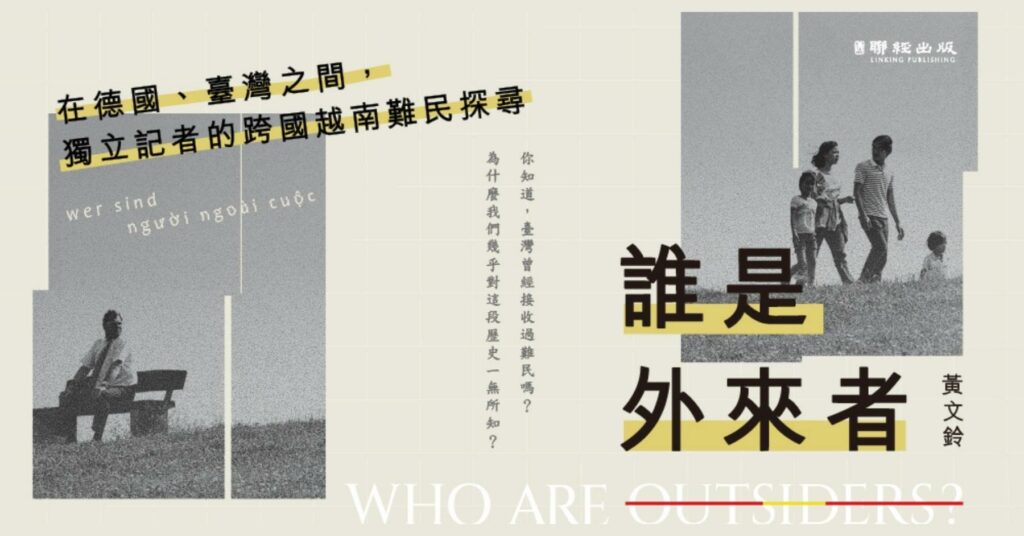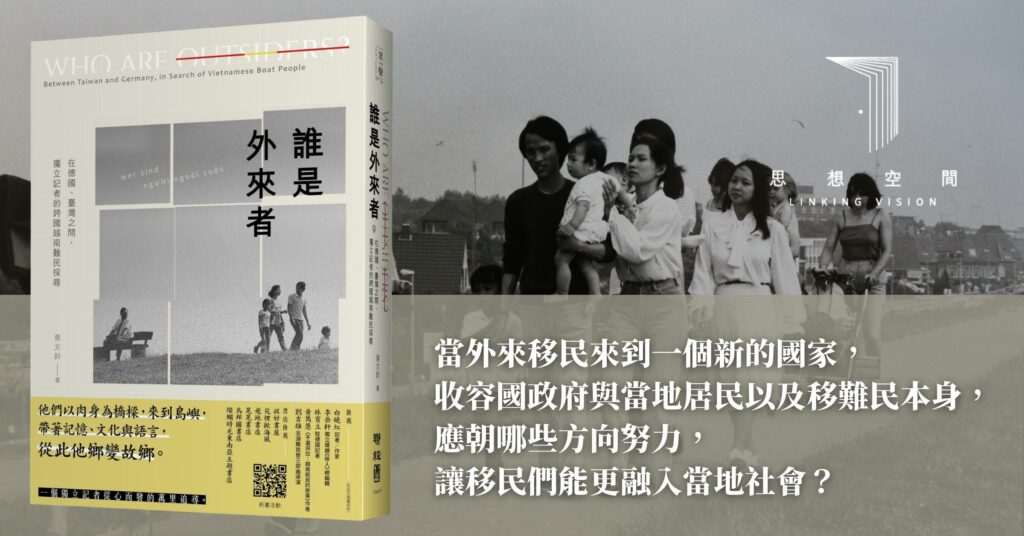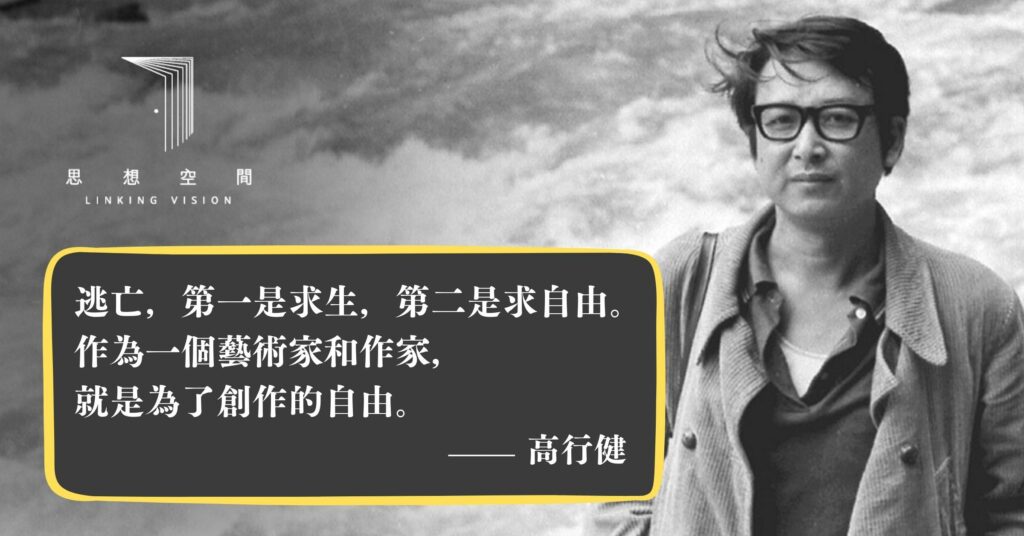文/蕭雲(記錄者)
編按:胡適和錢穆求學上取徑相異、想法多有牴牾,兩人的思想如何能在余英時身上融會貫通?而自道「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的余英時,其眼中的「中國」與另一個「大國崛起」的中國,又有哪些不同之處?余英時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但他的學問著述、思想與為人,至今仍在影響著後代知識人、讀書人。2022年7月,聯經思想空間策劃徵稿活動,邀請讀者以「2022,我在重讀余英時」為主題,寫寫對於自己而言影響最深的余英時著作是哪一本、余先生的學術與思考又為個人帶來怎樣的啟發。記錄者蕭雲從余英時關於文化中國、以及對抗專制的思想主張談起,為我們揭開余先生帶來的隱諱教誨。
一、兩個余英時
「這一天適值羅斯福總統逝世,他在日記中寫了一首悼詩,起句云:『章憲煌煌告五洲,大西洋月印如鉤』,正是頌讚羅氏的『大西洋憲章』。」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
昔年筆者讀到此處,一直婉惜不已,因為余英時先生僅引用首兩句,沒有記下全詩。從此引以為憾,心癢難熬,甚至認真想過厚顏拜託學者去哈佛燕京圖書館調閱楊聯陞日記,但止於心裡盤算,始終不敢造次。很久以後才發現原來楊的後人早已成全,編成《哈佛遺墨》收錄此詩。
每讀余英時談胡適,必感受到他對胡適終生服膺。他曾援引胡適迥別時流的堅持:「我是學歷史的人……最近三十年來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團專制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同時他一生致力為胡適辯誣,澄清他的博士學位貨真價實,從未欺世盜名。我們在這裡看到「很胡適的余英時」。
但再讀〈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又會看到余英時的另一面。據悉〈意義〉影響極大,是他最早能在大陸刊行的文章,文中一再闡揚若干中國傳統可與「普世原則」相通,甚至比西方更早解決一些陋弊。比如西方在「上帝已死」後須要世俗化「天賦人權」,但中國早已接受「盡心知天」的人是道德價值的來源 [1]。而且每當他念及恩師錢穆,都會重申中國素仰「通儒」的傳統,思想自有其「內在理路」,不能機械地按西學的專業分科來牽強比附,換句話說就是「不能照搬西方一套」。我們在這裡看到「很錢穆的余英時」。
胡適和錢穆不僅求學上取徑大異,於私也有點不咬弦,錢穆遲至1968年才獲選中研院院士,便是聚訟不休的一大學案。兩人的想法多有牴牾,究竟截然不同的兩人如何在余英時身上融會貫通?
惟兩人(陳寅恪、余英時)在大節上都一以貫之,沒有因為民族認同而屈膝於專制政權。究竟兩個「中國人」依靠什麼抵抗專制統治?
二、連接錢穆與胡適的橋
余英時解釋他從來無緣拜謁胡適和陳寅恪,有幸識荊的是哈佛的老師楊聯陞。陳寅恪是楊聯陞在清華的老師,可以形容余英時是陳寅恪的再傳弟子。
一生斂抑的陳寅恪一定不喜歡自己被追捧為「國學大師」,其愛國情操更在中國大陸被用於官方宣傳。然而陳寅恪還有藏於井底的「心史」,他曾私下告訴吳宓:
「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極,只成下等之工匠……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此後若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浚闢,則中國人經商營業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莊思想高尚,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
陳寅恪一生婉委其辭,隱約其說,下筆千迴百轉,從不輕易表態站邊。但余英時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證明他為保學術自由,居然在中研院的院長選舉發言為胡適拉票。
後來「地變天荒」,國共易幟,楊聯陞輾轉得悉在清華園為王國維所修的紀念碑被毀,晚年受盡迫害的老師依然屢問此碑下落,「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陳寅恪一直強調「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余英時也一直重申自己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他甚至曾自嘲「我所保存的中國文化成分也許過多了,但這不是我自己所能做主的,價值的選取往往不是理智可以單獨決定的。」惟兩人在大節上都一以貫之,沒有因為民族認同而屈膝於專制政權。究竟兩個「中國人」依靠什麼抵抗專制統治?
陳寅恪和余英時都遵奉「獨立自由之意志」,甚至為之殉節而不渝,恰恰由於兩人不肯「尊西人若帝天」,而是因為他們一生都「淪肌浹髓」浸潤在儒家傳統裡面。
三、儒家的普世正義論
當陳寅恪在1925年由柏林大學歸國執教清華,另一邊廂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則在波恩大學開始構思《政治的概念》[2]。
《概念》裡有一處經典的轉折,施密特先說國家是由民族構成的「政治統一體」,批評國內的「多元主義」削弱國家作政治上的「敵友決斷」。但當話題轉向國際,他卻肯定世界的「多元主義」,因為各民族「一直依照敵友而在從事著群體劃分」,正是「敵友決斷」保障世界不致淪為一元統治。
爾後無數極權支持者都乞靈於這名投靠納粹的法學家,對此「邏輯」安之若素,居之不疑。對內他們擁護專制政權,但凡他們聲言為同一民族,就得服從其一元統治;對外他們反對「西方霸權」,但凡有人批評他們專制,就說不同民族各有「特色」,因為世界「多元」。
這套「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思想根本不符中國傳統,因為儒家從來是一套普世正義論。施密特認為各民族的「敵友決斷」是「命運中注定的劃分」,徹底依賴現實主義,毫無道德可言。反觀儒家卻更易與自由主義相契,因為兩者都奠基於「價值決斷」。
早於《論語》的〈子罕〉篇,孔子就反問別人質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的世界裡沒有絕對的「禹內」、「禹外」之分,關鍵在於有沒有「君子」。
多年後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抓了一名官員,此人不但世代簪纓,而且家學淵源。藤原惺窩偶爾結識被軟禁的姜沆,向他問學討教。兩人都信奉儒家典籍,但不會自居「夷狄」,生於他國的儒者擺脫了「天朝中心主義」,藤原惺窩在更廣的視野下拓闊儒家的普世正義論:
「異域之於我國,風俗言語雖異,其天賦之理,未嘗不同。」
「理之在也,如天之無不幬,似地之無不載,此邦亦然、朝鮮亦然、安南亦然、中國亦然。」
去到晚清西學東漸,余英時再不同時趨地點出「最先接受這些觀念和價值的正是晚清的儒家。」他已有專文論及王韜、郭嵩燾及薛福成,拙文則補上魏源和徐繼畬,因為兩人都推許同一國度。
魏源先在《海國圖志》提到美國:
「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徇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可不謂周乎。」

隨後徐繼畬出版《瀛寰志略》,再仔細介紹華盛頓: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彊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
「周」和「三代」(堯舜禹湯的時代)都是儒家最高的讚美,不能再高的了。《明史》記載朱元璋讀《孟子》時大怒,一度想廢黜孟子所享的祭祀,直到臣子死諫才作罷,但朱元璋依然下令刪改《孟子》。儒家一直想建立公義的社會,但始終沒有足夠的思想資源抵抗專制。所以舊學出身的純儒有見民主能夠成就儒家千年未逮的理想,願意不恥下問師法達者為先,再次拓闊儒家的普世正義論。
陳寅恪和余英時都遵奉「獨立自由之意志」,甚至為之殉節而不渝,恰恰由於兩人不肯「尊西人若帝天」,而是因為他們一生都「淪肌浹髓」浸潤在儒家傳統裡面。余英時曾闡釋宗教變遷,傳統的演變不完全來自異端的衝擊,更多是來自正統的衛道。因為伯克(Edmund Burke)便在《反思法國大革命》說過,一個國家若失去改變的能力,即意味要冒上更大的風險:失去最想保存的地方。
晚年被共黨排擠的陳獨秀由迷轉悟,「每一封建王朝,都把孔子當作神聖供奉,信奉孔子是假,維護統治是真。」與民主不合的並非傳統,而是膜拜極權的沙文民族主義。
余英時一生轉益多師,道假眾緣,終成一家之言。他心懷的「中國」沒有本質化的「體」、「用」之分,所有民族文化都有普遍和特殊的成分,都有精華值得保留,都有糟粕應該更新。
四、余英時永不過時
儘管「大國崛起」數十年,但余英時的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決不從時俗轉移。有些人目為執拗背時,但當迷霧過去,顯山露水,余英時才是真正的先知。
很多華裔學者在海外學有所成,享負盛名後陸續成為招安目標,結果都晚節不保拜倒在極權「裙下」。許章潤俏皮地透露箇中原委,不盡然是因為榮華富貴:
「夜幕低垂,而微風不興,空氣裡蕩漾著絲絲曖昧,好個富貴溫柔之鄉。眼見座中師大女生簇擁外籍華裔教授,聆其教誨,仿其身段,引偉人語錄,作深沉思考,偶或聳肩撇嘴,令我明白我親愛同胞華裔教授並非只是看中錢財,實在是因為同時兼收海外課堂難以收獲之職業尊崇與學子膜拜。」
以余英時的地位,只要他願意折節,不但可以衣錦還鄉,而且可以呼風喚雨,甚或可晉身為師王師,為今上捉刀寫詔書。陳寅恪和余英時都不曾以儒家自詡,但他們都踐履了朱子所說讀書從來只是「第二義」,最重要是立身行道。
2020年9月允晨出版社重印《史學與傳統》,燈火闌珊的余英時依然誠摰地再寫〈重刊序〉,特別提到香港人為了「爭取自由」不惜「傾城而出」,接著他說『文化傳統和現代普世價值的匯流是當前中國的「大事因緣」』。
彼時余先生已一燈如豆,自然難以申詳何謂「大事因緣」。筆者不揣冒昧,大膽附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中的「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料想余英時的一瓣心香,正是陳寅恪向吳宓透露的心聲:
「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義理之高明詳盡,足以救中國之缺失,而又憂其用夷變夏也。乃求得兩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採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書五經,名為闡明古學,實為吸收異教,聲言尊孔辟佛,實質佛之義理,已浸漬濡染,與儒教之宗傳,合而為一。此先儒愛國濟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諒者也。故佛教實有功於中國甚大。」
古希臘人根本不會自視為「西方」一部分,全因歷史的因緣際會,遺澤才會流衍成為西方的「傳統」。同理作為「外國勢力」的佛教,最初也被儒家排擠,最後卻徹底改變儒家,成為中國「傳統」一部分。所以余英時肯定「傳統文化是完全可以和西方文化匯流。」遺憾近代的努力中道夭折,終被「反西方的西化」取而代之。
陳寅恪始終如一地秉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過胡適也曾援引尼采的話:「一個始終聽話的學生是最對不起老師的。」余英時一生轉益多師,道假眾緣,終成一家之言。他心懷的「中國」沒有本質化的「體」、「用」之分,所有民族文化都有普遍和特殊的成分,都有精華值得保留,都有糟粕應該更新。所以他多番援引胡適的英文文獻,澄清胡適並非主流歸類的「全盤西化」,而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由諸子百家到各族文明,都可以用「平等的眼光」斟酌損益。
「普世正義論」自有其缺點,就是以我為主的「中心主義」,既見諸西方所謂「白種人的負擔」;也見諸中國所謂「化被四夷」。但余英時決不容「文化多元主義」墮入「文化相對主義」,因為不同文化雖各自有「厚」的傳統,但依然可以比較高下,彼此參照,從而得出「薄」的起碼要求。Michael Walzer 便曾以「家」和「旅館」為喻:所有人都希望能待在家(厚的生活傳統);但當家的環境連旅館都及不上(薄的普世原則),家就要受到批判。
余英時道破「大熔爐」只是美國一廂情願的民族神話,其實美國的「白人中心主義」一直遭黑人等少數族群挑戰,傳統與進步一直互相激盪,至今不絕。但美國勝在有民主的保障,大部份衝突都能在制度內競爭。可是當不義打破了共識,就不能枉道而從勢,無道於黎元。
很少人在意梭羅在〈論公民不服從〉引用過《論語》,就是大家熟悉的「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雖然梭羅不諳中文,但為了修習四書認真兼讀英譯和法譯,而且非常推重《孟子》[3]。「我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受統治的人民」(we should be men first, and subjects afterward)。在美國民主運動的經典文獻後,確實有一條「道尊於勢」的思想源流,悄悄流入瓦爾登湖。
回望梭羅的光風霽月,香港和台灣讀者就不必介意余英時的「中國情懷」。他堅持香港和台灣都屬於「中國文化區」,然而「中國」於他而言只有超越政治的文化意義。「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一旦盡棄其文化傳統而重新開始。」
余先生過身之後,各方都在爭奪其詮釋權,這在情理之中,筆者亦難免俗。惟筆者念念不忘真正的尊重,就是雙方即使不盡相同,相異的地方依然值得尊重。余先生一生夢寐的「中國」未必是我們心中所屬,但他的品格足以讓我們尊重差異,不需要將他整個人拉到自己陣營代言。余先生反對所有黨派的專制統治,支持所有「中國」地區的民主運動,立身行道自足千古。

五、結語
1944年6月6日,老羅斯福的長子羅斯福準將(Theodore Roosevelt Jr)運用他的地位一再請求:他要參與諾曼第登陸,而且要在第一波搶灘。他堅持申請兩次,認為身先士卒才能安撫軍心,軍方終於勉從所請。56 的他成為第一波搶灘部隊中年紀最大的人,也是官階最高的將軍。他手拴枴杖在猶他灘頭躲避德軍炮火,奮不顧身抱住受傷的年輕人。儘管他在D-Day活下來,但一個月後在巴黎病逝。
1945年4月12日,小羅斯福逝世,楊聯陞有感總統一門忠烈,足堪為天下式,寫下〈聞羅斯福總統病逝〉:
章憲煌煌告五洲,大西洋月印如鉤。
三扶病骨安天下,一代雄才冠美歐。
康濟新猷才幾種,衣裳盟會已千秋。
捷音初報元戎死,四海風雲繞墓邱。
1946 年 4 月 19 日,陳寅恪為治眼疾,先往英國,再赴美國,楊聯陞偕周一良與趙元任夫婦一同探望。其時陳寅恪的目力已衰退到「僅辨輪廓」,聽到眾人呼喚「頓然悲哽」。楊聯陞向老師稟告他和周一良皆已在哈佛博士畢業,自己將到北大任教,陳寅恪則說他有意定居南京。以為他日定可重聚,不意當日竟是永訣。
1955 年 10 月,楊聯陞終於遇到可以傳燈的人。
註釋
[1]:後來該文收錄在《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余英時在書中序言特別補充:『由於受到「因事命篇」的限制,此文的焦距集中在傳統與現代的可能接榫點上,因此其觀察的角度是特殊的,並不代表我對於中國文化的全面意見,特別是具有批判性的意見。』
[2]:兼引台灣與大陸譯本。過去筆者一直參考大陸譯本,直到最近才有幸買到台灣姚朝森先生的譯本,發現有些句子顯然譯得更好。
[3]:其實梭羅在〈論公民不服從〉不僅援引《論語》,還在最後一段寫道:“The progress from an absolute to a limited monarchy, from a limited monarchy to a democracy, is a progress toward a true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 Even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was wise enough to regard the individual as the basis of the empire. ” 後世學者考證梭羅的藏書和筆記,認為文中的 Chinese philosopher 就是孟子。由於一般美國讀者知道孔子是誰已屬難能,所以引介孟子時改稱中國哲學家。筆者難以稽考梭羅參考了《孟子》哪一篇,請恕大膽從上文下理推斷,應該就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參考文獻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
余英時《中國與民主》
余英時《論士衡史》(序言)
余英時《現代儒學論》(序言)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余英時《史學與傳統》(允晨出版社 2021 年版)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楊聯陞《哈佛遺墨》
梭羅〈論公民不服從〉
許章潤《人間不是匪幫》
溝口雄三《中國的思想》
吳宓《吳宓日記》(第二集)
卡爾・施密特《政治的概念》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
Chris Brown《當代國際政治理論》
桑兵《學術江湖: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風》
瑞安《最長的一日 : 諾曼第登陸的英勇故事》
吾妻重二〈日本江戶學初學塾之發長與中國、朝鮮〉
彭國翔《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序言)
Austin Bernard Ross, “Confucian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The Dao of Henry David Thoreau, and the Transmut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into Transcendentalism”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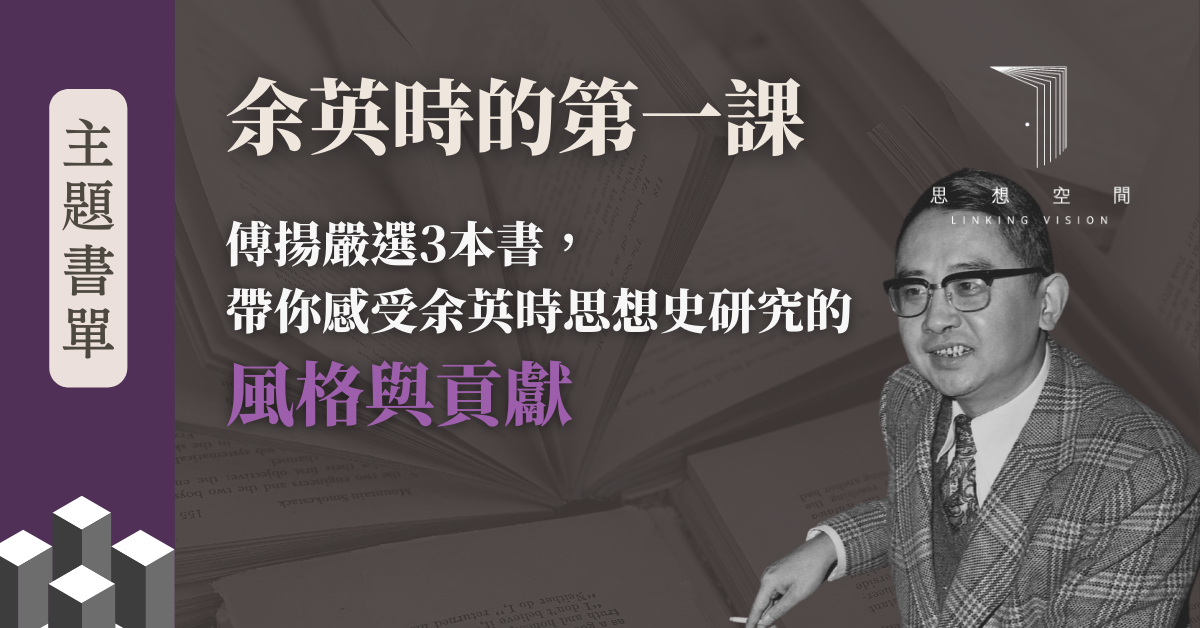
【主題書單:余英時的第一課】傅揚嚴選3本書,帶你感受余英時思想史研究的風格與貢獻

容啟聰:第三勢力與冷戰:由余英時的《香港時代文集》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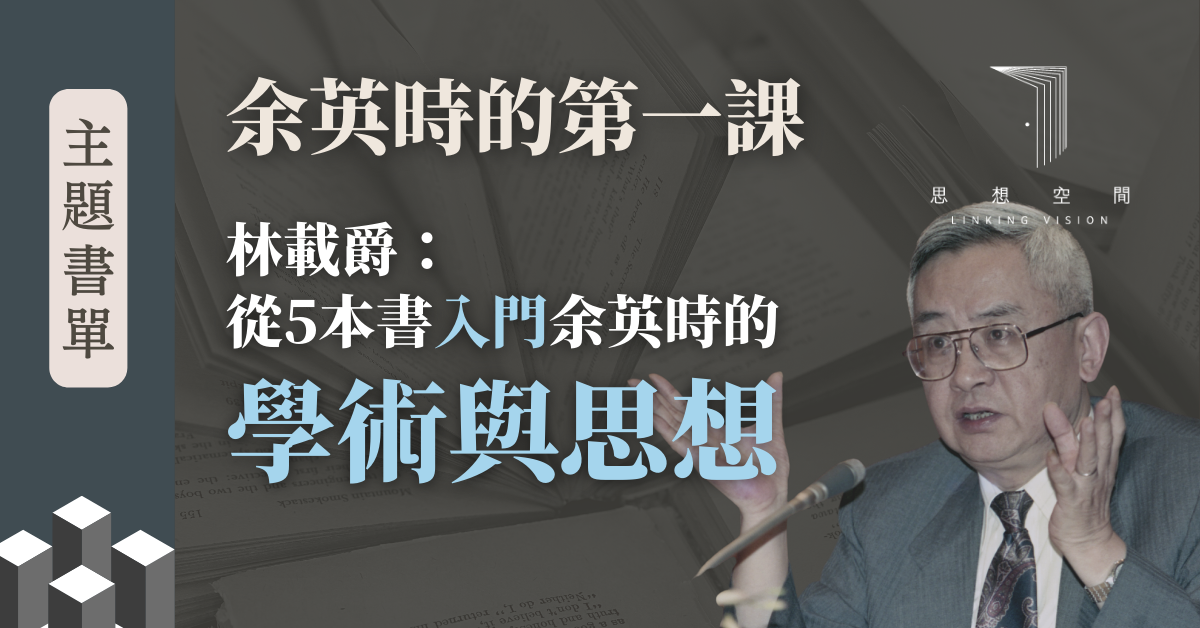
【主題書單:余英時的第一課】林載爵:從5本書閱讀余英時的學術與思想
| 閱讀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