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忻穎(曾任澎湖、新北地檢署檢察官)
編按:日前,台南兩位警察因追緝逃犯而遭到攻擊,不幸離世。案件轟動全台,警方在追捕過程中先後鎖定疑犯,隨即他們的相片也在網路上廣泛流傳、也引發不少網民進行「肉搜」,最後才發現兩人並非犯案者;此事也被製作為「梗圖」,兩人被嘲是「當日最倒霉的兩個男人」。然而在這件看似荒謬的事情背後,卻暗藏著非常尖銳的社會問題——刺激人心的全民追捕是否合理呢?網民及媒體的「人肉搜索」,又是否為相關人士帶來煩擾、抑或並不利於案件偵破?帶著這些疑問,我們重讀前檢察官吳忻穎的著作《扭曲的正義》,了解司法與警察體系內、外亂象,反思社會正面臨的極其嚴重的法治問題。(* 本文節選自吳忻穎《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第十章〈跨越倫理界線〉,標題為編者擬。)
來去自如的司法記者
司法官學院的師長們都會殷殷告誡學員,案件應由司法機關發言人發言,不宜由檢察官擅自向記者說明案件。法務部也早有規範新聞處理注意要點,比如檢察機關就偵查案件的發言,應該要指定新聞發言人並設新聞發布室,統一由發言人或其代理人於新聞發布室發布,規範採訪時間。
我在司法官學院結訓,初分發至澎湖地檢署任檢察官時,澎湖地檢署全署加上主任檢察官僅有四名檢察官,除了一樓大廳洽公與為民服務樓層,均有門禁卡管制,且嚴禁記者、閒雜人等前往檢察官、法醫辦公室、紀錄科辦公室等樓層,僅有司法警察、與檢察公務有關之人,經檢察官允許後得於法警室登記姓名並領取訪客門禁卡前往辦公區域。絕大多數地檢署也都採取這樣的門禁規定,以符合法務部的規範。
抗爭的過程,讓我看清了現實與理論的距離,也深刻體悟到:一個人如果要在數十年來如一日的體系中對於權力無懼,前提是他要先對權力無欲。
然而,並非所有實務運作皆是如此。以北部某些地檢署的媒體互動狀況為例,司法記者不但可以「自由出入」檢察官辦公室詢問案情,還可以逐一詢問公告偵結的案件,甚至會詢問尚未偵結的案件。地檢署偵查終結公告的案件,並不等於已經確定(例如告訴人可能會針對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適不適合由個別檢察官回答記者問題也有疑問,更遑論還沒有偵結公告的案件,怎麼可以透露給媒體呢?
除了司法記者與檢察官平時太過密切的關係,記者在某些「名人」涉案經警逮捕解送地檢署時,拼湊各種不知哪來的腥羶色消息並大肆報導後,為了想要再挖多點料,還會群聚在當日內勤檢察官辦公室裡「當面詢問案情」。檢察官辦公室裡的卷宗堆積如山,卷宗封面上還有被告姓名、案由,這些都是偵查不公開的範疇。記者這樣堂而皇之自由進出檢察官辦公室,意味著記者很可能有機會看到卷宗封面,知道何人涉犯何罪、正在被偵辦。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媒體記者自由進出檢察官辦公室,完全不迴避的「奇觀」,就是因為某些檢察機關「畏懼」稍有不從會遭媒體進行「報復性」的醜化報導。在這樣的壓力下,公家機關只好配合記者濫用「新聞自由」,放棄偵查機關對辦公場所的管制權。
相較於澎湖地檢署的門禁森嚴,調任新北地檢署後,我便發現那裡的記者個個身懷「破解門鎖」的絕技,竟可以在樓層有門禁卡管制的檢察官辦公室區域裡來來去去,甚至隨意進出檢察官辦公室。
我曾拒絕回答找上門來的記者問題,請他離開我的辦公室,去找地檢署新聞發言人。孰料,某些有心人不但不反省新北地檢署這個「便利媒體」的「傳統」是否合乎規定、合宜,竟然還將我後來在臉書與群組裡針對此事的不公開貼文,以及其他同事在這則不公開貼文下的留言截圖傳給記者,記者便憑這則「內部線報」去跟襄閱主任檢察官告狀,甚至揚言要「修理」我。
被記者告狀的我,認為問題出在襄閱主任檢察官沒有好好善盡發言人的義務。原本該由他作為對外發言的管道,告訴記者可知的消息,怎麼反而放記者自己去找檢察官打探呢?這不是違反了法務部的要點規定嗎?
在長期訴求與媒體維持「良好關係」的環境下,聽聞此事的部分同事竟認為要求記者離開檢察官辦公室的我是「不知好歹」、「不知入境隨俗」,並進一步表示記者進出辦公室是在給檢察官「表現」的機會,好像見到記者找上門來的我沒有千恩萬謝很不應該;還有學長大方向我們分享他「操作媒體的技巧」、自己如何告訴記者有趣的案子,甚至還幫記者下新聞標題。
當時,一位長官就此事找我談話。
「妳的『問題』在於妳是個無法被體制規訓的人,在這個體系內,我們都知道什麼是事實,然而說實話是要勇氣的。」
「如果沒有人說實話,要怎麼進步?」我提問。
長官回答道:「是的,這些實話需要有人說,而且應該讓沒有包袱的年輕人說。」
我則反問:「但是這些說實話的壓力應該由我們扛嗎?」
在我的堅持下,地檢署上級面對司法記者的施壓,轉而要求並警告我:「既然妳不准記者直接問妳,那妳這股以後的結案書類就要全部都要求書記官隱去個資後,製作媒體版交給地檢署發言人,妳自己也要小心妳的案件被記者放大解讀。」
對於這樣的要求,我無所畏懼,但我知道,上級這樣的做法,是藉由增加配股書記官的工作量,透過書記官在紀錄科的抱怨與流言對我施壓。
當時有幾位同事笑我傻,說我「何必用自損一萬的方式來殺敵三千」。但最後我並沒有「自損一萬」,因為事實證明,根本沒有記者有耐性閱讀每個月數十,甚至上百件枯燥萬分的書類全文,最後不了了之。書記官沒有如預期的增加到多少工作量,我也沒有因此遭媒體報復。
這個抗爭的過程,讓我看清了現實與理論的距離,也深刻體悟到:一個人如果要在數十年來如一日的體系中對於權力無懼,前提是他要先對權力無欲。
從歷史經驗中我們能深刻了解「新聞自由」有多重要。所有修過大學《憲法》課程的法律系學生都知道,一旦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遭到不當的限制,將斲傷好不容易爭取到的自由民主價值,也因此司法體系長期以來謹守《憲法》、大法官解釋楬櫫的新聞自由標準,這也是為何大多數提告媒體妨害名譽的案件中,當個人名譽權遇上新聞自由時只好退讓,記者大多都獲得不起訴處分的原因。
然而,《憲法》為了公益、為了民主自由,給予記者高度的新聞自由保障,時至今日,卻有不少忘了責任的記者像上述那樣,不知尊重自己的權利/權力,跨越了倫理的界線,使新聞自由與知的權利成為「修理」不配合的司法官署與司法人員的武器,甚至導致某些檢察機關「放棄」機關的門禁管制權,不少檢察官也迫於媒體的力量,在不得已之下只好配合(當然,也有一些逐利之士樂於有這種上媒體的「表現機會」)。
記者不只進出地檢署恍若逛自家後院,他們出入警察局的頻率更是高得可以,有人甚至整天都泡在裡面「駐點」。警察和記者這樣的良好「關係」,反映在一篇又一篇在理應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的偵查期間卻洩漏內部消息做成的新聞上,也反映在一場又一場表彰警察功績的記者會上。警方公關單位提供員警密錄器、警車行車紀錄器甚至卷證照片給記者,由記者進行「選擇性報導」,這是再常見不過的事,民眾觀看、閱讀新聞時,之所以能看到同一個案件每天都有那麼多的「突破」,這不見得是因為辦案辦得很順利,而是有部分公務人員為了某些目的,或害怕被記者「修理」因而違背倫理,向司法記者通風報信、自動供給情報的關係。
我曾在受媒體諮詢關於「偵查不公開」的意見時,對此情況表示:「檢警疏漏、媒體亂象,當然是大問題。但一件命案發生了,給警方最大破案壓力的人是誰?是民眾。命案可能才公布十個小時,大家已經在檢討警察辦案不力,警方只好不斷釋出進度。」
是的,民眾熱愛刺激、嗜血、追逐案件進度、在網路上一窩蜂的鍵盤柯南行為,甚至因此展開參與號召圍事的實際行動,正是完整這扭曲迴圈的最後一個關鍵。對外必須向大眾交代案件、對內要邀功論賞的某些偵查人員;努力滿足觀眾需求、衝點閱率衝得違背倫理的媒體;愛看熱鬧又喜歡妄加評論、對司法單位指手畫腳的民眾,三者成了緊緊相連的圓環,互咬互扯、互相戲弄,然後一起墮落。

當人們滿足偷窺偵查祕密、觀看免費警匪片的心理後,真能認真思考每一宗犯罪背後真正的問題嗎?
我們習以為常的偵查大公開
「偵查中之卷宗、筆錄、影音資料、照片、電磁紀錄或其他重要文件、物品」,是明文規定絕不可公開的資料,如果有對外特別說明或澄清的必要,必須書面敘明理由、經機關首長核准,並且以去識別化方式做適當處理後,才能夠適度公開。此外,案件在偵查中,不得帶媒體一起辦案,或使被告、犯罪嫌疑人受到媒體不當的拍攝、直接採訪或藉由監視器畫面拍攝;也不得恣意發表公開聲明指稱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對審判結果做出預斷。
然而大家平時看新聞,最常看到的是什麼呢?沒錯,就是這些資料大外洩、偵查還沒結束就宣布「結案」而「成就」的「精采」內容。
帶著媒體跑辦案現場的情況想必大家都看過,通常會出現在警方高層意圖展示執法成果時,最常見的就是警方帶著媒體隊衝轄區舞廳進行臨檢,讓媒體拍攝、報導,自己導一場作秀大戲。不過像這樣臨檢的新聞真的有壯大警察威名的效果嗎?不見得,因為面對這一場大戲,感到些許無趣的記者們,為了讓事件看起來更精采,往往關注的重點都在酒店小姐的裙子有多短、腿長不長、有沒有在補妝,滿版的搞錯重點。
再例如二〇二〇年三月,新北市新店區發生一起持刀攻擊陌生路人,引起國內輿論譁然的凶殺案件。事件發生後沒多久,案件還在檢警調查期間,有一段毫無去識別化、清晰錄下犯罪過程的影片就在社群網站與媒體上流出,引起民眾瘋傳。
只要具有刑事司法實務經驗者,應該都可以看出該段影片顯然是由行車紀錄器錄下,且就攝影的角度看來,不難看出這應當是「被告自己的」車輛行車紀錄器錄下的完整影片。理論上,案發現場行車紀錄器會在第一時間由警方扣押,但為什麼作為警方重要證據而予以保密的偵查中證據資料,會外流到媒體手上,變成新聞不斷播放、民眾爭相觀看的驚悚影片?
這樣嚴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的事件,並非開天闢地第一宗。警方類似外流偵查影片的事件,或是把自導自演的「愛與鐵血」史詩般英雄影片、與緝獲的被告「合照」交給媒體發稿之類的事層出不窮。甚至往往還是在檢方完全不知情、有共犯在逃的狀況下,將連檢察官都還沒看到的證據直接洩漏給媒體,產生承辦檢察官「看到新聞才知道有這個證據」的荒謬狀況。
我也有經手過這類「看新聞比看卷宗還要快速詳盡」的案子。那是新北市樹林區二〇一九年三月發生的一起凶殺案,當承辦檢察官、同組協辦與代理檢察官知道人犯緝獲,媒體便在幾乎同一時間搶先報出新聞。我當時身為同組檢察官,才剛接到警方電話告知人犯緝獲、被告與卷宗要在晚上才能送到地檢署,但就連承辦與同組檢察官們全部都還沒看到內部完整資料的時候,警方就已經提供資料給媒體,讓記者先司法調查一步,不只卷宗內文、相片,甚至影片內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人犯到地檢署之前,新聞就已刊登媒體理當不可能拿到的行車紀錄器與監視器畫面,報導裡甚至還有兩名員警與被緝獲的被告「一同看著鏡頭合照」的畫面。
新聞把案件描述得離奇,彷彿照片中的警察是英雄,殊不知,這起案件最初被警方當成車禍案件報請相驗,首先懷疑這並非車禍而朝向凶殺方向調查的,是檢方——當時就在我的辦公室裡,與承辦檢察官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一致覺得案情有疑。當然,檢方不會跟警方「搶功勞」,因為光是收拾善後、調查證據、處理新聞所造成的風波,與承受一看到凶殺案就「罵司法」的壓力,就已經喘不過氣了。
幾年前臺南一起轟動一時,七分鐘扛走ATM提款機的竊案,也出現像上述的情況,甚至更為荒唐:在檢方以串證為由聲押其中一名被告,打算繼續追查另外幾名共犯時,某市長與警方卻一起大動作開「破案記者會」,鉅細靡遺向外界交代案發經過,等同向在逃的其他共犯「自掀底牌」。原本檢方欲透過已聲押的其中一名被告快速查出另兩名在逃共犯,被這場「破案」記者會一攪和,什麼都很難談了。
為了塑造辦案英雄、滿足大眾情感而破壞偵查不公開原則,影響的不只是被告權利,也會造成被害人及其家屬二度傷害,更嚴重的是,很可能阻礙後續偵查發展的可能性。
再回頭看看本節開頭提及的持刀攻擊案,依照警方事後的說明以及報導,那段影片的確是被告車輛的行車紀錄器畫面,且是檢察官命警方第一時間扣押的證據,依照常理判斷,不可能外流。對此,新店分局的解釋,是「疑有警務人員翻拍後散布至網路通訊群組」,除了暴露警方證據保全不周、員警倫理有問題,更讓人懷疑其中是否有與媒體交換消息或好處的「互利共生」。
針對影片外流,有些媒體與輿論認為「大眾有知道犯罪以提高警覺的權利」。是的,媒體的確有權利報導真相,但難道憑此就可以大肆放送偵查卷宗中的圖片、影片嗎?一定要使用血腥、暴力甚至破壞偵查祕密的偵查影片,才能報導真相嗎?
民眾固然有「知的權利」,但用「提高警覺」的藉口合理化自己的獵奇心態,凸顯的是人性卑劣面;有多少人自己喜歡看熱鬧,看完以後又高喊「好怕」,痛罵「治安不好」,最後朝司法與警察機關丟石頭,責怪「一切都是司法的錯」。
面對這種「莫須有」的罪名,司法何其無辜。
當人們滿足偷窺偵查祕密、觀看免費警匪片的心理後,真能認真思考每一宗犯罪背後真正的問題嗎?又有多少人意識到,自己在社群網路中每一次的轉傳、媒體接二連三的播放,對於本來應該祕密進行以防止遭到破壞的偵查流程、被害人或其家屬的情緒、被告的人權造成多大的傷害?散播偵查不公開資料的媒體,到底是在報導,還是想撩動人們的情緒、恐懼?
這到底對社會有什麼幫助呢?
延伸閱讀:

彭明敏流亡返台首次演講:放棄教條、放棄口號、放棄虛構、放棄神話

葉虹靈:誰是陳文溪?二二八歷史中的幽微

花亦芬:面對二二八,轉型正義的三個迷思
| 閱讀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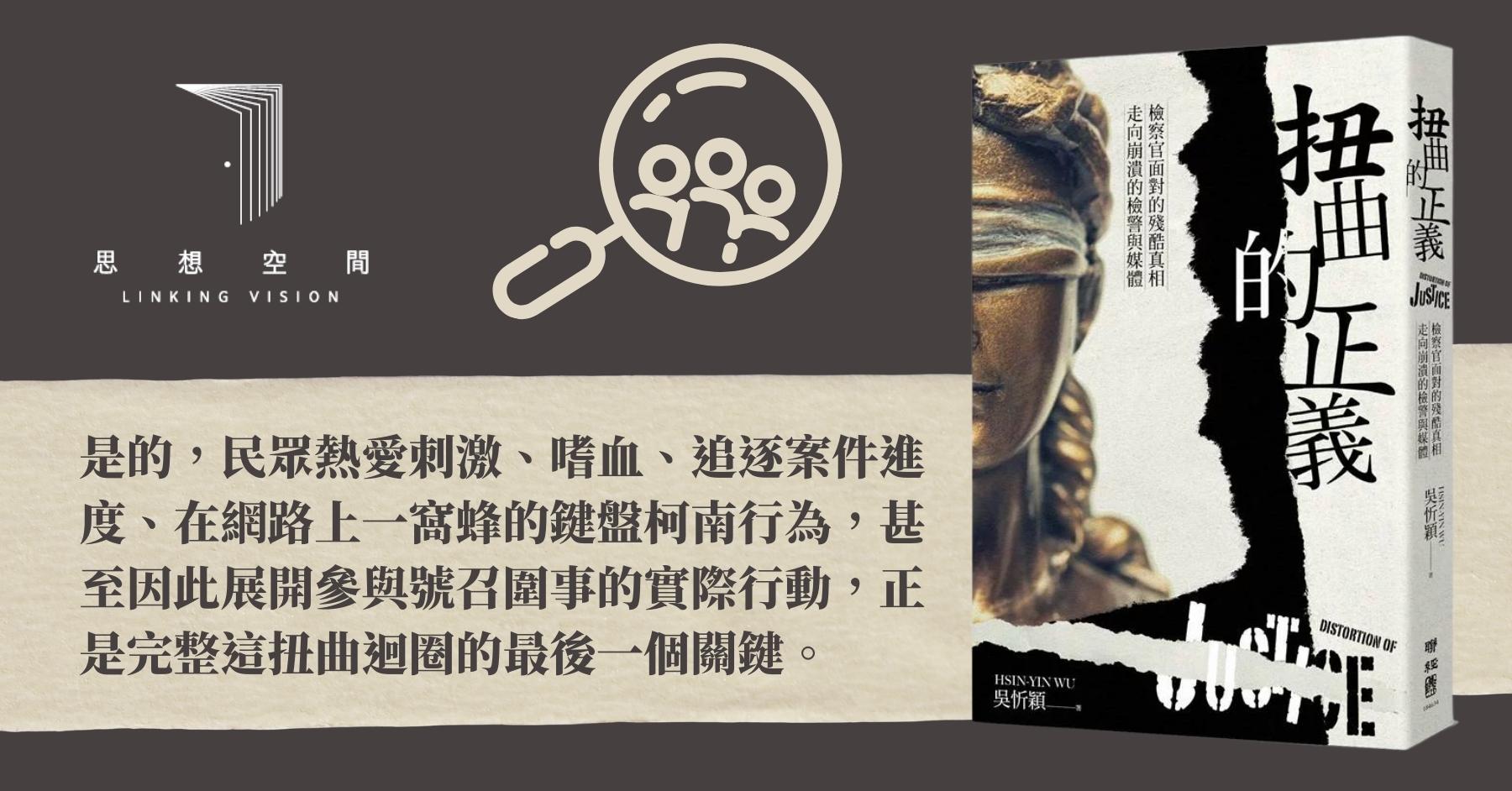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