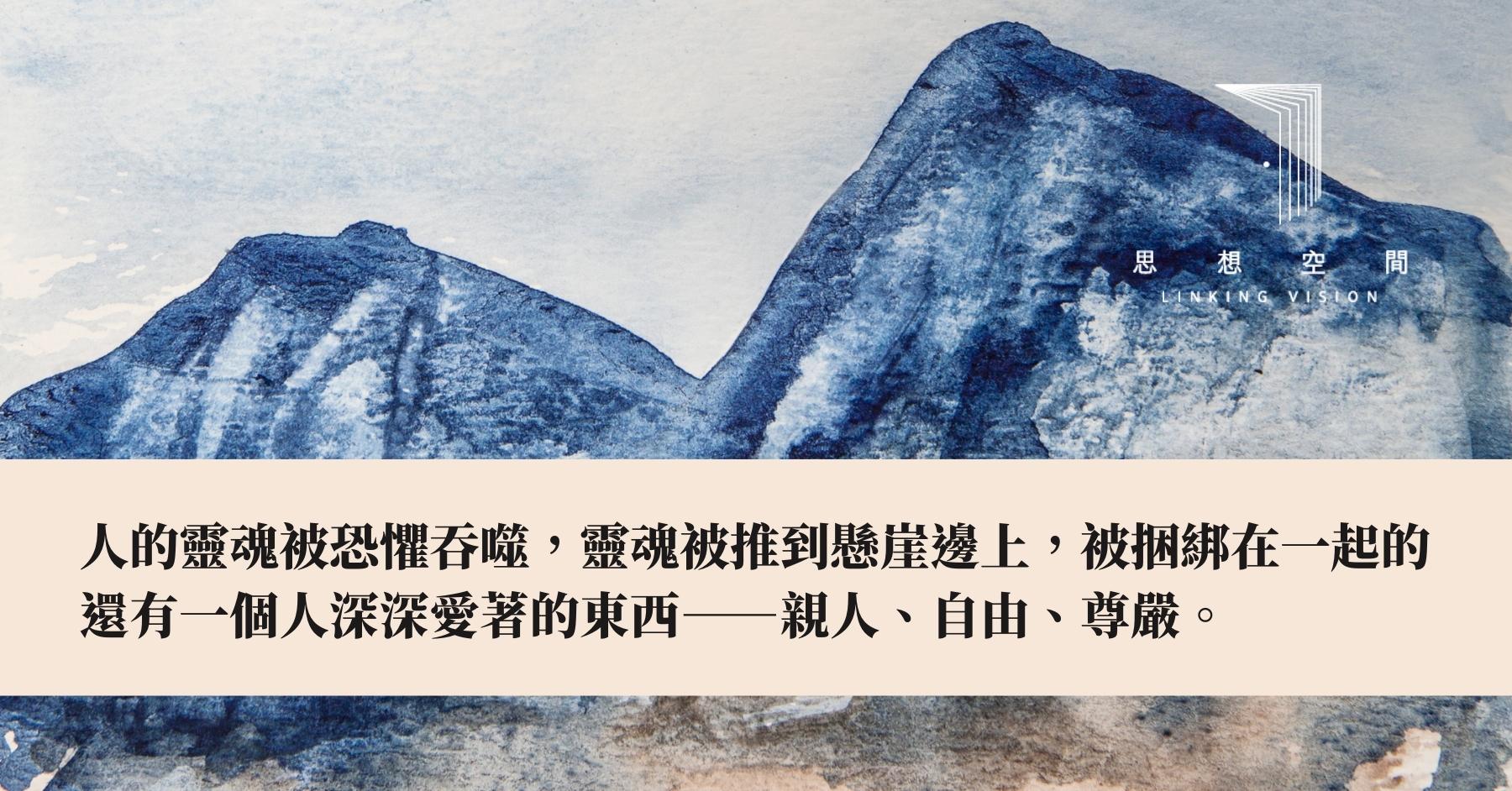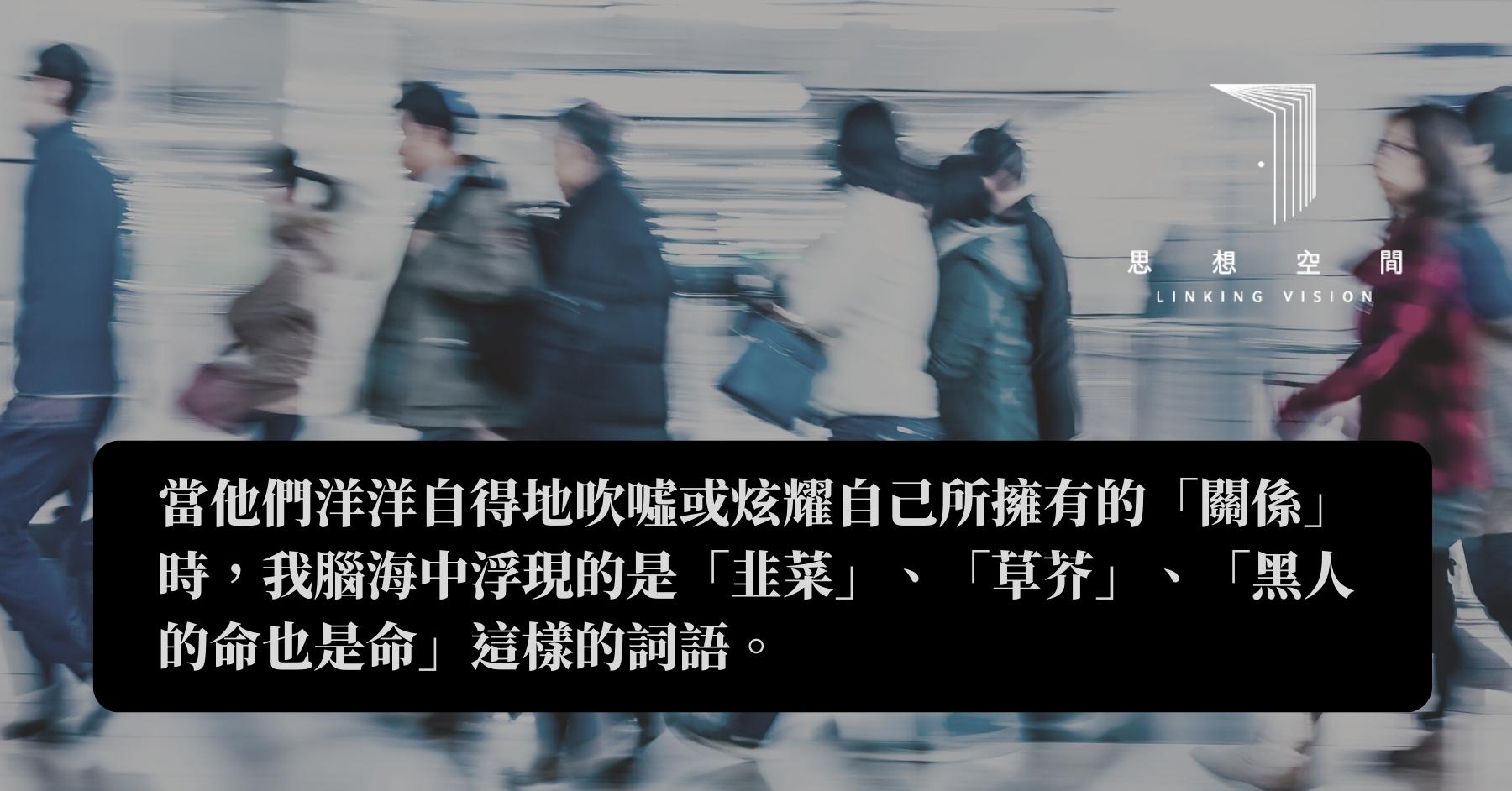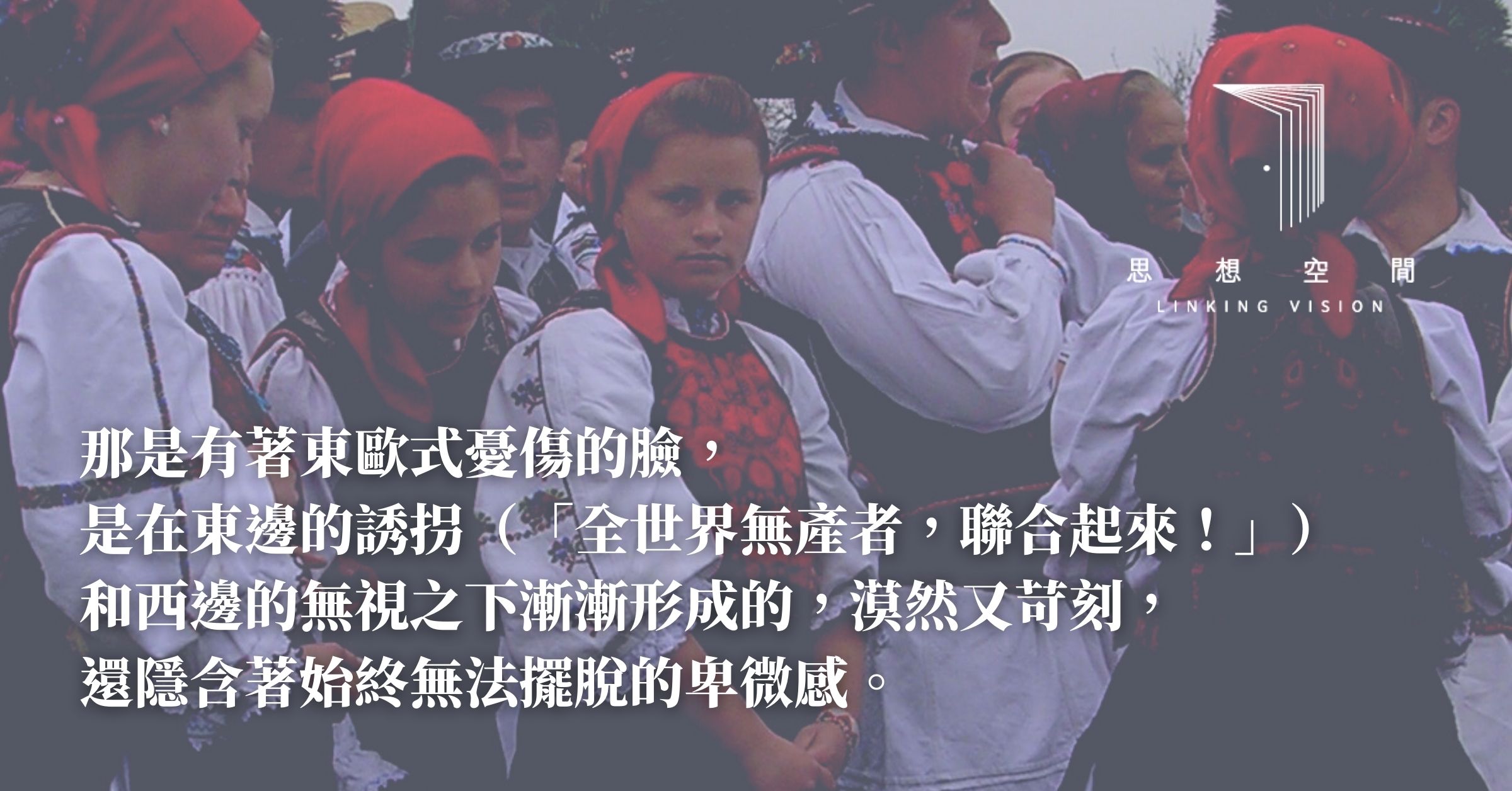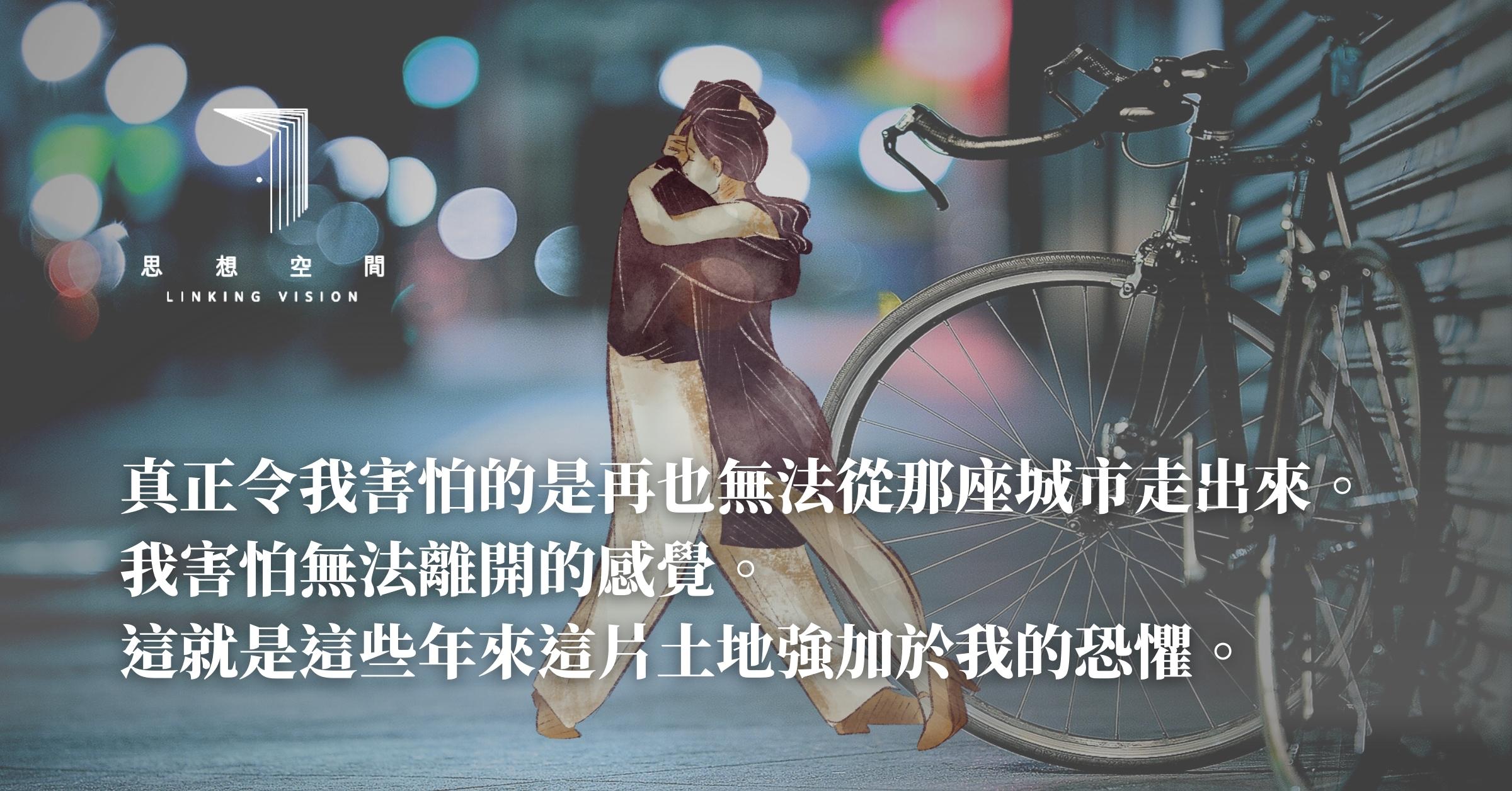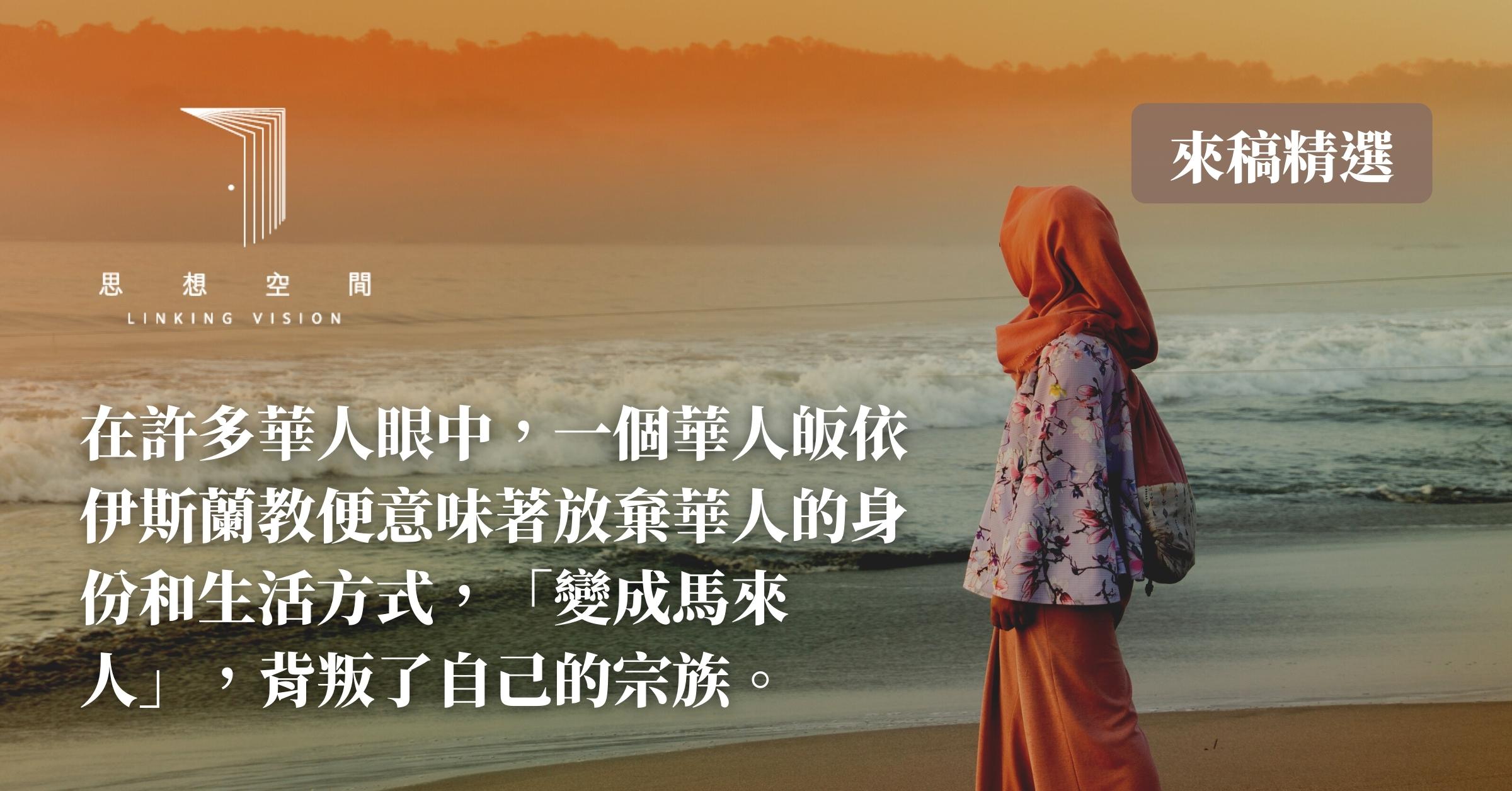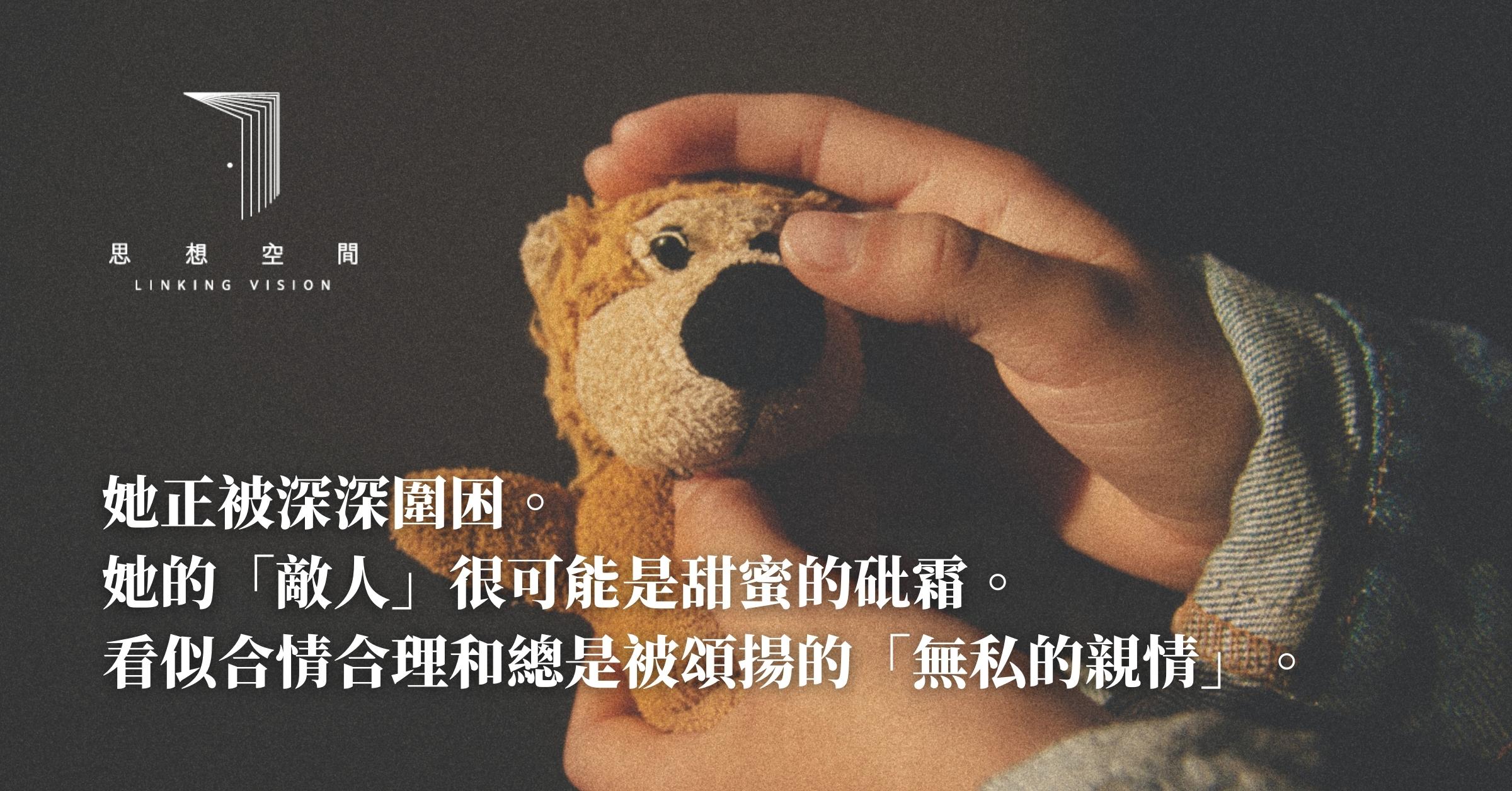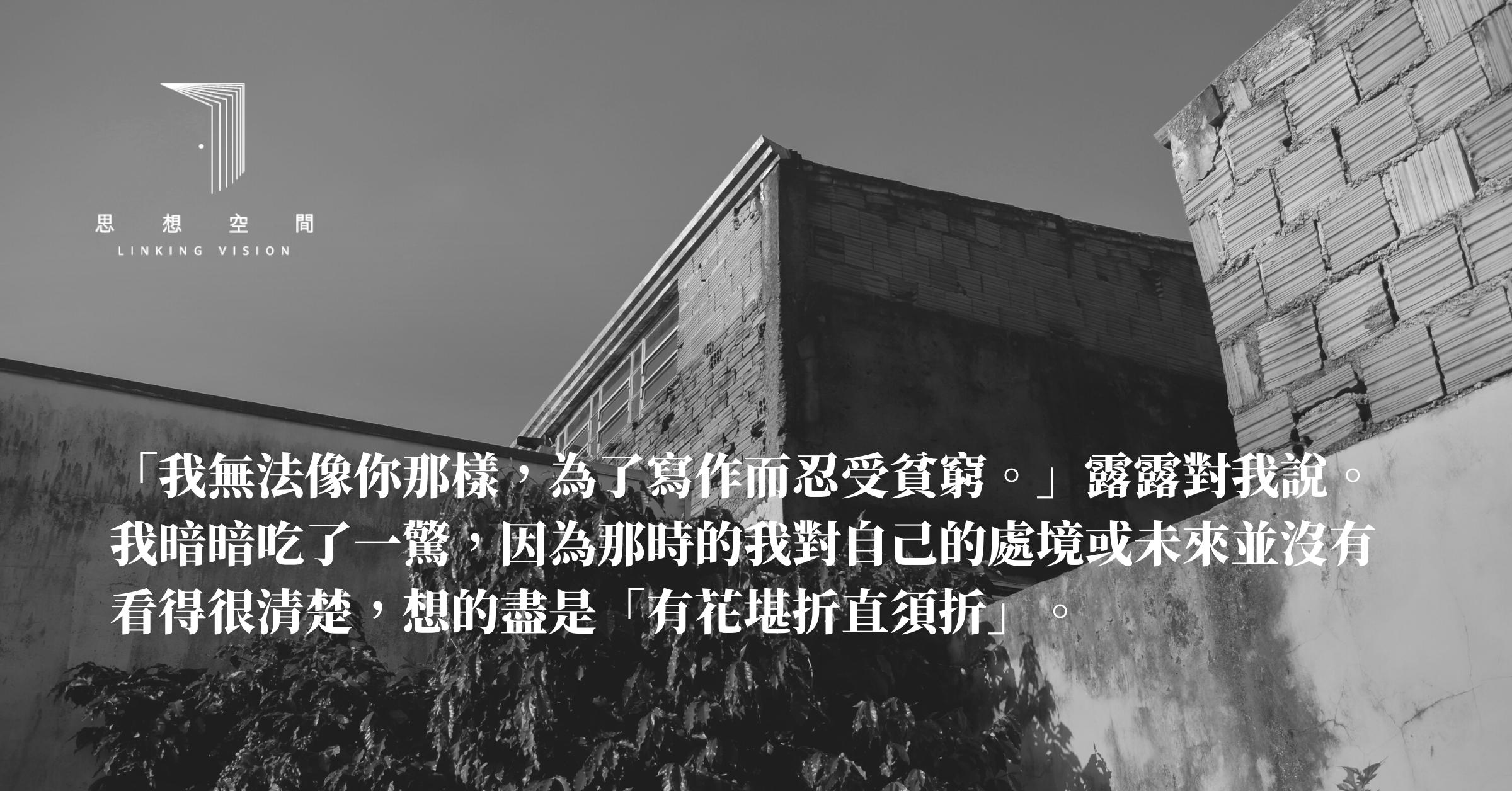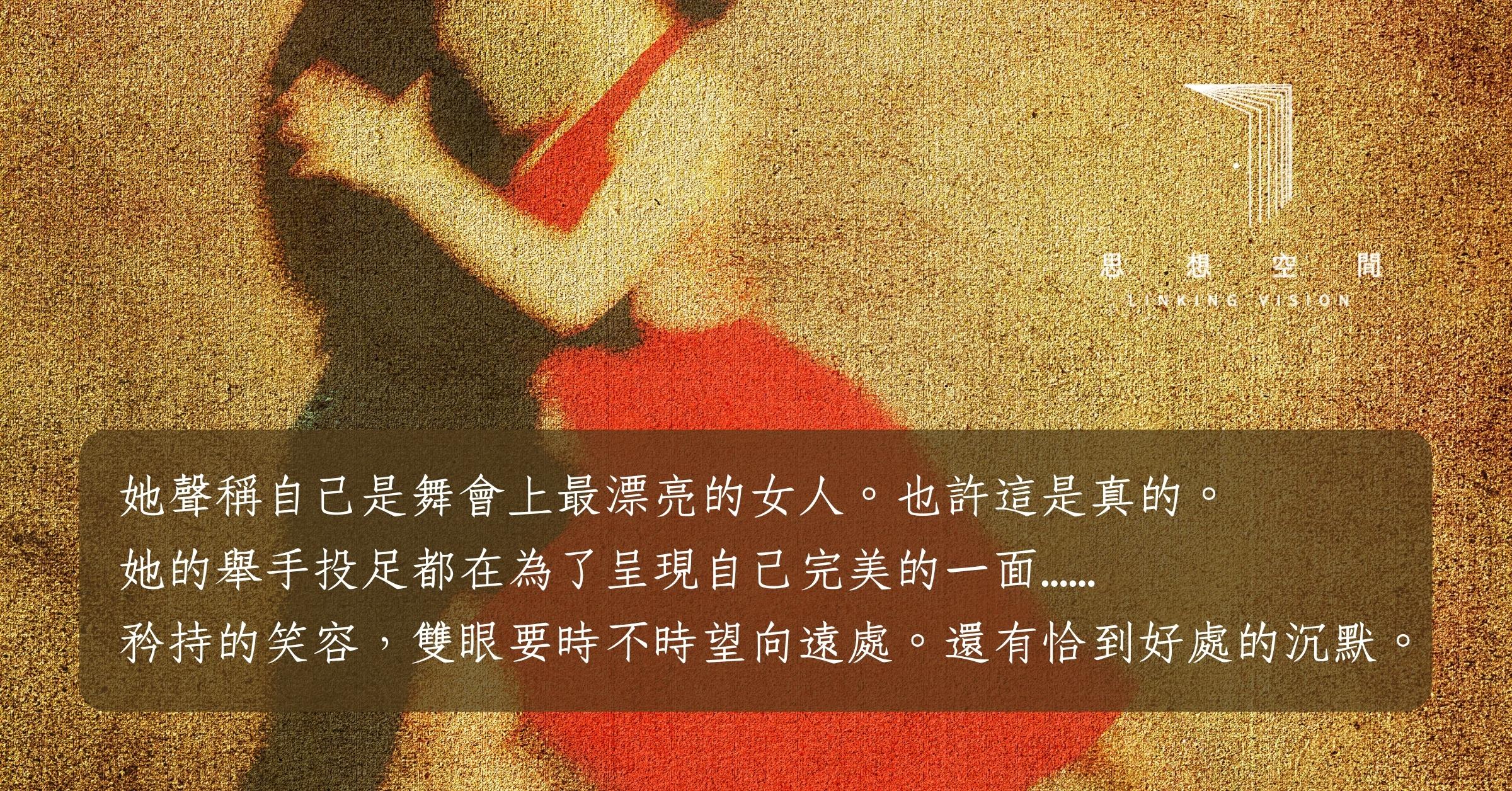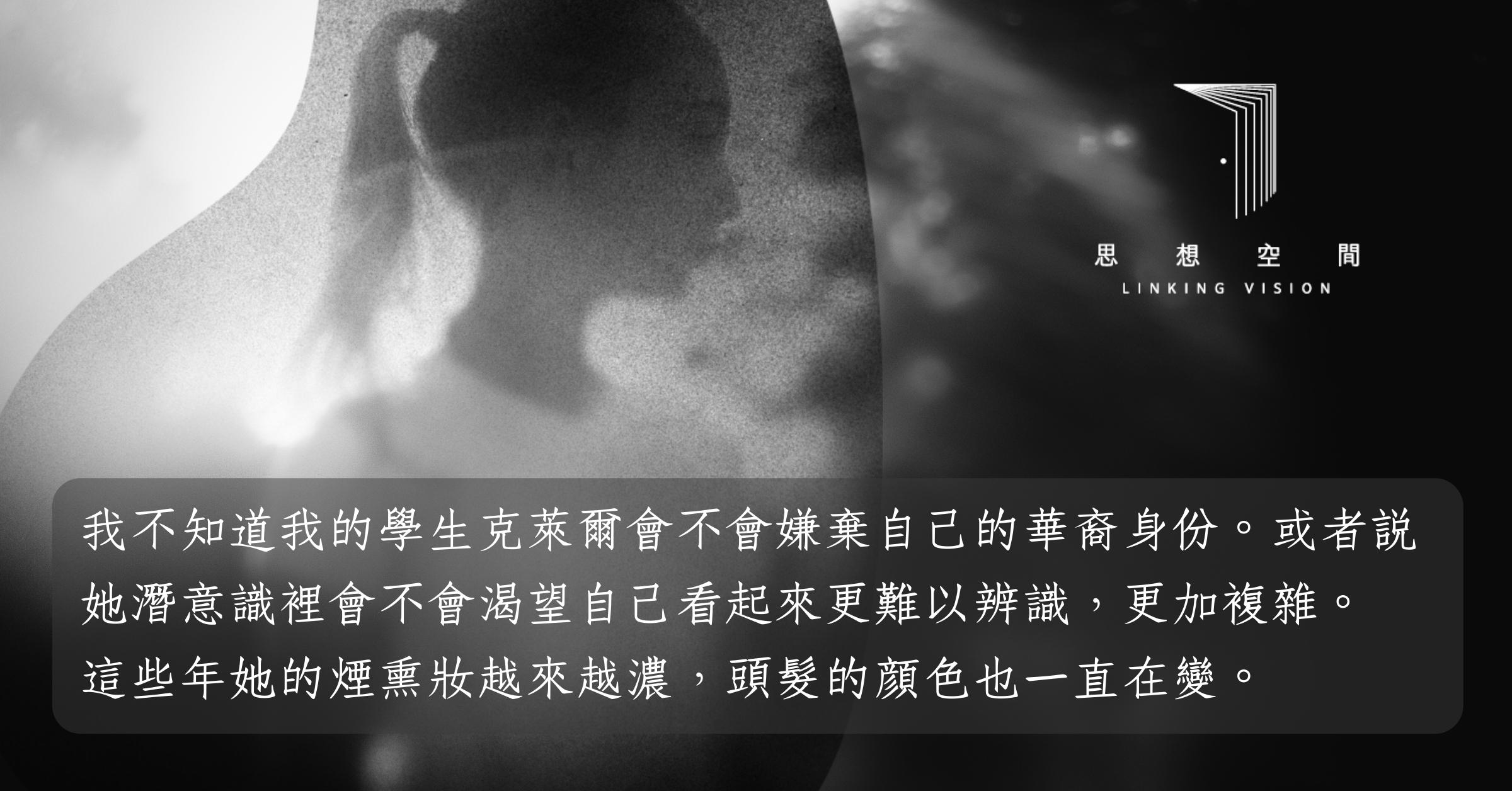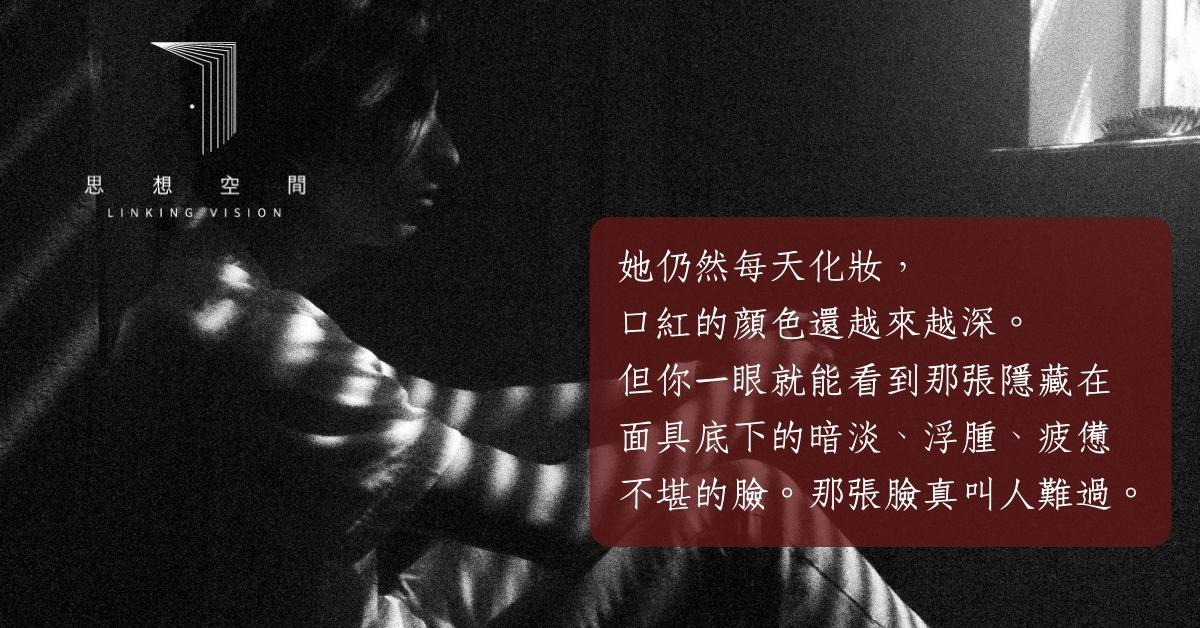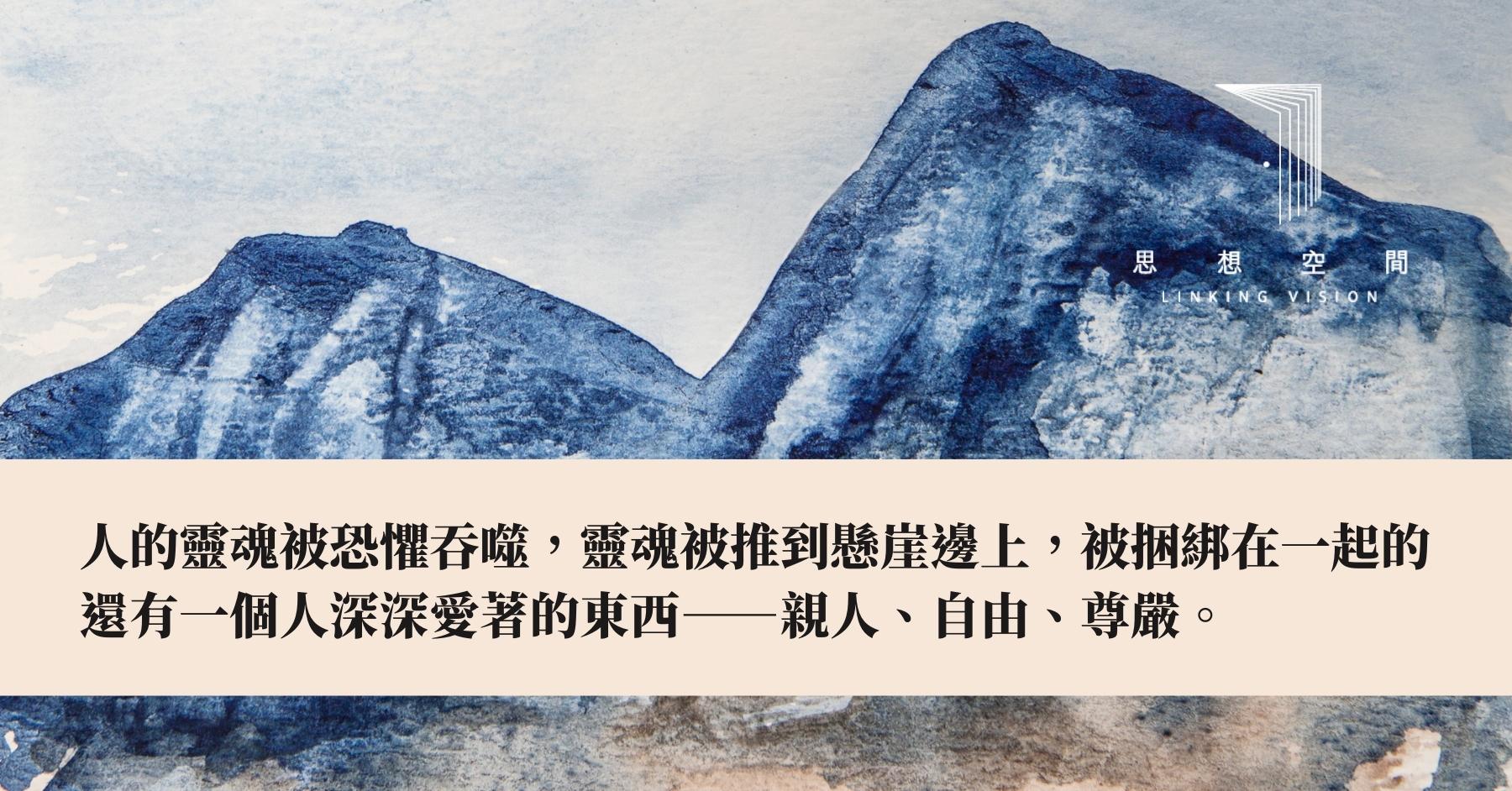
【美好年代】林雪虹:玩笑與危機四伏
學德語以前,我學的是法語(就像我的其他興趣那樣,它很快就被拋棄了)。那是七年前的事,我早已把那些名詞的性別和語法規則忘得一乾二淨。但有一件小事卻總也忘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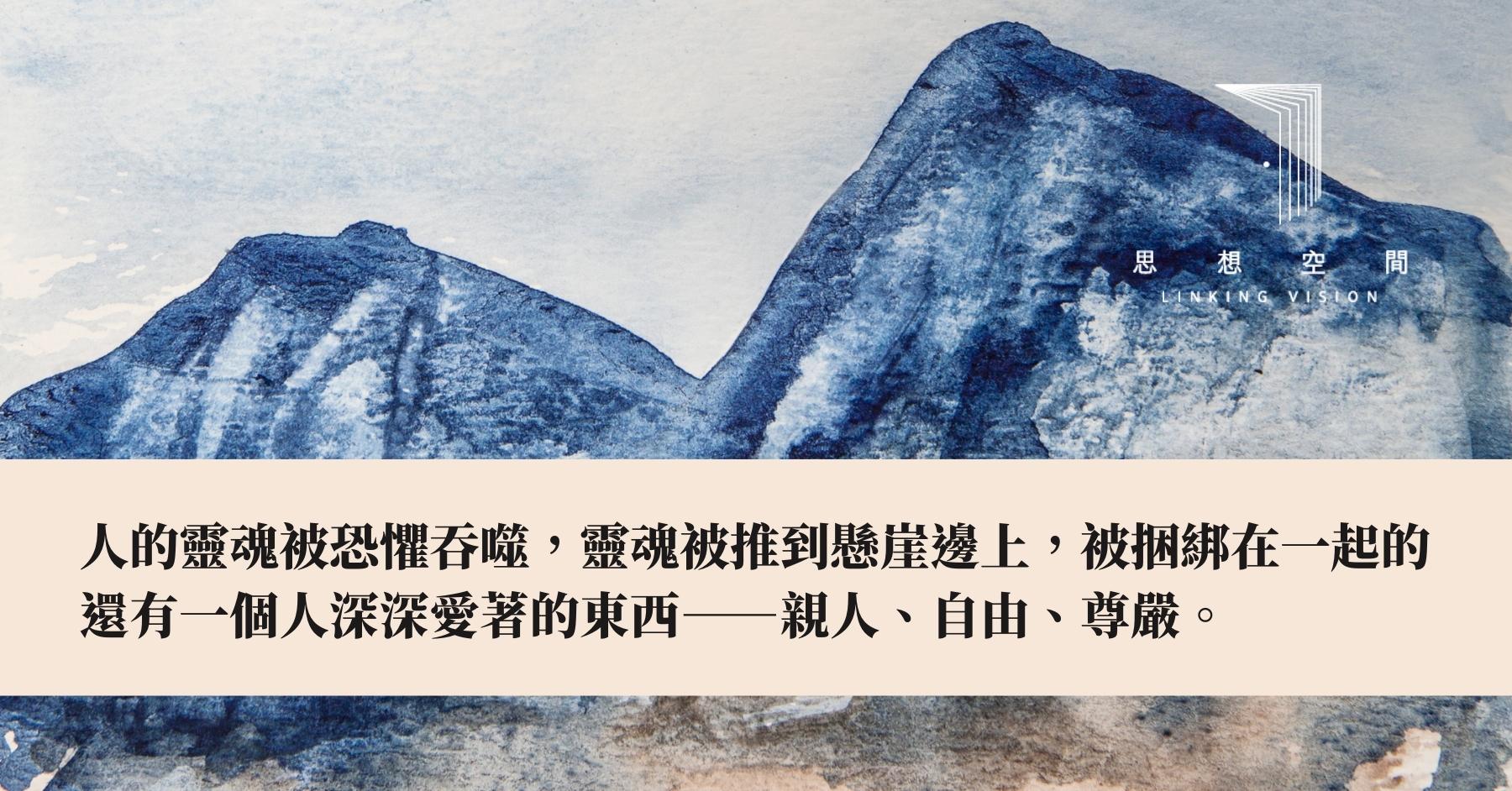
學德語以前,我學的是法語(就像我的其他興趣那樣,它很快就被拋棄了)。那是七年前的事,我早已把那些名詞的性別和語法規則忘得一乾二淨。但有一件小事卻總也忘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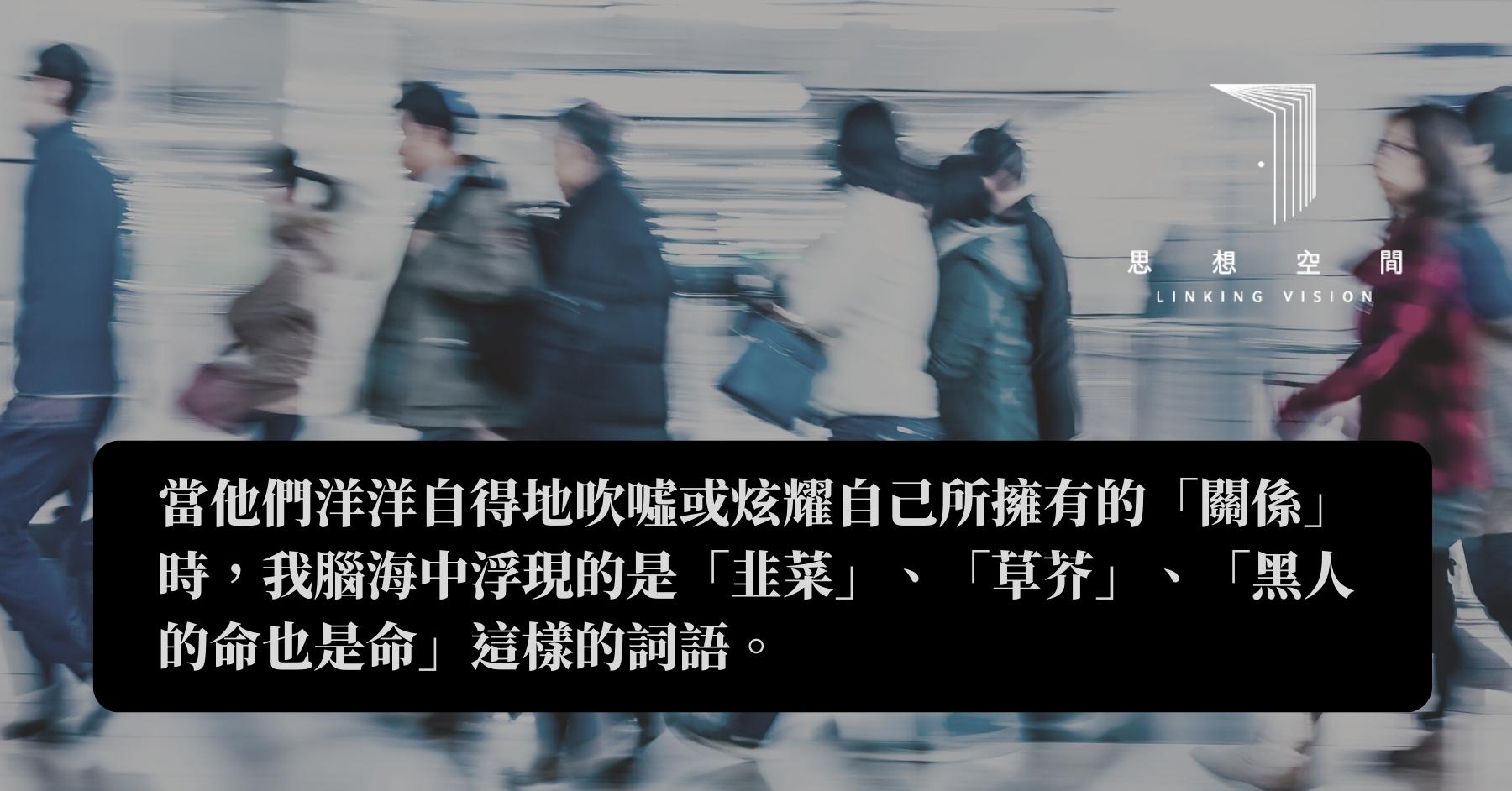
這兩年我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醫院。先是夏木生病,然後到我。最初夏木去的是朝陽醫院,但由於那裡的醫生拿他的巨大腦動脈瘤沒辦法,我們便改為去以治療心腦血管疾病著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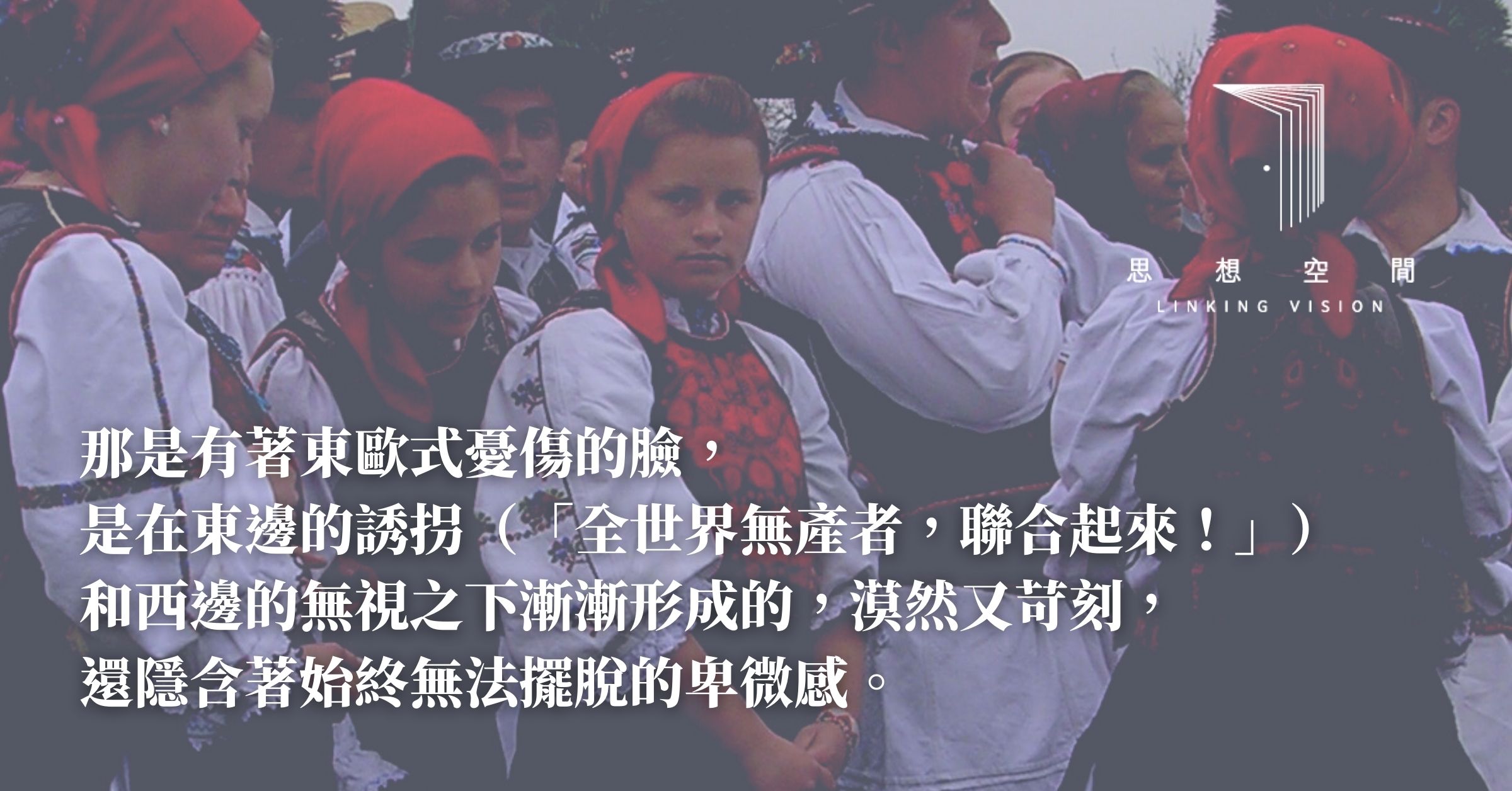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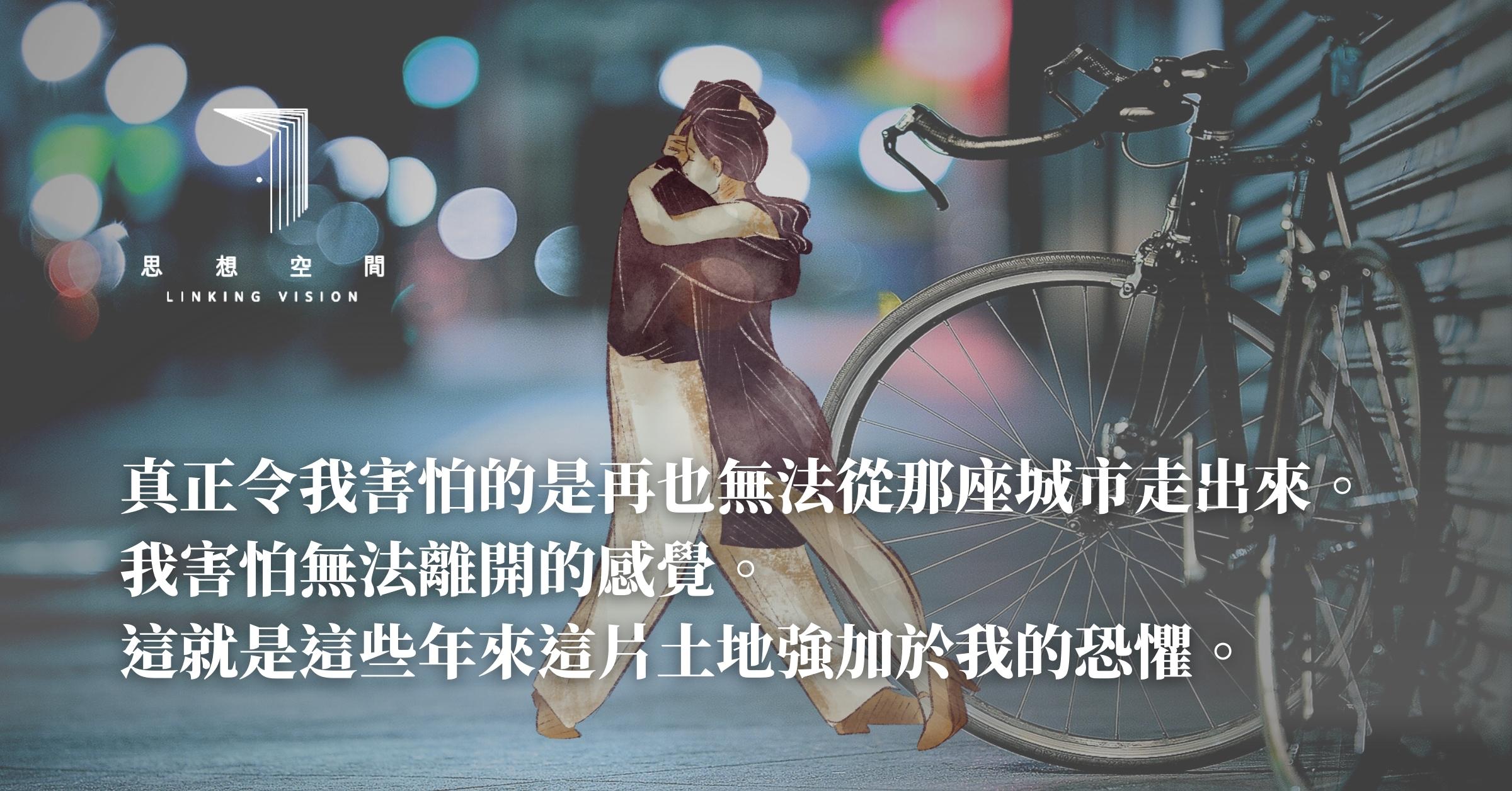
最近我一直在想搬到天津這件事。這座城市對我們具有特殊的意義……十七年前,我們在那裡相遇,很快便墜入愛河,輕易就說出「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樣的話。一切都是新奇、刺激的。這是我對這座城市最初的感受。我將在這裡生活兩年。在此以前我從未去過任何國家。我作為旅居者的身份將由此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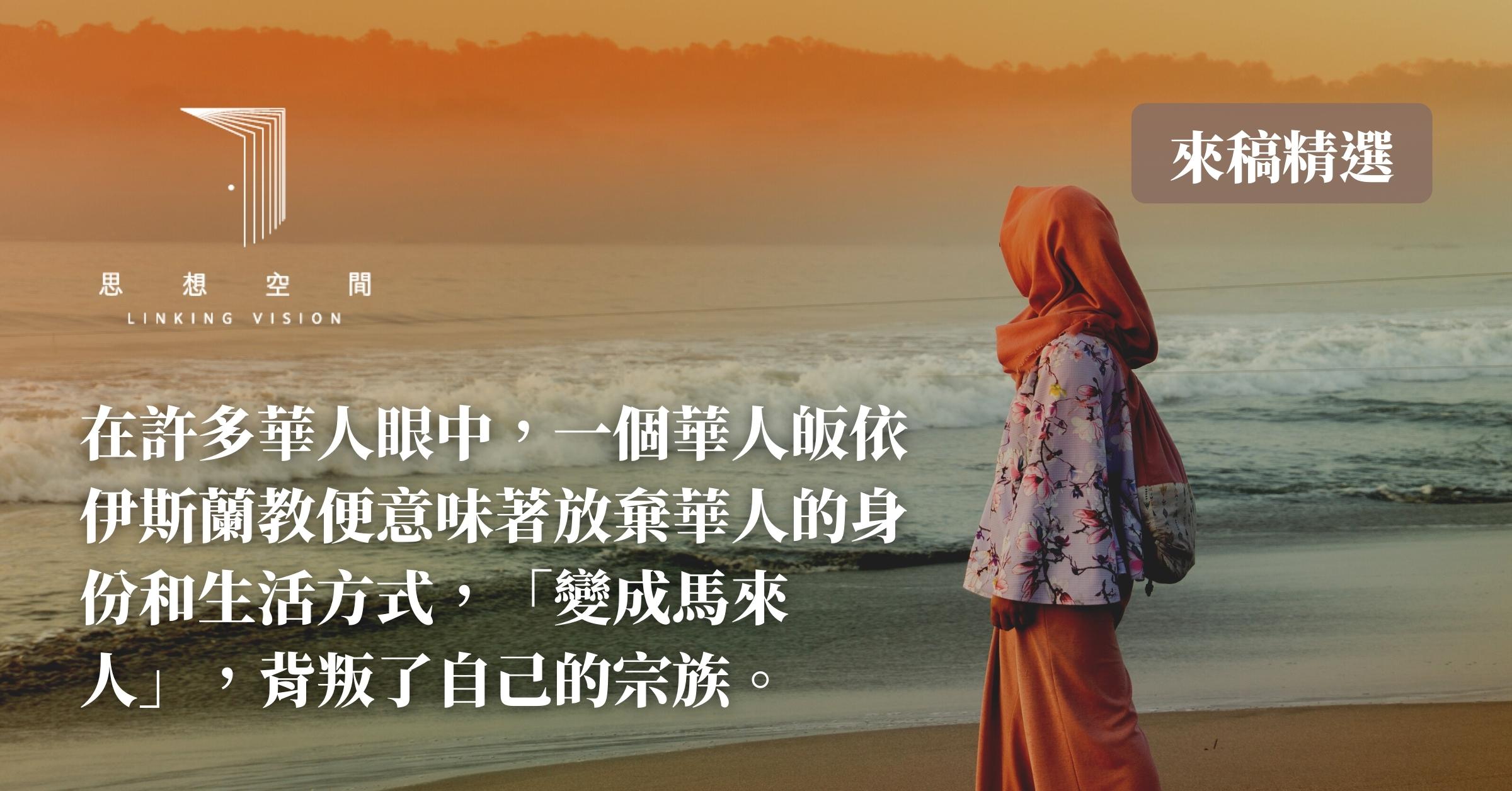
許多年前,我帶著我的丈夫夏木(當時我們還只是情侶,而且都是學生)回馬來西亞旅行一個月。我記得那是北京的盛夏,在馬來西亞正巧是伊斯蘭教徒的齋戒月。那是夏木第一次去馬來西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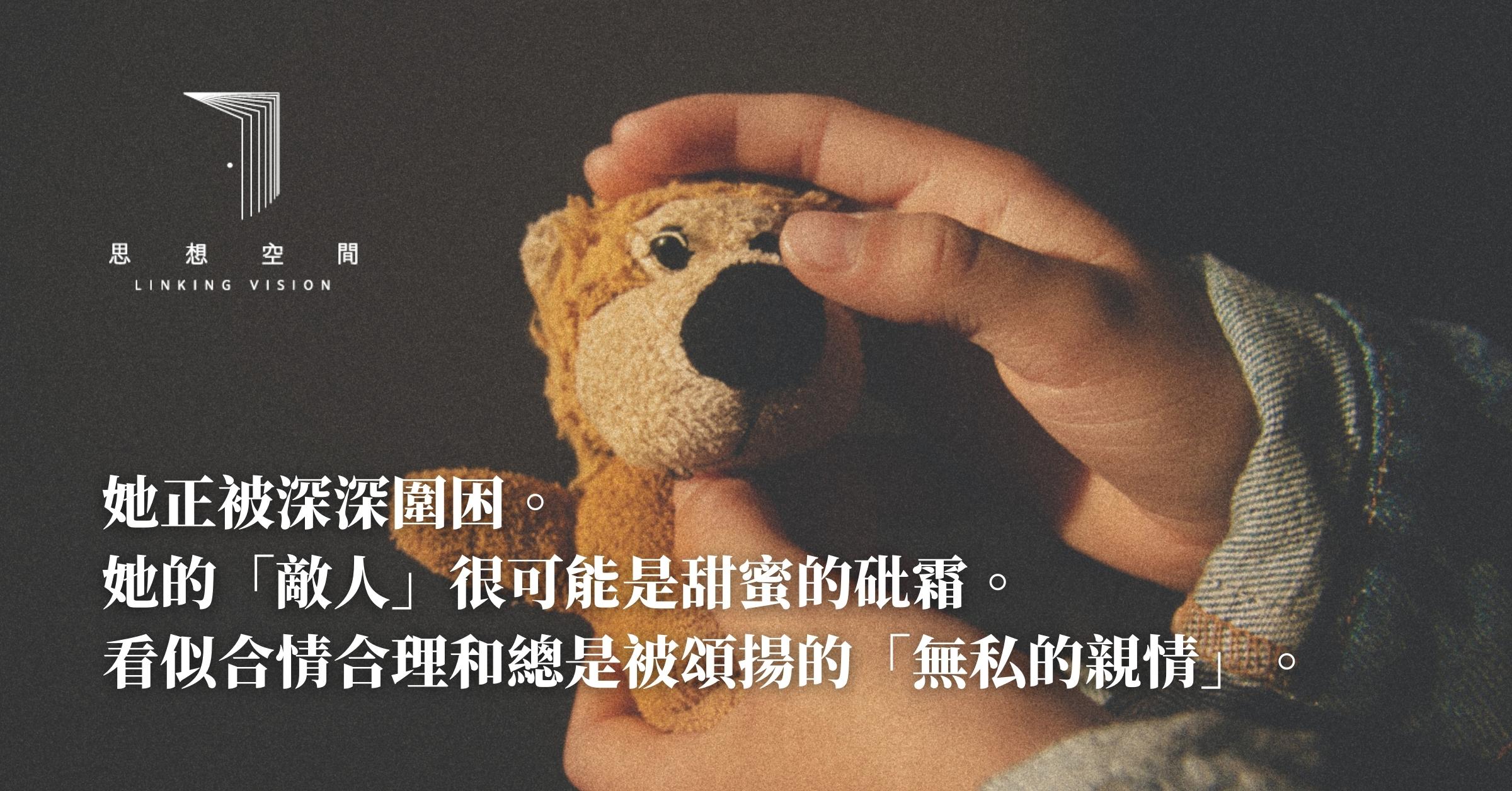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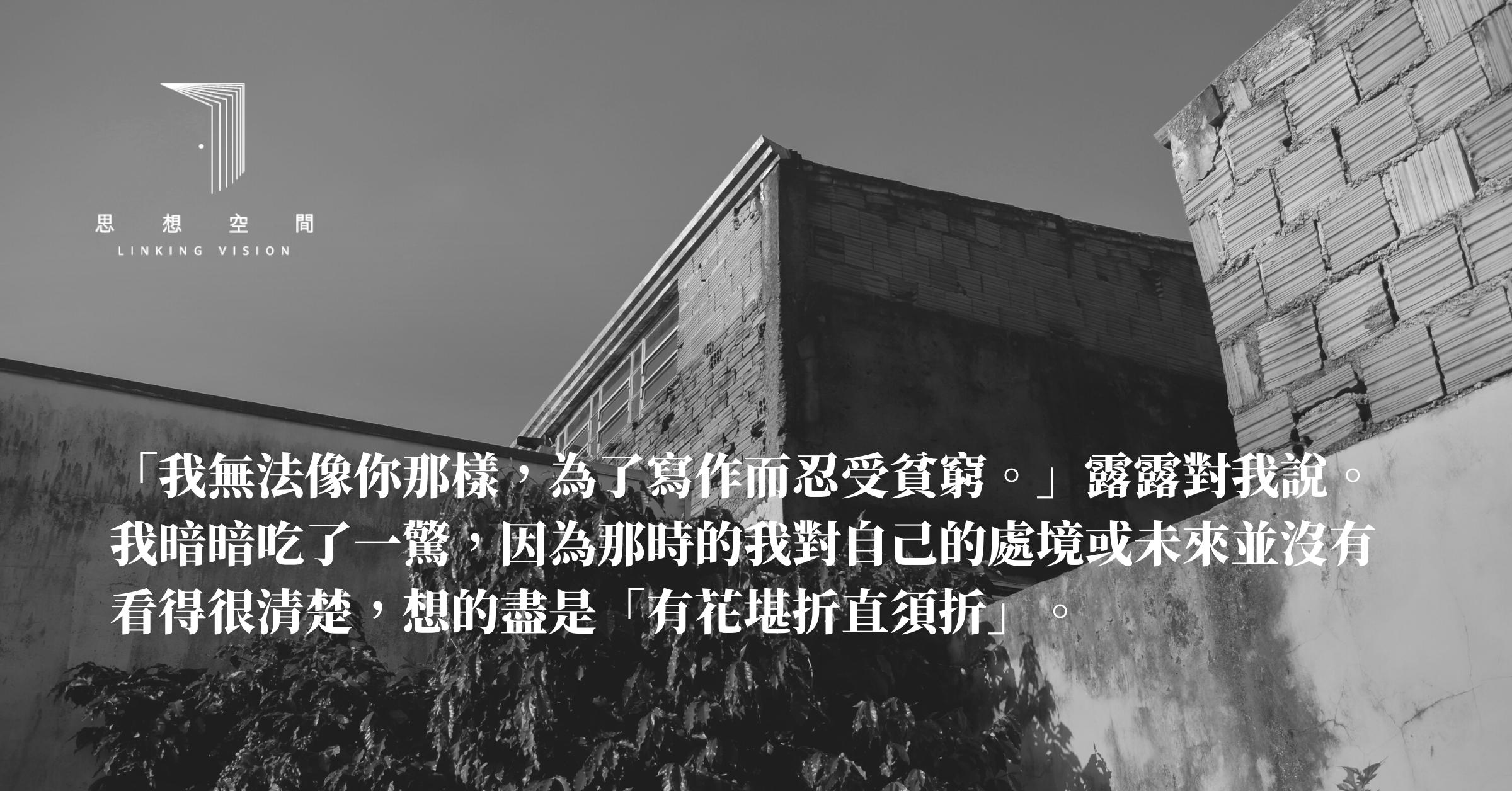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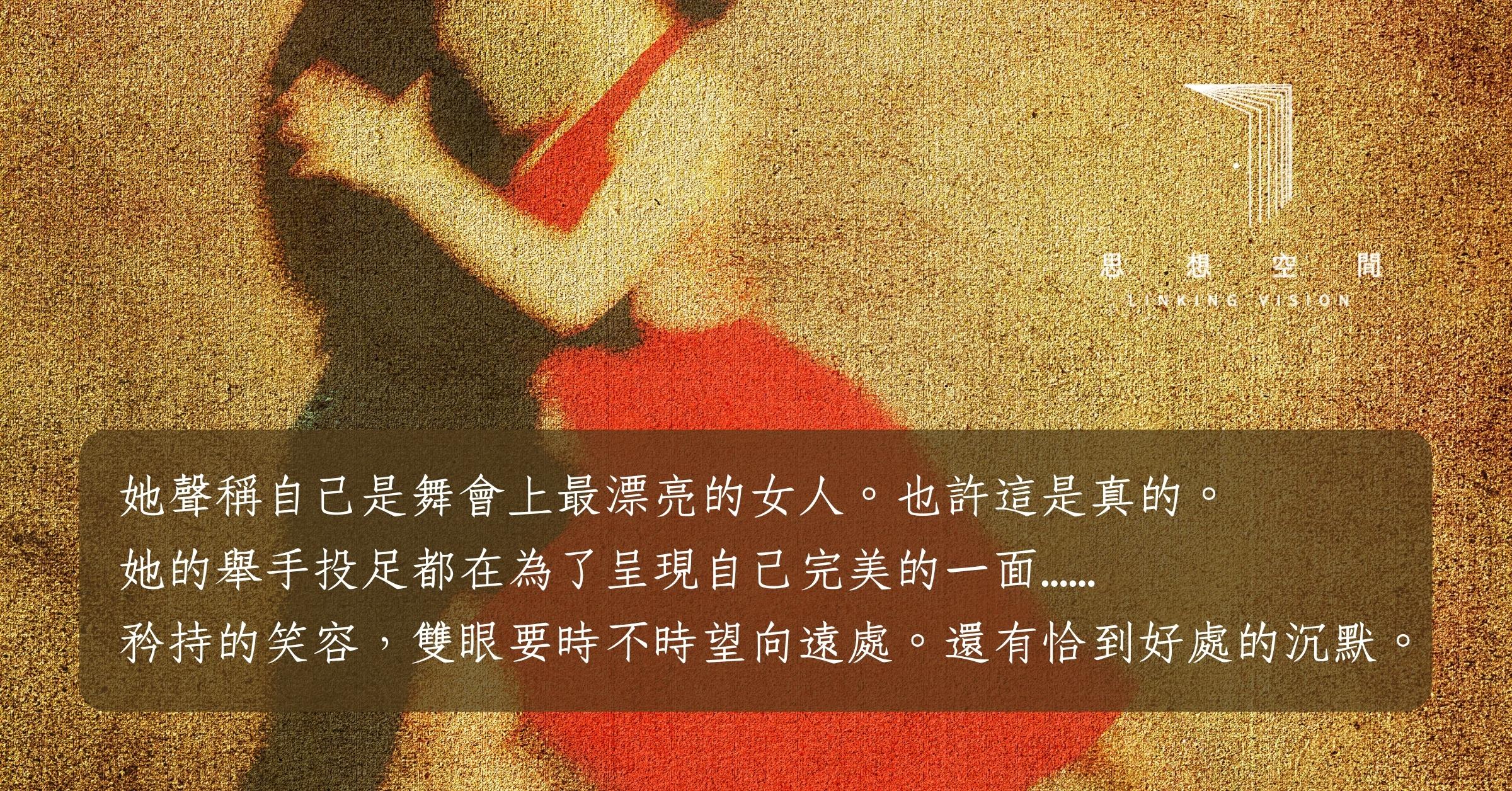
在廣場舞盛行以前,這裡的女人跳的是交誼舞。男人也跳,他們牽著女人的手,挽著她們的腰,和她們一起在公園的樹蔭下扭呀扭,轉呀轉。我的房東吳阿姨每天晚上都在北土城公園跳舞。她的房子就在公園後面,從公園的最深處沿著斜坡走到盡頭就能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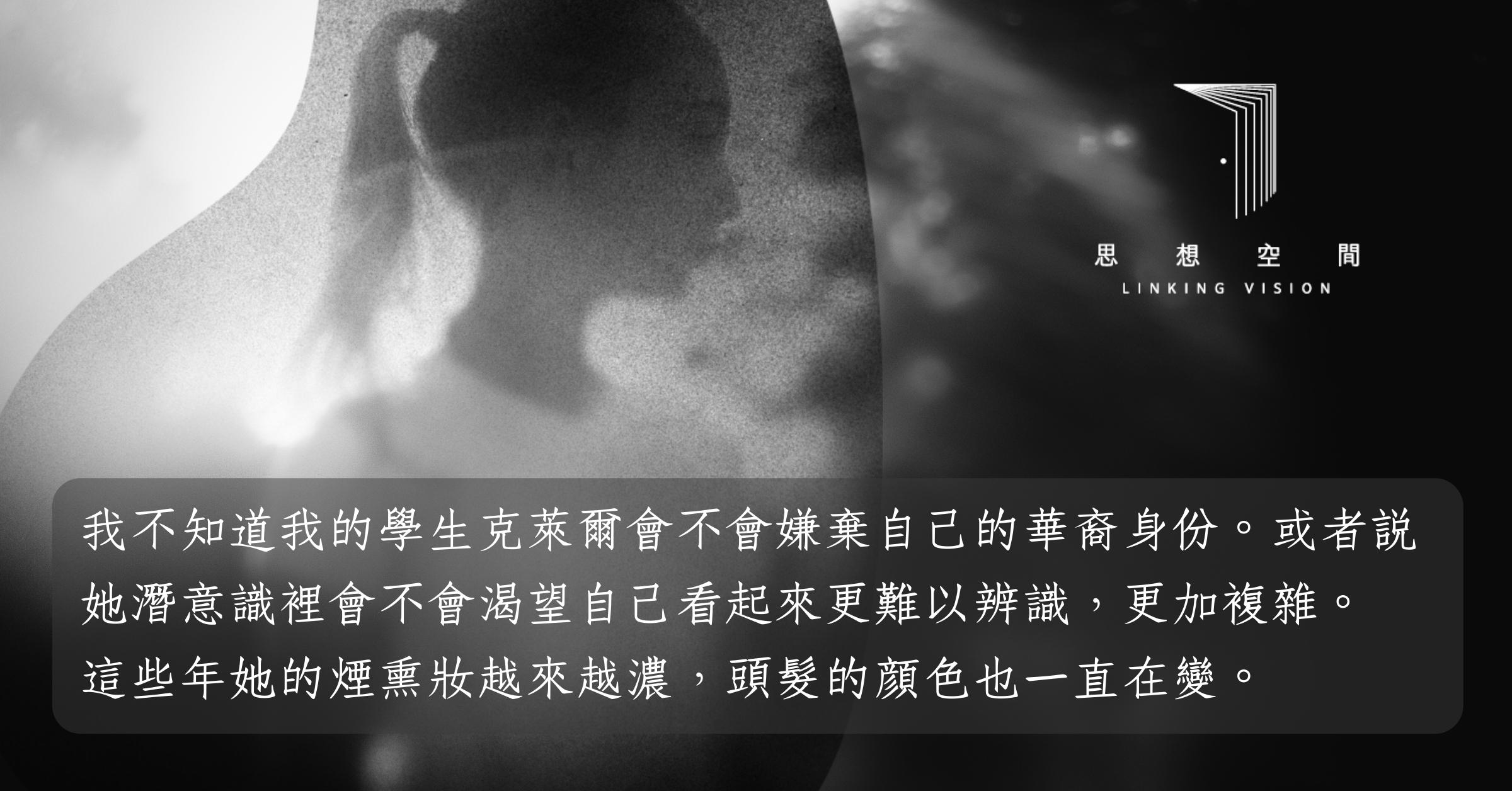
這樣的中國孩子在我們的學校和教會裡能見到不少。她們大多是女孩,被重男輕女或無力繳付超生罰金的父母拋棄後暫時寄居在孤兒院,直到有一天被某個善良的西方家庭認領,從此在異國他鄉開始新生活,除了無法改變的五官和膚色以外,思維、品味和言談舉止都是「西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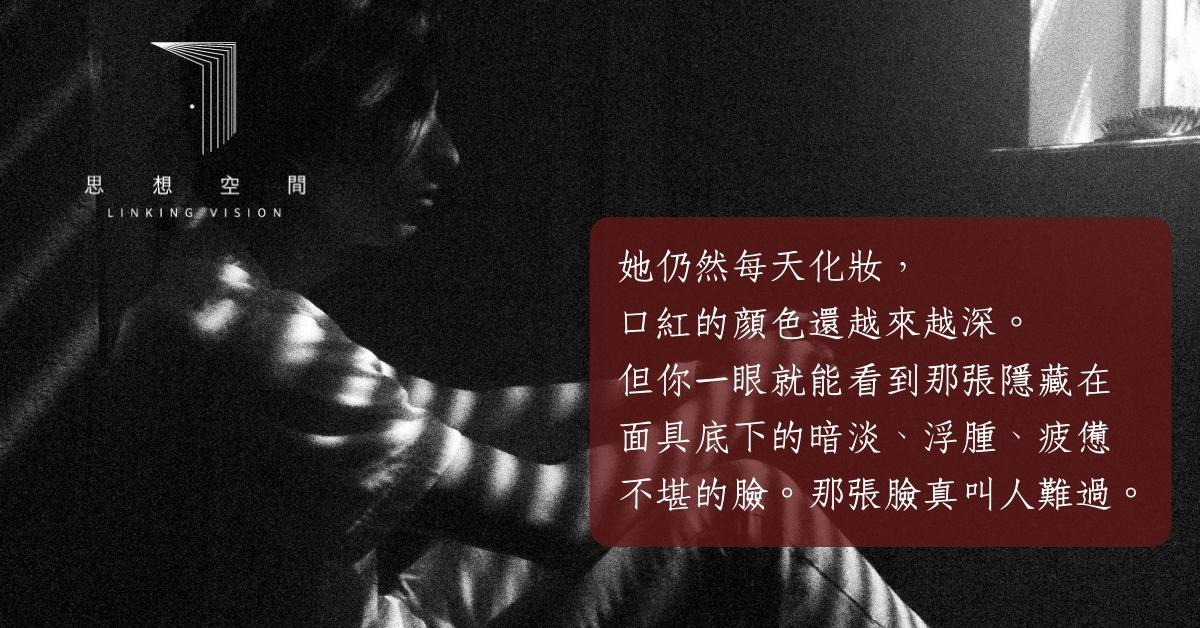
我們這些外國人總是容易多愁善感。我們輕易就會沉浸在對往昔的追憶之中。之於我們,從前與現在不只是關乎時間而已。當我們回憶起從前時,我們對所在的感知變得異常敏銳。我們能聞到某條街道的氣味,能感受到曝曬在赤道的日頭下的刺痛感,耳邊會響起宣禮塔的召喚和混雜著幾種語言的交談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