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雪虹(思想空間專欄作家)
我的朋友愛瑪在臉書寫下這段話: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這個小不點來到我們的家。她是第一個叫我們『媽媽』和『爸爸』的。二十六年過去了,我們將繼續蒙福。收養紀念日快樂,索菲亞。」
愛瑪還分享了索菲亞幼年的照片。照片中的索菲亞看起來剛滿周歲,頭戴一頂藍色的漁夫帽,帽子上別著三朵漂亮的菊花。她張開雙臂,快樂地笑著,抬頭看著鏡頭外那個正在逗弄她的人。
除了索菲亞,愛瑪和她的丈夫還領養了茱莉和克萊爾。三個女孩都來自中國南方。幾年前,當我在希望國際學校教中文時,克萊爾是我的學生。那時候,索菲亞和茱莉已陸續回到美國上大學。漢語對姐妹仨來說只是一門可有可無的外語,畢竟她們不需要以中文維生,而且中文學起來又是如此地困難。
初級班學的不外乎就是如何問路、購物、談論嗜好之類的。課堂上,克萊爾腼腆、拘謹,看起來總是缺乏自信和熱忱。偶爾她還會忘了交作業。她是那種被動,甚至總顯得意興闌珊的學生。面對她,你很容易感到沮喪和受挫。不過,也許她真的已經盡力了。誰知道呢。
這樣的中國孩子在我們的學校和教會裡能見到不少。她們大多是女孩,被重男輕女或無力繳付超生罰金的父母拋棄後暫時寄居在孤兒院,直到有一天被某個善良的西方家庭認領,從此在異國他鄉開始新生活,除了無法改變的五官和膚色以外,思維、品味和言談舉止都是「西式的」。
大人們很容易對她們有所期許。你的根在中國,你應該學好中文,他們會這樣說。失望透頂的老師會斷定她們故意不認真學習,認為她們想擺脫「中國人」這個難堪、沉重的身份。甚至有傳聞說孤兒院的人曾叮囑她們到了國外別再說漢語,否則會被送回中國。
我只和克萊爾單獨聊過一次。那天她難得興致很好,告訴我她出生在福建省,原名是「小花」或「小華」。當時的我有點過於謹小慎微,沒有問她想不想到福建尋根,想不想了解自己的身世。我不確定「尋根」對她而言有多重要,究竟意味著什麼。
許多年後,我看紀錄片《尋》,突然想起克萊爾和學校、教會裡的那些中國孩子。《尋》講述的是三個被美國家庭收養的中國女孩通過基因檢測發現她們是表親後回中國尋親的故事。那是女孩們第一次回中國。她們回到當初被遺棄的地方,回到撫養她們的福利院,拜訪曾經照顧她們的保姆和那些可能是她們親生父母的夫妻。旅途交織著疑慮、悲傷、慨歎和歡樂,那是我永遠無法感同身受的。
我曾在丫曳鎮聽聞類似,也更富有戲劇性的故事。我母親有一個很要好的馬來朋友——普蒂(Putih直譯過來就是「白色」)。普蒂的皮膚又白又嫩,甚至比許多華人還要白皙。一直要到她結婚生子以後,她才發現原來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華人。當年她的父母因為貧窮和生養太多孩子而將她送給了一對馬來夫婦。幾經周折,普蒂終於找到了親生父母,三個人抱頭痛哭起來。怪不得她那麼白,原來是華人!母親為普蒂能尋找到親生父母而感到高興。這件事令人想到電影《白色通行證》裡那個膚色淺得足以被人認為是白人的克萊爾。克萊爾其實是混血兒,自幼被兩個白人姨媽撫養,後來嫁給一個富裕的白人男子。為了更好地融入白人社區,她甚至刻意表現出對黑人的嫌惡。
我不知道我的學生克萊爾會不會嫌棄自己的華裔身份。或者說她潛意識裡會不會渴望自己看起來更難以辨識,更加複雜。這些年她的煙熏妝越來越濃,頭髮的顏色也一直在變。棕黃色,淺金色,紅色,紫色。乍看之下你會以為她是菲律賓人或馬來人,仔細一看又有點像南方女孩。總之就是個看似特立獨行的女孩。
在中國的頭兩年,總會有人以為我是馬來人。不是因為膚色的緣故。我看上去一點都不像馬來人。我想那時候有很多人還不太了解東南亞華人這個群體。後來開始有人以為我是韓國人、日本人、香港人或台灣人。這很有趣。我不厭其煩地解答人們的各種疑問——你們過春節嗎?你們吃餃子嗎?為什麼你的漢語那麼流利?中國和馬來西亞,哪個比較好?歡迎回到祖國,最後對方會友好地這樣說。
這幾天,夏木、漢娜和我在廈門旅行。我對廈門知之甚少,對這趟旅程也沒有任何期待。但很快我就發現自己像是在進行一場尋根之旅,儘管我的根在泉州的永春縣。路邊的榕樹、棕櫚樹和九重葛使我有種置身南洋的錯覺。吃著那些熟悉的食物——芋頭煲、五香肉卷、花生湯、炒米粉,我感慨地對夏木說原來我真的是福建人啊。
還有鄉音。我幾乎是迫不及待地想跟人用閩南語交流,看對方是否聽懂我說的話。我甚至還用蹩腳的閩南語唱了兩首閩南老歌。在博物館,我會逐字默念《聖經》封面上的白話字。那是一八四零年代抵達廈門的美國傳教士羅啻和打馬字、養雅各等傳教士創造的以拉丁字母連綴切音的閩南語白話字。這樣做的時候,我腦海里浮現的是我的外公和外婆,以及一輩子生活在馬六甲,每個星期天都會到宏偉的殖民風格的基督教堂做禮拜的姨婆們。
旅行還沒結束,我們就已經開始籌劃明年冬天回到這裡了。我們還要到永春去。夏木比我更喜歡廈門,而我們也早已厭倦北京。他笑說他最喜歡福建女子,他自己就是個福建女婿。這裡的一切都使他感到親切。這個北方佬可喜歡雞同鴨講了,一點都不害怕出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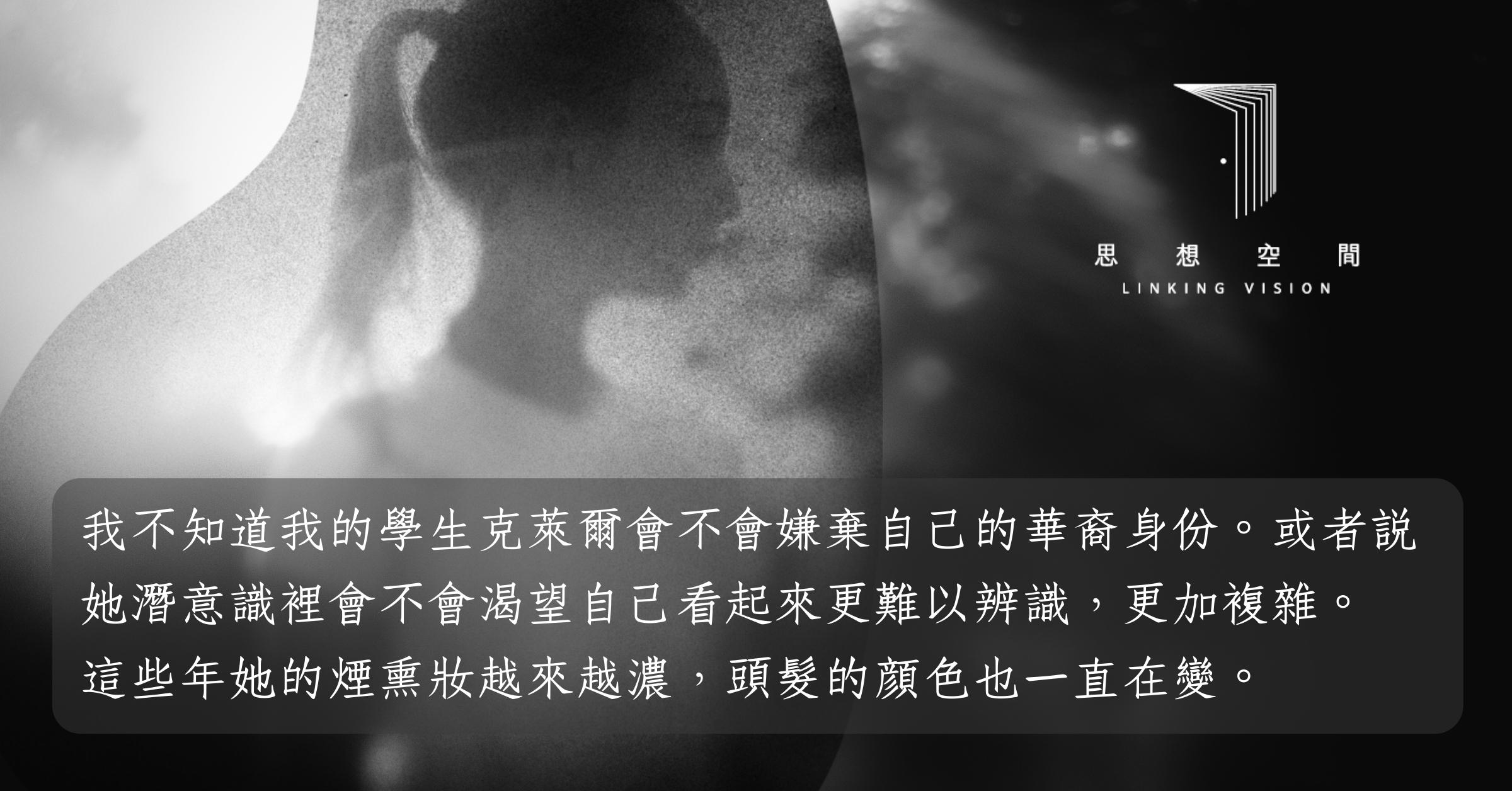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