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雪虹(思想空間專欄作家)
這兩年我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醫院。先是夏木生病,然後到我。最初夏木去的是朝陽醫院,但由於那裡的醫生拿他的巨大腦動脈瘤沒辦法,我們便改為去以治療心腦血管疾病著稱的宣武醫院。是放射師和一位的士司機建議我們這樣做的。當那個年輕的放射師從電腦屏幕上看到夏木左腦正中央那顆如黑洞般神秘、幽深的動脈瘤時,她不假思索地就建議我們去更好的醫院;而那位的士司機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的母親也得了腦動脈瘤,不久前才接受血管內介入治療。
到處都有人在炫耀。人人都清楚得很,要想(迅速地)獲得成功,你得要有「關係」……「哥兒們」。「老鄉」。「同學」。「朋友」。「導師」。那些才是可靠的人
總是有人給我們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建議。也許這是因為我們倆看起來不夠靈光(世故?聰敏?)的緣故。我那熱心腸的朋友瑩瑩也這樣做了。瑩瑩不信任這裡的醫生。她說自己險些就上當,差點要在一個醫生的哄騙、恐嚇下做一場不必要的手術。還有,她也受不了醫院的黃牛黨和醫生的漠然。所以她建議我們回馬來西亞動手術,因為那裡的醫生更可信,更值得我們託付生命。
夏木的父母也不怎麼信任醫生。許多年前,夏木的父親入院動手術,麻醉師曾向他們索要額外的兩百塊錢。那次經歷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陰影,以致當他們聽到朝陽醫院的醫生說夏木今後只能和他的動脈瘤共處時,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質疑醫生。
「他們一定是想訛詐人!」
「他們的醫術肯定不行。」
我在宣武醫院認識了一個從青海來的男人。他的妻子和夏木在同一天動手術。他沾沾自喜地告訴我他花了一千塊託人才成功掛到張鴻祺的號。張鴻祺是赫赫有名的神經外科專家,常常你會看到他出現在神經外科新大樓的大屏幕上。當那個青海男人說出「張鴻祺」時,周圍的人都露出羨慕的神情,饒有興致地聽他分享求醫經歷。那是散發著金錢和特權的氣味的故事。我熟悉那些故事,卻一次又一次地因為它們而感到不適。它們時時刻刻都在提醒你這裡的遊戲規則,還讓你冷不防地就心生疑懼,深怕自己錯過了什麼,做出了魯莽、錯誤的決定。
到處都有人在炫耀。人人都清楚得很,要想(迅速地)獲得成功,你得要有「關係」。你得有個領路人或引薦人。「哥兒們」。「老鄉」。「同學」。「朋友」。「導師」。那些才是可靠的人。你最好活躍一點,遊走於各種場合——飯局、講座會、觀影會、酒會、朋友圈。那些不再當記者,轉行學人類學或寫作的人,他們學的似乎是時髦的人脈學;而「文學圈」處處瀰漫著危險、腐朽的味道,稍不留神就成了形形色色的幫派的混居地。
在我即將入院動手術時,我參加了一場為娜娜舉行的歡送會。娜娜是我的德語班同學,很快她就要搬到法蘭克福了。餐桌上,坐在我旁邊的小敏建議我去協和醫院或北醫三院,因為那裡的婦科更好,名氣更大。
「你需要的話就跟我說,我幫你掛號。」小敏在國家機關工作,經常聲稱自己有各種「關係」。「過硬的關係」。
我沒有聽從小敏的意見。幾天後,我按約定回到中日友好醫院的國際部。一切都很好,清幽的庭院,友好的護士,還算舒適的單人病房。但很快這種踏實、無所掛慮的感覺就被擊碎了。
一直要到我徹底甦醒過來,我才感受到自己的憤懣與疑慮。我掀開白色的棉被,看著那具赤裸的軀體。空氣渾濁、悶熱,它冒著汗,又黏又濕。
在《手術知情同意書》上簽名後,醫生向我和夏木介紹了「腔鏡用帶密閉鞘粉碎取物袋」。這是一種能在不殘留任何碎屑的情況下取出病灶的醫療器材,它被裝在一個淺藍色的大盒子裡,看起來就像小時候過家家玩的醫生套裝。這個「玩具」的價格是四千八百三十人民幣,而且不在保險理賠範圍之內。我的醫生並沒有強迫我們買下它,她只說有些病人是為了以防萬一才使用它。如果切除下來的肌瘤帶有癌細胞,那麼用這個袋子就能防止癌細胞殘留在子宮裡。在聽到「癌細胞」這個詞後,我和夏木便戰戰兢兢地帶著信用卡到樓下醫院的藥房買了一個「淺藍色的大盒子」。
傍晚,一個中年男人推門而入,鄭重地向我們介紹自己。他是我次日手術的麻醉師。在問了幾個例常問題後,他問我是否要在手術後使用鎮痛泵。鎮痛泵的價格是一千多,也不在保險理賠的範圍之內。和主治醫生一樣,他也沒有強迫我們使用,只是告訴我們剛剛有個女人因為耐痛力較弱而囑咐他一定要記得為她準備鎮痛泵。「您考慮一下,要的話就在手術前告訴我。」他說。
第二天,躺在手術室外時,我託推我進來的醫護人員找到了麻醉師。我告訴他我需要鎮痛泵。他突然壓低聲音,「您昨天不是說不要嗎?您想好了?」隨即拿出一份文件,讓我在上面簽名。
「我昨天沒有說不要,我只是必須先了解那是什麼。這上面寫著什麼呢?我的近視很深,看不清楚。」
「本人同意使用術後鎮痛泵,並已了解可能發生的併發症和風險。」聽他讀了那個句子後,我便在那張紙上草草地寫下我的名字。
一直要到我徹底甦醒過來,我才感受到自己的憤懣與疑慮。我掀開白色的棉被,看著那具赤裸的軀體。空氣渾濁、悶熱,它冒著汗,又黏又濕。我的身體正在被一堆東西箝制、侵佔。電極片、導尿管、引流管、靜脈留置針、壓脈帶、指夾。它們在對我做什麼?
為什麼沒有人給我穿上衣服?
為什麼醫生讓我們買那個藍盒子?
那個麻醉師,為什麼他突然壓低聲音說話?他在掩藏什麼?
這麼多的中成藥,它們到底有沒有用?
我是不是不該來這裡?我是不是應該聽小敏的話?
回想起來,那時的我一定是有點難受,所以才那樣沮喪。我不應該滿腹牢騷。就像夏木常常說的,我們應該相信醫生。我們只能相信他們。
究竟我的這些疑懼和不信任感來自哪兒?
小賈臉上流露出的自信與樂觀是我許多中國朋友從來沒有的。它們在告訴我有那麼一小群人和多數人是不一樣的。彷彿他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我突然想起十七年前的一件極其微小的事情。那是深秋,我搬到天津的幾個月後。在來中國以前,我聽說過太多關於「黑心商人」的報導和傳說,有的簡直是駭人聽聞——假雞蛋、紙箱製成的包子餡、被循環再生的衛生巾。後來還有地溝油、假酒、羊尿貓肉、注水肉。那時候,在我們這些外國人眼中,這個國度總是既迷人又危機四伏。
我在立交橋底下的水果攤買了一些冬棗。那是我第一次吃冬棗。很快我便發現不遠處的水果攤賣的冬棗比我買的更便宜。一種受騙、被剝削的感覺瞬間湧上來。
「他不一定騙你。冬棗有不同的品種,不同品質的價格也不一樣。」當我對一個中國朋友抱怨時,他說道。
多麼簡單的道理。不管怎樣,後來我的確嚐到了不同品種的冬棗。不過,與此同時我也認識了「糖精棗」。
時過境遷,那些殘酷、帶有荒誕意味的假冒偽劣商品似乎再也不像從前那樣使我感到好奇和警惕。我在醫院裡的那些幼稚的牢騷也無關緊要了。此時此刻縈繞在我心中的是關於信任感與特權之間的關係。那才是我真正關心、在意的。在這裡,信任往往伴隨著特權而來,意味著更多的自由和選擇;而不信任則源於對未來無法掌控和不確定性的恐懼。
我還沒有告訴你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在娜娜的歡送會上,當我們談到遠方與理想時,小賈對我們說他的夢想是當公務員。
「以後最起碼也得是個中層幹部,像我姥姥姥爺那樣,」小賈情緒高漲,「當老幹部可好了,看病還不要錢。」
「如果夏木聽到了,一定會說『怪不得我們看病這麼難』。」我說。
「等我當公務員了,我就可以躺平,開一家咖啡館,想開店時就開,不想開就不開。」
小賈臉上流露出的自信與樂觀是我許多中國朋友從來沒有的。它們在告訴我有那麼一小群人和多數人是不一樣的。彷彿他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他們之間總是有一些規則與話語是我們永遠不會明白的。他們也並不在乎他人的眼光。當他們洋洋自得地吹噓或炫耀自己所擁有的「關係」時,我腦海中浮現的是「韭菜」、「草芥」、「黑人的命也是命」這樣的詞語。令人困惑的不適感再次湧現。看著那張臉,我差一點就讓這句話脫口而出——「你以為你是誰?」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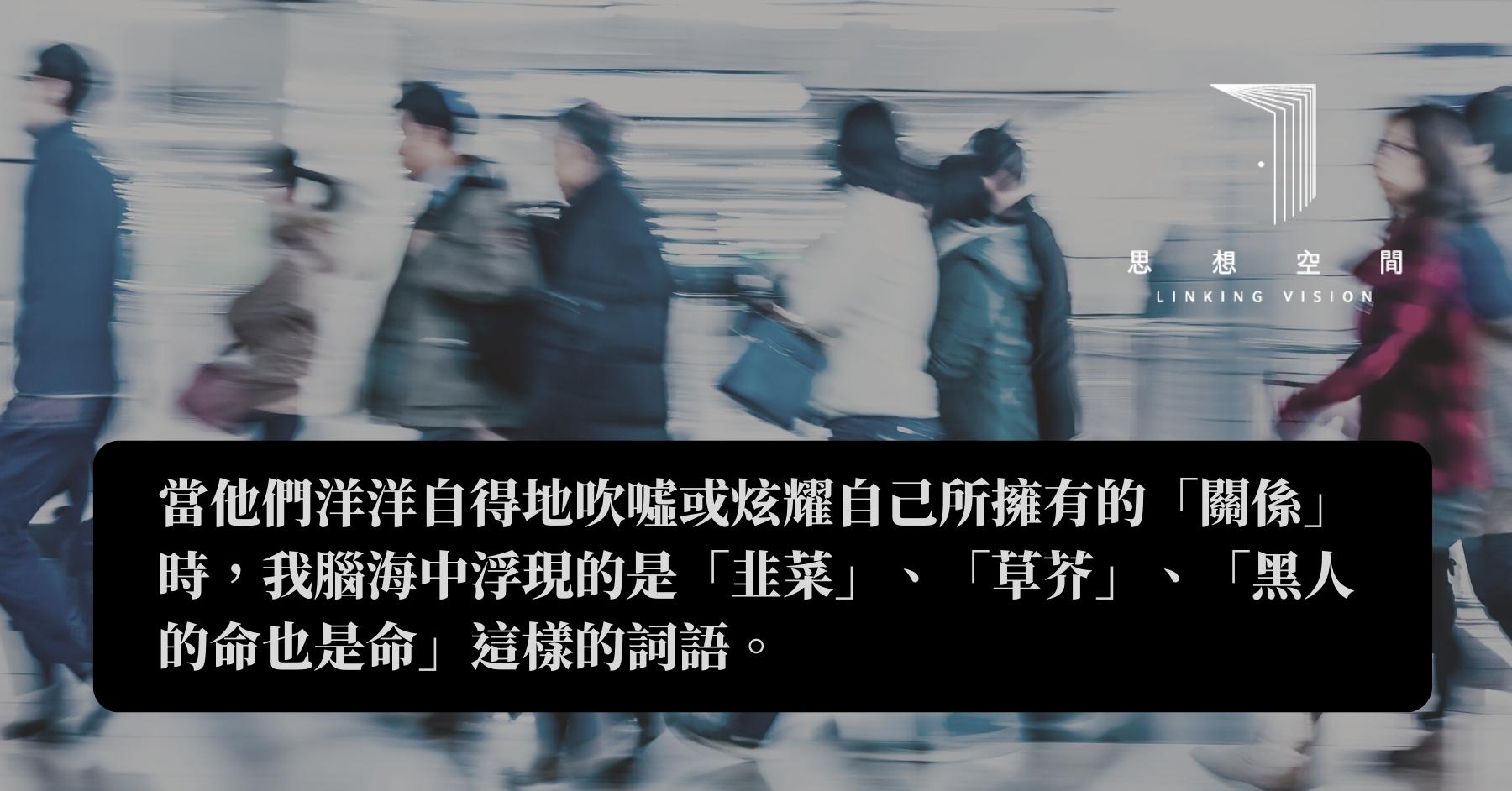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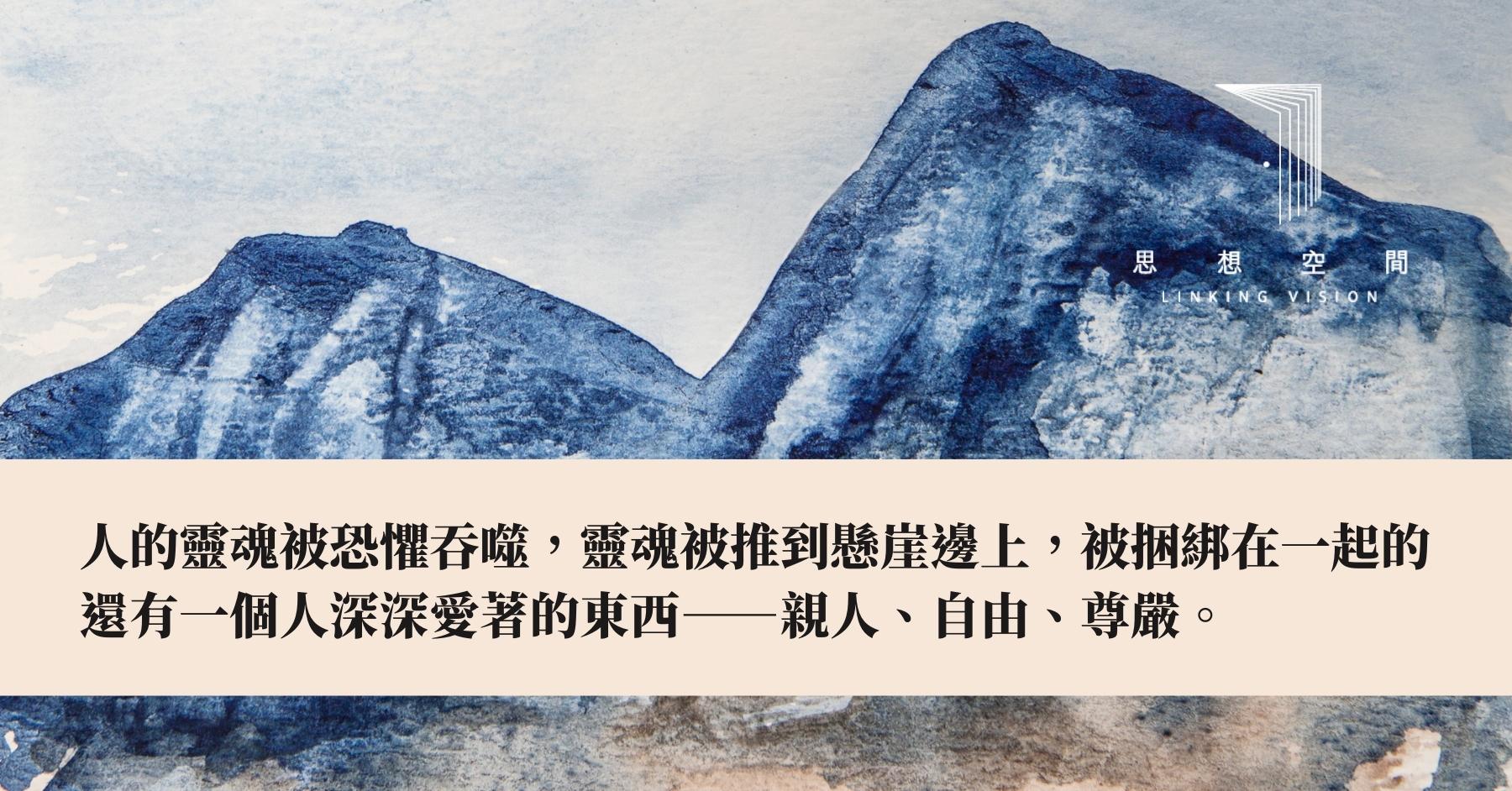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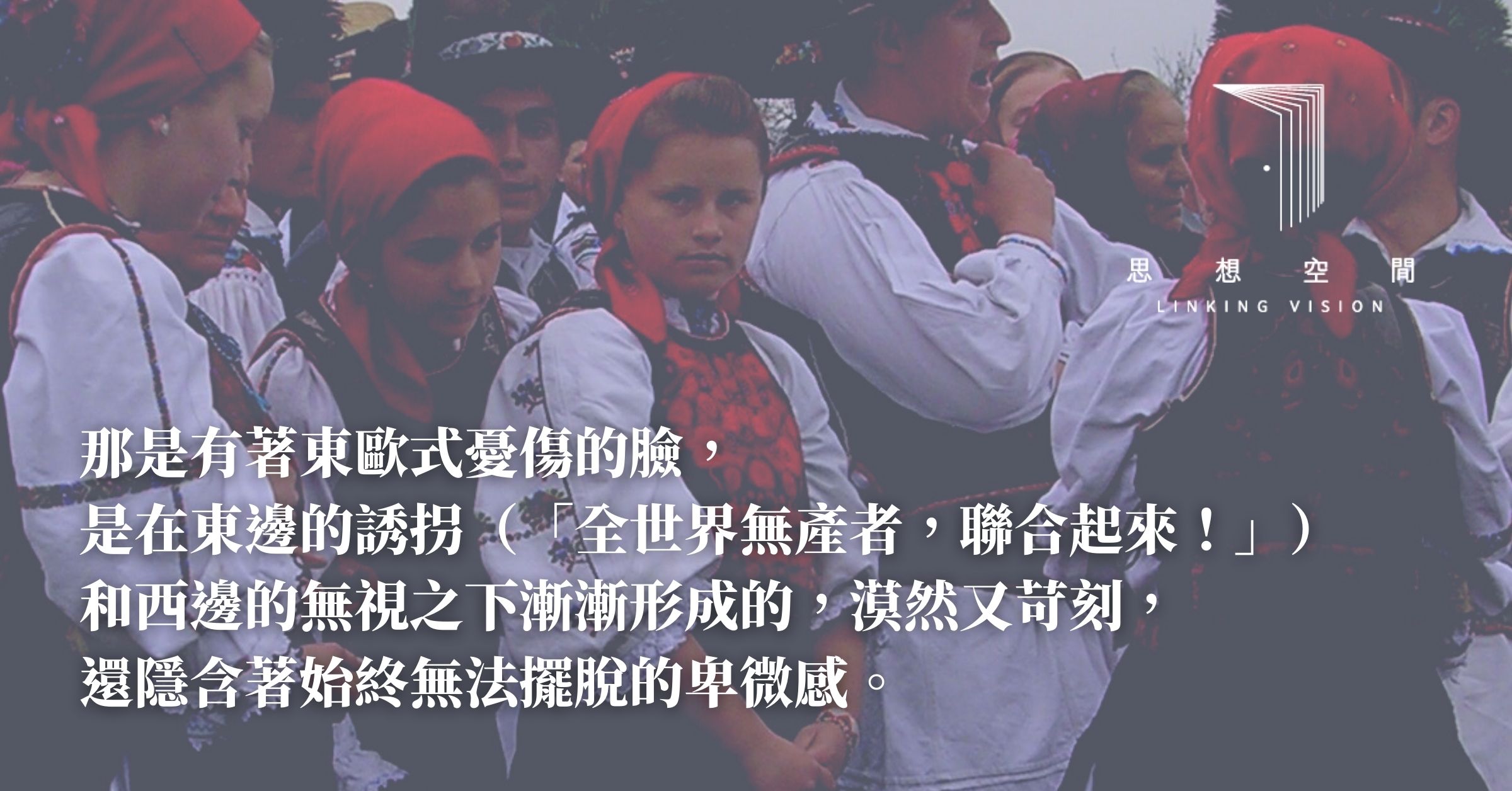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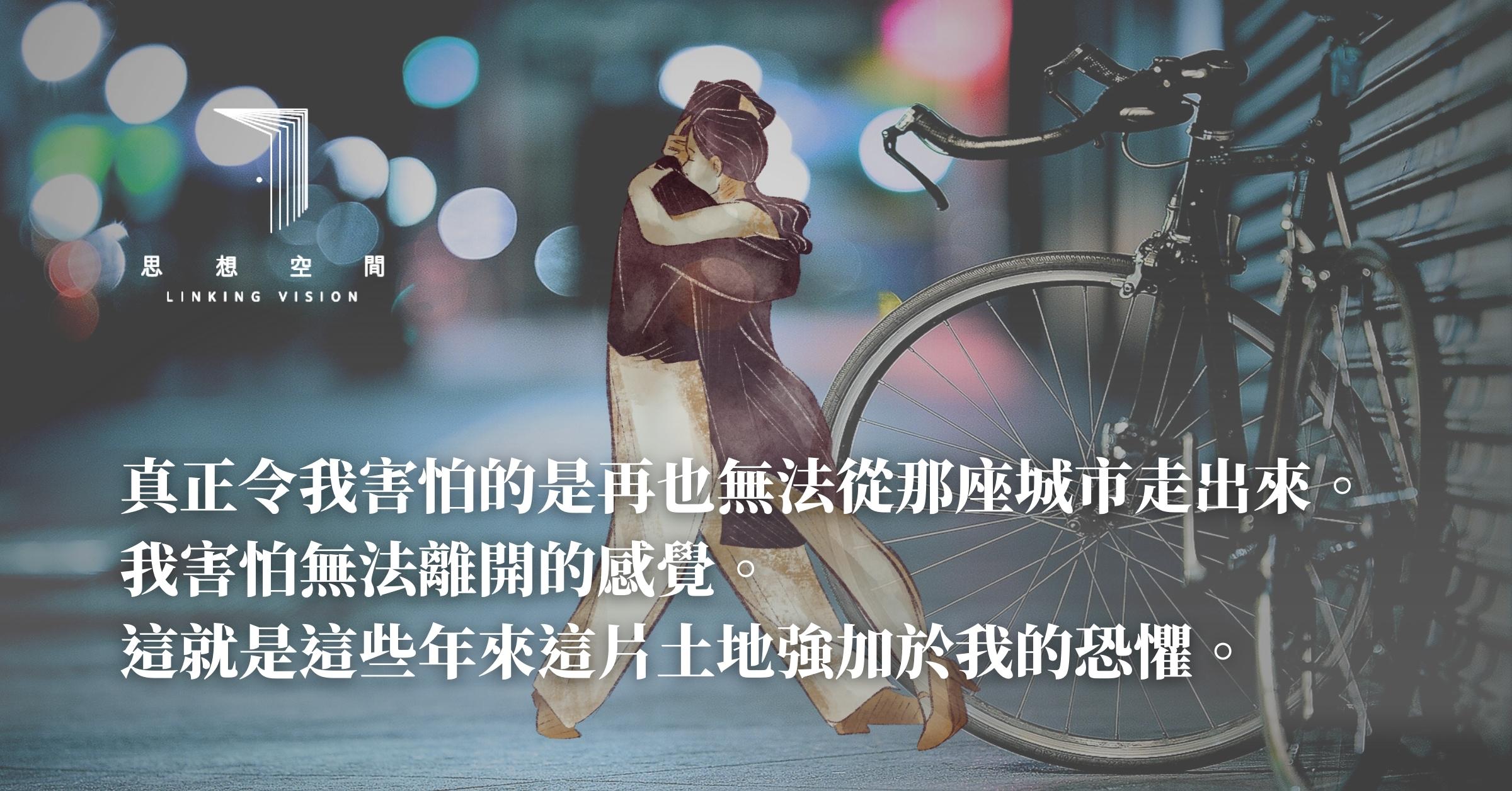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