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雪虹(思想空間專欄作家)
埃絲特和我一樣是「外埠新娘」。「外埠新娘」是我從前(我再也不會這樣了)自嘲時用的字眼。就像「下南洋」那樣,它含有奮鬥、掙扎和苦澀的意味,使我想起烏拉港幽深的河流和丫曳鎮那些絕望的街區。不過我從來沒有在埃特面前提到它。
那時候我還是學生。星期天,我在幼兒托管班服事。我替那些正坐在教堂裡聽牧師佈道的教友照顧他們的孩子。那都是些牙牙學語的寶寶,穿著尿不濕躺在嬰兒床上或是在房間裡橫衝直撞,偶爾會因為肚子餓或以為自己被父母遺棄而哇哇大哭起來。滿兩歲後,他們會被送到隔壁的兒童主日學,在那裡聽聖經故事、玩遊戲和吃餅乾。幾乎不會有人記得自己在托管班度過的那些時光。
所以當埃絲特問喬舒亞記不記得我時,我的臉頰一陣發熱。
「還記得這個姐姐嗎?以前你還是小寶寶時,她照顧過你的。」
你感覺自己無能為力,因為他只會對你說「我們老師說……」,而恰恰你這個家庭教師的任務無非就是執行「老師」的命令。
喬舒亞不會忘記的是往後的歲月。在他上一、二年級時,每週有兩個下午,我會到他的家陪他寫作業和輔導他的中文。暑假時去的次數要多些,還要上英文課。埃絲特可不希望喬舒亞的英文退步。
那時候埃絲特剛將喬舒亞從國際學校轉到公立學校。這是極罕見的。埃絲特這樣做是因為無法容忍老師懷疑喬舒亞患有注意力缺失症。她聲稱喬舒亞只是缺乏耐心和過於活躍。畢竟那是個挺聰明的男孩。她開始批評國際學校的氛圍太過鬆散,公立學校的教育方式才能培養孩子成為一個堅韌、自律、端正的人,而這些美德都是人在幼年時就應當重視的。至於錯過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國際學校自由、多元、具有啟發性和有助於培養孩子的思辨能力的教育,埃絲特一點都不擔心。
「喬舒亞將來可以回馬來西亞或去新加坡上中學,然後到美國上大學。」
「但他還是得學好中文。他將來是要繼承我們的事業的,不能連一份中文合同都看不懂。」
他們有的是自由選擇的餘地。
我第一次去埃絲特的家就感覺那裡像一座迷宮。是墻上的畫作、角落裡巨大的盆栽、屏風和隱藏在一扇厚重的木門後面的起居室使我有這種錯覺。房子坐落在隱蔽、清幽的住宅區裡,偶爾你會見到林丹的父親正在擦洗兒子的跑車,或是目睹林丹和夥伴們張揚地坐上跑車呼嘯離去。那是個令人感到壓抑、恍惚的陌生世界。
埃絲特帶我參觀廚房,向我展示她的嵌入式米箱。
「你看這個米桶,現在中國的設計越來越厲害了。」
真正使我驚訝的是喬舒亞在短短兩週內的變化。他彷彿被捲入到一個洶湧的漩渦之中。在課堂上,他整個人緊張兮兮、坐立不安,卻又始終將手臂交疊放在桌子上。回答問題前,他會像奧特曼發射梅塔利姆光線那樣舉起右臂。他比以前更在乎比賽的結果,也更在意老師對他的看法。
寫作業是最令人抓狂的。抄寫生詞時,老師規定詞與詞的間距是食指的寬度,於是每寫一個詞,喬舒亞都要用食指丈量距離;寫加減號時,他甚至用上了尺子,以致我們倆最後都精疲力盡了。你感覺自己無能為力,因為他只會對你說「我們老師說……」,而恰恰你這個家庭教師的任務無非就是執行「老師」的命令。
就像許多雙薪家庭那樣,住在這幢大宅子裡的還有喬舒亞的爺爺和奶奶。爺爺負責載送喬舒亞上下學,奶奶和保姆則負責全家人的伙食。奶奶還扮演家長的角色,負責和家庭教師溝通(「他們老師說……」),還有督促喬舒亞吃飯、洗澡和睡覺。儘管這是個熱情、友好的老人,但無疑她還是帶給人不少困擾。她總是在我們上課時突然出現,為喬舒亞端來一杯水或果盤,有時甚至像照顧一個三歲小孩那樣餵喬舒亞喝水和替他穿襪子。不僅如此,她對於約束喬舒亞的行為似乎一點辦法都沒有,連她自己也意識到了。
「我就是狠不下心來。」她對我苦笑道。
所有人最終都和這個國家形成一種弔詭的利益共同體。有人說這是一條正在撼動世界的巨龍。人們戰戰兢兢,亦步亦趨,深怕激怒了這頭巨獸。
因為巨額房貸和實現各種目標,埃絲特和丈夫喬治像兩隻跑滾輪的倉鼠般馬不停蹄地工作。他們越來越富裕,和喬舒亞相處的時間也越來越少。如此一來,他們就更依賴老人照顧喬舒亞了。兩個老人倒是樂此不疲。他們已然成了喬舒亞的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漸漸地,埃絲特陷入到一種尷尬的處境之中。為了表達對孩子的愛和愧疚,她一次又一次地給喬舒亞買樂高積木;而為了買那些昂貴的玩具和給孩子更堅實、體面的生活,她又不得不繼續拼搏下去。
埃絲特當然也會想像家裡只有她、喬治和喬舒亞,沒有老人的生活。也許他們並不需要那麼大的房子。也許她能兼顧家庭和事業(黃阿麗:「男人永遠不用兼顧家庭和事業!」)。但很快她便感到進退兩難。
「我也沒想到他們會住那麼久,一住就是六年。」誰都沒有想到當初的幫忙竟然成了沉重的精神負擔。但埃絲特不敢和老人談論這件事。喬治更是難以啟齒。
有時候我會感覺埃絲特在孤軍作戰。她正被深深圍困。她的「敵人」很可能是甜蜜的砒霜。看似合情合理和總是被頌揚的「無私的親情」。那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使人聯想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樣的真理。還有她對財富和強者的崇拜。她推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信仰「勝者為王」,汲汲於在這個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城市(國家?)紮根、攀爬。這一切已然使她這個外來者騎虎難下。
我見到越來越多的「埃絲特」。他們當中有的是「外埠新娘」或「外埠新郎」,有的是中國企業的職員,有的從事的職業與中國緊密相關。他們當然也是聰明、敏銳,充滿奮鬥精神的一群人。與此同時,他們也堅信「適者生存」這樣的法則。所有人最終都和這個國家形成一種弔詭的利益共同體。有人說這是一條正在撼動世界的巨龍。人們戰戰兢兢,亦步亦趨,深怕激怒了這頭巨獸。
我最後一次見到埃絲特也是在一個星期天。那時我剛從教堂出來,正在向車站走去。突然一輛黑色的寶馬越野車停在我身旁。埃絲特從那個龐然大物伸出頭來向我打招呼。我們僅僅是打了個招呼,我甚至沒來得及打聽喬舒亞的近況,我們便分道揚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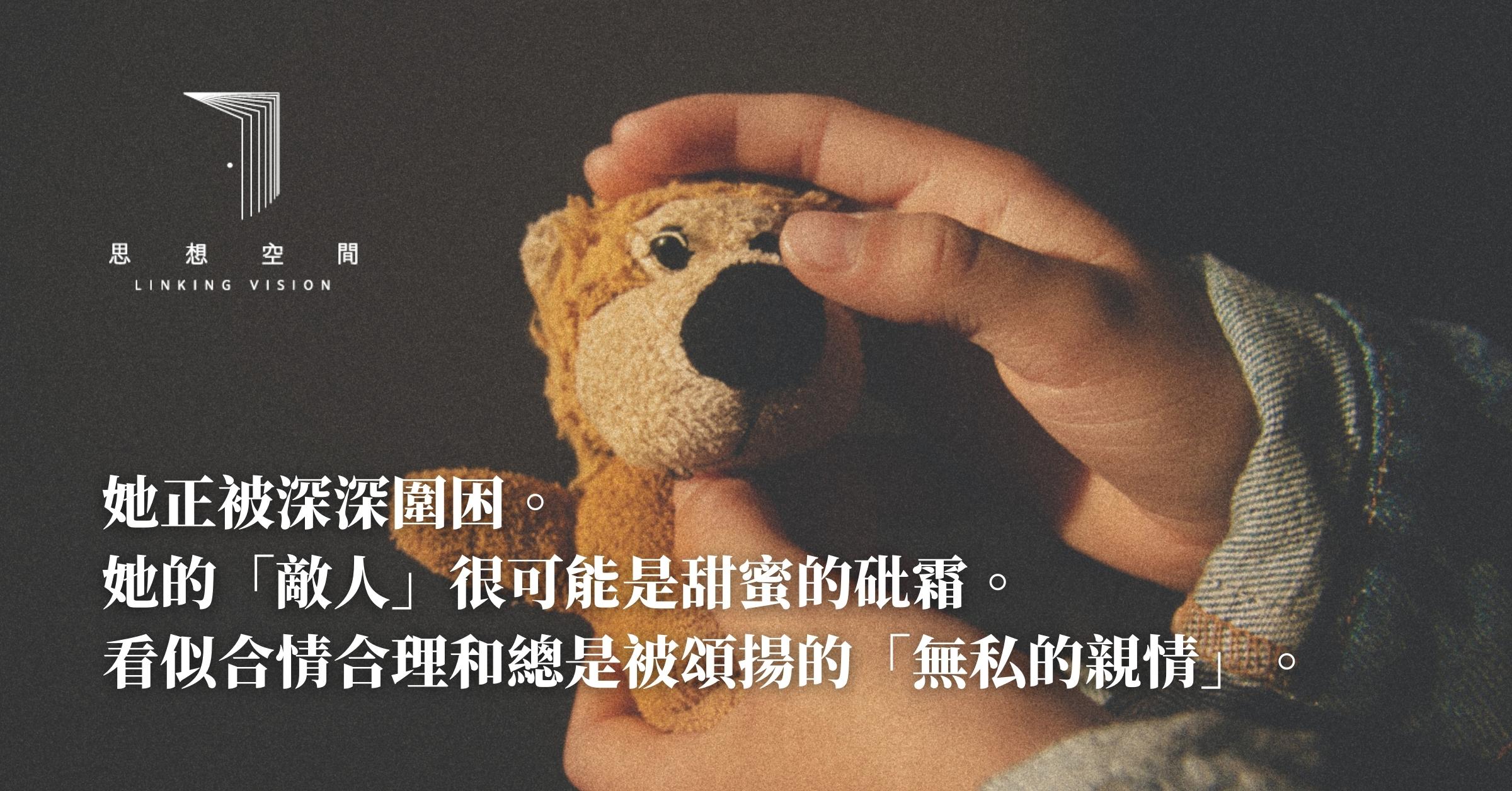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