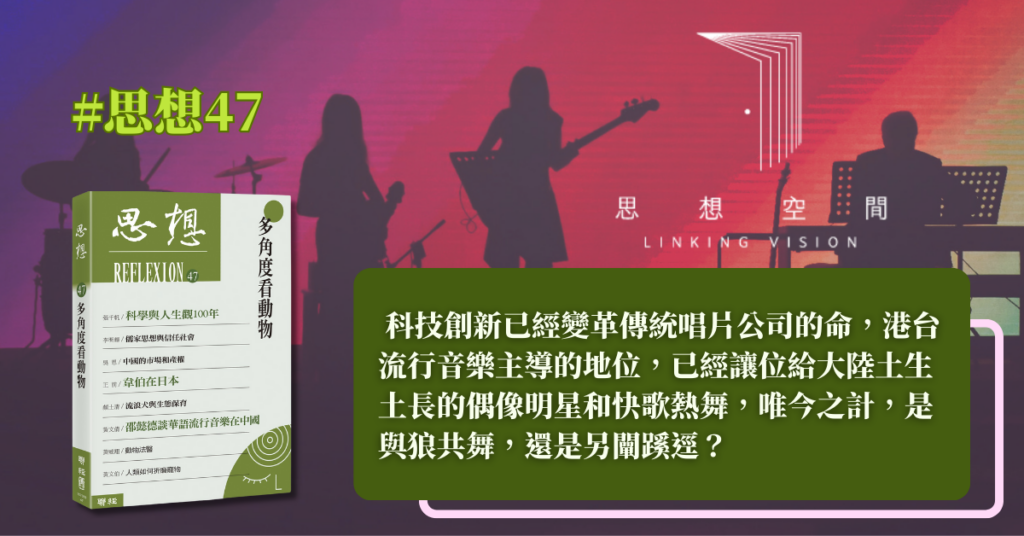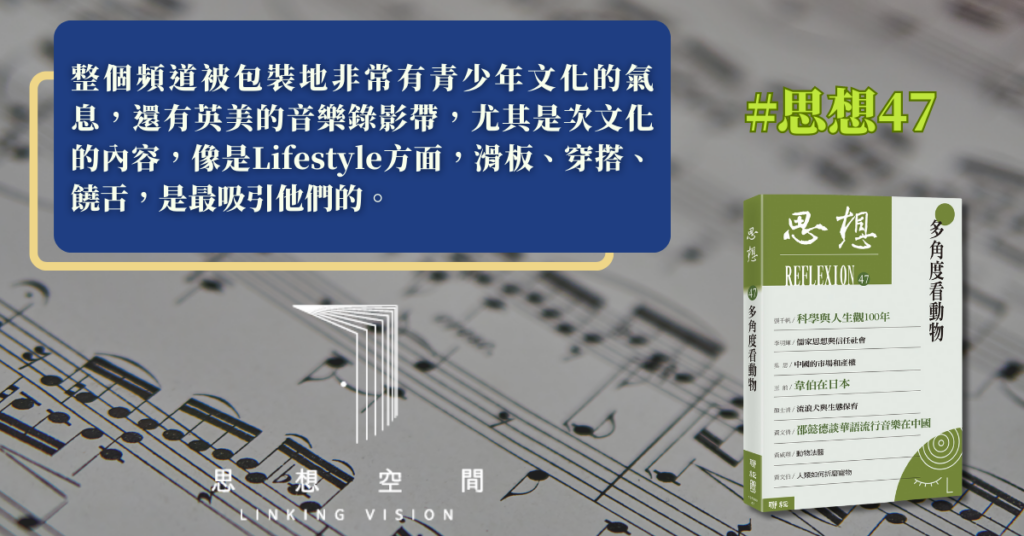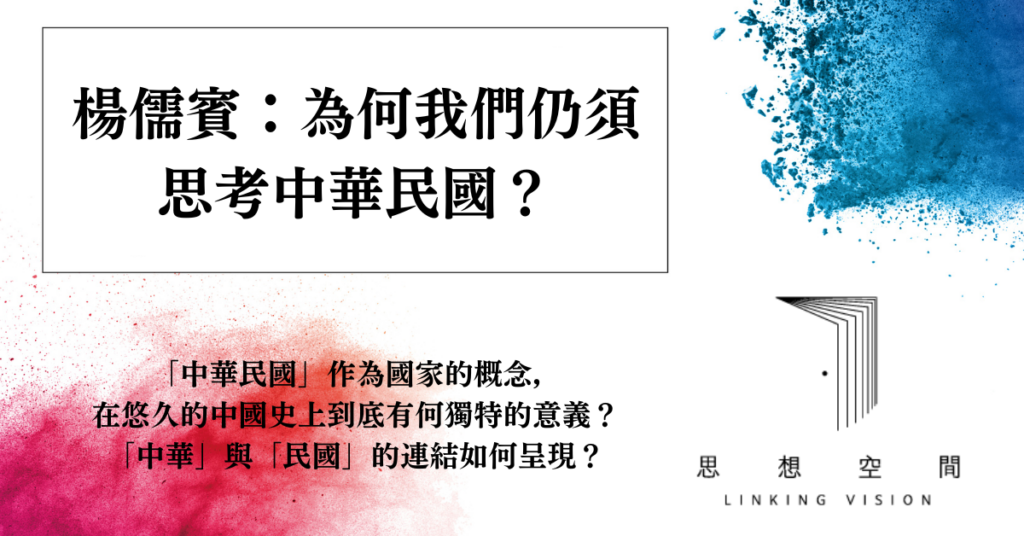文 / 涂航
編按:這是一本知識分子如何歷經政治狂潮,磨煉思想邏輯,堅守或改變理念信仰的專書——這是思想史的路數。但涂航教授更希望從中梳理出更複雜的線索,如陳寅恪的史論如何「痛哭古人」;李澤厚的儒家「樂感」文化如何導向「告別革命」;陳映真的憂鬱如何啟發後革命行動;劉小楓的「海洋性激情」如何接軌古典公羊學說等。換句話說,思想不只是綱舉目張的思辨過程,也牽涉思維主體的癡嗔與愛憎;政治不只是公眾運動或權力取予,也牽涉行動主體的希望與悵惘。更進一步,情感不僅源自個人,也是一種公共意向投射和意象流傳,直通威廉斯所謂的「感覺結構」。
中國大陸在過去四十年所經歷的引人矚目的市場經濟轉向引發了學界對中國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現代性的「重估」。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以空前之姿重塑知識場域和政治想像的同時,毛澤東革命的幽靈卻徘徊不去,以文學敘述、思想爭鳴和記憶政治等諸多形式魂兮歸來,甚至變本加厲地挑戰和嘲弄啟蒙的共識和資本主義的合法性。
自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關於中國已從宣揚世界革命轉向「發展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說法幾乎成為西方學界的共識。在西方觀察家看來,1981年由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試圖對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做最後的歷史裁決,否定極左政治,推動形成發展市場經濟、參與資本主義全球生產的共識。 九十年代以降,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大陸思想界眾聲喧嘩,支持文化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民族主義的呼聲層出不窮,使得整個學界呈顯出告別革命、拒斥烏托邦空想、走向「漸進改良」和「現實主義」的趨勢。
無論是「革命」還是「啟蒙」都是誤入歧途、積重難返的西洋現代性之產物,而唯有回到靈韻猶存的儒家政教傳統方能重鑄共識,以超越性的文明理念來維護政治共同體之存有
在思想分化、理念碰撞的背後,每一種主義的言說都蘊含了獨特的歷史記憶與政治慾望。在自由派看來,從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到群眾運動氾濫的「十年浩劫」,三十年的極左實踐不啻於一連串的人道主義災難,凸顯極權政治的暴虐,因而告別革命、擁抱自由民主乃是歷史正義使然。新左派卻認為,需要區分作為歷史性悲劇的文革和作為解放性理念的文革:激進民主實踐的歷史性失敗並不意味著左翼平等理念的破產。相反,只要壓迫性的資本主義宰制仍四下蔓延,左翼的鬥爭總是未有盡時。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眼中,五四以降的左右之爭凸顯世俗主義之濫觴。無論是「革命」還是「啟蒙」都是誤入歧途、積重難返的西洋現代性之產物,而唯有回到靈韻猶存的儒家政教傳統方能重鑄共識,以超越性的文明理念來維護政治共同體之存有。最後,民族主義的旗手們將毛澤東的革命大業看做是結束屈辱歷史、重建國威、復興天朝榮光的里程碑。將「大國崛起」奉為圭臬的民族主義者因此極力淡化中國革命中有關階級鬥爭、國際共運、以及反傳統主義的激進左翼元素,轉而宣揚社會主義實踐的反帝反殖民色彩。
多有學者將意識形態的兩極化歸咎於不同派系的知識分子所持的基本學理立場和政治信仰之間的巨大差異。例如,許紀霖、張旭東和汪暉等學者認為,九十年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根源在於當新啟蒙運動所持「態度的同一性」瓦解之後,不同學者對於現代性的基本價值「自由、民主、市場、公正、平等」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堅持個人權利優先的自由派希望通過引入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來推進自由和法治進程,而左派則更為強調激進民主和經濟平等,認為毛時代的政治遺產有助遏制跨國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差距和體制性腐敗。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義者關心的則是現代性的倫理規範虧空:失去了宗教靈韻庇佑的世俗國家無法以超越性的價值來塑造國民認同和政治共識。簡而言之,八十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共識崩塌之後,道術為天下裂。思想分化的根本原因在於「道不同不相為謀」。
文化遺民之「遺」,並非陶潛之隱逸出世,而是於禮崩樂壞之際遺世獨立,繼志述事,由此生出自由精神和抗爭意識,成為超越政治遺民的倫理關切所在
作為陳寅恪的「後世相知」者,余英時認為,陳寅恪的遺民情節並非消極避世,而是一種高揚獨立自由的抗爭精神。1927年,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引發眾人猜測。羅振玉等滿清遺老紛紛宣揚王氏殉清一說。早在1924年馮玉祥驅逐末代皇帝溥儀出宮之時,王國維即言明「主辱臣死之義」。
在余英時看來,陳寅恪的泣血之作《論再生緣》,正是繼承了王國維的遺民精神,以文化懷舊來睥睨世俗、質疑政治權威。陳、王二人均身處「新舊蛻嬗之間際」,目睹「不肖者巧者」因「善應付此環境」而致「富貴榮顯,生泰名遂」,內心瀰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對降志辱身的恐懼。王國維身陷北伐戰爭的時代洪流,深恐於長沙葉德輝、武昌王褒生等宿學為國民革命軍槍殺之暴虐,以為革命黨人旦夕將至,因而為避免「再辱」憤而自沉。同理,陳寅恪在解放初期先是因暴風驟雨的土改運動而「領略新涼驚骨透」,繼而諷刺思想改造運動中不惜「塗脂抹粉」、媚俗求全的讀書人,在士人節氣蕩然無存之際,唯有寄情於「明清痛史」、「興亡遺恨」,稱頌陳端生、柳如是等紅妝之奇才異節,方能以傳統守舊與時代革命相抗。在這個意義上,文化遺民之「遺」,並非陶潛之隱逸出世,而是於禮崩樂壞之際遺世獨立,繼志述事,由此生出自由精神和抗爭意識,成為超越政治遺民的倫理關切所在。
然而,余英時的文化遺民說的曖昧之處在於,他對於陳寅恪所懷「了解之同情」是如此深切,對陳氏之興亡遺恨是如此感同身受,以至於陷入了一種基於共情的詮釋學。余氏對陳寅恪的認同實則來於自身的文化遺民情節。然而如此一來,余英時對「摧殘文化」、「侮弄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反而更加義憤填膺。原因無他,正是五十年代初舉國趨新、厚今薄古、文人言必「遵朱頌聖」的時代風潮導致了陳寅恪的痛苦,進而讓同為遺民的余英時唏噓不已。
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士人無時無刻不心繫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天下情懷,因此往往陷入一種揮之不去、無法排解的憂鬱
為何憂鬱這一頗具小資產階級文藝色彩的情狀會成為二十世紀左翼理論家津津樂道、爭論不休的話題?回首馬克思主義革命在二十世紀的旅程,失敗和挫折總是如影隨形。唯其如此,左翼的男男女女深陷理想與幻滅的兩難,在痛斥革命傷感主義之際卻又無可救藥地墮入憂鬱的革命美學——正可謂愈要革命,愈發憂鬱,愈是想擺脫憂鬱,愈發革命。
憂鬱體現在左翼思考的肌理之中,將沉溺化為一種自省,將難以割捨的愛慾化為一種隱晦的執念,在納粹禍亂歐洲、世界大戰與美蘇爭霸此起彼伏、千萬人流離失所的災難年代,在革命已經蛻變腐化的曖昧不明的時空裡,執著地搜尋、捕獲和闡明人類解放的微弱的可能性。
為了進一步闡釋左派的憂鬱症所孕育的美學和政治潛能,本文將視野聚焦於當代華語語境,以大陸和台灣文學為樣本討論亞洲左翼革命與憂鬱症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纏關係。如果說當代西方左翼的歷史經驗與革命意識根植於六十年代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青年造反運動,亞洲左翼的革命情懷則多半源於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毛主義試圖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與歐美資本主義之外構築一種另類的現代性道路,其中包括大眾民主實踐、繼續革命的軍事鬥爭策略,以及反帝反殖民的國際共運視野。這一切都曾經給六十年代的亞洲左翼的鬥爭(尤其是深陷西方殖民霸權、種族壓迫以及軍事獨裁的東南亞地區)帶來思想靈感和理論武器。八十年代初,隨著中國終止「輸出革命」的路線方針以及接踵而至的社會主義轉型危機,左翼烏托邦主義的光環日漸消散。大陸新啟蒙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批判文革暴力,徹底否定激進主義,進而在華語世界的左翼知識群體中產生持續的震蕩。
與西方憂鬱論述所折射的神學—病理學闡釋不同,儒家道德理想主義讚頌憂患意識,將「憂」看做是積極的政治倫理和君子品格。從憂君憂國到憂道憂民,士大夫的憂患意識表現為一種居安思危和危機意識和時代使命感。現代新儒家將儒學思想的起源歸結為一種非宗教的、充滿人文精神躍動的憂患意識之覺醒。
不同於原始宗教對神秘上蒼的恐懼和對命運無常的絕望之感,儒家憂患意識強調人的主體意識:正是因為現世主義傳統下的凡人拒斥上天垂憐,需要擔負起悲憫天地的情懷與拯救蒼生的職責,故而由力不從心而產生的抑鬱之感才會如影隨形。
毫無疑問,對天下蒼生的憂患之情與儒家士大夫兼濟天下的胸懷息息相關。歸根結柢,憂是由於儒家所追求自身和社會的道德完善的理想與現實政治格格不入而產生的存在主義式的焦慮。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無疑是這一憂國憂民情懷的經典寫照。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士人無時無刻不心繫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天下情懷,因此往往陷入一種揮之不去、無法排解的憂鬱。
延伸閱讀:

啟蒙者、自由主義者、左翼作家、保守主義者相互鏈接,從情感政治角度,勾勒當代思想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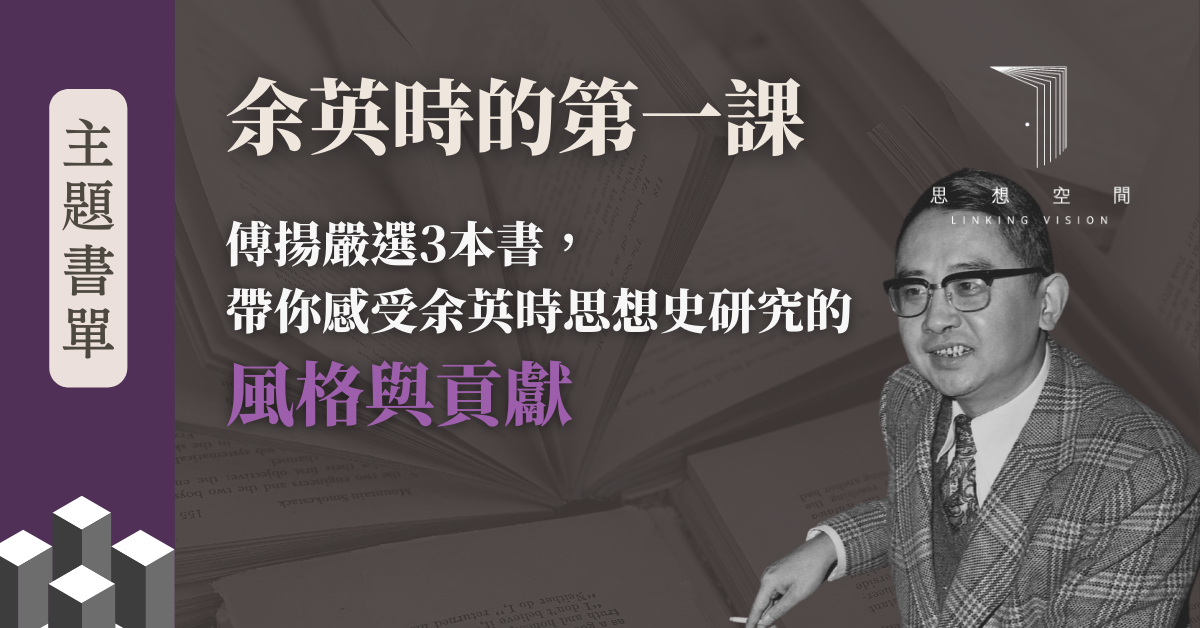
【主題書單:余英時的第一課】傅揚嚴選3本書,帶你感受余英時思想史研究的風格與貢獻

容啟聰:第三勢力與冷戰:由余英時的《香港時代文集》談起
| 閱讀推薦 |
無論是「革命」還是「啟蒙」都是誤入歧途、積重難返的西洋現代性之產物,而唯有回到靈韻猶存的儒家政教傳統方能重鑄共識,以超越性的文明理念來維護政治共同體之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