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宜樺(前任行政院院長)
編者按:2022年,是台灣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結束任務的一年,也意味著台灣首度於體制以「轉型正義」之名進行的工作,將畫下暫時的句點。回望與梳理這一段歷史,有四篇文章格外值得參考:四位作者均是曾經參與、或影響台灣這一波「體制內轉型正義工程」的行動者。
吳乃德2006年發表於《思想》雜誌的鴻文〈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是二十一世紀台灣啟動轉型正義工程的重要文件之一。
吳乃德文出刊後,引發時任台大政治系教授的江宜樺,在2007年以〈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一文回應。江宜樺後於2013年至14年間擔任行政院長,雖未直接參與體制內轉型正義工程(促轉會正式掛牌成立於2018年)運作,但於其任內高度關注轉型正義相關議題;同時,亦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警民衝突中,親身成為體制與社會運動對峙的第一線官員。
另外兩篇文章均曾刊發於端傳媒,其中一篇由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所著,她曾任促轉會早期委員,後於2018年辭職;另一篇由前真促會執行長、現任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所著。
這四篇文章,均發表於這四位學人仍身在「民間」、促轉會尚未成立時。如今,促轉會已屆終幕,回溯四位的思想源流,或許能給我們一些重要的反思,與全新的啟發。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近年來台灣輿論界的熱門議題,尤其在每年二二八紀念日前後,以「轉型正義」為主題的研討會、座談會、記者會及出版品似乎有增無減。今年(編按:2007年)適逢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轉型正義問題的討論,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在這些相關活動中,有的比較嚴肅且有助於我們對轉型正義的認識,譬如《思想》第2期所刊出吳乃德教授的文章(詳見:上篇、下篇),以及《當代》第230期所刊出的轉型正義專輯;有的則比較草率並充滿政治操作的鑿痕,如2007年初安排五國卸任元首來台出席的「全球新興民主論壇」,或是民進黨中常會在同年2月7日所提出的「去納粹化」運動。
雖然轉型正義的口號甚囂塵上,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一個饒富興味的現象:絕大部分倡導轉型正義概念的,都是泛綠或親綠的學者及團體;而泛藍或親藍的學者及團體,則刻意不觸及這個問題,或是以嘲諷、否定的態度看待這個問題。對於生活在台灣社會、凡事已經習慣按藍綠分野思考的人們,這似乎也是天經地義的發展。然而,如果我們希望台灣社會能夠就事論事、能夠擺脫藍綠本位的思考,並期待建立一個講理的、公正的民主社會,我們實在應該鼓勵大家真誠地面對問題,釐清轉型正義的意義與作法。也許我們無法在所有爭議性問題的處理上獲得共識,但至少對歷史有所交待,對未來世代也可以提供進一步思考的契機。
如果我們不要掉入政治鬥爭的泥淖,而回歸到轉型正義的原始涵意,就會知道「轉型正義」是一個與「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息息相關的概念,並不是無所不包的術語。
一、民主轉型與轉型正義
由於某些政治人物的蓄意扭曲,目前輿論在談論轉型正義問題時,會把許多相干、不相干的議題混雜在一起,使大家對轉型正義的內涵感到困惑,或甚至產生嫌惡排斥的心理。舉例而言,陳總統因家人濫用特權而遭到反對黨猛烈抨擊時,辯解說過去的「七海官邸」到現在都還享有特殊待遇,大家憑什麼指責民生寓所幫傭支領特工人員的津貼叫做貪腐與特權。我們遺憾的不只是陳總統以「過去別人可以,為什麼我現在就不行」的心態看待此一事件,更在於他主張這是「轉型正義」的問題,彷彿我們應該徹底檢討「七海官邸」的陋規,同時又諒解民生寓所的作法,這樣才符合轉型正義的要求。然而,轉型正義如果要有意義,當然是要一併檢討七海官邸(現在叫「大直寓所」)以及民生寓所(當時是總統女婿住所)是否必須配置國安人員、及以清潔工能否支領特工人員薪資的問題。陳總統以「轉型正義」替自己不當行為辯護的結果,只會使一知半解的人認為轉型正義並不是什麼好東西。
再以最近民進黨中常會所討論的轉型正義提案來講,游錫堃主席除了力主全國徹底消除「蔣中正」的名字(如「中正紀念堂」、「中正路」、「中正公園」改名),加速通過「政黨不當取得財產條例」之外,還主張威權時期曾參與政府體系者不得入黨,並呼籲立即制定新憲法、確立總統制或內閣制的問題。這個提案所涉及的項目中,有些的確與轉型正義有關(如國民黨黨產問題),有些作法上值得商榷(如中正路全部改名或擴大排藍條款),有些則與轉型正義沒有關聯(如修憲或制憲以確立中央政府體制)。這種提案事實上是假「轉型正義」之名,行貫徹一黨政見或遂行一人意志之實。雖然提案本身能夠幫助提案者爭取深綠選民的青睞,但是不斷操弄議題的結果,也同樣讓敵對政黨的支持者鄙夷其動機,並質疑轉型正義訴求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如果我們不要掉入政治鬥爭的泥淖,而回歸到轉型正義的原始涵意,就會知道「轉型正義」是一個與「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息息相關的概念,並不是無所不包的術語。所謂民主轉型,是指一個原本屬於威權專制或極權獨裁性質的國家,因為各種因素的作用,轉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的過程。這種情況較早的例子,有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義大利與日本(由法西斯主義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但都是由外力主導)。比較晚近的例子,則包括許多「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新興民主國家,如南歐的希臘(1974)、西班牙(1975),拉丁美洲的阿根廷(1983)、巴西(1985)、烏拉圭(1985)、智利(1990),東歐的波蘭(1989)、匈牙利(1989)、東德(1990),非洲的南非(1994)、獅子山共和國(2002),東亞的菲律賓(1986)、韓國(1993)、台灣(2000)等等。由於一個國家從威權或極權政體轉型為民主政體是一件相當複雜的事情,因此相關的研究就包含了「轉型原因」、「轉型過程」、「民主倒退」、「民主鞏固」等等文獻。我們所關心的「轉型正義」,也是在這個脈絡之下出現的。
借用Louis Bickford的界定,轉型正義指涉的是「一個原先不民主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所發生過的人權侵犯、集體暴行、或其他形式的鉅大社會創痛(包括種族滅絕或內戰),以建立一個比較民主、正義、和平的未來」。換言之,威權或極權統治時期,當政者曾經對人民(尤其是異議分子)所施加過的種種暴行(如任意逮捕、囚禁、酷刑、殺害、栽贓、侵佔等等),到了民主轉型成功之後,都必須在正義原則下,獲得釋放、平反、道歉、賠償,或司法上的訴究。在過去的政治學文獻中,人們稱此種彌補措施為「溯往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現在由於「民主轉型」研究的盛行,學者改稱之為「轉型正義」。
由於轉型正義與民主轉型息息相關,因此它的運用有一定限制。譬如說相反方向的政治轉型(由民主國家變成威權或軍事獨裁國家),就不容許我們稱轉型後的追溯行為(如逮捕政敵、沒收企業資產)為轉型正義。同樣,單純的政權更迭(如英國工黨在1997年代取代保守黨執政),也不涉及轉型正義問題。這並不是說單純政權轉移的社會不存在正義補償的問題,而是說其他正義概念已經足以處理(包括貫徹「司法正義」打擊犯罪、落實「分配正義」以縮短貧富差距、追求「性別正義」以創造男女平等的社會等),因此與「轉型正義」所關切的問題沒有直接關係。
根據前述瞭解,我們可以說「轉型正義」主要適用於兩種情境:第一種是「一個國家由威權或極權政體轉型為民主政體後,對過去各種違反公義情事的追究與矯正」;第二種情形是「一個國家在戰爭或內戰結束,並建立民主政體後,對過去各種違反正義情事的追究,以及衝突各方對和解的追求」。除此之外,也有人將轉型正義應用在主流社會對邊緣社群的長期壓迫,而如今必須採取的補救措施(如美國白人對黑人的剝削、加拿大白人對原住民的壓迫、或各個社會男人對女人、異性戀對同性戀的欺凌等),但這顯然是一種擴大解釋的做法,恐怕會治絲益棼,因此較少為學界所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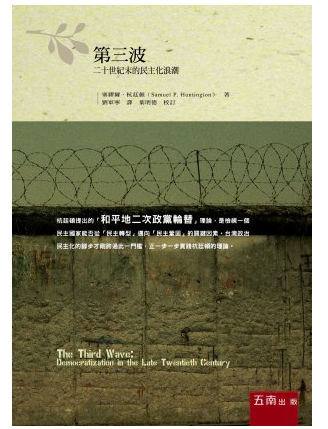
如何讓罪行輕微的從屬者有機會表示懺悔、讓心胸開闊的受害者(及其家屬)有機會表示諒宥,以結束過去的不幸經歷,共同生活在一個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新社會,便成了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挑戰。
二、轉型正義的具體內容
轉型正義當然不只是一個口號,而牽涉到許多具體的做為。「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根據他們協助處理各國轉型正義的經驗,把主要工作區分為幾個項目。如果我們按處理時序的可能先後加以排列,並將女性受害者問題併入一般受害者,則大致如下所示:
1. 真相調查(Establishing the truth about the past)
2. 起訴加害者(Prosecution of the perpetrators)
3. 賠償受害者(Reparation of the victims)
4. 追思與紀念(Memory and memorials)
5. 和解措施(Reconciliation initiatives)
6. 制度改革(Reforming institutions)
7. 人事清查(Vetting and removing abusive public employees)
「真相調查」往往是落實轉型正義的第一步工作,因為過去的專制者往往不會清楚留下自己暴行的紀錄,所以轉型之後的政府(或受害者)就必須先釐清每一樁不義行為的時地、經過、受害人數、損失規模、長期影響等等。有了真相調查作為基礎,受害者及其家屬才能提出具體的正義訴求,譬如要求物質或精神賠償、起訴加害人,或給予寬恕與和解。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會」是人們最津津樂道的處理模範,因為它在屠圖主教的領導下,以兩年多的時間對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暴行進行調查,總共聽取了超過23000位受害人或目擊者的証詞,舉辦了無數次的公聽會,最後完成了厚達五冊的調查報告。當然,南非的處理方式也蘊含著一些爭議,因為它是以「坦承暴行者可獲得赦免」的條件,來換取加害者的志願配合調查。如此一來,真相調查與正義伸張無法建立必然的關係,有些受害者固然能在獲知真相之後原諒加害者,但也有些受害者覺得正義沒有獲得伸張,始終無法原諒加害者。由此可見,真相調查絕不是容易之事,因為這裡可能涉及「如何順利取得証據」與「如何追究應有責任」的兩難之局。
「起訴加害者」是轉型正義的重頭戲所在,因為唯有將侵犯人權、製造不幸的原凶繩之以法,才能昭告世人正義獲得伸張,也才能嚇阻其他未來的獨裁者,讓他們知道迫害百性的下場。智利的獨裁者皮諾契特將軍在1973年推翻民選總統阿葉德,以鐵腕政策統治這個國家長達十七年。在他的統治期間,據估計至少三千多人被處死、謀殺或平白失蹤。1990年政權轉移之後,智利法庭試圖以各種罪名將他繩之以法,但是他在2006年12月去世,逃過了可能的審判。與此情況類似的還有墨西哥總統Echeverría,他在1968年擔任內政部長時,涉嫌下令殺害政治抗議者。其後他擔任總統的期間,也曾下令鎮壓並殺害過學生。墨西哥在2000年民主轉型之後,新政府設立了特別檢察官辦公室以調查並起訴Echeverría任內的罪行。雖然墨西哥最高法院認為這些罪行已超過三十年的追訴期,但是2006年11月,他還是被一個法官下令軟禁,並等待進一步的法律行動。其他著名的獨裁者如伊拉克的海珊總統,則於接受審判後被處以極刑。
「賠償受害者」是轉型正義另一個面向上的重要工作。曾遭受專制政府迫害的人,只要能夠向新成立的民主政府提出充分的証據,則理應獲得國家的補償。補償的形式很多,包括罪名的平反、名譽的恢復、身體的醫療、教育的提供、金錢的賠償、財產的歸還、工作的保障等等。當然,基於國家財政資源的限制,新興民主國家很難做到讓所有受害者滿意的程度。在有些情況下,政府能夠提撥的經費,根本不足以支付人數龐大的受害者(及其眷屬)的各種需求;在有些情況下,受害者真正在意的並不是金錢賠償,而是精神層面的彌補。至於身心傷害的長期醫療、子女教育權的優先考慮、工作機會的提供等等,更不是剛從威權專制轉型過來、或剛從內戰兵禍掙扎出來的新興民主國家所能企求。祕魯政府目前正針對藤森總統任內的貪污、濫權、侵犯人權罪嫌進行追究,同時也成立一個高階的委員會去落實國會所通過的賠償條例。南非則是在真相和解委員會之下,專門設置了一個「賠償與復權委員會」(Reparationand Rehabilitation Committee)來處理種族隔離期間受害者的各種求償問題。這份工作之艱鉅,誠如2003年所發表的報告書所言,絕非南非政府獨力所能承擔。因此,如何鼓勵企業部門及非營利組織一起合作,想出具有創意的方案,應該是大家可以努力的方向。
「追思與紀念」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因為指定特定日期為國家紀念日、興建紀念碑或紀念館、舉辦溫馨的追思活動,都不需要鉅額的經費;同時此舉對受害者心靈的撫慰以及社會和解前景的開創,也具有正面的意義。世界著名的紀念館很多,譬如德國、法國、以色列、波蘭等國為了紀念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所興建的「大屠殺紀念館」、南非為了記取種族隔離政策之教訓而興建的「第六區紀念館」、阿根廷為了提醒後人獨裁者濫用國家安全之名遂行恐怖統治之實的Abrerta紀念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追思與紀念應該以「教育後人絕勿重蹈覆轍」為宗旨,而不只是為了讓受害者家屬發洩傷痛,或製造社會內部的怨懟與仇恨。


「和解措拖」是一個涉及層面廣泛、但不容易界定清楚的概念。轉型正義以調查真相、追究加害者責任開始,但是絕不希望整個社會因此陷於相互對立或分裂的境況,因此除了審判罪行嚴重的加害者之外,如何讓罪行輕微的從屬者有機會表示懺悔、讓心胸開闊的受害者(及其家屬)有機會表示諒宥,以結束過去的不幸經歷,共同生活在一個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新社會,便成了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挑戰。國際轉型正義中心建議,各國在處理和解問題時,一定要著眼於「公民信任」(civictrust)的建立。所謂公民信任,就是超越個別加害者與受害者兩造之間的恩怨,而致力於全社會所有公民之間的基本信任感。
一方面,要讓所有公民彼此之間能夠相信對方不再有迫害或報復的意圖;另方面,要讓他們都能夠信任新興民主國家的制度。因為只有制度上軌道,公民才不會擔心侵犯人權的事情重演。不過,和解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事情。以南非為例,黑人政府執政已達十年以上,真相和解委員會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然而目前黑白種族之間仍有極多嫌隙及緊張。有的白人自始不諒解戴克拉克對非洲民族議會的讓步,有的黑人也始終無法原諒白人統治者所犯過的罪行。這種緊張的社會關係,一旦加上經濟衰退、治安惡化、失業上升等其他因素,就更難期待有重大的突破。或許我們必須瞭解:和解需要時間。撕裂過的社會,尤其需要有堅定的和解意志及協商智慧,來度過這段漫長的時間。
「制度改革」也是轉型正義極為重要的工作。一個專制國家的統治者之所以能做出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多半是因為這個國家沒有符合法治原則的制度,或是既有的制度名存實亡,無法發揮防止濫權的作用。因此民主轉型之後,人們必須認真檢討政府制度上的缺失(尤其是軍隊、警察、情治、司法及教育等部門),廢除所有容許獨裁者再度產生的機制,徹底改革政府機構的功能,使基本人權及民主程序得以確保。許多東歐國家及拉丁美洲國家,都是在專制政府垮台之後,大規模地整頓警察及安全部門,限制行政首長的裁量權。不過,司法及教育體系由於涉及的人事問題比較複雜,通常無法像裁撤安全部門或縮小軍警編制那樣,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行政部門的改革,其實也會涉及另外一個敏感而複雜的轉型正義問題,那就是「人事清查」。許多威權或極權主義國家都曾經建立龐大的祕密警察機構,以控制人民的自主結社或反政府活動。這種單位的公務員以及替他們蒐集情報的線民,當然都是廣義的壓迫體系的一部分。民主轉型之後,究竟要如何處理這些公務人員、究竟能否讓他們繼續擔任公職,便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以匈牙利的經驗為例,共產黨政府垮台後,國會在1994年通過了一個與公職人員任用資格有關的「淨化」法案(lustration),任命了三名法官去徹底檢閱所有現任重要公職人員(包括總統、部長、議員、法官、國立大學校長、國營企業主管等等)的安全檔案。
他們如果發現其中有人曾參與過去政權的安全運作,就會私下通知當事人請他自動辭職下台,否則就公布其過去資料。不過這件事情後來引起憲政爭議,而且三名法官之中竟也有兩名的「潔淨度」也出現問題。幾經辯論及修正妥協,後來的法律縮小了人事背景清查的範圍,基本上只有總統、國會選任的高官、以及正式任職於情治單位的公務員,才需要經過「淨化」程序。至於國會議員,如果被查出有從事特工的紀錄,則可選擇辭職或面對資料被公開的後果。另外,匈牙利也成立一個歷史檔案局,負責保管所有共黨統治時期蒐集的人事安全資料,只對申請檢閱的當事人提供資料。當然,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同,人事清查的必要性及其範圍,也隨著專制政府的暴虐程度而有差別。通常大部分的國家都是針對黨政高官員進行檢驗,以免政府運作因撤換所有公務員而陷於癱瘓,或整個社會產生無法承受的分裂。
「和解」是轉型正義的另一個要點,然而台灣在這一方面的成果十分有限。基本上,無論是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大多對國民黨懷有強烈的恨意。
三、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
以上我們在說明各國轉型經驗時,用以界定民主轉型開始的時間,大致是以威權政府垮台、反對黨贏得選舉上台的年份爲根據。然而台灣的情形比較特殊,因爲廣義的民主轉型可以從解除戒嚴或國會全面改選起算,而狹義的轉型則要等到2000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才開始。如果仿照其他國家的界定方式,那麼許多與轉型正義有關的措拖其實在狹義的民主轉型之前就已經進行,這似乎顯得邏輯不通。但是如果我們採取廣義的界定,則表示威權政黨(國民黨)本身是在喪失政權之前,就已經開始從事轉型正義的工作了。這一點與其他國家比起來,也顯得相當特殊。雖然如此,但國內大部分的政治學者,都是以1980年代後期爲台灣民主轉型開始的時間。而且杭亭頓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中,也認爲台灣的民主轉型確實是在1987、1988年左右開始,還不必等到反對黨上台。因此,基於實際經驗及大部分學者的判斷,本文採用廣義的觀點。
台灣與轉型正義問題關係最密切的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I960年代的白色恐怖。因此,針對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的迫害事件所進行的眞相調查、平反、道歉、賠償、紀念等等行動,就構成了目前台灣轉型正義的主要內容。如果我們根據上一節所介紹的工作項目,逐一檢視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在1987年之後所做的事,就可以得出台灣轉型正義的大致經驗。
台灣最早的轉型正義措拖,是二二八事件的公開化以及各地二二八事件紀念碑的興建。在解嚴之前,二二八事件基本上是個不能談論的禁忌。隨著1980年代末期整個社會風氣自由開放的快速發展,與二二八有關的書籍、報導漸漸可以公開流通,而受害者及其後代也開始要求平反。嘉義市率先在1989年樹立了全台第一個二二八紀念碑,其後全國各地紛紛跟進,尤其是幾個曾經發生過大規模抗爭或軍事鎭壓的地方。截至目前為止,絕大部分縣市都有二二八事件紀念碑;除了台北市的二二八紀念館之外,少數縣市也興建紀念館。與此同時,官方及民間對二二八受難者的追思活動也陸續展開。這些活動⁵屬於上文所說的「追思與紀念」。
「眞相調查」爲各國轉型正義之必要工作,台灣也不例外。1990年,行政院決議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由陳重光與葉明勳擔任召集人,賴澤涵擔任總主筆,邀請專家學者對二二八事件展開詳細的調査研究。1992年研究報告出爐,其客觀性大致爲各界所肯定。一年之後,此書正式發行。除了此一官方研究報告之外,民間對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也在1990年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政府繼續擴大對二二八事件的調查,由另一批學者針對責任歸屬問題進行硏究,於2006年完成「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認定蔣介石爲元凶,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另外列出軍警情治人員多人為共犯。2007年,民進黨政府再度強調蔣介石是一切罪惡的源頭,也是不可饒恕的「獨裁者」,希望藉此推動「去蔣中正化」運動。不過,由於社會各界對蔣介石在歷史上的功過評價不同,再加上這份報告的撰寫人鼓勵二二八家屬向國民黨提出五十億的賠償,使許多人對責任歸屬報告的客觀性存疑。無論如何,這是台灣在處理轉型正義上另一個重要的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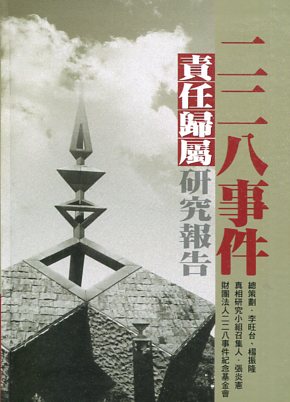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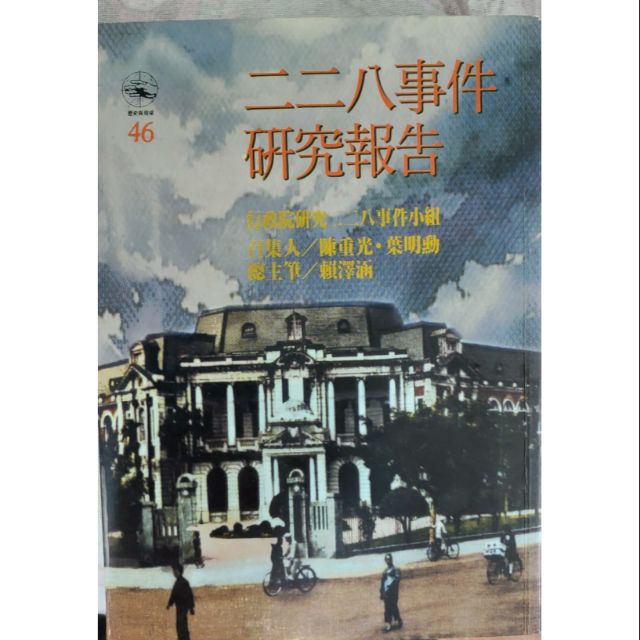
1992這一年,除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公布,也是「警備總部」走入歷史的關鍵年代。警備總部是戒嚴時期最著名的治安特務機關,除了嚴格控制思想言論自由,也負責監控、逮捕、刑求政治異議分子。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案件,無論是以匪諜案為名、還是以台獨叛亂案爲名進行逮捕,大多出自警備總部,因此警總在民主運動人士眼中,可說是最惡名昭彰、最具有代表性的威權統治機構。1987年解嚴之後,警總的角色逐漸淡化。1992年動員戡亂時期終止,警總改制爲海防司令部,其原始功能正式終結。筆者特別提出警總的變遷,主要是以之做爲「制度改革」的重要例子。除了警總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單位也在解嚴之後發生轉變,此處不一一贅述。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或許出於監控政敵的考慮,並沒有完全將侵犯人權的情治機構(如國安局、調査局)導入正軌,反而利用舊有特工人員蒐集有利於己的情報,並不時以此情資威脅反對黨。這種現象說明了政治權力的確具有腐化當權者的本質,同時也讓我們了解「制度改革」在實踐上有多麼困難。
在「賠償受害者」方面,立法院於1995年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並由行政院據以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處理二二八受難者申請補償事宜。自1996年至2004年為止,基金會共受理2,756件申請案,審核通過2,253件,每位受難者(或家屬)依不同程度可獲得10萬到600萬元的補償。歷年來,政府總共發出71億多的補償金,受領人數則接近一萬人。另外,政府也在1998年成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針對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及家屬)進行補償,其受理案件及補償金額總數都比二二八事件還多。儘管如此,部分受難者及人權團體仍然批評政府的補償金額不夠、補償方式不充足。尤其是在名譽恢復及精神傷害的撫平方面,可能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和解」是轉型正義的另一個要點,然而台灣在這一方面的成果十分有限。基本上,無論是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大多對國民黨懷有強烈的恨意。雖然國民黨在執政時期就開始進行上述的轉型正義行動,並且李登輝也曾經代表政府及國民黨向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但是時至今日,仍不乏痛恨國民黨至極的政治受難者。這種現象,一方面說明了國民黨過去所犯下的惡行確實很深,無法輕易得到受害者的諒解;另方面也說明即使當年的「元兇」已經作古,受難者也不會因為後繼者(無論是李登輝或馬英九)的公開道歉而願意原諒國民黨。的確,以國民黨歷來的作爲及表現而論,可能並沒有太多値得諒解的地方。不過吊詭的是,台灣的政治迫害經驗距今久遠,絕大多數的「元凶」或「共犯」皆已作古,而比較年輕的世代幾乎都談不上對威權政治有什麼切身經歷。以「轉型正義」為名要求現在已經在野的國民黨替蔣中正或彭孟緝的罪行負責,是否具有足夠的正當性及合理性,實在値得斟酌。國民黨的黨產必須以符合正義原則的方式處理,這是絕大多數公民的共識。但是如果要求一定年齡(譬如50歲)以上的國民黨員都應該退出政壇,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徹底「清理」過去的宿怨,是否也是過於偏激的要求?從自主公民的角度來看,眞正有助於「和解」的途徑,應該還是「防止煽動族群仇恨的言行」以及「建立有利合理競爭的民主制度」。
以上所述,是台灣在轉型正義概念下所發生的若干經驗。如果我們逐一對比上一節所列出的各項工作,就會發現台灣在「眞相調查」、「賠償受害者」、「追思與紀念」、「和解(道歉)」、「制度改革」等方面已經有所努力(無論其努力程度如何),而在「起訴加害者」與「人事清查」方面則沒有動作。「起訴加害者」之所以沒有做,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加害者多已過世。「人事清查」之所以沒有做,則可能是太過敏感,無法預測會造成政治社會多大的動盪,同時也不確定該把清查範圍設定在那裡。此外,關於國民黨的黨產與黨營事業,以及黨職合併公職計算的問題,也是部分提倡轉型正義人士所熱衷討論的議題,大致都還屬於「制度改革」的範疇,値得有興趣的人繼續研究。
在整個社會頌揚轉型正義如何崇高、如何重要之際,筆者也願意提出一些觀察與想法,以避免我們對一個崇高理想的追求,不愼滑落爲廉價的意識型態。
四、轉型正義之反思
自由民主是目前人類追求的價値,因此民主轉型及轉型正義也自然而然成為眾人肯定的現象與理念。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威權或極權獨裁對平民百姓所造成的身心傷害,確實不是任何藉口(如經濟發展或社會穩定)所能夠合理化。因此,一個民主轉型之後的國家,絕對應該設法實踐轉型正義。正如同許多提倡轉型正義的作者所言,如果我們輕易放棄追究眞相、輕易遺忘歷史,那麼前人的犧牲就會變得毫無意義,而類似的悲劇也將一再上演。爲了讓受難者的哀痛得以撫慰、為了讓撕裂的社會得以獲得和解,我們必須重視轉型正義。
對於這一切說法,筆者由衷贊同。然而,在整個社會頌揚轉型正義如何崇高、如何重要之際,筆者也願意提出一些觀察與想法,以避免我們對一個崇高理想的追求,不愼滑落爲廉價的意識型態。畢竟,在人類歷史上,並不乏立意良善、理據充足的論述,卻由於野心人士的操弄利用,或是對現實與理想差距的錯誤判斷,而變成一場徒留嗟嘆的運動。
首先,無論我們如何肯定轉型正義,請不要忘記它只是人類社會諸多價値之一。轉型正義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値,但是它並不是唯一的價値,也無法宣稱是最高的價値。以撒 · 伯林說得好:自由、平等、正義、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等等,都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融貫,人類的各種理想,當然更無法完全相容」。轉型正義是「正義」價値的一個次類,既無法涵蓋分配正義,也無法等同代間正義。它與其他次類一樣都具有「給予人人應得之分」的正義核心意義,但無法適用於所有與正義有關的情境。更重要的是,即使它可以等同於正義本身,它也無法取代自由、平等、幸福或安定。實現了轉型正義,我們仍然要面對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環境生態惡化的問題、教育品質下降的問題、複製科技泛濫的問題……。不同的問題,需要不同的價値作為導引,而不同的價値之間可能存在衝突。如果對這一點毫無認識,那我們等於仍未了解自由民主社會的本質。
因此,當我們聽到人們呼喊「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和平」,「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未來」的時候,我們必須理解這種修辭的眞正涵意,是要督促我們重視人類的某個重要價値,並不是要我們把這個價値擺在所有價値金字塔的項端,以之作為一切行動論述的起點。而當我們眞正體會轉型正義與其他價値之間的關係之後,我們就會知道爲什麼一位致力於轉型正義的學者(Tuan E.Mendez)要告訴我們:「轉型正義既不能全盤抹煞,也不能期待全盤落實」。目前國內每逢二二八紀念日前後,轉型正義的口號就會以無上價値的形貌出現,雖然其原因不難理解,但我們終究必須在紀念日之後,恢復我們對政治社會問題複雜性的如實掌握。
其次,轉型正義論述本身建立在一套環環相扣的論證上,彷彿一切事理皆可依此邏輯發展,但這種假設並不一定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基本上,轉型正義認為我們首要之務是調查眞相、追究元凶。如果罪行較輕的加害者爲自己過去的行爲感到羞愧,也願意主動向受害者誠懇地道歉,則受害者在了解眞相之後,可能願意原諒加害者,從而使整個社會獲得和解與和諧。然而,誠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南非的「眞相與和解」經驗似乎並非如此。許多受害者在得知眞相之後,終其一生無法原諒坦承犯下暴行的加害者,也無法接受國家法令對暴行坦承者的赦免。南非的治安在近幾年間急速惡化,除了經濟衰退、失業攀升之外,多少也跟黑白種族之間迄未能眞正和解有關。另外,拉丁美洲國家的經驗則顯示,威權政府的受害者視獨裁者爲萬惡不赦的元凶,必欲去之而後快;然而威權政府也曾嘉惠過相當人口,後者對政府獨裁的說法未必接受,因此經常與前者發生衝突。由於眞相無法順利帶來和解,因此社會陷於動盪之中。
上述不幸情勢的發展,自然只是部分國家的實況,不足以代表轉型正義論述之失效。尤其目前許多國家的轉型時間仍然短暫,更加無法判斷轉型正義措施的長期效果。理論上,我們寧可相信眞相的發掘,終究有助於社會和諧的達致;而且人類是一種具有探究眞相本能的動物,沒有人會願意(關於自己的)眞相永遠湮沒。只不過,我們目睹其他國家的先例,知道轉型正義進程未必如理論陳述那般順暢,就有必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妥善因應人性脆弱的本性,以及脆弱人性所構成的社會關係。容筆者再度引用伯林所經常轉述的康德名言:「人性本是扭曲的素材,不能從中產生直截的事物。」所有有心處理轉型正義課題的人士,不妨深思此一略顯悲觀、但也充滿智慧的話語。

最後,關於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實踐,我想大家都看得到政治人物操弄的痕跡。每當二二八來臨時,總會有人以轉型正義為名舉辦政治動員意味濃厚的大型活動,而藉此爲特定政黨或特定政治人物造勢。如果這個時間點正好與選舉日期接近,則輔選的味道更是濃厚。因此,近幾年的二二八紀念日除了例行的追思與平反之外,有時跟「牽手護台灣」結合,有時又是「向中國說不」。雖然主事者都會道貌岸然地表示這與選舉造勢無關、與族群動員無關,而只是凝聚全民的共識。然而去年泛綠陣營發生內鬨,某些台獨人士痛罵陳總統不知報答此種活動輔選之功時,我想許多一度相信活動公正性的參與者,心裡一定有被玩弄的感覺。
更有甚者,原本在轉型正義的論述中,民主化之後的新政府應該是清廉的、公義的,如此它才有充分的正當性去改革過去不義的制度、追究專制的統治集團。然而台灣何其不幸,政黨輪替之後的新政府領導人在不到幾年之內,已禁不起權力誘惑的考驗,淪落爲貪腐無能的代名詞,甚至還毫無羞恥地辯解自己的犯行,說是轉型正義尙未實現的緣故。如此濫用轉型正義的結果,使現存政府大幅喪失追究過去政權不義行為的正當性,也使轉型正義的伸張,蒙上了一層令人無法釋懷的陰影。
看著人類悲劇與鬧劇此起彼落,我們無法不爲台灣政治發展的未來感到煩憂。如果轉型正義的理念最終禁得起各種漠視、抗拒、扭曲與濫用,而在遙遠的未來發揮彌合傷痛、凝聚共識的效果,我們今天的努力或許値得欣慰。然而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每一位公民都只能以戰戰兢兢的心情,持續摸索通往正義的道路。
(本文摘錄自思想(5):《轉型正義與記憶政治》)

江宜樺,1960年生,台灣基隆人。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士、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行政院院長、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研究員、劍橋大學訪問學人、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政治思想史、當代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國家認同理論等。著有《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揚智文化),編有《政治社群》(中研院社科所)、《洛克作品選讀》(誠品)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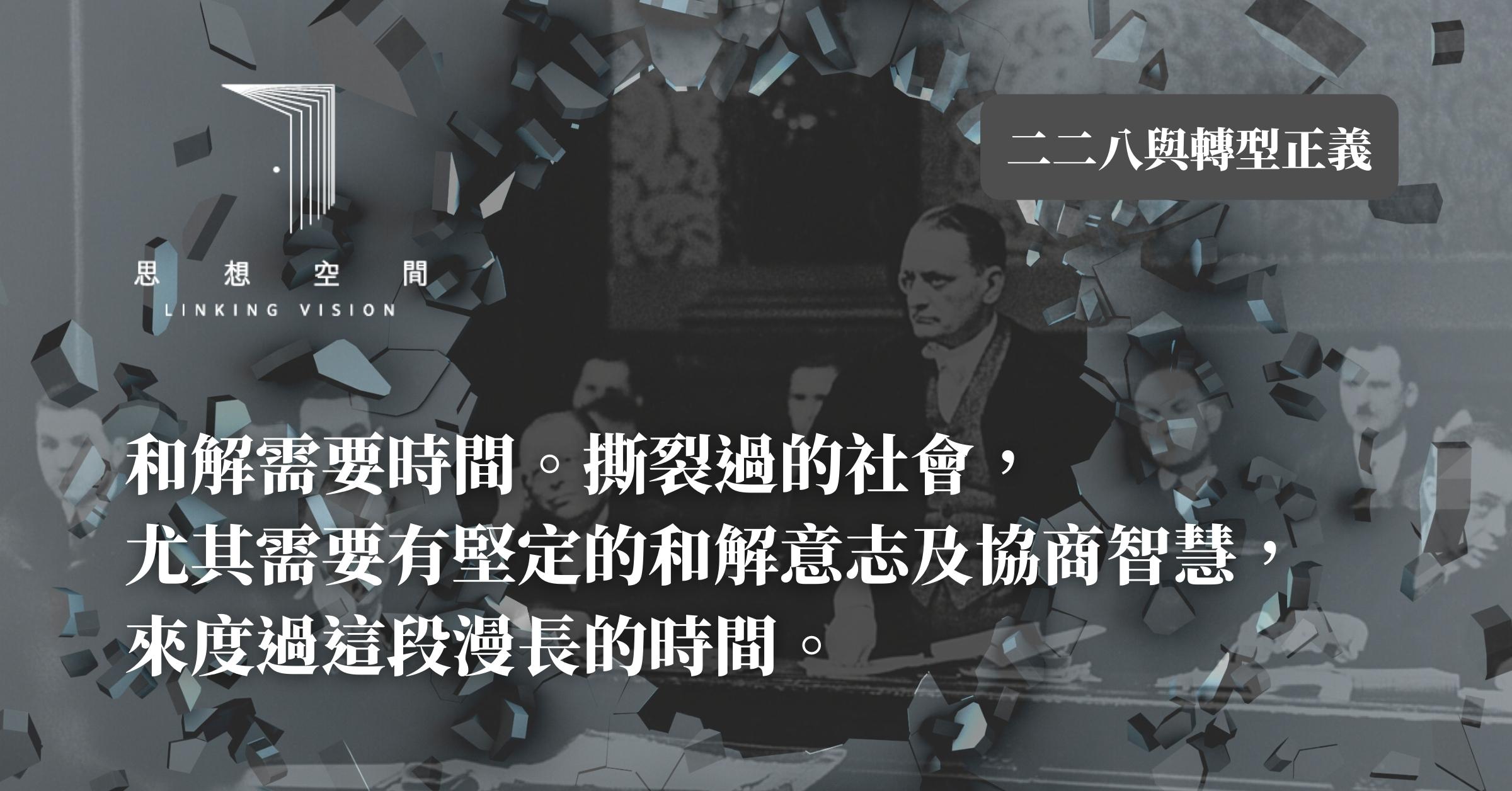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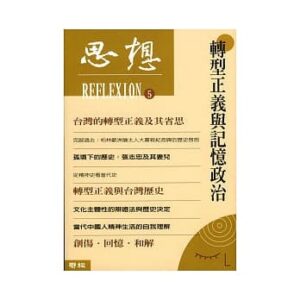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