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乃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編者按:2022年,是台灣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結束任務的一年,也意味著台灣首度於體制以「轉型正義」之名進行的工作,將畫下暫時的句點。回望與梳理這一段歷史,有四篇文章格外值得參考:四位作者均是曾經參與、或影響台灣這一波「體制內轉型正義工程」的行動者。
吳乃德2006年發表於《思想》雜誌的鴻文〈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是二十一世紀台灣啟動轉型正義工程的重要文件之一。
吳乃德文出刊後,引發時任台大政治系教授的江宜樺,在2007年以〈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一文回應。江宜樺後於2013年至14年間擔任行政院長,雖未直接參與體制內轉型正義工程(促轉會正式掛牌成立於2018年)運作,但於其任內高度關注轉型正義相關議題;同時,亦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警民衝突中,親身成為體制與社會運動對峙的第一線官員。
另外兩篇文章均曾刊發於端傳媒,其中一篇由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所著,她曾任促轉會早期委員,後於2018年辭職;另一篇由前真促會執行長、現任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所著。
這四篇文章,均發表於這四位學人仍身在「民間」、促轉會尚未成立時。如今,促轉會已屆終幕,回溯四位的思想源流,或許能給我們一些重要的反思,與全新的啟發。
歷史記憶和民主未來
雖然民眾對轉型正義的要求並不強烈,可是為了民主的未來,我們仍須加以處理,特別是在歷史正義方面。回憶過去,經常是為了未來。許多學者和思想家討論轉型正義的動機,主要也是為了未來,為了「讓它不要再發生」(never again)。雖然過去的裂痕和傷痛,經常阻礙未來的共存和合作;可是遺忘過去,過去可能在未來重現。歷史正義和歷史真相在防止過去重現上,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雖然民主體制在今日的世界思潮中已經取得主流的地位,也已經成為今日世界的主流趨勢。可是民主並非不可逆轉。近代世界許多國家,不只拉丁美洲,甚至具有高度文化、高度教育水準的西歐,都曾經發生民主政體崩潰回到威權統治的案例。民主政體依賴什麼得以鞏固?政治學者可能會列舉許多條件和因素。可是這些條件和因素要發生作用,最終還是公民對民主體制和民主價值的信奉,並且當政府侵犯這些價值的時候,願意以行動護衛它們的決心。歷史真相和歷史正義在培養一般公民的民主價值上,應該具有重要的角色。
歷史真相是否應該揭露?關心轉型正義的人,對這個問題所提供的答案其實是非常紛紜的[1]。歷史真相和歷史記憶有許多層面。就其和民主體制的未來有關而言,有兩個議題值得討論。第一是短期上,是真相的揭露還是歷史的失憶,比較有助於民主體制所須要的社會和諧?第二是長期而言,真相的揭露是否有助於民主體制的穩定?
並不是所有「真相和解委員會」的觀察家都會接受這樣樂觀的評估。委員會運作的過程和結果顯示:大多時候真相並不能帶來和解。
在討論揭露真相還是忘懷過去比較有助於社會和諧之前,我們或許必須先討論另一個先決的道德問題。我們很難否認:受害者有權利知道真相,知道誰應該為他們的苦難負責。許多人因此認為,也只有受害者有權利決定是否遺忘、寬恕或記憶。在個人層次上,遺忘還是記憶對他們比較好,沒有人能替他們決定。在「真相和解委員會」的聽證時期中,南非一位法官說,「有些人說:夠了,不要再打開傷口了。我經常覺得奇怪,他們所說的傷口到底是誰的傷口?顯然不是他們自己的。而且,他們憑什麼說,受害者的傷口已經痊癒了?」[2] 只有受害者才有權利決定是否要遺忘過去。可是許多沒有受過傷害、不曾體驗人性(humanity)不被承認是何種經驗的政治領袖、專家學者們,卻經常要受害者遺忘過去,「走出悲情」,「向前看」。
而在社會效果的層次上,到底是遺忘還是記憶比較有助於社會和諧?許多人相信,只有揭露真相才能為社會帶來寬恕和和解,為受害者和加害者同時帶來痊癒。正如南非一位父親被警察殺害的女士所說的,「我們很想寬恕,可是卻不知道要寬恕誰。」[3] 透過揭露真相以創造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和解,是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成立的宗旨中比較積極的面向。委員會的主席、也是該一精神的具體象徵圖屠主教,在委員會的運作結束後,以如下樂觀卻保留的語氣這樣說:
真正的和解必須暴露可怕、濫用、痛苦、作賤和真相。揭露真相有時候可能讓情況更惡化。這是一個具有風險的行動。可是從結果看來,它是值得的。因為揭露真相有助於受害者的痊癒。……而如果加害者能終於認知自己的錯誤,那麼或許就有懺悔,或至少悔過或難過的希望。……我們也希望受害者可能因加害者的道歉而原諒他們的罪行[4]。

並不是所有「真相和解委員會」的觀察家都會接受這樣樂觀的評估。委員會運作的過程和結果顯示:大多時候真相並不能帶來和解。許多加害者在公聽會上的表現,讓人覺得他們並沒有悔悟,讓人覺得:「是的,如果回到從前的狀況,我還是會做同樣的事情。」[5] 而在受害者這一方,其效果也令人有所保留。許多人期望真相的揭露能撫慰受害者的傷痛,同時也帶來寬恕。這是對巨大創傷的心理治療術的基本信念。有許多例子確實指出揭露真相的治療效果。南非一位在16歲時遭受刑求的受害者,在「真相和解委員會」的公聽會結束後說,「我過去好幾次說過我的故事,我總是不斷的哭、哭、哭;覺得我的傷痛還沒有過去。不過這一次我知道,全國的人都會知道我的故事了,我仍然哭了一陣子,不過我內心也開始感覺快樂。」公開的證言將創傷的故事「從羞恥和屈辱,轉化成尊嚴和美德;透過對創傷的公開談論,受害者重新獲得他們的世界和自我。」[6]
可是也有許多例子顯示,受害者並沒有因真相大白而釋懷;相反的,他們的憤怒被真相重新點燃。一位因為支持黑人而太太和女兒被警察用郵包炸彈謀殺的白人說,他痛恨的一直是「體制」。可是12年後,透過委員會的證言,他終於知道,是誰殺了他的太太和女兒,他開始痛恨「人」,「我想,有一天我會殺了他。」[7] 這個例子,對在評估揭露真相的政治效果上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顯示,揭露歷史真相將人對「體制」的憎恨,轉變為對「人」的憎恨。對壓迫性體制的憎恨,正是我們期許於一般公民的重要價值。而對人的憎恨,顯然無助於社會和諧。這個例子似乎不是孤立事件。委員會結束運作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南非人認為,「真相和解委員會」讓南非人更憤怒、族群關係更惡化[8]。以色列一位學者警告,不要對揭露真相的後果太樂觀:「記憶常帶來和解,也同樣地常帶來報復,而希望透過解放的記憶帶來罪行的洗濯和救贖,結果將只是一個幻影。」[9] 因此,在受害者的個人層次上,有些例子支持揭露真相的和解效果,有例子則對這樣的期待加以否定。
而對社會整體而言,揭露真相是否能帶來和解,也缺乏有系統的研究。至目前為止,只有一個研究和此有關。2001年於南非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研究指出:真相的揭露可以為社會帶來和解。在這個研究中,「真相」是以幾個對種族隔離態度的道德評價做指標,如「種族隔離是違反人道的罪行」、「維護種族隔離體制是正義的」、「種族隔離體制背後的理念基本上並沒有錯」等。這些態度都是道德評價,而非真相的認知和接受。難怪研究者發現:和解的態度和真相(「對過去的知識」)顯著相關。由於這項研究在方法上的瑕疵,其結論仍然需要有所保留[10]。
雖然民族認同較不涉及意識型態,可是甚至不同的族群,都用不同的歷史記憶來塑造他們自己版本的民族認同。而在新民主國家中,集體記憶經常成為一個衝突的競技場。
至於我們所關心的第二個問題呢?真相的揭露是否有助於民主體制的鞏固?在這個問題上,學者的答案同樣分歧。有些人認為,挖掘過去只會危及脆弱的新民主政體。他們同意尼采的說法,「如果不要讓過去葬送未來,它必須被忘記」,也正是因為對納粹歷史的特赦和遺忘,才能讓西德於1950年代建立穩定的民主體制[11]。可是也有人認為,透過對獨裁者的追訴以保留歷史記憶,將能為民主體制建立穩固的基石。「雖然審判加害者在短期上或許會危及拉丁美洲的民主前景,可是對其長期的健康而言,卻是非常重要的。」[12] 這位作者有力地指出,從獨裁轉型到民主的社會具有兩項義務。第一個義務是對受害者,那些被謀殺的、被刑求的、不合理監禁的、在他們的專業中被剝奪工作權的。第二項義務則是對他們未來的世代:保證獨裁不再重現的義務。[13] 在台灣,第一項義務或多或少得到了滿足;可是因為疏於處理歷史正義,第二項義務,對為來世代的義務,仍然等待我們去承擔。
可是追求歷史正義經常是一項複雜的工作。追求歷史正義經常牽涉到對社會記憶的重塑。而重塑社會記憶可能永遠沒有「定論」。因為對社會記憶的解釋,經常植根於政治、社會、文化團體和利益之間的衝突,想要重建一個所有團體(不論是種族的、族群的和階級的)都可以接受的社會記憶並不容易。不同的團體,經常賦予歷史記憶不同的面向、甚至不同的解釋;有時候甚至要共享相同的紀念儀式都不可能[14]。以民族認同較有共識、較不分裂的美國為例,雖然民族認同較不涉及意識型態,可是甚至不同的族群,都用不同的歷史記憶來塑造他們自己版本的民族認同[15]。而在新民主國家中,集體記憶經常成為一個衝突的競技場,「記憶的營造家在其中互相鬥爭,爭相推銷經他們重塑的不同過去、有時甚至是不相容的過去,以促進他們的政治目標。」[16]
由於不同的歷史經驗,台灣的不同族群,對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也有不同評價和感情反應。外省籍的民眾由於抗日戰爭、中國內戰、以及移居台灣的經驗,對國民黨有深厚的歷史感情。而本省籍的民眾對國民黨統治經驗的記憶,則是二二八事件的屠殺和白色恐怖。兩個族群對威權統治的歷史記憶,似乎很難相容。兩年前我關於蔣經國的論文所引起的爭論,就是一個的例子[17]。該篇文章的主題是關於前面所提,近代台灣政治兩個最重要的道德問題之一:台灣民主化到底是誰的貢獻?該文檢討了許多外國和本地學者的論點: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這樣的講法不但違反一般的常識,也違反歷史事實。該文指出:蔣經國晚年的解除戒嚴,從而啟動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主要是在美國和反對運動的壓力下不得不做的妥協。此外,身為白色恐怖時期擁有至高權力的獨裁者,他也必須為在他統治下的人權侵犯事件負責。文章發表之後,引起不同政治立場者完全對立的反應。對我論點的贊同,幾乎全部來自「本土派」的學者和媒體;批評我的意見,則幾乎全部來自對立陣營的政治人物和媒體。同時,反對的意見中很少是針對事實的討論和爭辯,幾乎全是對作者的人身攻擊和人格謀殺,包括政黨領袖的意見和《中國時報》的社論[18]。台灣社會的歷史記憶和對歷史的詮釋,明顯是以政治立場為分野。
台灣社會對二二八的記憶,也同樣是分裂的。對許多本省人而言,二二八的屠殺象徵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外來統治者必然帶來災難和殘酷。在台灣認同勃興的現階段,這個事件成為台灣人悲哀的象徵,也是台灣獨立自主的合理性來源。而在中國認同者的眼中,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白色恐怖,都是內戰的延長。根據陳映真的闡釋,「二二八論述早已成為台灣反民族政治和歷史論述的『原教主義』的教條,發展為『台灣民族主義論』、『國民黨再殖民台灣』等意識型態的基礎。」其實,「二二八事變的忿怒,基本上在於認識兩岸兄弟同胞之情的基礎上,反對兄弟同胞間的掠奪和壓迫。」[19] 不同的民族認同,導致不同的歷史詮釋和不同的集體記憶,台灣當然不是唯一的例子。例如智利,該國在獨裁統治下同樣獲得不錯的經濟成長,民眾對過去時代的功和過同樣沒有基本的共識[20]。而日本社會在終戰五十多年後,仍然為戰爭和暴行的責任所分裂。
然而此種社會記憶的分裂並非難以避免。欲重塑一個所有族群都能共同接受的歷史記憶,讓它成為未來世代的民主教材,並非不可能。畢竟,兩個族群都有成員曾經勇敢地反抗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而兩個族群也都有成員,在白色恐怖下受難。如今已知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中,有40%是外省人,遠高於其在總人口中所占的15%的比例[21]。此外,歷史真相的揭露,也可以讓特定族群的一般成員,不再需要承擔過去統治團體的罪惡。正如雅斯培對紐倫堡大審評論,「這個審判對德國人的好處是,它分辨了政治領導人的罪刑,而沒有譴責所有的德國人。」[22] 我們對歷史記憶的分裂,部分原因或許來自我們對歷史正義和歷史事實的疏於追究。

雖然揭露真相、整理事實,不會自動成為足以承擔民主教育功能的歷史記憶。可是揭露真相、整理歷史卻是第一步。
在追求歷史正義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從瓜地馬拉「歷史澄清委員會」的報告《沈默的回憶》中獲得若干啟發:在保存歷史記憶的時候,避免以攻擊獨裁者為最高目標;同時不去忽略導致了大規模人權侵害事件的國內和國際政治情境和背景因素,如冷戰、古巴和美國的介入、反對派使用暴力和武裝革命手段等等[23]。我們或許也可以將焦點專注於政治權力(特別是獨裁的權力)的危險性;當別人為了人性尊嚴(他們的和我們的)而戰鬥的時候,如何不袖手旁觀;以及當我們面對一個不道德的指令的時候,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方式。這些問題即使在民主體制中,仍然沒有失去時效。我們不一定能成功地達成這些任務,然而,那卻是我們對下一代的責任。
可是這樣的民主教育,為什麼要使用我們自己的歷史素材呢?為什麼不將全人類視為一個單一的道德共同體?為什麼不用其他社會的例子,來做民主教育的素材,以避免我們社會的進一步分裂?20世紀畢竟是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世紀;如果要利用其他社會的例子,我們並不缺乏這樣的歷史教材。以色列學者瑪嘎利特曾經在不同的脈絡下討論,將全人類視為一個單一的道德共同體可能遭遇的一些實際難題。其中兩個難題是,第一,我們可能不容易找到一個機構來儲存、並且散發全人類的記憶。第二,更重要的,歷史記憶要被回憶、並成為有意義的知識和資訊,它必須屬於某一個整合的網絡關係,而非孤立的、不相關的人群和事件;家庭、地理社區、階級、國家都屬於這樣的網絡[24]。
即使將全人類視為單一的道德共同體沒有這些實際上的困難,我們仍可以更積極地假設:來自自己社會的經驗和記憶,有更強烈的教育效果。任何人造訪納粹集中營的遺跡,經過牆壁猶留有抓痕的煤氣室,站立在火化爐之前,都不可能不被震撼。可是如果犯行是來自我們自己的同胞,施諸我們自己的同胞,我們應會有更強烈的震撼。正如我們比較容易被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所吸引、所感動。
為什麼自己的同胞比較獨特?這倒不是因為原始粗糙的部落主義,也不是盲目的民族主義。而是因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同時也是一個道德共同體;在這種共同體之中,人和人彼此關連,也共同為感情和道德情操所維繫。我認為,雖然我無法證明,如果一個歷史記憶要成為民主教材,它必須是自己社會的歷史、是自己民族的回憶。雖然揭露真相、整理事實,不會自動成為足以承擔民主教育功能的歷史記憶。可是揭露真相、整理歷史卻是第一步。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台灣社會可以認真追究歷史正義;特別是在民主轉型已經近20年之後,我們可以不再蹉跎。也只有將正義還給歷史,我們才能真正告別威權年代,同時可以不再延續威權年代的族群分裂。這是我們對現在的責任。而因為這段歷史記憶對民主教育的重要功能,它也值得珍惜。這是我們對未來的責任。
(本文摘錄自《思想2:歷史與現實》;文章共分為兩篇,本文為下半篇)
[1] Paloma Aguilar and Katherine Hite, “Historical Memory and Authoritarian Legacie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Change: Spain and Chile,” p. 198.
[2] 摘自Martha Minow, Between Vengeance and Forgivenes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8), p. xii.
[3] Ibid., pp. 270-271.
[4] Desmond Mpilo Tutu, 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 (New York: Doubleday, 1999), p. 149.
[5] Wole Soyinka, The Burden of Memory, the Muse of Forgive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5.
[6] Judith Herman, Truth and Recovery, cited in Martha Minow, “The Hope for Healing: What Can Truth Commissions Do?” in Truth v. Justice: The Morality of Truth Commissions, ed. Robert I Rotberg and Dennis Thomps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3.
[7] Priscilla B. Hayner, Unspeakable Truths: Confronting State Terror and Atro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42.
[8] Ibid., p. 156.
[9] 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
[10] James L. Gibson, “Does Truth Lead to Reconcili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8, 2 (April 2004): 201–17.
[11] Jeffrey K. Olick and Joyce Robbin,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998): 118.
[12] Tina Rosenberg, The Hunted Land: Facing Europe’s Ghosts after Commun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 404.
[13] Ibid., p. 397.
[14] Mark Osiel, Mass Atrocity,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Law (New York: Transaction Press, 1997), 20.
[15] John Bodnar, Remaking America: Public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Patriot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2).
[16] Paola Cesarini, “Legacies of Injustice in Italy and Argentina,” 168.
[17] 吳乃德,〈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收於《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台北:國史館出版,2004)。
[18]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生說我「想要成名,就幹掉國王。」《聯合報》,2003/9/26。國民黨發言人說,我是為了求官(電視訪問)。中國時報社論說,「學者為政治服務,看了令人難過。」《中國時報》,2003/9/26。
[19] 陳映真,〈序文〉,曾建民等編,《文學二二八》(台北: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5-9。
[20] Hayne, Unspeakable Truths, p. 159.
[21] 感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所提供的初步統計數字。
[22] 摘自Rigby,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after the Violence, p. 4.
[23] www.shr.aaa.org/guatemala/ceh/report/english/toc.html.
[24]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pp. 79-80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系訪問副教授,台灣政治學會創會會長,《台灣政治學刊》總編輯。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和台灣政治發展,出版論文包括台灣的階級政治、民主轉型、族群關係和民族認同等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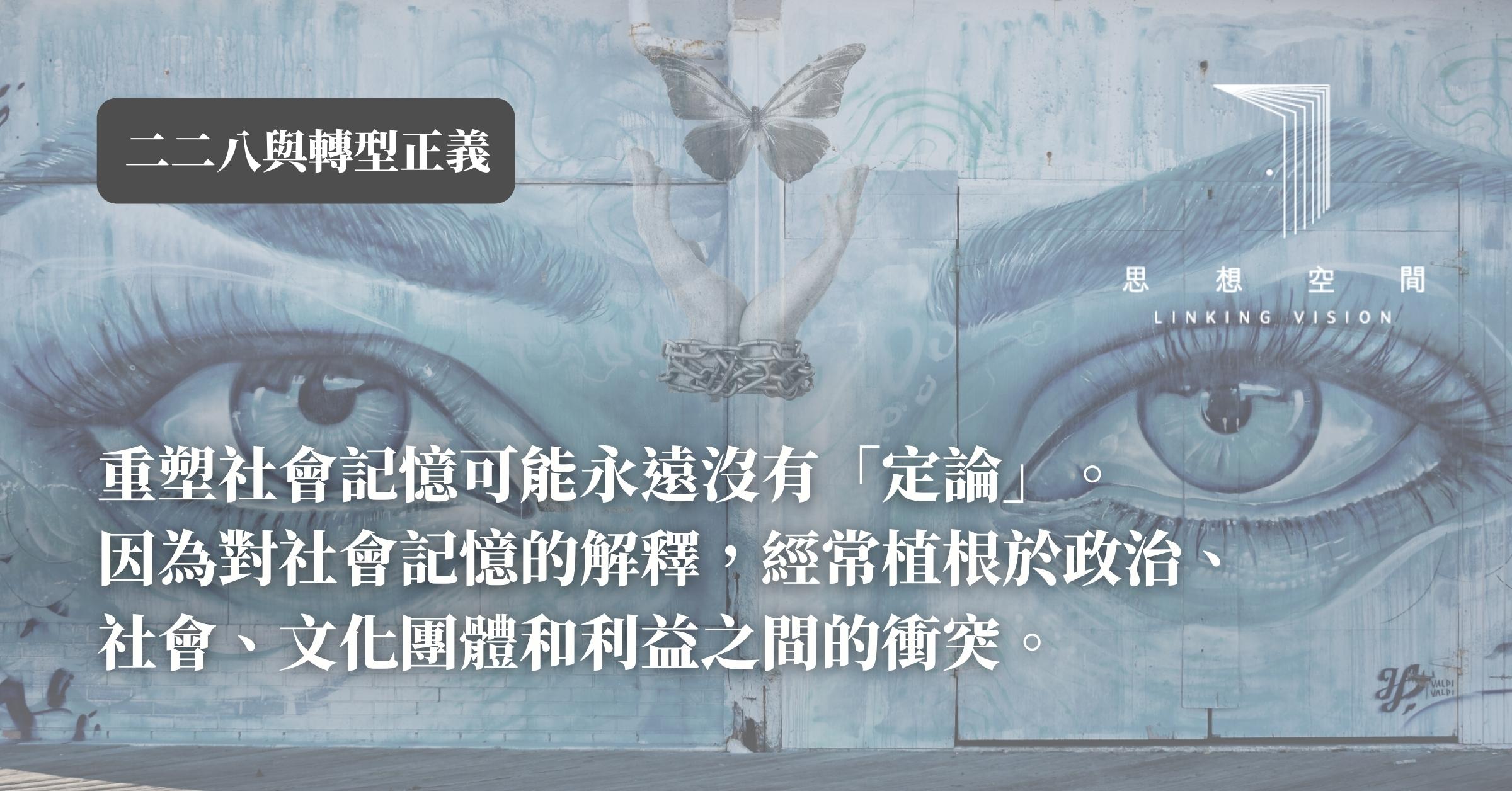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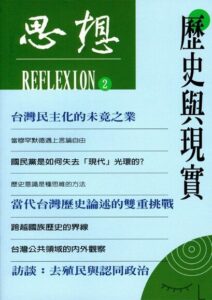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