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儒賓
編按:本書摘自楊儒賓《中國現代性的黎明》導論〈龍場一悟——良知學的登場〉。
一、前言:晚明、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
如果說王陽明是五百年來影響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一位儒家學者,這個判斷縱然無法得到學者普遍的同意,但至少王陽明獲選的機會極大,這樣的判斷很可能是可以被接受的。王陽明活在十五世紀末期至十六世紀早期之間,頭尾的年分各占一半,他的後半生穿越了以舉止荒唐著名的明武宗正德十六個年分,又進入了以專斷剛愎著名的明世宗嘉靖的前七年。這段時間並不是對思想友善的歲月,但王陽明的思想因他本人的功業及門生的努力推廣,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他的思想的解釋力道,竟深刻地衝擊了晚明的帝國。
王陽明的學問以良知學的名義著稱於世,他的影響不僅止於儒學的範圍,良知學的因素還滲透到晚明的社會及文化上去,並引發明末清初的另類儒學的反動。他的影響也還不僅見於晚明,兩百多年後,良知學在清末民初又是一支重要的思想力量,同時,明末清初思潮也曾活躍於清末民初。「良知學之於晚明思潮」、「晚明及明末清初思潮之於清末民初文化」的現象很明顯,不太需要強調。如果我們關心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我們對「晚明及明末清初思潮在清末民初」這股隔代影響的現象再下一轉語,可以說即是「良知學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如何理解的問題。
十六、十七兩世紀的中國原生現代性碰上清末傳進來的西洋現代性,兩相混合,衍化出現代中國的格局。
本書認為晚明及明末清初的重要文化議題在清末民初再度顯現,也就是在密切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脈絡下返魂重現,關鍵的時間點在甲午(一八九四)、乙未(一八九五)年間。但之前的十九世紀下半葉,也就是鴉片戰爭以後,大清王朝已不能不浸漬在歐風美雨的侵襲下,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大清王朝大不同於秦漢以後的歷代王朝者,在於代表現代西方文明的歐美政治勢力已及於中國。如何同時回應來自歐亞大陸的帝俄勢力以及海上的歐美資本主義帝國的挑戰,這個新因素已是大清王朝必須面對的政治困局。到了日清甲午戰爭大清大敗,乙未訂立馬關條約大清大輸,大清王朝朝野上下才徹底地翻轉過來,死心塌地地想到變法革新,救亡圖存,刮骨入髓的現代化工程於焉展開。這個新時代帶來重要的新議題,其衝擊之大可以說是秦漢後僅見,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議題不能不推出並擺在歷史的議事臺上。
然而,正是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向歐美敞開大門之際,它同時也向被它滅亡的勝國思潮招手呼喚,清末民初的新議題和再度流行的晚明及明清之際的文化議題交涉重疊,合流競馳,王學及明末清初的儒學思潮事實上介入民國新文化的建構裡面。學界談中國現代化的議題時,不論是新儒家的良知坎陷說模式,或是日本漢學家的中國近代思維模式,遂有將中國現代性上推至王陽明啟動的晚明思潮的論述。這樣的解釋再稍加推衍其內涵,也可以說它意味著中國現代化工程的解釋應該採混和的現代性的提法,亦即十六、十七兩世紀的中國原生現代性碰上清末傳進來的西洋現代性,兩相混合,衍化出現代中國的格局。雖然在混合變遷的過程中,混合現代性的路途並不平坦,對新議題的認識並不清楚,初步的結果也不一定可欲。但工程仍在進行中,排難解紛,批卻導款,現代化的工程總不會一步到位的。演變至今,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兩種現代性銜接的模子。
從混合現代性的角度著眼,良知學的出現不可能不是關鍵性的因素,而王陽明於正德三年(一五○八)在龍場的那場著名的一悟,則是良知學正式成立的標誌。良知學絕不會只是理學史的概念,它是中國現代化轉型重要的一環,釐清過去,正是為了正視現在,並看清未來。我們如果釐清王陽明於正德三年那晚在那麼窮困荒蠻的地區發生的精神轉化事件,了解這個事件到底啟發了何等顛覆現實的機制,我們對良知學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或許可以有另類的想法。
二、新格致說的出現
《王陽明年譜》於正德三年戊辰條下,記載王陽明經過曲折的心理掙扎過程後,於當年春天到達了貴州的龍場。龍場當時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鳺舌難語。」這是個活像《山海經》的《大荒經》的世界,也像屈原〈招魂〉裡的異類空間。年譜接著記載對人生命運已有相當了悟的王陽明之心情與行事如下:
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黙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
《五經臆說》今已散佚,王陽明所以作此書,意在表示他所悟的內容並沒有離經叛道,反而與儒典是相合的。年譜是王陽明的弟子錢德洪等人在王陽明逝世三十五年後初步編成的,其時已是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年譜所以有上引這段話,潛臺詞當是當時頗有人認為王陽明體悟的《大學》格致說是新說,未必符合聖人本意。所以王陽明要以《五經》之言印證自己的體證,以示所悟格致新說雖是臆說,卻與聖人本懷若合符契。
龍場一悟帶給王陽明極大的自信,良知學正式成立。年譜記載他隔年即開始暢論「知行合一」的旨趣,而且席山、徐愛、冀元亨、蔣信等著名門生已圍繞著他,開始研習良知學的真諦。王陽明的講學生涯一啟動,即不可遏止,縱然他以後公務倥傯,戎事雲集,而且在惡劣的政治文化氛圍下,無意間即捲入糾纏不清的政治鬥爭中。但他從來不廢講學,良知學隨著他的足跡散布到江南、西南,甚至大明江山各地。他晚年居越,其時隨他學習的門生多到甚至居不能容。錢德洪記載嘉靖二年之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剎,徙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環繞在旁的門生已來了一年多了,姓名竟然還記不全。教學時,王陽明甚至要他的一些及門弟子等人分擔工作,擔任良知學的講師。講會的規模真是不小了,五十而知天命以後的王陽明親眼目睹了良知學流行的榮景。
什麼叫「致知在格物」呢?他的「格」字意指感而正之。
上述所說,只是越中一地的盛況。良知學之特殊者,在於其學並沒有人亡政息。相反地,王陽明逝世以後,類似的講會還會繼續在各地,尤其是王陽明過化之地,如野草蔓延般地散開。一場講會,甚至可聚集聽眾達四、五萬人。講會之盛,遠邁宋元,開儒學史上未有之新局。萬曆早期,張居正執政,他對書院、講會特多禁忌,不是沒有原因的。一位以嚴厲整肅天下秩序自許的大政治人物,在沒有學術自由理念的背景下,他怎能容忍最有動盪社會潛能的良知學的講會呢?我們如不了解良知學,毫無懸念地,我們即無法了解晚明的社會文化。
關鍵還是要回到正德三年龍場的那個夜晚,王陽明「大悟」,所悟的內容為何?為何窮鄉深夜發生的一場私人性的事件竟能攪動寧靜的大明天下。據年譜所說,其內容當是「格物致知」的道理,但「格物致知」的議題自從經過程伊川與朱子的轉手的解釋,它的解釋變得有名地複雜,成了一潭難以澄清的濁水。哪家的「格物致知」說的提問因此不能不出現,龍場大悟,到底這場和「格物致知」有關的悟覺事件該如何解釋?
王陽明的龍場之悟所悟者是「格物致知」的道理,此事見之於年譜所記,得到他的幾位著名門生的印可,而且其語很可能出自王陽明自己所說,事無可疑。如果我們要追究王陽明所悟的內容是哪家的「格物致知」?答案只能是王陽明自家體證的新格物致知說,他的新格物致知說就是《大學》原本的「致知在格物」一句而已。但什麼叫「致知在格物」呢?他的「格」字意指感而正之。用他自己的說法,這個新說的命題如下:「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知(推拓良知)是格物窮理的前提,良知推拓出去了,物得其理,物得其理是後得的效應。主體的良知是實踐的起點,主體所對的客觀世界(社會與自然界)的意義是有待良知賦予的,它處於受納端的位置。但為什麼良知會賦予意向之物「理」的性質?為什麼物的價值地位可以由良知決定?顯然,王陽明的良知具有特殊的規定。我們後文還會提到,他的良知是儒道性命之學中的「本體」之另稱,它不只是道德主體的涵義。
王陽明的新格致說對朱子的舊說作了哥白尼式的迴轉,兩說對衝開來。朱子的舊說是王陽明在追求成聖路途上最大的障礙,難以攻克的鐵關。
我們還是回到「格物致知」一詞的物—知關係看,王陽明的新說是有針對對象的,此事絕無可疑。王陽明的格物致知說針對朱子的經典說法而來,朱子論格物致知:「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致知(體得心知)是窮理的後續效應,客觀世界的理被朗現後,主體的理才同步呈現。雖然理的體現沒有先後內外之分,但主體所面對的客觀世界的理有實踐秩序上的優位性。
比較兩說,兩者的實踐程序正好顛倒,王陽明的新格致說對朱子的舊說作了哥白尼式的迴轉,兩說對衝開來。朱子的舊說是王陽明在追求成聖路途上最大的障礙,難以攻克的鐵關。他年輕在京時,為求格物之義,日夜格庭前之竹,結果竟格出一場重病來,這是樁有名的故事。他還曾一度因為此挫折,而自認此生已和聖賢之學絕緣。如果不是他解開了纏繞多年的謎團,王陽明不會在龍場那個夜晚,因大悟而「不覺呼躍」。
王陽明以新格致說取代舊格致說,此一思想的轉折所以會帶來震撼社會的效果,關鍵在於王陽明的新格致說切斷了主體與外在世界的連結。他的致知即是致良知,也就是推拓良知往外作用;格物即是事物獲得良知所賦予之理,每一事物因而各得其正。一切的判斷當下由主體出發,主體獲得空前的自由,良知教是徹底的頓教。相對地,在朱子的格致論中,雖然說格物所得的物理也是心中之理,所以朱子學不接受「義外」的批判。但在實踐的過程中,以我心之知去格對象的物之理,物理明後心知之理也跟著明,這樣的向外一彎的曲折過程是不可繞過的環節。所以只要是朱子學,一定是漸教。行動的主軸一定是以心知格外物–物之理引動心之理–內外相合後,才有後續的動作。在朱子格物的過程中,物是泛存在論的事事物物,物本身的理是物在其自體的理。朱子的客觀世界的物理有詮釋學的優位性,「物理」包含聖賢的經典、社會的風俗禮儀、家族的倫理位階等等,它們都享有先於主體運作的權威,它事實上主導了格物者心靈的方向。在朱子學的世界中,我們很難想像可以看到王陽明所說的「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興師」這類顛倒傳統儒家價值體系的說詞,這種不顧禮儀規範而純任良知作主宰的主張乃陽明家風。
朱子的儒學常被稱為理學,王陽明的儒學則被稱作心學,理學/心學的稱呼相當籠統,是大寫意的筆法。但大寫意突顯了整體的風貌,未嘗沒有超乎形似外的神肖。朱子的理學確實以求得外內相合的理為核心要義,他的思想結構必然是漸教的、歷程的,過程的主客對立與終局的主客合掌同時成立。就歷史的經驗考察,朱子學容易導致保守的主張,有利於社會的穩定。相對地,王學瓦解了主體以外的任何權威,事物的理原則上不是內在於事物本身,而是主體賦予(致)事物,事事物物才能得到自己存在的正當性(各得其理)。行動的主軸在良知,良知不接受任何外在的軌約,只對自己負責。良知學本質上即和經典的傳統、社會的風俗、朝廷的體制有結構上的矛盾,良知永遠處於最上階的位置,良知學對社會的衝擊力道的根源即在良知概念本身。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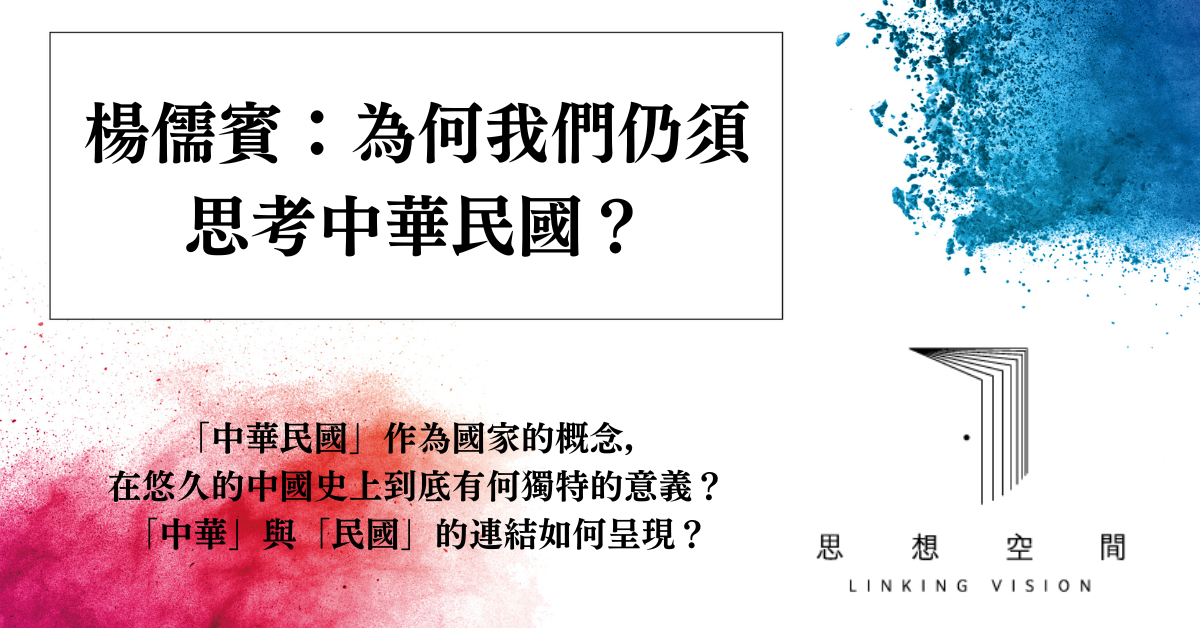
楊儒賓:為何我們仍須思考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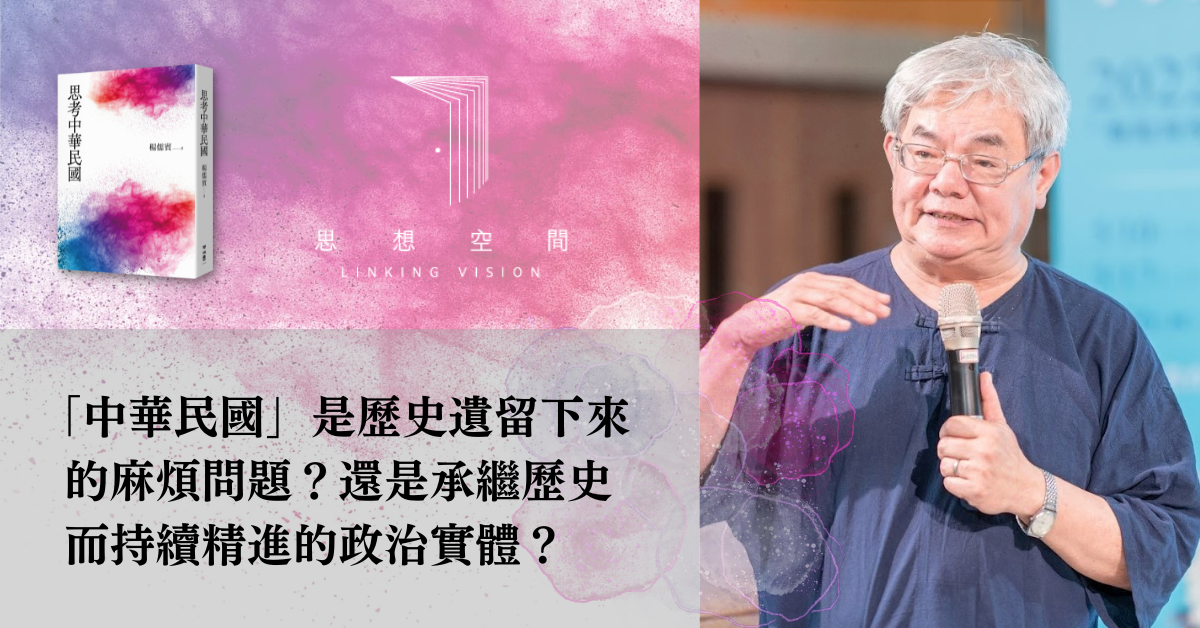
有文明的高度才有尊嚴——超越統獨,中華民國應回到兩岸共生共利的原始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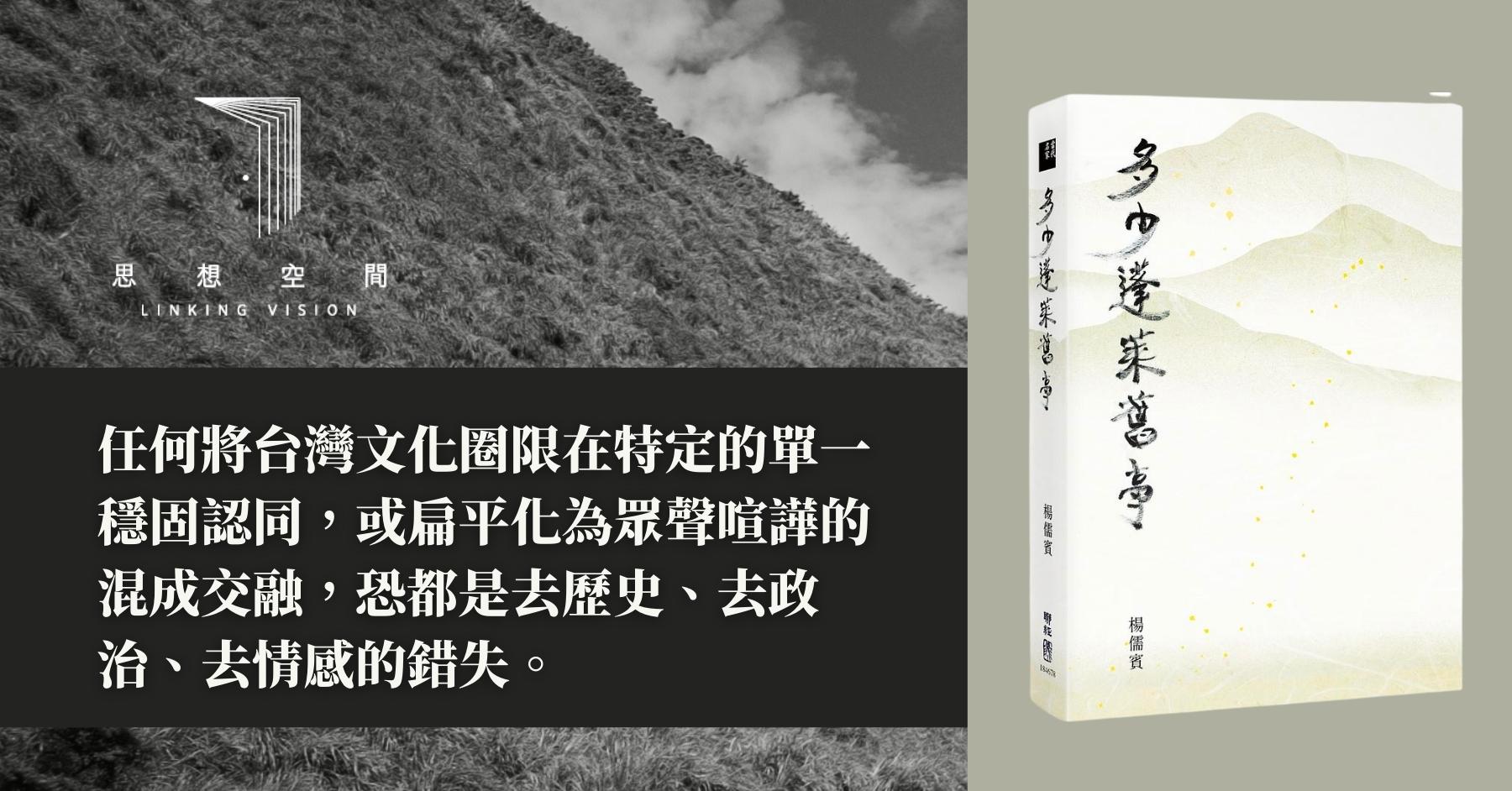
張小虹:歷史的左手——讀楊儒賓《多少蓬萊舊事》
| 閱讀推薦 |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出版《儒家身體觀》、《儒門內的莊子》、《原儒》、《1949禮讚》等書,並有譯著及編著學術論文集多種,也編輯出版了多冊與東亞儒家及近現代思潮為主軸的展覽圖錄。目前從事的文化工作以整編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的書畫墨蹟為主,學術工作則嘗試建構理學第三系的系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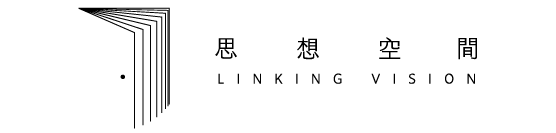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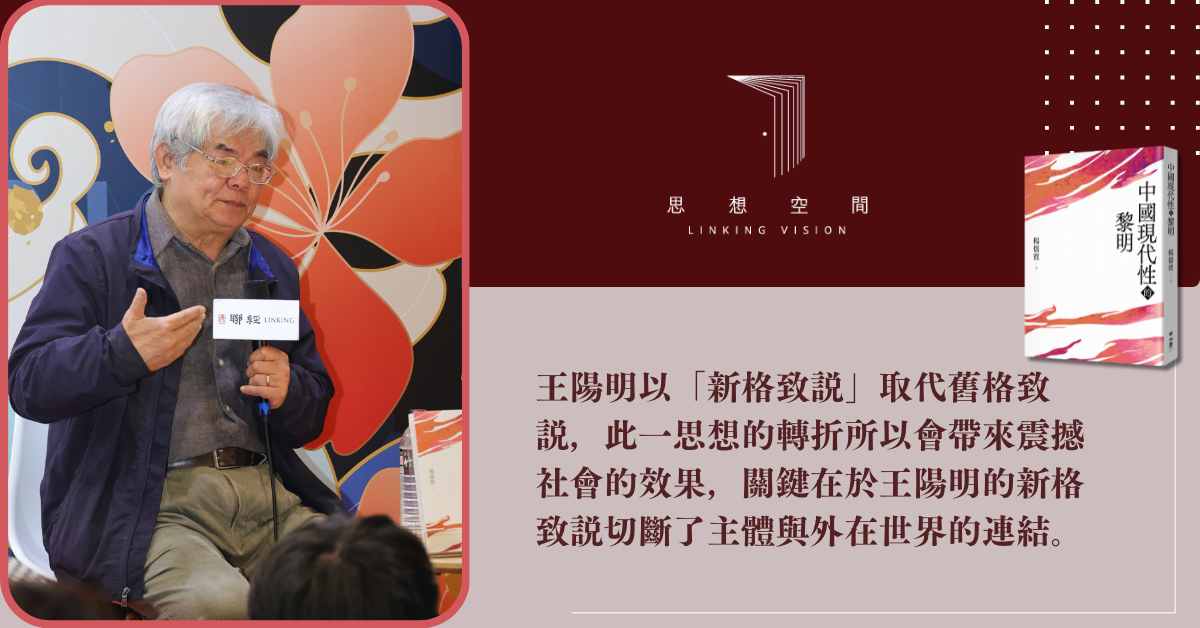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