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瑞明,曾任記者、教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香港人應該思考的40個哲學問題》、《年青生活哲思20則》、《全球正義與普世價值》(合著)、《上有天堂的地方》,編有《守住這一代的思考》、《吾考通識,通識唔考》,喜寫書評。
哲學軌跡 | 曾瑞明 and 專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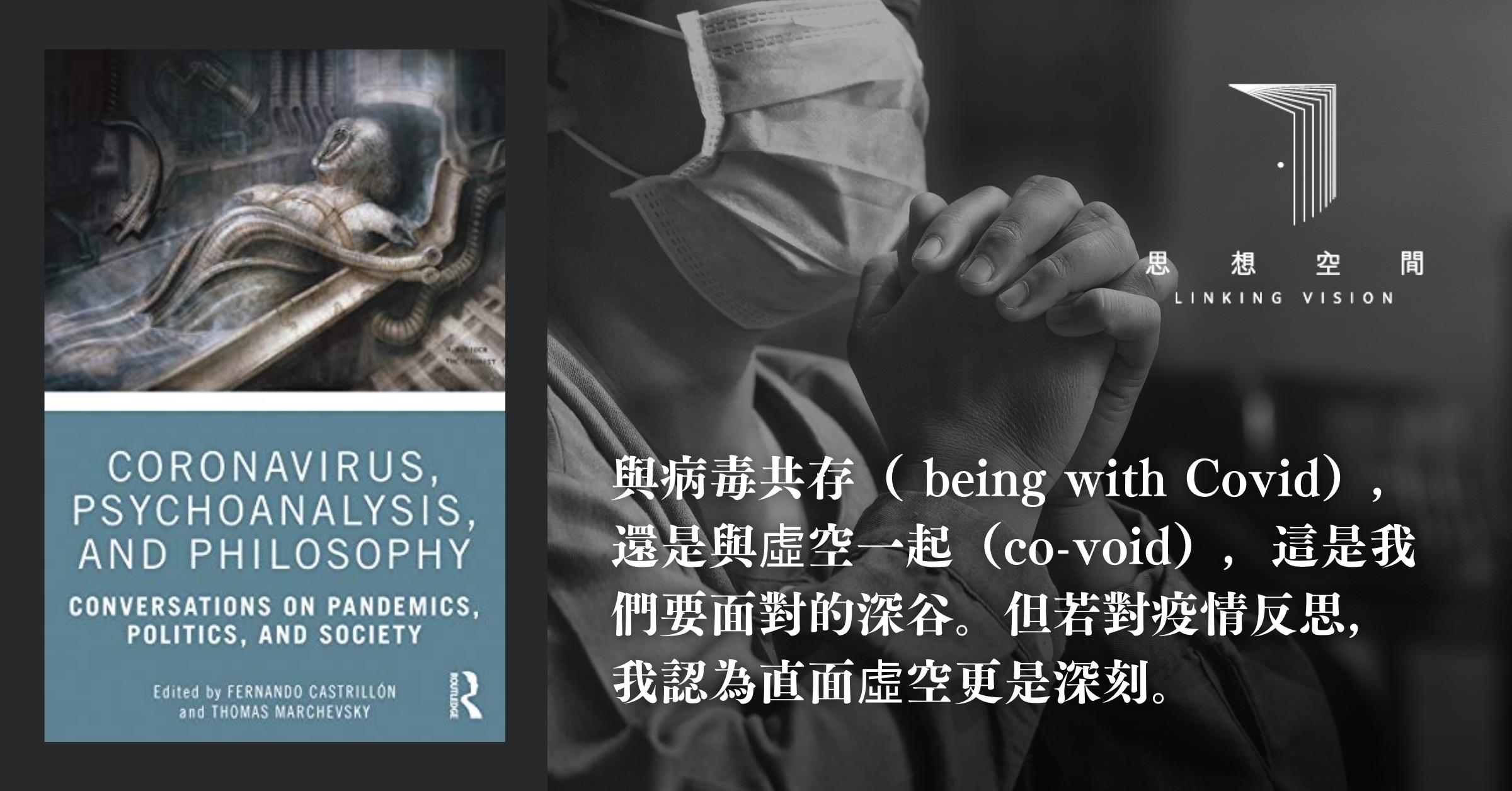
文/曾瑞明(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政治哲學和倫理學)
總覺得對新冠疫情沒有像樣的反思,社會急於復常,也像無可厚非。但我們現在身處的,還是三年前的世界嗎?似乎大家都暗裡知道,我們回不了去。
但究竟世界改變了什麼?還是老樣子的世界格局︰民族國家、資本主義、大國較勁,我們受阻受困,但沒有革命因此出現。甚至,我們的權利和自由都倒退了。一些地方有無日無之的封城、圍封,又有不少以控制疫情為名的監測系統,要每個人申報自己的行蹤……我們真有信心一切能如常?
哲學學者們也紛紛對世界作出反思。Fay Niker和Aveek Bhattacharya編的Political Philosophy in a Pandemic: Routes to a More Just Future就引領我們去思考疫情引發的政治哲學問題,這也是一本比較標準的,分析式的政治哲學著作。而由Fernando Castrillón、Thomas Marchevsky編輯的Coronavirus, Psychoanalysis, and Philosophy也引起我的興趣。一來是因為它收錄了一些歐陸哲哲學家如讓-呂克 · 南希(Jean-Luc Nancy)、喬治 ·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羅伯托 · 埃斯波西托( Roberto Esposito)的文章,還也有精神分析學家的文章。這都不是筆者比較熟悉的英美哲學背景,但在學科的交匯下,究竟我們會否看到更廣闊的風景?這是筆者期待的。
這本於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EJP)出版,特別強調文章出版的日期,原因是每個發言者,其實只可按他們當時所知所感,去發表看法。事後的孔明再看他們言論,會覺得好笑也說不定。但也許,更耐心的細嚼,比一笑置之會更有得著。
在疫情高峰期,阿甘本的說法好像「離地」至極,忽視了疫症的「厲害」;但退潮後,我們似乎又看到他的理論效力。在國家體制下,人算是什麼?疫情後,人的地位更高,還是更低?
阿甘本的一篇文章說起
在2020年2月26日,義大利著名哲學家阿甘本出版了一篇叫〈流行病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an Epidemic)的短文。他質疑政府和傳媒是否在「所謂疫情」下,制造恐慌,營造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群眾則為了追求安全,隨意讓政府限制我們的自由。
這篇文章因版權問題並沒有收在本書,但卻是整個討論的引發點。這當然跟阿甘本的一貫看法相關。他不認為國家只是提供福利,或守者守夜人的角色。他認為國家是一個全能式的權力(a totalizing power),可控制我們的生與死。
主權(sovereignty)把生命分為兩種,一是政治生命(bios) ,一是自然生命,是裸命(naked life),即人作為動物那樣的生存狀態。國家可以透過政治認同和代表,把裸命轉化為政治生命。這當然也意味它可以撤銷我們的身份,把我們的權力和保護拿走。
國家宣佈例外狀態,就是容許我們拿走任何人的政治確認。過去,納粹可以將猶太人送到集中營,正是現代國家的結構所導致的,國家可以對我們的生死作決定的重要一例。被美軍用於拘留和審訊、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等地區的戰事中捕獲嫌疑人的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和美軍虐待伊拉克戰俘的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則是較近代例子。而疫情期間的限聚令,也變相奪走了集會的自由。
對身體的控制,可追溯至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論,本書收有《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的選段,國家至17世紀開始,就對人的生物生活監管和控制,這被稱為生物權力(biopower),透過科技的的權力來達致既定的價值和目標,形成了生物政治(biopolitics)。全方位,近乎強迫的疫苖接種就反映了這點,打針成了復常的條件。若要工作、出入公共場所,就必須證明自己已接種疫苖,否則形同沒有自由。(編按:目前香港政府推行「疫苗通行證」,以限制未完全接種疫苗的民眾出入特定場域,例如餐飲店、健身房等。)看福柯描寫十七世紀一個小鎮如何為何控制疫情、如何禁止民眾外出、如何通過一層一層的管理,這幾年也都歷歷在目。
當然,在疫情高峰期,阿甘本的說法好像「離地」至極,忽視了疫症的「厲害」;但退潮後,我們似乎又看到他的理論效力。在國家體制下,人算是什麼?疫情後,人的地位更高,還是更低?
要區分近期發生的事情和長遠過程:初期疫情不明朗,也許我們要加倍小心病毒;但長遠來說,我們更應關注生物政治。
南希的回應
另一位師承德希達(Derrida)的哲學家讓 – 呂克 · 南希則在2020年2月27日發表了一篇名為〈病毒的例外〉的文章,調侃了他的朋友阿甘本。他指出疫情可以威脅我們整個文明,這次是病毒帶來的例外,他認為阿甘本提出的只會是轉移注意力,而非政治反思。南希還笑說,三十年前阿甘本曾叫他不要做心臟手術,若聽阿甘本的話,一早死了。阿甘本今次的文章,可能是他精闢意見的一次「例外」。
不是每個人都選擇「一笑置之」。義大利哲學家羅伯托 · 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在2020年2月28日在〈治愈到底〉(Cured to the Bitter End)一文中,指出了南希跟阿甘本的分別在於不接受生物政治的範式(the paradigm of biopolitics),但他認為生物生活(biological life)、政治和生物政治都是當今政治衝突的徵結,認為我們難以否認生物政治的存在。他也提醒我們,要區分近期發生的事情和長遠過程:初期疫情不明朗,也許我們要加倍小心病毒;但長遠來說,我們更應關注生物政治。因此,南希和阿甘本可以是沒有衝突的。埃斯波西托也提到義大利的混亂情況,他認為這像一個失敗國家多於極權國家的作為。這也提醒我們要對實際脈絡多加留意。
對此,南希的回應是,「生物」和「政治」都不是精確定義的詞語,所以沒有使用生物政治這個詞。其後阿甘本在2020年5月10日在其博客發表了一篇名為〈生物安全與政治〉(Biosecurity and Politics)的文章,他這樣寫道︰
當政治被經濟取代,當要管治時,就需要引入生物安全的新典範,而其他要求則會被犧牲。我們要麼有合法性去問這種社會是否仍能定義自己是人性的,要麼會損失了一些敏感的關係,面孔、友誼、愛,都可以完全被抽象和假定是虛構的生物安全犧牲掉。(筆者試譯)
我們學習到的是……
我們判別彼此的言論時,除了時效性外,牽涉到具體情況跟理論框架的配合,還有更普遍性的考慮,就是理論有沒有預示性和能否顯明更多問題。無疑科學是我們必須仰賴的,但是當科學也無可避免地混入政治的肌理時,我們就必要更小心所謂衛生和健康是什麼東西。筆者不敢認為生物安全是純然虛構,但它跟政治聯繫時,我認為在阿甘本身上學到的無疑是更多的。特別是在不民主的地方,以安全為名的壓迫和操控實在是比比皆是,因此,筆者以為他的理論會更有預示性和重要性。
篇幅關係,在本文未能著墨於本書的精神分析部份。但就用他們的風格作結吧。精神分者者會作以下類似的分析,與病毒共存( being with Covid),還是與虛空一起(co-void),這是我們要面對的深谷。但若對疫情反思,我認為直面虛空更是深刻。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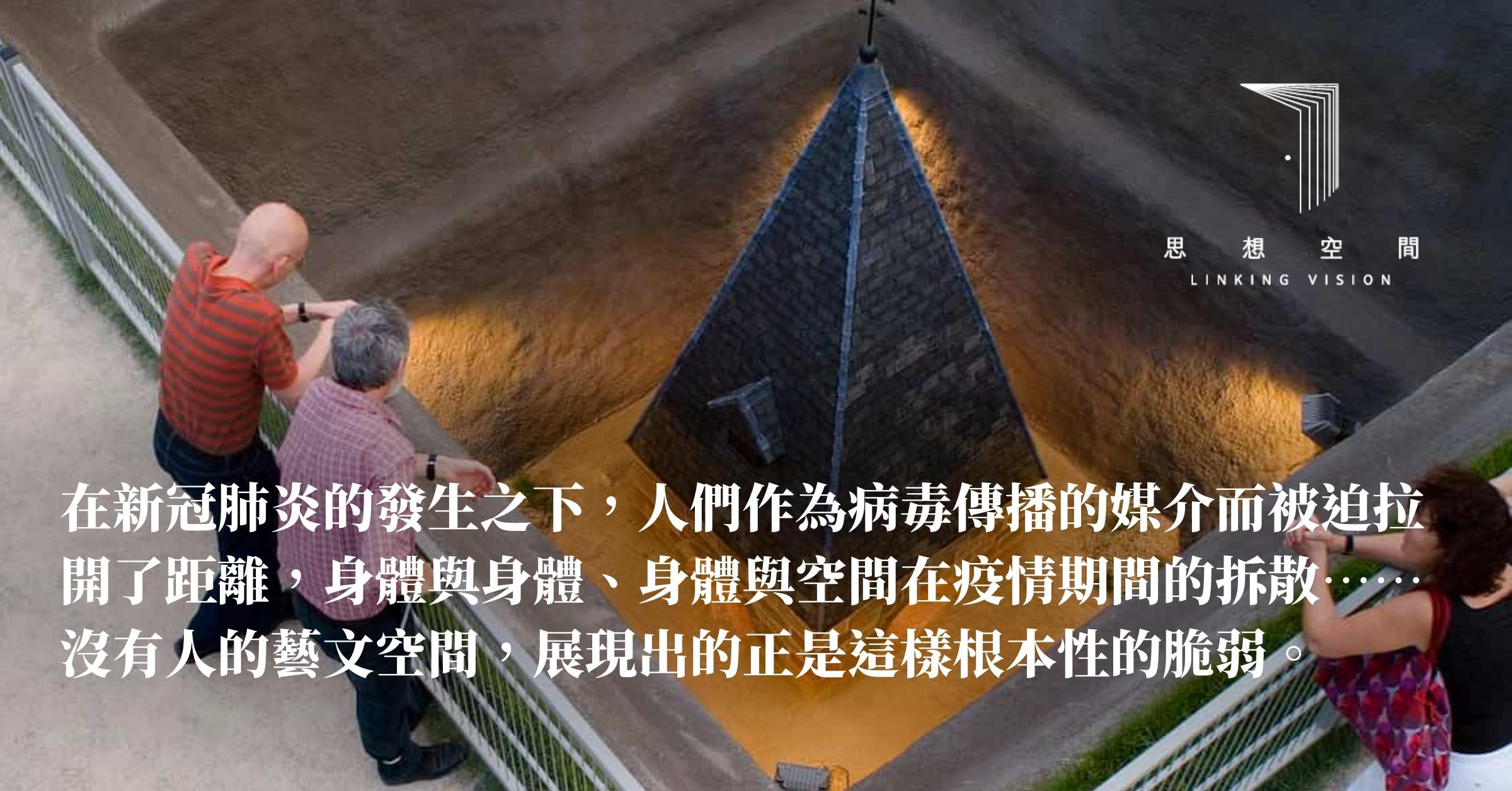



曾瑞明,曾任記者、教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香港人應該思考的40個哲學問題》、《年青生活哲思20則》、《全球正義與普世價值》(合著)、《上有天堂的地方》,編有《守住這一代的思考》、《吾考通識,通識唔考》,喜寫書評。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