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蘭登・波瑞爾(Brendan Borrell)(資深記者,《疫苗戰爭》作者)
編按:Covid-19侵襲全球至今已兩年,從毫無準備、到疫苗普及,中間經歷了哪些波折?哪些人又在這場與時間的賽跑之中作出努力?過去,最快推出臨床疫苗的時間是10個月;但是,這次世界的要求是:60天。記者布蘭登・波瑞爾透過訪問超過百位疫苗研發競賽中來自官方與民間的關鍵人物,爬梳世紀瘟疫始末、深入分析Covid-19疫苗研發實況,書中也透露了一段罕為人知的事件:武漢疫情爆發時,一位美國疫苗專家曾第一時間親臨現場。他親歷、見證了什麼?又如何將封城期間的疫情狀況傳播出來?
本文摘自《疫苗戰爭:全球危機下Covid-19疫苗研發揭密,一場由科學家、企業、政府官員交織而成的權力遊戲與英雄史詩》,第三章〈沒有禁止,也沒有授權〉,標題為編者擬。
| 出場人物簡介 |
麥可 ‧ 卡拉漢(Michael Callahan):衛生部防備應變處特別顧問、麻薩諸塞總醫院員工內科醫生
羅伯特‧凱雷克(Robert Kadlec):華盛頓特區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總部,主管衛生部防備應變處的助理部長
布列特‧吉羅爾(Brett Giroir):華盛頓特區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總部,主管衛生的助理部長
亞歷克斯‧阿札爾(Alex Azar):華盛頓特區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總部,部長
中國官員正計畫加強武漢的隔離措施,甚至禁止居民外出購買食物。卡拉漢搭乘小船——黑市通道——渡江並返回南京,在那裡他與同僚和武漢兩家醫院的加護病房架設視訊連線,以便提供建議和追蹤病患的情況。
武漢原本不在麥可 ‧ 卡拉漢(Michael Callahan)一開始的行程裡。他在一月十七日經過約三十小時的飛行後,踏出降落在中國南京的一架飛機。這位美國醫生期待見到他的中國朋友,兩位二〇〇二到二〇〇三年SARS疫情爆發期間他在香港認識的抗疫工作者。他一直藉由為他們的學生和子女寫推薦信給美國大學,還有每隔兩年訪問中國三到六個星期以從事禽流感的合作來保持與他們的友誼。「我們已經變得更老,也更禿,但我們還是同樣的人。」他說。
身材削瘦的卡拉漢年輕時是救護車隨車醫生和住院醫生,他曾在飛機墜毀和登山意外的情況下拯救人命。他稱這些孤立的事件其實是同一件事,都是他初始熱情的延續:災難醫療。在嘗試過海嘯和地震的醫療救援後,他開始參與疫情救援。第一次經驗發生在一九九三年,當時他跟隨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病毒特別病原體分部,調查美國西南部一場致命的漢他病毒疫情爆發。很快的,他開始搭乘飛機往返亞洲和非洲,每次有疫情爆發,他似乎總是第一個出現在現場。有一次他必須為一名發狂的伊波拉病患注射鎮定劑,同時得避免他自己穿的生物防護衣被札出洞來。「你要是被傳染了,就非死不可。」他說。
在二〇〇〇年代初,卡拉漢的生涯第一次出現出乎意料的轉折,當時美國政府派遣他從事一項不同於尋常的任務。他的目標是與俄羅斯和前蘇聯共和國時代最機密的生物武器實驗室的一些科學家組成聯盟。「這些人為俄羅斯管理國家死亡研究所,不是嗎?」卡拉漢說。他的工作是協調他們的力量以對抗疾病,而不是將它武器化。他記得與這些殺手站在一個苔原湖旁釣鱒魚,然後邊烤魚和聽俄羅斯民謠,一邊聽他們叨絮如何把孩子送進一所好大學。他們交給他禽流感病毒的樣品,並建議他如何躲避俄羅斯可怕的聯邦安全局。「今天晚上別離開。」有一次他們告訴他。又有一次則說:「你現在必須離開俄羅斯!」當他們的科學家之一意外地用裝著致命病原體的注射器戳到自己時,卡拉漢奮不顧身地協助治療她。
後來卡拉漢加入國防部,在那裡從事加速疫苗與藥物發展的工作,和建立一套國際疾病監視系統,透過十幾個國家的地方醫院協助,其中包括墨西哥、奈及利亞和印尼。現在已經五十七歲的卡拉漢已回歸平民生活,他的頭髮確實逐漸稀疏,日子不再像過去那麼忙碌,但他也沒有鬆懈下來。
位於長江畔的南京是中國古代的南方首都,和今日的科學中心。那裡是躲避波士頓冬季的宜人地方,因為卡拉漢在波士頓哈佛大學的麻州總醫院有一份兼職的工作。卡拉漢帶著行李坐在金茂威斯汀飯店大廳,服務員把房間的鑰匙卡遞給他時,他不禁笑了起來。這棟旅館有四百個房間,而我每次都住進相同的房間?他心想。那是個很好的房間,清潔的浴室、厚實的床墊,那也是一條線索。自從中國駭客偷走一個裡面有他的高階安全許可證明資訊的資料庫後,卡拉漢知道有人可能會監視他的一舉一動。「我不是長得那麼帥的男人,但在我上酒吧喝啤酒時,你可能以為我是布萊德‧彼特(Brad Pitt)。」他說:「我就是目標。不過,你知道,我們都受過那種訓練。」
卡拉漢幾個星期來都在密切注意來自南京上游約五百公里處武漢的訊息。卡拉漢抵達後不久,他的中國醫生同僚注意到一則協助控制疫情的全國性警訊。卡拉漢想到還有其他重災區就感覺胸口緊繃起來,那種高度警戒的狀態讓他感覺特別充滿活力是有原因的。如果他到了武漢,他知道不能告訴妻子自己的計畫,那只會讓她徒增憂慮。他不能隨便告訴其他人,畢竟,他沒有獲得到武漢旅行的官方許可。「那是沒有禁止、也沒有授權的情況。」他說。
他還是去了武漢,並住進另一家旅館,避免引起注意,然後等著他的朋友傳訊息給他。「他們必須檢查以確保情況對我很安全。」在一月二十二日,卡拉漢穿上醫療防護衣、戴上N95口罩和護目鏡,以便通過武漢市中心醫院的入口,那是一座從該市空曠的街道拔地而起的長靴狀玻璃建築。他在那裡的同事把他登記為「臨床客座教師」,這個頭銜讓他能以觀察者的身分進入病房。第二天武漢封城,卡拉漢剛好進到這場疫情爆發的原爆點。
他很快從呼吸愈來愈急促、心情愈來愈絕望的武漢感染病患身上,看到熟悉的恐怖和困惑的眼神。也許他們從空氣中吸進了幾百個病毒分子,然後入侵者降落在他們的鼻毛上,或深入鼻竇和上呼吸道。兩天過後,受害者感覺喉嚨背面發癢,那是情況不對勁的第一個跡象;然後一些地方開始有幾個細胞死亡,釋放出求救的化學訊號。在冠狀病毒感染的初期階段,免疫系統發動一波一般性的防衛,加快製造黏液以淹沒入侵者,並在病原體和細胞間創造一種實體障礙。它也放大那些求救訊號並動員白血球——免疫系統的步兵,這就是咳嗽和打噴嚏開始的時候,也許還有點發燒。由於從未暴露在這種病毒下,人體並沒有對抗它的手段。
逐漸的,更特化的白血球抵達現場,這個程序在年齡較大和免疫系統較弱的病患可能得花更久的時間。在這段加速期,身體會啟用特定的武器來對抗病毒:抗體。抗體是有黏性的Y形蛋白質,會附著在其他分子上。你的血清有五分之一的重量是由這種白色的黏稠物構成,透過組合的魔術,身體製造的抗體種類有如仙女座星系的星星,多達一兆種。其中有些抗體會碰巧黏住冠狀病毒,但只有極少數抗體能在個別的病毒感染新細胞前使它失去能力。然後,這些被抗體黏住的病毒被掃除乾淨,由身體內的家庭清潔工吸走。
在抗體反應仍在升高時,冠狀病毒大體上可以任意地複製自己,這是病毒的大好機會。病毒一次一個地咬破人體細胞,將它們變成有傳染力的粘液。粘液流下受害者的喉嚨,進入並感染更難清除的肺部。身體發動它風險最大的防線——派出殺手T細胞,去尋找被感染的細胞,並觸動它們的自毀按鈕。隨著肺部裡面的戰區白熱化,附帶傷害變得無可避免。一半的免疫系統與另一半打仗,紅血球爆破並吐出它們的血紅素,一種富含鐵的分子,會在肺部造成大破壞,就像不小心把手榴彈掉在戰壕裡。隨著受創的肺部充滿垂死細胞的有毒黏液,病患感覺就像要溺斃。這種絕望的感覺在病患實際被溺死前很久就已發生,所以醫生的職責就是維持病患的鬥志,用自己肺部的力量來對抗疾病,並以輔助的氧氣、類固醇和止痛藥來協助他們。當藥物在病患身上不再發揮作用、當氧氣也幫不上忙、當脈衝式血氧機指數掉到七〇、六〇、五〇……卡拉漢的同僚唯一能讓病患活著的方法是:麻醉他們,並為他們接上呼吸器。
那些呼吸器裝在有輪子的基座上,所以可在病患不再需要用它時很快移至下一位病患身旁。但是卡拉漢也看到,病患被接上呼吸器的速度要比脫離呼吸器的速度快得多。病例數從數十個激增到數百個,每一次呼吸管被插入某個人的喉嚨,空氣中就充滿了感染的病毒分子霧。卡拉漢幫助他的同僚設置所謂的層流式(laminar-flow)房間,就像他在SARS疫情時所做的一樣,把風扇安裝在窗戶以便把被汙染的空氣吸出去。醫院的房間即將用罄、呼吸器即將缺乏,即使在這個早期階段,他就可以看出這場疫情將比SARS更加嚴重。
卡拉漢正在目睹最戲劇性、最立即帶來衝擊的嚴重感染,即它對肺部、心臟和腎臟造成的壓力。但當你如此刺激免疫系統時、當身體不斷引爆這些手榴彈時,有些損壞是無法修復的。那些足夠幸運能活著離開加護病房的病患,出院後將無法恢復正常的生活,他們將繼續有呼吸困難的問題、可能一輩子咳嗽不斷,關節和胸部的痛楚也將在餘生中如影隨形。有些人可能有腦霧(brain fog)問題,使他們難以專注,經常感到恐慌、抑鬱揮之不去;其他人可能定期出現發燒和畏寒,伴隨著心跳加速或其他心律不整的症狀。卡拉漢知道,即使是較不嚴重的冠狀病毒感染也可能導致人體的正常機制混亂,使人出現皮疹和掉頭髮。
卡拉漢用了將近一星期時間在現場協助他的同事保持醫院的運作,學習病毒對人體的侵害,並記錄醫生們用哪些藥物來對抗病毒。中國官員正計畫加強武漢的隔離措施,甚至禁止居民外出購買食物。卡拉漢搭乘小船——黑市通道——渡江並返回南京,在那裡他與同僚和武漢兩家醫院的加護病房架設視訊連線,以便提供建議和追蹤病患的情況。卡拉漢知道他必須向在美國政府的朋友報告自己看到的狀況。
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總部位於韓福瑞大樓(Hubert H. Humphrey Building)裡面,一座粗獷主義的八層樓水泥建築,跨立在一條穿過首都的地下公路隧道和一條輸送首都汙水的主要下水道上。此部門控制超過一兆美元的預算,比整體的軍事預算還高,而它號令的機構包括國家衛生研究院、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簡稱食藥局)、美國聯邦醫療保險與補助服務局(Center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CMS),和幾個較不為人知的分部,其中之一即衛生部防備應變處。
「我最有信心的兩個資訊來源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凱雷克說:「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過去兩天來,中國湖北省報告的確診病例增加了65%,從2744例變成4515例……
在六樓,凱雷克陰森、沒有窗戶的辦公室裡面一團亂。辦公桌和茶几上幾乎每一吋空間都堆疊著高聳的文件、活頁夾和牛皮紙夾;一小塊空間放著一碗糖果,上面插著一面美國國旗。
在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凱雷克和布列特 ‧ 吉羅爾(Brett Giroir;卡拉漢的前導師,現任衛生部主管衛生的助理部長)都接到卡拉漢的電子郵件。他告訴他們,他看到的資料顯示病例的數量是向世衛組織報告的四倍。有二萬三千人與確診者接觸而接受每日觀察。在他密切觀察的二百七十七名病患中,有二十二人已出院,一人死亡。病毒在人體內保持活躍約九天,他認為這對病患是「一大挑戰」。冠狀病毒最狡猾的一個特性是,有些人感染後病況很嚴重,有些則不嚴重。這種病毒較難控制,因為它們可能輕易躲過檢測。卡拉漢寫道,無症狀和輕症病患「將把病毒散布到遙遠的社區」。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是一種嚴重的疾病,但其致死率卻因人而異。它不是有一半感染者死亡的伊波拉,但它比導致六十五歲以上感染者出現0.1%死亡率的季節性流感嚴重。他警告凱雷克和吉羅爾,在第一次SARS疫情爆發中有效的單株抗體治療法,已證明在對抗新型冠狀病毒中無效。
凱雷克認識卡拉漢已二十年,而這位傳染病醫生現在見過的新型冠狀病毒染病人數,可能超過任何其他美國醫生。但卡拉漢說的與凱雷克稍早從疾管中心得到的保證,或與來自情報圈幾近空白的資訊並不一致。「我最有信心的兩個資訊來源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凱雷克說:「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過去兩天來,中國湖北省報告的確診病例增加了65%,從2744例變成4515例,這證實了卡拉漢說的較可信。
凱雷克開始想像美國境內可能展開的大混亂,而避免危機將是他的職責。在上午九點與部門的一些領導人開會後,他把吉羅爾拉到一邊,問他對卡拉漢的訊息有什麼看法。理著平頭髮型、下巴方正的吉羅爾外表威武,總是穿著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USPHSCC)的深藍色制服,因為他是該團的首席醫生。他同意情況似乎很嚇人,他們必須說服衛生部團隊的其他人要升高美國對抗這種病毒的因應措施,包括說服部長亞歷克斯 ‧ 阿札爾(Alex Azar)。
在幾天內,凱雷克已和卡拉漢簽訂六個月的工作合約,要他藉由他的中國連絡人的情報,協助衛生部防備應變處提供病毒情報,並建議如何在美國境內因應病毒。「實體地點和會議將由衛生部防備應變處決定。」他的工作說明上寫著。「他將被期待根據事件命令系統(ICS)的時間線(全天候行動通路:二小時到機場;自主資源)做反應。他將不是美國政府官員,將不代表美國政府的意見,將不與媒體或社群媒體溝通,而且將假設所有資訊都必須遵循SBUC/PNOFORN(敏感但非機密/不可向外國人透露)規範。」換句話說,這個在武漢的野人將隨時隨地聽候美國政府的召喚。
| 新書快訊 |

資深記者,曾為《大西洋雜誌》、《彭博商業周刊》、《國家地理》和《紐約時報》撰稿。喜愛自然,對生物學有著極大的興趣,經常探討人與自然之間奇妙的關係,並撰寫相關議題的深入報導。希望能在了解大自然的奧妙之際,對照人性的善與惡。曾獲得美國記者和作家協會、醫療保健記者協會和環境記者協會獎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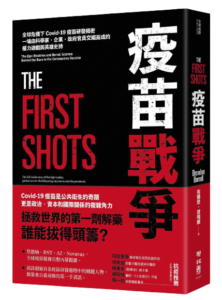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