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學家,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教授。著作有《冷親密》(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消費浪漫的烏托邦》(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痛苦的魅力》(Oprah Winfrey and the Glamour of Misery)等,其中《痛苦的魅力》獲美國社會學聯盟圖書獎。2018年,易洛斯獲得了EMET獎,是以色列最高的科學榮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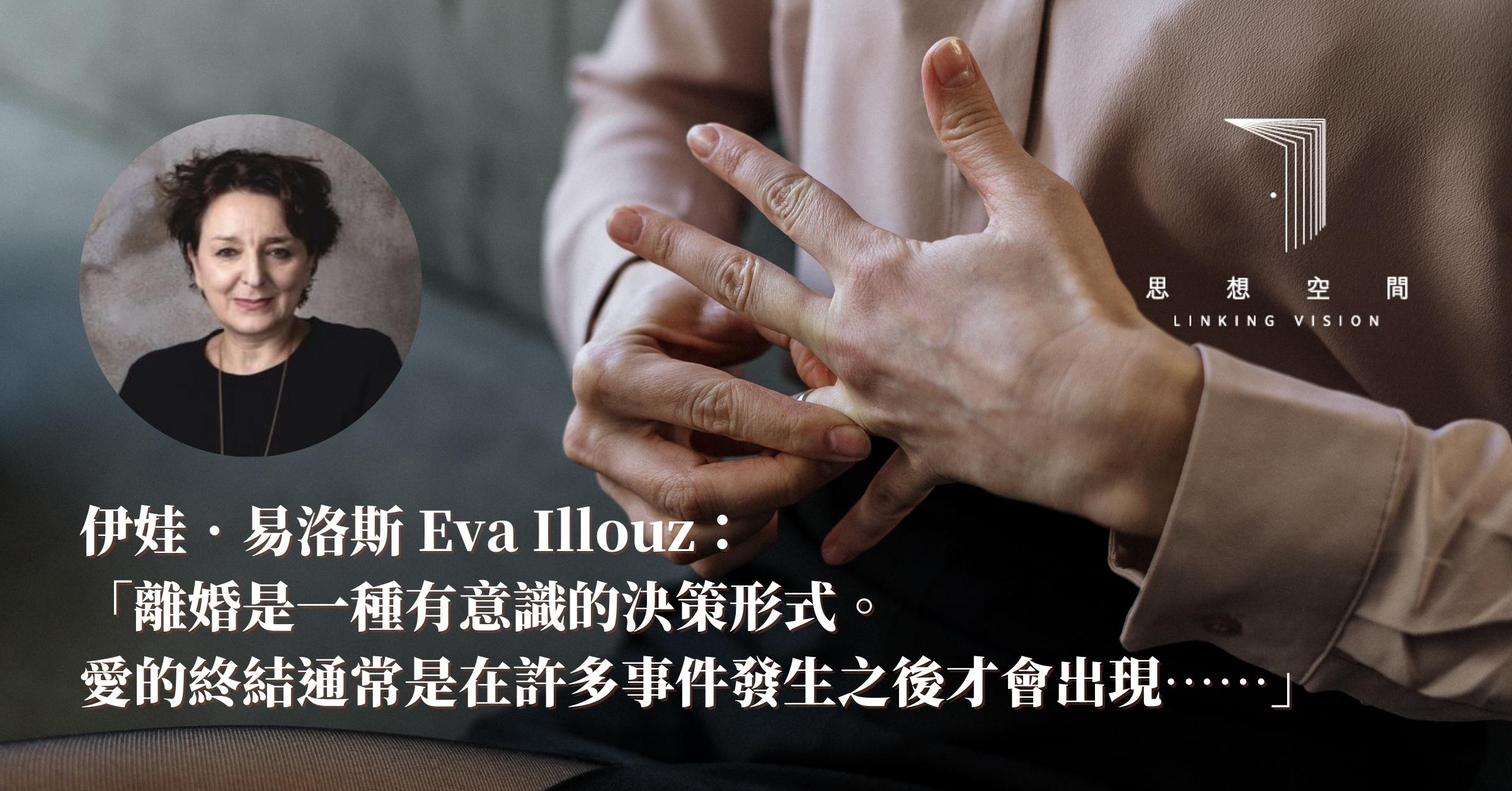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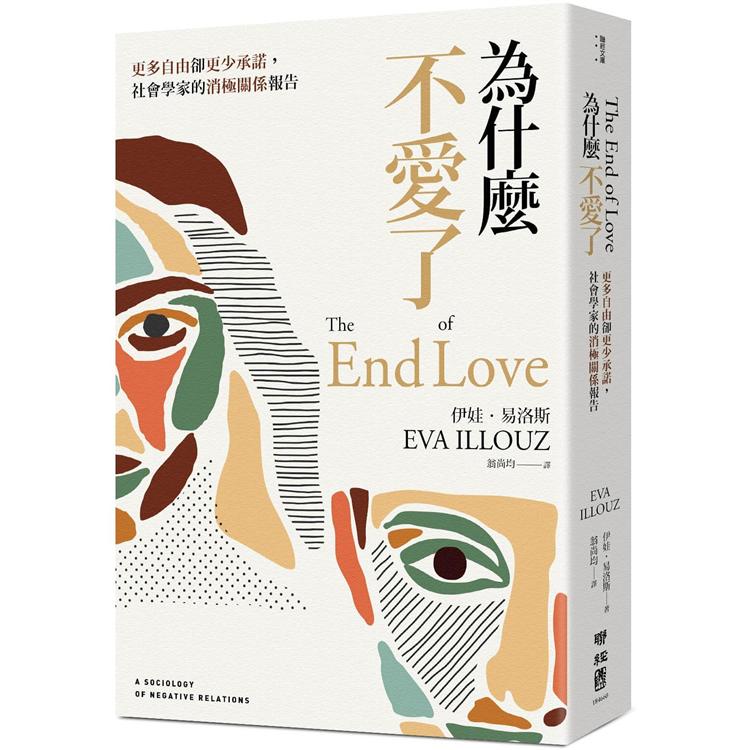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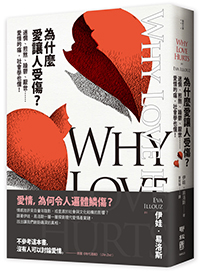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