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菁芳(作家,學術工作者)
編按:2月14情人節將至,無論目前的感情狀況如何,愛情始終是我們一生都在研習的課題。當每一段感情從「愛」走到「不愛」時,如何告別親密關係、重新面對自我,則是許多人都在苦惱的問題。2021年,聯經出版了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的著作《為什麼不愛了》中譯本,作家許菁芳撰寫書評,梳理了現代親密關係中幾乎人人都會面對的疑難,以及背後的動因。
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所著的這本書,是非常具有企圖心的大書。英文原書名直譯,題為「愛情的終結」,副標為「研究消極關係的社會學」;換言之,作者想解釋的主題是愛情消散的普遍現象,而她命名了「消極關係」為切入點,並提出了一套體系來幫助我們理解這種親密關係的起源、發展與後果。
結合20餘年的研究成果,易洛斯其實要從這本書裡回答她最關心的議題,即資本主義以及現代文化如何改變我們的情感生活。
我們所習慣的浪漫愛關係或者性關係所根據的不是某種契約邏輯,而是長期的、結構性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在感情中所經驗到的,經常是困惑與混亂。
當代關係的消極結構:感情中所經驗的,經常是困惑與混亂
對現代的我們而言,親密關係無庸置疑是一種自我表達的自由。傳統婚姻是屬於宗教管轄的領域,也是家庭與宗族之經濟生活的支柱。個人在其中——或者更精確地說,個人的感情在其中——並不是重點。人們對伴侶的愛情,並不構成親密關係的起始點或者終點;唯有在家族、宗教與穩定經濟結構下所發展的情感/性關係,才是「正常」甚或是唯一可行的關係。
現在,戀愛與婚姻都自由了——但這樣的情感/性自由,就讓我們的感情一路順遂了嗎?易洛斯指出,在今天的社會中,感情自由與性自由雖然已經成為理所當然,但也帶來負面的效果:「性自由使得性與情感契約的實質、框架和目標變得難以掌握,大家都可各自表述,但也不斷受人爭議,『契約』這個隱喻變得十分晦澀,乃至於無法被清楚說明。」
而這就是易洛斯所指稱的「消極關係」:行為者不知如何根據穩定的、可預期的社會腳本來定義、評估或經營自己所建立的關係。這也就是現在親密關係的特色,易洛斯稱之為「當代關係的消極結構」(the negative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relationships)。我們所習慣的浪漫愛關係或者性關係所根據的不是某種契約邏輯,而是長期的、結構性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在感情中所經驗到的,經常是困惑與混亂。
我們的親密關係,深深鑲嵌在市場與文化當中
發展浪漫愛情(乃至於性關係)的遊戲規則變得不明確,是易洛斯最主要的分析之一。人如何體驗一段感情,其實必須依賴外部世界的遊戲規則,才能內化於人的感受而被經歷——如紅色玫瑰花象徵熱情,收到99朵玫瑰花的體驗是驚喜,這都是社會上具有規範性質的評斷先行,而個人將其內化,成為一種情感經驗。
以婚前互動為例,我們可以看出,在200~300年前的歐洲與美國,親密關係的遊戲規則是相當明確的。過去,在18、19世紀的歐洲與美國,婚前的求愛標誌著一種轉型中的情感決策模式——求愛是以結婚為目的的一種過程,在男方獲得女方父母的首肯之後進行,在這段期間男女雙方探索彼此的感受,而必然以女方明確的「要」或「不要」進入婚姻的決定,結束這個階段。
雖然這是建立在性別二分與男性優越之上,不過這個互動的意義框架非常清楚,男性、女性與所有關係人都知道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與角色:男性可以選擇求愛的對象,而必須獲得雙方家族的認可,在公開的場合、特定的方式與女性來往互動,而女性有責任接受或者拒絕男性的求愛。
當然,這每一步驟都還有一些明確的程序。例如,「拜望」(calling)是可以被接受的互動方式,而求婚則必須先取得女方父親的許可,才可以向女性本人提出。如珍・奧斯丁(Jane Austen)所說,在這個過程裡,「男人具有選擇的優勢,女兒只有拒絕的權利。」
這是一條明確的戀愛/性關係軌道,順著軌道走,即使非常快速,也不至於危及男女方的名聲。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在當時的小說或者歷史文件中讀到,男性以冒昧的語氣寫下一封信,直接向尚不熟識的女性求婚——因為求婚為他們的關係立下了明確的框架,也為女性提供明確的角色與選項。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每個人基本上都能夠決定(或者起碼發動)自身婚姻的終結,無庸置疑是一項個人自由的勝利。
要性不要愛,也是現代關係中賦予的自由
不過,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經濟與文化的巨大變遷,讓婚姻逐漸擺脫宗教的制轄,這些力量也感變了性與情感的意涵。性開始具備一種享受的性質,目的不在於生殖繁衍;而環繞著性的情感關係,對於成人來說,也變成各種探索、實現自我的方式,尤其是在消費場所發生。
伴隨著這種轉換,遊戲規則也就變得相當不明確。在過去的結構中,情感與性的關係是非常固定的:情感關係的發展是為了抵達性的結合,而性行為必然是被保護在婚姻當中的。但現在的自由讓各種排列組合都變得可能。尤其,由於性關係的合意是錨定於身體之上,因此,性關係其實避開了「情感」內容的合意。換句話說,在性關係上達成共識,其實比在情感關係上達成明確的內容與共識,來得容易。
舉例來說,我們身邊可見的約會故事,常聽到男女維持了一段隨性的性生活,雙方都曾經表達過性愛是兩人要的,而其他再說;但最後,女生發現男生有多重性伴侶,在生氣傷心之餘,卻不太確定自己的感受是否有正當性。易洛斯精闢地指出,在這類的故事中,男女雙方似乎都同意建立在性行為上的關係(而且這種性關係不是兩人生活中主要的關係),但雙方卻以不同的方式同意這種關係:「女人同意建立性關係,是因為她希望性只充作愛情的序曲。對於男方來說,挑明其意圖的範圍(只要性愛)即足以合理化他那無法投入情感的態度。」
易洛斯也指出,現代關係中,強調人們有締結關係的自由,其實也就等於強調人們有離開關係的自由。能夠隨時抽身而出,確實是契約自由的一項特徵;傳統上,個人沒有權力結束自己的婚姻,而必須交託給更高道德的機構(如教會、法院)。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每個人基本上都能夠決定(或者起碼發動)自身婚姻的終結,無庸置疑是一項個人自由的勝利。
情感自由最重要的一項特徵,就是在終止關係的時候可以不給任何「正當的」理由。畢竟,雙方關係建立的正當理由是「我願意」,那麼關係終止的理由,也只需要「我不再願意」就足夠。
在親密關係中表達自我的最終方式,是分手
不過,也正因為抽身是一種表達自由的方式——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種方式——現代的親密關係,也就建築在一種很大的不確定之上。在感情的互動過程當中,雙方都在探索、展現自己,而一旦感覺到受到威脅,抽身而去成為一種最終表達自我的方式。
我們熟悉的各種約會故事在在展現這個特性:女方發現男方對金錢不夠大方、與媽媽同住、在床上喜歡控制,馬上就會警鈴大作,身邊的朋友都警告她要快速走人。甚至,有很多互動上的自我表現成為零和遊戲:男方心思多在工作上,經常因為職場上的挫折而沒有餘裕傾聽女方,而女方認為自己的情緒受接納是關係的基石,在溝通數次未果後雙方決定分手。雙方都在強調自我的發展,而把對方所強調的自我視為對於自己的威脅,最終表達自我的方式就是關係的終結。
最後,這種自由退出的特權,來到一種極致的形式:悶聲不響地離去,英文稱之為鬼沒(ghosting)。這種分手聽來並不陌生。原本在關係中的一方毫無預警地消失,或者在沒有給出明確、完整理由的情況下,直接宣告斷絕關係。易洛斯指出,這種被分手的經驗,其實算不得意外,因為如果我們把親密關係的基礎放在「合意」之上,那麼,單一方的情感發生變化即可抽身的行為,也變得無可厚非。
事實上,情感自由最重要的一項特徵,就是在終止關係的時候可以不給任何「正當的」理由。畢竟,雙方關係建立的正當理由是「我願意」,那麼關係終止的理由,也只需要「我不再願意」就足夠。給足理由已經不是義務——而且,分手方所認為足夠的解釋,也不一定是被分手方認同。在這裡,情感自由又再次允許人們產生分歧,而恰恰是這種分歧,導致人們在關係中不斷經驗著差別、混亂、各說各話與不確定性。
易洛斯在本書達到的成就是顯而易見的:她成功地捕捉一種神出鬼沒的感受,並且給予明確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解釋。我們在現代感情生活中所體驗到的不確定性、混亂與茫然,可以用這樣的時空來理解,可以用抽象的分析來解釋。本書的學術語言並不容易吸收,但是其中的企圖卻很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鳴:我們的親密關係,深深鑲嵌在市場與文化當中,我們的感受其實也是透過外部的結構與意義框架來形塑。理解這來龍去脈的,能對自身產生一種深刻的同理。我們在感情裡的徬徨,並不孤獨,也不怪異,而是普遍的現象與經驗。
延伸閱讀:
伊娃 ‧ 易洛斯(EVA ILLOUZ):離婚的另一面:在經濟與情感上,女性正在重新定義婚姻
伊娃 ‧ 易洛斯(EVA ILLOUZ):男人總是迷戀性感、卻害怕承諾?從社會結構看性別權利
| 新書速遞 |
| 閱讀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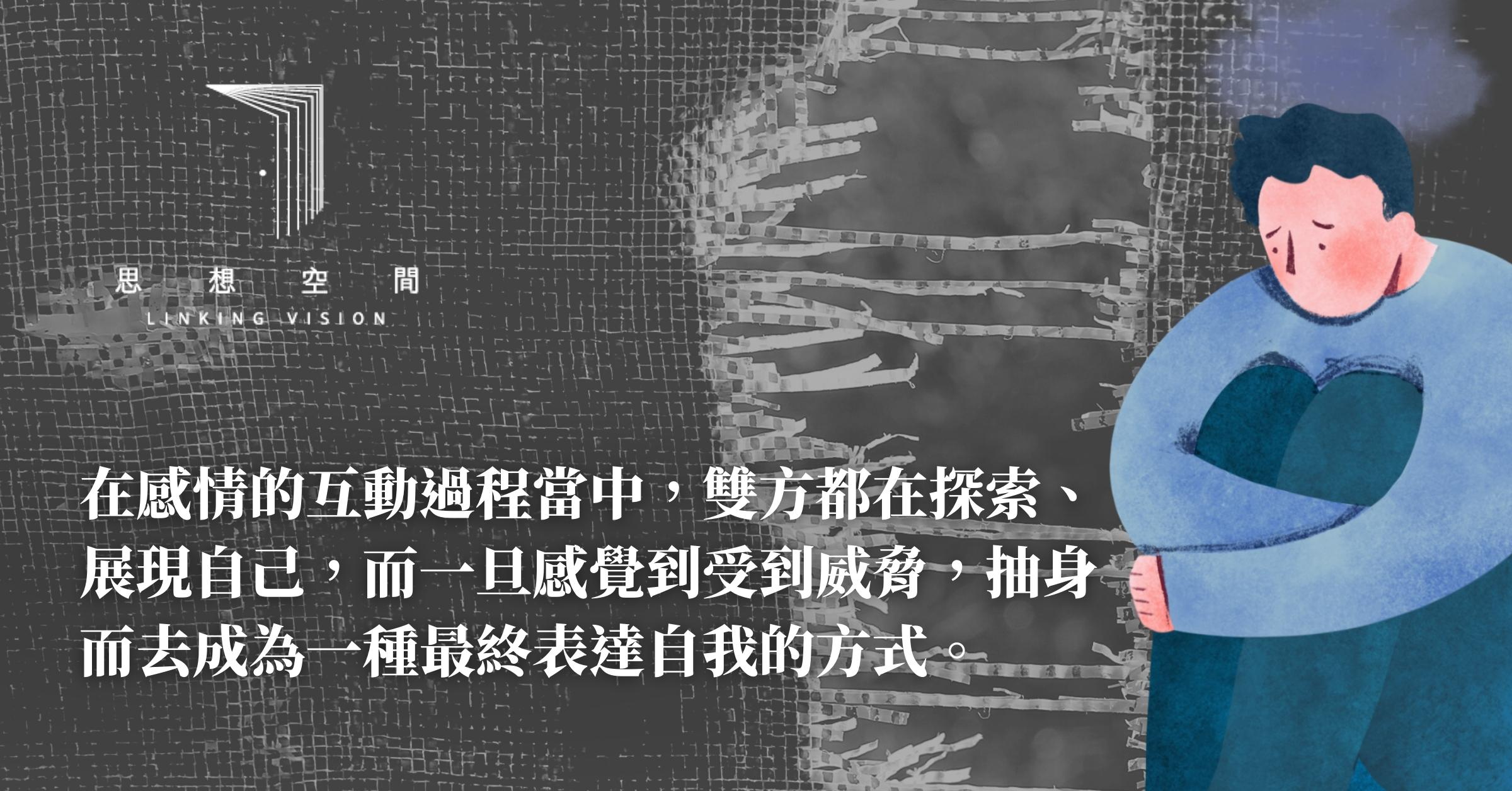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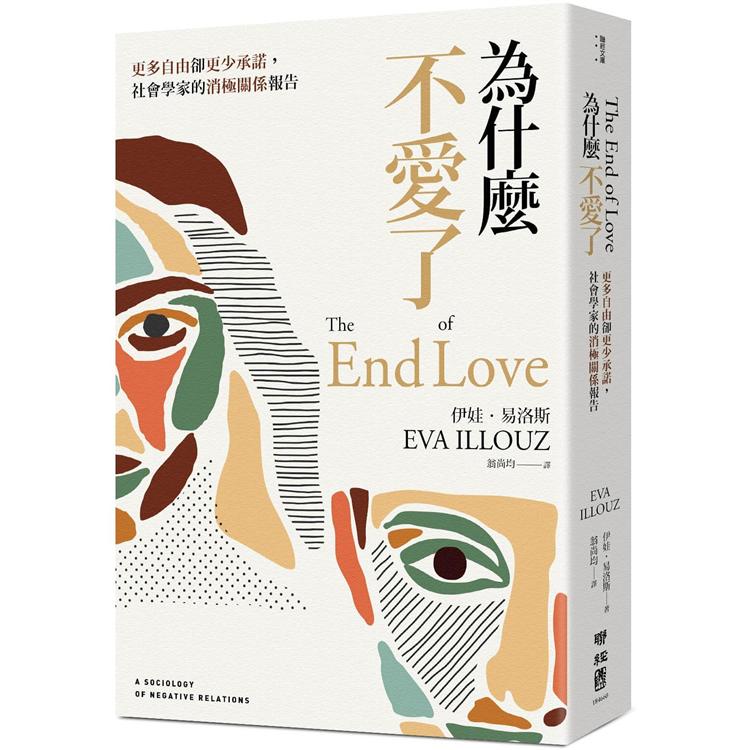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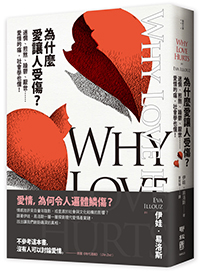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