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孝悌(中研院史語所兼任研究員)
* 上篇請見:李孝悌:史景遷——一位閃耀的明星(上)
《婦人王氏之死》:再現貧苦民眾的日常生活
除了細緻地描述整個世代或關鍵性的歷史事件,史景遷也擅長描寫人物,從皇帝、包衣、傳教士、文人/士大夫,到籍籍無名的信徒、女性,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也是在這個領域,史景遷教授發揮了他無限的創意和天賦的文學才華。《胡若望的疑問》(台北:唐山,1996)和《婦人王氏之死》(台北:麥田,2001)一樣,都讓人讀後產生了一個疑問:這些書到底是歷史還是小說?這個疑問其實正好反映了前述余英時先生所說的『才兼文史』的特色與才華。作者利用他的語言天分,利用了在倫敦大英圖書館、巴黎的國家外事檔和梵蒂岡的教廷檔案,講述一個中國天主教徒胡若望在神父傅聖澤的提攜下,遠赴法國。言語不同的胡若望貿然來到異鄉,因為舉止乖張,最後被關進瘋人院裡,三年後才終於返回廣東老家。作者利用多種語文的記載,拼湊出雍正年間一幅匪夷所思的廣東人流落法蘭西街頭的圖像。雖然是小人物的小故事,卻反映了東西文化的差異和文化認同的大問題。
這本從王氏之死切入的傑作,看似是一個文化史的課題,但其實是對郯城基層社會的每一個面相和貧苦民眾的日常生活,作了具體而鮮活的再現。
《婦人王氏之死》利用了三種資料寫成:第一種是作過郯城縣令的馮可參編纂的《郯城縣志》,這本在1673年編成的縣志雖然在內容和格式上和其他的縣志沒有什麼不尋常之處,但它對這個縣的困苦的描述寫實而鮮明,主編馮可參似乎也滿意編纂一部真實的淒涼記錄。第二種資料是同樣作過縣令的黃六鴻所編纂的一本關於縣官生涯的個人回憶和官箴《福惠全書》。第三種則是知名作家蒲松齡寫的小說《聊齋誌異》。
1668年7月25日,一場地震襲擊郯城縣,震垮了大部分的城墻、垛口、官衙、廟宇和數以千計的民房。到此為止,郯城居民已經歷經了五十年的苦難。許多人死於1622年的白蓮教起事。在1630年代,更多的郯城人死於饑餓、盜賊或疾病。1640年代,新一波的災難循環開始。1640年,大群蝗蟲飛進郯城,繼一整個夏天的乾旱之後,蝗蟲摧毀了小麥收成所留下的所有殘餘。那年冬天的饑荒延續到第二年的春天,結果造成「兄食其弟,夫食其妻」的悲慘結局。饑荒之後,盜匪接著來到。1643年,阿巴泰率領的一支滿洲軍隊攻進郯城: 「大兵破城,屠之官長。俱殺紳士、吏民,十去七八。城之內外,共殺數萬餘人。街衢宅巷,尸相枕藉。」
而阿巴泰給皇帝的報告中,對某些村社的細節不屑一顧,只說從華北一帶獲得:「黃金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各色緞共五萬二千二百三十疋。——貂狐豹虎等皮五百有奇。——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我們再次從作者偏好的具體數字中,看到郯城的悲慘機遇和清軍入關後的燒殺劫掠。
郯城雖然是春秋古國郯國的所在,但位於魯南山區,和魯西北、魯西南一樣,都是相對貧窮的區域。從周錫瑞的名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中,我們知道在山東六個區域之中,魯南山區從1851-1900年間,每五萬人中的舉人人數只有1.34,僅高於盜賊淵藪的魯西南地區的0.81。郯城是一個窮困的農業縣,沒有什麼物產。縣志除了列舉三種當地製造的棉絲混合布外,就沒有別的了。也沒有太多貨物經過此縣,只有馬頭鎮有比較多的商業活動。現實生活的悲慘際遇,讓這個地方的人有著超乎尋常的迷信,鬼魂和夢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史景遷教授用《聊齋誌異》來建構這個地方鬼怪妖狐的世界,可說是神來之筆。
在《郯城縣志》中,有許多傳記是關於女人如何靠著自己的決心和嚴格的道德目的而守寡,自力謀取生活並撫養小孩長大。但《大清律》中一條關於寡婦權利及繼承法的例則,讓守寡除了單身的煎熬外,變得格外的艱難:「其(婦人)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嫁奩,並聽前夫之家為主。」(頁124)許多寡婦亡夫的親戚為了搶奪財產,不僅逼迫寡婦再嫁,並且常有將寡婦之子謀害的案例。
這本從王氏之死切入的傑作,看似是一個文化史的課題,但其實是對郯城基層社會的每一個面相和貧苦民眾的日常生活,作了具體而鮮活的再現。從這些描述中關於外來客投宿旅店時的登錄規定——不管是個人或團體,都必須註明客人來自何處,要到何地,他們可能攜帶準備出售的貨品,他們的騾子或二輪馬車,他們的武器。單身的行腳客,不管有沒有武裝,只要沒有行李,又沒有城裡人作保,都可能被趕走——我們看到保甲制度如何在地方具體的運作。
雖然有十六世紀末開始的稅制改革,將過去的勞役和徭役稅改用白銀支付,但在表面的低稅率政策之外,一般民眾還是要負擔各種沈重到無法承負的勞役和官方無理的需索。郯城持續的財政危機,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在地裡位置上,位處兩條南向主要幹道的東邊那一條上。這條重要的戰略道路通往浙江,既是作為軍用補給品的運輸線,也是政府經由驛遞系統傳送訊息的主要管道——不管是緊急的還是例行的。這意味在任何時間,郯城的居民都可能為維護道路或運輸服務的額外要求所苦。此外還要花不少經費照顧過境的官員及其隨從,這種情形又因為整個區域的相對貧窮和馬匹、驛站的匱乏,而變得更加複雜。政府撥付的稅收完全不夠支付秣料、馬夫、信差的薪水,以及裝備和其他馬房設施的花費,更別提獸醫費和添購額外馬匹的花費。
在這本讓人想起法國文化史的經典之作《蒙大猶》的全景式的地方史最後,作者終於回到標題所說的一個婦人的私奔、情感和死亡。王氏大概在1660年代末的某個時期,嫁給某個不知其名的任姓男子。王氏可能是以童養媳的身份進入任家,幫忙做些家務雜事,等年紀夠了,就嫁給任。任靠著在別人的耕地上做傭工維生。他們的家裡只有一個房間,裡面有飯鍋、一盞燈、一床編織的睡席和一個稻草床墊。王氏纏了腳,白天的時間多半一個人在家,沒有小孩。1671年,她跟著一個不知道名字的男人跑掉了。
在一個保甲制度運作嚴謹的小地方,這對私奔的情侶要找一個藏身之處,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跑路對兩人當然是一件苦事,對不久後遭愛人拋棄而單獨留在路上的王氏來說,更是一場惡夢。最後王氏走投無路,被迫選擇返回歸昌的老家。在王氏住的村莊附近有一座道教廟宇三官廟,主持的道士給了王氏一個棲身之所。她的先生很快就從鄰人的言論中得知此事,1671年底,王氏別無選擇的回到歸昌集外的家。兩人又開始生活在溫度是零下幾度的陋室中。1672年一月底的一個傍晚,王氏在燈旁傍任縫補外衣。稍晚,鄰居聽到兩人的吵架聲。其後,王氏脫掉外套、褲子和笨重的鞋子,小腳上穿了一雙磨損的軟底紅布睡鞋。當任的雙手緊緊掐著王氏的脖子時,她從床上彈了起來,但掙不掉任的手。儘管她奮力踢打,內臟也裂開,但他一直不鬆手。
郯城依然下著雪。任抱起老婆的尸體,用她的藍色夾衫包裹著她的肩膀。他打開門,抱著她走過森林,朝鄰居高家走去。兩人宿有恩怨,高是第一個在三官廟發現王氏的人,為此,高任兩人在廟裡爭吵撕打起來。任本來打好算盤,要控告高和王氏有姦情,並因故殺了她。
「王氏的尸體整夜都躺在雪堆裡,當她被人發現時,看起來就像活人一樣:因為酷寒在她死去的臉頰上,保留住一份鮮活的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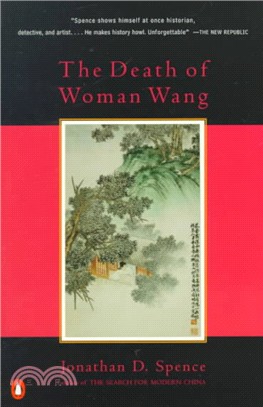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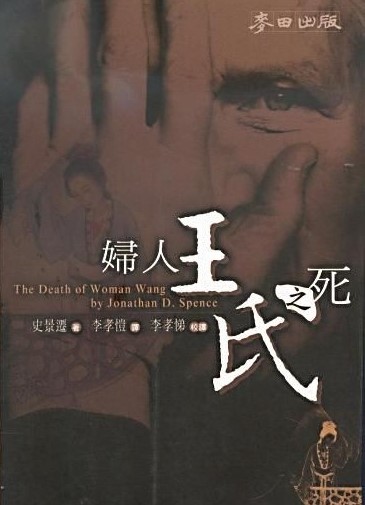
史景遷用了特殊關係,讀到這批清宮檔案。雖然是一本科班訓練出來的嚴謹學術專著,但已經顯現出作者高超的選題眼光和敘事能力。
《曹寅與康熙》:把學術提升到美的範疇
《曹寅與康熙》(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是根據作者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英文原書在1966年出版。為了搜集研究資料,還是博士生的史景遷特地跑到台灣,到霧峰的故宮博物院閱讀清宮檔案。1948底開始,故宮的文物輾轉遷運到台灣,先是存在台中糖廠倉庫,1950年遷往霧峰北溝村。史景遷用了特殊關係,讀到這批清宮檔案。雖然是一本科班訓練出來的嚴謹學術專著,但已經顯現出作者高超的選題眼光和敘事能力。曹家是滿族統治者的包衣奴僕,到曹雪芹的祖父時,受到康熙皇帝的高度信賴,被派到南京作江寧織造。江寧織造的職守是管理江寧城中皇家的絲織工場。康熙在南巡途中考察地方行省的情形,並因此發展出密摺制度。
曹寅因為受到皇帝的信任,奉命在原來被稱為「請安摺」的密摺中,定期向皇帝報告地方的雨水、米價、收成情況,並特別留意高官和江南士大夫的行為舉止。康熙在1684、1689、1699、1703、1705和1707年,共進行了六次南巡。第一次南巡是康熙在1681年最終平定三藩之亂後數年間進行的全面巡視的一部分,所以某種意義上是偵查探險。雖然他特別注意到河道事務,但直到1689年第二次南巡時,才認真解決這個問題。1699年的南巡相對枝蔓,皇帝不僅帶了皇太后佟佳式,還帶了七個兒子同行。由於對河運的關心,他幾次離開隊伍,到前方視察河務。度過黃河後,他又離開隨行人員,搭乘一支小船詳細檢查了一些堤防,並在這次旅行後下達了關於河道應保持水位的最詳細指示。(頁149)在這次的南巡過程中,他還偶爾離開隨從,幾乎是單獨一人與百姓交談。
1705和1707年的最後兩次南巡都很悠閒,分別花了108天和117天。兩次皇帝都是從水陸沿大運河和南方的河流前進。途中他接見地方官員,視察堤防,評論地方局勢,與隱退的學者交談,赦免稅收,寬恕罪行,練習騎射,舉行額外測試,犒勞地方駐軍和扈從,通常也都會應百姓的請求多留一天。(頁151)
河運不僅牽涉到人民的生死、田地的灌溉,也牽涉到南北貨物、訊息的流動,漕運更關係到整個政府的財稅收入和北京皇室、官員的衣食廩入。康熙作為一位勤政愛民的統治者,對河運的關切,從上面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看出來。1707年3月23日,皇帝再度視察河道,總督張鵬翮為了降低連接黃河和運河的河流水位,建議開鑿運河的地點,皇帝很不滿意。視察後他命令所有扈從成員和同行的文武官員,張鵬翮以及他的治河官員跪在臨時行宮前面。隨後他質問張鵬翮根據什麼提議開河?聽到他無關痛癢的話後,皇帝嚴厲批評張,提醒他寫空幻的文章和實際治河問題大不相同。皇帝的威嚴由此可見,這點我們在康熙自畫像一書中,還可以看到更多的描述。
康熙最後四次南巡,都是由曹寅負責安排所有的事務。要讓皇帝有一次舒適安寧的旅行,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差事。除了這些重任,曹寅的官署衙門和居所成為皇帝的江寧行宮。1699年,康熙在江寧住了一周。正是在這次巡視中,他召見曹寅的寡母,愉快地與她交談,並寫下「萱瑞堂」三個字給她。曹寅的同代人將此視為不同尋常的恩典記錄下來。1705年3月,曹寅陪同康熙緩緩地展開第六次南巡。5月14日皇帝抵達江寧,中午經過西華門前往織造衙門,他命令侍衛不要驅趕平民,准許他們隨意沿途圍觀。而曹寅似乎掌握了如何送禮物才能贏得皇帝歡欣的訣竅,所以他送給康熙一些櫻桃。康熙大悅,說要先進給北京的皇太后佟佳氏,自己才敢享用。隨即差官騎馬送往皇宮,驚人的是他們在不到兩天的短時間內就送到了,是當時傳遞緊急文書規定最快速度的兩倍。這裡皇帝以誇耀的姿態迎合了滿人對飆騎的熱愛和漢人對公開表現孝道的尊敬。當晚曹寅準備了第二次宴席,席後上演了幾齣名戲的片段。(頁162)
1711年,江南鄉試的結果在10月20日公佈,迅即引發一場抗議風暴。在獲得舉人功名的秀才中,差不多有十三人來自蘇州,其中許多是富裕鹽商的兒子。當中的一些人大家都知道文學才能低劣,不可能通過真正的考試。落榜的秀才激烈的抗議總督噶禮和副主考收受賄賂,出賣舉人功名。河南出身的巡撫張伯行上褶控訴噶禮通過直接出售舉人功名和收取安撫金,共收受了五十萬兩銀子。康熙從一開始就收到曹寅和李煦的密摺。後來他雖然派出了自己任命的大員南下調查此案,但對他們的調查報告和建議,都置之不顧,反而是接受了曹寅和李煦的報告和建議。康熙這位英明的統治者,當然清楚這之間敏感的滿漢問題,他在公開的明發上諭中,一再清楚地表明他作為滿漢仲裁者的立場:「朕臨蒞天下五十餘年,遍諳諸事,于滿洲、蒙古、漢軍、漢人毫無異視——閱朕此旨,是則是,非則非。」在聽取、閱覽了各種立場幾乎一致的建議後,康熙乾綱獨斷,做出了和所有這些建議完全相反的判決,他在簡短的朱批上說:「噶禮著革職,張伯行著革職留任」。這樣的判決固然出於皇帝的政治判斷和敏感性。曹寅、李煦的密摺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皇帝對這位下屬的信任,可見一般。
1709年間,曹寅變得越來越衰弱,他試著用補藥,尤其是人參,來維持體力。康熙對藥物及其功效宜忌有很廣博的知識。1710年春天,曹寅回到江蘇後得了眼疾。皇帝在他上呈的奏摺中用粗重的筆墨寫下批語:「你在南方住久,變虛弱了。年初得眼疾,必得停用補藥,最好飲六味地黃,配方勿改,到量自然生效。」曹寅在1710年12月22日另一份給皇帝的奏摺中說自己得了風寒,因誤服人參,得解後,旋復患疥,臥病兩月有餘。皇帝的朱批如同臨床一樣:「知道了。惟疥不宜服藥,倘毒入內,後來恐成大麻風病症,除海水之外,千萬不能治。小心,小心。土茯苓可以代茶,常常吃去亦好。」(頁286-287) 這樣的關係,簡直就像好朋友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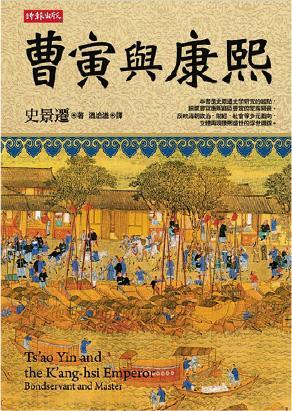
我們看到了帝王的威嚴和決斷力,他的仁慈、同情心、孝順;也看到了他作為戰士和征服者時的強悍、兇猛、殘暴,以及身先士卒、吃苦耐勞的鋼鐵般的決心與毅力。
在寫《曹寅與康熙》時,由於閱讀了許多康熙的奏摺,史景遷教授已經在醞釀寫一本康熙的傳記。1974年,這本《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的英文本終於出版。(中文本見上海:遠東,2001)與眾不同的是,作者決定採用自傳的形式,由康熙以第一人稱,說出自己作為戰士、統治者、游歷者等的各種面相。這本將創意、文學天賦和史學訓練並冶於一爐的作品一問世,就引起出版界的轟動,並且深受讀者歡迎,成為暢銷書。知名的記者、歷史學家、小說家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甚至譽為「經典之作:把學術提升到美的範疇」。(見鄭培凱、鄢秀為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史景遷全集》總序)
在這本夫子自道的傳記中,我們看到了帝王的威嚴和決斷力,他的仁慈、同情心、孝順(在《曹寅與康熙》一書中,我們已經深切的體會到這些特質);也看到了他作為戰士和征服者時的強悍、兇猛、殘暴,以及身先士卒、吃苦耐勞的鋼鐵般的決心與毅力。他謙虛自誇、博學多聞、心胸開闊,又脆弱妥協固執。
康熙喜歡遊歷他辛苦創建的壯麗山河、湖泊、沙漠。他巡游的興趣之一,便是收集、比較那些偶然碰到的各種不同的植物、鳥類和動物。在他的各個行宮和花園裡建起的一個個生物園、動物園,是他分送這些動植物的地方。他一生的不同時期,分別對幾何學、機械學、天文學、繪圖學、光學、音樂和代數學都表示過興趣。他是這些或其他超乎尋常的學術和百科全書工程的支持者。
正文一開始,他就說從孩提時代起,我就喜歡觀看幼苗生長,從他省和異國移植花木和幼苗。我從南方巡游中帶回來的香稻谷和水栗樹等不適應北京的嚴寒氣候。經過悉心照料,——綠竹幸存下來了,——西洋參在宮中花園盆景裡培植。
我所熟悉的有關狩獵的一切,都是由我的侍衛官阿蘇莫爾肯在我兒時教給我的。自從我兒時拿槍挎弓時算起,我共殺死了一百三十五只猛虎,二十頭狗熊、二十五頭豹子,二十隻大山貓,十四尾麋鹿、九十六條狼,幾百隻普通的母鹿、公鹿和一百三十五頭野豬。——最普通的人們一生所殺過的動物不及我一天所殺的數目。
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和收復台灣後,西藏和蒙古就成為他最主要的敵人。和西藏建立緊密關係的噶爾丹最後成為整個蒙古草原的統治者和中亞的霸主,也因此成為康熙必除而快之的心腹大患。
在1696年第一次噶爾丹戰役中,我在拂曉前已是第五次起來觀察。——我只吃了白天的剩飯,但是我不能鼓勵其他人也這樣做。在行軍的時候,我的生活很粗陋,不正規,那些經過我前面的人不必下馬,就像打獵時一樣。我們用簡單的方式烹魚煮飯。在邊疆的小鎮上,不可能走在清淨的街道上,但我寧願特別慢地經過,以便所有的人都有機會看見我;或者我讓普通的人聚成一個圓圈,看著我吃飯,分給他們粟和肉。
邊疆地區可能是寒冷的、潮濕的、荒涼的,沙漠一望無際,只有一些野綿羊和驢子,就是沒有人,沒有房子,甚至沒有飛鳥。我曾經親眼看見,人們烹煮小塊的泥土充飢以維持生命。
1696年從北京出發後,我們得到了承諾——殺死噶爾丹。——二十年前,張勇將軍已就噶爾丹作了秘密調查,偵查到了他的魯莽又猶豫的性格,他的年齡與家庭狀況,他與穆斯林之間的問題,以及他對酒與女人的嗜好。從那時起,我就已經注意觀察到噶爾丹的狡猾和聲東擊西的嗜好。他的過於自信,他的欺騙伎倆以及他的缺乏深謀遠慮。我們派出了特使之後,我們的偵查兵觀察他宿營的炊煙,估測他的部隊運行中的牛蹄印和馬糞。當噶爾丹開始逃跑時,我們便隨後追捕。
噶爾丹跑進了我們的包圍圈,在昭莫多碰上了費揚古,他們在三十里的戰線上展開四小時的激戰。雖然殺了兩千多厄魯特,但噶爾丹本人卻逃跑了。第二年春天,我第三次追捕他,陝西巡撫竭力地勸阻我,請求我不要再次深入不毛之地的荒漠了。但我說噶爾丹必須像吳三桂那樣被殺死,雖然我們的士兵因連續作戰而疲憊不堪,但還是想一展他們的英勇。
我曾告誡官員們,如果你們迷信書籍,你們就永遠不會贏得戰爭。人們所需要的是堅韌的毅力與細緻周密的計劃。因此,就在1697年的孟夏,在遙遠的黃河灣的西北面,我聽到了噶爾丹眾叛親離,被迫自殺的消息。現在噶爾丹已經死了,他的同夥又復歸順了,我的大業完成了。在兩年裡,我旅行了三次櫛風沐雨的跨越沙漠,並日而食,在不毛荒涼的沙漠里——人們或以為這是辛苦的,但朕可不是這麼想。——不斷地行幸和勤政已使我取得了偉大成效。如果不是噶爾丹的話,我將永遠體會不到這一切。蒼天、大地、祖先已默佑我取得偉大的成就。至於我自己的一生,可以說是幸福的,可以說是盡職的,可以說是我獲得了我想要的一切。
康熙客觀、誠實而毫不客氣的用動人的語言,為自己在蓋棺前就作了精準的評估和定位。他許多詩一般的文字,不禁讓我想到法國年鑒學派大師布勞岱爾在其名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中各種文學性的描述。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國歷史上統治最久的帝王,他為中國留下了一個幅員廣大的龐大而強盛的帝國。他雖然只活到69歲,但對養生之道的講求,對醫藥的精通,對疾病的治療,對身體殘缺人士的同情(詳見本書第四章「壽」),不僅讓他寵信的曹寅受益,也有許多有趣而言之成理的見解,值得我們這些現代人參考。
而今斯人已去,我只能用這篇誠摯的文章,來紀念這一位讓中國史普及於西方及中文世界一般讀者的一代風雲人物和成就非凡的史學大師。
今時憶往:史景遷的誠與真
2004年,我的一個學生/助理(後來是我的同事)打算去美國讀博士,由於我是他碩士論文的口試委員,深切了解那本論文的成就和貢獻,所以幫他寫了一份非常好的推薦信。2005年春節過後的某一天,史景遷教授的夫人金安平教授突然打電話到我台北的家中,說史教授非常欣賞這位學生,希望我能努力遊說他去耶魯。如果可以說服他,由於史景遷教授第二年休假,他們願意把我當成這個學生入學獎勵的一部分,去耶魯幫史景遷教授代課一年。不過我知道,哈佛也同時給了他入學許可和獎學金。到後來,我才知道其實是我的老師在續任系主任的最後一年錄取了他。
2005年11月,史景遷教授應時報文化之邀,和他的夫人一起到台北敦南誠品發表演講並介紹他們的新書,我和一些同事也應邀與會。史景遷教授見到我,在簡單的寒暄後,特地提起這個學生的事。他說原以為他的競爭對手是普林斯頓大學,沒想到還有一個哈佛大學,那就沒有話說了。雖然我使命未達,但對史教授的愛才心切,深有所感,我也要特別感謝他的好意和盛情,願意請我去耶魯幫他代課一年。而今斯人已去,我只能用這篇誠摯的文章,來紀念這一位讓中國史普及於西方及中文世界一般讀者的一代風雲人物和成就非凡的史學大師。
延伸閱讀:
【敬悼史景遷】23年前,史景遷對談余英時:世紀交替中的中國知識人
【敬悼史景遷】北島:上帝的中國兒子
鄭培凱:重讀《曹寅與康熙》——兼懷史景遷老師
李孝悌:史景遷——一位閃耀的明星(上)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委員會博士。曾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著作有: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9)、《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台北:聯經,2008)、《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998)。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