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灣水巷生(哲學博士生)
編按:隨著香港步入政治寒冬,愈來愈多人開始談論關於暴政、極權、抗爭的著作。在此之際,南灣水巷生與讀者們一起回顧身為異議分子、曾任捷克共和國總統的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所寫的〈無權力者的權力〉,反思每個普通人應該如何面對暴政、在極權日常中生活。
(本文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擬)
生在壞時代,活在真實中
生在壞時代,人人身心受創,會憤怒,會疲倦,會逃避,會失憶。如何在無邊漆黑中保持心境明亮,成了亂世中人的日常功課。
時勢所趨,近日愈來愈多人談論關乎極權與抗爭的名著,包括捷克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所寫的〈無權力者的權力〉[1],其格言「活在真實中」也許會成為香港人的新口號。此作無一段不精彩,任何想在暴政橫行時守護心中最後一片淨土的同路人,確實值得翻一翻。
在這篇長文中,哈維爾反覆提到一個菜檔老闆,在其店前掛了印著「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的橫幅。他並非忠實的共產黨信徒。那他為何會掛此橫幅呢?無非向四周上下的監視者擺個姿態,證明他服從黨的領導而已。而這小小的配合,實默默鞏固了暴政延伸至更多人身上的爪牙。而哈維爾的的著名忠告,為「活在真實中」。
這格言大有來歷,甚至可上溯柏拉圖哲學,希望他日詳談。簡要言之,他提醒人活在一個充斥謊言的世界時,但凡覺得不舒服,但凡心志受到委屈,你應忠於自己,不應阿意曲從,說你深信正確的話,做你深信正確的事,即「活在真實中」了。由此對付暴政不必假手他人,作家堅持發表地下文章,學者堅持開私人講堂,教師堅持傳授隱䁥的真相,教徒堅持秘密禮拜,畫家歌手堅持自由創作,工人堅持營運工會,眾人堅持不平則鳴,就是對暴政最大的嘲諷。
哈維爾模仿馬克思(Karl Marx)及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無權力者的權力〉開首就擲下意味深長的一句:「一個幽靈在歐洲東方游蕩,那幽靈西方稱之為『異見』。」我一直覺得哈維爾是個帶給人希望的劇作家,在他筆下那座鐵鑄的舞台,他鼓勵一眾拘謹的演員展現本色,任異見行雲流水,任異見遍地開花。
像〈無權力者的權力〉這類警世文章,多則多矣。只是大家尚可從容翻閱時,無人問津,到大家迫不及待去搶讀時,一切都遲了。
哈維爾在忍辱負重下完成此作。不出所料,旋即遭禁。作者身陷囹圄,作品亦只能在地下流傳,並偷運至他國。
心中的正義不應只是個幽靈
「一個幽靈在歐洲東方遊蕩,那幽靈西方稱之為『異見』。」[2]哈維爾名作〈無權力者的權力〉即以此句開頭。為何形容異見為一個幽靈呢?要先知道其原型來自馬克思及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首句云:「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據說此處的幽靈乃自嘲語。按十九世紀作家舒茲(Wilhelm Schutz)在德國《國家辭典》所記,時人多談及共產主義,或懼之若鬼魅,或以此恐嚇他人。[3]而《宣言》的一下句,就說舊歐洲的一切勢力聯合起來,對這個幽靈發動「神聖的圍剿」,那共產主義自當屬邪魔外道了。
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就拿《宣言》首句大造文章,寫了整整一本書《馬克思的眾幽靈》(Spectres de Marx),去說明正義為何永遠遲遲未來。幽靈在法文又喚作「歸徒」(le revenant),意指重返陽間的亡者。沒錯,幽靈每次出現都是一趟回歸,來自過往未了的心事,徘徊不去。比起可怕,德里達更注重幽靈(le spectre)與精神(l’esprit)的雙關。他畢竟不是馬克思,不認為共產主義最終會道成肉身,住在你我中間,為大地帶來恩典。執行正義的夙願卻使之一次又一次重生,即便永不完整,淪為幽靈,殘留人間。
若然馬克思的幽靈遊蕩全歐洲,哈維爾筆下的幽靈則率先縈繞東方諸國。不但影子淡泊,甚至連名字都沒有,得待西方稱之為「異見」。尤諷刺者,等到共產主義的幽靈變成真正駭人的厲鬼,席捲歐洲,卻處處提防一隻沒有名字的怪物。也許潛伏於極權體內的異見就真的那麼可怕,以致街談巷議都成了禁忌。〈無權力者的權力〉這部著作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九六八年,坦克從華沙公約國駛進瓦茨拉夫廣場,布拉格之春慘遭鎮壓,極權重臨捷克斯洛伐克。十年後,哈維爾在忍辱負重下完成此作。不出所料,旋即遭禁。作者身陷囹圄,作品亦只能在地下流傳,並偷運至他國。〈無權力者的權力〉首句變相成了自況。
然而,哈維爾每每提到異見,必冠上引號,反映了本人並不多滿意這個外來稱呼。[4]他心中的正義不應只是個幽靈,而原應堂堂正正,擁有獨立的生命。人不必怕鬼,只有鬼才當怕人。
民主鬥士非其所願,謹想默默做好自己喜愛的事。但正正因為想做好自己喜愛的事,不少人無可奈何就成了當局的眼中釘,迫上梁山。
暴政當前,做好自己也是錯誤
德里達之所以大講馬克思的幽靈,甚至提出「幽靈學」(l’hauntologie),用意即在提醒人共產主義亦正亦邪的特性。一方面,蘇聯解體後,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急需制衡。另一方面,蘇聯亦留下慘痛教訓,即共產主義一旦奪得權力,代理神職,世界將飽受威脅。既然如此,有識之士必須學識「養鬼仔」,與幽靈共事而不遭其附身,毋復妄圖建立地上天國。
哈維爾撰〈無權力者的權力〉時,正處於蘇聯治下。共產主義的幽靈化成體制,整個歐洲東方皆遭其附身,哈維爾稱之為「後極權體制」。後極權與舊時的獨裁有別,在於後極權倚賴意識形態去調和體制與生命的衝突。甚至可以說,主宰後極權體制的黑手不再是獨裁者,而是意識形態本身,獨裁者的功能僅限於確保整座機器能持續運行。換言之,他無非一具遭惡鬼附身的肉囊而已。
德里達期許學者成為通靈師,看到共產主義的幽靈本質。那遊蕩歐洲東方、名為「異見」的幽靈,又該由誰去看呢?哈維爾及其同路人並不喜歡「異見者」這個稱呼,那只是西方記者的冠名。而〈無權力者的權力〉泰半篇幅都在解釋為何「異見者」並非形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恰當字眼。
按哈維爾印象,異見者意味離著一小撮高瞻遠矚且離經叛道的文人,敢於組織反抗勢力去挑戰權威。哈維爾當然熟悉這群人,自身已是箇中佼佼。但他不認為這個精英意味甚重的標籤足以概括同路人。更多同路人根本無心參政,民主鬥士非其所願,謹想默默做好自己喜愛的事。但正正因為想做好自己喜愛的事,不少人無可奈何就成了當局的眼中釘,迫上梁山。今天香港充斥所謂「政治素人」,想來不就那麼一回事嗎?
哈維爾記起一九七四年時,曾在酒廠打工。他頂頭上司是個酒痴,敬業樂業,全心全意鑽研釀酒技術,一絲不茍到令下屬亦感到為難。此外,他也多番向高層進諫,指出酒廠應改善之處。可惜酒廠經理不諳此道,區區一個熱衷權力的黨人。他逐漸感到冒犯,愈鬧愈僵,最終利用其黨內關係,革扯酒痴,誣陷酒痴作「政治顛覆犯」。哈維爾案:「由你想做好你的工作始,至你獲悉為社會的敵人終。」[5]為何酒痴會犯上政治錯誤呢?無非因為他堅持做好自己。
假若異見是個幽靈,那異見者即指遭異見附身的人。但亦因為遭異見附身,他開了陰陽眼,見到極權努力想要撲殺的異空間。由此,他也陰差陽錯歸入通靈師之列,識破虛妄,看盡生命的泉源。
哈維爾不直接告訴你誰是誰非,他只要求你誠心問問自己:在極權下,你快不快樂。
植根尋常,不卑不亢
上回提到,西方傳媒好稱蘇聯治下的反抗勢力為「異見者」,哈維爾及其同伴卻不怎麼喜歡這個外來稱呼。他寫〈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文,可以說就是為了替同路人正名。那句膾炙人口的格言「活在真實中」,實即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自況。
若然他所謂「後極權體制」的幕後主宰不是獨裁者,而是意識形態的話,那麼抗爭一方的對手就不再是個別敵人,而是整座散播謊言的機器。「活在真實中」的矛頭指向「活在謊言中」。那應該怎樣做才算活在真實中呢?我做建制派,服從黨國機器,就代表我助紂為虐,活在謊言中嗎?請勿誤會,哈維爾並非馬克思,他不打算高高在上,訓示正義。真假對錯的判決權最終還得交回每個人的內心。
哈維爾眼中的極權仿如生命一般,會不斷擴張及鞏固自己,任何個人意志反倒成了危害體制健康的異物,必欲除之而後快。故此,反抗源於體制與個人的衝突。而意識形態的本領,在侵入你內心,不斷告訴你個人福祉繫乎黨國強大,誘使你放棄自主,服從權威。所以哈維爾才會認為極權下的正邪對決,並非發生在壓迫階層與被壓迫階層之間,而實上演於每個人的心裏。老大哥的眼皮下,人人都兼飾受虐者與施虐者兩角。
至於你,又想過這樣的生活嗎?哈維爾不直接告訴你誰是誰非,他只要求你誠心問問自己:在極權下,你快不快樂。他清楚一樣米飼百樣人,不可能萬眾一心,都願意為民主自由丟掉飯碗。有人但求溫飽,有人爭取尊嚴。而活在真實中指的是忠於內心,不要怕去做你深信為正確的事,哪怕只是認真釀好一桶啤酒。只要人人堅持本色,政權編造的幸福謊言將不攻自破。
相較馬克思的唯物辯證史觀,哈維爾所理解的真實簡直過份唯心了,幾乎可比擬儒家的心學傳統。而在異見者樹起反旗之前,就不過有一群尋常人忠於內心、認真過活、繼而得罪當權而已。基於當權壓迫,這群不滿的人往往只能螫伏地下,撰文、講課、排戲、演唱、祈禱,做西方社會覺得不像是抗爭的事。沒錯,相比起這群堅持活在真實中的人,旗幟鮮明的政治抗爭僅似冰山一角。哈維爾多番強調,異見賴以生長的土壤是個「前政治」的隱蔽域,這片隱蔽域首先就由一群尋常過活的人開闢而成。植根尋常,不卑不亢,拒絕在菜檔前掛宣傳橫額,最終自成獨立社會,用人性來藐視謊言,即「無權力者的權力」了。此情此景,不必多費唇舌,相信香港人已感同身受。
看似平凡的格言,背後大有文章。「活在真實中」一語非哈維爾孤見,而是他與師友的共通想法,堪稱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自況。以後再續談那些啟發過哈維爾的其他想法。
內文註釋
[1] 捷克原文為「Moc bezmocných」,解非常無力。
[2] “A spectre is haunting eastern Europe: the spectre of what in the West is called ‘dissent’’.” Living in Truth, p. 36.
[3] “Communismus”, Supplemente zur ersten Auflage des Staats-Lexikons, vol. 2, p. 23.
[4] “Sometimes,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we even use the label ourselves, although it is done with distaste, rather ironically, and almost always in quotation marks.” Living in Truth, p. 77
[5] “It begins as an attempt to do your work well, and ends with being branded an enemy of society.” Ibid., p. 83
參考讀物
Derrida, J., (2006), Spectres de Marx : l’état de la dette, le travail du deuil et 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 Paris : Gallimard.
Engels, F. & Marx, K., (1999),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Eine moderne Edition, Hamburg/ Berlin: Argument.
Havel, V., (1990), Living in Truth: 22 Essays Publish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ward of the Erasmus Prize to Vaclav Havel, ed. Jan Vladislav, London: Faber & Faber.
von Rotteck, C. & Welcker, C., (1990), Das Staats-Lexikon. Encyklopädie der sämmtlichen Staatswissenschaften für alle Stände. Hammerich: Altona.
延伸閱讀:
【鴨巴甸讀書札記】趁香港還有書——在荒謬時代讀《書店有時》
舉報、放逐、抹殺記憶,香港還有時間嗎?評《我城存歿》
【2021華文出版回顧 · 香港】鄧正健:政治紅線當前,低調進行文化「戰術」
| 推薦閱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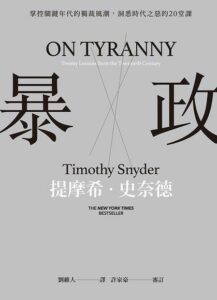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