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沐羽(青年小說家)
編按:第六屆台積電文學賞中,香港作家梁莉姿憑藉作品〈僅存者手記〉,書寫時代裂變下的痛苦、省思及重新探尋自處方式,最終斬獲評審團特別獎。同樣來自香港的小說家沐羽,在讀畢小說後撰文評述,也回應了這個特殊時代下書寫小說的種種疑慮與方法。(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者擬)
小說會挑選它的讀者,我們可能會因為形式或是內容離棄一部作品,說兩句「看不下去」或是「我以後再回來看吧」之類的場面話。梁莉姿的《僅存者手記》沒有挑選我,它沉溺、綿延展開、帶有劇痛、把傷害擰緊疊加成一條繃緊的麻繩。而我還是把它看完了。即使小說沒選上我,還有更多別的把我網羅進去,一路前行到結尾。
《僅存者手記》獲得了第六屆台積電文學賞的評審團特別獎,是這個文學獎第一次出現特別獎,意思是它與另一篇作品並列為雙冠軍。「這是一部與政治相關,又擦邊而過的小說。」梁莉姿在故事大綱裡這樣歸納著,小說裡的人物有各種尖銳的對立:去與留、抗爭與日常、勇武與和理非、前線與後勤、黃藍。諸如此類。但總的來說它是一部講述距離的中篇小說,約七萬字左右。
無論是小說內容還是評審記錄,圍繞著的討論都是距離。朱天心提到時間上的距離,「影像是快的,可是文字或文學是得很花時間的,所以我第一個反應是不太信任的在看」;楊照指向的是政治上的距離,說自己閱讀時帶有戒心:「在我們台灣會有一個壓力,只要是這種香港題材就應該要得獎」;駱以軍更指出了「距離」和「選擇」這組問題,在於和理非被時局剝奪選擇權的悲哀:「我到底是要跟這些人一起去打去鬧去砸,還是說,我沒有選擇的可能?」
無論距離如何,還是有著一個尷尬的問題,它不在文本內部,而在以外:據說香港的書店決定不進這期印刻(台積電文學賞的作品會收錄在印刻文學雜誌)。也許還是得靠博客來,現在總是這樣,寫香港的東西無法在香港輕易獲取。但在此之前,我想圍繞這篇作品講幾個看法,希望可以簡短講完,盡量濃縮至每節三段,你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四篇短文,這樣會讀得比較輕鬆一點。
如果我們遵循嚴格的資格論行事,那甚麼都不用做了,那就懷著痛苦沉默地活下去,然後移民,生出下一代,在沉默中消亡。
人血饅頭資格論
寫香港時必然會提到的問題,人血饅頭。《僅存者手記》在全文結束於一場文學討論裡,把小說從人物裡拉出來,進入了嚴肅討論的範疇。「有人說,(非虛構寫作)還不是在亂世中收割人血饅頭,借機上位。」這問題會連結到寫作者的存在意義,我們究竟是選擇了經濟上的利益、地位上的提高、思想的進步,還是如小說人物林微般被認為是「只想獲得肯定,需要外界的支撐點才能維持自身?」
然而寫作必然與人血饅頭脫不了關係。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裡早就說過,經典的故事總是圍繞著死亡而展開,它是聽故事的人為雙手取暖的爐火。死亡給予了講故事的人權威。如果要指責寫作的人大啖人血饅頭,其實是拉出了一條測量的鬥黃尺規:誰比誰付出更多、付出更多的人才有語話權,那麼結論只有一個:唯有死亡以及被禁錮滅聲的人才能說話。我們這些在監獄以外的、每天被政權當狗耍、又或移民,甚至流亡的人,都沒有資格。因為人血饅頭必然是錯誤的,無論你吃的時候有多悔疚也好。
「難道只有黑人女同志單親媽媽才能講述黑人女同志單親媽媽的故事嗎?」齊澤克和巴迪歐在一場對談裡提過了這個弔詭的問題,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如果我們遵循嚴格的資格論行事,那甚麼都不用做了,那就懷著痛苦沉默地活下去,然後移民,生出下一代,在沉默中消亡。「不在沉默中消亡」這一段話,本來就是吃了滿口「人血饅頭」後,決定把現今的事情傳播出去的行動。《僅存者手記》就是這樣的行動,它立體地展示了從一四年至今各個光譜底下人物的行為及後果。
《僅存者手記》的方法是把敘事者的情緒塞到壓液機底下,把敏感的心靈用力砸扁,由於旁觀他人的痛苦並不道德,便以大量反思將自己的痛苦提升至能夠同理他人的等級。
沉溺與矯情
當然,人血饅頭最純粹的意義還是負面的,它主要指向兩件事:一)用他人的苦難來賺錢,如《僅存者手記》裡批評的某些黃店行徑;二)矯情,「活像過分文藝的傷春悲秋腔調揉入公共領域的寫作中,不能接受;也有人簡單認為只是作者文筆太爛。」
沉溺與矯情的問題從來都是文學想要解決的問題,換言之,怎樣才能在僅存時活得不傷人一點,好看一點,經反思一點,誠懇地與別人靠近一點。《僅存者手記》的方法是把敘事者的情緒塞到壓液機底下,把敏感的心靈用力砸扁,由於旁觀他人的痛苦並不道德,便以大量反思將自己的痛苦提升至能夠同理他人的等級。「我想我們都將會活得越來越極端,越來越吹毛求疵,越來越神經質,直至沒有退路,」文裡這樣寫著:「直至,所有人都沒有退路。」
人血饅頭的論述早就迫使所有人沒有退路,而當作者理解到這一點時,便將它消化為一部文學作品。它最先的難關就指向語言,如何能讓吃相不那麼嘔心?如何讓他人的痛苦看起來並不那麼輕易?矯情和冷硬如何劃分?布朗肖將文學語言劃分成兩種,「陳腔濫調的語言」以及「純潔的語言」,而前者會因為執著地抓捕種種慣例與規則,放逐了文學;後者則會因為不斷實驗與突破變成了一種擺脫了理解的怪獸。換言之,文宣與胡言亂語。而這兩個都是我們所不想做的,因為前者通常指向矯情而後者指向沉溺。回到《僅存者手記》的語境來說,那就是它讓自己的愧疚稍為靈活一點、輕盈一點,遊走在純潔與陳腔濫調之間。
讓類似的重複擠壓出嶄新的能量,讓情緒的高度因似曾相識而提升,是貫穿整部《僅存者手記》的寫作手法。
堆疊敘事
我不是狀聲詞和疊字的粉絲,除非在玩語言遊戲,不然我自己使用時都有種不得不為之的尷尬。在《僅存者手記》裡,這些詞彙還真的不少:「我們鄰近的另一所學校校舍因殺校已久被清拆,轟轟轟。」「眼鏡重新架在她臉上,鏡框鏤出巨大的洞,空空的。」「房間附近的公路傳來名貴跑車飆速的『嗡——!嗡——!』聲,餘音很長,而且多輛齊發,似乎在較勁。」
每次我看到這些修辭時,都會像馬利奧賽車踩到加速般往下跳一兩行,想讓自己逃遠點。在陳腔濫調和純潔之間二擇一的話我會選擇後者,但這也只不過是些個人偏好。但《僅存者手記》的這些狀聲詞和疊字提供了一個解讀全文的密碼,這在「多輛齊發,似乎在較勁」這句話裡側漏了出來。因為在全文中,這些疊字修辭是堆疊起來、反覆出現、互相較勁的。在幾段後,它甚至把尷尬收納起來,轉化意義,帶有差異地重新展露於你的眼底:「於是她小心翼翼(地處理傷口),一片一片用夾子抽出來,餘下那朮目驚心的洞,繼續空空的。」
讓類似的重複擠壓出嶄新的能量,讓情緒的高度因似曾相識而提升,是貫穿整部《僅存者手記》的寫作手法。期間,各種矛盾與反思涉入這道重複的螺旋階梯當中,諸如此類。而故事的能量就節節攀升,直到全文最後跳出人物,如散文般進入了嚴肅討論的範疇。我不是這種寫作手法的粉絲,但在這裡的處理還真找不到甚麼問題。成功的作品就是能夠說服你放下成見,跟著它在它的節奏裡走一趟。
掙扎著去與留、抗爭與日常、勇武與和理非、前線與後勤、黃藍的人物們在這部寫實主義的小說裡來回翻滾,痛楚地向讀者展開了香港如今的「生活性」。
寫實主義
而我始終沒有被這部小說揀選,又或是沒有徹底進入的原因,都圍繞在美學上(而不是政治)。我認同童偉格在評審會議裡的一段話,大意是這個作品分為三部分,頭尾部分使用第一人稱半知,中間部分使用第三人稱全知。問題來了,如果敘事者由此至終都是「我」,那第中間部分我是怎樣還原那個人物的內心,甚至為她作出判斷的?如果第一人稱容許敘事者講得直白,甚至進行嚴肅討論,但在第三人稱裡提出「代價付出了,比我們以為的更重更疼,但我們仍不配許獲民主」這樣的直接判斷句,才是讓我出戲的原因。第三人稱始終是個要保留較遠距離的敘事方法。
不過我記得梁莉姿說過這部作品其實還沒寫完,以後出書會再改一次,這個問題也不是甚麼大問題。《僅存者手記》的強項是寫實主義,以及揉合在寫實主義第一人稱半知框架下靈活的反思與批判,還有層層疊加上去的情緒強度。「寫實主義廣義上是真實展現事物本來的樣子,不能僅僅做到逼真,僅僅做到很像生活,或者同生活一樣,而是具有『生活性』。」這是伍德對於寫實主義的評斷,寫實主義不是再現,不是把經歷過的事情羅列出來,而是說服你:我寫下來的事情有生活的紋路,它折射出一些現實生活的斷片,而你無法稱之為假。
而這就是小說的作業,它不是一場紀錄,不是文宣,不是搖旗吶喊或站在任何一方。因為人從來就不是扁平動物,台積電文學賞是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的意思便是:讓扁平人物回去短篇的國度磨難成長,讓立體的回去長篇的世界走完生命歷程,只有來回於兩者間靈活切換的才能在中篇遊刃有餘。於是,掙扎著去與留、抗爭與日常、勇武與和理非、前線與後勤、黃藍的人物們在這部寫實主義的小說裡來回翻滾,痛楚地向讀者展開了香港如今的「生活性」。而無論是現實的生活,還是小說中的生活,也始終是要脫離政治的一元壓制,正如伍德所說的:「真正的作家是生活自由的僕人,必須抱持這樣的信念:小說迄今仍然遠遠不能把握生活的全部範疇;生活本身永遠險些就要變成常規。」
恭喜梁莉姿,恭喜《僅存者手記》,要繼續讓香港不要變成一言堂的常規。
延伸閱讀:
顏忠賢×黃以曦:文學元宇宙——《地獄變相》的虛實與心念
專訪歐大旭:我所要尋求的許多答案,都已經永遠失去了
連明偉:沒有自我的證言——讀歐大旭長篇小說《倖存者,如我們》

來自香港,現居台灣。 著有短篇小說集《煙街》。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創意寫作課程首屆畢業生。香港文學館媒體〈虛詞.無形〉編輯。曾獲臺北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中興湖文學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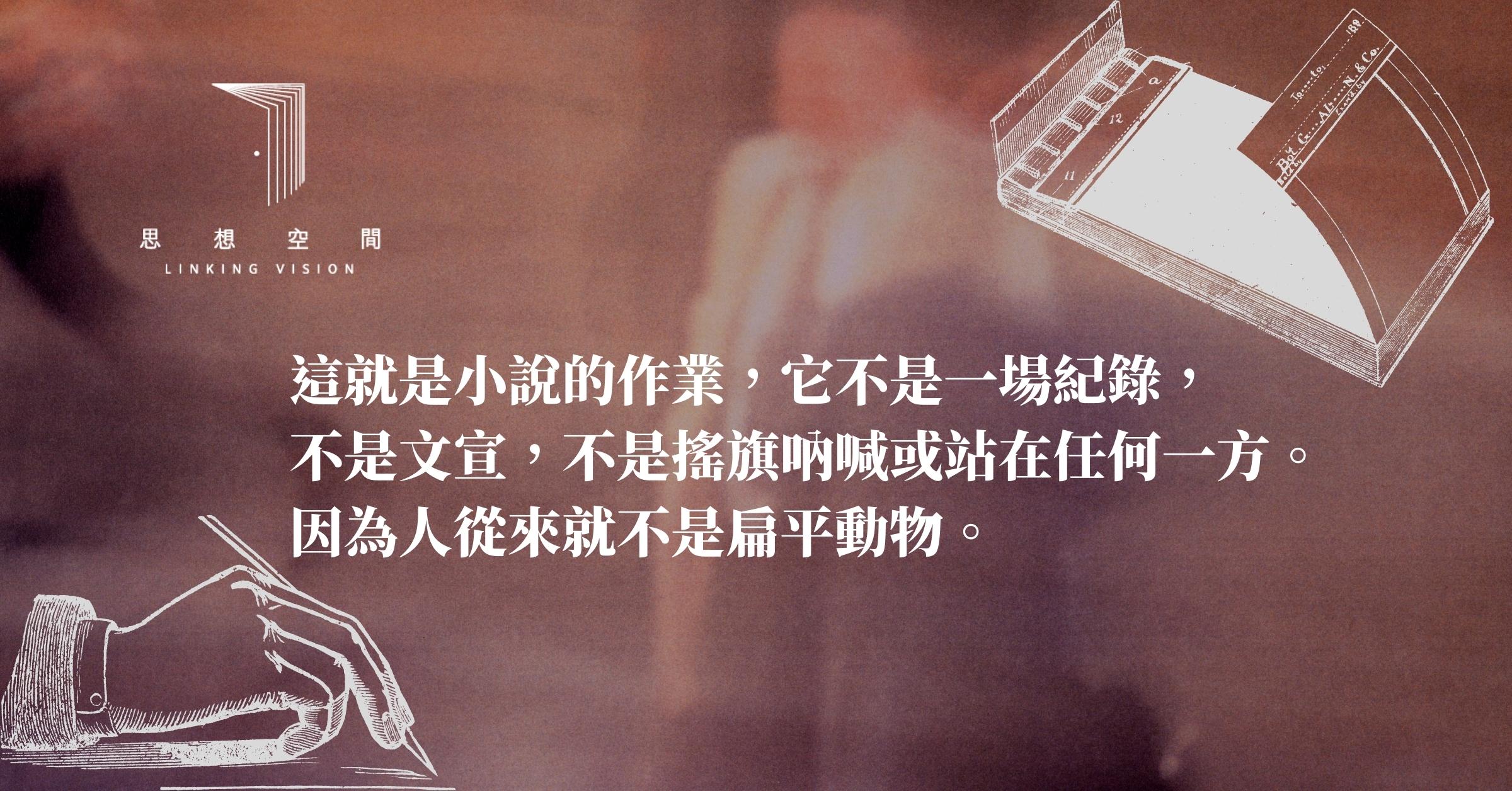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