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德坤(青年小說家、書評人)
關於蘇聯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註:又譯作蕭士塔高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的遭際和言論,相信大部分中國讀者是從《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口述,伏爾科夫記錄並整理)一書中獲取印象的。
我喜歡《見證》,雖然此書的真實性大有爭議,但我認為其中一些論述平實、深刻。不過,我讀伏爾科夫(Solomon Volkov)寫的引言,見其將肖斯塔科維奇視為俄國文化中以裝瘋賣傻,狂言反語諷世的「顛僧」(又作「聖愚」)角色,並稱「既然踏上了顛僧的道路,肖斯塔科維奇也就對他自己所說的一切卸脱了責任:任何語言都已失去它表面上的意義,即使是最高的頌辭、最美的辭藻。
關於人所熟悉的真理的宣講卻原來是嘲弄:嘲弄往往反而包含著可悲的真理」(花城版中譯本,頁9)時,我是深不以為然的。如此說,是不是太方便,太無辜了?事情,真就是如此簡單嗎?
《見證》中,肖斯塔科維奇的話語之間,有一種超然;《時間的噪音》中,肖斯塔科維奇這個人物頗為曖昧,在不確定中遊走。
險惡時代,裝傻的「合法性」
英國作家朱利安 · 巴恩斯(Julian Barnes)以肖斯塔科維奇為主人公的小說《時間的噪音》,則時時提醒讀者:事情即便一目瞭然,也不是簡單的。如果,事情是簡單的,那麼肖斯塔科維奇這個人物,還會閃現觸目的火花,引人深思嗎?
對於肖斯塔科維奇,《時間的噪音》並不作一個傳記式的看上去較完整的描繪,而只截取他一生中三個重要的「時刻」:
1936年,斯大林觀看肖氏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時中途離場,《真理報》之後發表譴責肖氏等人的評論《混亂取代了音樂》。次年,肖氏被當局找去談話後,連續十個晚上等在電梯旁,等待被逮捕;1949年,肖氏受斯大林指派,前往紐約參加國際和平會議,發表當局給定的演講稿,攻擊斯特拉文斯基(註:又譯作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等人;1960年,肖氏加入蘇共。
小說以此三個「時刻」為中心,輔以「閃回」手段,截取肖斯塔科維奇生命中另一些具意味的畫面作補綴。有意思的是,《見證》中,對這三個「時刻」,撇除相關背景之外,幾乎全未觸及。 《見證》中,肖斯塔科維奇說,這是關於他人的回憶錄,而非關於自己的。這自然是不太能當真的。關於談什麼,不談什麼,《見證》中的肖斯塔科維奇有自己的揀擇。避免談論什麼事情,也是有意味的事情。
巴恩斯在《時間的噪音》中揀擇的三個「時刻」,有相當大的空間,供小說家深入挖掘肖斯塔科維奇複雜、矛盾、左衝右突的心緒。《見證》中,肖斯塔科維奇的話語之間,有一種超然;《時間的噪音》中,肖斯塔科維奇這個人物頗為曖昧,在不確定中遊走。
雖然,肖斯塔科維奇自己,或其稱頌者,能為他的處世之道找到一種「合法性」:險惡時代,保存生命乃第一要義。那麼,說些違心話,乾點違心事,便是必要的生存策略。而且,這些違心話、違心事,客觀上來說,也未造成什麼顯明的大的傷害。與此同時,說這些違心話,做這些違心事時,肖氏還表現出了一種顯明的抵觸的姿態,讓人很容易就看出那是「違心」的。
如此,這些話語、行為就成了反諷——這正是伏爾科夫,以及其他許多人為表明肖斯塔科維奇的清白所強調的手段——更重要的,還有藝術作品這一更高級別的「補救」手段:那是一片淨地,藝術家無需裝模作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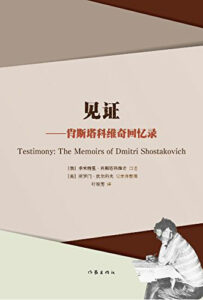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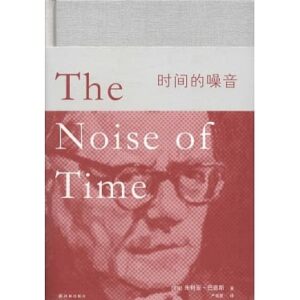
反諷這種東西,亦有一種「自返性」:你以為在諷刺別人,事實上往往把自己也包括進去了。有一種關於反諷的反諷。
反諷的限度與現實荒蕪
肖斯塔科維奇可以這樣申明「合法性」;他的支持者也可以如此證明他的清白;作為某種意義上與肖斯塔科維奇隔得很遠的、沒有受到哪怕十分之一壓在他身上的強力因而並無太多發言權的局外人,我們覺得,肖斯塔科維奇的作為,亦是可理解的。可是,儘管如此,《時間的噪音》中的肖斯塔科維奇,卻時時表現出自我懷疑,「無法心安理得」(頁195),自認是神經病、懦夫。
為何如此?朱利安 · 巴恩斯給出的答案是:作為那種被認為是無懈可擊的保持清白的「反諷」手段,合法性不足。
在我看來,反諷,是《時間的噪音》這部小說最重要的話題。與這個話題相比,什麼懦夫,什麼英雄,都是皮相之談。小說裡,有大段大段的關於反諷的直白探討,讀來使我震動。《時間的噪音》承認反諷的作用,但這種承認,更多的是賦予它一種上解剖台的資格。它有多大的作用?取得了怎樣的效果?有何副作用?在《時間的噪音》這個解剖台上,是顯明、刺目的。
比如反諷的效果,巴恩斯就認為是深可懷疑的:
「但是,他(引者註:指肖斯塔科維奇)不再那麼肯定了。那可能是裝模作樣的反諷,就像會有自鳴得意的抗議。一個農家孩子把一顆蘋果核扔向一輛路過的汽車。一個喝醉的乞丐脱下褲子,朝那些可敬的人們露出光光的屁股。一個著名的蘇聯作曲家往一首交響樂或絃樂四重奏裡塞進了微妙的嘲諷。無論動機,還是效果,這裡面有差別嗎?」(頁218-219)
反諷這種東西,亦有一種「自返性」:你以為在諷刺別人,事實上往往把自己也包括進去了。有一種關於反諷的反諷。有多少人體察出了此種情境?恐怕是不多的罷。這一點,可參看《時間的噪音》中譯本第106頁,那段「權力與公民第二單簧管」對話,是肖斯塔科維奇與對他作品有意見而要求作出修改的指揮家之間對話的戲仿,權力和肖斯塔科維奇用一種相似的輕鬆方式打發了後兩者。讀過《見證》的人,對這個段落,會有更微妙的體會。此處足見朱利安 · 巴恩斯的敏鋭。
關於反諷,《時間的噪音》中還有其他不容忽視的探討。朱利安 · 巴恩斯提出:
「諷刺是有限度的:你不能一邊在信上簽字,一邊摀住鼻子,或背著手,相信別人會認為你並不當真。」(頁208)
對於此種困境,《時間的噪音》裡有一種強大的悲觀的聲音,認為在強權的壓迫之下,人們的神經已被碾碎,無法像換琴絃似的更換神經線:人生進入一個逼仄之境,就只能待在那個逼仄之境了。在我看來,巴恩斯這裡不僅觸及了反諷的限度,也觸及了藝術的限度,甚至語言本身的限度。這一切,都要求人們在反諷等等之外,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這聲音聽上去樂觀了些,但很可能會被指為蠢笨的、不切實際的。
朱利安 · 巴恩斯是清醒的,有些人可能會責他是太過清醒的,撕裂不少東西,讓人難以直視。但是,對於無限度的反諷的清醒認識,有其深廣的意義。雖然,《時間的噪音》描摹的是特定時代的特定人物,但是,刻下,無視反諷的限度的狀況亦是普遍的,犬儒主義亦是普遍的。那麼,我們可以說,《時間的噪音》所描摹的反諷展現出來的荒蕪,在當下也是普遍的。
(本文原刊於「四季書評」,經思想空間編選後刊出;原文題為〈反諷的限度〉,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
四季輪迴,生生不息。 《四季書評》以書評為載體,以閱讀為導向,亦古亦今,亦中亦西,不求新潮,不追熱點,不隱鋒芒,不媚權威,不設藩籬,不問出身,希望同世界各個角落的讀者一同返回讀書交流的初心。嚶其鳴兮,求其友聲。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