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上、下)》(杜斯妥也夫斯基200歲冥誕紀念版)中譯本導讀,標題為編者擬。
編按:在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誕生兩百年之際,聯經出版推出了其經典著作《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200歲冥誕紀念版。這部完成於1880年的作品,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所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也被視為他創作的最高峰。本書收錄魏玲撰寫的深度導讀,帶讀者穿越語言的艱澀與時代的溝壑,更透徹地了解這本書到底講什麼?杜氏寄於文學中的思想內核有哪些?
在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中,思想不是生硬地夾在情節之中,更不是遊離於情節之外,而是自然地融入人物的行動和事件之中的。
思考性與文學性的無縫接合
應當承認,在農奴制改革後的俄羅斯,正經歷著一個社會劇烈變動的年代。按照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理解,這場變動本身就矛盾地兼有「瓦解」和「建造」的兩重性,它既有悲劇性地接近於「混亂」和「災禍」的一面,又有對新的「世界大同」和人類所追求的「黃金時代」熱烈嚮往的一面。他深信,人周圍的世界越是「荒誕」﹑越是缺乏人性,這世界上的人對理想的思念就越強烈,藝術家也就有更大的義務「在人的身上挖掘人」,並且以「充分的現實主義」既展示出統治世界的畸形和「混亂」,也展示出隱藏在「人類心靈中」的追求理想的熱情,以及想「讓被環境﹑世世代代的蕭條和社會的偏見不公正地壓垮的人恢復尊嚴」的意願。正是按照這種信念,作者在深刻地揭露這個黑暗世界的同時,也向人們顯示了從這個黑暗王國裡射出的一線光明。
關於「孩子們」的這一組人物形象在小說中雖然篇幅占得不多,但卻十分引人矚目。他們是「荒誕世界」中的健康力量,是黑暗社會中的光明「天使」。斯涅吉廖夫的兒子體弱多病的伊柳沙從小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公正,並且深深地為父親所受的屈辱而痛苦,同時他年紀雖小,卻沒有失去自尊,他甚至咬傷阿廖沙的手,來報復德米特里.卡拉馬助夫對他父親的侮辱,投石子打那些嘲笑他的同學來維護自己一家人的尊嚴。伊柳沙懂得憎恨,學會了反抗,同時又擁有一顆愛心,他渴望著友誼,深情地眷戀著丟失的小狗。他有著一顆在窮困中受盡煎熬﹑在屈辱中竭力掙扎的兒童的敏感心靈。十四歲的「虛無主義者」科利亞.克拉索特金是一個聰明﹑大膽﹑愛尋根究柢﹑充滿活力﹑具有強烈正義感的熱血少年。他在生命垂危的伊柳沙的床前與伊柳沙相互和解,並千方百計地找回了伊柳沙的愛犬,這是他唯一能奉獻給朋友的慰藉和歡樂。作者在這些孩子們身上寄託了自己對於俄國新一代的希望。他通過阿廖沙.卡拉馬助夫在伊柳沙墓前的講話向人們呼籲:「第一和首要的一條是,我們要善良,其次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再其次是永遠不要彼此相忘」。「即使我們將來身居要職,日理萬機,或者我們陷入什麼大不幸中——你們也永遠不要忘記,從前我們在這裡有多麼好,大家同心協力,擁有一種非常美好﹑非常善良的感情,因而彼此聯繫在一起……。」
作者注意對於黑暗王國中的一線光明進行描寫,表明他對於人類並未喪失信心,表明他對於人類未來的前景抱有一種善良﹑美好的願望。只是他所著力宣揚的所謂吸收人民的「本源精神」,即篤信基督﹑崇尚博愛﹑寬恕﹑謙恭的精神,實質上是主張人們崇奉逆來順受的人生哲學,這並不是把黑暗王國引向「黃金時代」的現實道路。除了孩子們以外,作者筆下的正面形象,從阿廖沙到佐西馬長老,都顯得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這個事實,是上述論斷的有力佐證。
杜思妥也夫斯基是俄國最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家之一。他始終遵循普希金﹑果戈理﹑別林斯基倡導的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同時,他又不斷地進行藝術探索,開拓,創新。他不是濃墨重彩地描寫外在客觀世界,而是注重描寫人們的內心所感受的世界。他的作品直接表現的對象往往是人們的心理活動。他在晚年說過:「人們叫我心理學家,不,我只是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也就是說,我描寫的是人類心靈深處的一切。」這是因為,正如巴赫金所說的那樣,杜思妥也夫斯基塑造的思想形象「從來不無中生有,從來不杜撰它們」。他的作品中的思想形象在當時的社會裡都可以找到他們各自的原型,他們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社會思潮鬥爭在文學創作中的形象反映。在作者筆下,不僅伊萬.卡拉馬助夫是思考著的人,就連次要人物如老卡拉馬助夫等也是獨特的「思想者」,他們都有自己的一整套人生哲學,都在按各自不同的方式解答著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在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中,思想不是生硬地夾在情節之中,更不是遊離於情節之外,而是自然地融入人物的行動和事件之中的。情節的生動性和故事的完整性,不但沒有弱化作者所表現的思想觀念,反而為他充分展示思想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天地。他不是抽象地描述思想,而是在展示社會思想形成的生動過程,同時又表現這些思想對情節的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比如伊萬的「人可以為所欲為」的思想,就不是他一開始就具有的。作者結合有關的事件,敘述了舊道德基礎的瓦解和利己主義的日益膨脹,而伊萬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形成了這種思想。當他把這種思想灌輸給斯梅爾佳科夫之後,便對斯梅爾佳科夫陰謀弒父的行動提供了思想根據,起了催化作用。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情節與俄國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的情節不完全相同。在他的作品中,情節的發展不像岡察洛夫﹑托爾斯泰作品中那樣緩慢﹑平穩,它們總是起伏跌宕,一波三折,令讀者既感到意外,又覺得入情入理。比如,當米佳聽說格魯申卡趕往莫克羅耶會見自己的初戀情人——一個波蘭人穆夏羅維奇去了,米佳也急忙奔向那裡,當時他已處於絕望之中,並已作好自殺的準備。一到客棧,米佳又立即加入了波蘭人玩紙牌的牌局,在賭博中,波蘭人作弊耍賴,並對格魯申卡進行侮辱,其卑鄙下流暴露無遺。隨之由米佳做東,一場狂歡的飲宴開始,格魯申卡對那個波蘭人魂牽夢繞多年的戀情被徹底粉碎,她投入了米佳的懷抱。正當米佳如醉如癡地享受著這意外的歡樂時,大禍從天而降。原來小城中發生了凶殺案。在米佳眼前出現的新生活的曙光一閃而過,站在他面前的是檢察官﹑法院預審官﹑縣警察局長……。他們對他提出了他是弒父嫌疑人的指控。如此大起大落﹑扣人心弦的精彩描寫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書中並不鮮見。
杜思妥也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把生活中突發的事件作為故事情節的主要環節,把經過縝密思考和深入研究過的觀點和信念形成的體系的代表者即思想形象作為小說描寫的中心,並巧妙地把這二者結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為了塑造眾多的思想形象,作者往往設置了一幕幕的戲劇場面,在這些場面裡集中表現情節的衝突,加劇情節的緊張性,同時給思想形象提供了在互相交鋒中亮相的大舞台。比如,在小說的開始,作者巧妙地安排了全家到修道院聚會的場面。當時,老卡拉馬助夫與德米特里為爭奪格魯申卡當眾口角,要求決鬥。這時佐西馬長老突然當眾跪倒在德米特里的腳下,向他磕了個頭。他想以這種非同尋常的方式警醒眾人,防止慘劇的發生。因為「他嗅到了犯罪的氣味」。在第二部,作者安排了在酒店裡伊萬和阿廖沙兄弟倆就有沒有上帝的問題展開的一場對話,尖銳地表現了信神和不信神這兩種思想體系的對立。在小說的末尾,作者把幾乎所有主要人物都集中到了法庭上,安排他們在這個決定德米特里命運的動人心弦的場面上,共同演出了一場多聲部的大合唱。
小說中的對話猶如戲劇舞台上的台詞,具有明顯的行動性,不僅表現出人物複雜而豐富的思想活動,而且可以看到人物本身的性格特點,人物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所處環境的氛圍。如德米特里的未婚妻卡捷琳娜與情人格魯申卡在阿廖沙面前的那場對話就十分精彩。作者通過對話,展現出了卡捷琳娜對格魯申卡的輕信﹑寬容﹑憐愛和被她侮辱後的惱羞成怒﹑歇斯底里大發作,由此深刻地揭露出這個貴族女學生天真爛漫﹑愛好幻想,卻又自私﹑自信﹑自負﹑傲慢的性格特點。對話也表現了格魯申卡這個風塵女子自尊與自卑交織變化的複雜情感及其性格中粗魯﹑大膽﹑任性﹑詭詐的一面。對話並且把兩個情敵之間箭拔弩張的緊張氣氛傳神地鋪展在讀者面前。
在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心目中,「莎士比亞是神派來向我們宣布人和人類心靈之隱秘的預言家」。對於杜思妥也夫斯基,我們也同樣可以這樣說。
善寫內心衝突,是因經歷過各種痛苦
表現人物的平和心境﹑緩慢的心理活動流程並非作者的興趣所在。他對於描寫人物內心的善與惡的衝突鬥爭情有獨鍾。他善於表現人物內心的尖銳衝突和激烈鬥爭而導致的精神分裂和兩重性格。他把這種內心衝突視為卡拉馬助夫整個家族所共有的心理活動的特徵,就連「小天使」阿廖沙也不例外,他的心裡也有著那被稱之為「昆蟲」的情欲在蠕動。卡拉馬助夫家族的心靈就是「能兼容並包地把各種對立物集中於一身,一下子省悟到兩個無極:一個是我們頭上的無極,至高無上的理想,一個是我們腳下的無極,最低級下流和臭氣熏天地墮落。」這是不難理解的。正如盧那察爾斯基所說的那樣:「杜思妥也夫斯基處於社會危機尖銳的時代,即是在各種互相矛盾的強大社會潮流影響之下,俗語叫做『靈魂』的那個東西分裂為兩半或好幾個部分的時代。」作者不過是把這種時代中的人們的心理特徵藝術地再現出來罷了。他認為,這種反常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現著事物及其過程的本質的。他明確地說過:「我有自己看待(藝術中的)現實的觀點,大多數人幾乎稱之為荒誕而獨特的東西,對我來說,有時正是現實的本質。」
人物的對話和獨白是作者表現人物內心分裂的重要手段。在許多場合,他筆下的主人翁與其說是在與自己的思想論敵進行爭論,不如說是在與自己爭論。例如伊萬在與阿廖沙就有無上帝的問題進行爭論時,人們可以看到,他是在與自己內心深處的上帝進行搏鬥。儘管在爭論中,一個處於攻勢,一個處於守勢,但處於攻勢者其實也很虛弱,因為他一方面在竭力論證自己的觀點以期說服對方,另一方面也是在設法說服自我,消除自己內心中的疑慮。作者有時會用對話中的獨白來表現人物內心的分裂。
在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相當大的篇幅是用來表現人物病態的分裂的心理。正因為如此,威格曾稱他為「被侮辱和病態的心靈的解剖學家」。作者所以對病態的心理學感到特殊的興趣,是因為這些病態的心理現象反映了時代的病症及其引發的社會道德危機和個人道德危機,表現出了社會生活內部的隱患。在他看來,犯罪者的心理﹑精神失常者和自殺者的心理,都是極富時代特徵的。作者正是通過對卡拉馬助夫家族成員進行病態心理學的分析,來勾勒他們的形象,揭示他們為當時的社會條件所規定﹑必然走上的生活道路。小說中的伊萬最後的精神失常,斯梅爾佳科夫的終於自殺,這只是他們的病態心理發展的終極結果,其實,在這之前,在他們的心理活動中就早已潛藏著種種病態的因素了。在這方面,伊萬與魔鬼交談的這個奇異的章節,是值得注意的。伊萬一再對魔鬼說,「你是我的化身」,「是我的幻想」。因為他意識到魔鬼是從他身上分離出來的另一半,是他內心中被壓抑的一種潛意識,即對父親的厭惡,希望有人殺死他;但是他的另一半,頭腦中的理智卻又在對魔鬼發怒,並與之進行較量,試圖戰勝它。正是這種內心矛盾,最後把伊萬引向了瘋狂。小說對人的病態的自尊心的表現也堪稱一絕。例如德米特里,他就一再強調「自己是卑鄙小人,而不是賊」。他把卡佳讓他匯給她姨媽的三千盧布,花掉了一千五百;挪用的第二天,他就想把剩下的半數還給卡佳,並一直想把花掉的一千五百補上。他說他「並不懼怕懲罰,而是害怕恥辱」……他竭力找尋賊和卑鄙小人之間的區別,病態地守衛著心中已然崩潰了的道德防線。作者企圖通過描寫這種顯得可悲又可笑的病態心理,顯示德米特里雖然墮落成了「賊」,但他仍然在捍衛著作為人的某種尊嚴。正因為如此,他才能繼續自信地活在這個世界上,他才會在往後的某個時刻獲得精神上的復活。
在世界文學史上,很少有人能夠像杜思妥也夫斯基那樣,對人的反常的病態心理作出如此生動而深刻的描寫;因為事實上,在作家群中,很少有人曾經像他那樣,有過如此曲折而苦難的經歷,接近過如此眾多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了解過社會底層的這些人的悲慘的命運。他是「靠著充分的現實主義在人的身上挖掘人」這一原則,在研究人這個秘密,在「刻畫人物的心靈深處的全部奧秘」。高爾基把杜思妥也夫斯基和莎士比亞相提並論,是毫不過分的。在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心目中,「莎士比亞是神派來向我們宣布人和人類心靈之隱秘的預言家」。對於杜思妥也夫斯基,我們也同樣可以這樣說。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書的這個新譯本的譯者,是著名翻譯家臧仲倫。臧先生係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教授,曾擔任該系俄羅斯語言教研室主任,是一位長期從事俄羅斯語言和翻譯理論教學與研究的學者。
多年來,他致力於譯介十九世紀俄羅斯古典文學名著,譯著甚豐。對於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他尤其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並且是《死屋手記》﹑ 《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罪與罰》﹑《白癡》等新譯本的譯者。臧仲倫先生的譯作,準確﹑流 暢﹑ 傳 神,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巴金曾高度評價他的譯作,並請他校訂自己翻譯的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我認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個新譯本,是臧先生貢獻給讀者的又一個精品。我相信,它是一定會受到讀者歡迎的。
| 新書快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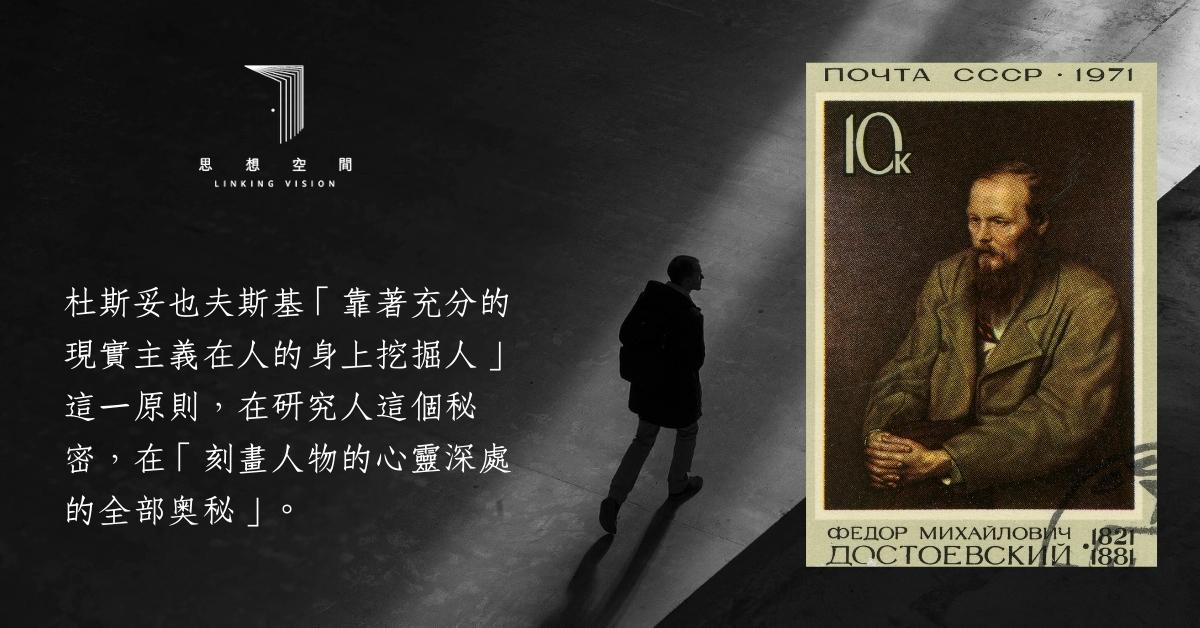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