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次級實在」的產生,也會扭曲人使用的語言,語言也逐漸會喪失作為人的思考和真實的實在兩者間媒介,而不再和現實有關,成為次級實在的一部分,也就退化為了意識形態的框架。
一位年長的學者談論過去,他說當年,他們是真心相信糧食產量大躍進(儘管不是那種天文數字),也用科學思考進行論證過。他們中學時晚上打數盞探照燈試圖讓植物進行更多的光合作用……他現在覺得,「那時好像生活在虛幻中一般。」這是一個長期困擾我的問題,眾多善用理性,獨立的人是如何被裹挾進入一個虛幻的世界呢?在沃格林(Wilhelm Vögelin)《希特勒與德國人》中對於小說《堂吉訶德》的分析,提供了一個解釋的視角。
沃格林論堂吉訶德
「第一實在」是一個真實的世界,而「次級實在」則可以說是現代意識形態的前兆。沃格林通過分析兩者之間的運動關係,試圖解釋納粹德國的思想起源問題。他指出第一波「第一實在」和「次級實在」之間的運動關係出現在封建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舊的道德秩序不能夠再反應人類真實的現實,從而退化為一種「次級實在」,而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是英格蘭地區則出現了新的道德秩序的設想,如湯瑪斯.莫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指出傳統道德秩序的衰敗。
「第一實在」是如何被「次級實在」所代替的呢,沃格林關注到17世紀初一個最有趣的現象,就是賽凡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所寫的《堂吉訶德》,賽凡提斯是莎士比亞同時代的人(這點在中文譯文中翻譯錯誤),《堂吉訶德》第一卷於1605年出版,第二卷在十年之後的1615年才出版。第一卷中講述了兩次堂吉訶德的冒險經歷,而第二卷所描繪的是他第三次冒險記。
堂吉訶德本身是一位愚人,在第一次冒險中,他是獨自一人胡鬧,人們也因為他是一位丑角而願意捲入這場娛樂(Divertissement)的鬧劇中。但是在第二次冒險中,出現了另一個人物桑丘,他生活在「第一實在」,並沒有受到堂吉訶德的「次級實在」的影響。因此,堂吉訶德眼中的巨人,在桑丘的眼中是現實世界的風車。這兩個世界中必須有一個轉化者,否則兩個世界是無法彼此對話的。因此這個轉化者就是想像出來的巫師,巫師將真實世界的「第一實在」轉化進入到堂吉訶德所構造的「次級實在」中。當桑丘在「第一實在」,也就是在真實世界中看到風車,其原因就變成為是巫師把巨人變成了風車,而堂吉訶德自己則認為是看到了巫師把巨人變成了風車來掩蓋巨人存在這樣一個事實。一旦桑丘接受了巫師的存在時,他就迅速滑入到「次級存在」中,成為了繼續構造次級世界的僕人和愚人。在第三次冒險開始時,賽凡提斯設定了一個背景,就是前兩次的冒險讓堂吉訶德變得家喻戶曉,無聊的貴族們開始對堂吉訶德這個愚人、丑角進行招待,把他當成一種「娛樂」。沃格林認為來源於帕斯卡(Blaise Pascal)思想中的「娛樂」這個詞涉及到特定的社會階級,就是在道德衰落到一定程度時,這個特定的社會階級已經厭惡了真實的「第一實在」,而加入到這種滑稽的思想遊戲中,甘願墮入到「次級實在」中。於是,在第三次冒險中,貴族們參與其中,設計幻境讓桑丘認為自己是總督來斷案,以此進行娛樂大眾,給堂吉訶德和桑丘蒙上雙眼騎木馬,製造鬧劇說他們升到了天上,讓他們講述所見所聞。所有人都這樣進入到了一個「次級實在」中,正如堂吉訶德因為幻想病症關在木籠子裡、被教士護送回家時對自己的一個辯護,關於他的書,各種各樣的人都在讀,這些都是得到皇室許可和批准印刷的,怎麼可能不是真實的呢?對此,沃格林在總結「次級實在」時說,「首先,如果愚蠢的舉動變得普遍,那麼它就會成為社會的主導;並且如果它被權威所粉飾時,就更被視為是社會的主導和正確的。從而,你已經具有了一個全權(totalitarian)政體的條件——那裡決定性的意識形態被制定,並且宣傳說要服從國家,它都是對的。」這也被沃格林稱之為巴特摩斯勒(Buttermelcher)綜合症,也就是如果這是權威人士說的,那麼它就一定是對的。(第244頁)
伴隨著「次級實在」的產生,也會扭曲人使用的語言,語言也逐漸會喪失作為人的思考和真實的實在兩者間媒介,而不再和現實有關,成為次級實在的一部分,也就退化為了意識形態的框架。因此,在「次級實在」取代了「第一實在」真實的現實存在時,這個社會將以各種「娛樂」的形式去將人拉入到虛幻中,更加會爆發巫術幻覺,而語言的真實性也被扭曲。在這個社會中儘管依舊在表面上展現著人類社會的形式,但事實上已經背離了人性。而那些依舊活在真實實在中,沒有異化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對它徹底地背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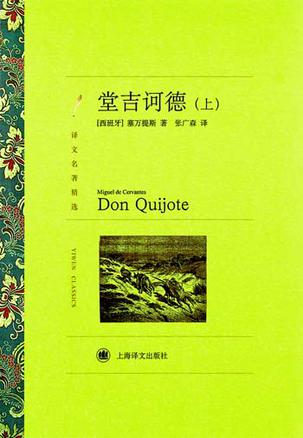
在我們生活的現實中,次級實在的存在,並不因為創造者的消亡而消亡。東方不敗死後,他仍舊將人們拖入在這種虛幻的意識形態中,權力作為巫術的角色轉換了任我行進入到次級實在中。
幻象的可能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堂吉訶德在中國的傳播和解讀,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最初林紓翻譯為《魔俠傳》,是和當時本土的武俠小說一道出現。到1950-60年代,楊絳的翻譯,年代的背景就會讓人浮想聯翩。然而,在中文世界中我們也能夠找到相類似的描述,金庸所寫的《笑傲江湖》中東方不敗以及他/她生活的周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笑傲江湖》寫作的時間是1967-69年,這是一個社會急劇變革的時期,舊的秩序和道德被打破,新的文化、秩序和語言繼續被人所確立。這個故事的背景是超脫於具體的時代,儘管一些推斷可能將其放置在明代,然而故事的核心和表達卻適用於任何一個時代,因為它涉及到了關於欲望和自由之間的張力問題。這種張力首先就表現在了東方不敗的身上,並且進行了自我的分裂。
金庸也許沒有意識到「東方不敗」稱呼本身就是一種幻象。在書中,東方不敗被譽為無論武功和才智都是無與倫比,即便是再最後的決鬥中,當世的三大高手同時出全力攻擊也被東方不敗壓制的毫無招架之力。然而這個名字本身就是異化的,因為只有絕對的自由作為普遍、完整的實體才能夠實現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與其抗衡的情況,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絕對的自由必須完成普遍意志與個體意志之間的對立,精神在自我異化後,否定自我,從而過度到一種自覺的精神上。但人不是絕對的精神,無法逾越絕對的深淵,是無法不依賴他者。在東方不敗的身上,則是通過《葵花寶典》這種近乎巫術的設置,完成了東方不敗主體性的分裂。一方面,他是日月神教的教主,讓人即便聽見名字都不寒而慄;另一方面,她成為了深居閨房繡花的女子。在書中,金庸是這樣寫到令狐沖和任盈盈進入到東方不敗內室時,「一進門,便聞到一陣濃烈花香。見房中掛著一幅仕女圖,圖中繪著三個美女,椅子鋪了繡花棉墊……房內花團錦簇,脂粉濃香撲鼻,東首一張梳粧檯畔坐著一人,身穿粉紅衣衫,左手拿著一個繡花繃架,右手持著一枚繡花針,抬起頭來,臉有詫異之色……眾人都認得這人明明便是奪取了日月神教教主之位、十餘年來號稱武功天下第一的東方不敗。可是此刻他剃光了鬍鬚,臉上竟染施了脂粉,身上那件衣衫式樣男不男、女不女,顏色之妖,便穿在盈盈身上,也顯得太嬌豔、太刺眼了些。」(第1101-1102頁)
笑傲江湖
東方不敗的異化,是通過權力的欲望和以巫術存在的《葵花寶典》所共同完成的。在自我分裂中,他的絕對自由的虛幻,在於他/她兩者的對立並不能夠在自身中統一起來,東方不敗仍舊需要依存一個他者。這種轉化非常有趣,就是他曾經幻想成為神和至高主權的欲望無法在自我中和解,而被投影為了一位依靠順從於男人楊蓮亭的女子的幻象中。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東方不敗與楊蓮亭如同堂吉訶德與桑丘的對應,他們共同構造出了一個次級的實在,在本能中欲望仍舊隱藏在暴力殺戮和大清洗之中,在主體中他卻試圖分裂為一個柔軟、仁慈的女性,他以母性的身份出現,將暴力和支配再生產連結並隱藏了起來。對此,東方不敗說,「我初當教主,那可意氣風發,說什麼文成武德,中興聖教,當真是不要臉的胡吹法螺。直到後來修習《葵花寶典》,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諦。其後勤修內功,數年之後,終於明白了天人化生、萬物滋長的要道。」然而,東方不敗實際上卻仍舊在自我所創造出的「次級實在」中,楊蓮亭用語言和恐懼統治維持了一個外在的「次級實在」,也就是東方不敗和後來任我行所聽見的文成武德,各種溢美之詞。但是東方不敗接著深化了這個虛幻,有進一步創造了一個內在的虛幻,只有生活在真實中的人才看出了問題,「眾人聽他尖著嗓子說這番話,漸漸的手心出汗,這人說話有條有理,腦子十分清楚,但是這副不男不女的妖異模樣,令人越看越是心中發毛。」(第1106頁)
在我們生活的現實中,次級實在的存在,並不因為創造者的消亡而消亡。東方不敗死後,他仍舊將人們拖入在這種虛幻的意識形態中,權力作為巫術的角色轉換了任我行進入到次級實在中。在復仇奪位之前,任我行看到這種阿諛奉承的言辭,暗自打算廢掉這些,然而一旦他坐在教主之位發號施令時,聽見下屬稱他為「文成武德,仁義英明聖教主。教主中興聖教,澤被蒼生,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時,漸漸他也欣然接受了這就是真實的世界。舊的世界依舊沒有被革命所顛覆,革命的洪流浩浩湯湯,吞噬著自己的兒女,成為了一種迴圈,一種偽裝成崇高的獻祭。金庸在這裡,將令狐沖拉出了次級的存在,讓他活在「第一存在」的真實中,令狐沖眼裡所看到的是,「燈光又暗,遠遠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經頗為朦朧,心裡忽想:『坐在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還是東方不敗,卻有什麼分別?』」當語言和外在環境徹底被巫術和權力虛幻的時候,當人面對「次級存在」的時候,一旦我們通過參與和娛樂就會迅速被捲進到這個世界中,然而卻可以用厭惡來提心我們的良心,這是一個虛假的存在。當教眾都在表忠心時,「令狐沖站在殿口,太陽光從背後射來,殿外一片明朗,陰暗的長殿之中卻是近百人伏地,口吐頌詞。他心中說不出的厭惡……」
《笑傲江湖》和《堂吉訶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在於,缺失了娛樂和愚蠢在構建「次級實在」中的作用。只有到1969-1972年這些重要的年代中,在連載的《鹿鼎記》中,金庸通過韋小寶作為娛樂和貌似荒誕的角色,加深了神龍教的「次級實在」的情況,藥物和權力支配,大力提拔年輕一代,並通過激進年輕人清洗老部下的過程中,洪教主卻被韋小寶拖進了「次級存在」的更深處,以為自己是太陽和不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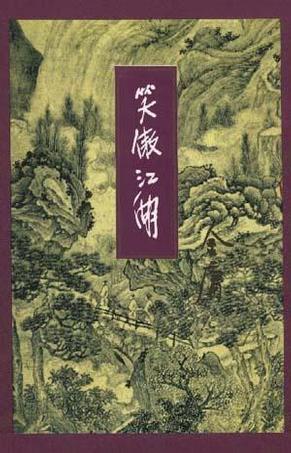
活在真實中
人應當如何活著,是政治哲學的首要問題。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卻在今日被娛樂化,通過技術遮罩了真實,我們甚至無法獲知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什麼是正發生的大事,什麼是具有價值的事情,滿螢幕的娛樂和荒誕的文字和更大的權力意志構造著一個荒誕的「次級實在」,從今日語言看似變化實際卻蒼白無力的狀況就可以窺見。如果我們無力對抗,那麼哪怕僅僅是對它的厭惡,不用已經敗壞的語言,也足以讓我們有力去脫離這種虛幻之境,活在真實中。在《沃格林革命》中,政治學者桑多茲也指出了這點,「每個精神上敏感的人,不論是柏拉圖、還是保羅,或是致命的極權主義或別的什麼主義的意見氛圍之當代的受害者,在他們的生活中要朝向真理敞開而為生存重新定向,必不可少的首要行動,就是堅決抵抗非真理。而抵抗運動,加入它並不只是敢於對惡的要求公然說不,或不只是在不同於教條性爭吵的雜音中添加點自己的聲音,那麼,抵抗就能在一個人求索大問題的真理的意識中,形成反應性象徵符號——見諸於神話、哲學、啟示、文學和藝術。」(該書第203頁)
| 閲讀推薦 |
四季輪迴,生生不息。 《四季書評》以書評為載體,以閱讀為導向,亦古亦今,亦中亦西,不求新潮,不追熱點,不隱鋒芒,不媚權威,不設藩籬,不問出身,希望同世界各個角落的讀者一同返回讀書交流的初心。嚶其鳴兮,求其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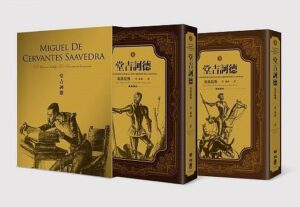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