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兆正
(*本文轉載自《今天》總第117期)
無論從風格、主旨抑或寫作時間,《在天涯:詩選1989—2008》收錄的最後一首〈過冬〉,均已無限接近於〈歧路行〉。某種意義上,長詩正是詩人的自傳,他於其中回顧了個人命運和當代歷史的糾纏,處理了此前諸多短詩無從完整呈現的疑難,那首略帶悲愴色彩的〈過冬〉,即是這一自傳式書寫的開端,後者有着標誌性的「醒來」,點到為止地涉及了「心與狼群對喊」「債務」「鄉愁」、見證等主題。在《過冬》的結尾,北島預告了「重織的時光」留下一首「未完成的詩」,這或許便是自二〇一〇年起寫,直到二〇二一年歲末才落筆完成的〈歧路行〉。
二〇一六年的某次活動中,詩人把「歧路」解釋為「迷路」:「作為一個詩人,我永遠在迷路」,此亦〈過冬〉裏一閃而過的詩眼「迷失」。此外,「迷途」一詞也素為他偏愛。隨着時間推進,這個詞組的情感多義性不斷顯露,如九十年代中期有過「在昨天與大海之間/哦迷途的歡樂」(〈無題〉)這樣的表述,廿餘年後悼念妹妹的〈安魂曲——給珊珊〉一詩,「迷途」又是「離別」。千禧年後,詩人又一次踏上故土,「歸程」與「重逢」對位,「迷途」和「告別」等同,是以「歸程/總是比迷途長/長於一生」,「重逢/總是比告別少/只少一次」(〈黑色地圖〉)[2]。將時光回溯至九十年代中葉,這個詞首次出現在詩人筆下,是在一首題為〈在歧路〉的詩中,那是「歧路」的發端:「沒有任何準備/在某次會議的陳述中/我走得更遠/沿着一個虛詞的拐彎」。
「歧路」也好,「迷途」也罷,惟當詩人意識到自己面對着這段歷史,而且負有表達與見證的責任時,長詩便是不可或缺的載體。當然,要找到「引爆故事的/導火索」(〈據我所知〉),以世人熟知的風格切入就是最穩妥的。這是〈歧路行》的序曲與第一章——那個熟悉的北島又回來了。
那個原點,如今只是剩下了一堆雜亂無章的記憶碎片:夜與晝、交通信號燈、救護車、手風琴、歌手、吉他手、帳篷、月光、失眠、佚名的日記本。
序曲第一段,詩人拋石機一樣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為什麼此刻到遠古/歷史逆向而行/為什麼萬物循環/背離時間進程/為什麼古老口信/由石碑傳誦」。此為面對東方歷史的沉思,如黑格爾所言:「我們在談論這個帝國最古老的歷史時,並不是談論他的以往,而是談論它當今的最新形態。」[3]序曲第二段轉入詩人親歷的歷史,「今天派」的抽象風格仍在,卻已然不容爭辯地把歷史轉換為「歷史的為我論」——這是筆者在閱讀〈歧路行〉時新造的詞:詩人耳順之年思索六十年的經歷,他同時也就是在思索着這個國家的過往,反之亦然,並且只有在兩者相關聯時,「談論這個帝國最古老的歷史」或「它當今的最新形態」,才不會言之無物,儘管他未必不清楚「標語隱藏在牆上/這世界並沒有多少改變」(〈給父親〉)。
沉思令提問變成自問,略去「紅罌粟」「開鎖」等熟悉的字眼不談,在序曲結尾,長詩切入的具體歷史浮現:「何時放飛一隻鴿子/把最大的廣場/縮小成無字印章」。大與小的轉換亦是「歷史的為我論」的題中之義。於是有了雄辯的第一章,自序曲「為什麼……難道……誰……哪兒……何時」推至「逝去的是……返回的是……」;「我是……」。尾聲部分暗藏了兩個施動者的更迭:作為施動者的大他者(「槍殺古老記憶」「劊子手思念空床」),被詩人匿名處理(「是時代匿名的時候了」)。餘下的數千詩行,正是「詩歌泄露天機的時候」。
序曲和第一章都可作為長詩的序言,正文始於第二章:一九八九年,詩人四十歲,此刻的他將從中年往後與向前俯瞰自己的一生,而作為敘述原點的這一年難以略過。恰恰是由於它,「路」成為「歧路」,但它是否又意味着存在一條弗羅斯特所言的「未走之路」(在另一個平行時空,「歸程」並不漫長,「重逢」亦不難得);選擇一條路,便意味着另一條路永遠不被踏上[4]?事實上,也容不得當事人選擇——不僅僅是因為早在十年前或十五年前他便認定自己「沒有別的選擇」(〈結局或開始〉),「只能選擇天空/決不跪在地上」(〈宣告〉),也因為「真理在選擇它的敵人」(〈布拉格〉),而且還由於這一切原本就「沒有任何準備」(〈在歧路〉),是以「談判與農貿市場 討價還價/剎車失靈而猛踩油門」(〈歧路行》)。
那個原點,如今只是剩下了一堆雜亂無章的記憶碎片:夜與晝、交通信號燈、救護車、手風琴、歌手、吉他手、帳篷、月光、失眠、佚名的日記本。詩人在八十年代中期寫過一首短詩〈無題》,第二段是「掛在鹿角上的鐘停了/生活是一次機會/僅僅一次/誰校對時間/誰就會突然衰老」。這是否又可看作一種預言?「僅僅一次」,所以骰子一旦擲出,其他可能性的宇宙便重回黑暗。五年後的另一首詩,北島重述此意,卻是異國輾轉難眠的夜晚反顧半生的圖景:「我調整時差/於是我穿過我的一生「(《在路上》)。
「詞的流亡開始了」,「歧路」也開始了;「更多的人加入難民的路線」,也「加入失眠者的行列」。
自第三章,長詩開始有了腳註,前文的「今天派」風格又一變為另一種敘述特色,這也是統攝整部作品的根本風格,我稱之為「蒙太奇」[5]:「城市上空 火光與煙/裝甲車 鋼盔 槍口/血 三輪車 傷員/死亡的臉 人影搖晃」,下一段鏡頭迅速被切換:「這是星期日大清早/在故宮筒子河邊//有人照樣吊嗓子/回聲拍擊紅牆/他字正腔圓/唱歪水中的角樓/鼓點讓歷史過場」。前者是詩人的中年,後者彷彿衍自詩人的童年,兩個鏡頭竟攝於同一歷史時空。從當年五月起即在西柏林訪問的詩人給北京的家打電話:「從西柏林到北京/佔線 斷斷續續」;「西柏林與北京一牆之隔/子彈呼嘯而過」。三個月後,他在哥本哈根再次撥打北京的長途,四歲的女兒問他:「爸爸 你怎麼不回家」。缺席的回答被寫入同時期的另一首詩:「他變成了逃亡的刺蝟」(〈畫——給田田五歲生日》)。
「詞的流亡開始了」[6],「歧路」也開始了;「更多的人加入難民的路線」,也「加入失眠者的行列」。第六章,歷史翻頁(「所有新聞變成舊雪」),時間也向前移動來到八九年的歲末,此時的詩人從西柏林前往奧斯陸做訪問學者,他開始和朋友商討《今天》復刊的可能,「詞的逃亡」的主題仍在延續。換言之,《今天》復刊,「正是為失敗的意義突圍」。雜誌復刊的決定最終在一九九〇年元旦的奧斯陸機場作出,它也讓長詩的鏡頭在第七章由原點附近的徘徊轉向了久遠的過去:以趙一凡先生為阿里阿德涅的線頭,詩人將七十年代的記憶梳理為黃皮書、工地勞作、「九一三事件」、曝光暗室寫出的《波動》、「四五運動」、毛澤東逝世等片段。由那些死去作者餵養的寫作,是同黑夜搏鬥的武器。
第八章看似述古(公元前493年),實際卻是自述。此處的蒙太奇在於,兩個截然不同的時空,主人公年歲相當,心境在詩人的想象裏也大抵相近,有賴於此,「你年近六十/夕陽下 白發作筆鋒/歪斜的影子如敗筆/直指東方的故鄉」,雖是和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對話,亦未嘗不可看作詩人內心的訴說。所以我們也就是在閱讀着兩份被《為政》篇界分的履歷,一份是顯在的古,一份是隱匿的今,二人共同叩擊午夜之門。第十、十五章的筆法大率類此。
前九章寫成同年,北島在香港中風——他在第三十三章交代了這段往事——長詩因之不得不暫緩。〈歧路行〉的發表情況大體如下:除去二〇一五年《收穫》選刊的八、九兩章,長詩全部發表於《今天》雜誌,計二〇一二年春季號的序曲與前九章(飄風特輯,總第96期),二〇一九年春季號的第十至十八章(總第121期),二〇二一年春季號的第十九至二十六章(總第129期),以及本期刊載的第二十七至三十四章。了解了這一點,可知第九、十兩章是長詩前半部與後半部銜接的地方。第九章是詩人初試長詩的落筆之處,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它同時也是一個多重意義上的開端。首先,北島在此復以散文體的形式回到了敘述的原點:「冷戰剛剛結束……我身份可疑 流亡是穿越虛無的沒有終點的旅行——我的一生」。去國後九十年代的遊歷開始被講述(維也納、斯德哥爾摩、奧斯本……),又一次被總結的廿世紀[7]呼應着六月。其次,策蘭〈卡羅那〉的詩句——「是石頭開花的時候了」——既為前九章畫上句點,也遙遙呼應着開篇的籲告:詩比歷史更永久,時代僅是詩的註腳,此刻「是詩歌泄露天機的時候」。
詩人不曾在爭論裏停留,而是沿着自己的思索向前走去,覺察到詩歌中存在着令自己不安的「回聲」。同期完成的〈同謀〉即是反思的明證:「我們不是無辜的/早已和鏡子中的歷史成為/同謀」。這是一份絕對嶄新的宣言:要從時代的幻覺和歷史的催眠中「醒來」,「鑰匙與鎖是敵對的同謀」。
北島在六十歲試寫長詩前九章,七十歲時又捧出了新的九章,可謂「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中有調劑而人不知」[8]。第十章所敘介於四、五兩章之間,時在一九八九年八月,他搭乘陳邁平夫婦的汽車從紐倫堡來到布拉格。這一次蒙太奇由以自擬的對象是卡夫卡:「一八八九年 我出生的房子/毀於大火」;「一九八九年 我們穿過大火/突圍撤退還是逃亡/內與外——東方的智慧/中國長城建造時」。卡夫卡名篇的楔入讓人拍案叫絕。緊接着,敘事銜上了一九九〇年元旦奧斯陸機場的決定,同年五月,關於雜誌復刊的編輯會議在奧斯陸召開。這件事的歷史意義絲毫不亞於一九七八年九月某天傍晚白塔寺東街六十四號的聚會,所以第十二章的鏡頭又轉向了一九七八年的秋天。這是詩體化的《斷章》[9],細節不變:老楊樹下的二鍋頭,屠格涅夫的《羅亭》,鐘鼓樓附近棚戶屋裏播放的古典音樂,沿新街口外大街騎車夜歸,亮馬河出租房中《今天》的誕生。
北島自述「人生階段很清晰」,從出生到二十歲是第一段;從二十歲開始寫詩至四十歲去國離鄉為第二段,「四十歲那年開始漂泊至今」是第三段。[10]「三段論」亦印證於長詩鏡頭的切換。舉例來說,域外經歷首先見諸序曲及前六章,隨後是本土的第七章,緊接着又出現了書寫域外的第九至十一章,然後是本土的第十二章。長詩的寫作大抵以此切換貫穿始終。第十三章「在北歐變幻莫測的天空下」,第十四章前溯至詩人親歷的六十年代,扣上了序曲裏帶有黑格爾味道的天問(「為什麼此刻到遠古/歷史逆向而行」)——「風沿着磨刀石的方向/垂柳順從朕的意志/沿中軸線貫穿四九城」。第十五、十六、十八章,詩人分而向古今中外、哺育過自己的詩人致敬。
在楊立華先生看來,「如果前九章詩人努力尋找的是自我表達的形式,新九章則指向更深層次的自我理解」[11]。確乎如此,但第十七章才是長詩新的開端。這裏的新指向了自我更新,是對個體成長經驗的反觀,重審那些無從迴避的「回聲」問題[12]。某種意義上,自我更新也是在拓深原先的「歷史的為我論」。這一章起始,詩人首先是毫無愧怍地亮出了自己的主張:「反抗流亡反抗土地的邀請……反抗命運反抗我的河床……反抗死亡反抗命運開關……反抗知識反抗輕的塵土……反抗皇權反抗思想人質……」。「1984」與「美麗新世界」重疊的年代,反抗也許不得不復雜化,甚至變成魯迅所說的「橫站」[13],然而「自我更新」的要求並不意味着當以輕浮的知識蛛網覆蓋詩歌的批判性。
這不矛盾:詩人仍然相信一九七三年的宣告「我——不——相——信」(〈告訴你吧,世界〉),他「決不會交出這個夜晚」(〈雨夜〉),也「決不跪在地上」(〈宣告〉),「不祝福,也不祈禱」「不在綠色的淫蕩中/墮落,隨遇而安……表演着被虐待狂的歡樂」(〈走向冬天〉);與此同時,請注意,早在一九八三年以前,他便寫下〈履歷〉,自言宿命是「不得不和歷史作戰/並用刀子與偶像們/結成親眷」。一九八三年是怎樣的年代?一些老詩人仍在呼天喊地地聲言「朦朧詩」乃是一種「精神污染」。〈履歷〉的「結成親眷」顯然意不在此。詩人不曾在爭論裏停留,而是沿着自己的思索向前走去,覺察到詩歌中存在着令自己不安的「回聲」。同期完成的〈同謀〉即是反思的明證:「我們不是無辜的/早已和鏡子中的歷史成為/同謀」。這是一份絕對嶄新的宣言:要從時代的幻覺和歷史的催眠中「醒來」,「鑰匙與鎖是敵對的同謀」。
詩人無須他者為自己的詩藝作證,但他自感有義務敘述這份「友誼」。講述「友誼」,則是為了見證一個精神共同體的存在……這些人因其如出一轍的無家遭遇,如出一轍的對身份尊嚴、自由平等的捍衛和對母語詩藝的忠誠,組成了一個文人共和國。詩歌對他們來說即是「無家可歸者的家園」,是讓他們能夠飛昇於此地而通向彼岸的保證。
第十九章是長詩蒙太奇色彩最濃郁、詩藝最嫺熟的章節,它是北島人生第二段(本土)與第三段(域外)的融合,其間每一節都以具體的時間點寫起:一九三六年夏、一九九二年冬、一九三三年春、一九七一年、二〇一一年五月以及今晚。「一九三六年夏」的主人公是洛爾迦。在《今天》雜誌刊載的版本里,作者為此加註如下:「1936年8月18日凌晨,他在格林納達山腳下被長槍黨人槍殺」。第二段轉入九十年代,詩人驅車前往格林納達祭奠這位西班牙詩人,第三段重回三十年代,主人公是與洛爾迦同時代的中國詩人戴望舒,正是由他最早翻譯出了洛爾迦的詩作。這一段裏,北島還借施蟄存為《洛爾迦詩抄》撰寫的編後記語,為他和這位西班牙詩人的緣分埋下伏筆。伏筆在第四段揭櫫,七十年代的「跑書」運動中即有那本為他鐘愛的《洛爾迦詩抄》,且時至今日仍不能忘情:「洛爾迦/你屬於北京的地下沙龍/隱身煙霧 喝下月光/——群星中的無冕之王」。此處賡續第七章的講述,那些完成黃皮書、如今已經死去的作者,開始在記憶長廊走動。第十九章餘下的兩段交代了兩人未盡的緣分,時間流淌至廿一世紀,詩人來到洛爾迦居住過的馬德里寄宿學院朗誦,在洛爾迦侄女的辦公室,他親手觸摸了詩人留下的鉛筆手稿。
第二十章(「巴黎我的第二故鄉」)重回第四章裏的一句(「更多的加入黑名單」),而洛爾迦章節一閃而過的燕保羅是線索。北島一面邀請當年那些同行者出來和讀者「見面」,或直引其言,或仿其語言:「我是高源 老子就是我」,「我是老木 沒人認識我」,「我是宋琳 而鏡子是空的」,一面細數同他們交往的點滴。此處的化用亦是蒙太奇的變奏,有如向讀者播放一段嘈雜錄音,它使人想起北島在另一處關於金斯堡的回憶:「艾倫很念舊。在紐約他那狹小的公寓裏,他給我放當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凱魯亞克一起喝酒聊天的錄音,臉上露出悲哀。」[14]亦令人回憶起金斯堡的名詩——「我看見這一代最傑出的頭腦被瘋狂毀壞」[15]。北島同樣目睹了類似的悲劇,而寫下是見證。
〈歧路行〉於二〇二一年第三次連載。此前一年,《今天》春季號編發過一組「春之祭——庚子疫詩專輯」,北島並未加入其中。如果說詩人的中風分割了第一次與第二次刊載,那麼從第二十一章起,可以看到詩人對庚子疫情這一嚴峻事實的思考:花冠病毒、訓誡、李文亮、「真相比平反更重要」。又一次「醒來」,卻不再「口中含鹽 / 好似初嘗喜悅」(〈早晨〉),亦沒有自由(「自由失去自由/時間告別時間」),只是剩下「關閉門窗」與「封城的法令」,睡夢裏如同放電影一樣閃過三十餘年的海外奔波,江山渾作夢中看[16]——希臘、地中海、馬略卡島、馬拉喀什、洛杉磯——「醒來 仍在隔離中」。
第二十三章談到了一九九四年回國的遭遇[17],由此引入詩人長久耕作的另一母題,漢字和鄉音。「在漢字中越獄」的說法呼應了此前章節「漢字圍城」[18]「圍城漢字」[19]的表述[20],「鄉音追趕異鄉人」對應第十三章裏的「鏡中有鄉愁的主人」[21]。第二十四章是對〈拉姆安拉〉一詩的補充。二〇〇二年,作為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的成員,詩人前往圍城中的拉姆安拉和加沙走廊,牛津版的〈歧路行〉在此刪去了半句腳註,此行的目的是「支持巴勒斯坦作家」。更具體地說,是聲援被圍困在巴勒斯坦的達爾維什。可是如何理解在上一章剛剛「被中國立即驅除出境」的詩人對達爾維什懷有的深情(「哦達爾維什 你引導我/敲開午夜之門 我的領路人」)?達爾維什是第十六章諸多致敬者之一,《今天》刊發的版本與牛津版略有不同,前一個版本,詩人特意標明他是向「沒有家園的」異鄉人達爾維什致敬,在紀念達爾維什的〈我屬於那兒〉一文,他如是寫道:「正如達爾維什在詩中所說的『我屬於那兒』,『那兒』是人類共同做夢的地方,代表着良知、勇氣和創造力。正因為有了『那兒』,才有了此刻與身份,才有了我們超越現實存在的可能。」[22]也就是說,兩人的交往正是一位早已失去家園的詩人在引領着另一個同此遭遇的詩人,他教導後來者要「穿越虛無的沒有終點的旅行」——要把流亡當作家園。
惟其如此,才能理解為什麼北島會在長詩裏不厭其煩地援引不同國家的詩人。詩人無須他者為自己的詩藝作證,但他自感有義務敘述這份「友誼」。講述「友誼」,則是為了見證一個精神共同體的存在——「為自由獻身」的「羅亭」、一九四七年穿越邊境的策蘭、「永遠的異鄉人」茨維塔耶娃、「挑戰午夜暴君」的「太陽歌手」巴爾蒙特、「為花的暴動而鋃鐺入獄」的巴略霍、「永遠不與權力認同」[23]的布萊頓巴赫、「叛逆的阿多尼斯」[24]、「被高爾基文學院開除/沒有身份證 影子代表自己」的艾基、「在美國流浪」的施耐德、「引導我/敲開午夜之門」的達爾維什。這些人因其如出一轍的無家遭遇,如出一轍的對身份尊嚴、自由平等的捍衛和對母語詩藝的忠誠,組成了一個文人共和國。詩歌對他們來說即是「無家可歸者的家園」[25],是讓他們能夠飛昇於此地而通向彼岸的保證。
設若長詩敘述的中心始終不曾偏離詩人在天涯的行腳和《今天》四十年的源流,那麼日本就是其中一站,一如第三十二章的印度是另外一站。與首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同年舉行的中印作家對話系列,從二〇〇九年持續至二〇一八年。
第二十五章又是一個讀解長詩蒙太奇特色絕好的樣本。如果第十九章的線頭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洛爾迦詩抄》,北島藉此鋪陳了不同時空作者(洛爾迦,1936)、讀者(北島,1992/1971/2011)、譯者(戴望舒,1933)與編者(施蟄存,1956)的冥冥感應,那麼第二十五章就是將時間鎖定在七十年代的某日。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在辦公室自殺,同年,正在建築工地幹活的青年工人趙振開讀到這則新聞,他「為智利哭泣/……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二十四歲呵我的熱血」;下一段仍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病中的聶魯達聞聽阿連德自殺的消息,決意返回智利,同時期的詩人則在建築工地的通鋪上認真地閱讀聶魯達的詩,寫下筆記。回顧往昔,第二十六章中帕斯的評價[26],詩人未必沒有同感,是以才又接連抽掉聶魯達一生詩歌的兩根立柱:「愛情與革命 正如火的描述/熱烈耀眼而轉瞬即逝/愛情——最多會組成家庭/革命——和大衆和權力有關/往往變成暴力與專制」。對聶魯達的改觀和反思詩歌的「回聲」[27]一脈相承。
長詩變幻莫測的時序從第二十六章逐漸恢復正常,詩人顯然清楚,那許許多多個城市和年份,正是並不可靠的記憶長河裏唯一牢固的碼頭,所以他緊緊地抓住了這一點:二〇〇〇年在紐約大學石溪分校英文授課,與楊振寧相遇,他是日後促成詩人回國的重要人物;一九八九年中國作家討論會上和帕斯夫婦的交談;二〇〇七年《今天》聯合哥倫比亞大學和林肯中心籌辦中國獨立電影節;在莫斯科、鹿特丹、哥本哈根、柏林、威斯康星等城市和艾基的相遇。數十年的遊歷或可歸結為兩句詩:其一,「尊嚴比失敗的事業更偉大」;其二,「逃亡 我繞過每一個祖國」。
最是刺穿人心的力量來自第二十八章:二〇〇一年,仍然「匿名」[28]的詩人自八十年代末之後首次回國,敘寫此事的〈黑色地圖〉在我看來亦是北島最好的詩作之一。黑發壯年的遠遊定有苦衷,十三年後歸來(「北京,讓我/跟你所有燈光乾杯/讓我的白發領路」),則是為了償還親情的債務。滄海桑田,「母語讓我更陌生」,童年與青年的光影從兩個世紀與兩個世界的裂縫涌現。父親在等待着北島,曾經的文學「父輩」們也在等候着他——牛漢、蔡其矯、馮亦代、嚴文井。接下來的一句補全了上文兩個細節[29]之間的空白:「午夜 黃銳在門外送客/我正對準北斗七星 / 想想有多少朝代興衰」。
第二十九章與之構成否定性的互文:重回北京,為了探望父親,可北京終究已不再是詩人的家。所以,以駕車在不同公路為線索,海外高校的生活軌跡繼續被勾勒——二〇〇五年夏天的八十號公路(「從戴維斯到薩克拉門託」),二〇〇二年晚秋的五十號公路(「從柏洛伊特到戴維斯」),二〇〇五年的二十號公路,二〇〇六年的九十四號公路(「從芝加哥機場到南彎」),正在學習開車的一九九四年(「從安娜堡到底特律機場」),直至落筆於初次飛回北京的二〇〇一年,他「行進在八十號公路 / 從一一三號公路轉拉索大道」。北島為父親留下名句:「你召喚我成為兒子 / 我追隨你成為父親」(〈給父親〉),關於女兒,則寫道:「華燈溼潤 這是我的家——/ 歷史以外的避難所 / 陪我的女兒長大成人」。兩相對照,親情仍在延續,但北京已不再是故土。
進入第三十章,詩人為交往時間最長的一位外國詩人蓋瑞·施耐德留下篇幅。一九八四年他和艾倫·金斯堡來到北京在竹園賓館和詩人秘密約會,一九九七年因北島被加州大學解聘又為之打抱不平,二〇〇九年兩人共同參加首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以上均是友誼的見證。依舊有蒙太奇的筆法,當時空由域外的千禧年轉換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蓋瑞定居的內華達山林裏土狼「追着長長的信」,在另一個時空,即彷彿是「反精神污染運動(在)追着我」。
可能是源自蓋瑞在日本十二年的修行,北島此刻想到了他的日本友人——安達壯一(詩人的第一位日本朋友)、谷川俊太郎、大岡信、白石壽嘉子、吉增剛造(參加在東京舉辦的《今天》二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日本詩人)、高橋睦郎、財部鳥子(參加在靜岡舉辦的第二屆國際連詩活動的部分日本詩人)、是永駿(北島的日本譯者),誠然,也包括兩位特殊的「友人」,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他們是黃皮書的作者——設若長詩敘述的中心始終不曾偏離詩人在天涯的行腳和《今天》四十年的源流,那麼日本就是其中一站,一如第三十二章的印度是另外一站。與首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同年舉行的中印作家對話系列,從二〇〇九年持續至二〇一八年。詩人提到的印度拉賈斯坦邦的土著民族令我眼前一亮:「吉普賽人 自由的祖先 / 種姓制度中不可接觸的人」。可見詩人的身份認同亦不侷限在文人共和國——「我的影子繼續流浪」,「自由不過是驗證我的名字」。
我希望讀者看到這一點:詩人並未暗示存在一條「正確的路」。「歧路」或為「迷路」或為「迷途」,但嚴格地說,它只是不曾設想與無從預料的道路。
第三十四章細數和香港的緣分:一九八五年,詩人的中篇小說《波動》在香港付梓,這也是北島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新世紀出版社的《北島詩選》與花城出版社的小說集《歸來的陌生人》,均在一年之後);一九八七年,他受邀前往香港參加小說研討會。一九九七年,北島參加第一屆香港國際詩歌節,直到又一個十年過去,詩人從美國移居香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學,也開始籌辦香港國際詩歌之夜。本章的蒙太奇是北島為兩句舊詩賦予了當下性,第一處來自香港作家也斯:「只可惜你戴起了口罩 / 聽不清楚是不是你在說話」(《城市風景》);第二處是對〈太陽城札記〉一字名篇的改寫:「網——人類是魚的祖先 / 正進入大數據的生活 / 手被牽動 心在右舵 / 自由不過是驗證我的名字」。此刻回首四十年,詩人的情緒不免低沉,是的,「這世界並沒有多少改變」(〈給父親〉),人們在「美麗新世界」比在「1984」的世界喪失得更多,多到已經喪失了抗拒幸福的權力;惟當「當病毒和數字王國為鄰」,對自由的禁錮就更為變本加厲:曾經,「流亡者的窗戶對準 / 大海深處放飛的翅膀」(〈毒藥〉),此刻,「窗口面對海灣的全景 / 大歷史升級到單人牢房」。
第三十四章也是〈歧路行〉的終章,香港之於北島,是「我被香港收留」,可香港同樣「不是我旅程的終點」。這理由在第九章已有揭櫫,詩人把寫作視為守夜,把自己的後半生描述為一次始於原點的射線[30],此間唯有「歧路」開始的原點不可忘卻。職是之故,長詩始於此,也訖於此;始於北京:「風在耳邊說,六月 / 六月是張黑名單 / 我提前離席」(〈六月〉),訖於香港:「六四晚會是新的黑名單 / 而活着的都是守夜人 / 燭火呼應 正是缺席的意義」(〈歧路行〉);「起於怒濤般的發問,而終於寬闊而靜緩如大河般的回答」[31]。
但也許這回答並不指向開篇的設問?抑或是這問題原本就沒有答案[32]?問與答預設的是「正確的道路」,即便是後見之明——辯證法的狡計。我希望讀者看到這一點:詩人並未暗示存在一條「正確的路」。「歧路」或為「迷路」或為「迷途」,但嚴格地說,它只是不曾設想與無從預料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這首長詩就是「受僱於一個偉大記憶」者的自我見證,亦是詩人寫給自己的歌——「我是你 歧路的陌生人」。
2022.2.26改定
[1] 特朗斯特羅默語,北島在〈聽風樓記——懷念馮亦代伯伯〉一文有所引用。北島:《青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4-15頁。
[2] 另可參看長詩這一段:「踮着雙腳移動 嚴文井/打開威士忌 燈光紡着暮色/我緊緊摟住樹神的牛漢/觸摸蔡其矯手中的火花/病房解凍 馮亦代露出光腳/在歧路的盡頭喚醒我」。本文除特別標註,引文均來自〈歧路行〉。
[3] 「這個帝國始終保持自立,始終像它以往那樣存在着。以後,它先是在13世紀被成吉思汗、在[歐洲]三十年戰爭之後的時間又被滿洲-韃靼人所佔領,卻從未因此而被改變。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把自己的特性一直保持下來,因此它始終是獨立的帝國。這樣,它就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帝國,只是自身平靜地發展着,從來沒有從外部被摧毀。其古老的原則沒有被任何外來的原則所取代,因此說它是沒有歷史的,所以,我們在談論這個帝國最古老的歷史時,並不是談論他的以往,而是談論它當今的最新形態。」黑格爾:《黑格爾全集》第27卷,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14頁。
[4] 弗羅斯特:《弗羅斯特集:詩全集、散文和戲劇作品》,理查德·普瓦里耶、馬克·理查森編,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3頁。
[5] 筆者這一想法後來在《城門開》一書得到參證,詩人在談到自己的童年閱讀時有云:「我的閱讀興趣剛好相反——自下而上。首先從電影雜誌開始,特別是電影劇本(包括供導演用的工作腳本),大概是由於文字簡單,以對話為主,情節緊湊,畫面感強,那是從小人書到字書的過渡階段。雖說跟着一大堆專業術語——定格、閃回、淡出、長鏡頭、畫外音、搖位推移等,但一點兒都不礙事,就像不識五線譜照樣會唱歌一樣。讀劇本等於免費看電影,甚至比那更強——文字轉換成畫面,想象空間大多了。我後來寫詩多少與此有關。依我看,愛森斯坦關於蒙太奇的探討,與其說是電影理論,不如說是詩歌理論。」北島:《城門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18-119頁。
[6] 〈無題〉(他睜開第三隻眼睛)的最後一句。
[7] 「落日與二十世紀的輓歌 散落的編年史和被劃掉的黑名單」。
[8] 章學誠〈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中語:「人徒見著於書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既經裁取,則貴陶熔變化,人第見誦其辭者之渾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章學誠:《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405頁。
[9] 北島:〈斷章〉,《今天》2008年第4期(總第83期)。
[10] 北島:〈古老的敵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4頁。
[11] 楊立華:〈〈歧路行〉新九章試讀〉,《今天》2019年第1期(總第121期)。
[12] 北島在一次對話中曾談到這一點:「現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會覺得慚愧,我對那類的詩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那時候我們的寫作和革命詩歌關係密切,多是高音調的,用很大的詞,帶有語言的暴力傾向。我們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沒法不受影響,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寫作中反省,設法擺脫那種話語的影響。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是一輩子的事。」翟頔:〈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北島訪談〉,《書城》2003年第2期。
[13] 見〈魯迅致楊霽雲信〉(1934年12月18日)。魯迅:《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頁。
[14] 北島:《藍房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6頁。
[15] 阿倫·金斯堡:〈嚎叫〉,趙毅衡編譯:《美國現代詩選》,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頁。
[16] 王英孫〈題高房山夜山圖〉中的一句。
[17] 另可參看〈創造〉:「一個被國家辭退的人/穿過昏熱的午睡/來到海灘,潛入水底」;〈舊地〉:「此刻我從窗口/看見我年輕時的落日/故地重遊/我急於說出真相/可是天黑前/又能說出什麼」。
[18] 「雲的思想成為一顆流星/照亮那大地的瞬間——/兵書落雪 漢字圍城」。
[19] 「從圍城漢字到放射形廣場/記住了丁香的呼吸」。
[20] 第二章也有類似說法:「在漢字的陷阱突圍/地下格柵外也是監獄」。
[21] 這個說法來自1989與1990年之間創作的〈鄉音〉:「我對着鏡子說中文/……/祖國是一種鄉音/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聽見了我的恐懼」。
[22] 北島:〈我屬於那兒〉,《今天》2017年第3期(總第115期)。
[23] 這個表述來自《今天》雜誌刊發的版本:「向牆中的布萊頓巴赫致敬/你釋放的瘋狂/是鑄造寂靜的真理/永遠不與權力認同的人/我追着他的影子逃跑/每天早上 盧森堡公園/他光着腳小跑——哭泣/來自權力迷宮的高牆/一朵白雲在山頭追問寂靜」。
[24] 這個表述來自《今天》雜誌刊發的版本:「向叛逆的阿多尼斯致敬/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從童年貧窮的地平線/看權力之夜信號彈上升/代替那些隕落的星星/永恆——火與火之間的深淵/在父親的蘇菲血液中/君臨廢墟的宗教與禁忌/我的詞語是撼動生命的風」。
[25] 北島:〈我屬於那兒〉,《今天》2017年第3期(總第115期)。
[26] 「關於聶魯達 帕斯搖搖頭/僭越了政治與道德的準則」。
[27] 「空行——請等等/上個世紀如隔岸觀火/回放的是摺疊時刻——/狂風正掙脫門框/閃電的鞭梢抽打鬃毛/軛下是奔流的土地/門牙嘶嘶吐出革命/我腎上腺素急升/戰歌加上抒情的翅膀/這是十七歲的戰爭/用耳朵吹響號角」。
[28] 「我被匿名 獵人也沒有名字」,這句詩反向解釋了「是時代匿名的時候了」的意思。
[29] 「在那棵老楊樹的蔭庇下/黃銳、芒克和我/半瓶二鍋頭半瓶暗夜/酒精照亮綠色膽汁/為暗夜掌燈共同擊掌/聽太陽穴的鼓手」;「沿新街口外大街騎車/在流水中刻下的青春:/我們倆互取筆名/猴子搖身一變——/他是芒克 我是/被大海浸蝕的島」。
[30] 「冷戰剛剛結束……我身份可疑 流亡是穿越虛無的沒有終點的旅行——我的一生」。
[31] 這句話引自作家阿乙為〈歧路行〉撰寫的短評。
[32] 「逝去的逝去的是無窮的追問/返回的沒有聲響」。
延伸閱讀:
| 閱讀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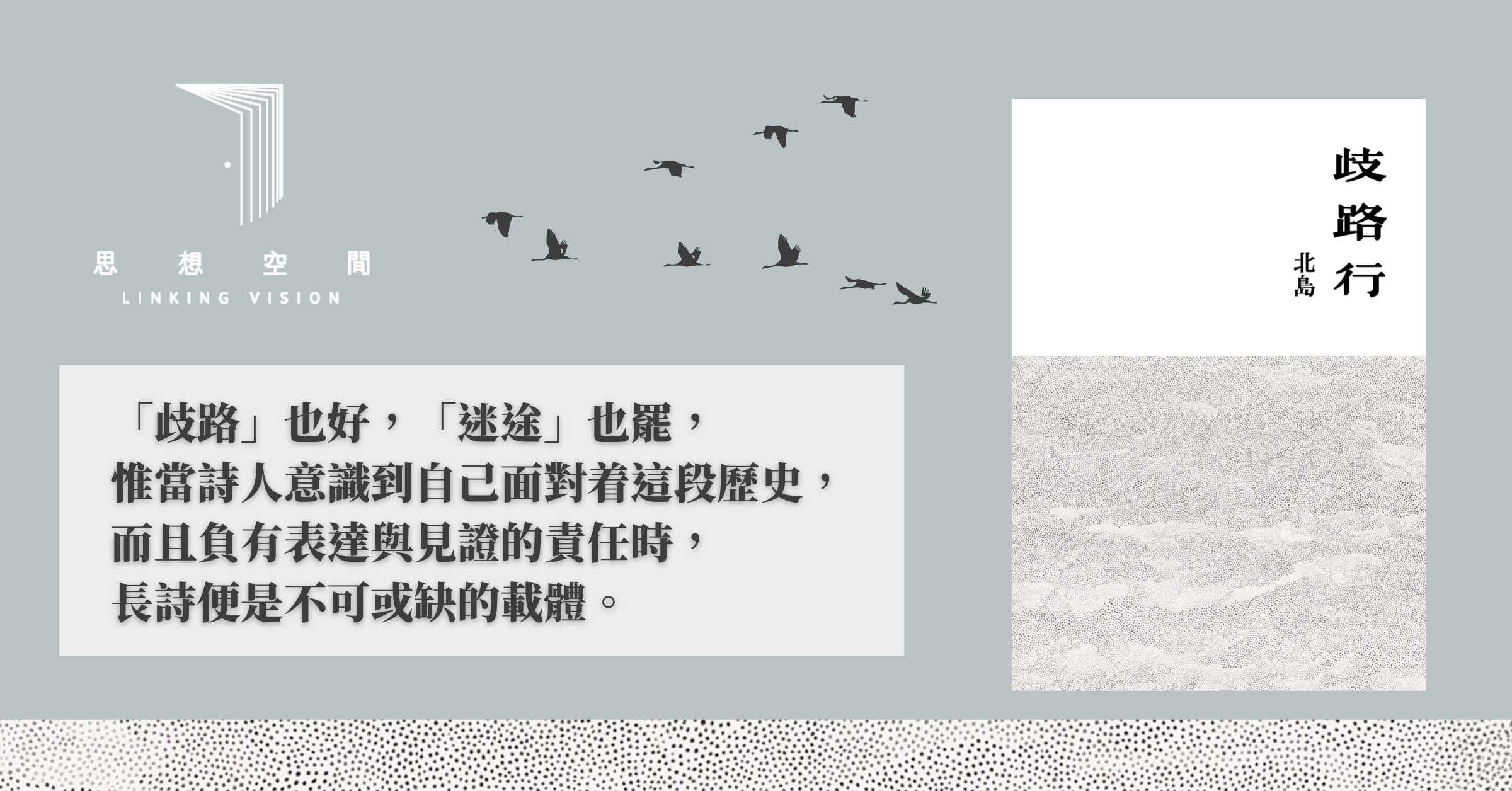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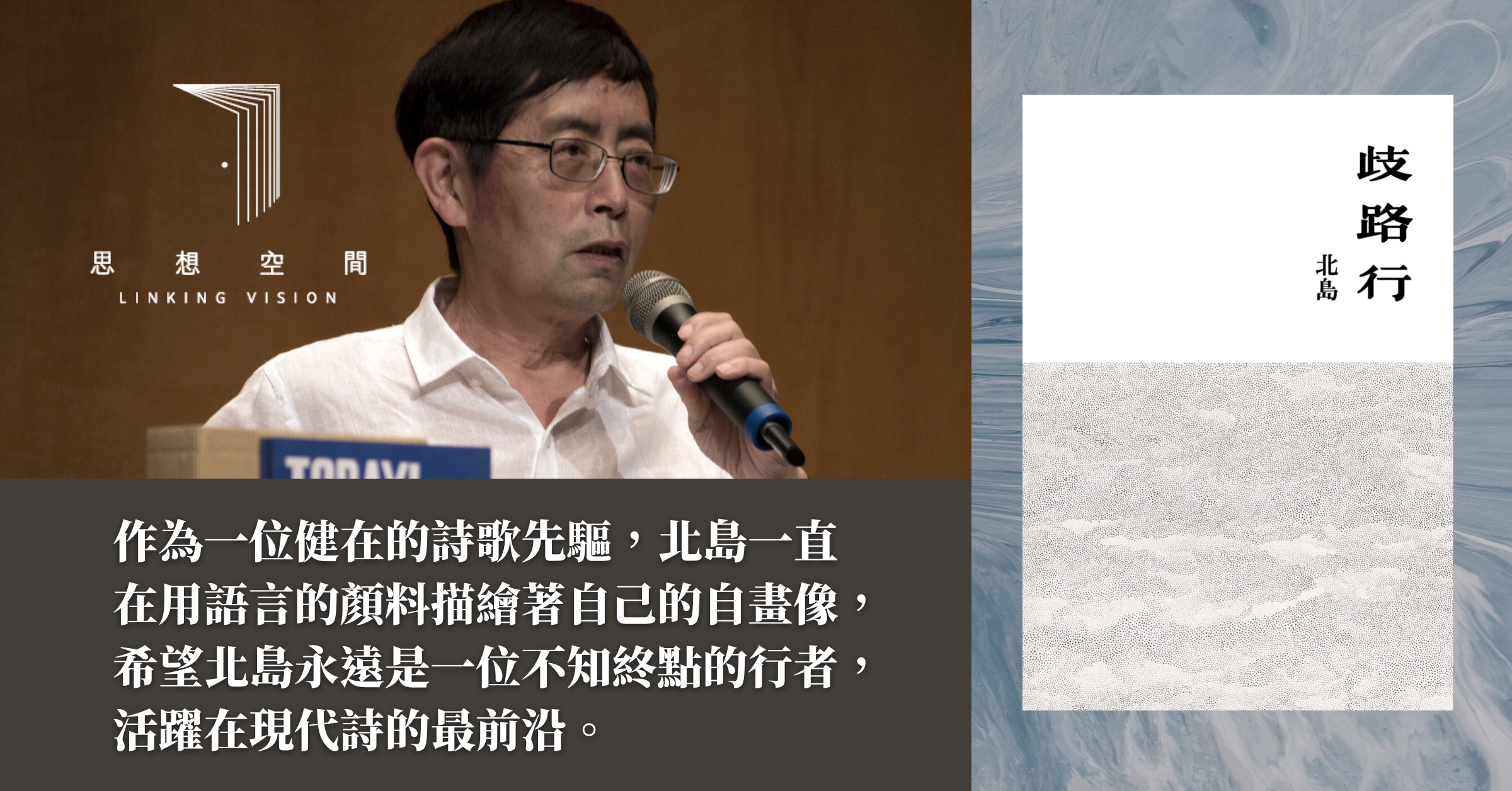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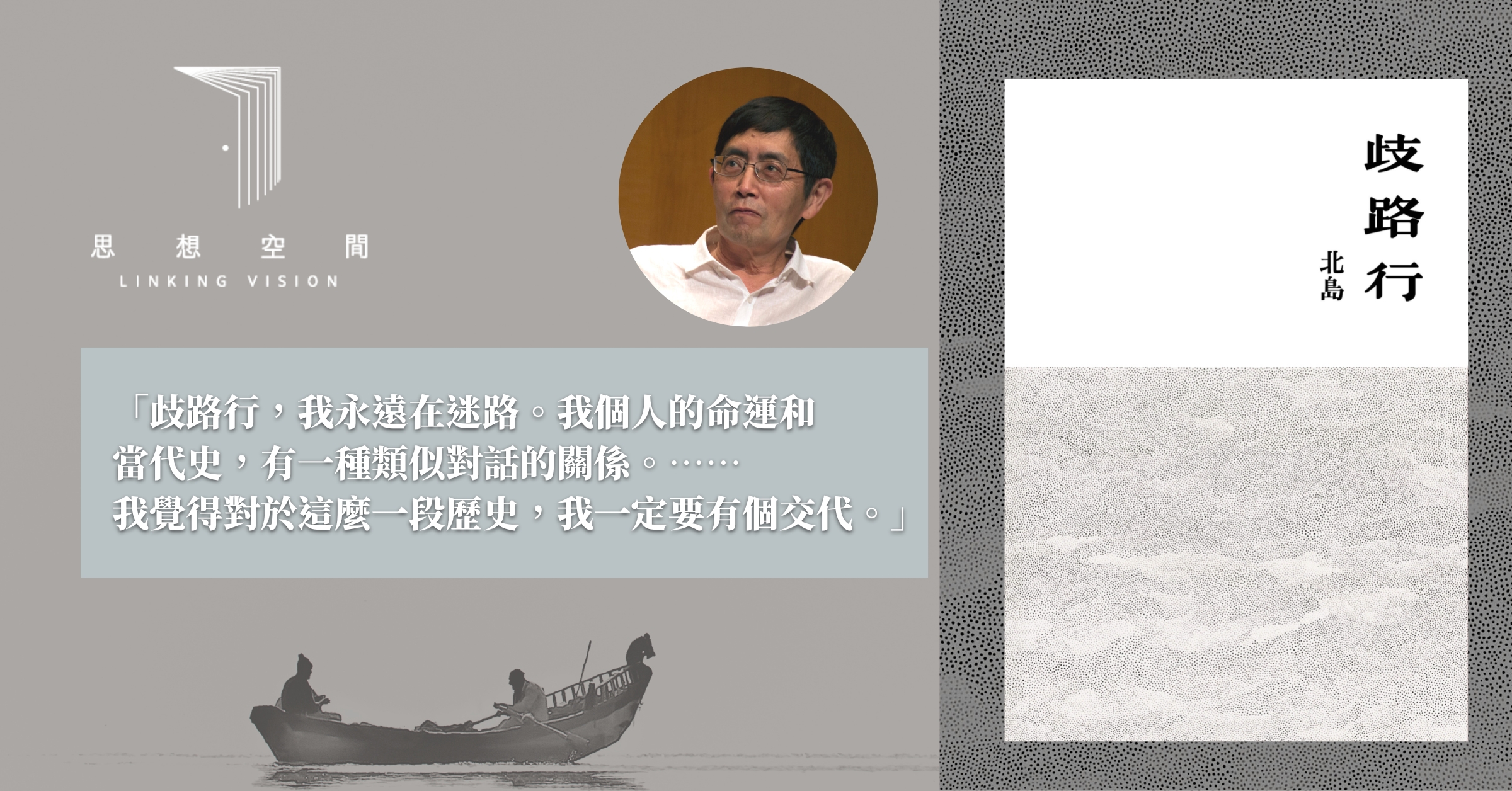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