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胡詩專
編按:本文轉載自《人社東華》第36期,原題為「人與人與文學的真誠對話:顏崑陽教授《中國詩用學》新書發表暨學術座談側記」,此標題為編者所擬。此文記錄了《中國詩用學: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行為詩學》作者顏崑陽於2022 年 10 月 27 日在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學院的新書發表會內容。發表會原標題為「中國古代詩歌的『社會性』與『藝術性』」,當日主持人為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吳冠宏,而除了發表人顏崑陽外,參與與談的還有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孔子博物館榮譽館長兼國立東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龔鵬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臺灣中文學會常務理事梅家玲,以及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王欣慧。
繼 2020 年的《學術突圍》,顏崑陽教授「又」出新書了。2022 年 10 月,由聯經出版《中國詩用學: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行為詩學》,這是顏教授近幾年來的第五本系統性理論專著。顏教授說:「我這二三十年來,一直努力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改變「五四」以來,挪借西方「純文學」觀念,以詮釋中國古典詩學的那種知識型。」
中文學界不少學者習於挪借一些與中國古典詩學不相應的西方理論,用來批評中國古典詩。如此一來,就讓整個中國古典詩學,完全喪失掉它應該有的民族文化以及區域社會性。顏教授說:「科學可以無國界,但是文化一定有國界、社會一定有國界,不可能全世界都一樣。研究中國古典詩,如何能夠把它真正的特質顯發出來,而不只是消費西方理論。這樣才能把中國古典詩的研究做好。所以,我就想要去改變近現代學術史,這個工程當然非常浩大,花了我二三十年的時間,連續出了五本書。研究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學,一定要回到它歷史文化的語境中,深入理解。」
顏教授特別以〈壬寅仲秋龔鵬程教授久遊神州忽爾歸來予設宴邀飲 林安梧吳冠宏彭衍綸諸教授同席盡歡〉這首詩的手稿做為開場,並現身說法,實際呈現古典詩之美(藝術性)與朋友之間交往的社會行為(社會性)一體不分。展現中國詩歌,如何「用」在人際之間的互動關係。人格美、秩序美才是中國詩歌之美的精華。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性」與「社會性」並非截然為二。顏教授說:「老龔雖然自投羅網,出席我兩場新書發表會,擔任主談人。老朋友之間,還是要感謝,所以我就親自下廚,燒了幾道菜,當中有我最拿手的炒米粉,宴請老龔,並邀安梧、冠宏、衍綸作陪。」
〈壬寅仲秋龔鵬程教授久遊神州忽爾歸來予設宴邀飲 林安梧吳冠宏彭衍綸諸教授同席盡歡〉
老龔忽爾遠遊歸,烈日經天更晚暉;對酒談文論霸業,臨秋橫氣看花飛;
鯤從北海因鵬化,士作南金與世違;快得諸君共嘉宴,青雲散後掩寒扉。
——顏崑陽
朋友之間的交往,就是社會行為。「將『為藝術而藝術』與『為人生而藝術』截然二分,這是濺染西學之唾沫。」離開人生,沒有文學,每一個詩人,都是活在他的社會文化情境當中;作詩,必然也在他的社會文化情境中作詩。所以,文學的藝術性、社會性,兩者連在一起,無法截斷,分開討論。
這次座談主題是:「中國古代詩歌的『社會性』與『藝術性』」。顏教授以手稿詩作證明:中國古代的詩人之間,就是這樣來往。我們閱讀這首詩時,彷彿回到唐宋,或在蘇東坡與黃山谷之間,或在杜甫和李白之間,他們都是以詩相互來往。
這次盛會由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吳冠宏院長主持。除了顏教授發表新書之外,更邀請臺灣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創校校長,現任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孔子博物館榮譽館長、東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龔鵬程;臺灣中文學會常務理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梅家玲;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王欣慧。這三位學者主談重要學術議題:〈中國古代詩歌的「社會性」與「藝術性」〉,針對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意義,發表真知灼見。這是一場轉變近現代中國古典詩學史的關鍵性盛會,預期影響深遠。
「龔鵬程離開台灣已經有二十年左右,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不久之前,我正在籌備新書發表會,他自投羅網,自己打電話來說:『崑陽,我現在回來了。』哦!你回來得正好!我兩場新書發表會,你都要出席。」
——顏崑陽
座談首先由中文系主任彭衍綸教授進行承辦工作彙報。彭主任為了尋找適合場地,走遍校園,勘查各類型空間,最後選定藝術學院最嶄新的階梯教室;並挑選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辦公室裡,風格典雅的明式家具,做為主持人、新書發表人、主談人的雅座;可謂是現代與古典的完美結合,將座談的空間佈置為劇院模式,讓大家感受到有別於一般座談的氛圍,舒朗而優雅。
吳冠宏院長風趣的說:「一般新書分享會,很難辦到這樣大規模,大多是小而美;但是只要放到顏老師身上,活動自然就會變得很大氣。」吳院長認為:「這像是詩用學的開展,它絕對不只是文學人自己的對話,而是開展到與媒體應用、各個面向的連結。正呼應顏老師『有破有立』的學術精神。」從《學術突圍》的「破」開始,漸漸展現「立」的典範,《中國詩用學》就是非常重要的環節之一,往後還會有文體學、原生性文學史觀等等,這是非常可觀且令人佩服的學術能量!並且能不受限於學術框架,而自成一格。這樣的延續性開創,著實令學子們非常感動。
龔鵬程教授說:「我跟崑陽的交情就不用再敘述了。我們年輕時就認識,經常一起論學,爭辯到火花四射,卻是越辯越愉快。今天這個題目,讓人有很多話想說。因為,崑陽這本書,它不是一本孤立的書,它是前面《詩比興系論》、《學術突圍》這些具有連貫性的相關著作。」
「我們希望能夠創造一個新的時代,可是目前環繞在我們周邊,還是一堆烏雲;『五四』的知識型態,其實就像烏雲瀰漫在我們身邊。『五四』雖然已經過一百年了,感覺距離很遠,但它的影響力還在。
針對五四的時代情境與知識型態,龔教授指出:「我們希望能夠創造一個新的時代,可是目前環繞在我們周邊,還是一堆烏雲;『五四』的知識型態,其實就像烏雲瀰漫在我們身邊。『五四』雖然已經過一百年了,感覺距離很遠,但它的影響力還在,例如:我們今天這個演講廳,是屬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怎麼會有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呢?我們這裡又不談科學;但是我們把『科學』泛化了。其實,我們從來沒有建立什麼科學,只建立了科學主義;所以人文學、社會學的科系,都納在科學的框架裡。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都是科學,設立這些科系的學院就稱『社會科學學院』。大陸也是這樣,郭沫若之後,就分出了「人文社會科學院」。這種科學主義的知識,就是「五四」的知識型態,它並沒有走遠,一直在我們社會中,產生具體的作用。這種『科學主義』,怎麼能行呢?理論上是行不通的。」
龔鵬程教授指出:「顏教授這本書,就是要挑戰我們對文學的基本認知。『社會性』與『藝術性』就是文學的本質、詩歌的本質。」這本新書就是以此為發端,論述五四知識型態的特質以及它的局限。龔教授還指出:「『社會性』與『藝術性』是就學理上說;但五四時期,認為詩只有藝術性,而沒有社會性,並不是針對學理說。五四時期雖主張純文學,但其實並沒有純文學,而是背後的政治性操作:包庇同黨、假造學歷等等這些行為,都很惡劣。我們現在不也是在延續這種包庇同黨、假造學歷的傳統嗎!這就是五四的餘孽啊!我們藉《中國詩用學》這本書,不僅要打破那些觀念,更重要的是『反省』我們這個時代,如果經由這本書,能起到『反省』作用,我想這本書的影響不會只有在文學研究上。」
梅家玲教授對古典與現代文學的研究,都非常專精。她的《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正是文學社會學向度的開拓。梅教授說:「我深深的感受到,從先秦以來,賦詩言志,一路到漢魏六朝以降的擬作、代言與贈答之作,與其說是純粹抒發個人心靈的純文學之作,不如說是在社會文化情境之下,因為實際的政教或私人往來有需要,因此才應運而生的一批詩與賦。要研究這些作品,不可能只有純文學的角度,而必須要納入社會性的考量。」
梅教授針對今天的主題提出:「『藝術性』跟『社會性』,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思考這兩者中間的關聯?我想,在這裡面,不管是談藝術性也好,社會性也好。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連結點,就是寫詩當下的『自我』,『我』要如何寫詩?『我』為什麼要寫詩?這個『我』又是如何形成?放在整個社會情境的脈絡當中,如果我們參照所謂社會學家的說法,就會發現,其實社會學家他們所看到、所強調的就是:他們認為所謂的『我』,本來就是在互相交流跟聯繫當中發展起來的。例如:顏老師也曾經引述到的社會學家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他曾經有過下面這些論述:我們大概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面向去把握,第一個是從回憶來說,如果你試圖回憶一種感情,你必然會發現,如果沒有引起這種感情的人的形象出現,你是不可能回憶起什麼樣的感情。如果你思念一個人,會發現你的意識裡,其實主要是圍繞著他的形象情感。也就是說,所謂的情感,所謂的回憶,其實都是跟「人」扣連在一起。除了『我』之外的他人,我跟他之間,一定要有一些相互的聯繫,彼此才能有進一步的回憶、思念,以及後續的文學書寫。」
其實自古以來,中國文學之所以產生,與社會性、應用性有關。可是,難道它只有應用嗎?這個應用的藝術性,又從哪裡產生?在應用的當中,這個個人的「我」(主體),又在哪裡?
另外,庫利還提到:「與他人的聯繫」其實還有一種「想像」的形式,這個想像的形式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把它放在贈答,以及扣連到剛才顏老師寫的這首詩上面,我們會發現,在寫詩者,特別是寫贈詩的這個作者來說;他在落筆作詩的時候,其實心裡面不但有一個他想要傾吐的對象;甚至於他,原先就預期對方,應該是要有所回應;而他當下的書寫,其實就已經是為了因應接下來對方的回應,而開始落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所謂的「自我」,他,其實就是透過一種想像的形式,出現在他人的意識當中;而且這種自我的感覺,決定於個人對於這個形式的態度,而這個態度乃是受到他人意識的影響。
庫利的意思是說,我們對於「自我」的形塑,絕對不是憑空而生,而是憑藉著:他一定要有一個對象、有一個「他」,然後才能夠形成所謂的「我」;唯有在人際往還、交通的過程當中,所謂的「自我」、所謂的「對方」,才能夠面目清晰;人,也才有可能更加的認識自己。這個是從「跟他人往還」方面去談,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面向,就是「語言」,因為語言本來就是社會的產物。
庫利提到:普通語言當中的「我」,本來就有「聯繫他人」的意義,他從該語詞,以及其後所代表的意義,能夠反映語言和交流、生活的現象這個事實,就是證明。在沒有或多或少、明確的想到別人的情況之下,是否「有可能運用語言」是值得懷疑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他人」存在的話,這個語言有沒有必要,這是值得懷疑的。有了語言,其實就是因為要有一個溝通、聯繫、對話的對象。
庫利又說:「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命名的事物,以及在我們的反思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物,幾乎都是通過我們和其他的人交流,而留在我們的意識中的;沒有交流事物,就不可能有名稱,人類就沒有發展的思維活動。我們所說的「我」,或者是「我的」,或者是「我自己」,並不是獨立於普遍生活之外的某種東西。」
從這幾個面向來看,人類的所有的活動,都有它的社會性;而且,由此而產生的種種文學更是如此。在這樣的理解之下,梅老師針對〈壬寅仲秋龔鵬程教授久遊神州忽爾歸來予設宴邀飲林安梧吳冠宏彭衍綸諸教授同席盡歡〉這首詩說:顏老師寫這首詩,很明顯的就是跟龔老師有關,也會希望能夠得到龔老師的回應。在這個理念,詩的「社會性」跟「藝術性」兩者具有相互關係,不是截然二分。我想,顏老師的意思是說,過去因為五四以來,我們受到西方知識的影響,以至於太偏向討論文學的藝術性。其實自古以來,中國文學之所以產生,與社會性、應用性有關。可是,難道它只有應用嗎?這個應用的藝術性,又從哪裡產生?在應用的當中,這個個人的「我」(主體),又在哪裡?
我覺得,從剛才顏老師送給龔老師這首詩,在整個詩作的行為當中,也許可以看到所謂的「藝術性」跟「社會性」,他們相互辯證交流的狀況。當顏老師要寫這首詩,而且這首詩是要送給龔老師,當時心裡一定是對龔老師有些想像、有些情懷要傾吐;於是他在詩裡面,展現了一個文字背後的自我形象,然後他也想像了龔老師的形象;接著他就透過這首詩作了表述,而這首詩作本身,是在整個文學傳統裡面,一脈相承,從魏晉六朝一路下來的。所以他的整個書寫,必然也就是受到這個文學傳統某一些啟發,或者規範。所以他必然也有一個外在的,除了人與人之間,還有跟文學傳統之間的對話。如果龔老師,讀了這首詩之後,也希望給顏老師一些回應的話,他首先,必然要接收顏老師的詩裡面所有的訊息,所有的情思,甚至於他在閱讀這首詩的時候,等於也主動的參與、分享了顏老師的心靈世界。在這裡,因為有了社會性相互的融滲,使得兩者之間有了對話,進一步交流,以及彼此了解的可能;而當龔老師如果再要落筆為詩,予以回應的話,他或許會根據顏老師詩作裡面所談的種種,有一些回應、對答。」
梅教授最後總結說:「我們讀顏老師的這部書,應該要有更多的,不只是思考,恐怕還要有一些『自我期許』;怎麼樣可以在這方面努力,能夠達到顏老師在書裡面所體到的,讓我們整個社會文化,都還是一個『用詩』的文化,這個『用詩』的文化背後是,每一個人都有『人文化成』這方面的教養。」
王欣慧主任除了有詩方面的研究,還有許多文學理論也串連在其研究脈絡中。王主任認為今天的盛會,彷彿是顏老師親自帶領、參與了一場所謂「士人的社會文化行為」,並分享許多重要的觀點,王主任說:「顏老師這本書《中國詩用學: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行為詩學》最主要的寫作宗旨是:五四以降,新知識分子追求現代化而反傳統,卻沒有能力對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詮釋,並經由『內造建構』,轉而做為中國古代人文學研究的基礎知識。所以,顏老師認為:百年來的中國古代人文學,其實已經淪為西學的殖民地,而且是自我殖民;我們應該要對百年來的學術思維進行突破。」
王主任歸納:「反思,是重要的關鍵詞。我們可以看到顏老師從『反思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一直到『反思五四知識型』。顏老師似乎不斷在『反思』」;因此,王主任提出:「什麼是『反思』?」並且提出對於「反思」的見解。
王主任認為:「『反思』是不媚俗、不跟風、不盲從、不安於現狀,而且必須要有好奇與質疑,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氣』。做學問必須如此,要有勇氣去質疑舊典範,挑戰前人,才能形成自己的問題意識;而有膽量對既有的論述進行批判,以形成新典範。」《中國詩用學》即是反思批判後而形成的中國古典詩學新典範。」
王主任提出:「如果把『五四知識型』當成你要對付的敵人,我應該要拿什麼武器來對付它呢?」王主任認為:「顏老師選擇了春秋至漢代讀者所建構的知識型。這樣的方式、進路,確實是可以將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從西方的新批評,就是為了實現某一個目的,而必須依循的普遍有效性的行動規則,一種可以實踐操作的技術性規則,拉回到中國文化體質所孕生的批評方式;就是藉由文學作品而得到個體生命的相互通感與關照,去建構一個跟西方詩學不一樣的詩用學。」
王主任的專長是詞賦,當中也涉及到先秦兩漢。所以更進一步提出:「在早期,儒家對於詩的說法,難道只有『主體通感』嗎?例如:毛傳把《詩經》三百零五篇詩裡頭的一百一十六篇,在發端處標舉出『興也』,又多用一些『若』、『如』、『猶』等字詞去解釋興詩中的詩句。在毛傳裡面,似乎也是把『興』當成是詩三百的表現手法。到了朱熹,更說賦比興是作詩的骨子,無詩不有,直指賦比興是《詩經》的三種創作方法。除了標註賦比興之外,朱熹還標註了賦而興、賦而比、比而興、興而賦、興而比這樣的名目。難道,從毛詩到朱熹的傳註,這不能算是一種語言形式或是修辭技巧的批評嗎?如果不去談『興』的用,純粹單就毛傳跟朱熹的註來看的話,它不能算是一個鎖定在文意上、文學上,對儒家典籍的語言形式跟修辭技巧的批評嗎?在這裡,我想向顏老師提出一個問題:「『詩用學』究竟是中國固有的詩用學?還是顏老師建構的中國詩用學?」
顏教授回應說:「鵬程跟梅家玲教授沒有直接提出問題,倒是欣慧最後單刀直入,提出問題。但是問題相當複雜,我的總體回應是:那些問題,假如把我近幾年的五本書,延續性的閱讀,大概都可以得到解答。就一個學者來講,他雖然分了五本書去寫,每一本書解決的是一些個別不同面向的問題;但是,把它總體合起來,很多問題都是相關的。例如,毛傳在《詩經》一百一十六篇的某些句子下面標註『興也』。欣慧說,難道這個跟修辭技巧沒有關係嗎?我認為,從鄭玄之後,對毛傳都是誤讀,因為孔子講『詩可以興』是從讀者的『閱讀效果』講。孔子那個時代,沒有『創作詩』的問題,跟修辭技巧也沒有關係,他只是帶著學生讀這三百篇,告訴學生:讀詩,要能夠從詩當中去興發你的志意。朱熹解得很好,『興者,感發志意』。或者,王夫之的《薑齋詩話.詩繹》裡講得更好:『可以者,隨所以而皆可』、『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孔子在他那個時代讀詩,非常自由,沒有什麼客觀唯一的答案。他的重要就是:讀者如何能夠透過詩的閱讀而對內在的情感、志氣、甚至於整個人生觀、宇宙觀,能夠達到啟發的效果。因此,『作詩』的語言技巧,在孔子那個時代,完全不是問題。毛傳就是繼承孔子『詩可以興』的本意,在那些標示『興』的地方,有些有解釋,有些完全沒有解釋,只是『興也』,指引讀者自己去感發。漢代解經,其實是『通經致用』,關係到整個國家、政治的問題,如何去改革;從「經」當中如何找到政治或人生的答案。因此毛傳標示『興也』,是在提醒帝王、士大夫的讀者們,讀到這個地方,要好好『興』一下,應該會給你啟發;啟發是自由興感,各有心得,這就是『詩用』,不只是語言層次的修辭技巧而已。我所建構的『中國詩用學』當然也就是中國固有的詩用學,只是我用現代話語把它做了創造性、系統性的重構。」
座談尾聲,龔教授特別集歐陽永叔石屏句「歲月裁如熟羊胛,功名未必勝鱸魚」,灑墨揮毫相贈,以回報顏教授的贈詩,最為此次盛會讓人欣羨的雅事,活現了文人的「詩用」行為。
這本《中國詩用學》指出,「五四」以降,很多學者挪借西方「純粹審美」觀念,用以批評中國古代詩歌,造成古典詩學詮釋視域的迷蔽;中國古代詩歌的民族「文化性」與「社會性」完全被剔除。顏教授乃全面反思批判,回歸中國古代文化與文學情境,博學深思,費時二十餘年,終而「內造建構」系統性的理論「中國詩用學」;揭明「詩」是中國古代士人階層社會文化行為的特殊語言形式,因而提出近現代中國古典詩學的詮釋視域,面臨二十一世紀,必須創造性的轉向,以促成典範的遷移。假如中國的人文學術想要在世界化的平台上,與西方平等對話,而不是西方的文化殖民地;則我們整個文化、學術的主體性,必須凸顯出來。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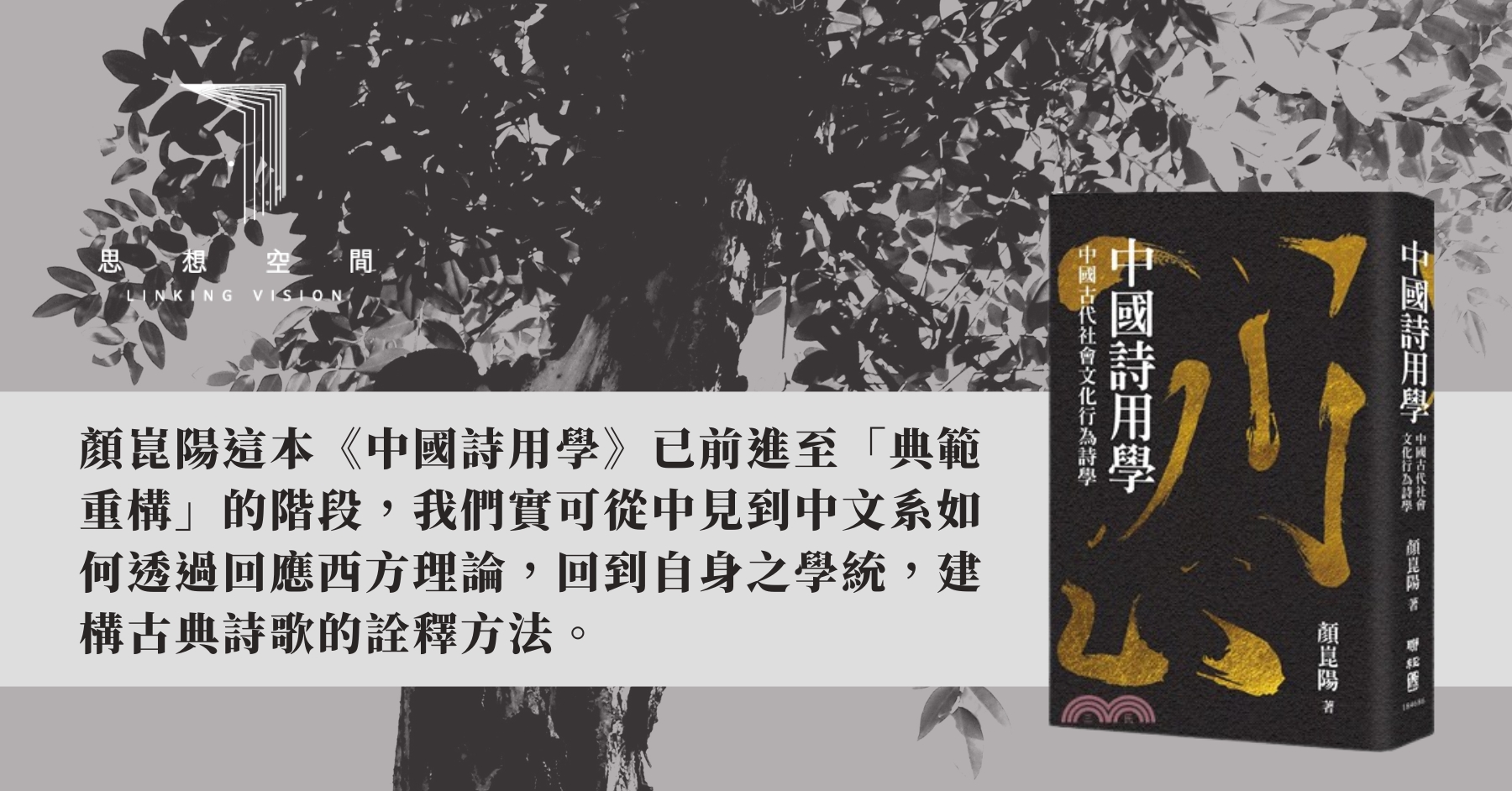
學術突圍與生命情調——顏崑陽與《中國詩用學》

陳國球:圓球體的反思視域——《中國詩用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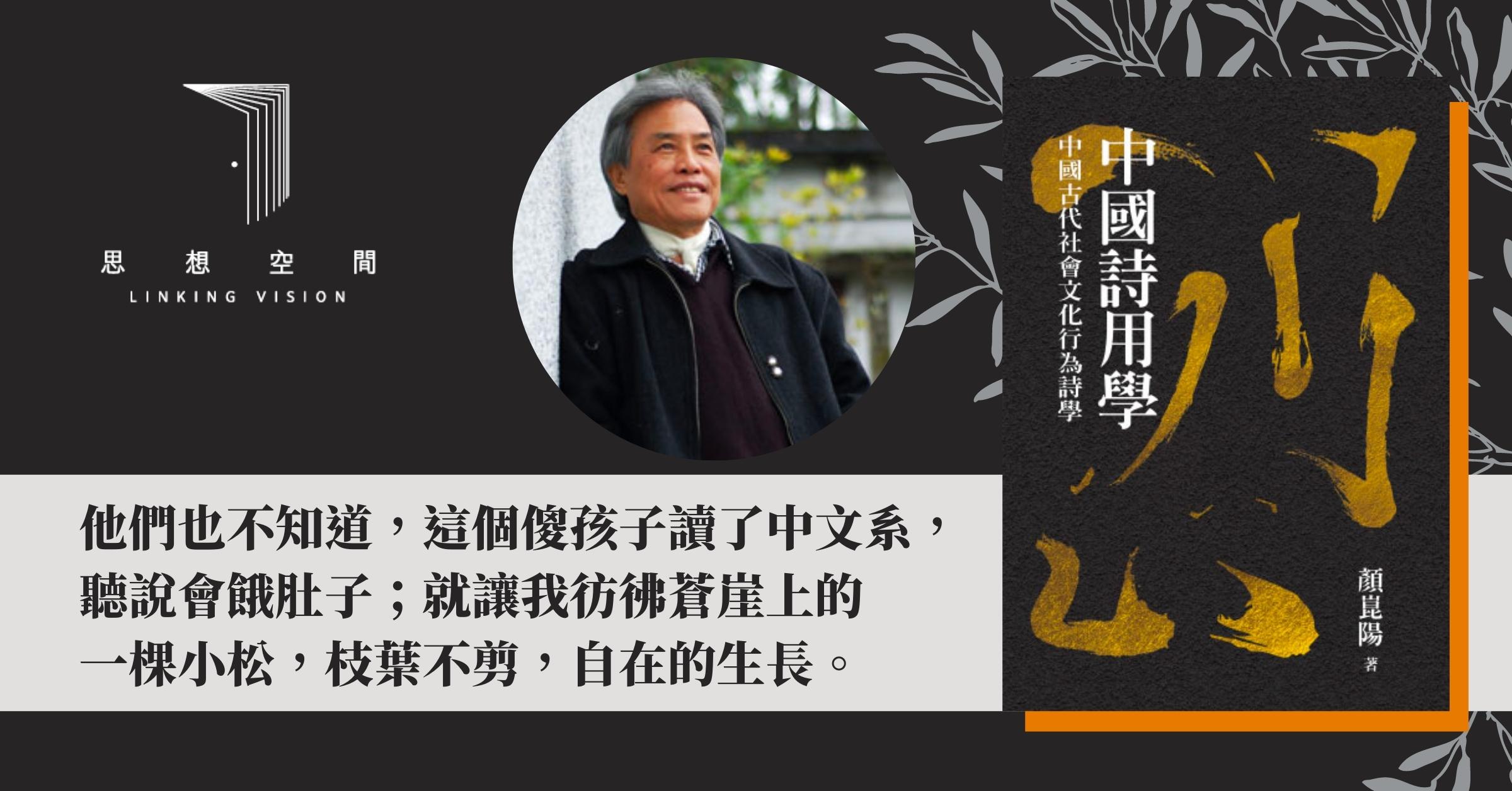
顏崑陽:我,因詩而存在!
| 閱讀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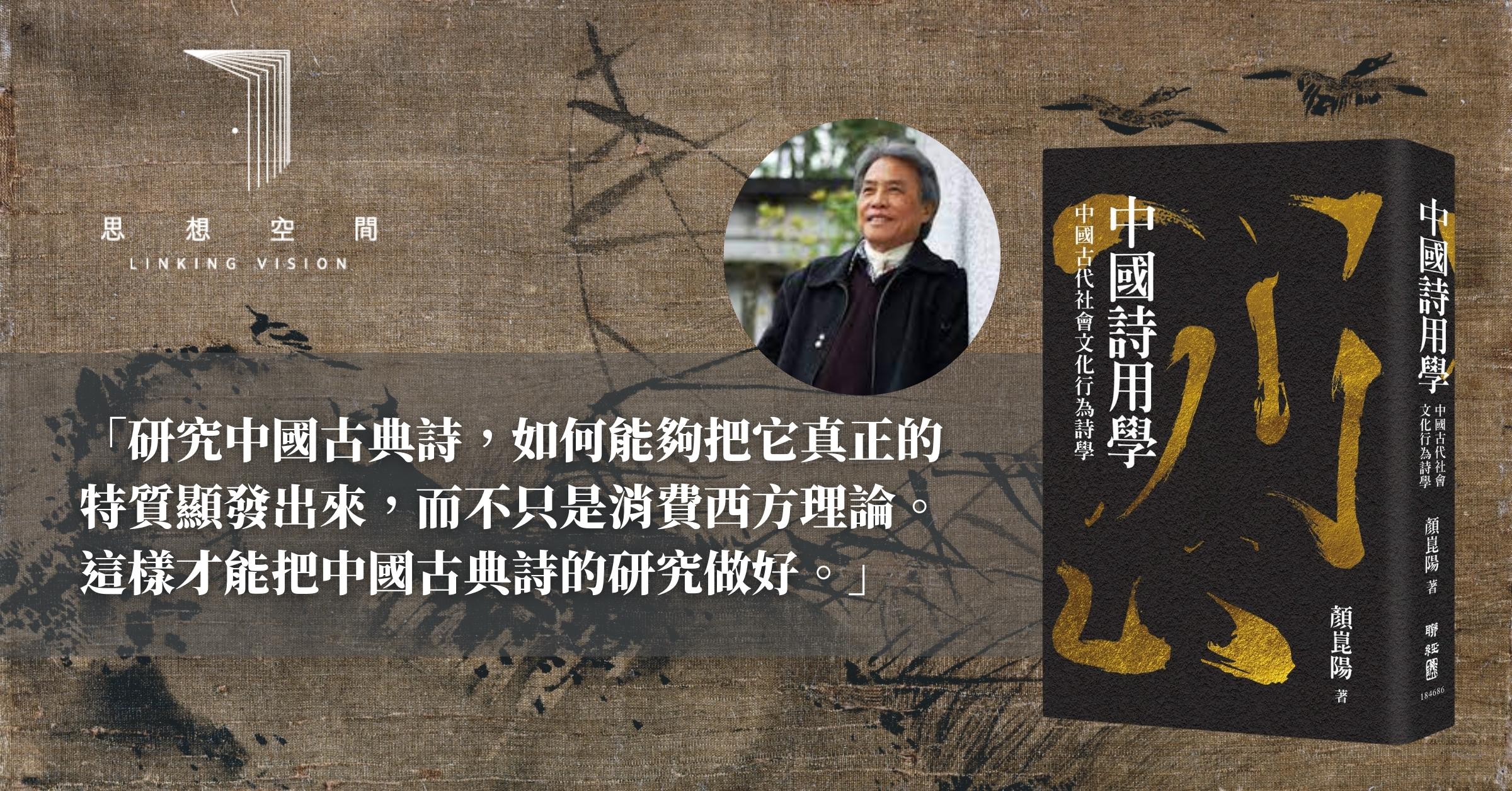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