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國清(文學翻譯家)
編按:既是艾略特文學理論的研究學者、翻譯家,同時也是詩人的杜國清譯詩,深刻挖掘艾略特對歷史意識的承載、古典傳統的經營、詩之本質的探究,在字句意義的傳達之外,兼重其語言、詩意、節奏和音樂性之重現及再創造,並針對冰山之下龐大的隱喻、象徵、典故、哲學、現世、宗教等深奧概念的思索與探尋,同時輔以譯註與解說,如同踏入艾略特曲折紛繁之思想世界的路標。(* 本文摘選自《艾略特詩選:〈荒原〉、〈四重奏〉及其他觀察》)
原詩:
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Winter kept us warm, covering
Earth in forgetful snow, feeding
A little life with dried tubers.
原詩:
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Winter kept us warm, covering
Earth in forgetful snow, feeding
A little life with dried tubers.
趙(蘿蕤)譯:
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荒地上
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欲望
參合在一起,又讓春雨
催促那些遲鈍的根芽。
冬天使我們溫暖,大地
給助人遺忘的雪覆蓋著,又叫
枯乾的球根提供少許生命。
葉(維廉)譯: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逬生長
紫丁香,從死沉沉的地上,雜混著
記憶和欲望,鼓動著
呆鈍的根鬚,以春天的雨絲。
冬天令我們溫暖,覆隱著
大地,在善忘的雪花中,滋潤著
一點點生命,在乾的塊莖裡。
杜(國清)譯:
四月最是殘酷的季節
讓死寂的土原逬出紫丁香
摻雜著追憶與欲情
以春雨撩撥萎頓的根莖。
冬天令人溫暖,將大地
覆蓋著遺忘的雪泥
讓枯乾的球根滋養短暫的生命。
查(良錚)譯:
四月最殘忍,從死了的
土地滋生丁香,混雜著
回憶和欲望,讓春雨
挑動著呆鈍的根。
冬天保我們溫暖,把大地
埋在忘懷的雪裡,使乾了的
球莖得一點點生命。
趙毅衡譯: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在死地上
養育出丁香,擾混了
回憶和欲望,用春雨
驚醒遲鈍的根。
冬天使我們溫暖,用健忘的雪
把大地覆蓋,用乾癟的根莖
餵養微弱的生命。
李(俊清)譯:
四月這殘酷的季節,滋育
紫丁香於乾旱土地上,混合
記憶和希望,一陣春雨
擾亂半死根莖的平靜。
寒冬卻令人溫暖,飄灑
忘憂之雪掩飾險巇,而以
乾球根飼育少許的生氣。
裘(小龍)譯:
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哺育著
丁香,在死去的土地裡,混合著
記憶和欲望,撥動著
沉悶的根芽,在一陣陣春雨裡。
冬天使我們暖和,遮蓋著
大地在健忘的雪裡,餵養著
一個小小的生命,在乾枯的球莖裡。
劉(象愚)譯:
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在死去的
土地裡哺育著丁香,混和著
記憶和欲望,又讓春雨
撥動著沉悶的根芽。
冬天使我們溫暖,把大地
覆蓋在健忘的雪裡,用乾枯的
球莖餵養著一個小小的生命。
趙(蘿蕤)譯:
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荒地上
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欲望
參合在一起,又讓春雨
催促那些遲鈍的根芽。
冬天使我們溫暖,大地
給助人遺忘的雪覆蓋著,又叫
枯乾的球根提供少許生命。
葉(維廉)譯: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逬生長
紫丁香,從死沉沉的地上,雜混著
記憶和欲望,鼓動著
呆鈍的根鬚,以春天的雨絲。
冬天令我們溫暖,覆隱著
大地,在善忘的雪花中,滋潤著
一點點生命,在乾的塊莖裡。
杜(國清)譯:
四月最是殘酷的季節
讓死寂的土原逬出紫丁香
摻雜著追憶與欲情
以春雨撩撥萎頓的根莖。
冬天令人溫暖,將大地
覆蓋著遺忘的雪泥
讓枯乾的球根滋養短暫的生命。
查(良錚)譯:
四月最殘忍,從死了的
土地滋生丁香,混雜著
回憶和欲望,讓春雨
挑動著呆鈍的根。
冬天保我們溫暖,把大地
埋在忘懷的雪裡,使乾了的
球莖得一點點生命。
趙毅衡譯: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在死地上
養育出丁香,擾混了
回憶和欲望,用春雨
驚醒遲鈍的根。
冬天使我們溫暖,用健忘的雪
把大地覆蓋,用乾癟的根莖
餵養微弱的生命。
李(俊清)譯:
四月這殘酷的季節,滋育
紫丁香於乾旱土地上,混合
記憶和希望,一陣春雨
擾亂半死根莖的平靜。
寒冬卻令人溫暖,飄灑
忘憂之雪掩飾險巇,而以
乾球根飼育少許的生氣。
裘(小龍)譯:
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哺育著
丁香,在死去的土地裡,混合著
記憶和欲望,撥動著
沉悶的根芽,在一陣陣春雨裡。
冬天使我們暖和,遮蓋著
大地在健忘的雪裡,餵養著
一個小小的生命,在乾枯的球莖裡。
劉(象愚)譯:
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在死去的
土地裡哺育著丁香,混和著
記憶和欲望,又讓春雨
撥動著沉悶的根芽。
冬天使我們溫暖,把大地
覆蓋在健忘的雪裡,用乾枯的
球莖餵養著一個小小的生命。
〈荒原〉這部作品,當它那晦澀而嫻熟的文字形式,最後顯示出它的秘密時,沒有人不會感到這個標題的可怕含義……
1948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略特(T.S. Eliot, 1888-1965)的成名作〈荒原〉(e Waste Land),最初發表於1922 年10 月文學季刊《標準》(The Criterion)創刊號上,公認是二十世紀英美文學的一部劃時代的作品,也是西方現代詩的一個里程碑。
第一個中文譯本是在十五年之後,1937 年6 月,由「新月派」詩人陳夢家的夫人趙蘿蕤所完成。促成這件大事的是當時主持《新詩社》的戴望舒,由他策劃、約稿、仔細審閱譯稿,將這部翻譯列為《新詩社叢書》的第一種出版。在《新詩》月刊上的「出版廣告」可能出自戴望舒手筆,聲稱這部「附以三萬餘言的注釋」的翻譯,「譯筆流麗暢達,注釋精細詳明。卷首有葉公超先生序言,對作者做精密的研究,並附有作者肖像,均為此譯本增色不少。」可惜這個譯本當初只印三百五十冊,而且在1937 年6 月正值抗戰爆發前夕,早已絕版。趙蘿蕤四○年代在芝加哥大學深造,四○年代末回大陸之後就不得不與「資產階級作家」艾略特「劃清界線」;在大陸對艾略特的介紹從此中斷[1]。
臺灣最早的〈荒原〉譯本,也是第二個中譯本,是1961 年正當臺灣詩壇大力推展現代主義運動時,由詩人學者葉維廉所翻譯,發表在《創世紀》詩刊第16 期。第三個中譯本是我翻譯的,發表在1966 年《現代文學》第28 期。當時在臺灣是看不到趙蘿蕤的譯本的。
第四個中譯本是由四○年代「九葉詩人」之一穆旦,本名查良錚,在七○年代後半期秘密翻譯的。查良錚於1948 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1953 年回國之後,致力於翻譯工作,到1958 年五年之內,譯有普希金、雪萊、拜倫、濟慈等人的詩集十餘種。1958 年12 月被判為「歷史反革命」,受勞動改造,且被剝奪了著譯出版的權利。1977 年12 月病逝。他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翻譯了當時無人過問,事實上被禁的艾略特的作品十一首,一直到1985 年才收入於《英國現代詩選》[2]作為遺著出版。
〈荒原〉第五個中譯本的譯者是趙毅衡。他原任職於北京社會科學院,1985 年5 月出版的《美國現代詩選》[3]包括艾略特的作品〈荒原〉等十二首;序文寫於1983 年5 月,說明這本詩選的編譯工作前後斷斷續續地進行四年,可見大約譯於1980 年前後,當時他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比較文學博士。他後來任教於英國倫敦大學。第六個中譯本是臺灣東吳大學李俊清教授於1982 年6 月在臺北出版的譯註《艾略特的荒原》[4]。第七個中譯本的譯者是裘小龍。他在1985 年9 月出版《四個四重奏》[5]一書,是艾略特詩的全譯本。他原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1988年到美國深造。第八個中譯本譯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象愚,收入於陳敬容主編的《中外抒情名詩鑑賞辭典》,1988 年8 月出版。[6]
受限於時間和篇幅,本文無法對〈荒原〉這八種中譯本的特色和優劣詳加評論。為了論證文學翻譯的特色和文學翻譯人才必備的幾個條件,我們只能以〈荒原〉開頭七行兩句為例,略加比較和說明。
艾略特在1948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對艾略特的作品推崇備至,其中指出,〈荒原〉這部作品,當它那晦澀而嫻熟的文字形式,最後顯示出它的秘密時,沒有人不會感到這個標題的可怕含義,並認為,這篇淒涼而低沉的作品,旨在描寫現代文明的枯燥和無力,而全詩只有四百三十六行,但它的內涵大於同樣頁數的一本小說。在我看來,〈荒原〉這部作品的主旨和內涵,更是具體而微地包含在開篇這七行之中。
艾略特在原註中說,這首詩的題目、計畫,以及大多的象徵表現都受到韋絲頓(Jessie L. Weston)女士所著《從祭儀到傳奇》(From Ritual to Romance)一書,有關聖杯傳說的啟發,同時也取材於另一本人類學名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關於豐年祭或繁殖神的崇拜儀式。有關聖杯傳說和繁殖神的文化背景,對了解〈荒原〉的題旨,至關重要。
中世紀傳說中有一位漁王(Fisher King),他的城堡坐落在河岸;他所統治的是一塊受詛咒的土地,一片乾旱不毛的荒原,而他本人也是殘廢不育的。這土地的命運和統治者的命運分不開,除非他的殘疾治癒,否則這土地永遠受詛咒;莊稼不長,百畜不生。只有當一個尋找聖杯的騎士歷經重重難關,來到漁王的宮堡,經過考驗,解答各種問題之後,聖杯顯現,詛咒才消失,漁王的病才能得治,他的國土和人民才能恢復生殖能力。聖杯原指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時,聖徒用來承接他的血的杯子,另有一說是指基督及其門徒在最後的晚餐上用的杯子,後來丟失;中世紀騎士的最高榮譽便是找回聖杯,但須經過許多險阻,歷經各種考驗。
《金枝》中關於繁殖神崇拜的神話,主要是敘利亞、埃及、小亞細亞一帶的,有關的祭祀儀式是慶祝繁殖神死後再生,大地由枯寂凋萎中復活,恢復生機。將尋找聖杯與繁殖神崇拜結合在一起,可以說是受基督教化的原始崇拜,其象徵意義猶如生民失去繁殖神,大地失去生機變成了荒原;尋找聖杯是為了救治漁王的殘疾;慶祝繁殖神再生,為使荒原復甦;對西方現代文明而言,其救贖在於找回宗教信仰
荒原上的生命不是朝氣蓬勃的,而是臨死前僅存的一點兒生命,因此翻成「一點兒生命」最為適當。
〈荒原〉開頭七行所描寫的便是這樣一個世界的浮影:荒廢、無能、愛死不活、雖生猶死、不生不死、非生非死、亦生亦死的生存景象或精神形象。以下讓我們逐行討論原詩的含義和各家翻譯的差異。
〈荒原〉一開頭,詩人故作驚人之筆,說:四月最是殘酷的一個月(「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四月正是大地回春,草木復甦,欣欣向榮的時候,怎麼說是最殘酷的呢?對荒原外的人來說,這是有悖情理的;可是對荒原上的任何生命來說,正是如此。對於一個了無生機的荒地,或生機殘廢的生命,硬要他展示生機或萌生春心,知其不可能而強迫其所不能,這何等殘酷!這句原文,翻成「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趙譯),或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葉譯、衡譯),或「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裘譯、劉譯),都沒錯,「信」而且「達」,但是不夠「雅」,缺少詩的韻味。查譯翻成「四月最殘忍」,將「一個月」或「月份」略去了,不夠「信」的標準,但是有道理的─他一定也認為「一個月」或「月份」在中文的語感上太沒有詩意了。這正是杜譯認為四月代表春天,因此將它譯成「季節」的理由。此外,杜譯不將「is the cruelest」直翻成「是最殘酷的」,而翻成「最是殘酷的」,也是基於詩的感受性。有些讀者一定會聯想到李後主「最是倉皇辭廟日」,或是徐志摩在〈莎喲娜拉〉那首詩中的名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徐志摩不愧為詩人,將「那一低頭是最溫柔的」這九個字的散文,鍛鍊成一字不差的優美詩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譯「四月/最是/殘酷的/季節」在節奏上完全呼應英文原句「April / is the / cruelest / month」重輕相間的四個音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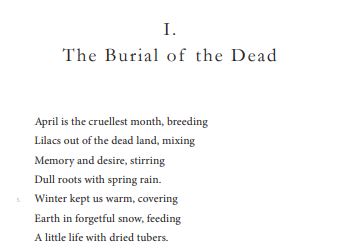
其次,原詩以三個「- ing」結尾的動詞斷行,說明何以四月最是殘酷,頗有欲斷還續、苟延殘喘的味道。先說「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這個片語直譯成散文的意思是:「使紫丁香從死去了的土地上長出來」。這裡「breeding」是及物動詞,除了「使繁殖」之外,也有「促使」、「導致」、「引起」的意思。四月之所以最是殘酷,在於使乾死的土地長出紫丁香。這種不可能的強迫,勉其所難的酷使,是違反生命和自然之道的。這種不可能的強求,違反萬物本性的殘忍,在趙譯(荒地上/長著丁香),查譯(從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衡譯(在死地上/養育出丁香),裘譯(哺育著/丁香,在死去的土地裡),劉譯(在死去的/土地裡哺育著丁香),或李譯(滋育/紫丁香於乾旱土地上)中,都沒有暗示出來。葉譯(迸生長/紫丁香,從死沉沉的地上),略有勉強長出之意,而杜譯(讓死寂的土原迸出紫丁香)卻強烈地暗示這種天地不仁的殘酷性。「Lilacs」,該譯為「紫丁香 」而不是「丁香」;前者屬木犀科,春季開花,可供觀賞;後者屬桃金娘科,夏季開花,大多藥用或作香料。至於將「dead land」譯為「荒地」(趙譯),不夠準確;譯為「死沉沉的土地」(葉譯),「死了的土地」(查譯),「死地」(衡譯),「乾旱土地」(李譯)或「死去的土地」(裘譯、劉譯),與杜譯 「死寂的土原」比照之下,也顯出譯者對詩語的感受性的差異。
下一個跨行片語,「mixing / Memory and desire」各家的譯法大致一樣,將「memory」翻成「回憶」或「記憶」,將「desire」翻成「欲望」(李譯翻成「希望」諒是誤植),唯有杜譯別出心裁,翻成「追憶」和「欲情」,在語感上更有抒情詩的意味。這種帶有強烈感性的情緒也正是生命痛苦和煩惱的根源,是讓荒原人難以忍受的。
下一個片語,「Stirring /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各家的翻譯差別較大,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對詩意的感受不同。「stir」的含意包括「攪動」、「使微動」(cause something tomove slightly) 、「激起」;翻成「催促」(趙譯)、「鼓動」(葉譯)、「驚醒」(衡譯)、「擾亂」(李譯)都不夠準確,不如「撩撥」(杜譯)、「挑動」(查譯)、「撥動」(裘譯、劉譯)庶幾近之。「撩撥」和「挑動」隱含春雨撩人的誘惑,更具感情色彩。「Dull roots」翻成「遲鈍的根芽」(趙譯)、「呆鈍的根鬚」(葉譯)、「呆鈍的根」(查譯)、「遲鈍的根」(衡譯)都沒錯,只是略嫌呆鈍,不夠生動。李譯翻成「半死的根莖」,過於強解。杜譯為「萎頓的根莖」,含有性無能的暗示,尤其是在惱人春雨的撩撥之下,形成極大的反諷;這種暗示力即使超過原詩,只要不違背原詩的含意和「荒原」的主題,該是可取的。裘譯和劉譯翻成「沉悶的根芽」,是違反詩情的,因為荒原人深知追憶與欲情所帶來的痛苦,對春雨的撩撥採取否定的態度,雖然愛死不活,萎靡頹廢,但在主觀上對這種生存狀態是認同的,不該覺得沉悶 。這種了無生趣、無所作為、安之若素的生命觀,在以下三行表現得更為明顯:
Winter kept us warm, covering
Earth in forgetful snow, feeding
A little life with dried tubers.
荒原人認為「冬天使我們溫暖」;所謂「溫暖」不僅指溫度上冷熱適中,更指心理上的溫馨舒適。正像前一句描寫對春天的反常心理,這一句對冬天的描寫也是違背常情的,而在句法上,同樣以跨行片語對這種反常的心理感覺加以說明。第一個理由:冬天「將大地覆蓋在遺忘的雪泥」。所謂「forgetful」,趙譯翻成「助人遺忘的」,葉譯翻成「善忘的」,杜譯翻成「遺忘的」,查譯翻成「忘懷的」,李譯翻成「忘憂的」,衡譯、裘譯和劉譯翻成「健忘的」,語意不盡相同。就我的理解而言,雪本身無所謂善忘或健忘,更無所謂忘懷或忘憂,也許因趙譯翻成「助人遺忘的」,比較合乎常理。然而,英文「forgetful」也有「不掛在心上」或「不在意」(not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or neglectful of something)的意思。亦即,雪對外界「遺而忘之」,漠不關心,不受牽掛或干擾,因而保持覆雪下與外界隔絕的寧靜。翻成「忘懷」或「忘憂」似乎顯得過於超脫和瀟灑。李譯「飄灑/忘憂之雪掩飾險巇」,過於浮誇;將「覆蓋」變成「掩飾」、「大地」變成「險巇」,語意不同,都顯得不夠信實。
最後一個片語,「feeding /A little life with dried tubers」。各家譯法大同小異,但對「A little life」的不同理解卻值得一提。趙譯翻成「少許生命」,葉譯和查譯翻成「一點點生命」,杜譯翻成「短暫的生命」,衡譯翻成「微弱的生命」,李譯翻成「少許的生氣」,裘譯和劉譯翻成「一個小小的生命」。這裡該指荒原上的一般生命現象,翻成「一個⋯⋯生命」,不足取;翻成「短暫的」或「微弱的」是解釋,也不可取。「生氣」作為「飼育」的受詞,不無勉強。荒原上的生命不是朝氣蓬勃的,而是臨死前僅存的一點兒生命,因此翻成「一點兒生命」最為適當。冬天讓埋在雪地下的枯乾的球根滋養一點點兒生命,極言生存的極限狀況,而荒原人卻認為「冬天使我們溫暖」,可見他們甘於苟延殘喘,對這種奄奄一息的生存狀態並無怨言,然而只要一息尚存,應該仍然有希望獲得救贖的。
從實踐中,我深知翻譯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要達到這種理想境界是不可能的,包括上述八種〈荒原〉的中譯本。
從以上的解釋中,我們可以對〈荒原〉的主旨有了較明確的了解。在荒原的世界裡,春天是殘酷的,他們規避欲望,拒絕回憶,不願生命力的復甦,固然是逃避的心理,也是對現實的消極反抗;他們喜歡冬天半死不活的狀態,無為無欲,如果不能獲得救贖,是寧死勿活的。然而,這首詩的主題,並不在於讚揚或歌頌這種反常的生命觀。詩中涉指聖杯傳說的象徵意義,主要在於尋找聖杯以救治漁王的殘疾而使不毛之地恢復生機。因此,繁殖神崇拜的象徵意義,在這首詩中更為重要。換句話說,生與死是〈荒原〉的兩大主題,其根本意義在於,漁王的傳說象徵由生到死的頹廢,而繁殖神的崇拜象徵由死到生,乃至由死達到生的救贖。〈荒原〉開篇這七行的主旨在於前者,極言荒原世界的頹廢心態。若不能獲得救贖,這種生是不如死。這也是〈荒原〉這首詩在詩題之下那段引文的主旨:
「在庫瑪耶我親眼看見那位女巫被吊在甕中,每當孩童問她:女巫姑,你想怎樣?她總是回答說:我想死啊。」
這段題辭引自羅馬詩人佩特洛尼厄斯(Petronius, ?-86)作品。在希臘神話中,阿波羅愛上女巫西比爾,她向阿波羅要求永生,但卻忘了要求青春,因此她的生命只能老而不死,最後衰老萎縮成一個瘦小的軀殼,被吊在甕中或瓶子裡。這種老而不死的生命,簡直生不如死,因此她但求一死,以得解脫。這個題辭用來喻指荒原上的生命,奄奄一息,不死不活,其實是,這種生不如死,甚至可以說,生命荒廢到如此地步無異於死,這題旨是相當明顯的。

從以上的比較論述中,可以看出,翻譯不只是散文意義的傳達,尤其是翻譯詩。詩的語言,不同於散文,有特定的色調、節奏、暗示、聯想、象徵等等語言藝術的要素,也是詩之為詩的特質。能將這些要素或特質,在另一種語言中重現或再創造,才是優越的翻譯。因此,文學作品的翻譯,包括原文語意的理解,文學特質或詩意的把握,以及以另一種語言的再創造。這是文學翻譯人才必備的三個條件,亦即,外國語文(包括文化)的理解能力,本國語文(包括文學傳統)的學養,以及文學的感受性。這三者表現在翻譯作品上,亦即,對原文語意理解的準確性,曲盡原意的表現力,以及再創造的藝術效果,也就是一般所謂的「信達雅」這三者合一的翻譯的理想境界。
從實踐中,我深知翻譯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要達到這種理想境界是不可能的,包括上述八種〈荒原〉的中譯本。然而,這無礙於我們在理論上探討理想的翻譯。我曾在〈談翻譯〉的一篇文章中,認為「翻譯是一種藝術,也是一門學問。理想的翻譯者應具有創作者的感受性和表現技巧,以及學者的學養和為學的態度。」優秀的翻譯必備的「信」、「達」、「雅」,也可以解釋為作學問的信實態度、語言的感受和表達能力,以及藝術效果再創造的技巧。「從事翻譯和作學問一樣,在態度上最重要的實實在在,不虛不巧⋯⋯以作學問的態度從事翻譯,則尊重原作者的意思與原著的尊嚴,遇有疑難之處不致隨意增刪或出於不負責任的猜測⋯⋯對原作的文學特性,藝術風貌,或者立論旨趣,典故象徵等等,經過研究有了確實了解之後,翻譯起來才能得心應手。」就語言的感受和表達能力而言,對原文的感受能力和以另一種語言的表達能力一樣重要。「詩的翻譯者應該具有詩人一樣的匠心,必須也具有詩人那種感受性和表現技巧。有了敏銳的感受性才能了解原詩中的『詩』;有了優越的表現技巧才能將原詩中的『詩』再創造出來,而達到同樣或相應的藝術效果。」「翻譯與原作該是不同語言的雙胞胎,不同國境的形與影。」就藝術效果的再創造而言,「翻譯不外乎是以另一種語言表現原文所表達或暗示的一切;這一切在文學作品,尤其是詩中,包括語意、句法、語氣、象徵、暗示、聯想、風格,以及整體的藝術效果等等。」「由於語言的結構不同,譯詩與原詩中字句的組合方式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不同的組合所放射的光芒應該是一樣晶瑩輝煌的。」[7]
[1] 陳子善,〈《荒原》中譯本及其他〉,《香港文學》第108 期,1993 年12 月,頁70-71。趙譯本後收入袁可嘉、董衡巽、鄭克魯選編,《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一冊( 上),上海文藝出版社。
[2] 查良錚譯,《英國現代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5 月。
[3] 趙毅衡編譯,《美國現代詩選》(上),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 年5 月。
[4] 李俊清譯註,《艾略特的荒原》,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2 年6 月。
[5] 裘小龍譯,《四個四重奏》,廣西:灕江出版社,1985 年9 月。
[6] 陳敬容主編,《中外現代抒情名詩鑑賞辭典》,北京:學苑出版社,1989 年8 月。
[7] 杜國清,〈談翻譯〉,《幼獅文藝》第273 期,1976 年9 月。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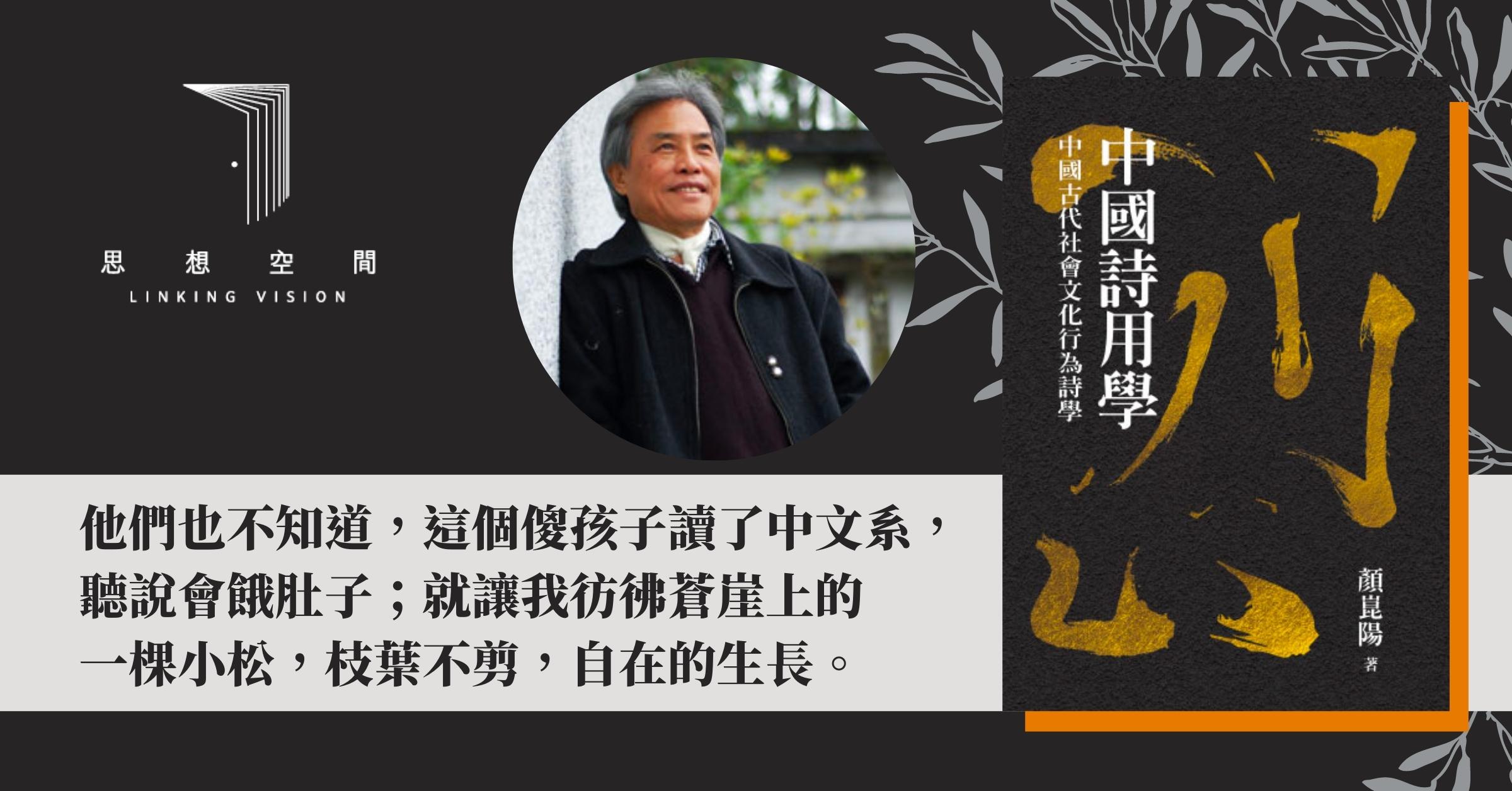
顏崑陽:我,因詩而存在!

楊宗翰:未盡的詩史與未來的詩——如何寫一部台灣新詩史

李癸雲:女人專用之髒話:夏宇的女性詩學
| 閱讀推薦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文學系畢業,日本關西學院大學日本文學碩士,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任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教授、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暨台灣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創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Series),致力於臺灣文學的英譯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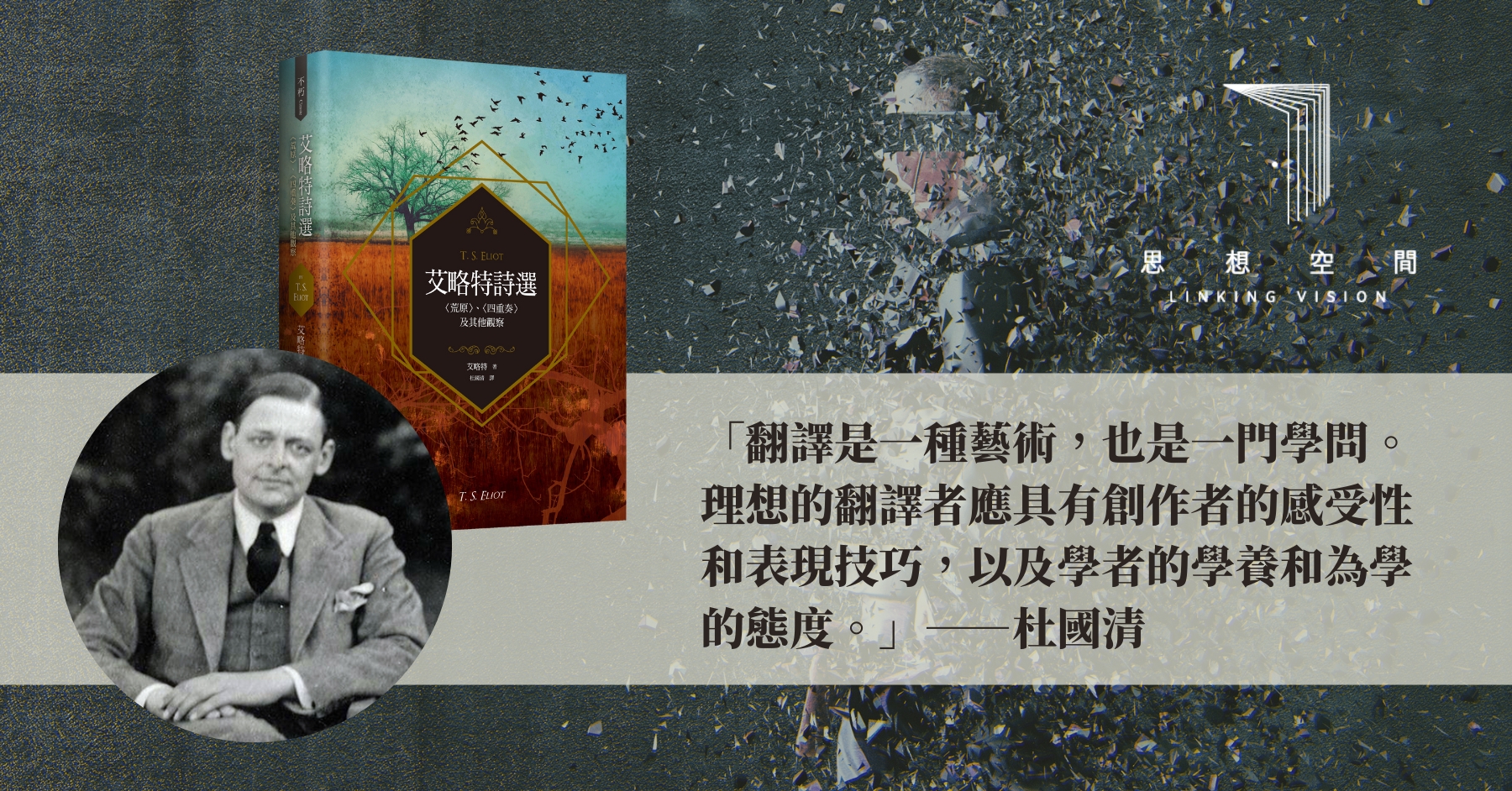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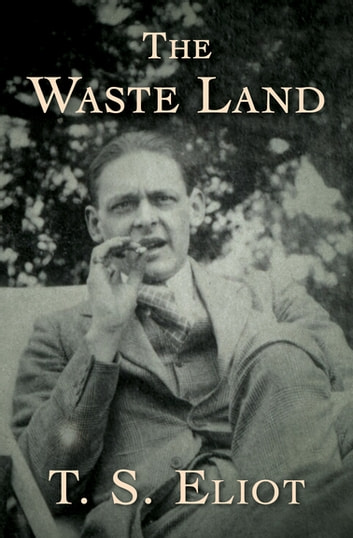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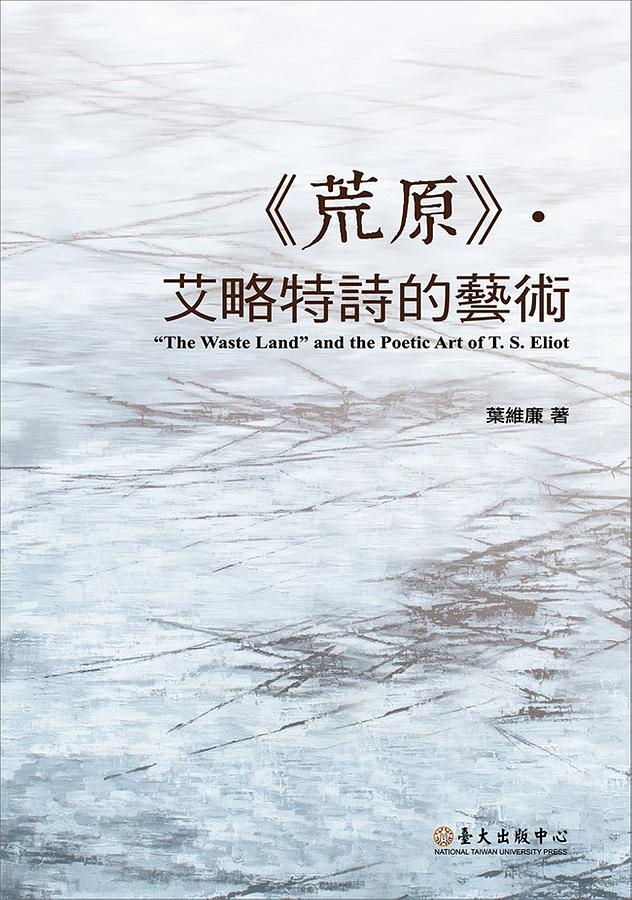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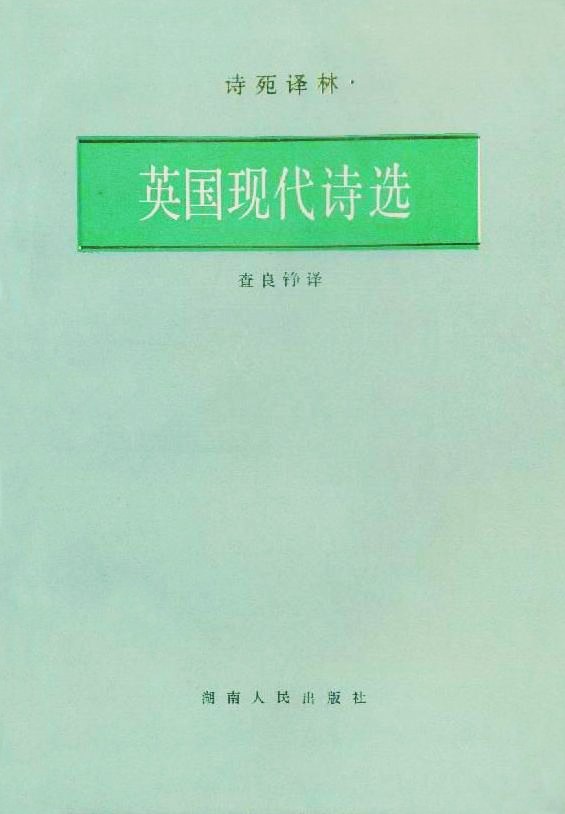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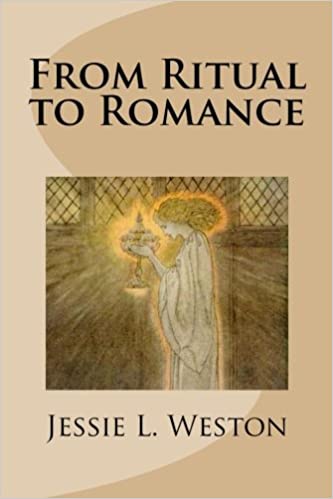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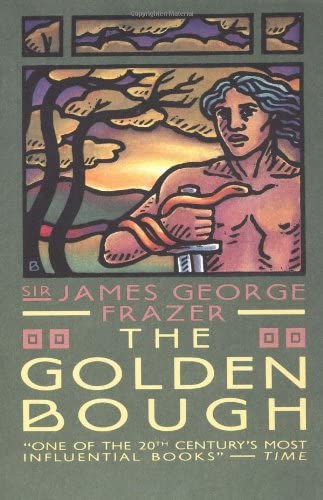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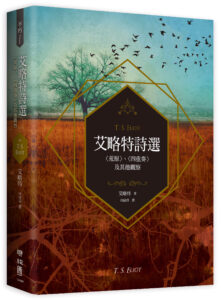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