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提摩希‧史奈德 Timothy Snyder(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編按:人們長久以來對二戰大屠殺的刻板印象是,納粹德國透過精密的計畫,對領地進行全面控制,對外侵略的同時也對內屠殺。因此人們以為,形成大屠殺機制的關鍵因素是,一個高效能的國家威權,宣傳極端的種族偏見,運用極致冷酷的科學理性來進行種族清洗──在今天,這些因素似乎不太可能重現。知名歷史學專家提摩希‧史奈德的《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正是為了打破上述迷思,嘗試將當前國際時局發展如何與二戰發生關聯,提出新的見解⋯⋯(* 本文摘自《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結論,標題為編者擬。)
關於納粹德國的主導的刻板印象是:有一個無所不能的國家,將自己的公民中一種人全體歸檔、壓迫、然後滅絕。但這並非納粹達成猶太大屠殺的方式,甚至也不是他們對這件事的認知方式。猶太大屠殺受難者當中絕大多數都不是德國公民;是德國公民的猶太人倖存的機率遠比那些被德國摧毀的國家的猶太公民來得大。納粹知道他們必須去到國外,踐踏鄰國的社會,才能將他們的革命帶回到自己的國度。要是希特勒於一九三九年遭到(幾乎要成功了的)謀殺,今天對納粹德國的記憶就只不過是許多法西斯主義國家當中的一個。不只是猶太大屠殺,所有德國犯下的主要罪行都發生在國家體制已經被摧毀、瓦解或者大幅妥協的地帶。德國人殺了五百五十萬名猶太人、逾三百萬蘇聯戰俘、以及約一百萬(以反游擊隊行動之名殺的)公民,這些都發生在無國家狀態的地帶。[1]
由於猶太大屠殺是近代史上的軸心事件,對事件的誤解會讓我們朝向錯誤的方向去思考。一旦猶太大屠殺被歸咎於現代國家,弱化國家威權就好像有所助益。對政治右翼來說,國家權力被國際資本主義所侵蝕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對政治左翼而言,群龍無首的革命將自命為有道德的革命。在廿一世紀,無政府狀態的示威抗議運動與全球的寡頭政治參與在一場友善的打打鬧鬧,在這打鬧當中沒有人會真的受傷,因為雙方都把國家當成了真正的敵人。比起秩序的毀滅或者秩序的缺席,左右翼雙方都更害怕秩序本身。後現代性是共同的意識型態反應方式:要小不要大、要碎片不要結構、要管窺不要全景、要感受不要事實。對左右翼雙方來說,後現代對於大屠殺的解釋方是傾向於依循德國和奧地利一九三〇年代的傳統。結果他們所製造出的錯誤只會讓未來的犯罪行為變得更為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發生。
如果除了競爭之外什麼都不重要的話,那麼淘汰抗拒競爭的人以及防止競爭的體制也就變得再自然也不過。對希特勒來說,那些人就是猶太人,那些體制就是國家。
在左翼這邊,猶太大屠殺的主流詮釋可以說是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這個學派的成員多是移居到美國的德國猶太人,他們將納粹國家描繪成發展過度的現代性之表現。阿多諾(Theodor Adorno)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頗具影響力的《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開頭的假設(和希特勒一樣)是「資產階級文明」即將崩毀。他們將科學方法化約為實踐上的統治,(和希特勒一樣)未能把握科學調查的反身性與其無法預估的特質。希特勒將猶太人描繪為偽普遍主義(bogus universalisms)的創造者,這種偽普遍主義是猶太人統治的表象;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則反對所有的普遍主義,因為所有的普遍主義都是統治。他們稱以理性來指導政治本身就內含著對變異的不夠包容,而猶太屠殺只是其中一個例子。這個錯誤的判斷的影響之深之廣難以估量。希特勒並不是啟蒙的支持者,而是啟蒙的敵人。他並不擁護科學,而是將自然與政治混為一談。[2]
右翼對猶太大屠殺的主流解釋可以稱之為維也納學派(Vienna School)。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追隨者宣稱是不可一世的福利國家導致了國家社會主義,因此開出了放鬆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作為政治性的惡的解藥。這種敘事是很方便的敘事,但在歷史來講卻說不通。從來沒有一個打造出社會福利制度的民主國家因為該制度而向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低頭。在中歐所發生的恰好相反。希特勒上位時正值經濟大蕭條期間,而經濟大蕭條之所以散布到全球正是因為各國政府還不知道怎麼介入經濟週期。海耶克的家鄉奧地利根據當時的自由市場正統實施資本主義,下場是經濟衰退極其嚴重,而且似乎永無止境。奧地利猶太人受到壓迫的起始點不是國家的成長,而是國家於一九三八年的瓦解。[3]
倡議自由市場的人所預見的理想資本主義仰賴於社會的美德(social virtues)和睿智的政策,這些並非由資本主義自身所產生出來的。在猶太大屠殺期間,由德國的政策所產生出來、並且由猶太人和他們的拯救者所經驗到的特殊資本主義形式當中,所有的交易都仰賴於個人之間的信任,在這樣的交易安排當中,對方也有可能會背信或甚至殺人。在海耶克自己也反對的某種極端市場烏托邦主義中,維也納學派與艾茵.蘭德(Ayn Rand)的思想合為一體。她認為競爭就是生命的意義本身[4];希特勒也說過幾乎相同的話。雖然這樣的化約論相當誘人,卻也相當致命。如果除了競爭之外什麼都不重要的話,那麼淘汰抗拒競爭的人以及防止競爭的體制也就變得再自然也不過。對希特勒來說,那些人就是猶太人,那些體制就是國家。
當國家不在場時,權利——無論是哪種定義下的權利——都不可能維繫。國家並不是理所當然存在的結構,也不是應當被剝削、被拋棄的結構,而是一個漫長、寂靜的努力下的結果。
如同所有的經濟學家都知道的,市場並不能在宏觀層次或微觀層次上完美運作。在宏觀的層次上,不受管制的資本主義受制於經濟週期的極端情況。理論上,市場總是能從經濟蕭條中復原;但實際上,經濟崩盤所導致的苦難可能在復原之前就已產生深遠的政治性後果,包括資本主義自身的終結。在微觀層次上,公司在理論上可以產生出他們自身不予以補救的外部支出。這種外部性的經典案例就是汙染,汙染不會為生產者帶來花費,但卻會損及他人。[5]
政府可以為汙染訂下成本,將外部性給內部化,以便減少不想要的後果。要將造成氣候變遷的碳汙染成本內部化的方法很簡單。要反對這樣的作法並宣稱這樣的作法是反資本主義的,得要找出一種教條,這個教條仰賴於市場,而最終也會保存市場。在美國的世俗右翼組織,有些支持市場完全不受約束的人已經找到了這樣的教條:那就是宣稱科學不過是政治。由於氣候變遷的科學很明確,有些美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意志派(libertarian)便否認科學自身的有效性,將其科學上的發現都描繪成老謀深算的政客的把戲。像這樣將科學和政治混為一談很可能是危險的。
雖然沒有美國人會否認坦克車在沙漠中能夠運行,但有些美國人的確會否認沙漠正在擴大。雖然沒有美國人會否認彈道學(ballistics),但有些美國人會否認氣候變遷。希特勒否認科學可以解決基本的營養問題,但卻認為科技可以贏得更多的領土。[6]這樣說來,等待研究成果是毫無意義的,必須立即採取軍事行動的這種想法也就不足為奇。以氣候變遷的案例來說,否定科學同樣也合理化軍事行動而非投資在科技發展上。[7]要是人們自己不為氣候問題負責,他們就會將氣候問題造成的災害責任轉嫁到其他人的身上。只要否定氣候問題阻礙了科技的發展,就可能加速真正的災害,而災害又進而可能讓災難性的思考(catastrophic thinking)變得更為可信,加速政治變成生態恐慌的惡性循環。
自由市場是自然的這種流行的概念本身也是將科學與政治混為一談的結果。市場並非自然的;市場仰賴於自然。[8]氣候並不是可以拿來交易的商品,而是經濟活動可以成立的先決條件。以少數人能牟利為名就毀滅全世界的「權利」本身就揭露了嚴重的概念性問題。權利意味著拘束。每個人都是自身的目的;一個人的重要性並非取決於其他人想從他或她身上取得的東西。個人有權利不要自己的家園被定義成棲息地。他們有權利不要讓自己的政體被摧毀。
當國家不在場時,權利——無論是哪種定義下的權利——都不可能維繫。國家並不是理所當然存在的結構,也不是應當被剝削、被拋棄的結構,而是一個漫長、寂靜的努力下的結果。無論是像右翼般興高采烈地將國家分割成碎片,或是像左翼般意味深長地窺視國家的碎片,都極為誘人,但卻危險重重。政治思想不是毀滅,也不是批判,而是由歷史所啟迪的多重結構的想像——是一種當下的勞動,可以用來保存未來的生命和尊嚴。政治與科學之間的多重性也是一種多重性。肯定政治與科學之間不同的目的讓思考權利和思考國家成為可能;將他們混為一談則是朝向諸如國家社會主義這樣的總體意識型態邁進一步。另一種多重性是秩序與自由之間的多重性:儘管秩序與自由並不相同,但它們仰賴彼此。宣稱秩序即自由、自由即秩序終將走向暴政。宣稱自由就是沒有秩序則終將走向無政府狀態——那也不過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暴政。政治的要點在於保存多重的、不相化約的要素處於相互競合的狀態,而不是向某種總體的迷夢(無論是不是納粹)屈服。[9]
[1] 參閱Arendt, Origins, 310. 筆者在Bloodlands討論過這些政策。
[2] Horkheimer and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especially 212, 217;引言見頁1, 15. 亦見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176–77. (形式不那麼激進的)同樣的錯誤可見於諾伊曼(Franz Neumann)給戰略情報局(OSS,譯按: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提交的報告。見Secret Reports, 28, 30. 另見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135, 138;Kołakowski, Main Currents, 347;Zehnpfennig, Hitlers Mein Kampf, 129.
[3] 更詳盡的討論見Judt and Snyder, Thinking.
[4] Burns, Goddess, 175.
[5] 見Powell, Inquisition, 63, 98, and passim;Oreskes and Conway, Merchants of Doubt, 169–215;Economist, 15 February 2012;Tollefson, “Sceptic,” 441. 二〇一一年,化石燃料工業為了造成的麻煩斥資約三百萬美元。見Silver, Signal, 380. 另見Farley, “Petroleum and Propaganda,” 40–49. 亦見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Got Science?,” 18 October 2012以及Weart, “Denial,” 46, 48. 資本主義肯定將氣候變遷的資料登記在案。保險公司保留了精確的暴風資料,並以此對水災的保險設限。見Parker, Global Crisis, 691–92. 在某些方面,自由意志右派(libertarian Right)的錯誤也在基督教右派(Christian Right)的一些成員那裡聽見了迴響。創世論者(Creationists)反對幾個世代的科學家擴充的達爾文理論關於非人類的動物的說法,反而使用「科學」一詞來描繪上帝所創造出的靜止不變的自然秩序。這又是一種將科學與政治混為一談的說法。在他們支持不受規範的資本主義的同時,許多創世論者卻都套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概念到其他的人類身上。人類有權宰制世界,而更有競爭力的人類則有權宰制較無競爭力的人類。這是將科學與政治混淆的又一例。
[6] Hitler and His Generals, 62. 見Thomä, “Sein und Zeit im Rückblick,” 285;Genette, Figures I, 101;Robbe-Grillet, Pour un nouveau roman, 133.
[7] 否認氣候科學對於美國的海軍會造成嚴重的問題,因為海軍面對的是基地可能被淹沒的問題,以及要競爭北極圈融化的水源。見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 March 2010.
[8] Bloom, Closing, 84;Bauman, Modernity, 235. 參閱Moses, “Gespräch.” 論證到此,筆者已經是在展示概念之間彼此的關係,而不是在探詢歷史上的關係。參閱Moyn, Last Utopia, 82–83.
[9] 納粹德國主要殺害的對象是其他國家的公民。那麼對自己的公民進行大規模殺害的國家呢?廿世紀最駭人聽聞的三個案例——中共、蘇聯、波布(Pol Pot)統治下的柬埔寨——都是黨國體制。在黨國體制中,意識型態上和實踐上都要求國家體制次於黨的體制,且國家的合法性完全被黨領導人所提出在意識型態上集體的未來訴求所削減。這些歷史與納粹德國及其鄰邦所走的軌跡不同,但在一方面提供的是同樣的教訓:在庸常的保守意義下,國家作為權力壟斷者以及義務和權利的對象的重要性。這個主題廣泛,需要另外為文討論;某些相關議題在筆者的Bloodlands中已經提出。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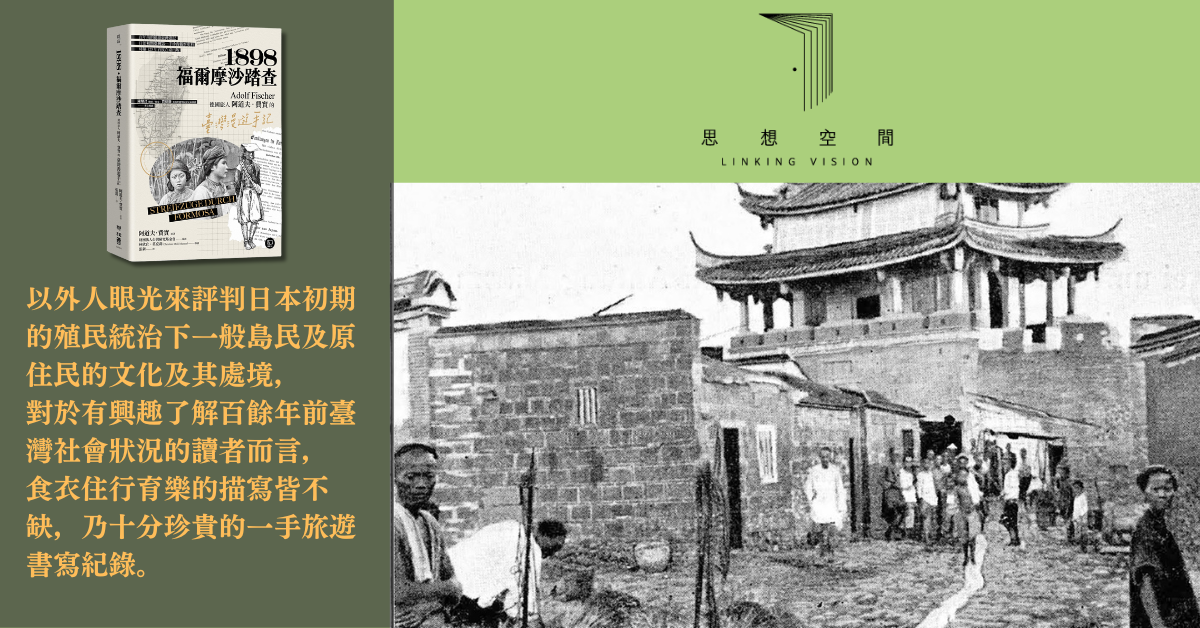
藝術與殖民之糾葛:阿道夫.費實的臺灣

Timothy Snyder:不要向某種總體的迷夢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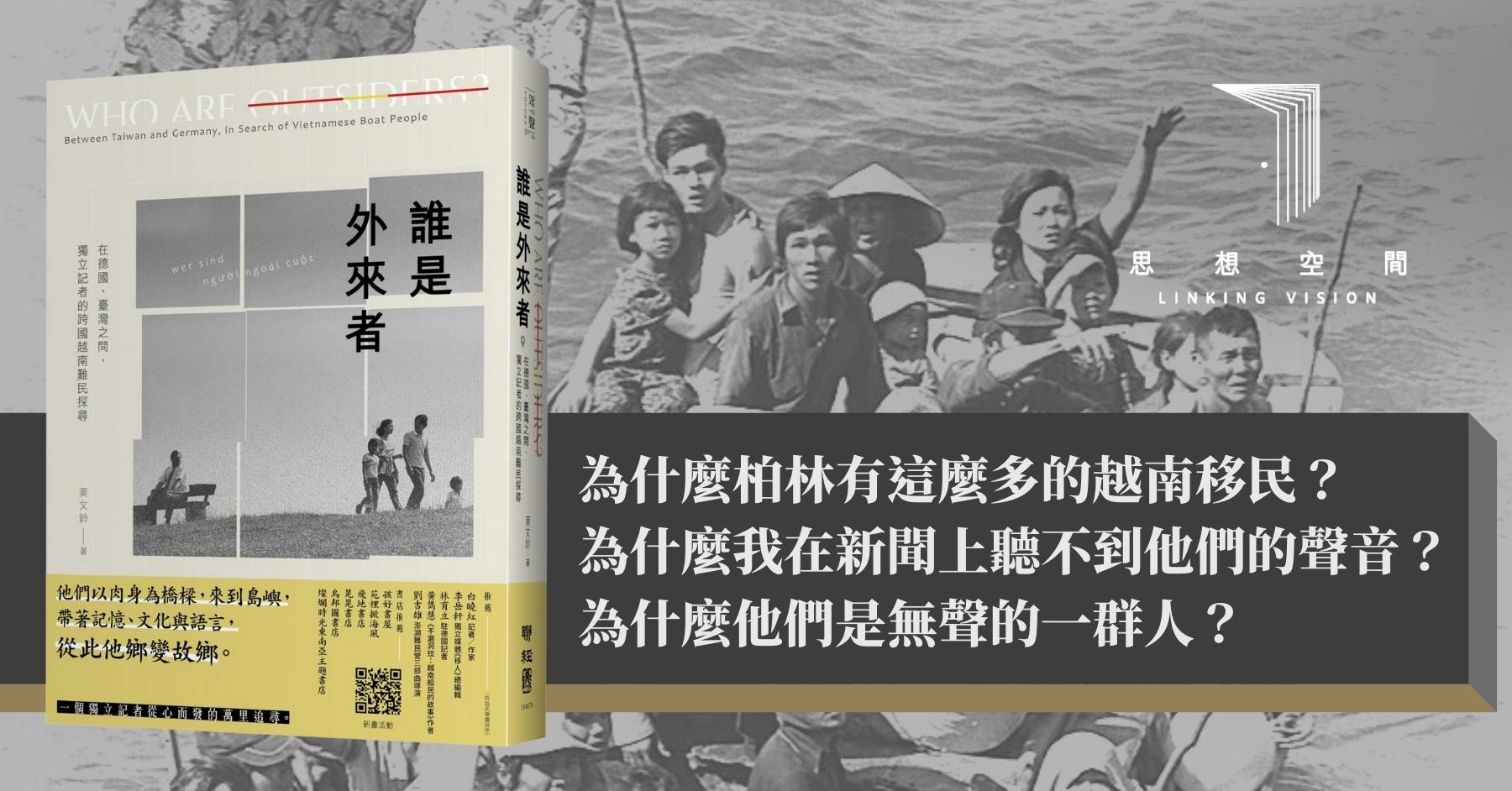
黃文鈴:越南船民在德國——為什麼他們是無聲的一群人?
| 閱讀推薦 |

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東歐史,畢業於牛津大學,曾在巴黎、維也納和哈佛大學擔任過研究員。曾獲漢娜.鄂蘭獎章、萊比錫書展大獎、美國藝術文學院文學獎項,文章評論散見全美各大媒體、報章雜誌專欄。撰有多部備受稱譽的史學著作,包括《血色之地: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歐洲》、《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暴政: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The Road to Unfreedom: Russia, Europe, America(即將出版)等。同時也是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外交關係理事會暨良知委員會的成員、維也納人類科學研究中心的常駐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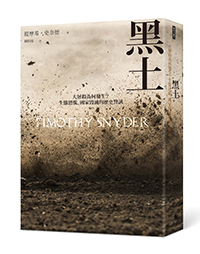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