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任職平面媒體文字記者,Covid-19 爆發前花了近兩年的時間遊走南美洲,最大夢想是跟心愛的男人在南美洲一起生活,目前在南台灣小鎮過著安靜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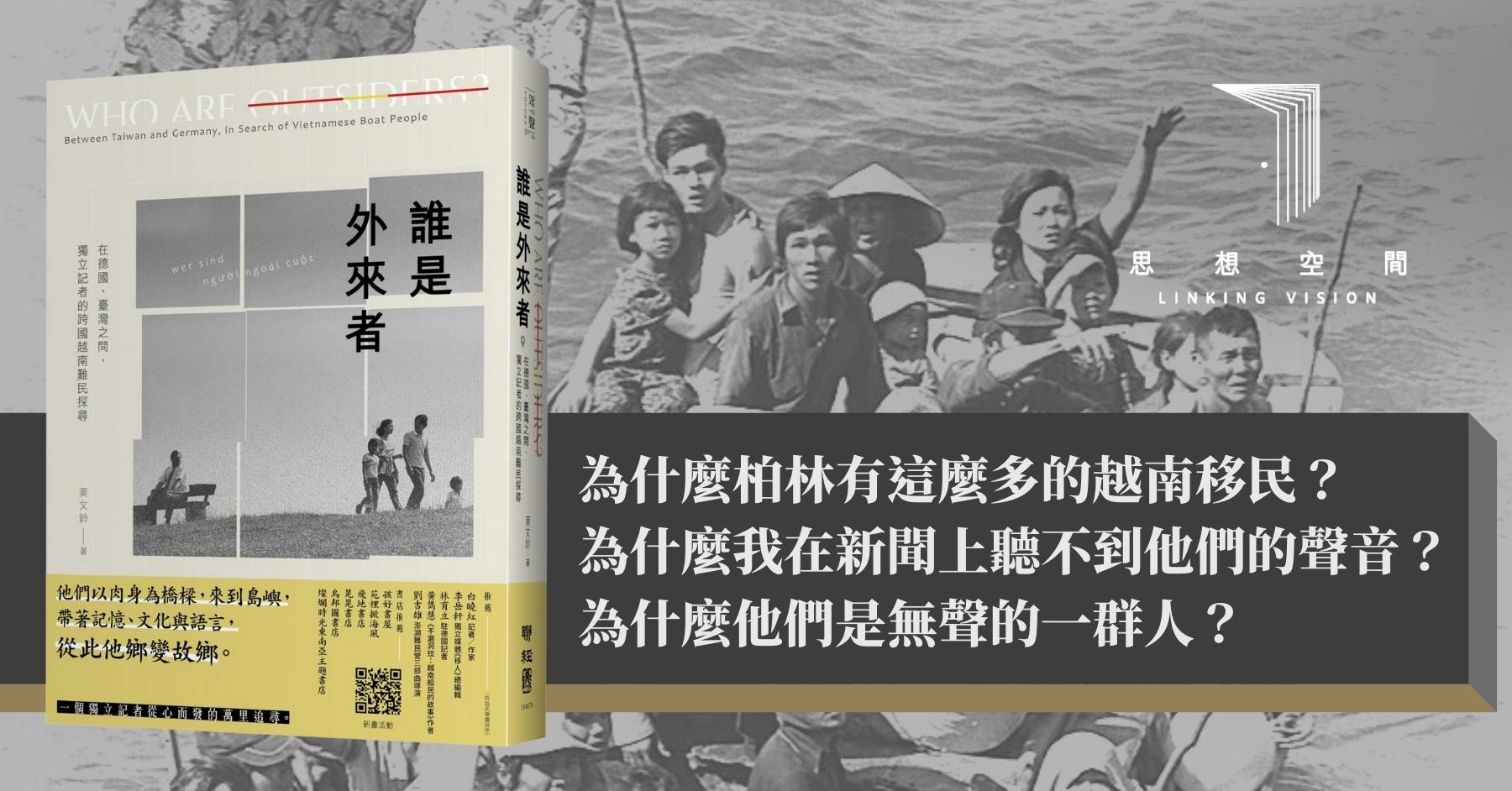
記錄/Soledad
編按:對於現在的人們來說,在世界各處移動、移民似乎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然而在1975年時,卻有一群人甘願冒險犯難、飄洋過海,只為了尋求更好的未來可能。2022年9月23日,臺南烏邦圖書店舉辦了《誰是外來者》新書分享會,以「旅德記者眼中的越南移民:當東西德與南北越相會」為主題,除了分享新書內容之外,也談談黃文鈴作為一位旅德的「外來者」他的觀點和心得。
越南河粉、越南麵包、生春捲……在臺灣每個城市幾乎都吃的到越式料理,更不用說菜市場裡也常看到越南新住民開的美甲店。但你能想像,在德國也有類似景況嗎?柏林是越南餐廳、越南小吃的天下,美甲店也是一家接一家,這正是在德國定居邁入第五年的獨立記者黃文鈴最深切的觀察與感受。她今年出版新書《誰是外來者:在德國、臺灣之間,獨立記者的跨國越南難民探尋》,就是在探討越南移民到德國、臺灣的歷程。
2022月9月23日,臺南烏邦圖書店舉辦了《誰是外來者》新書分享會,黃文鈴以「旅德記者眼中的越南移民:當東西德與南北越相會」為題,與讀者、觀眾分享她的所眼所聞。
對比黃文鈴的新書英文書名《Who are outsiders?》,越南移民在德國的處境,是不是就像壽司般,身為外來者,形塑出不一樣的面貌了?
2017年9月,黃文鈴辭去聯合報近三年的記者工作,隻身離開臺灣去了德國。當時的起心動念來自於2015年發生近代最嚴重的難民危機,敘利亞內戰以及伊斯蘭國(ISIS)崛起,中東與北非的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紛紛湧入歐盟,至今仍是一場看不見盡頭的人道危機。2017年她看了很多外電報導,很想去現場跟他們對話、進行報導,又或者只是聊一聊也好。由於德國在這場戰事中收容百萬名中東難民,她決定前往德國,開啟獨立記者的生涯。
但明明黃文鈴最一開始的目標是想採訪中東難民,怎麼反倒生出一本談越南移民在德國的書?她娓娓道來其中的故事。
2017年剛到柏林,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在街頭散步,但卻看到很多越南餐廳,這些店清一色在門口掛著長長竹燈籠,又或是有一些很摩登的招牌,甚至有寫著「Imbiss」(德文,意指小吃)的越南小吃店,辨識度非常的高。最讓她嘖嘖稱奇的是,那邊的越南餐廳還賣壽司,問題是德國不靠海,所以壽司放的不是魚,反而是以其他配料用炸壽司的方式撒上芝麻,有所謂的「Inside Out Sushi」之稱。
對比黃文鈴的新書英文書名《Who are outsiders?》,越南移民在德國的處境,是不是就像壽司般,身為外來者,形塑出不一樣的面貌了?
正因為舉目所及全是越南移民的店家,她開始思考,「為什麼柏林有這麼多的越南移民?為什麼我在新聞上聽不到他們的聲音?為什麼他們是無聲的一群人?」
黃文鈴也提到,當然除了越南餐廳外,柏林幾乎每個地鐵站的外頭都會有越南移民開的花店,很多修改衣服、清潔鞋子的店清一色由越南人打理。正因為舉目所及全是越南移民的店家,她開始思考,「為什麼柏林有這麼多的越南移民?為什麼我在新聞上聽不到他們的聲音?為什麼他們是無聲的一群人?」進而爬梳越南移民來德國的歷史,採訪超過50位的越南移民,試圖留下記錄。
她談起書中的第一個主軸–去了西德的越南船民。1975年南北越統一,但3年過後,南越人民眼見衰敗的經濟看不見復甦的可能性,加上種種迫害、驅逐境內華僑的政策,他們決定逃離家園。1978年,越南政府針對華僑實施公開偷渡政策,由政府協調大型船隻,以付金條當船費的代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民眾逃出越南。
一艘原本應該被銷毀的老舊貨船、名為「海鴻號」的難民船,在越南政府的默許下啟航,全船2564人超載一路駛向印尼。未料颱風侵襲,船隻引擎故障,最後只好停在馬來西亞的外海。糧食、飲水均耗盡,飽受酷熱天氣的曝曬折磨,越南人雖然很渴望馬國能出援手,但馬國以船上乘客早付錢給越南政府為由,拒絕承認其難民身分。
當時有記者獲准上船採訪,形容眼前所見景況:「我們真的就是踩在人的身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都奄奄一息。」慘絕人寰的影像透過國際媒體揭露後,開始引發歐盟關注。法國由左翼領袖格魯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率先發起「為越南派出一艘船」行動,德國的廣播記者諾伊德克(Rupert Neudeck)在一場聚會中聽到對方談起船民的慘狀大受震撼,決定跟進救援行動,當時西德救起的3萬8000名越南船民中,光諾伊德克租下的「阿納穆爾角號(Cap Anamur)」及其創立的「德國緊急醫生組織」就救出1萬多人。

但西德這一波救援越南船民的熱潮,有其天時地利人和的時代背景。當時整個社會仍深受「六八運動」影響。西德1967年發起學運,青年學子質疑上一代並未反思納粹過去犯下的錯誤,這波改革運動雖然失敗告終,但卻推動社會思想轉變,讓多數民眾能以人道關懷為出發點;對越南船民伸出援手,猶如幫助納粹時期遭受苦難的猶太人,對於西德人而言,無疑是種遲來的彌補。
但即使「阿納穆爾角號」寫下光榮記錄,3年後它卻黯然終航。這得從西德政府針對越南船民的收容負擔龐大談起,為了讓船民能融入社會,由公部門支出安排免費德語課程、寄宿家庭。但船民人數越接越多,對地方政府來說,財政不堪負荷,加上這批船民擁有永久居留權、合法工作權,對當時失業率節節升高的西德人來說,難免衍生工作機會被剝奪的仇外情緒。龐大民意的衰退,讓西德從原先熱情響應越南船民的立場,轉為不再支持的下場。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東德與越南政府簽署的協議失效了,契約工的命運更是混屯,該何去何從呢?
西德有所謂的越南船民,那東德呢?這是書中第二個主軸——飄洋過海的越南契約工。黃文鈴提到,自1960年代起,東德有大量年輕人逃亡到西德,為了填補勞力大幅短缺,東德陸續與友好盟國簽署協議、引進外國契約工,1980年更與越南政府簽署契約工協議,大量引進越南契約工,形成西德有所謂的越南船民,東德有越南契約工的特殊現象。
正因德國分裂的過去,讓它成為唯一同時擁有大量越南船民、越南契約工的國家,
也由於德國匯聚了這兩大族群的越南移民,不難理解「為什麼德國的越南人這麼多?」這個獨特性是黃文鈴為何對德國的越南移民很著迷的一大關鍵。
1989年,東德9萬4千名契約工中,越南就佔了近6萬人。不過契約工當時簽下的協議內容有許多不合理規定,大幅影響契約工在東德的處境。舉例來說,契約工在東德期間結婚、生子就是犯大忌,女契約工一旦懷孕得立即通報上級,若不接受墮胎,便只能踏上被遣返的回鄉之路。
黃文鈴曾採訪越南契約工舍監韓雀(Tamara Hentschel),對方就曾幫助過懷孕女工。她指證,當初在東柏林一處叫做考斯多夫(Kaulsdorf)的小鎮,有一家診所願意幫忙非法懷孕的女契約工,那些女工「一個接一個像工廠流水線般墮胎,有人因為頻繁墮胎,再也無法自然受孕。」不願墮胎也不願被遣返的女契約工,則想方設法躲避追查,有人甚至躲在衣櫥裡長達數月,一直到孩子出世,整件事才曝光。
另外,契約協議當時寫著上工前會接受一個月至三個月、包括語言與工作技能的職前訓練,但黃文鈴採訪的很多契約工回憶,根本就不是這樣。換言之,他們未如西德船民能有妥當的事前準備融入東德社會;加上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東德與越南政府簽署的協議失效了,契約工的命運更是混屯,該何去何從呢?要留下來爭取合法居留權,當然就只能先打黑工,90年代許多越南契約工開始加入賣私菸的行列,但私菸也衍生出搶地盤等黑幫流血衝突,讓越南移民從原本認真勤奮、很愛笑的良好形象,淪為「微笑的黑幫」稱號。
德國後來甚至爆發被視為二戰後境內最嚴重的種族主義暴力事件,也就是向日葵攻擊事件,受害者正是這批前越南契約工。兩德統一後,一棟繪有巨幅向日葵的大樓被改作難民庇護申請者中心,隨著各國難民紛紛湧入德國,該棟樓人滿為患。1992年,該棟樓人聲吵雜加上四周環境髒亂,引來當地居民不滿,對難民的怨氣逐漸沸騰,當地人朝大樓扔擲石塊、丟汽油彈,來不及撤出的許多越南移民只能靠自己脫離險境,還得面對圍觀民眾不斷鼓譟叫好的局面。

德國的分裂,造就境內擁有越南船民、越南契約工的特殊現象,但兩者的命運卻大相逕庭,加上過去政治背景的不同,絕大多數來自北越的越南契約工,與來自南越的船民們歧見極深,這些隔閡即使飄洋過海到了德國,仍根深蒂固,反而是他們的下一代,少了包袱,比較容易成為朋友。
黃文鈴在書中必問受訪者的一個問題:「你覺得住在德國數十年後,自己屬於這個社會嗎?」她希望可以讓讀者感受到當一個外來者的處境。她不諱言,自己在德國就是個少數族群,她也在找歸屬感,就像臺灣有著多元族群,也有社會融合問題,希望大家看完書,可以彼此多認識一點。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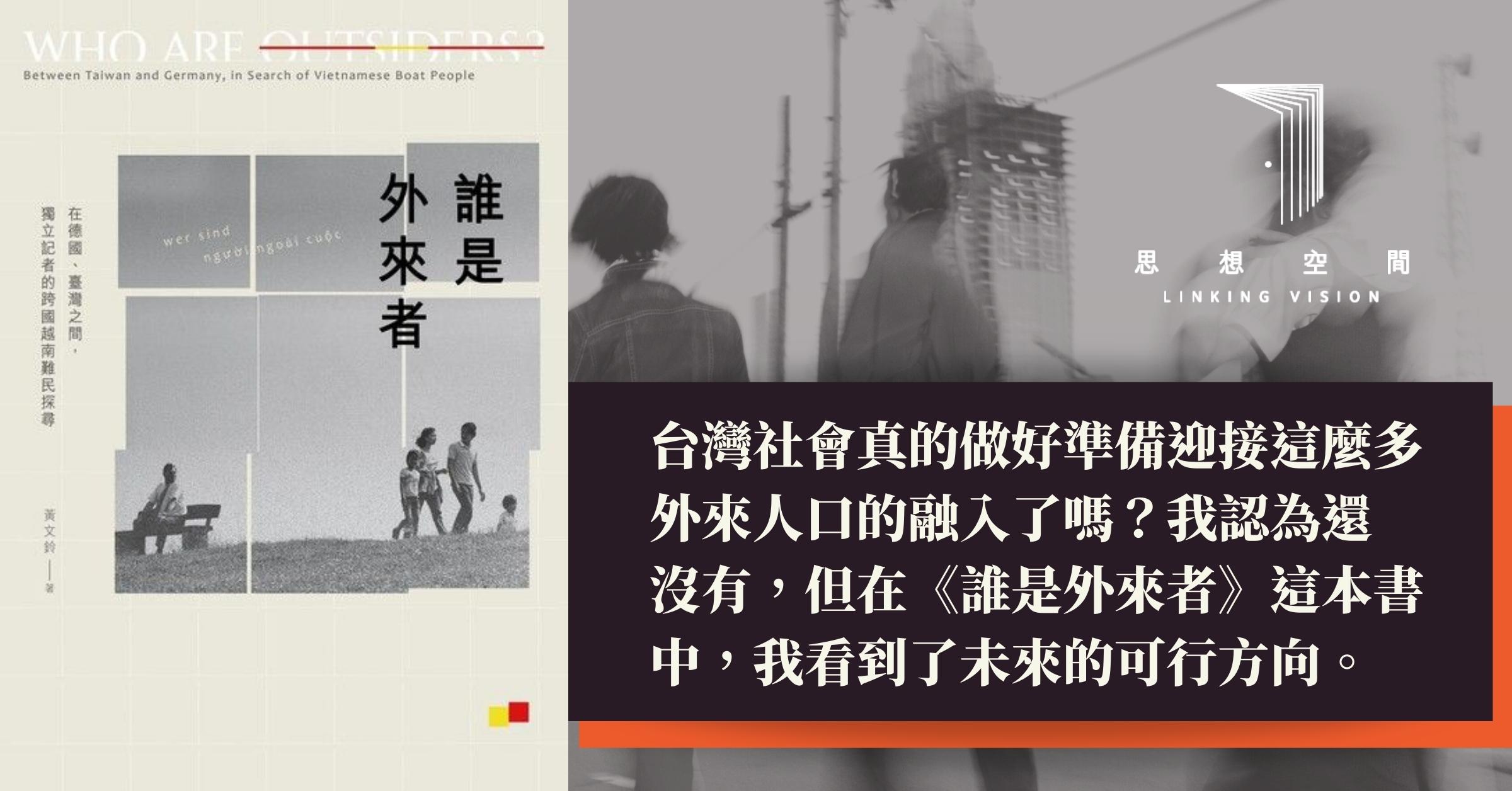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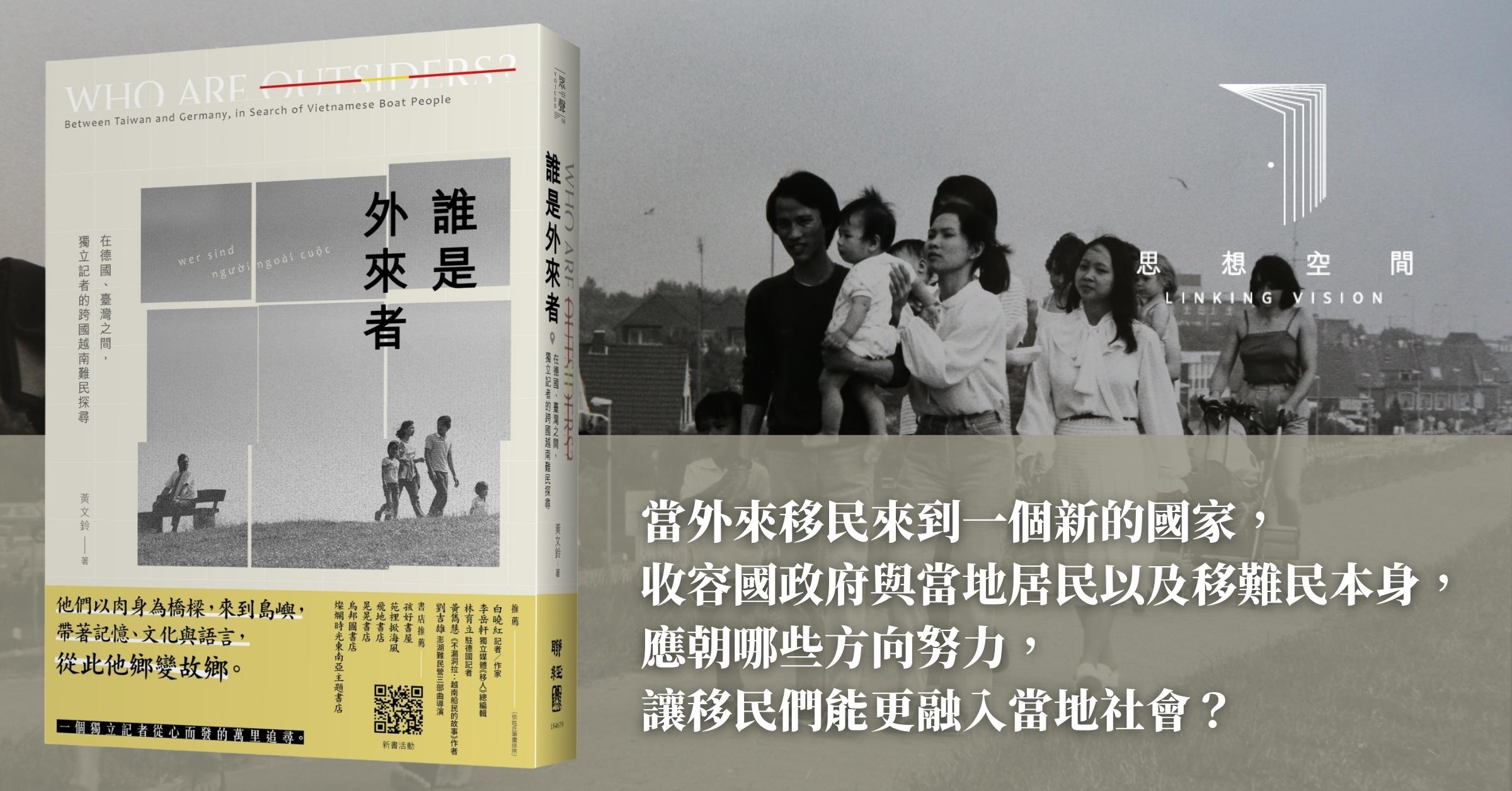
| 閱讀推薦 |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