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f(思想空間專欄作家)
當從社交媒體中得悉,有本名叫《根莖葉花——花墟的記憶與想像》(下稱《根》)面世,不禁興起了「花墟有乜好寫」(註:花墟有什麼好寫的)的好奇。後來了解到這書原來是由位於花墟商廈11樓的獨立書店「閱讀時代」所策劃,讓我進一步對這書產生興趣。畢竟「閱讀時代」乃香港近年新一波獨立書店運動中其中重要一員,以歷史、社科類書籍為主打座落於讓人意想不到的花墟,令人印象深刻。

在1860年清朝割讓九龍半島以後,西人開始住到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華界內的村落便開始有人嘗試以種花謀生,慢慢發展出在界限街附近定期交易鮮花的墟市⋯⋯
我對花墟一帶最早的記憶,來自於高中年代與一眾喜愛足球的「波友」(註:球友),相約從新界西坐巴士出旺角大球場觀看本地足球聯賽。作為「新界牛」的我們在沒有網絡的年代,只能從《香港街道圖》中記下要去旺角大球場,要坐巴士到界限街下車再走過去的路線,但我們對界限街把九龍與新九龍分割開來的歷史卻是如斯懵懂。九十年代尾的香港足球已經相當低迷,我還記得與友人進入只得小貓三四隻的旺角大球場,坐在尚未翻新的石屎看台(註:混凝土看台)觀看不大激烈的比賽,學著阿叔們高叫著髒話。坐位下突然傳來水聲及肥皂的香味,才意識到原來看台下為球員更衣室,完成上場賽事的球員正在沐浴。那是一段青春、不知地厚天高的時光。
我猜我與大部份香港人都一樣,雖然知道花墟一帶有很多園藝店,偶爾會去那裡走走、買點小盆栽,又或於農曆年時去那邊找點平宜抵買(註:物美價廉)的年花,但對那裡的認識也就僅限於此。經歷2019年的社運後,我們自然也更記得花墟毗鄰旺角警署和港鐵太子站,這大概也是為什麼當「閱讀時代」在花墟開業時,在我意識的底層留下了印記。但無論如何,如果不是讀了《根》,我大概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花墟叫花墟,為什麼花墟會座落於旺角北、界限街附近。
其實也應怪自己對花墟這名字太過掉以輕心,畢竟地名很多時正是解開歷史迷底的鑰匙。感謝《根》的爬梳,讓我終於認識到花墟於界限街一帶的出現,與英國殖民歷史有很大關聯。隨著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西人流行以鮮花裝飾家居的習慣帶動了花市。在1860年清朝割讓九龍半島以後,西人開始住到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華界內的村落便開始有人嘗試以種花謀生,慢慢發展出在界限街附近定期交易鮮花的墟市,向英界內的「消費者」售賣鮮花。
即使後來清朝進一步把界限街以北的新九龍及新界租借予英國,已建立起來的花市仍然繼續運作,只不過後來賣的可能是來自新界的鮮花,甚或到上世紀中開始售賣來自世界各地的花卉。就像「聯和墟」、「石湖墟」、「大埔墟」一樣,初期花墟只是花農定期於空地上擺賣的墟市,後來殖民政府劃出空間作批發市場,再後來則演變成今天以花墟道、園圃街及園藝街為核心,外溢至洗衣街、運動場道、花園街等花店、園藝店、花藝店琳立的片區。

花墟一帶另一突出之處,自然是由旺角大球場、界限街球場、大坑東球場、花墟球場乃至警察體育會球場所組成的一大片體育空間。
除了勾勒出花市的歷史,《根》也整理了花墟附近重要空間的演變。首先書中談到了現在仍基本保存下來的花墟唐樓群,介紹了設計這些唐樓群的比利時、法國合資的義品地產公司,建築師尹威力,以及太子道西的建設與旺角、何文田、九龍塘一帶發展之關係。除了獨特的建築外,透過不同作者的文章我們更知道那一帶唐樓群留下了不少著名文化人士的足跡,包括戰時來港的左翼文人茅盾、薩空了,戰後回港筆耕一段日子的張愛玲等。而因為新九龍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有不少電影公司與片廠運作,電影人像吳宇森、陳果、陳慶嘉等亦曾落戶花墟現存的唐樓群當中。
花墟一帶另一突出之處,自然是由旺角大球場、界限街球場、大坑東球場、花墟球場乃至警察體育會球場所組成的一大遍體育空間。根據書中文章所示,足球運動於香港先於港島興起,隨著城市發展於上世紀5、60年代開始在九龍落地生根。因為市民缺乏文娛康樂也好,因為港英政府需要利用足球來吸納(或消耗)從石硤尾一直向北延展至白田、長沙灣、向東則蔓延至九龍城、黃大仙一帶的年青人也好,當時的花墟球場(現在已變回警察體育會、不對外開放)便成了萬千年輕人觀看甲組足球聯賽大戰、揮灑青春的場地。雖然今天香港本地足球已不復當年勇,唯界限街南北這篇「波地」(註:踢球的地方),仍然是九龍區居民難得享有的一篇開闊空間。
此外,《根》也呈現了花墟社區內不同人物的面貌。書中收入不同的訪談,包括專營白事的花藝店店主、探索新式插花的藝術家、花農、街頭報攤攤販等,讓讀者能超越日常由買賣、逛街構築起來對花墟的認識,透過在花墟打拼、營生的人物的生活中去感受這地方。除了訪問與散文外,書中也收入了多篇小說創作,讓讀者透過梁莉姿、黃怡、盧卓倫等作者的故事作品,進入由創作所構建出來的小說花墟中,從不同的維度與故事人物來體味花墟以至我城。


他們建立了社區連結(比如和街坊的訪談),整理了這片地方不被重視的歷史,並透過散文、小說的創作匯聚了作者們對花墟的認識與想像。
在序言中,「閱讀時代」的執筆人表示當初生起編輯這書的想法,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發現關於香港的出版太少,書店內賣的主要是台版書,故想出版一本以花墟為座標的作品。雖然要出版更多香港作品的志向讓人敬佩,惟這並不意味著「閱讀時代」就要從花墟入手來編書,比如我們完全能想像他們可出一本與閱讀相關的書籍。我認為《根》的出版,與香港近年扎根社區、地方營造(place-making)的思潮不無相關。
與一些售賣懷舊情懷的作品,又或由學者所執筆的掌故或歷史研究不一樣,「閱讀時代」作為初到花墟貴境的社區新丁,《根》的出版更像是一個複合的過程。在其中,他們建立了社區連結(比如和街坊的訪談),整理了這片地方不被重視的歷史,並透過散文、小說的創作匯聚了作者們對花墟的認識與想像。在某個意義上,《根》的出版界定了、充實了「花墟」的意涵。是故,《根》不只是純粹的文藝創作,而更像是一個營造地方的實踐與行動。除了《根》外,我也注意到文化團隊「土家」前年出版的《光榮結業:告別土瓜灣小店》以及「影行者」今年出版的《百工百業:我們與小店的相遇手記》,都明顯帶著行動與記錄相結合的意味,反映了香港在書寫地方的一個小潮流。這種書寫也讓我回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黃幡翻飛處》、《推土機前種花》、《菜園留覆往來人》等嘗試,這些書寫與行動記載了香港在社區保育、地方營造已走過的道路。
關於地方營造,不管是日本、台灣還是香港近年都有不同的探討。同時我也注意到身在德國的人類學家項飆近年在中國大陸引起一片關於「附近」的討論,建議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從身邊500米開始建立與社區的連結,以作為對當代社會的一㮔回應。香港政府剛宣佈油麻地旺角的重建研究,竟味著花墟在下一輪的都市更新正面臨不可預知的衝擊。雖然各地地方營造的倡議、探討與實踐源起於不同的社會脈絡,但發展巨輪對社區、城市空間、草根庶民的影響與踐踏卻是普遍的現像。也許透過類似《根》的書寫與傳播,我們能帶動起各地更多的交流互動,促進彼此的理解,刺激大家的想像,為彼此在地的行動找到新的靈感與方向。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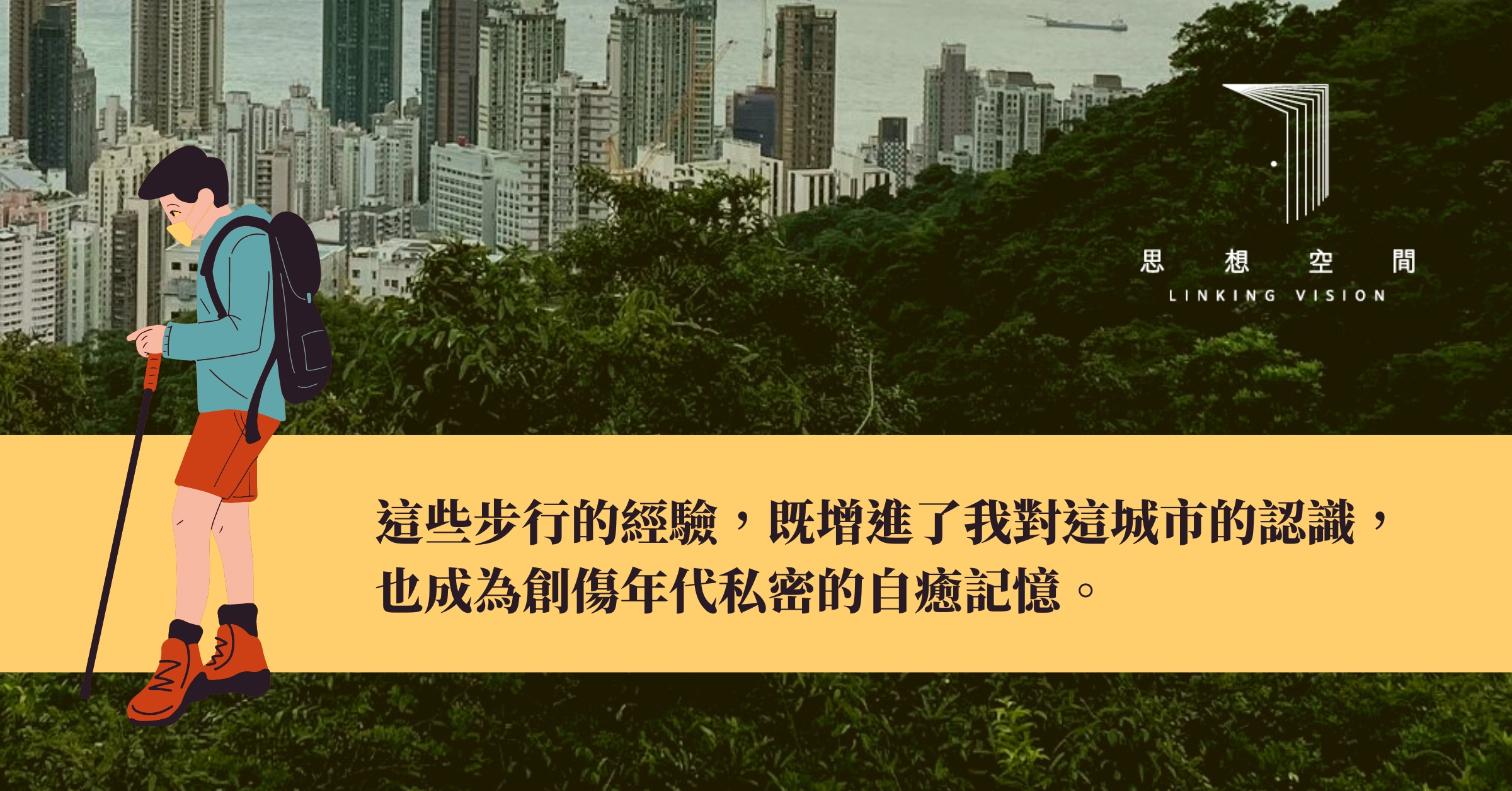
【鴨巴甸讀書札記】近在咫尺的文化與自然:讀《感知西半山——就是自然》

【鴨巴甸讀書札記】來自過去的時間囊:《一道門》與變幻中的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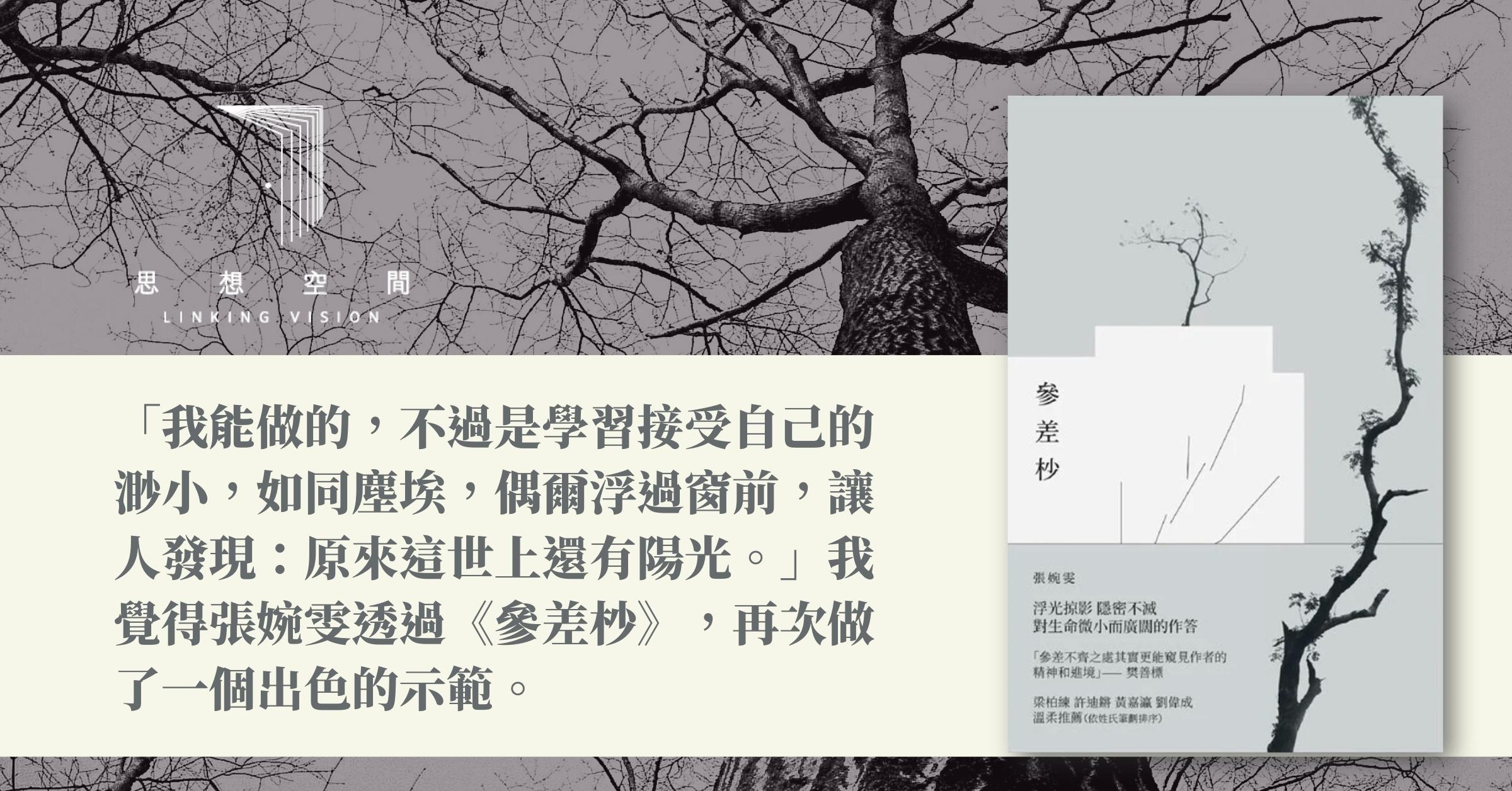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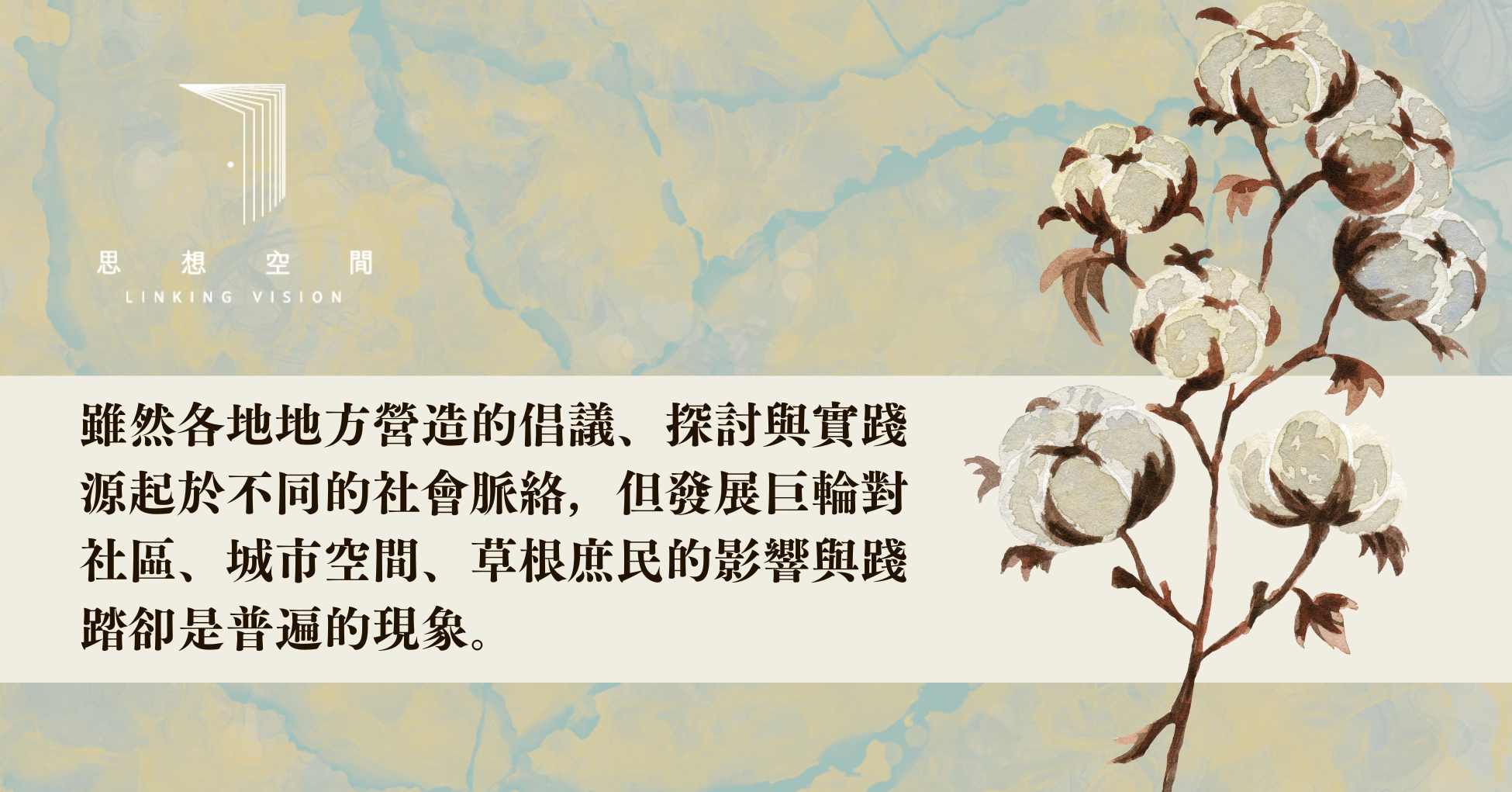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