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生於杭州,是所謂的「共和國同齡人」。《河殤》總撰稿人。1989年,40歲,64後被迫離鄉,生命經歷第一次斷裂;1993那年與妻子傅莉在美國同遭車禍,生命第二次斷裂。遭逢比他人更跌宕離奇的人生哀樂,筆下內化為比他人更沉鬱的感悟情采。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1989-2019)》、《西齋深巷》、《瘟世間》等著作。

文/蘇曉康(作家)
編按:2022年11月22日,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先生過世,享壽88歲。林毓生是研究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著名學者,1934年8月出生於中國瀋陽,後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1960年起,林先生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受思想家海耶克(F. A. Hayek)親自指導和影響,對自由主義在中國前途的討論提出以往中文世界從未觸碰到的關鍵議題。作家蘇曉康在1989年流亡海外之後,常與林先生聊天、分享見解。先生逝世,蘇曉康亦分享撰寫新書中的篇章,以懷念過去的交往點滴、以及林先生一輩人的思考與潛移默化的影響。(* 本文經授權轉自作者臉書專頁)
【作者按:剛剛張淑伶從電報上轉給我中央社的新聞,林毓生教授辭世。我自從八九年流亡海外以來,常跟林教授聊天、開會,也有文字往來,他是我吸吮自由主義理論的一個來源,而那是一股直接來自哈耶克的源頭活水。我們最後一次聊天,是二〇一一年底,十年前了,我只知道林先生晚年頗有病苦,也離開了威斯康辛,踪影全無,其實那時他就隱退了這個痛苦的世界。作為一個思想史家,他是帶著對中國的失望,可能還有憤怒而離開的,另一位思想史家余英時教授,我猜也是如此。他們這一代學人,一生以破解中國近現代落後、激進,墜入超常集權以及其解道為志業,最後看到的是一個最壞的中國,其悲涼痛苦可想而知。我手頭正在撰寫的一本新書,臨時找出其中一段文字,以紀念林毓生先生。】
清晨雲霧未散,如海如濤,山頂竟有一座藏傳佛教寺廟,隱隱傳出鐘聲,優美無以言喻。進寺歇息,只見一個喇嘛,径自誦經擊鐘,旁若無人。山頂一寺一喇嘛,還有比這裡更香格里拉的嗎?況且這既不在西藏,也不在印度,而是在歐洲的心臟日內瓦。2011年底我飛到歐洲日內瓦,因我參與的一個人權組織,在那裡辦培訓班。
「你不留一個電話號碼,我能找你?」
臨行前傅莉嘟囔了一句。我哪裡會有日內瓦的一個號碼?可是在她,我可能真的會一去不復返,叫她上哪兒找我去?我在費城機場,起飛前就用iPad 上網,再安慰她一番。她很緊張,不願意我走,最後還是放手了。我只去五天,飛躍大西洋抵達倫敦希思機場,不能上網聯絡她,很焦急,好在一個小時就飛抵日內瓦,趕到旅館就上網叫她,叫了好一陣子,她才上來,說美國已是早晨,她要去弄早飯了。
日內瓦瀕臨一湖,素有歐洲「西湖」之稱,晚飯後大家一道散步到湖濱,夜色裡湖畔很有西湖的味道。白天我也盡可能在附近遛遛。拜謁日內瓦,應是我們這種流亡者的份內之事,過去沒有機緣。我特別找到國際難民總署,一棟藍色大廈,讓我倍感親切,我是「國家級」通緝犯,後半輩子就是靠它的政策而延續,沒有它我大概還在中國坐牢。還有國際人權服務中心(ISHR),它在聯合國附近,其廣場上有一尊巨型雕塑,是一把三隻腿的椅子,其隱喻雖關乎觸雷而斷肢,更廣泛的則是「傷殘的尊嚴」,我面對它暗暗垂淚,後悔沒帶傅莉一道來此。平時他們培訓,我也心不在焉,要溜回住宿的旅館,上網查一下傅莉可好?有時叫不應她,我就給鄰居發個電郵,央求他們打個電話給她……。

那天禮拜,日內瓦培訓班放假,我隨眾人去北郊爬山,那是與法國交界處,有一纜車可吊至山頂。學員都是來自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召集他們來這裡,可以方便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旁聽其作業流程,我也隨他們去聽過一次「反酷刑委員會」審查白俄羅斯報告,荒誕者中共竟是該委員會成員之一,而他們酷刑異議者可稱世界之最。聯合國各機構設計一套程序來監督各國執行狀況,確係一種精緻文化,只是世界紛擾野蠻不堪,其效果堪憂。
我在日內瓦遇到的這群人,都很年輕,大家說說笑笑,氣氛頗好。他們是中國第一代「人權捍衛者」,我們需要組織西方資源來培訓他們,以育苗培植人權意識於中國貧瘠土壤,這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一件事情。我對他們說:
「大家都知道方勵之吧?八九之前他曾在北京被警察圍追堵截,後來他跟我描繪他們當時的感覺:『就像在荒野裡被一群狼圍追』。這個形容,給我印象深極了,這其實是對八十年代的另一種寫照,通常的說法是『開放』;這種感覺今天可以擴展到國內的無數維權律師、異見知識分子、訪民,無後台的民營老闆,甚至主張復辟文革的左派們。」
那天爬山,有個西南來的小伙子,一路上跟我聊天,他剛從牢裡出來,還留著光頭,他在國內不僅熱心人權救助,還跟隨一位西藏禪師信過喇嘛教,所以給人印象樸質而堅韌。他跟我說,中國下一步的抗爭群體是所謂「貧二代」,農民工子弟,這一代人已經拒絕再做父母那樣的奴隸勞動(廉價勞力),也對教育、就業等多方面的歧視身份憤怒已極,這代人聚居大城市周邊,一有風吹草動便群起暴動,焚燒一切,最近的廣東增城、浙江湖州兩地騷亂皆他們所為,已成體制的心頭大患。「我要到這個群體中去生活!」他說。
我很喜歡這個男孩,他比我的兒子不長幾歲,所以我也很擔心他回去的處境,雖然我很清楚他的看法太簡單,卻也不忍心潑他冷水。他提到的這一代農民工,在中國有兩三千萬之巨,乃是塑造出一個「全球化」的廉價勞力,而剝削壓榨他們的是兩頭巨獸,中國權貴和西方資本,不要說中國,整個世界也沒有一絲力量來替他們討公道。

我從日內瓦回來不幾天,威斯康辛的林毓生教授就來電話:
「我跟余英時說,共產黨弄到今天這步田地還不垮台,那麼我讀過的所有書都算白讀了!余先生說他同意我這個說法!」
他大概是聽到最近關於中國局勢分析才給我電話的。我則跟他說了一點不一樣的分析:如今中共裡頭有危機感的,反而是所謂「紅二代」,也只有他們有「變」的能力,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都是無聲的、麻木的,底層和貧苦大眾則是「碎片化」,每年雖有幾十萬起抗議,但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除了表達憤怒之外,其他的政治意義不大。
我也提到,「紅二代」只有回到毛澤東,無論是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還是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因為從鄧小平開始搞「資本主義大躍進」,中國被貧富撕裂,而至今只有毛澤東這麼一個「思想資源」,在中國管用。
我沒有說的是,其實林先生他們一代所讀的書裡面,沒有關於今日中國的答案。他並沒有白讀。他所學到的政治判斷是:暴政只能維持於一時,經濟比較好的時候,恰好是最容易爆發革命之際。那是從法國大革命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或者說「歐洲中心」的一種看法,跟今日亞洲尤其發達之後的中國,不大相干了。林先生最後說「恐怕也只能慢慢來」,我說開放了三十年,也「西化」了三十年,毛澤東那一套還管用,這一點外面的人不懂。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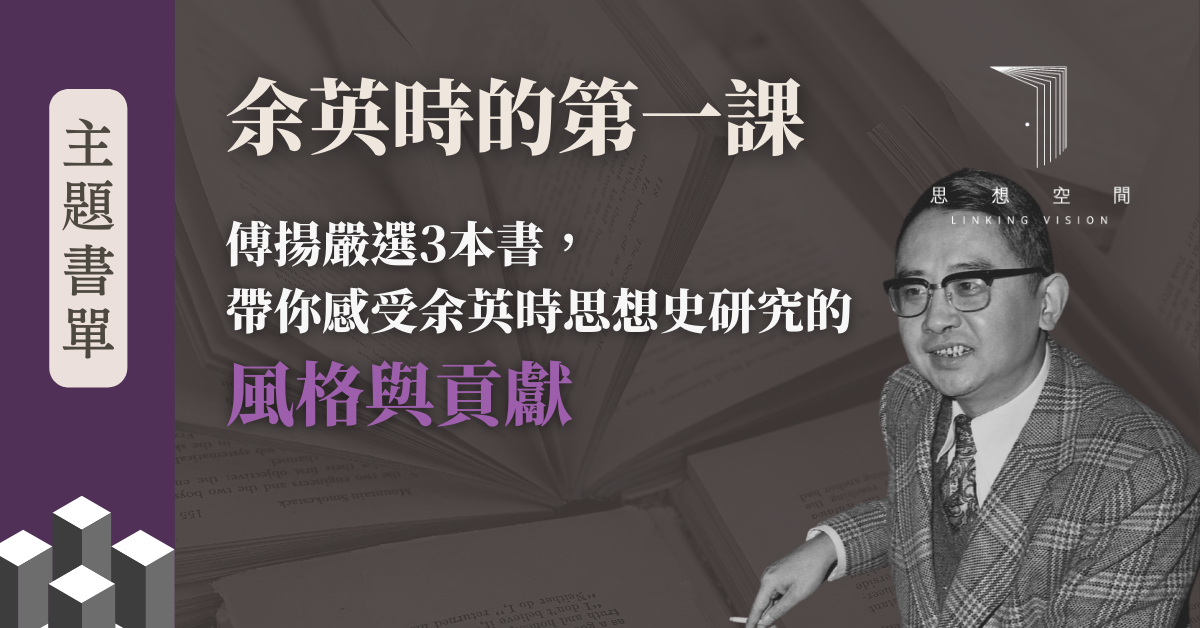

1949年生於杭州,是所謂的「共和國同齡人」。《河殤》總撰稿人。1989年,40歲,64後被迫離鄉,生命經歷第一次斷裂;1993那年與妻子傅莉在美國同遭車禍,生命第二次斷裂。遭逢比他人更跌宕離奇的人生哀樂,筆下內化為比他人更沉鬱的感悟情采。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1989-2019)》、《西齋深巷》、《瘟世間》等著作。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