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蕭公權(中國政治學與社會史家)
編按:著名政治學與社會史家蕭公權,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和蘇聯研究所教授,講授中國政治思想、中國社會制度以及中國政治思想及制度資料閱讀等課程。其著作《中國政治思想史》共五編二十五章,上起先秦,下至辛亥。從政治思想的歷史背景,可分為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與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三大部分;依政治思想的演變趨勢,則分為創造、因襲、轉變及成熟四個時期。在書中,作者也帶我們探索了兩宋時期的思想大勢,細緻分析了王安石、李覯、陳亮、葉適等思想家的理路。(* 本文摘自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三版)》第十四章〈兩宋之功利思想〉,標題為編者擬。)
宋代思想之大勢
宋太祖受周之禪,崇元即位,中原復歸統一,宇內得以粗安。此三百餘年中之政治思想可分為理學與「功利」之二大派。前者承唐代學術之餘緒而光大之,後者懲國勢之積弱而思振救之。二者均依傍孔氏而皆不守秦漢師法。故宋元兩朝可稱為儒學再度獨尊之時期,亦為儒學內容變古之時期。
理學之興,遠可溯源於韓愈、李翱,而促其成就之主要物質原因,則為佛家之心性與道家之象數學說。[1] 韓氏推尊孟子,立「道統」之說。李氏著《復性書》,[2] 取梁肅止觀統例之說以解《大學》《中庸》之言性情,[3] 其影響尤為深遠。此儒、佛合流之新儒學醞釀至宋,遂成二程朱陸之理學。兩漢以後,儒道二家早有混合之趨勢。道家要籍,每援引《周易》,[4] 而道經中本有「太極先天之圖」。[5] 宋時周敦頤、邵雍竊取陳摶舊說,加以變通,遂成理學中象數之一派。故宋之理學家雖自命繼先聖之絕學,實陰取「二氏」之異端以立門戶。惟吾人宜注意,理學得佛學之助,蔚為中國空前未有之哲學系統,而其對政治思想之貢獻則極細微。各家之哲學思想固多新穎分歧之點,其政論大旨則不外搬演《大學》《中庸》之正心誠意,孟子之尊王黜霸與乎一治一亂諸陳說而已。
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學,而在與理學相反抗之功利思想。此派之特點在斥心性之空談,究富強之實務。其代表多出江西、浙江。北宋有歐陽修、李覯、王安石,南宋有薛季宣、呂祖謙、陳傅良、陳亮、葉適等。而安石主持新法開「維新」之創局,尤為其中之巨擘。按經世致用,本為儒學之傳統目的。然先秦漢唐之儒多注重仁民愛物,休養生息之治術。一遇富強之言,即斥為申、商之霸術,不以聖人之徒相許。後漢王符、荀悅諸人雖針砭衰政,指切時要,[6] 然其所論亦不過整飭綱紀,補救廢弛諸事。積極有為之治術,固未嘗為其想像之所及。至兩宋諸子乃公然大闡功利之說,以與仁義相抗衡,相表裡,一反孟子、董生之教。此亦儒家思想之鉅變,與理學家之陰奉佛老者取徑雖殊,而同為儒學之革命運動。
儒學大變於宋,其歷史上之原因,尚不難於探索。主要者似有二端。一為時勢之背景,二為思想之背景。前者可解釋功利思想之發生,後者則兼及理學。請先論時勢。趙宋立國之初,即有契丹之患。不徒石晉所割之燕雲十六州始終不得收復,7而遼勢日盛,澶州戰後,屢增歲幣,以求苟安。西夏坐大,亦數內侵。元昊請和援例復遺歲幣。[8] 以大事小,示弱於人。此誠奇恥大辱,而當時君臣居然肯受者,殆亦深知兵弱財乏,故不得不姑忍之也。宋兵之弱,原於太祖。太祖由將士擁立以踐阼,懲於兵強之危險,乃「務弱其兵,弱其將以弱其民。」[9] 總天下之兵集之京師,「分番屯戍以捍邊圉。」又募強悍失職及凶歲饑民以入兵籍。「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10] 然而其失也,悉變雄武可用之材為媮惰文弱之卒。內不足以為亂,則外亦不足以禦侮。[11] 又況兵額日增,坐耗廩幣。[12] 積弱之兵,復為積貧之直接原因乎?宋財之乏,其由不一。曰歲幣,曰軍費,曰政費,曰糜費。皆耗巨資,有增無已。[13] 而賦役無方,民生日困。國力衰削,危亡可虞。至仁宗時其勢蓋已可覩。朝廷不能及時整頓奮發有為,反「解散天下而休息之」,[14] 真如燕巢魚呴,坐俟焚涸。於是深思遠識之士,惄焉憂之,發為富強之議,圖振萎弛苟安之習。及南渡定局,故態依然。和議或求瓦全,主戰亦乏勝算。[15] 論者懲前世之失,度當時之要,益信理國非恃空言,救亡必資實學。朱、陸一切心性仁義之說,不啻儒家之「清談」,足以致中原於淪喪而莫可挽回。永嘉、永康諸子乃大講致用功利之學以與紫陽、象山相抗。故北宋功利思想之產生,大體由於時勢之刺激。南宋則時勢之刺激更深,而兼為理學之反動。
次論思想之背景。孔子之學經孟、荀等發揚以後,其精義殆已闡露無餘。漢儒承兵燹之遺,收尋舊籍,爬梳章句,固不足預於義理之發明。董子、何君輩乃託「微言」以寓臆說,援陰陽以入孔孟。蓋為窮極之變,勢出自然。逮東京季世,其流又竭。老莊清談,竟奪名教之席。降及李唐,儒學於九死一生之後雖有復興之機,而道、佛勢盛,未獲獨尊。思想界天下三分之局面實與唐代之一統國祚相終始。且唐代為佛學全盛時期。新經大量輸入,舊經繼續進展。[16] 生氣蓬勃,大異於儒道二教之衰老委頓。道教自度不能抗佛,乃仿傚其一部分之組織與儀式。儒學不能覓得前進之坦途,乃採取佛氏心性或道家象數之哲理以解說先秦之舊籍。此仍蹈襲漢人混雜陰陽家言之故智。其不同者,陰陽為中土固有之學派,佛學為殊方傳入之宗教。其為窮極之變,則前後如一也。抑儒學雖受佛氏新血液之賜而產生理學,此混種之寧馨兒僅表現絕世之哲學天才,而對於當時實際之政治問題則缺乏創新之貢獻。於是同族弟兄大起非難,力詆其得自異族遺傳之心性諸說,別樹先儒致用之義以糾彈矯正之。矯之每有過正,遂漸近於偏激之功利主義。此所謂「有為言之」,與尋常學術門戶之爭實大異其趣也。吾人又當注意,孔孟致用,以修身為治國之先圖。功利家多置此不談,而以富強之策略為重,則雖明尊孔孟,亦為儒學變態。宋人侈言列聖相承之道統,囂囂然以傳道繼統自任。夷考其實,則儒學一變為心性,再變為功利,孔孟之道,至此真如水盡山窮,別開天地。此後許衡之徒,竊理學之唾餘以事蒙古,王守仁、李贄等縱「禪狂」以抗程、朱。滿洲假程、朱以制漢族,顏元、李𤧴復倡致用以排心性。及太平天國之起,儒學更遭嚴重威脅。儻非曾國藩扶清衛道之軍事底於成功,則二千年粉飾君政之儒術,必不免隨異族專制政權以倶盡矣。
理學與功利思想為宋代政論之兩大主流。此外尚有反對功利而不屬理學範圍之守舊思想,以及另闢宗風意近「縱橫」之蜀學,凡此皆支流別派,雖未足代表時代精神,而亦具重要之意義。本章及下章分別簡述及之,庶免偏廢之失。
理學家於南渡危亡之世,猶高談性理,欲以正心誠意為救國之方,可謂不達時務。而李氏於仁宗承平之時,已先覩內憂外患之可危。
李覯(1009-1059)
兩宋之功利思想雖以王安石為中堅,而致用之風氣則歐陽修倡之於先,李覯廣之於後。李氏之勳名遠遜荊公,其立言之富有條理,則有過之。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生於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卒於仁宗嘉祐四年。俊辨能文,舉制科不中,以教授自資。後范仲淹薦授太學助教升任說書。[17] 所著有《潛書》十五篇,[18]《禮論》七篇,[19]《平土書》二十則,[20]《廣潛書》、[21]《富國》、《強兵》、《安民策》三十篇,[22]《慶曆民言》三十篇,[23]《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常語》三卷等,[24] 今俱保存無失。
歐陽修謂「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又謂「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事而及焉,非為性言也。」[25] 李氏根本上同情於此態度,而其譏彈宋初儒者參合佛老,極研心性,放言象數之學風,則尤為直率中肯。如《易論》云:「聖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競習異端。有曰我明其象,猶卜筮之書,未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則釋老之學未為荒也。晝讀夜思,疲心於無用之說,其以惑也,不亦宜乎?」蓋《易》之為教不在天道性命而在人倫世用。「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萬事之理,猶輻之於輪,靡不在其中矣。」[26] 夫《易》之一書,世儒視為六經中玄妙之尤,而自李氏觀之,猶不離乎致用,則其他聖人之言,必非無用,可不俟辨矣。抑又有進者,聖人雖言性命,其言之也亦不離乎人事之實際。李氏謂「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於善也。觀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則知天之命。」性命之理如此。「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導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27] 豈須探玄入眇,端坐屏息,如理學家之所為乎?
致用之說既明,李氏復大闡功利以矯俗儒。自孟子以來,[28] 儒者承其遺教,多以言利為恥。李氏一反其風,以為聖人無不言利者。覯謂「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29] 蓋人生而有欲。非利無以養之。養之有節,是為仁義。李氏明之曰:「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30] 理學家每欲以天理壓人欲。[31] 李氏此論,恰與相反。然而理欲之辨,卒占上風,宋明儒學,幾乎全部受其影響。至清戴震始復明目張膽,伸欲以合理。[32] 殆由潮流所向,雖得李氏之明辨,亦無以挽回之歟。

孟子謂「聖人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33] 荀子謂「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霸。」[34] 後世儒者遂多嚴王霸之辨,而宋之理學家尤斤斤致意於此。李氏乃立論平反,為霸政作辨護。《常語》駁孟子黜桓、文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35] 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36] 推孔子所以亟言霸政者,實以霸政不可厚非。「儒生之論,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強國也,豈易及哉!管仲之相齊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內尊京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強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強,較之於今何如?」[37] 理學家於南渡危亡之世,猶高談性理,欲以正心誠意為救國之方,可謂不達時務。而李氏於仁宗承平之時,已先覩內憂外患之可危。曰外攘戎狄,國富兵強,較之於今何如?快哉此論,真足令腐儒結舌矣!
李氏不僅辨霸政為可取,又嘗探究昔人謬分王霸之失,而得其致誤之所在。一曰誤定王霸之區別。王霸之分,繫於君主之地位,而非由其政術有本質之上差異。《常語》曰:「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也,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王者霸者之地位既異,其職務亦遂不同。「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吾人若接受此分類之標準而以之論三代漢唐之君,則文王為霸而漢唐皆王。詩人以「王業之艱難」稱后稷先公者,「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修德,始於后稷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為此言者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38] 二曰誤認王政純用仁義。頃言王霸各有粹駁。李氏於此雖無明文詮釋,然據其「焉有仁義而不利」之言,足知粹駁之分在乎功利之大小,而不在義利之比例。昔陸賈以仁義折高祖。宣帝謂周政純用德教,而以漢家制度參雜王霸自命。李氏以為皆昧於治道與王霸之辨,乃為二詩以譏之。其一曰,「君道乾剛豈易柔,謬牽文義致優遊。高皇馬上辛勤得,總被儒生斷送休。」其二曰,「孝宣應是不知書,便謂先王似豎儒。若使周家純任德,親如管蔡忍行誅。」[39] 王政不純於仁義,則前人一切粹駁之分皆不可持矣。抑又有進者,俗儒以仲尼之徒自命,而實皆貌襲仁義之陳言,志在干祿[40] 而學無足用。「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41] 彼放言道統者其亦知愧乎。
李氏破毀俗儒之說,略如上述。其積極之建設理論,大旨為孟子之民本而參以荀子之禮治。此雖因襲前人,而其富有條理,注重實際之特色,則為前所罕有。
李氏認安民為君主之天職,亦即政治之目的。其言曰:「愚觀書至於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為民立君而不能為天養民。立君者天也,養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為億萬人也。民之所歸,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42] 養民與否,可決君位之安危,亦可定君品之上下,世人知三代卑漢唐,而每不能舉正確之理由。實則其事甚明。「古之天下,君養民也。後之天下,民自養也。」[43] 君至於不養其民,已失職矣。若更加以暴虐,則其罪彌大。「生民病傷,四海寃叫。湯武之為臣,不得以其斧鉞私於桀紂。」44夫生民至重,一夫可誅,則是富國強兵,興利圖霸之目的,皆在安民而不在尊君。此李氏之功利思想所以究竟屬於儒家而非商、韓之學也。[45]
李氏論禮,大較合於荀卿。其主要相異之點在棄性惡而主性善,且以禮為仁義智信及樂刑政之總和。李氏謂人受命於天,則其性善。[46] 聖人「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47] 則禮由此起。「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持是論者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蟲蛆,何不恭之甚也。」[48] 夫所謂人性善者,以其含仁義智信之德也。既有其德,見諸實行,而立為法制,則總名之曰禮。[49] 故仁義智信為「禮之四旨」。法制既立,又「節其和」、「行其怠」、「威其不從」,故樂、政、刑為「禮之三支」也。[50]
禮為「聖人之法制」,則禮治者以法制治天下之謂。李氏之思想雖不能全脫「人治」之覊絆,實頗傾向於法治。此亦與理學家正心修身之論相背。李氏謂「民之所從,非從君也,從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國也,守其令也。」「封彊有固,山川有險,人猶踰之。比閭小吏,執三尺之法,則老奸大豪無敢違者。是君守國不如守令也。」[51] 雖然,守令者非取法申、商,立威嚴貪戾之制。李氏深信《周禮》乃百代之典型,故其論制度,大體以此為依據。[52] 昔人斥王安石者,或謂其誤用此書以亂國,53不知李氏先已主之。假使得君執政,恐不免如王氏之舉事皆稽。熙寧中鄧潤甫上其遺集,請官其子,[54] 雖出門人之私誼,亦可知盱江學術之精神與臨川固有暗合之處矣。
安石推究宋代開國將近百年,天下未臻大治之故,以為由於祖宗雖有法度,不合於先王之意。故欲致太平,必變法度。然而人才不足,雖有良法而其效不逮於下。
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生於真宗天禧五年。少好讀書,過目終身不忘。友生曾鞏以其文示歐陽修,修大加歎服,為之延譽。慶曆二年進士第四名,簽書淮南判官。秩滿知鄞縣,興水利農貸,民受其利。嘉祐三年〈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雖館閣之命屢下,五年乃應詔直集賢院。六年,知制誥。神宗以韓維稱道,夙知其名。及即位,遽命知江寧府,數日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二月參知政事。與陳升之同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時安石年四十九。新法如農田水利、均輸、青苗、保甲、募役、經義策士、市易、保馬、方田、均稅等事先後施行。范純仁、蘇轍、韓琦、呂公著、趙抃、司馬光、富弼、文彥博等先後以沮新法貶謫。三年,加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七年四月以反對者眾,且多疾病,屢乞解機務,乃以禮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八年二月復以昭文館大學士入相,九年十月罷相判江寧府。計執國政約達九年。君臣知遇,古所稀有。元豐元年封舒國公。三年改荊國公。八年進司空。哲宗元祐元年薨,[55] 贈太傅。所著有《文集》、《三經新義》、《春秋左氏解》、《禮記要義》、《論語解》、《孟子解》、《老子注》、《字說》等約近三百卷,[56] 政治家著述之豐,亦屬罕覯。
宋人反新法者每斥王氏之學為申、商之異端。其實安石乃「儒而有為者」,[57] 排斥老莊則有之,入於申、商則未也。嘗考王氏立言,殆以人生不能自治,必待君長制臨之一假定為其出發點。安石有〈彼狂〉一詩示其政治起原之理論曰:「上古杳然無人聲。日月不忒山川平。人與鳥獸相隨行。祖孫一死十百生。萬物不給乃相兵。伏義畫法作後程。漁蟲獵獸寬群爭。勢不得已當經營。非以示世為聰明。」[58] 就此言之,則樸散為器,因立長官,乃聖人無可避免之舉動。而有為之術,亦政治之本來面目。道家者流不明此理,見後世有衰亂之政,遂謬倡無為之說以眩世惑俗,誠為有識者所當棄。王氏明之曰:「太古之人不與禽獸同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明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為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為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59] 至於老子本道之自然以論人事,其理不誣,而其應用則失當。蓋「道有本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為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60]

雖然,聖人有為者,以禮樂刑政為常道,非有取於刑名法術也。神宗嘗謂「舉官多苟且,不用心。宜嚴立法制。」安石曰:「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為吏事,非主道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化,使人自然遷善遠罪者,主道也。」[61] 本此見解,故王氏譏始皇,抑霸政,斥煩擾。其抑霸政也,謂王霸同用仁義禮信之道而其心異。「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62] 惟其心異,故霸者有惠而不廣。孟子謂「五霸假之。」安石此論,意旨略與相同。至於煩擾之失,亦在操切而寡效。安石謂「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法令誥誡之間。」[63] 然而猶有不服教者,雖加刑殺,終不可止。凡此所言,亦無殊於正統之儒術。抑吾人又當注意,自孔孟以來,儒者皆重禮樂而不廢刑政。王氏本之,為〈三不欺論〉。[64] 其大旨在說明任德、任察與任刑三者乃聖人所兼有,不可偏廢。蓋「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65] 故以堯之德化比屋可封,猶察驩兜舉丹朱之誣,戮四罪而天下咸服。徒主一端之不足為治,彰然不待辨矣。
吾人上述王氏學術之宗派如尚非誤,則可知安石之異於俗儒者在其具「有為」之精神,復本此精神以講求有為之方法,實行有為之政策。而此政策之表現即為熙寧之新法。新法之內容,非本書所能討論。然究其歷史上之意義則至為重大。蓋新法者,中國專制天下繼體君主第一次大規模之變法維新,先於光緒戊戌者逾八百年,而康梁變法,不過百日,安石執政,幾及九年。反對者雖極口譏詆,終加破壞,然平心論之,其成績實未可厚非。元豐之世,物阜民康,[66] 雖蘇軾亦自悔昔日攻擊之孟浪,[67] 則亦遠過於戊戌之效果矣。
王氏超邁俗儒,特點有二。一為其堅定積極之態度,[68] 一為其切實詳盡之計畫。攻新法者或謂王氏迷信《周禮》以誤國。安石雖推崇此書,[69] 偶引之以自作辨護,[70] 然既非墨守六官之文,[71] 且明斥拘古之失,至謂「古之人以是為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為天下之害莫大。」[72] 以如此主張變法之人而謂其尊奉六官,一一緣襲,其誰肯信之乎?蓋王氏新法雖非出於憑空之創造,然其立也,或變通前人之成法,[73] 或依據前此之經驗,或應付當前之需要,誠不失為抗流振習之新政。不獨異於兩宋一般士大夫因循苟且之政策,即後漢崔實、王符輩補䘺救衰之說,[74] 亦不可與之相提並論。良以安石深知宋勢久積危弱,非根本上整頓刷新之,不足以見效有為。[75] 故有變法之舉,先之以老謀深算之擘畫,繼之以徹頭徹尾之行動。即以此論,已足與於大政治家之林而無愧矣。
安石治術之綱領見於嘉祐三年之〈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熙寧元年〈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乞制置三司條例司〉(二年),〈乞改科條制劄子〉(二年),〈上五事劄子〉(五年)等。[76] 吾人請略述為新法基本之教育政策及新法主幹之理財政策兩端。
安石以變法救貧弱,雖注重制度,而始終認人才為根本。〈上仁宗書〉洋洋萬言,所論實不過陶冶人才一事。考其立論,誠明確而不可易。安石推究宋代開國將近百年,天下未臻大治之故,以為由於祖宗雖有法度,不合於先王之意。故欲致太平,必變法度。然而人才不足,雖有良法而其效不逮於下。足見陶冶人才乃富強之先決條件矣。此後與神宗問對亦本此一貫之見解,再三申論教育之需要。如熙寧二年安石與上論天下事謂「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之臣,庸人則安習故常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效功,早為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能麤有所成。」[77] 如此云云,不啻後此新法遭受阻撓之預言。惜乎神宗求治過急,不能盡納安石之主張,以至新法既行,攻之者自命為君子而擁之者又每多小人,遂至橫生枝節,不能得一徹底試驗之機會也。
王氏理想之教育制度,為封建天下之庠序學校。[78] 執政之後乃略師其意,擴充京師諸路州府之學。其教育之方針則為培養致用之人才。王氏認以文章取士,「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79] 於是改科舉、罷詩賦,設武、律、醫諸學。[80] 然而限於歷史之環境,教育之方針雖變,仍未有新創之教材而不得不以經義取士。且士子習於聲病對偶之文,一朝廢之,頓失所憑,其怨憤不平心,殆所難免。蘇軾之異議,不啻為此儕申辯。[81] 新法反對者眾,此或原因之一。
安石理財諸政,當時攻之者尤力,以為聚斂貪求,與民爭利。[82] 然而新法之最後目的雖在立富強之基以禦外侮,[83] 自安石視之,則理財為養民之要圖,亦即富強之根本。其用心實大異於商君、桑大夫之流,徒欲取民以資國,而未嘗一計黔首自身之福利。故青苗、均輸、市易、農田水利諸制皆以增加生產、減輕負擔、抑制豪強為目的。而青苗一法,行之於鄞而民受其利,尤足證安石之言利,乃欲生萬民之利,奪豪民之利,並非與民爭利。其政策之真精神,以今語舉之,殆近於所謂「統制經濟」;方之古人,則略似管子之「輕重」。安石曰:「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與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84] 又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85] 人主苟欲復操大柄,均平天下,「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貨賄,不通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聚斂之權不可以無術」矣。 [86] 新法之內容,以現代之眼光論之,容有不盡合用之處。至其裁抑豪強之政策,則原則上無可訾議。其所以終難施行者,殆由其精神既與中國傳統之放任習慣相反,又大違士大夫既得之利益,[87] 遂不免備受多方之攻擊。加以有統制之政策而無適當之人才與機構以推行之,[88] 其遭失敗,誠亦勢之必然。所可異者,安石竟能持之至八年之久,而大部見之事實耳。抑又有進者,據現有文獻推之,似神宗較注意於攘外,安石較注意於安內,而欲以定民生為充國力之基礎。故神宗急於求功,而安石務從根本著手。世徒稱熙豐知遇,古今鮮有,而孰知君臣之間尚未有完全一致之主張與觀點乎!
[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二編第十章及十一章。
[2] 《李習之全集》,四部叢刊本。
[3] 《大藏經》卷四六。《李習之全集》卷一,〈感知己賦〉謂嘗受知於梁肅。
[4] 如道教之「丹經王」《周易參同契》。《道藏》六二八冊。
[5]《道藏》一九六冊《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品》。《宋史》卷四三五〈儒林傳〉朱震謂陳摶以〈先天圖〉授种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穆修以〈太極圖〉授周敦頤。又《宋元學案‧百泉學案》引黃宗炎《太極圖辯》,謂周子得陳氏〈無極圖〉,顛倒其序,附於《易經》,以為儒者秘傳。朱彛尊《曝書亭集》卷五八〈太極圖授受考〉略同。
[6] 本書第九章第五節。
[7] 曹翰獻取幽州之策於太祖,趙普沮之。王夫之《宋論》卷一極言不取之失策。
[8] 仁宗慶曆二年「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納撫,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宋史》卷一七九〈食貨下一〉)
[9] 梁啟超《王荊公》(《飲冰室合集》專集卷二十七),頁11。
[10]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序〉。
[11]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二五〈宋軍律之弛〉。
[12]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開寶兵籍三十七萬八千,至道六十六萬六千,天禧九十一萬二千,慶曆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七十年間兵額幾增四倍。
[13] 《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至道末歲入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至天禧約增七倍。歲出略相當。嘉祐治平時則歲出不敷恒二千餘萬。所謂糜費如宗室食祿、郊祀賞賚、東封、祀汾、明堂等費少者五百萬,多至千二百萬。
[14] 《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15] 王夫之《宋論》卷六。章兗《王荊公集‧後序》論北宋局勢極明,可閱。
[16] 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六章第三節。《舊唐書》卷一九一〈僧玄奘傳〉,玄奘就西域得梵經六百五十七部。律、淨土、俱舍、天臺、華嚴諸宗皆起六朝而盛於唐。法相、真言二宗均唐代初入中土。
[17] 《宋史》卷四三二〈儒林傳二〉,《宋元學案》卷三〈高平學案附案〉,《胡適文存》二集卷一記李覯學說,《李先生集‧附年譜》。
[18] 仁宗天聖九年作,時覯年二十三。
[19] 明道元年作,覯年二十四。
[20] 景祐三年作,覯年二十八。
[21] 寶元元年作。覯年三十。
[22] 寶元二年作。
[23] 慶曆三年作,覯年三十五。
[24] 皇祐五年作,覯年四十五。以上諸書均收入《盱江文集》三十七卷,盱江書院刻本,及《直講李先生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附《年譜》一卷,四部叢刊影明刻本。
[25] 《居士集》卷四七〈答李詡第二書〉。
[26] 〈易論一〉。按論凡十三篇,大體就卦爻以明人事,如君道(一),任人(二),臣道(三)尤著。
[27] 〈刪定易圖序論六〉。
[28] 李氏不喜孟子,常語中屢駁之。此與理學奉孟子為正統者相背。
[29] 〈富國策第一〉。
[30] 原文。
[31] 朱熹其尤著者。嘗謂「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語類》卷十二。
[32] 〈原善〉三篇(《文集》及《遺書》本,文小異),緒言及《孟子字義疏證》。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24-355。
[33] 《孟子‧梁惠王上》。參閱本書第三章第三節。
[34] 《荀子‧仲尼七》。
[35] 舊說衛人美齊桓公之詩。
[36] 《常語上》。
[37] 〈寄上范參政書〉。
[38] 《常語下》。
[39] 〈元紀〉二首。
[40] 〈閔俗〉詩為誅心之論曰:「君門若無祿,陳編孰能讀。公庭若無法,穢德誰不足。煦煦儒者口,沉沉小人腹。」
[41] 《潛書》。
[42] 〈安民策第一〉。
[43] 《潛書》。
[44] 《潛書》。《常語上》謂「君何可廢也」,與此不合。《安民策第六》亦反對聽民之說。
[45] 本書第六章第二節。
[46] 《廣潛書》。
[47] 《禮論第一》。
[48] 與胡先生書。此駁胡瑗〈原理篇〉。然《安民策第八》謂「夫物生有類,類則有群,群則相爭,爭則相害。(中略)不有王者作,人之相食且盡矣。」則又襲荀子性惡之意。
[49] 《禮論》第四、五。參《禮論第三》。
[50] 《禮論一》。
[51] 《安民策第六》。
[52]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乃李氏治術總綱,〈安民〉、〈富國〉、〈強兵〉諸策及《平土書》則其分論之一部份也。其要目有內治、教道、國用、官人、軍衛、刑禁等項。
[53] 《文獻通考》卷八一,《經籍考》卷八引晁公武語。王氏非墨守《周官》,詳下。
[54] 《宋史》卷四三二〈儒林傳二〉。鄧由王薦引,熙寧中官知諫院,知制誥,御史中丞。嘗上書為新法辯護,攻排舊黨。
[55] 《宋史》卷三二七本傳。曾鞏《元豐類稿‧王公墓誌銘》。舊記多不足信。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楊希閔《王文公年譜考略節要》,推論《熙豐知遇錄》(北平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排印本)辨正甚詳,為不可少之參考書。梁啟超《王荊公》(《飲冰室專集》卷二七)亦便參考。專述新法者有熊公哲《王安石政略》(河南省政府排印)。述學術者有《宋元學案》卷九七〈荊公新學案〉。
[56] 《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分傳共只一百卷,為元金谿危素所輯,非其舊也(梁啟超《王荊公》,頁192)。今以四部叢刊影明本為善。又《拾遺》一卷,羅振玉輯「宣統十年」排印本。《三經》中《周官新義》二十二卷為王氏手著。今存十六卷,附〈考工記〉一卷(錢氏刊經苑本)。《詩經新義》二十卷及《書經新義》十三卷(此二義為王雩及門人著,今均佚),《洪範傳》一卷(今存集中),《春秋左氏解》十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義》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卷,《老子注》二卷,《字說》二十四卷(此上均佚)。此外有《唐百家詩選》二十卷,有疑非王手者。
[57] 明鄒元標〈崇儒書院記〉,《年譜考略》卷首之二引。又陸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謂安石「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乃為伊周,公之志也。」則竟以王氏為正統矣。
[58] 《集》卷十。《集》卷十三〈秃山詩〉曰:「吏役滄海上,瞻山一停舟。怪此秃誰使,鄉人語其由。一狙山上鳴,一狙從之遊。相匹乃生子,子眾孫還稠。山中草木盛,根實始易求。攀挽上極高,屈指亦窮幽。眾狙各豐肥,山乃盡侵牟。攘爭取一飽,豈暇議藏收。大狙尚自苦,小狙亦已愁。稍稍受咋囓,一毛不得留。狙雖巧過人,不善操鋤耰。所嗜在果穀,得之常似偷。嗟此海山中,四顧無所投。生生未云已,歲晚將安謀。」意尤明切。
[59] 〈太古〉,《集》卷六九。
[60] 〈老子〉,《集》卷六八。此文作於元豐六年,時安石致仕已七年。司馬光熙寧三年〈與王介甫書〉引老子言,安石非老,或有所指歟。
[61] 楊仲良《通鑑長篇紀事本末》卷五九。事在熙寧五年二月。
[62] 《集》卷九〈秦始皇詩〉曰:「勒石頌功德,群臣助驕矜。舉世不讀《易》,但以刑名稱。」
[63] 〈王霸論〉,《集》卷六七。
[64] 〈原教〉,《集》卷六九。
[65] 《集》卷六七。
[66] 梁著《王荊公》第十五章。
[67] 〈與滕達道書〉云:「吾儕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68] 《宋史》本傳謂其「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為謗書,卻近事實。《集》卷七三〈答司馬諫議書〉謂「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足相印證。
[69] 《周官新義‧序》,《經苑》第九冊。
[70] 熙寧三年〈答曾公立書〉謂「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集》卷六七。
[71] 如《集》卷六三〈諫官論〉駁地官司徒之屬有師氏、保氏,以為周公嘗為師,召公嘗為保,非大夫之秩。又如《集》卷七○〈復讎解〉辨復讎非周公之制。
[72] 《集》卷六七〈非禮之禮〉。文中又謂「天下之事,其為變豈一乎哉!」
[73] 如均輸始於漢桑弘羊,至唐劉晏而法益密。市易漢之平準也。
[74] 見本書九章五節。
[75] 《臨穿集拾遺》〈再上龔舍人書〉。又《集》卷八〈我欲往滄海詩〉,卷三九嘉祐六年〈上時政疏〉。
[76] 分見《集》卷三七、三九、四一、四二。
[77] 《通鑑長篇紀事本末》卷五九。
[78] 《集》卷四二〈乞改科條制劄子〉,卷六九〈進說〉,卷八三〈慈溪縣學記〉。
[79] 〈上神宗皇帝言事書〉。又《集》卷十〈彼狂〉及〈和王樂道詩〉、〈進士試卷詩〉。
[80] 王氏教育政策實施略見《宋史》卷一五七〈選舉志三〉。
[81] 《東坡集‧奏議集一》,熙寧四年〈議學校貢舉狀〉。
[82] 如司馬光元豐五年遺表,謂其青苗法「朘民取利。」《溫公文集》卷二。
[83] 陸佃《陶山集》卷十一,〈神宗實錄敘論〉謂帝「常惋憤,敵人倔強,久割據燕,慨然有恢復之志。聚金帛內帑,自製四言詩一章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積帛內帑,幾以募士。曾孫承之,敢忘厥志。每庫以詩一字目之,既而儲積如丘山,屋盡溢不能容,又別命置庫增廣之,賦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顛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王夫之《宋論》卷六「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指此。
[84] 《集》卷八二〈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85] 《集》卷四〈兼并詩〉。〈發廩詩〉謂「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窮主兼并。非民獨如此,為國賴以成。築台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丕忍此,願見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苦營營。」
[86] 《集》卷七○〈乞制置三司條例〉。《集》卷十〈寓言詩之四〉曰:「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此青苗、市易之理論依據,亦輕重之一術也。
[87] 神宗與近臣論免役之利,謂「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梁著《王荊公》頁84引。章袞《王臨川文集‧序》云:「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芻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趯然蹄而斷然齧。」按《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仲淹於仁宗時力求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苟安之徒反對振作,不獨於荊公為然也。
[88] 《王荊公年譜考略》卷六,〈存是樓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論青苗行於鄞縣而不行於天下曰:「一縣者公之所得自為也,故其民安。天下者非公之所得自為而必藉其人以行之。於是有貧吏蠢役乘勢以行其私。此所以不得其人則亂而為禍於天下也。」《集》卷七三〈荊公與參政王禹玉書〉謂「自念行不足以悅眾而怨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遊之厚。」《集》卷四二〈上五事劄子〉亦曰:「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王氏並非不見及此也。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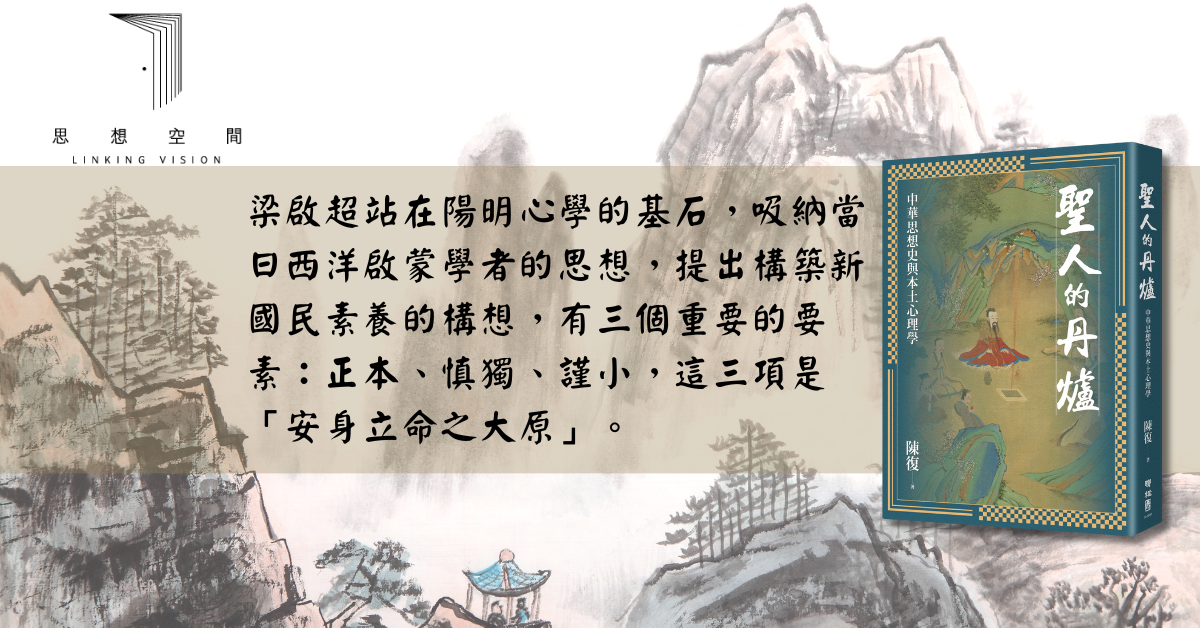
陳復:梁啟超主張新民說

【主題書單:余英時的第一課】 李顯裕嚴選3本書,帶你逐步深入余英時的思想史宇宙

【主題書單:余英時的第一課】 翁稷安嚴選5本書,帶你看到余英時思想中入世和現實一面
| 閱讀推薦 |

字恭甫,號迹園,1926年獲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導師是專精倫理學與政治學的唯心論派哲學家狄理(Frank Thilly)教授、專精美學和希臘哲學的韓莽(William Hammond)教授,以及講解形上學與英國哲學的阿爾比(Ernest Albee)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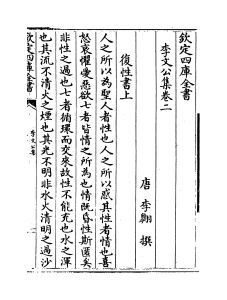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