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史所教授)
編按:2022年,中研院人社中心兼任研究員瞿宛文的最新研究論著《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面世。台灣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之時,為了徵收出租耕地要補償地主,故將公營的四大公司(水泥、紙業、工礦與農林)民營化後以其股票給付地主,做為地價補償中的三成;該書呈現了這事件的過程與其前因後果。同年5月,新書論壇——「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研討會在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舉行,並邀請了薛化元、劉瑞華、林子新、侯嘉星等學者擔任專題評論人,參與對於台灣農村土地改革的探討。(*本文原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二二期,思想空間經授權轉載。)
近年來,瞿宛文教授和她的團隊,針對台灣農村土地改革及其後續的影響,作了相當深入的持續研究,而《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重探台灣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2022)則是瞿教授最新的研究成果。瞿教授參考了既有研究成果,並以相關的史料和檔案為基礎,進一步論述,透過土地改革的政策,如何影響台灣的地主階層進行工業投資,或是促成地主階層在台灣經濟史角色的轉型。而為了促進本書相關內容的討論,特別舉行《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新書論壇,同時也將2015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重探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專題團隊的論文,與當時回應該專題論述的論文,提供給與會者參考。
基本上,有關此一研究課題雖然有不少的成果,但是特別以四大公司民營化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並將土地改革與之結合者,為數並不多。2018年莊濠賓的博士論文[1],是此一研究領域相當重要的新銳研究。誠如瞿宛文(2022:14)教授所指出的,莊濠賓的博士論文和瞿教授這本書的研究取向,不只在面向、關心點不同,而且論述的結果也有相當大的歧異,所以瞿教授認為,雖然一樣討論四大公司的民營化,莊濠賓博士和她研究的關切點、探討主題並不相同。不過,莊濠賓(2018:i)的論文提到四大公司民營化後,非經營階層的地主在台灣經濟扮演角色進一步弱化的問題,而此點與耕者有其田後原地主和工業化的關係,仍值得注意。
台灣的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的關係,是戰後台灣經濟史重要的課題,而四大公司民營化在這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相當的關注。因此,瞿教授以土地改革中股票補償政策的角度切入,討論四大公司轉為民營及其後的績效,進而探討地主階層在此一政策中受到的影響與轉型,這和過去的研究成果或是關注的方向,確能先後呼應─認為透過土地改革,特別是耕者有其田政策的轉移,和搭配地主取得四大公司的股票,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地主階層的轉型─也就是從農村的地主,轉變成為資本家或是企業的重要所有人。此種觀點雖有不少研究持不同的意見,不過在某種意義上,在1949年開始的土地改革政策,特別是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後,釋出四大公司股票作為給放領農地地主的部分補償,在歷史教育中常帶給部分學習者「透過耕者有其田,地主因而轉型企業家」的印象。
前述影響地主或是農業資本往產業發展的一般性論述,在歷史教育或研究中常被簡化,甚至放大,導致過度強調四大公司民營化與工業化的連結。與之相較,瞿教授這本書則提供了更深入分析與討論的空間。她努力蒐集了相關的檔案史料,進而更深入的論證,而且她關注的焦點還包括從政策的擬定、實施以及過程中員工面對的衝擊與問題,無論深度或是廣度,都非過去類似的論述所能相提並論。不僅如此,過去民間或是文史工作者所關心的取得股票的地主階層,在企業轉移過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問題(四大公司能直接進入取得經營權的地主終究相當有限,而辜振甫則是最常被提及的個案),以及取得股票之後,在當時社會的流通如何變現,或者是股票本身透過公司的經營,地主所得的收益問題,在瞿教授這本專書中也有相當深入的討論。就此而言,本書確實達到了瞿教授在書名小標題所揭櫫的內容:「重探台灣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
另一方面,作為系列的研究,本書延續了2015年瞿教授團隊的基本假設,認為二二八事件以後,國民黨當局和地主階層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協調,而將國民黨當局對地主階層的讓步,爭取地主階層的協力結果,呈現在土地改革的實踐上。非常榮幸個人有機會在2015年就參加《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舉辦的討論,而回應的論文後來也在瞿教授協助下,刊登於期刊上。[2]我當時也提出了和瞿教授團隊不同觀點的意見,參與討論。
基本上,筆者認為透過「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確實擠壓了農村剩餘及地主資本往產業流動。此點對促進台灣工業化的發展,有正面的意義。不過,針對瞿教授及其團隊所強調,土地改革過程中國民黨當局對地主階層的讓步(讓利),筆者認為可以再做進一步的分析。而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除了為數有限的地主/本土資本家成為四大公司,及取得政府標售以接收日產為主廠房設施企業的經營或主導階層(如董監事)外,為數更多的地主在釋出土地取得股票及實物債券補償後的狀況也值得思考。
台灣民間資本往產業投資的意願,在歷史的脈絡中,實早於土地改革政策的推動,之所以原本成效不彰,與國民黨政府接收日產之後的政策有相當程度的關係。而且透過土地改革,特別是「耕者有其田」政策,除了官方政策上宣示的減少租佃或農村的階級衝突之外,中華民國政府在落實政策時又取得了哪些資源?也有再討論的必要。
以下擬對瞿教授研究提出幾點商榷的意見,除供瞿教授參考,未來也可能再做進一步的研究討論。
回顧戰後台灣法律史的發展歷程,至少在政治改革之前,人民權益遭到不當侵害,透過行政救濟,乃至行政訴訟,能得到救濟的機率是嚴重偏低的。
一、「耕者有其田」方案中政府對地主階層讓步的問題
關於前述國民黨當局對地主階層讓步,爭取地主階層對土地改革的支持之論點,筆者在過去回應瞿教授團隊的研究時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對於國民黨當局的決策─主要是對台灣本土地主階層讓步的說法,持相對保留的態度。因為透過有關耕者有其田地主保留地政策的形成過程,參考目前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還有其他影響決策的關鍵性的因素,在瞿教授團隊的研究論述中可能相對被忽略了。就目前可知的方案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可以看到被認為是台灣地主階層意見的重要代表者─台灣省臨時省議會,其與台灣省政府研擬的土地改革地主保留地方案,呈報到行政院後,經過行政院內部的檢討、修正,再經過立法院審議完成立法的結果,地主保留地的規模不僅是維持,反而還有某種程度擴大,比起台灣省方面所提出的建議方案提高0.5倍的面積。[3]就此而言,不能忽略來自中國大陸的國民黨高層菁英,對於一旦「反攻大陸」,他們在中國大陸所有土地的所有權如何保留的問題,可能有所顧慮。時任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1967:19-21)即曾指出,國民黨當局過去在中國大陸無法有效推動土地改革的重要原因,在於政治權力的掌握者,在某種意義上也常常是大地主的代表。綜上所述,從地主保留地面積之決策改變的過程,單純視為國民黨當局對台灣地主階層讓步的意向,是有再商榷的必要。再者,此所謂地主保留地規模擴大,指的是個人地主的保留份額;相對地,沒有分割的共有地主,相較於個人地主而言,在保留地份額部分幾乎完全遭到忽視(〈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1953年1月26日;莊濠賓2018:6)。政府在1952年初步完成地籍總歸戶的統計工作,但並未清查分別共有的土地。其後,台灣省政府提出「台灣省扶植自耕農條例」草案後,臨時省議會慎重其事,先徵求各縣市議會的意見,再提出了修正版本,其中除了希望擴大地主保留地的面積、提高徵收土地的補償金(瞿宛文2022:21),也提出將共有出租耕地一律徵收一項刪除。不過,國民黨當局擔心影響徵收面積(共有地主的土地即佔徵收面積的69.5%),仍堅持對共有地主的土地全數徵收,更在草案條文中明定1952年4月1日以後的耕地移轉,除幾項特殊情形例外(一、耕地因繼承而移轉者;二、本條例施行前,耕地因法院之判決而移轉者;三、耕地已由現耕農民承購者。四、耕地經政府依法徵收者),一律視為未移轉,使共有地的地主完全無法事前保全其應有權益,而且公私共有的私人耕地也全數被徵收。莊濠賓(2018:68-76、284)便認為,此為國家在推行土改過程中,枉顧地主權益的例證。
特別必須注意的是,「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時,發生了部分地主產權遭到不當侵害的爭議案件,有土地被不當徵收、放領的地主提起民事訴訟,並且法院判決應將土地產權返還給原地主。政府則透過大法官會議解釋,禁止土地被不當徵收的人民對政府提起民事訴訟,且法院已作成之判決無效。[4]就形式上而言,該解釋似乎是要求權益受損的地主透過行政救濟的程序來維護其權益,但回顧戰後台灣法律史的發展歷程,至少在政治改革之前,人民權益遭到不當侵害,透過行政救濟,乃至行政訴訟,能得到救濟的機率是嚴重偏低的。
以四大公司資產重估,進行股票或資本額擴張,再支付給釋出土地的地主階層,此次資產重估的合理與否,是攸關本政策的重大課題。
二、證券市場機制與地主階層對股票與實物債券的偏好
其次,有關當時地主在股票與實物債券之間傾向選擇股票,瞿教授的研究認為,這是因為省市議員等民意代表比較了解政府工業化的政策,所以他們選擇希望拿到更多的股票(2022:84)。其實,台灣的地主階層原本就對投資事業有一定的興趣,呼籲政府將接收的日產盡量開放企業民營(瞿宛文2022:42),這樣的訴求自二二八事件以來即有,與土地改革沒有關係。1947年3月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處理大綱,即要求「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處委會闡明事件真相〉1947年3月8日)。台灣工業發展始於日治時期,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中國作家蕭乾來台灣旅遊、觀察,注意到日本人在台灣留下良好的工業基礎,寫下「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煙」(蕭乾1947年1月7日)這樣的記事,顯示出台灣戰後初期政府接收日產後,出現工業經營不善、生產停滯的狀況。
而要求政府標售日產給民間經營,更是土地改革之前台灣擁有投資資金的菁英(當然其中也有不少地主)的訴求,縱使沒有「耕者有其田」政策釋出公營企業,他們也早就有心投入經營。
此外,既有研究也有人認為:一般居於鄉村的中小地主較鍾愛實物債券,而居於都市之地主,則因較具投資心態,傾向選擇股票(莊濠賓2018:172)。另一方面,對具有投資心態的地主而言,實物債券有其期限性,股票如有效經營在形式上則相對有其將來性。不過,政府後來將四大公司資產重估、擴張資本,透過補償土地價款的股票比例和增加數倍的四大公司股票,就足以支付給地主的補償,也就不願再釋出原本納入開放民營名單內營運狀況較佳的台肥公司(薛化元2015a:186-187;范心仁1953)。
以四大公司資產重估,進行股票或資本額擴張,再支付給釋出土地的地主階層,此次資產重估的合理與否,是攸關本政策的重大課題。而且不僅是資產重估,股票定價與資產淨值之間,也非單純的等價關係。以目前一般決定公司股票上市定價或是現金增資的定價方式,除了現金增資幾乎都低於市價外(高於市價有意購買者可以直接在市場購買),折價出售的情形也屬常態。至於上市公司股票的訂價,除了資產淨值外,更重要的是必須考量公司獲利的狀況或是遠景,才會合理。再者,持有股票獲利與進行其他投資(包括投資其他企業或產業、定存、公債或市場/民間放貸利率,其中前者分析相對困難)的比較,在這本專書中討論是相對不足的。換言之,瞿教授的研究已經注意並討論了四大公司在1950年代的配股、配息狀況,甚至也注意到1952年底市場實際利率高達接近月息4釐(瞿宛文2022:179),[5]遠比預定土地實物債券和四大公司平均配息高。根據瞿教授的研究,1954至1960年四大公司配發股利的情形:台泥1954年0.4元,1957年增至1元,1959年更增至3.2元。工礦1954至1955年不配發,1956年0.1元,逐年增加至1959年0.35元。台紙1954年至1955年配發0.07元,之後到1960年不配發,農林只有1954年配發0.05元(瞿宛文2022:212-213)。其中台泥公司是當年進口替代政策的關鍵性產業,獲利甚佳,是四大公司中的績優生。然而這部分的討論或許並非瞿教授專書的重點,沒有再深入的探討。不過,欠缺前述的討論,則不足以釐清沒有取得四大公司民營化經營權的更多的地主階層,透過「耕者有其田」政策取得四大公司股票,所能獲得的利益或是相對損失的狀況。
關於政府配發四大公司股票換取地主土地的政策,還有幾個關鍵問題必須注意。首先,當時沒有證券交易所,地主取得的實物債券與四大公司的股票根本無法進行正常的市場買賣。儘管有來自省議會及輿論呼籲政府開放證券市場,以便股票和債券流通的聲音,經濟部內部當時也有推動證券交易所的建議與準備,然而政府決策官員基於過去在上海不佳的經驗,擔憂一旦開放會有人為投機操縱,遲遲不願設立證券交易所(瞿宛文2022:174-179;莊濠賓2018:181-183)。不過,縱使證券市場正常化,在當時財經條件下,土地實物債券的利息,以及四大公司絕大部分的獲利與配息,若都遠低於市場實際的利率與商業經營的利潤,一旦有了正常運作的市場,配息與市場利率相差甚大的股票與債券勢必出現拋售潮,導致價格的崩跌。以土地實物債券為例,年息4釐,然而市場實際利率則是月息4釐,差距之大可見一斑(瞿宛文2022:179)。再以1953年為例,實物債券年息4%,因遠低於市面上的優利存款,政府為此免除其利息所得稅與印花稅,使實際利率略高於4%(張宗漢1953:4,轉引自莊濠賓2018:172-173)。
農村農民所得應有明顯改善,這和1960年代(原佃農承領土地滿十年之後)台灣嚴重的離農化問題如何連結來討論,是一個未來值得再思考的面向。
三、土地改革與政府潛在的收益
在本書中,瞿教授特別針對透過土地改革政策,農民負擔的減輕,作了相當程度的論述。本書根據官方的資料指出,透過耕者有其田政策取得土地的佃農,前十年由於必須返還土地價款,他的負擔每年減輕6%,而在承領十年之後,每年的減輕更可達到31%(瞿宛文2022:50)。既然如此,農村農民所得應有明顯改善,這和1960年代(原佃農承領土地滿十年之後)台灣嚴重的離農化問題如何連結來討論,是一個未來值得再思考的面向。就此而言,除了與農業從業人口轉往工商企業界服務的所得做比較外,也與政府汲取農村資源的政策影響農民的實質所得有密切的關係。政府在土地改革之後,持續透過肥料換穀、田賦徵實、隨賦徵購等相關政策,低估穀物的價格,讓政府透過政策的落實,可以汲取更多的農村資源,使農民負擔了為數可觀的潛在稅捐。根據既有的研究成果,政府以「田賦徵實」隨賦徵收實物(米穀),1952年每賦元實物徵收14.16公斤,1962年徵收率調高為19.37公斤,1966年調高為27公斤,提高實物徵收率也就是實質提高了土地稅。「隨賦徵購」是伴隨土地稅強制收購農地生產物,而政府每年公定的收購價格,通常都遠低於自由市場的價格。「肥料換穀」是政府獨佔肥料公賣,以肥料換取糧食,且是不等價的交換,1950年代同單位稻穀與硫氨(台灣農民主要使用的肥料)交換比例約為1:1,但當時稻穀的市場價格約為進口硫氨肥料價格的兩倍(劉進慶1995:136-148)。這是必須注意的問題。
再配合前述有關四大公司資產重估,以及遠低於市場利率的實物債券利率,透過土地改革,政府從遵循政策釋出土地的地主方面,也得到了相當的利益。
公司民營化後,特別是標售廠舍成立的企業,取得產業的經營團隊/企業主,安排人事與原本政府保障忠貞來台人士就業的考量也有所不同。
四、四大公司(含標售廠舍)民營化的勞工抗爭
四大公司開放民營,相關勞工的抗爭問題(特別是被解雇勞工),在本書中也予以探討。就此,瞿教授在這本書認為,政府為了與地主階層妥協,因此沒有懲處解雇勞工之國營事業民營化後的經營者(瞿宛文2022:208)。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當時處於戒嚴時期,勞工的串聯抗爭是戒嚴時期相對關注、嚴格禁止的重點。[6]如能一起納入考量,或許更可以看出當時國民黨當局在此一解聘雇勞工引發的事件中,決策及處理方式的歷史意義。
企業轉手後,經營者/企業主檢視公司員工結構及薪資、績效,進行人事調整,常發生資遣員工及勞資糾紛。戰後初期公營事業的中上層員工,很多都是隨政府來台的外省人,根據事後台灣省政府向行政院提出的報告,之前政府為了保障他們就業,在公營事業中安插職位,導致公營事業員額過多(瞿宛文2022:207-208)。而這些外省員工幾乎都住在職員宿舍,這份工作關係到他們在台灣的棲身之處,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做好妥善安排(瞿宛文2022:128-129)。此外,我們還可留意,台灣在1950年代初期實施勞工保險政策,而當時勞保保障的勞工範圍,與目前定義的勞工大不相同,能夠得到勞保照顧的主要是公營(國營)事業的勞工。[7]是以,這些勞工一旦失去了國營事業勞動者的身分,其生活上原本享有的保障也連帶受到損害。換言之,國營事業民營化之後,遭到取得企業所有權的經營者資遣、解雇的勞工,失去的不僅是原本的工作而已,還有其他原本工作附帶的利益,他們採取抗爭是正常的反應。在公司產權轉移之前,公營事業員工就開始擔心民營化後原本的權益失去保障,1954年10月29日集體在報紙上登廣告抗議(薛化元2015b:129;〈四大公司即轉民營〉1954年10月30日),在非常體制下,前述的行動已涉及刑責問題,不過政府決定「酌情寬恕,免究刑責」,由省政府出面請負責人勸導,同時要求報紙不再報導此事(瞿宛文2022:134)。
而在公司民營化後,特別是標售廠舍成立的企業,取得產業的經營團隊/企業主,安排人事與原本政府保障忠貞來台人士就業的考量也有所不同。根據情治單位保安司令部的報告,遭到資遣的員工,大多是外省籍的工會幹部、黨工幹部(瞿宛文2022:207)。如前所述,原本政府機關透過關係在公營企業安插員工,即可能造成冗員過多。新的經營團隊/企業主基於精簡人事、專業考量、排斥工會或是希望由自己人脈掌握重要職務的思考,資遣了外省籍的工會幹部、黨工幹部,也引發了情治單位的注意。
問題是,在產權正式轉移、公司民營化以後,除非轉移時有附帶條件,政府本就無法限制私人公司不能解雇勞工,只能要求必須依法辦理資遣或解雇,這點或許說不上是政府與地主階層妥協或讓步。而且,根據事後官方的報告,經過協議,原本遭到資遣的488人中,包括技術員工、幹部有216人復職,另外272人則要求有條件的同意資遣,而資遣必須依照官方通過的《實施耕者有其田案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後輔導辦法》規定執行。而且在發生資遣/解雇爭議事件後,經濟部即邀集各相關單位官員及民營化企業負責人開會,要求相關企業務必遵守《輔導辦法》(瞿宛文2022:206)。換言之,政府並不是因為對取得企業所有權的企業主/經營者讓步,而不處理原有員工遭到資遣問題,而是要求企業主必須根據《輔導辦法》執行,且有相當比例的員工復職,顯示政府對於這些企業解雇員工事件,並非放手不介入。
透過土地改革政策,限制非自耕農購買農地,壓制投資農地的投報率,配合政府釋出戰後接收的日本產業,確實在某種程度引導台灣的農業資本往工業資本發展。
五、結論
如前所述,由農村土地改革來討論工業化,或由耕者有其田來討論台灣地主階層的處境,是戰後台灣經濟史的重要課題,而透過土地改革使原本投資於農村土地的資本轉移往工商企業發展的研究論述,也具體反映了此一時期台灣資本的流動或是經濟發展的方向。但是,將此一經濟史的發展,過度與四大公司的民營化結合,則有再審酌的空間與必要。過去的論述大多只注意到四大公司民營化的面向,過度強調地主釋出土地取得股票,角色朝向工商企業家轉換,而忽略了地主階層可以進入四大公司經營階層的人數相當有限,因此以四大公司民營化來論述地主階層在經濟領域角色的轉化,在本質上有它的問題和困難。瞿教授在這本書的研究中更進一步注意到原本四大公司下屬產業/企業的民營化問題,在某種層次上擴大了對地主階層取得土地補償之後,投入其他產業生產範圍的討論。但是這一部分的產業別或是公司數量,仍然相對有限,而且這一部分的公營事業民營化是否能與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所作的股票補償作有效的連結,也有再思考的空間。此外,透過前述政府標售廠舍或取得四大公司經營權的地主或資本擁有者,與國民黨當局之間發展的政商關係,也可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總體來說,政府透過三七五減租降低了地主佃租土地的收入,透過耕者有其田限制了地主擁有的土地,進而限制自耕農取得農地的資格,如此一系列的政策排擠了資本在農村土地投資的可能性和收益的限制,促使私人資本轉往工商企業發展,在此時的歷史架構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過這與前述土地改革釋出四大公司的股票,則未必有直接或是密切的關係。相對於取得企業經營權的少數地主階層,更多的地主階層在失去了土地所有權之後,若僅靠實物債券和四大公司的股票,所得的收益相對偏低,倘未轉型成功,他們家族經濟地位的沒落,也是歷史發展的重要面向。這一點或許與瞿教授關心點不同,但確實是土地改革對地主階層產生衝擊的重要歷史現象。就此而言,再回頭檢視國民黨當局與地主彼此妥協合作而造成土地改革的相關發展的論述,或許也有再思考審酌的空間。特別是沒有分家的地主家庭(共有土地),更完全失去了土地保留的資格,在此一過程中受到的打擊將更為嚴重。
可能值得再進一步研究的是:本書討論到極少數擁有大量農地的地主家族透過制度(例如成立公司)的安排,繼續保有大量的農地,而如果檢視這些家族在台灣政治經濟地位的發展,或許是釋出農地又沒有取得企業經營權地主家族的歷史對照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以國民黨當局的立場而言,透過「三七五減租」,降低了地主投資田產的收益報酬率(雖然有一些地主原本的租佃所得還低於此一規定),再透過「耕者有其田」政策,降低地主擁有的農地(共有地主更完全沒有保留原擁有一定面積土地的權利),這些都使原本投入農村土地的資本必須轉移投資標的。四大公司的民營化,是政府規劃的部分資金(作為失去土地的部分補償)一定必須流入的標的。進入四大公司經營階層的少數大地主,加上標售取得政府釋出部分戰後接收而來工業廠舍的經營者,台灣便有少部分的地主及資金擁有者,成功轉型成為前述台灣工業產業的經營者或主要所有者。不過,更高比例的(中小)地主,則不僅在前述的土地改革政策下遭到財物的損失,也無法轉型成為企業主,而失去其原有的影響力或沒落。相對地,原本在日治時期就擁有工業/產業經營經驗的企業主(他們通常也擁有相當田產),在戰後仍延續其企業,甚至擴大經營,在台灣產業史留下一席之地。如以鐵工業製造為主的唐榮成立於1940年(樊沁萍、劉素芬1996;高淑媛2003:233-234),大同鐵工所成立於1939年(高淑媛2003:233-234)。而在石化業相關方面,自日治時期延續發展而來的,則有永豐集團(謝國興2013:57)、長春石化集團[8]、李長榮化工[9]等。至於在戰後民生工業佔有一席之地的醬油、汽水,也有其日治時期的傳承,包括著名的丸莊醬油(王振寰、溫肇東2011:26-27)、黑松汽水[10]皆是。
整體而言,透過土地改革政策,限制非自耕農購買農地,壓制投資農地的投報率,配合政府釋出戰後接收的日本產業,確實在某種程度引導台灣的農業資本往工業資本發展。如同瞿宛文教授研究所指出的,四大公司的民營化(包括標售給民間的部分廠舍、設備成立的企業),配合其後續的發展,在台灣戰後傳統產業固有其一席之地,不過,除了土地政策引導的工業化發展外,戰後台灣工業化的發展與日治時期台灣產業的延續面,也不容忽視,值得進一步的考察。
【註釋】
* 本篇文章的完成,是閱讀瞿宛文教授的力作,引發的幾個思考的問題點。謝謝瞿教授的邀請,也感謝陳致妤的協助。而肥料換穀、田賦徵實等政策的討論,以及日治時期與戰後台灣企業經營者的連續與斷裂,謝謝李為楨教授和陳家豪博士長期的討論與協助。
** 服務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通訊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E-mail: hy5595@nccu.edu.tw
[1]莊濠賓(2018)〈世變下台灣地主層的沒落─以四大公司民營化為例(1949-1957)〉(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2]參見薛化元(2015a)〈土地改革與台灣經濟發展的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0(9月號):183-195。
[3]關於此點,筆者主要是得自劉進慶(1995)《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的先行研究。另參見吳望伋(1953)〈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的立法〉。
[4]參見司法院令,〈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115號解釋〉:「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耕地徵收與放領,人民僅得依行政救濟程序請求救濟,不得以其權利受有損害為理由,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土地。普通法院對此事件所為之相反判決,不得執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115號解釋〉1966年9月16日)。
[5]至於台灣在1950年代通貨膨脹仍然相當高,參考新台幣和美元的實質匯率,從1949年中的5:1,到1958年前後實質匯率至少36:1。
[6]《戒嚴法》第11條賦予戒嚴地域內最高司令官權力,得停止遊行請願,對於人民罷工、罷業得禁止及強制其回復原狀。參見〈戒嚴法〉(1949年1月14日)《司法專刊》6:162。
[7]臺灣省政府公布令,〈制定「臺灣省勞工保險辦法」、「臺灣省勞工保險辦法實施細則」〉(1950年4月13日),《臺灣省政府公報》39(夏:13)(1950年4月15日):196-203。
[8]長春石化創業的車庫是1932年創立的吉元鐵工廠(薛化元、張怡敏、陳家豪、許志成2017:47-48)。
[9]李長榮化工是從日治時期的李長榮製材逐步發展而來(薛化元、張怡敏、陳家豪、許志成2017:49)。
[10]黑松公司的官方網站指創業於1925年。參見黑松公司〈關於黑松〉:<https://www.heysong.com.tw/about/>(上網日期:2022年6月12日)。不過,官方檔案登記的成立日期則稍晚。
【參考書目】
王振寰、溫肇東(主編)。2011。《百年企業,產業百年:台灣企業發展史》。高雄:巨流圖書。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115 號解釋〉。(1966 年9 月16日)。《司法院公報》8(10)(1966 年10 月11 日):9-14。
〈四大公司即轉民營 員工發出呼籲 請求保障生活 希望政府合理裁處〉。(1954 年10 月30 日)。《聯合報》,第6 版。
吳望伋。1953。〈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的立法〉。《中國經濟》34:43-44。
〈戒嚴法〉。(1949 年1 月14 日)。《司法專刊》6:162。
〈制定「臺灣省勞工保險辦法」、「臺灣省勞工保險辦法實施細則」〉。(1950 年4 月13日)。《臺灣省政府公報》39(夏:13)(1950 年4 月15 日):196-203。
范心仁。1953。〈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問題〉。《中國經濟》36:1-3。
高淑媛。2003。〈台灣近代產業的建立─日治時期台灣工業與政策分析〉。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宗漢。1953。〈實物土地債券價格之分析〉。《土地改革》3(11):4-6。
莊濠賓。2018。〈世變下台灣地主層的沒落─以四大公司民營化為例(1949-1957)〉。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處委會闡明事件真相 向中外廣播處理大綱 除改革政治外別無他求 建議案本日可正式提出〉。(1947年3 月8 日)。《臺灣新生報》,第2 版。
黑松公司。(無日期)。〈關於黑松〉。<https://www.heysong.com.tw/about/>(上網日期:2022 年6 月12日)。
〈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1953年1月26日)。《總統府公報》383(1953年1月27日),第1 版。
劉進慶。1995。《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台北:人間。
樊沁萍、劉素芬。1996。〈一九六○年代唐榮鐵工廠公營化個案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8(1):189-226。
蔣夢麟。1967。《新潮》。台北:傳記文學。
蕭乾。(1947 年1月7 日)。〈冷眼看臺灣(下)〉。《大公報》(香港),第2 版。
薛化元。2015a。〈土地改革與台灣經濟發展的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0(9月號):183-195。─。2015b。《戰後台灣歷史閱覽》。台北:五南。
薛化元、張怡敏、陳家豪、許志成。2017。《台灣石化業發展史》。台北:財團法人現代財經基金會。
謝國興。2013。〈戰後初期台灣中小企業的殖民地傳承〉。《邊區歷史與主體性形塑: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謝國興編,頁45-85。台北:中央研究院。
瞿宛文。2022。《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重探台灣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新北市:聯經。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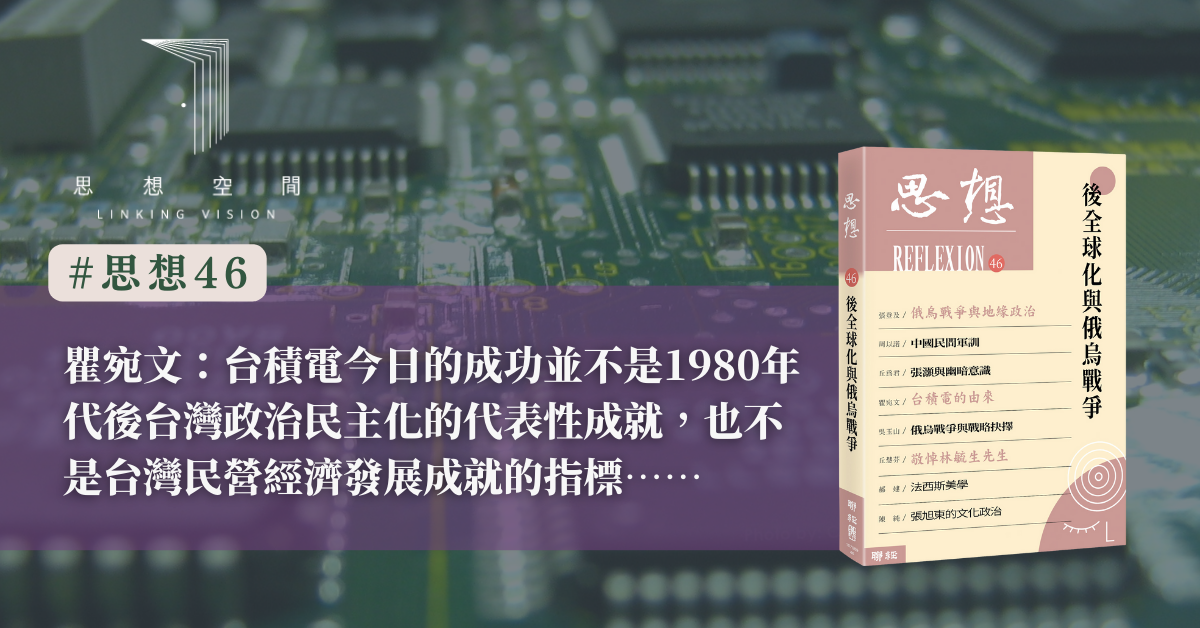
護國神山的由來:再談台積電與台灣經濟發展模式

瞿宛文:台灣土地改革與社會轉型——回應《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新書論壇

劉瑞華:我們從台灣的土地改革學到什麼?兼論《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 閱讀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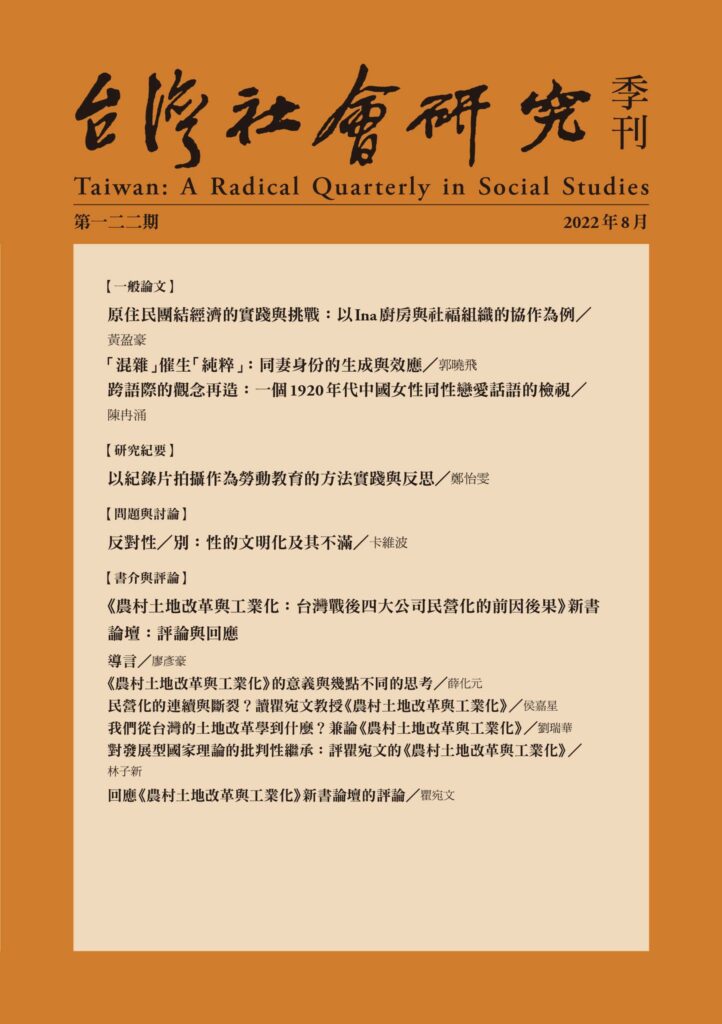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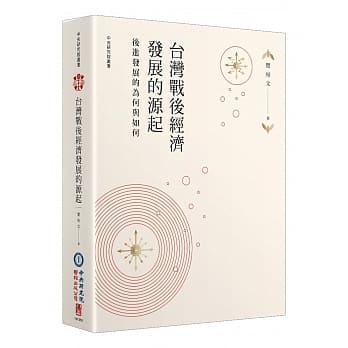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