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編按:2022年,中研院人社中心兼任研究員瞿宛文的最新研究論著《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出版,討論了台灣戰後初期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5月,新書論壇在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舉行,並邀請了薛化元、劉瑞華、林子新、侯嘉星等學者擔任專題評論人,參與對於台灣農村土地改革的探討。瞿宛文在本文中再次自道研究方法,並從不同角度回應了評論人提出的見解與問題。(*本文原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二二期,思想空間經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擬。)
《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2022)主要描述台灣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國府)實施耕者有其田之時,為了徵收出租耕地要補償地主,將地價補償中的三成,以四大公司的股票作為給付,因此意味著將四大公司民營化,把股票分發給地主。本書呈現了這事件的過程與其前因後果。此特定事件僅是當時牽涉廣泛的農村土地改革的一個部分,不過藉由較詳細地檢視這個側面,本書得以探索當時台灣政治、社會與經濟等相關層面。
大致而言,此次土地改革的範圍有限但宣示性強。國府刻意使得此次的土地改革溫和並且兼顧地主,在允許每戶地主能保留3甲出租耕地之下,土地徵收的範圍其實有限(僅總共徵收14萬甲,占私有出租耕地的56%;因對中大地主讓步,故徵收以共有耕地為主,受影響的個人地主戶數僅占個人地主總戶數的14%)(廖彥豪、瞿宛文2015;廖彥豪2020);因此所需要的地價補償的三成之數額並不龐大,在戰後所接收的日本工業資產中,此次民營化的四大公司的資產占比僅為27.6%(瞿宛文2017:191)。然而,即使範圍有限且手段溫和,所牽涉的政策作為卻仍具有革命性的意涵與影響,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強制性現代化政策,清楚傳達了政策方向,即限制以往地主依靠農地地租維生的模式,並推進工業化。這也是此次四大公司民營化的特殊之處,在於其連結民營化與農村土地改革,促進農業資本往工業資本之轉型。這不同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私有化,其多是源於意識形態上公轉私的目的。
除了回覆各位評論者的意見之外,本回應文也將一併討論一些在書中未能盡述的相關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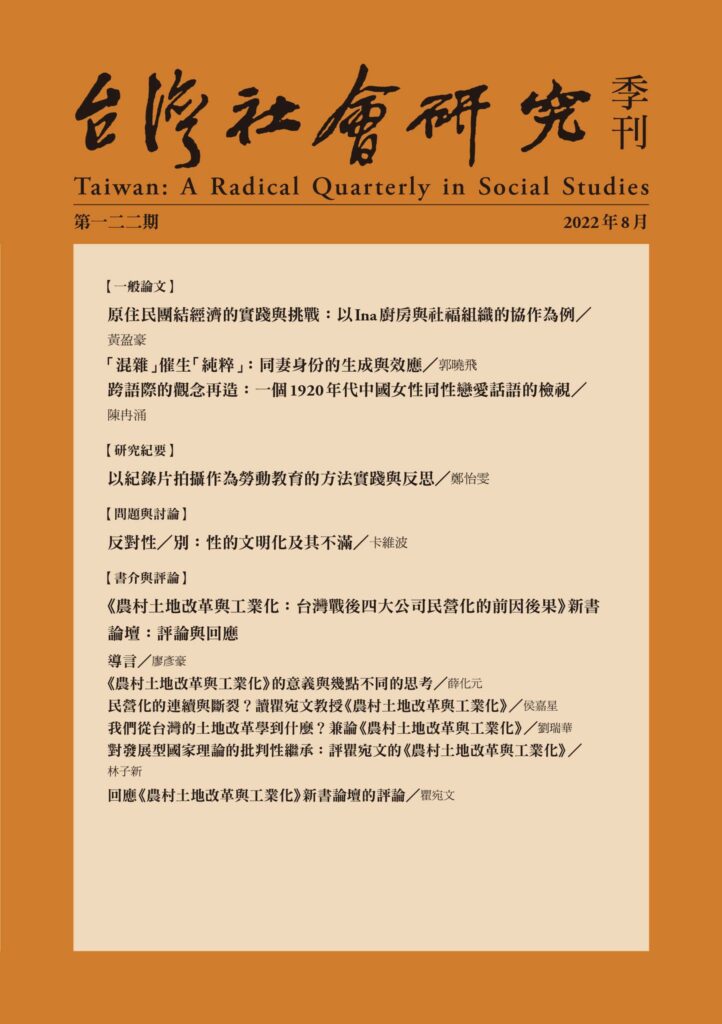
本書在研究方法上專注於事件,帶著理論問題與宏觀視野,試圖解釋事件的前因後果、政策形成過程,涵蓋多方面議題,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自行嘗試跨領域的研究。
關於研究方法
戰後以來,人文社會學科的規範日益嚴格,嚴刻的專業化要求也導致個別研究範圍的日趨狹窄,個別領域日益區隔出更多的次領域來,同時擬科學化、去歷史化的傾向也越來越普遍。筆者一向認為如此的研究取向,並不利於我們理解複雜的現實,因此近來在研究時嘗試一些跨領域的研究方法,本書也是另一試驗(瞿宛文2018)。茲在此稍作說明。
本書的研究取徑是帶著理論問題與宏觀視野,以分析歷史事件為主軸,並且設法結合各領域的知識。雖然無法做到全面性地敘述,但並不恪守學科分界,一方面是依據自身能力所及,更主要是依據對解釋事件發生的原由為主要考慮,來探討事件相關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等因素,同時伺機檢驗各種相關的理論問題。
此外,首先要確定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以及如何看待它的歷史視野。這一步當然涉及作者的價值判斷,然而這其實難以避免,不釐清歷史背景與視野,其實是假設一個去歷史化的世界,是隱含性地假設了現存世界是普世性的正常,相似於歷史終結論的假設。
本書將此事件置放於中國近代史中,探討國府如何在冷戰下、在國共鬥爭下敗守台灣之際,在國共競逐領導中國現代化的背景下,在鞏固政權的實際考慮下,進行了土地改革與四大公司民營化。這也是二戰後,前西方殖民地在獨立後試圖發展經濟的廣大潮流的一部分。
界定了歷史背景後,下一步是界定當時的環境,確定各方的行動者,他們的動力以及行動的條件。歷史背景有助於確定行動者的動力與條件。再則,需要理解當時的組織與制度,遊戲的規則,中央與地方的架構。在此基礎上,可以理解土改相關政策的形成過程,在其中各方的互動與博弈。各方的行動者包括政府高層、土改派官僚、經建官僚、本省菁英(省議員與其他政治人物、工商界人士等)。盡量結合各領域的知識來理解現實。
這樣的分析涉及諸多相關的領域,如民國史與台灣史等歷史領域;與政治相關的如政治發展,行政組織與政治現代化,政商關係;與政治經濟發展相關的官僚體系自主性,政府的發展傾向;與農村相關的如農村土地改革,農村經濟/農業生產,土地問題,農村土地,都市土地,平均地權等;與經濟學相關的如私有化與財產權問題,企業經營與發展,後進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產業政策,輔導民營企業政策,以及公營事業的管理與民營化等;與金融相關的如金融發展,財政問題等;也涉及較宏觀的發展領域如後進現代化,制度變遷,階級變化與轉型等。對這些領域筆者所涉略的必然甚為有限,所做的僅是就自身研究課題的需要出發,就理解所需而選擇採用。
簡言之,本書在研究方法上專注於事件,帶著理論問題與宏觀視野,試圖解釋事件的前因後果、政策形成過程,涵蓋多方面議題,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自行嘗試跨領域的研究。希望能在現今僵固的學科規範氛圍下,爭取多一些實驗的、跨界的空間,促進對研究方法的反思。相較於其他學科會有風潮變化,歷史學則必須面對歷史現實,較能維持跨界空間。
年鑑學派大師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曾討論社會科學劃分的問題,他認為要掌握事實的總和必然是要討論歷史、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各層面,但在敘述時也必然難以全面敘述。可行的辦法或是在進行分類時,仍保持總體的眼光,讓它在解釋中露頭,從而趨向於重建整體(布勞岱爾2018:478-482)。雖說他的博學榜樣實難以追隨,不過應可以此為學習對象、以其精神自勉。而筆者的總體眼光,則是將這一切置於後進地區追求現代化、經濟發展的角度中去理解。

本書這樣的研究取徑較不同於現今一般社會科學的取向,後者多是去歷史化的橫向角度,通常會聚焦於特定的因果關係,例如探討土地改革是否促進生產效率,並進而檢視兩組變數在統計上的相關性等,同時會假設可以排除其他變數的影響,而僅針對這組關係作去歷史化的探討。如此的取徑雖然在形式上可以專注於特定的細節關係,然而卻難以探討結構性因素、歷史變遷、行動者的動力因素等複雜元素。[1]或可說是在學術市場的競爭上,方法的「專業性」勝出,代價卻可能是對現實的解釋力。
相對照,本書以理解事件為主軸,在過程中涉及諸多因果性的「解釋」,每一項都可以是進一步橫向研究的課題,在研究方法設計上,本書與上述通行方法正好相反,是以解釋現實為主要目的,但當然也同時檢驗相關的理論。不過,這樣的方法有相當難度,需要諸多其他的研究做為支持。例如,筆者在本書各關鍵點的認定與理解,都有賴於自身與他人先前的研究,如對於相關行動者的動力與條件的認定,對於當時組織與制度的理解等,都奠基於先前的研究。[2]換言之,如此的研究方法有賴相關研究的累積與配合,有賴於在理論與實證研究中反覆來回,但以如此方式累積相關知識應很具有生產性,有助於整體性知識體系的建立。
源於冷戰與國共鬥爭的考量,高層決定施行土地改革,因而施行溫和的且兼顧地主的土改,是當時國府政策上折衝性選擇。
檔案資料
本書高度利用了新開放的各種政府機關檔案,除了一般相關檔案之外,此次最主要的資料依據是行政院的公文檔案。因為能夠取得足夠相關的行政院公文檔案,因此得以追蹤此案件進入行政院階段之後的政策形成過程,使得本書的寫作成為可能。
本書所涵蓋的範圍必然有限。不過筆者衷心希望本書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一則本書展示了一種以跨領域方式解釋一個事件的研究取徑,可做為討論研究方法的實例依據。再則本書在呈現民營化政策形成過程的同時,也顯示了諸多可以進一步研究的議題。
例如,侯嘉星(2022)在他對本書的評論文中即指出,當年台灣省政府的檔案已整理保存於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及檔案管理局,其中即包括《省府委員會議檔案》。本書依據行政院公文檔案,得以詳細呈現行政院階段的決策過程。而四大公司民營化草案的研擬始於省府處理的階段,本書雖然依據省府經費與條文小組的會議紀錄,對此部分有基本掌握,但若能參考省府委員會議記錄,應能有進一步的了解。一般而言,中央層級的行政院會對政策做出最後定奪,然而當時省政府一方面是草案的起草單位,另一方面必須直接面對省議會與其互動,省府其實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而這部分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此外,侯嘉星也提及與土地改革有關的省府地政處檔案,目前一部分存於行政院內政部中部辦公室檔案庫房。其實另一部分已由國史館數位化並予以公開。實際上,在耕者有其田施行過程中,各地對土地的徵收承領上有不同的做法,也產生了諸多爭議與訴訟,例如水利設施的徵收與否及徵收方式各地有差異,再如有佃農承領土地後提早付清地價以便變更地目獲利,而原地主興訟要求分享獲利等,這些豐富的訴訟資料皆保存於地政處的檔案中。新開放的檔案應提供了諸多研究的可能。
相關領域
因為本書採跨領域研究取徑,因而此次新書論壇邀請了四位不同領域學者來評論,而他們的評論正好提供從各自領域出發對本書的回應,指正本書之不足。從這些寶貴的互動之中,也呈現了各種不同的課題與研究視角。
全稱式「地主」稱呼之商榷
薛化元教授是台灣史方面的專家,他雖持不同意見,但願意再次參與我們土地改革論壇的討論,筆者甚為感佩。他主要認為國府施行土地改革是為了削弱本地地主菁英,因此質疑我們提出的國府此次土地改革時仍試圖兼顧地主的說法。因而對於四大公司民營化的過程,他認為在各個政策環節,如資產估值等,國府皆刻意採取對地主不利的做法(薛化元2022)。
就國府推動土改的動機而言,薛化元認為在《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制定過程中,是由大陸地主出身的立委占多數的立法院,將每戶地主保留地標準放寬,而不是國府主動兼顧本省地主。關於此點,廖彥豪與瞿宛文(2015)已做出說明,即省議會一直積極動員給予政府壓力。省議會對此條例草案所提出的建議案中,確實在形式上看似並未改動省府草案中每戶地主可保留2甲的建議,而最終立法施行的版本是放寬為保留3甲,因此容易造成省議會並未積極爭取的誤解。但是實際上,省議會的建議案放寬了地主保留地的界定標準與範圍,並且完全排除共有耕地,實質效果是將徵收耕地面積大幅降低至9萬甲左右,遠低於省府草案所預期的21萬甲,以及條例最終徵收的14萬甲。此外,將每戶地主保留地提高到3甲的決定,是由行政院院長陳誠在行政院院會中拍板達成的,並不是立法院決定的。而在陳誠拍板之前,反對再讓步者(土改派官員)與主張讓步者(如吳國楨、蔡培火等)雙方都積極對陳誠進行說服,主張讓步者當然代表著地主菁英的立場。
從現實政治考量來看,國府中央政權撤退至台灣之後,為了維持穩定,必須安撫本地菁英。實行土地改革必然會損及地主菁英的利益,但源於冷戰與國共鬥爭的考量,高層決定施行土地改革,因而施行溫和的且兼顧地主的土改,是當時國府政策上折衝性選擇。薛化元基本認為土地改革是國府壓制本地地主菁英的做法,因此否認國府當時政策的折衝性質。這說法確實顯示出本地菁英對土地改革的反對立場,然而卻忽視國府必須安撫本地菁英的實際需要,及其持續地施行相應的攏絡政策。[3]相比較,中共實行土地改革是動員貧下中農鬥倒地主,扶植了新的政治支持力量。國府是實行由上而下的土改,除了確保農村新設立的租佃委員會中地主不能過半之外,並未對佃農與自耕農全面進行動員,地方政治領域中既有的地主菁英仍然為大多數,因此在統治上必須安撫既有的地主菁英。
薛化元認為國府施行土地改革是為了壓制本地菁英,因此在施行中刻意擴大土改對地主階層所帶來的損失。他不贊同我們認為國府在實行土改時兼顧地主的說法,而他在對此說法提出質疑時,所採用的稱呼是「全稱式」的地主。事實上,土改對於不同類型的地主所帶來的影響,卻遠遠地不均衡。薛化元在提出質疑時,也指出是少數大地主受益,而小地主與小共有地主則常利益受損。實際上,他在這方面所描述的情況與本書說法並不相違背。重要的是,中大地主與小地主的政治影響力有甚大差異,在土改施行過程中,代表中大地主的本省政治菁英持續發揮政治影響力,使得每一次政策修訂的方向,都是趨向於相對地保護中大地主菁英的利益,因而必然是由較為弱勢的小地主,尤其是小共有耕地地主,來承受較大的衝擊。換言之,國府確實意圖兼顧地主,然而結果是主要兼顧了大地主,但這與小地主之未被兼顧並無矛盾。
如前述,地主菁英的壓力使得每戶個人地主的保留地由2甲放寬為3甲,因此受影響的個人地主戶數僅占個人地主總戶數的14%,在土改勢在必行的情況下,影響所及,最終被徵收的土地有七成是共有耕地。同時,《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刻意將都市土地的未來增值留給地主,而地主菁英更設法擴大都市土地的免徵範圍(廖彥豪、瞿宛文2015;廖彥豪2020)。[4]再例如,該條例在立法院審議階段時,因為弱勢小共有地主陳情,要求允許比照個人地主保留耕地以維持生計,因而立法院做出允許共有地主特許保留的修訂。但是同時間地主菁英也高度動員,訴求因血親繼承關係形成的共有耕地也得以特許保留。顯然源於政治影響力的差異,依據政策施行結果的統計,在被核予特許保留的共有耕地中,血親繼承類別佔了特許保留的總面積的59%,而主要提出陳情的老弱孤寡的社經弱勢群體,其得以特許保留的共有耕地僅占了6%(廖彥豪2020:88)。
最後,在本書述及的四大公司民營化過程中,既然被徵收的土地以共有耕地為主,分得股票者也必然以小地主及小共有地主為多數,然而,他們股權分散難以自我組織,顯然難以實質參與四大公司及衍生企業控制權的爭奪。相對照,地主菁英在土地徵收過程中,得以降低了自身受衝擊的程度,然而在民營化過程中,卻仍能積極參與承領並取得企業的主導權。
換言之,使用「全稱式」的「地主」來討論土改的政策作為與其影響,應會有誤導作用。土地改革目標是要改變農村的地主經濟,促使地主不再依靠耕地地租維生,靜態來說會損害地主利益,然而,動態來說,則須視地主經濟的轉型是否成功而定。如前述,因為中大地主菁英與小地主的政治影響力有甚大差異,使得小地主承受主要衝擊,而本省菁英較有條件從中得利並且轉型成功。無疑地,有些資源較缺乏的小地主轉型失敗,利益遭到損害。然如果用「全稱式」的「地主」來否定國府兼顧地主的意圖,進而認為「地主」整體利益在土改中受到損害,可能會忽視了土改對台灣社會轉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的作用,也忽視了大小地主間的差異,以及本省菁英在過程中的積極角色。
確實,土地改革的成功還依靠政府重建農業行政的功能,能夠取代原先地主的功能,提供農業急需的投入,並使得政府能獲得農業產出。
跨越經濟學的界線
劉瑞華教授(2022)則從經濟學的角度思考此次土地改革。他師從新制度學派大師諾思,而博士論文寫的就是關於台灣的農村土地改革,是本地經濟學界極少有的研究土地改革的專家。經濟學對此議題的主要關切點,在於財產權的變更對生產效率的影響。然而著名經濟學者張五常的佃農理論認為減租不會提高效率,同時他也認為國府推動土改的動機未必是如其所宣稱的。劉瑞華的博論即以此問題為基礎,推論認為國府實施土改的原因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
劉瑞華所師承的新制度學派是戰後經濟學一個重要的學派,強調制度對經濟行為的影響,尤其著重交易成本的角度及對財產權制度的研究。而此處則涉及政府的政策動機與目標的問題,而筆者即擬就此問題與之商榷。
政府推動政策的原因誠然未必是其所宣稱的,並且推論其動機確實並非易事,不過不同學科的處理方式卻有相當的差異。現今經濟學因為基本上遵循與政治學的「分工」,故對於政策的原由,多在經濟理性範圍內尋找解釋,關切生產效率以及各方的利益變化,也隱含假設行動者為理性經濟人。新制度學派發展出的政治經濟分析也大致在此範圍內。
筆者擬以國府推動土改的動機與目標為例,嘗試提出不同的研究取徑。筆者認為跨越學科的「分工」邊界,跨越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界線,可能會產生具有生產性的解釋,因為歷史現實並不依循這種學科界線。政策是由主政者所決定,這其實是政治行為,直接受到政治競爭的影響。政治雖必然會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但不易進一步認定經濟因素如何「決定」政治行為,這必然是具高度爭議性的課題。如果僅從經濟層面解釋政治行為,就可能會忽略其他重要的因素,如政治競爭的動態及意識形態的影響等。
簡言之,筆者認為國府推動土改的動機是政治性的,是源於長期國共之間政治競爭下形成的理念,而非短期經濟性的考量。依據對近代歷史的理解,包括中國與全球近代史,筆者認為中國知識菁英自鴉片戰爭以降,即持續尋求救亡圖存的道路。當1923年蘇俄顧問對孫中山提出土地革命日程時,孫中山理解到他領導的國民黨影響力極為有限,而中國人口超過九成為農民,必須要能動員到農民,才可能發動現代化革命,而土地改革應是動員農民的有效方法。因此他決定聯俄容共後,土地改革成為國共兩黨共同的目標,也是此後兩黨在政治競爭上的主要面向。如此的歷史視野,才能夠解釋為何相對保守的國民黨政府,在退守台灣之後,為了確保農村秩序、排除中共可能影響,也延續著國共的政治競爭,而在台灣實行了農村土地改革。在陳誠於1949年初於兵荒馬亂之中接任省主席之時,立即宣布即將實行三七五減租,應不會僅是出於對經濟效率或財政收入的計算與考量。[5]如歷史學者陳永發教授在當天主持本書論壇時,即曾表示中共推行土地改革是政治考量,不會想到效率問題。確實,這正是筆者對歷史發展的體認,在政治運動推動著後進國家的進程時,從政治層面去理解政治黨派與行動者的考量與行為,應該是比較接近現實的作法。這也是筆者跨越學科界線的理由,是一種與經濟學科不甚相同的取徑。
此外,劉瑞華作為土地改革的經濟學專家,指出了很多本書未能涵蓋的問題。例如他討論了三七五減租以價格上限(地租率固定為三七五)來取代原先高低不一的地租率,妨礙了市場機制的運作,這問題確實甚少得到關注。同時,他認為三七五減租破壞農地財產權的問題,而在實施耕者有其田後佃農變成自耕農取得完整的產權後,問題才得以部分修正。然而因徵收並不全面,至今時空早已轉變,但仍存留的三七五出租耕地因財產權不完整,而亟待制度上的修正。
今日的三七五出租耕地的問題確實需要處理,然而筆者並不認為三七五減租的作用僅是破壞財產權,僅在此提出商榷。中國傳統農村的租佃關係甚為異質且複雜,例如有些地區有永佃制,地主僅擁有田底權,佃農擁有可交易的田面權,有時土地交易完成後賣主仍可向買主再提要求等等。實質上,財產權可說是一種社會關係,中國傳統農村社會複雜的租佃關係或財產關係,正反映了當時複雜的社會關係,而不是現在被視為理所然的現代財產權。[6]在國府實施三七五減租時,農村土地產權仍有著複雜的前現代牽絆,公權力介入下訂定的三七五租約,明確化了租約關係與條件,並有正式法律文件作為依據。耕者有其田即是在此清晰的租約基礎上進行的,佃農承領耕地成為自耕農時,取得的土地產權是由公權力介入所界定,因而得以具備現代財產權的性質,與原先傳統的口頭約定有相當距離。同時,耕者有其田改革了所徵收的共有耕地的性質,使其所有者從多位成為單一,確立了其現代私有財產權的性質。也因此在土改之後,由耕者有其田「確權」過的土地,成為最容易變更地目而成為工業與建築用地的土地。換言之,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政策,變革了傳統產權,起到了建立現代化私有財產權的作用。如張五常等經濟學者多忽略土改當時的產權制度的前現代性質,而假設當時的產權制度不單已經存在並已是現代化的,因此會強調土改對產權的干預面,卻忽視了土改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作用。
此外,劉瑞華(2022)指陳土地改革不只是耕者有其田,影響工業化的更不只是四大公司民營化,這釐清確實是需要的。同時,薛化元(2022)也對此提出了相類似的意見。誠然,本書書名雖是《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但主要聚焦於四大公司民營化作為地價補償,對於促進農村資本進入工業的可能影響。土地改革還包括本書未能涵蓋的三七五減租與公地放領。工業化則更是遠較為廣泛的變化,如前述,此次土改範圍有限而宣導意義甚強,土改與民營化雖順利施行,但最終的成功實有賴全面工業化浪潮的支撐,那才是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故事(瞿宛文2017)。劉瑞華也提到當時政府施行地籍總歸戶與發展農會組織的重要性,確實,土地改革的成功還依靠政府重建農業行政的功能,能夠取代原先地主的功能,提供農業急需的投入,並使得政府能獲得農業產出。劉瑞華與薛化元對此的釐清再次提醒我們應看到當時的大背景。
要建立現代的工業企業,必須要能組成有共識的經營團隊,大股東可以互相合作,對經營方向有共識,取得主導權者,立意從企業長期發展中獲利,而非短期掠奪性牟利⋯⋯
民國傳承與派系的作用
侯嘉星(2022)教授從民國史及民國工業史的角度提出問題。確實,國府從大陸遷台,必然帶來了民國時期的傳承,包括對公民營企業的思考與政策。筆者對此議題曾進行梳理,7發現國民黨政府對於公民營企業的界線,一向沒有清楚的界定。孫中山所提出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僅是方向性指示,對於國家資本應涉入的範圍,大致定為涉及國家安全與民間難以經營的行業,涵蓋範圍甚為有限。在抗戰時期以及戰後接收與恢復時期,國府其實多依據現實考量來決定公營的範圍。例如,組織能力較強的資源委員會,在與官方配合下,仍然可以大致自行決定其在台灣接收哪些日資企業,而他們在台決定接收的十大公司,也在其努力下成為戰後經濟恢復的主力。不過,除資委會之外,有些接收的國營及黨營事業的績效則遭人詬病,成為國府在大陸戰後時期經濟治理敗局的一部分,後者更被認為是其失敗並退守台灣的原因之一。在1950年代,這失敗經驗也促使國府在處理經濟問題上高度地戒慎恐懼,同時也有著盡量不擴張公營事業的共識。
歷史學者較為注重人事或派系的問題,不過,筆者認為派系的作用或並非既定,因此本書也並未將派系當做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如侯嘉星(2022)所指出,本書指認了以陳誠為領導的土地改革團隊,主要包括陳誠及其幕僚、農復會主要成員、土地銀行相關人員以及地政人員等。不過筆者發現這土改派的集結主要是基於共同的理念(即「政策邏輯」),基於對土改目標的共同追求,既沒有組織也不是關係性的人事派系(即「派系邏輯」)。
土改派除了要面對本地地主菁英的反彈之外,也要處理執政隊伍中反對與消極的力量。蕭錚雖被認為是國民黨推動土改的領導性人物,但他此時卻與吳國楨合作,提出了貸款給農民向地主收購土地的間接性方案。這方案不單有籌募經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若地主如預期地不願意出售土地,則土改就無法實現。由於蔣中正堅持要實行土地改革,這方案之所以未得到認可,是因為其可行性低,而不是派系鬥爭的緣故。在國民黨通過施行土改的決議後,主持省府的吳國楨也必須施行徵收土地的直接性土改了。確實,在吳國楨擔任省主席那幾年,他與擔任行政院院長的陳誠之間持續有著矛盾衝突,雖說這必然牽涉人事派系的糾葛,不過本書發現若基本依據「政策邏輯」來分析,而不需要引入「派系邏輯」,即可以解釋土改的相關政策過程。這應顯示了當時在這個政策領域中,派系意識並未嚴重影響政策過程。
此外,一般而言,派系的涵蓋範圍與作用其實並不清晰,成員是否有相同的理念也令人存疑,因此不一定能夠作為解釋的因素。例如,一般認為CC派支持土改,然而,該派成員眾多,對土改理念未必一致。如前述,該派土改的領袖人物蕭錚在此次土改中,支持未被採用的間接土改方案。在立法院審查限田法案時,贊成與反對方都可找到CC派成員(廖彥豪、瞿宛文2015)。
我們藉由對於土地改革的研究,以及對於經濟發展過程的探討(瞿宛文2017),雖說涉及的領域甚為有限,但確實檢視了當時相關的政策過程。茲藉此機會陳述一下所累積的、對當時國府統治的一些歸納與觀察。
先來回顧土地改革這整個政策過程。最高領袖的支持當然是必要的,而蔣中正確實堅定地支持施行土改,不過他將這任務交予同樣堅持土改的陳誠,而甚少予以干預。同時間,本省政治菁英高度動員與國府高層進行博弈,試圖使政策對其較為有利。而陳誠則帶領前述的土改團隊推動土改,這些基於理念、追求理想的專業人員,基本上能夠主導政策過程,派系邏輯並不重要。此外,這政策過程並不符合一般對國民黨「黨政不分」或「以黨領政」的印象,除了最初土地改革議案是經由該黨中常會決議通過之外,在政策過程中黨部甚少介入,介入主要出現在該黨第五組對於四大公司員工的問題上。
而這樣的歸納,大致與筆者對當時經濟發展過程的理解相符合,即專業經建官僚基本上有自主空間,得以依據專業主導事務。不過,以上觀察僅僅限於我們研究所及的領域,而國府統治在不同領域應有顯著的差異,這些都有待更多的探討。再則,戰後初期國府與本地菁英在政治上的競爭融合過程,更是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侯嘉星也提到當時民營企業如何提升競爭力的問題。筆者(2017)曾對此進行初步的探討,並發現早期的產業政策已開始建立協助民營企業升級的機制,同時原資委會人員在諸多場域提供了重要的協助。不過,此次民營化的挑戰確實是一個新的現代化的挑戰。一則對政府帶來了輔導企業上的兩難。一方面省議會代表地主菁英持續要求租稅優惠與延長輔導,另一方面財經官僚堅持要培育出有競爭力的、而非依賴性的經營團隊,才算輔導成功。建立如此的現代企業是新的重要挑戰。確實,一般認為,不同於其他落後地區,東亞產業政策成功的關鍵在於優惠依據績效標準,有獎有懲,促進競爭,提升生產力,保護是有條件及期限的,才能避免依賴與怠惰。對地主菁英而言,民營化也帶來全新的挑戰。要建立現代的工業企業,必須要能組成有共識的經營團隊,大股東可以互相合作,對經營方向有共識,取得主導權者,立意從企業長期發展中獲利,而非短期掠奪性牟利,在在要學習並建立經營的組織與能力,台灣本地工業化主要始於戰後,需要學習。就日後經營情況言,鑒於這新的挑戰並不容易,成敗參半的成果或也是可預期的。這些也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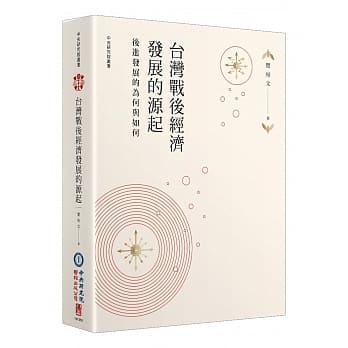
無論是土地改革或是產業政策,自主性要求專業堅持以及前瞻性規劃能力,而其之實現則要求「鑲嵌性」,即對現實利益的理解,以及政策對象的配合。
發展型國家理論
林子新(2022)教授則依據發展型國家理論對本書提出問題。他指出筆者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以發展型國家理論解釋東亞經濟發展之時,認為國家的相對自主性或強勢地位,是源於戰後初期地主階級失去了地位。而隨著筆者日後進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基於對台灣農村土地改革的研究,卻發現當時的本省地主菁英遠沒有失去地位,反而是能夠高度動員與官方博弈,迫使官方做出相當的讓步,使得土改最終是一個兼顧地主的溫和改革;因而對原先說法作出顯著修正。再則,林子新認為本書討論了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的關係,並從估價委員會的專業堅持,以及經建官僚建議分廠分售的案例,展示了發展型國家的自主性。他因而認為筆者批判性繼承了發展型國家理論關於自主性的說法,並重新界定了國家自主性。他認為筆者重新界定的自主性,並不是財經官僚在制定政策時的專斷能力,而是兼顧多方利益的統合能力。
感謝林子新指出了筆者對國家自主性的看法歷年來有所修正,確實,這修正也是大家一起推動知識前沿的成果。從1970年代起,在東亞展現出傲人的經濟發展成績之後,如何給予解釋成為發展學科的一大挑戰。一般認為,東亞模式特點包括政治菁英具有推動發展的意志,以及經建官僚具有能力和自主性等。如前述,經濟因素如何影響政治是一個高度複雜的議題,問題是在何種情況下政治會不由既得利益者所主導。關於台灣戰後初期的政治結構,在199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通行的本土論述是國府當時居於絕對強勢,威權統治下本省菁英只有被動接受。筆者在2003年的對東亞發展的綜述文中,因尚未自行研究此議題,因此在這部分依循了通行的本土論述。然而隨著之後開始研究土地改革,即發現了不一樣的歷史現實。本書的研究更是呈現了一個深具實力、能進行官商博弈、積極參與現代轉型的本地菁英階層。然而,如何界定發展型國家的相對自主性?
Huntington(2006)認為落後國家的土地改革在議會政治制度中不可能實現,因為地主必然會主導議會。落後地區會發生土改的可能情境,是在它追求獨立的政治運動中,欲推動現代化改革的新興政治菁英掌握了權力,進而推動土改,是一種變動社會中的改革力量。至於其是否能夠成功推動土改,那就依據其他各種條件而定了。他所說的與台灣情況大致符合,雖說國府能夠接收台灣是因為中國是二戰的戰勝國,不過國府在大陸時期的政權構成可說是一種變動社會中的改革力量,這是它意欲推動土改與發展的原由。
再回來討論林子新為筆者重新界定的自主性,他認為其不是財經官僚在制定政策時的專斷能力,而是兼顧多方利益的統合能力(林子新2022)。這說法恐仍需進一步地釐清與修正。發展型國家或其經建官僚的「自主性」,一方面是相對於既有利益,另一方面是配合著其推動整體經濟發展的目標,主要意味著經濟政策的制定,是依據後者,而不是維護既有利益。至於如此的政策是否能夠成功施行,則依賴諸多條件的配合,包括政策的可行性,既有利益者接受或反抗的程度,以及其他政治因素等。例如,林子新認為尹仲容等建議分廠分售,展現了兼顧多方利益的統合能力,因其符合地主菁英的需求。然而尹仲容等做出此建議,是認為如此更能夠促進民營部門的發展,並非為了兼顧各方利益,而地主菁英如此要求也顯示他們積極參與的意願。換言之,自主性意味了依據推動整體經濟發展的目標來擬訂經濟政策,這必然會有某種程度專業性的專斷,至於是否兼顧了各方利益,並不是自主性涵蓋的範圍,或更涉及既有利益者可能的反應。

發展型國家理論的始祖Chalmers Johnson曾論及發展型國家的統治正當性問題。他認為威權統治本身無法動員人民,發展型國家的正當性來自人民願意獻身投入現代化計畫,並因此改變經濟、政治與社會秩序,正當性來自國家推動發展的成績(瞿宛文2017:438-439;Johnson1999:50-54)。他的說法應符合當時台灣社會積極參與經濟發展的情況。而就此次土地改革以及四大公司民營化而言,地主菁英雖對土改不滿,但已理解到進一步土改勢在必行,因此積極參與並試圖影響政策,也意味著他們已準備轉型進入工商社會。同時,當時的大時代背景也必然有其影響,在中國大陸中共藉由土地革命取得政權,美國在日本實行土地改革,冷戰興起,地主菁英應也認識到時代潮流的變化,此外,諸多地主菁英也早已有了現代商業的經驗,因此進而願與國府合作。
再就產業發展來討論「自主性」。依據筆者對台灣經濟發展過程的研究,因為現代產業變遷迅速,發展過程中需要不斷為下一步產業升級做規劃,這規劃需要財經官僚具有「鑲嵌自主性」(瞿宛文2017;Evans1995)。自主性意味著不受既有利益者的左右,鑲嵌性則意味著理解產業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以及現存產業部門既有的能力與發展潛力。此外,如此前瞻性的產業政策能夠得以施行並且成功,也有賴社會對財經官僚的信任,或說其具有公信力。換言之,發展型國家的構成中,除了執政者推動發展的意志,以及財經官僚的自主性之外,還需要以下因素,一則,如Johnson(1999)所言,這需要社會願意為現代化計畫努力,再則,如Campos & Root(1996)所言,這需要推動政策者具有公信力,讓民眾相信他們將能夠分享到成長的果實。
簡言之,無論是土地改革或是產業政策,自主性要求專業堅持以及前瞻性規劃能力,而其之實現則要求「鑲嵌性」,即對現實利益的理解,以及政策對象的配合。無論如何,多年前筆者引用的本土論述─即國府依靠威權統治而地主菁英無實力反抗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經過知識的累積,我們得以增進對當年歷史的理解,也豐富了發展型國家理論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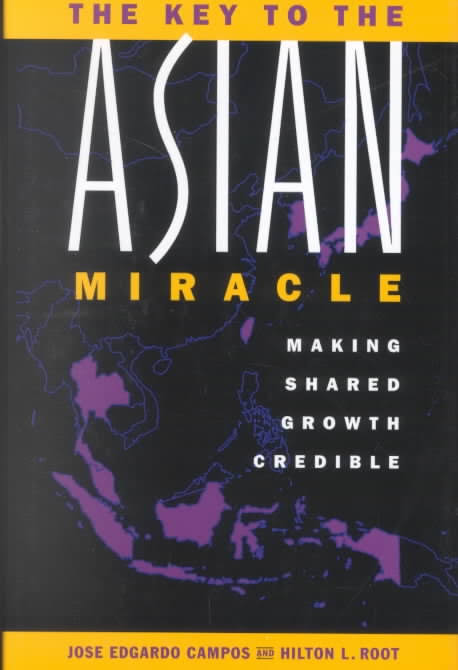
結語
四大公司民營化是否成功?本書認為就公司本身發展而言是成敗參半。然而,這事件的意義並不僅限於這些公司的成功與否,更主要是在於其配合從農村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的大變化。民營化政策在施行上大致是有序且順利的,做到了將四大公司的股票配發給地主作為地價補償的目標。雖說仍有公司資產是否高估等爭議,以及小地主利益未能被照顧等問題,然成功宣示了土地改革是要將農村資本轉入工業的政策目標。
大致而言,國府在台推動的土地改革,雖範圍有限,但仍然達到了強制性推動現代化進程的作用,建立了農村土地現代化產權制度,加快了農村地主轉入現代工商業的進程。土地改革中減租及徵收出租耕地的作為,雖衝擊本省菁英的利益,不過因國府無意改變本地政治生態、執意安撫,本省菁英得以藉由影響政策過程相對保護自身利益,並積極參與民營化過程。國府可說是以溫和妥協的方式協助本省菁英轉型。此外,有限度的土地改革必然還有其平均化的作用,有些農民受惠於減租與承領耕地,有些農民受惠於都市土地增值而成為新興城市小地主。然而諸多小共有耕地地主則在政商博弈中失利,更可能缺乏有利條件進行轉型。再則,民營化是一個新的現代化的挑戰。
被扶植的現代工業企業要具有市場競爭力,才算是成功。這對政府與接手的地主菁英而言,都是挑戰,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最終的成功來自於同時間國府的產業政策,其成功地啟動了戰後的工業化,以及農業政策促進了農業生產的進步,有助於新的自耕農成功立足。快速的工業化給予新企業成長的機會,提高了農村地主轉型的成功機率,而農業的發展有助於確保土地改革的成果。
[1] Tilly(1975)討論了他為何採用歷史論述,而不是社會科學較為通行的發展型及功能型理論。
[2] 除本專題導言中述及的土地改革專題之外,主要為瞿宛文(2017)及其中所引文獻。
[3] 例如,瞿宛文於《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2017)第七章討論了本地民營企業在戰後的發展,指出除了以外銷為主的競爭性產業之外,在戰後早期,國府保留了一些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產業為特許產業,如保險業等,並將特許執照分發給本地政治菁英。
[4] 依據廖彥豪(2020:90,表6),至1954年2月,經核准的免徵耕地面積近1.5萬甲,作為耕地雖顯得面積有限,但日後若轉為都市土地則價值將大幅增長。
[5] 參見瞿宛文提出的「國共競爭說」(2015:20-34)。
[6] 參見前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0期〈重探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專題〉,尤其何欣潔(2015)。
[7] 參見瞿宛文(2017)第6章。
參考書目
何欣潔。2015。〈由鄉莊社會到現代社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8(3月號):147-193。
林子新。2022。〈對發展型國家理論的批判性繼承:評瞿宛文的《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灣社會研究季刊》122(8月號):241-249。
侯嘉星。2022。〈民營化的連續與斷裂?讀瞿宛文教授《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2(8月號):213-222。
費爾南.布勞岱爾。2018。《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二:形形色色的交換》。台北:廣場出版社。
廖彥豪。2020。〈從都市化與工業化視野重探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77(2月號):81-99。
廖彥豪、瞿宛文。2015。〈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8(3月號):69-145。
劉瑞華。2022。〈我們從台灣的土地改革學到什麼?兼論《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2(8月號):223-239。
薛化元。2022。〈《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的意義與幾點不同的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2(8月號):197-211。
瞿宛文。2015。〈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8(3月號):11-67。
─。2017。《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新北市:聯經,中央研究院叢書。
─。2018。〈從後進發展反思社會科學的普世性:以台灣經濟學科本土化為例〉。《文化縱橫》2018(10):45-47。
─。2022。《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重探台灣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新北市:聯經。
Campos, J. E. L., & Root, H. 1996. The key to the Asian miracle: Making shared growth credibl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Evans, P. B.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 P. 2006.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C. A. 1999.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pp. 32-6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 1975. Western state-making and theori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p. 601-6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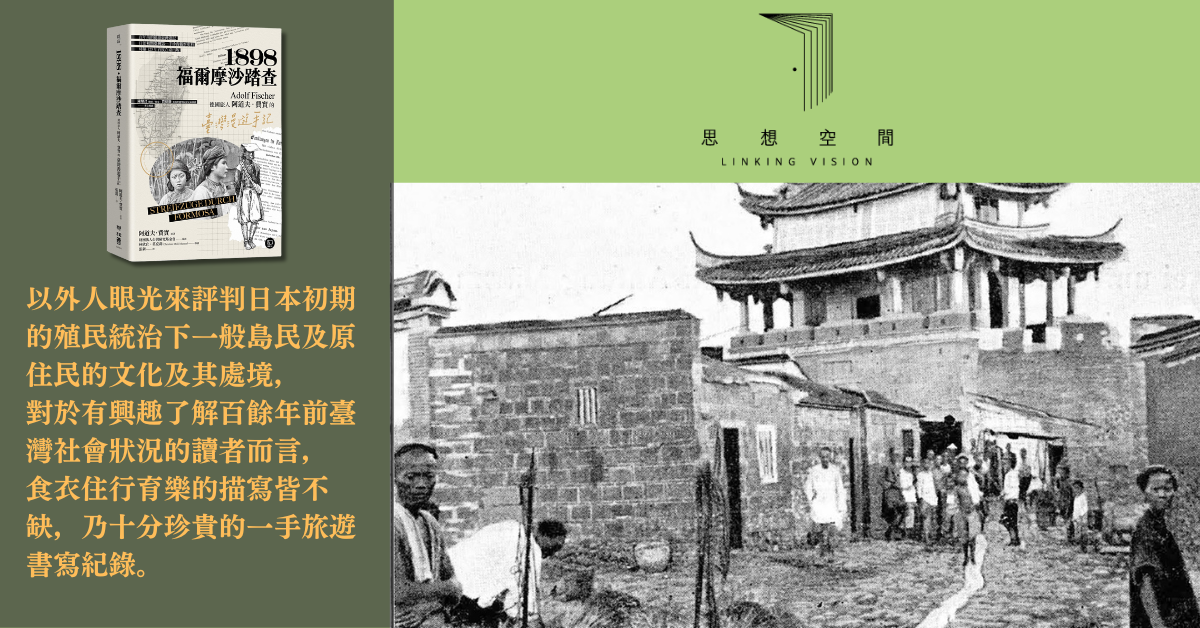
藝術與殖民之糾葛:阿道夫.費實的臺灣

漫長而隱形的界限之下,是台澎金馬的特殊命運

瞿宛文:台灣土地改革與社會轉型——回應《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新書論壇
| 閱讀推薦 |

美國史丹佛(Stanford)大學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曾任中研院研究員、臺灣大學城鄉所與經濟系兼任教授。研究著重於台灣與東亞經濟發展,近來也開始探討中國大陸經濟相關議題。曾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主編與社長。著作包括《中國產業的發展模式:探索產業政策的角色》、《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等。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