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偉棠,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 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及香港文學雙年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年度藝術家(文學),現旅居台灣,任台北藝術大學客座副教授。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後覺書》、《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半夜待雪喊我》等十餘種,講演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走近現代詩的四十條小徑》,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系列,散文集《衣錦夜行》、《尋找倉央嘉措》、《有情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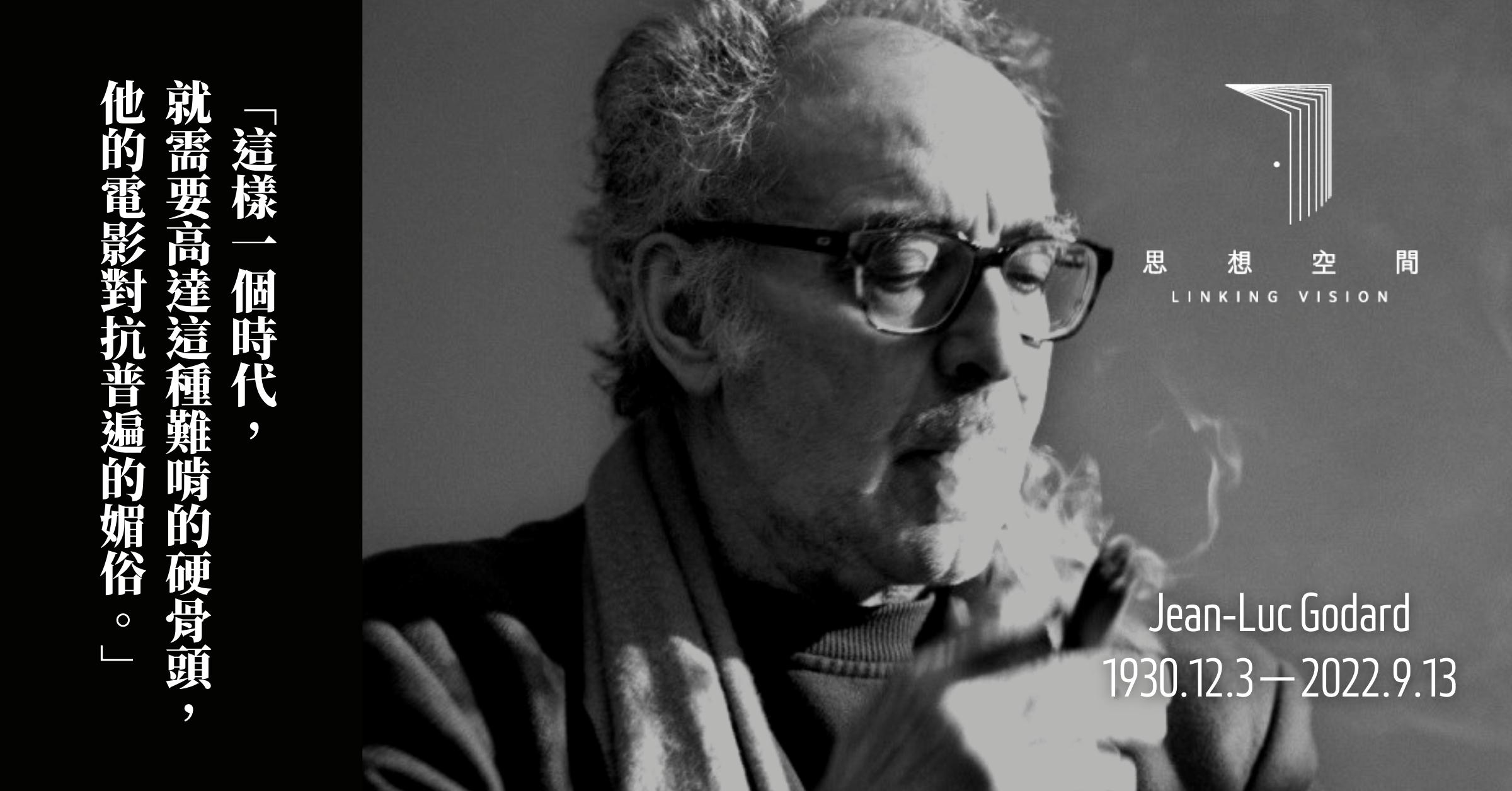
文/廖偉棠(香港作家、詩人)
編按:2022年9月13日,法國電影新浪潮重要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逝世,享壽91歲。高達1930年出生於法國巴黎,是法國新浪潮電影的奠基者之一,代表作品包括《斷了氣》(À bout de souffle)、《輕蔑》(Le Mépris)、《狂人彼埃洛》(Pierrot le fou)、《狂人彼埃洛》(Pierrot le fou)等。2014年,高達作品《告別語言》(Adieu au Langage)面世,斬獲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最佳影片等獎項;香港作家廖偉棠曾撰文回應高達的電影語言與詩意探索,我們也藉以懷念高達所帶來的顛覆與思考。(本文摘錄自《異托邦指南/電影卷:影的告白》(聯經,2017),原題為〈再見語言,走向語言〉,標題為編者擬。)
2015年,法國電影大師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1930年12月3日-2022年9月13日)的新片《再見語言》獲得了美國影評人協會的最佳影片獎,幹掉了風格更美國、呼聲也更高的《少年時代》和《鳥人》。老實說還是有點意外,美國影評人協會的口味雖然比奧斯卡當然高冷一些,但授予完全叛逆於主流電影美學、並且變本加厲挑釁新技術和觀衆口味的《再見語言》,不知道是因爲影評人們的大膽革命,還是高達一貫警惕的主流收編。
無論如何,這部在各種影評網站上獲分極其懸殊的電影,的確仍然是一部實驗電影,它依然嘗試對當下的電影進行顛覆分割——記得楚浮說過一句名言:「電影史可以分成高達之前的電影,和高達之後的電影。」而在高達迷眼中,高達的每一部電影都是這個分界線。
實際上這部電影要實驗或者探究的東西,在高達的個人電影史上是一脈相承的,諸如離題敘述、聲畫斷片、極度省略、畫面內部衝突等等早在《斷了氣》已經熟練運用。因此不必驚訝於高達這次更加實驗還是更加離譜,我們要驚訝的在別處。譬如說,爲什麼這樣一部顛覆性的電影,仍然讓人感覺到詩意?
即使他花樣百出、時而大刀闊斧時而細心設伏,表面上應該更接近解構者德里達的他,實際上回歸延續的還是通向語言之途,憑藉對詩的語言的重新建立。
高達一直在致力重新定義詩意,重新塑造電影語言。所謂「再見語言」翻譯得好,他告別的只是程式化的語言,他會重見一種新的語言——就像電影完結出字幕時畫外音裏那些呢喃和嬰兒咿呀所隱喻的。至於他要告別的語言,在男女主角貌似情感交流的對話中,不斷出現以致讓觀衆感覺諷刺,諸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們生活在這裏這裏就是我們的家」這樣的陳腔濫調,全球化時代的影視觀衆都熟悉這種雞湯,和TVB劇集「我煮個麵給你吃」那些萬能金句的作用是一樣的,它實際上無助於人與人之間溝壑的填補,最後這對男女還是以無法溝通分手收場——諷刺的是他們的狗學會了高達式的自言自語,還不忘反思人類的世界。
人類告別了語言,狗獲得語言,都是焉知非福的事,後者讓人想到夏目漱石的《我是貓》,最終它們還是願意回歸沉默的。倒是高達出離了饒舌與沉默之困,憑的是影像的隨心所欲。人七十從心所欲,何況他都八十多了。但即使他花樣百出、時而大刀闊斧時而細心設伏,表面上應該更接近解構者德里達的他,實際上回歸延續的還是通向語言之途,憑藉對詩的語言的重新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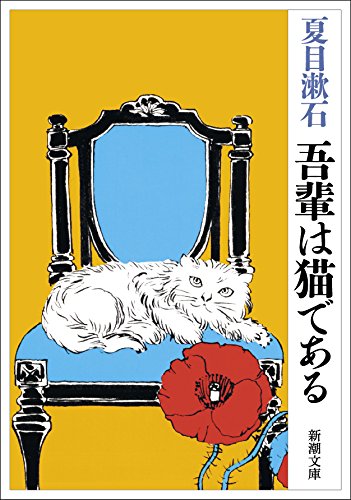
離題,是高達最擅長的,這也是從拉伯雷開始就有的歐洲文學傳統,離題是爲了拓展想象力的空間。《再見語言》開場劈頭就是一句:「永別了,那些缺乏想象力的現實」,接着我們可以看到這現實不單是高達一直批判的冷戰以降的意識形態飽和的現實,不單是歐美主流娛樂至上的世界馬戲團現實,還更多了對技術時代的批判。
高達非常幽默地拍了一部最不像3D電影的3D電影,比前幾年赫佐格用3D技術拍攝原始人洞穴還要出格挑釁。他以其之道還治其之身,技術時代的救贖來自技術的任性顛覆,連Go Pro都可以運用在拍攝中(於是有人諷刺說:高達揹着攝影機在街上蹓躂了一天忘記關機,回來就把亂七八糟素材剪成了一部電影),反3D、聲畫分離、色彩扭曲等都是等閒。越是粗糙之處越讓人反思3D技術是怎樣淪爲掩飾蒼白內涵的視覺奇觀的(試想《一步之遙》),然而正是在這粗糙中不時閃回塔可夫斯基般的靜謐詩意。
這樣一個時代,就需要高達這種難啃的硬骨頭,他的電影對抗普遍的媚俗。米蘭昆德拉不是說媚俗就是羞於談論糞便嗎?
技術常變,詩與哲思永恆。電影中手機不停出現在某些場景,但我們看到的第一個大特寫是男人手機上的索爾仁尼琴頭像屏幕保護圖。結尾出現的特寫則屬於一本破舊的平裝本科幻小說La Fin du A,加拿大作家A.E.van Vogt的《A的結束》,是關於一個不受未來規則玩穿越的人帶出的故事。這一頭一尾正好回答了語言何爲的問題,一個指向對過去(比如說古拉格的歷史)的拒絕遺忘,一個指向對未來的敞開。
這之間,是一個典型的二零一四年的歐洲:不斷的槍聲作爲背景,莫名中彈無端的血橫流;不斷被畫面外的暴力拽走的女性,從她們正在進行的藝術、隱喻的討論中。而隱喻,這個詞反覆出現,卻在表示着在技術神話遮蔽下詩意的淪亡,是靠隱喻所不能自欺解脫的,就像那艘在隱喻中不斷靠近的船,永遠接近不了真相。高達之詩,比隱喻真接,比真相曲折。
這樣一個時代,就需要高達這種難啃的硬骨頭,他的電影對抗普遍的媚俗。米蘭昆德拉不是說媚俗就是羞於談論糞便嗎?「每當你談起糞便,我就談起平等。因爲那是我們最平等的地方。」高達不但在這部電影裏和我們從容談論狗與人的糞便,還拍攝拉屎的男人、放大屎掉下馬桶的聲音,好讓習慣禮節性語言和浮誇唯美技術的人,皺緊他們高雅的眉頭。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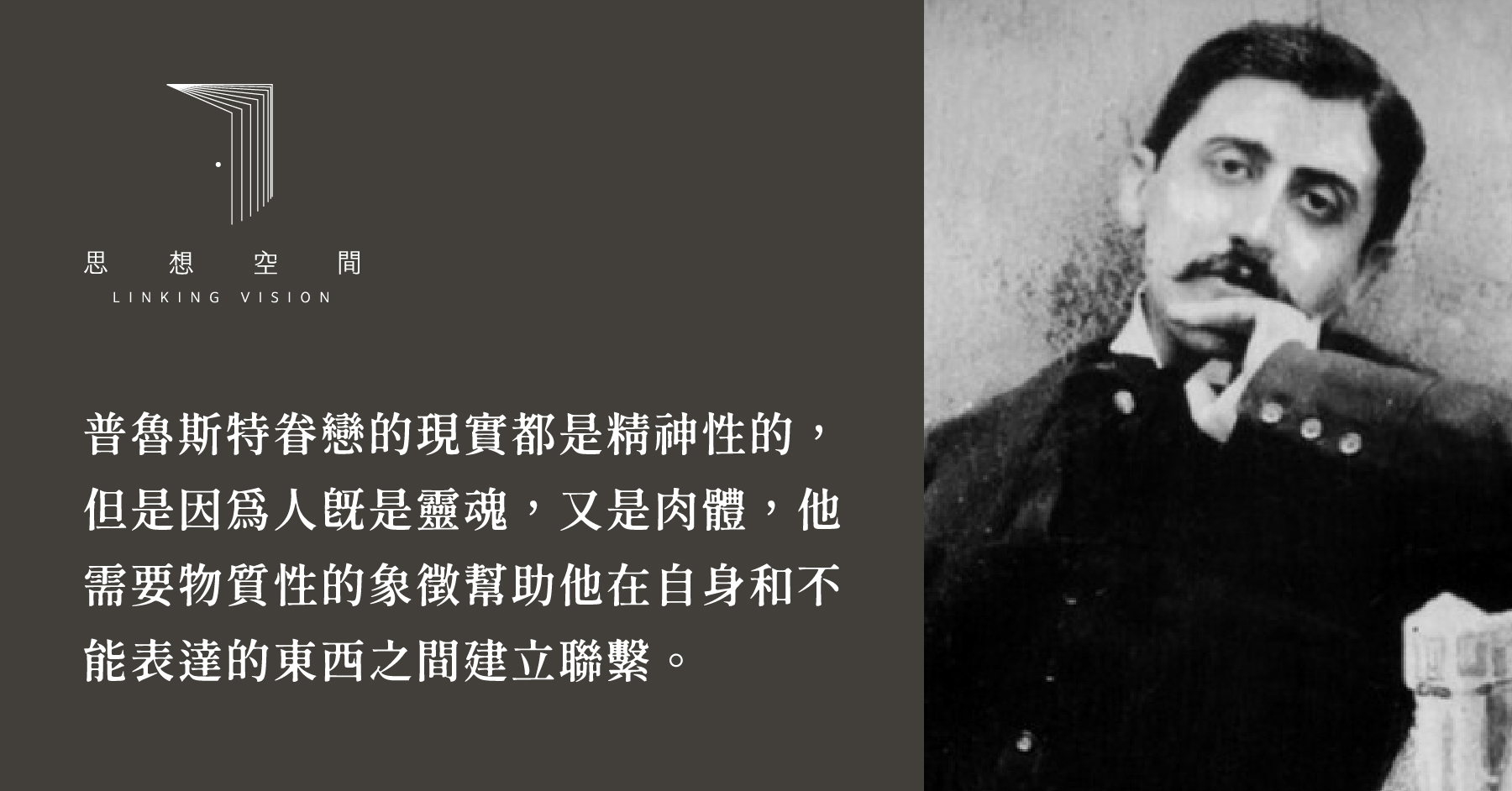

| 閱讀推薦 |

廖偉棠,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 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及香港文學雙年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年度藝術家(文學),現旅居台灣,任台北藝術大學客座副教授。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後覺書》、《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半夜待雪喊我》等十餘種,講演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走近現代詩的四十條小徑》,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系列,散文集《衣錦夜行》、《尋找倉央嘉措》、《有情枝》等。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