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文鈴(寫作者、記者)
編按:近來,台灣一則廣告因模仿越南口音而被抗議,認為該則廣告「把霸凌當有趣,量販口音標籤歧視」,引起各界廣泛討論。1975年4月,越南共產黨拿下西貢,讓載滿難民的船飄蕩海上;此後,越南人移居世界各地,擴大了人們對民族與國家的想像,也引發了不少關於身份認同、移民二代處境的探討。2022年,聯經出版《誰是外來者》,作者黃文鈴往返德國與臺灣,採訪超過50位越南移民,聽他們述說驚心動魄的親身經歷,探討理想的族群融合可能之道。(*本文摘自《誰是外來者》第五章〈自我認同的糾結〉,標題為編者擬。)
你到底從哪裡來?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截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德約有七萬名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越南裔移民。
德國政府是這樣算的,凡雙方父母在血統上有一方不是德國人,則視其為具有「移民背景」。其中,真正經歷過遷徙過程來到德國的第一代移民,則是擁有「移民經驗」的人。
越南移民在德國出生的後代,並不具移民經驗。他們自三歲進入幼稚園開始學習德語,與在家用越南語交談的父母,自此出現文化與語言的分歧,甚至如高牆般的隔閡。
從外觀來看,他們的亞洲臉孔,在同儕裡顯得與眾不同。又因為家庭背景的緣故,從小就夾雜在兩種文化、語言與東西方不同的價值觀之間。
這些在文化夾縫中成長的孩子,等到年紀稍微大了一些,便開始反思:「我到底是誰?」
在這個章節,我採訪了十多位越南移民子女,他們在年少時代幾乎都曾困惑過:為什麼自己與身邊的人這麼不同?我到底來自哪裡?而這些問題並不容易找到答案。
在德國社會裡尋找自己的定位,彷彿是每個越南移民後代不可避免的課題。黑頭髮黃皮膚的顯著不同,面對「你來自哪裡」這樣看似無意的問題,背後的好奇可能觸發被問者的矛盾情緒,或隱忍多時的情緒風暴。
「我很恨他們假設我不來自這裡」,陳艷在受訪時恨恨地說。在第一章曾提及,她的父母分別是越南船民與契約工。她認為,若從第一批越南船民來到德國算起,已經超過四十個年頭,在這裡繁衍下一代也實屬正常。但問她「妳來自哪裡?」的人們,卻似乎從沒這麼想過。
她抨擊:「他們應該要有自覺,這樣的問題會讓回答的人覺得他們不屬於這裡,而是他們國家的一個客人。」
她的好友鄭秋草(Thu Thao Trinh)則認為這個問題沒有非黑即白的答案。她的爸媽都是前契約工,之前她會回答自己來自越南,但有一次被同事糾正,來自越南的是她的父母。
她笑說:「我花了一點時間才想通這件事。對啊,我爸媽來自越南,而我在這裡出生長大。」自此之後,她一律回答她來自德國,但內心仍有一部分覺得自己是越南人,那是屬於她的根、她的文化、她爸媽的語言。
面對「妳來自哪裡」這個被問過不下數百次的問題,陳艷有自己的回答原則。如果別人毫無頭緒、劈頭就問,她會理所當然回答,自己來自柏林,若再追問,則接著回答,自己出生於紐倫堡或巴伐利亞邦。
但更常見的情況是(這個情況也發生在許多我採訪的第二代越南後裔),對方鍥而不捨問她:「原本」來自哪裡、或她「究竟」來自哪裡?彷彿對上述答案都不滿意。她遇到這種情形才會回答,爸媽來自越南。但這不代表她是越南人,她反倒始終認為自己是土生土長的德國人。
這些移民後代,在尋找自己定位的過程中,也免不了思考自身與越南的連結。
爸媽都曾在薩克森邦小鎮弗賴塔(Freital)擔任契約工的黎玉中(Le Ngoc Trung)認為:「即使我在(德國)這裡出生,我沒有忘記我的根在哪,用越南話形容就是飲水思源。」
從小爸媽就強調他是越南人,規定子女在家只能說越南話,餐桌上天天都是越南菜,晚餐後家人的娛樂便是一起收看越南連續劇或歌唱秀,這樣的潛移默化下,他根深柢固認為自己來自越南。
受訪時仍在柏林就讀大學的他,至今已去過越南多達六次,祭拜過祖先,親身感受到越南家人與他的連結。「對我來說,越南是我第二個家,那是我的身分,我的根。」
青春期的她很孤單,非常討厭自己。為了不落實外人對移民小孩的刻板印象,她在班上的德文成績始終比其他德國孩子好,對德國歷史、文學、藝術瞭若指掌⋯⋯
我想變成白人
但不是每個越南移民後代,都能這麼順遂地找到自己在德國社會的定位。
以第二章曾提及的武・凡妮莎為例,她的爸媽都曾是契約工,她則趕上一九九一年的嬰兒潮出生。
見面採訪時,她一身勁裝,全身黑衣黑褲,腳踩黑色皮靴,眼線細細勾勒出的雙眼眼神銳利,嘴唇塗上暗黑色口紅,散發出一種冷豔色調,與她一向在媒體曝光的穿著形象完全相符。彷彿黑色是她的保護色,她想透過這樣強大的氣場告訴外界:她不是好惹的。
若再深聊一些,了解她的成長背景,便能完全理解她為何選擇武裝自己。
凡妮莎一家五口住在德國南方巴伐利亞邦,一個叫做瓦爾德基爾興(Waldkirchen)的小城鎮。那裡是她的爸媽選擇申請難民庇護後,被分發到的難民營所在。她則在一處專門提供給難民的集合宿舍,一直住到六歲。
多年後,她撰文揭露在難民營長大的童年 ,讀來讓人忍不住倒抽一口氣:
當黑夜來臨,蟑螂們會從櫃子後方爬出來找食物碎屑。但牠們不會這麼輕易得逞。許多蟑螂都死在我們用牙籤或膠帶做出來的陷阱裡。早上起來我會四處搜尋牠們的屍體。
在這家收容了一百名難民的宿舍裡,只有三間淋浴間、四間廁所,男人貪圖方便就直接尿在走廊的牆上,他們的兒子也是,老是笑著將黃色尿柱噴灑在柱子上。廁所也糟透了,一名女人甚至在廁所裡了結生命,從狹窄的窗戶往下跳、落在外頭的人行道上。聽大人們說她是蒙古來的,很少人知道她的來歷。
凡妮莎如此不尋常的童年,即使在全家搬進新公寓後,並未變得比較輕鬆。在家裡她排行老大,弟弟妹妹比她晚幾年出生,由於爸媽沒日沒夜拚命工作,她從很小的時候就得姊代母職。「我要煮飯給他們吃、陪他們寫功課。我只是個孩子,卻得扮演大人的角色。」
等到開始上學了,更是一段在荊棘裡漫長摸索自我認同的路。
瓦爾德基爾興是座保守的天主教小鎮,鎮裡住著約一萬兩千名羅馬天主教徒,僅有寥寥幾戶越南家庭。在凡妮莎讀的文理高中(Gymnasium),Ⅱ她是唯一的有色人種。從小就因為長相、膚色、髮色和四周的人不同,「總是被霸凌、被別人推倒、被打、被嘲笑,他們在一旁還唱和著Ching Chang Chong(對黃種人的侮辱性稱呼)。」
有次和班上女生發生口角,對方甚至罵她:「妳應該被毒氣毒死。」暗指她下場就該像那些命喪集中營的猶太人一樣。這般惡毒的言論,她永遠記在心裡。
那時她年紀還小,還不懂得什麼是種族歧視,「我沒有反擊,因為我覺得都是我的問題,我才是那個和所有人都不同的人。」
孩提時代的凡妮莎,留著一頭烏黑長髮,但每次畫自畫像,她都會把自己畫成金髮、白皮膚。「我討厭自己的黑髮、細細長長的眼睛,這些特徵讓我深信自己有問題,為什麼我不能跟其他孩子一樣?」
和同儕不一樣的,還有爸媽取的越文名字。凡妮莎的本名是武紅雲(Vũ Hồng Vân),每次開學,新來的老師總要她在全班同學面前唸出自己名字的發音,或者要求她說一段越南話。德國人發不出正確的音,全班便笑成一團,連老師也跟著笑,讓她覺得渾身不舒服。
事隔多年她回想這段求學生涯,直言:「老師們也是霸凌者之一,他們並沒有盡到保護我的責任。」
凡妮莎坦言,青春期的她很孤單,非常討厭自己。為了不落實外人對移民小孩的刻板印象,她在班上的德文成績始終比其他德國孩子好,對德國歷史、文學、藝術瞭若指掌,「我做這些努力只是想證明我自己,我想變成白人。」
那時的凡妮莎在校表現優異,一口流利德語完全沒有口音。但男友的媽媽僅因為凡妮莎的亞裔背景便反對兩人在一起,理由是彼此來自不同文化,不會有好結果。
撕不去的「越南人」標籤
對於成天工作總是不在家的爸媽,她也曾心有怨懟,「我因為爸媽不會說德語覺得很丟臉。那時我還不明白他們是真的沒有機會學德文,當時沒有免費德語課,他們得賺錢養家,我媽甚至一人做三份工作。」
當時她不明白,為何爸媽無法像白人父母一樣,以流利德語侃侃而談。這樣的羞愧轉為憤怒,這股憤怒深深的埋進她心裡。身為孩子,她能做到最大的反叛僅是不告訴別人她父母來自哪裡。她捏造自己的來歷,或是堅稱自己是德國人、不是越南人。當受到別人霸凌,她不允許自己哭,更不能在幼小的弟妹或是忙碌的父母面前表露出來,只能將難過的事寫在日記裡。
一直到年紀稍長,她交了第一個德國男友,才開始反省這個過去從未深究的問題:「我是誰?」
那時的凡妮莎在校表現優異,一口流利德語完全沒有口音。但男友的媽媽僅因為凡妮莎的亞裔背景便反對兩人在一起,理由是彼此來自不同文化,不會有好結果。
凡妮莎聽到這樣的武斷說法,又驚又氣。「我深信自己非常融入德國社會,我德文非常好、在校成績很好,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是越南人。」
她提高音量強調,「我那時越南話講得很差、很少跟父母互動,我認為自己就是個德國人,我真的非常希望自己是德國人。」
直到被男友媽媽以種族背景為由否決,她才明瞭,原來自己做再多都不會被認同為德國人。這張越南人的標籤,會一輩子黏在身上怎樣也撕不去。
於是她開始大量閱讀,深究內心深處身為越南人的羞恥,反省過去為了想成為德國人付出的種種努力,也刻意參加有色人種的聚會,與同樣具有移民背景的人,討論自己的成長經驗。
她反思,貼在自己身上的「越南人」標籤,既然擺脫不掉,她可以用越南人的身分主動反擊。
反擊,以越南人的身分
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當年為了逃離納粹德國的魔掌逃亡到美國。她曾說過一段話:「如果因為身為猶太人而遭到攻擊,那你就應該以一個猶太人的身分反擊。」
這是凡妮莎最喜歡的一段話,她反思,貼在自己身上的「越南人」標籤,既然擺脫不掉,她可以用越南人的身分主動反擊。當外界已經習慣越南移民的安靜無聲,彷彿是德國社會一個隱形的群體時,她想突破這個既定印象,把描述自己族群的話語權從外人手中拿回來。
她想了解,生活在德國的越南人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群體?
二〇一八年,凡妮莎和同為越南契約工後代的記者陳明秋(Minh Thu Tran),因此共同成立Podcast節目:「Rice and Shine」。每個月邀請同樣具有越南移民背景的來賓,談論屬於自己族群的議題,像是政治、文化領域,或是熱門時事。例如:新冠肺炎時期許多過去在紡織廠工作的前契約工,又重拾舊業,縫製布口罩送人或販售等。她們請這些人上節目,說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觀點,聽他們的聲音。
凡妮莎說,成立這個Podcast並非為了建立一座連結德國與越南移民的橋梁,而是透過這些訪談,「問我們自己是誰?我們想要成為什麼?我們想從人生裡獲得什麼?」一般而言,德國媒體較常報導越南船民的故事,但越南契約工的觀點,卻鮮少獲得相同的關注。這個節目則彌補了這一塊空白。
節目開播後,陸續收到廣大聽眾迴響,字裡行間充滿了澎湃的情感與感謝。兩位主持人收到好幾封長達數頁的電子郵件,傾訴過去從未受到德國媒體重視,但節目替他們說出了心聲,並讚賞節目內容並不帶有過往對於越南移民的刻板印象。
「我因此知道我們正在做的事非常具有威力,因為以前沒有這種東西,我們總是被他者以某種特定的名詞描述,這是我目前為止知道,由我們自己形成的論述。」凡妮莎說。
透過對話,或許能讓對方更同理與尊重非優勢白人族群的想法,這樣就促成了所謂社會融合的第一步。
絕不噤聲
採訪中,凡妮莎提到一段人生中的小小勝利,也是她人生中首度敢於正面迎擊種族歧視,卻帶給她更多的反思。
四、五年前的某一晚,她和妹妹去跳舞,從舞廳走出來正要去買薯條吃。前方來了三名金髮男孩,對著她們大喊她再熟悉不過的「Ching Chang Chong」,一反以往總把情緒往肚裡吞,她轉過身對著他們說:「你說的到底是哪國語言?這根本不是語言,你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嗎?」
對方聞言只是哈哈大笑,凡妮莎再試圖曉以大義,最後被妹妹拉著離開現場。事後她回想這段經歷,心中百感交集。
一方面我替自己感到驕傲,人生中第一次終於反擊回去,但另一方面對我來說,那是個毀滅性的時刻,別人根本不需要恰當的語言就能羞辱你。我以一個花了這麼多努力學習的語言來反擊,組織出一個清楚有條理、有邏輯的論述,但他們只是繼續以聲音來回應,這讓我覺得非常無助,因為我根本無能為力,即使是那個語言也無法保護我。
她坦言,反擊回去是很累人的,她也不覺得自己能從中獲得力量。就像她身為記者,長期以來總會收到讀者寄電子郵件或透過推特,要她「滾回妳的國家!」但她並不因此噤聲停筆,因為唯有透過發聲才有可能達到社會的理解與尊重。
她也和陳艷一樣,很排斥剛認識的人不斷探問「妳到底來自哪裡?」在她看來,這個看似無害的問題,其實是想探究她的家族歷史與傳統背景,這對她而言是很私人的問題,不應該被強迫公開。
她在這樣的問法裡看見的是一種殖民歷史的連貫性,「在大部分的文化裡,擁有較多權力的人,能問那些沒權沒勢的人問題。」她舉例,像是殖民者、傳道士、人類學家到了殖民地,追問當地人私密的問題,強迫他們回答,當地人知道若不合作恐怕會惹上麻煩。而這樣的思維也呈現在當德國人隨意探問她的家族史,展現的是一種上對下的特權。
對此,她的做法是明白告知對方她的感受。問話的人也許沒有察覺這個問題背後代表的含義,但透過對話,或許能讓對方更同理與尊重非優勢白人族群的想法,這樣就促成了所謂社會融合的第一步。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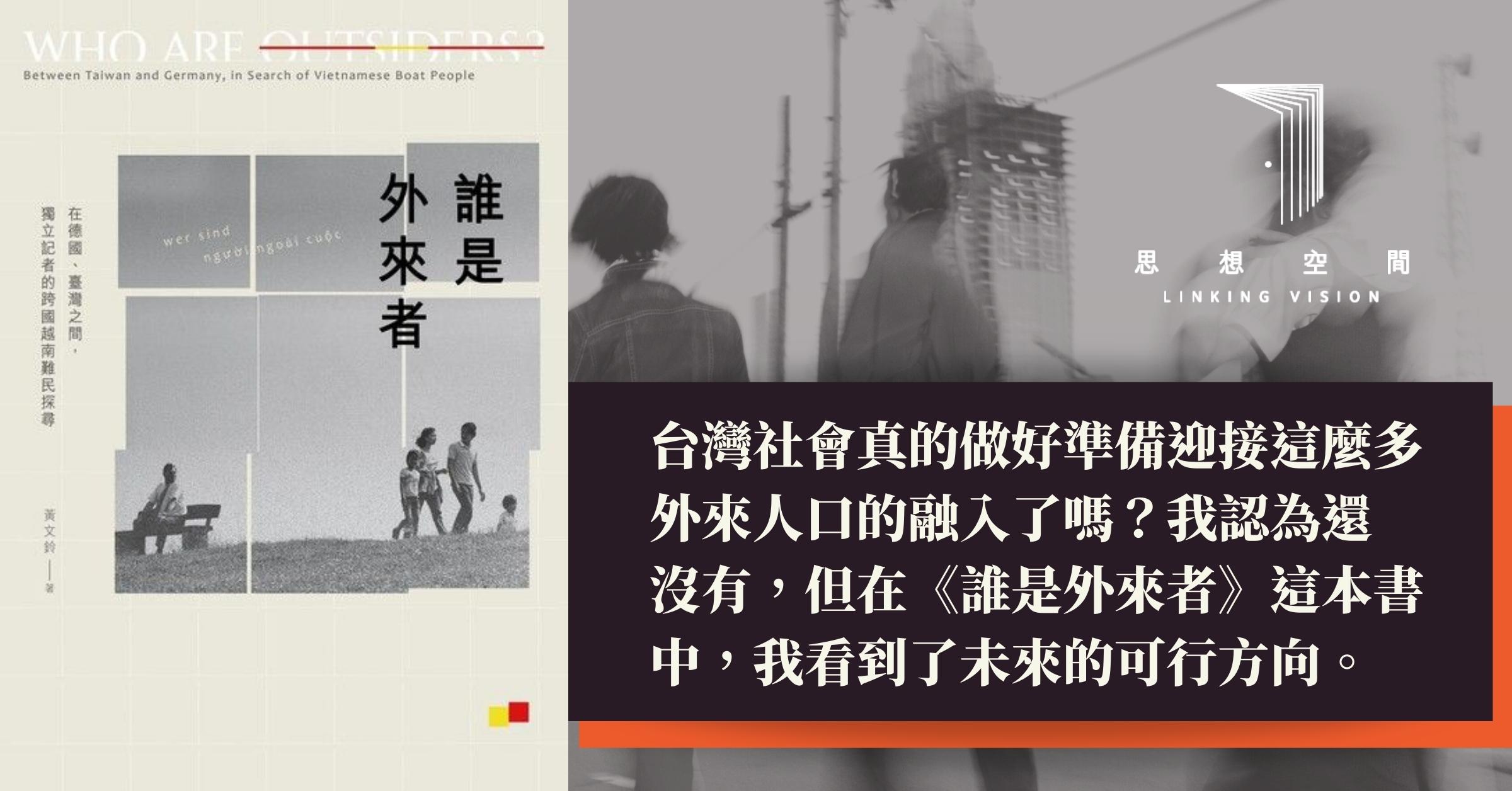
阿蘇卡:讀《誰是外來者》想像台灣未來:我們成為一個多元社會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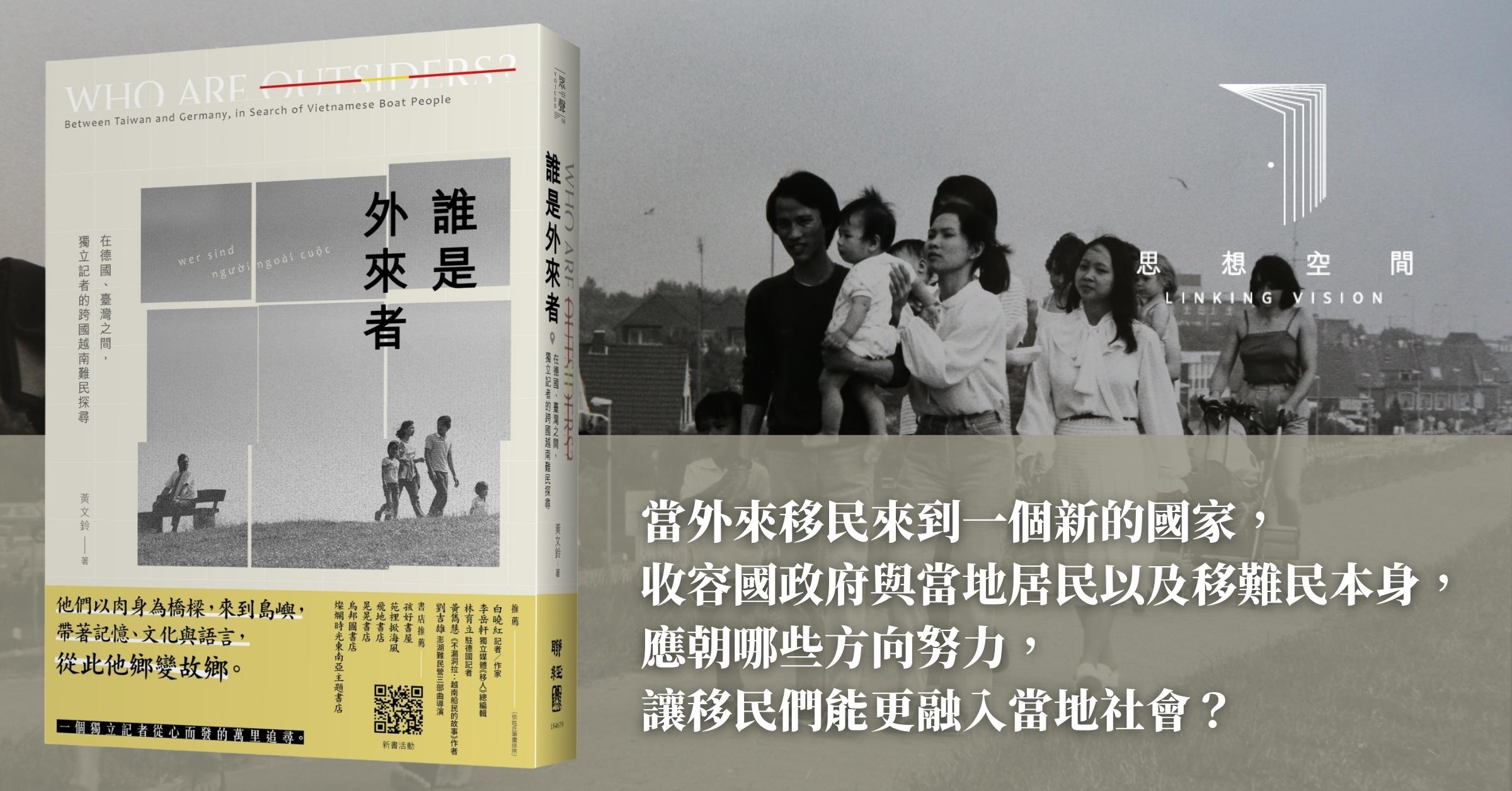
黃文鈴:寒冬柏林,藏在一碗越南河粉中的疑問——誰是外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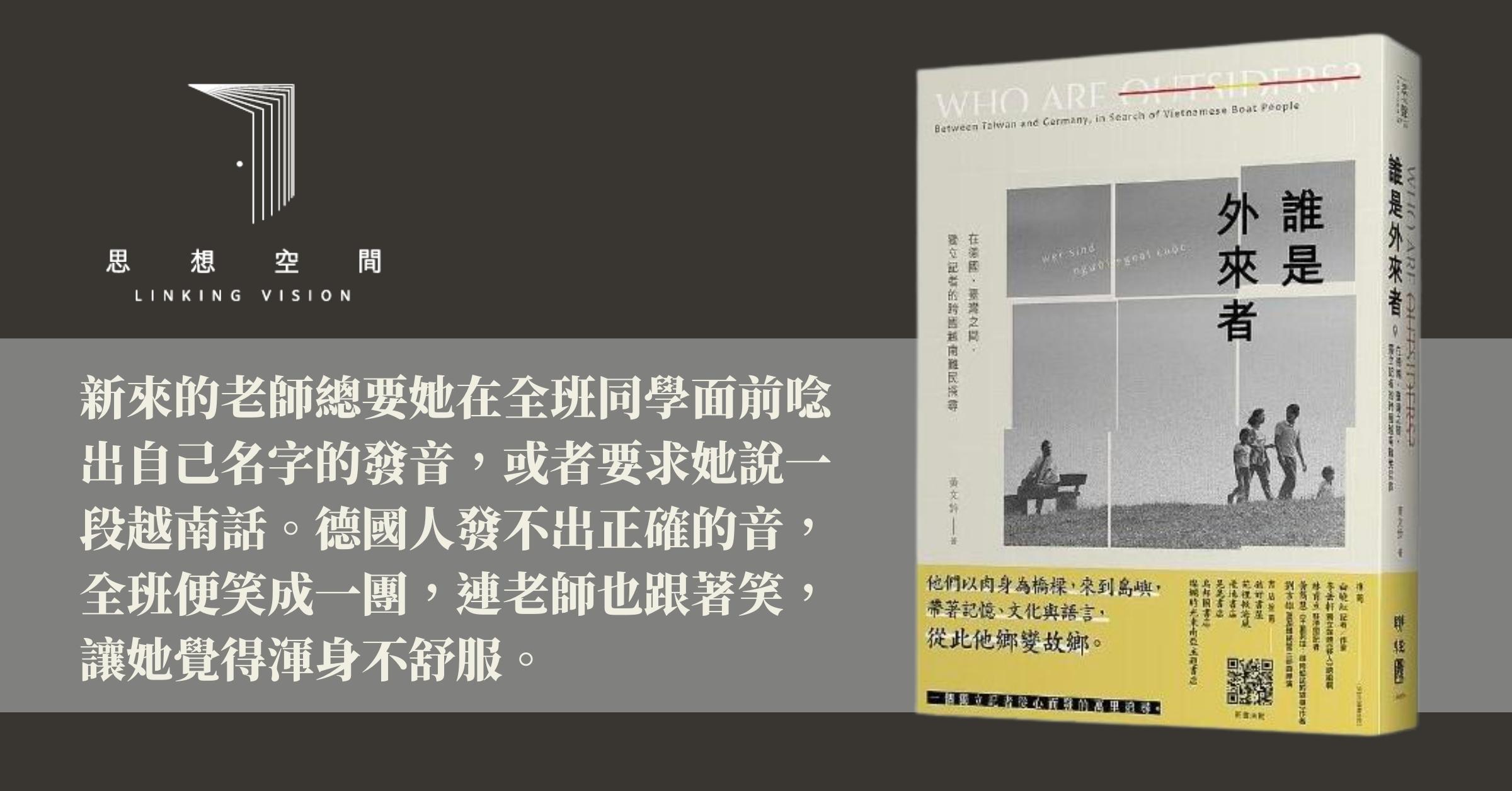
黃文鈴:在荊棘裡,她們迎擊「身為越南人」的羞恥
| 閱讀推薦 |

菜市場長大的孩子。35歲那一年決定離開熟悉的臺灣,目前定居柏林邁入第五年。喜歡這裡的自由跟可能性,但常常想念臺灣各種好吃的美食。曾獲柏林政府文學研究補助、國藝會長篇小說補助、文化部青年創作等補助計畫;曾任國內報社記者、《報導者》特約記者,因為想第一線採訪難民,選擇出走臺灣。目前定位自己是寫作者與記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到達很遠的地方,讓更多人聽見受訪者的故事。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