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晉(Sage Creative Foundation研究員)
編按:1918年5月15日,魯迅《狂人日記》首發於《新青年》月刊,一度被認為是現代白話中文小說的鼻祖。如今百年已過,我們如何再看文學中的狂人?革命之後,我們再藉小說裡振聾發聵的聲音問道:「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2018年,《狂人日記》面世百年之際,「四季書評」邀請學者李晉撰寫了這篇文章;四年後,目睹著疫情下的新管控,我們再度回顧魯迅筆下的狂人,思考現實生活的荒謬。
在現代中國研究中,通常圍繞「激進」、「反傳統」、「革命」等主題來進行討論,如林毓生先生在1979年《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主義》中就指出,在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革運動中是以思想爲導向引導政治、經濟的改革,而在五四一代中,雖然很多知識分子如魯迅、陳獨秀、胡適在各種具體立場上所持觀點各不相同,但有一點非常一致:就是對於中國傳統價值的徹底否定。在林先生看來,導致這種反傳統的是因爲西方文化不斷的進入,傳統政治秩序的瓦解以及中國內在的文化傾向。
很多對中國現代思想和社會變革的研究,通常會將中國放在一個傳統瓦解、面對西方衝擊進行回應,或中國傳統思想發生內在轉變等角度來進行解釋。這種「東西方」對立的構建,讓思想史和現代中國轉型成爲了內在邏輯結構中的深層共識,也就是,作爲主體的「中國」面對「西方」或者一個現代的「他者」所進行的種種反應。同時,最近的思想研究的論述以一種表面倒置的方式覆蓋在這個深層的結構上,用「東方」這個他者來反對「西方中心主義」。這點在當下流行的加州學派的理論中最爲明顯,即以一種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經濟決定論來將 「中國」作爲他者反對 「西方中心主義」。
然而,一個弔詭的事實是,在百年前,不僅中國感受到一種內在生存和思想轉變的壓力(甚至被稱爲「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同一時期,西方事實上也正面對着一種生存的危機和焦慮。
「歷史主義已經將心靈從教條主義的殘餘中解放了出來。但是誰能夠檢驗這個徹底的相對主義產生了什麼呢?」
西方的衰落
在上世紀初,西方學者的作品中也充滿對自身危機的焦慮。首先一個表現就是,斯賓格勒在一戰後很快發表出版的《西方的衰落》一書(1918)。「命運」、「焦慮」、「死亡」和「衰敗」這些詞充斥着這本書,繼而從這本書中發展出了「激進歷史主義」,指出人類(至少是西方)已經走上了衰敗的道路。這點背景很重要,它一方面影響了湯因比寫作《歷史研究》,一方面也爲後來的存在主義鋪平了道路。
從思想史可以看到西方歷史觀點的脈絡和變化。歷史進入到現代西方思想中,是以維科反對笛卡爾的機械數學觀和黑格爾反對康德的牛頓式的哲學,所引入到哲學的沉思中。在逐漸形成的這種歷史主義中,無論是被稱爲「絕對精神」還是「民族」「國家」,都和世界歷史逐漸交融在一起,向前發展。西方文化肩負着一種歷史的終極使命,在人類不斷的辯證進步中,最終達到歷史的終結,這種論點我們在福山《歷史終結及最後之人》中仍舊是其翻版。
然而,在1910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讓這種歷史進步觀遭到衝擊,如荷蘭現代哲學家和法學家杜伊維爾(Dooyeweerd)所說,「從此以後,西方文化纔不再被視爲是世界—歷史的中心,而是和阿拉伯、印度、中國和其他文化一樣是一種特殊的文明。」然而,歷史主義本身(從孔德到馬克思主義)逐漸侵襲了西方文明的根基,並且開啓了一種虛無主義,以至於歷史主義的重要代表狄爾泰在70歲時反思到,「歷史主義已經將心靈從教條主義的殘餘中解放了出來。但是誰能夠檢驗這個徹底的相對主義產生了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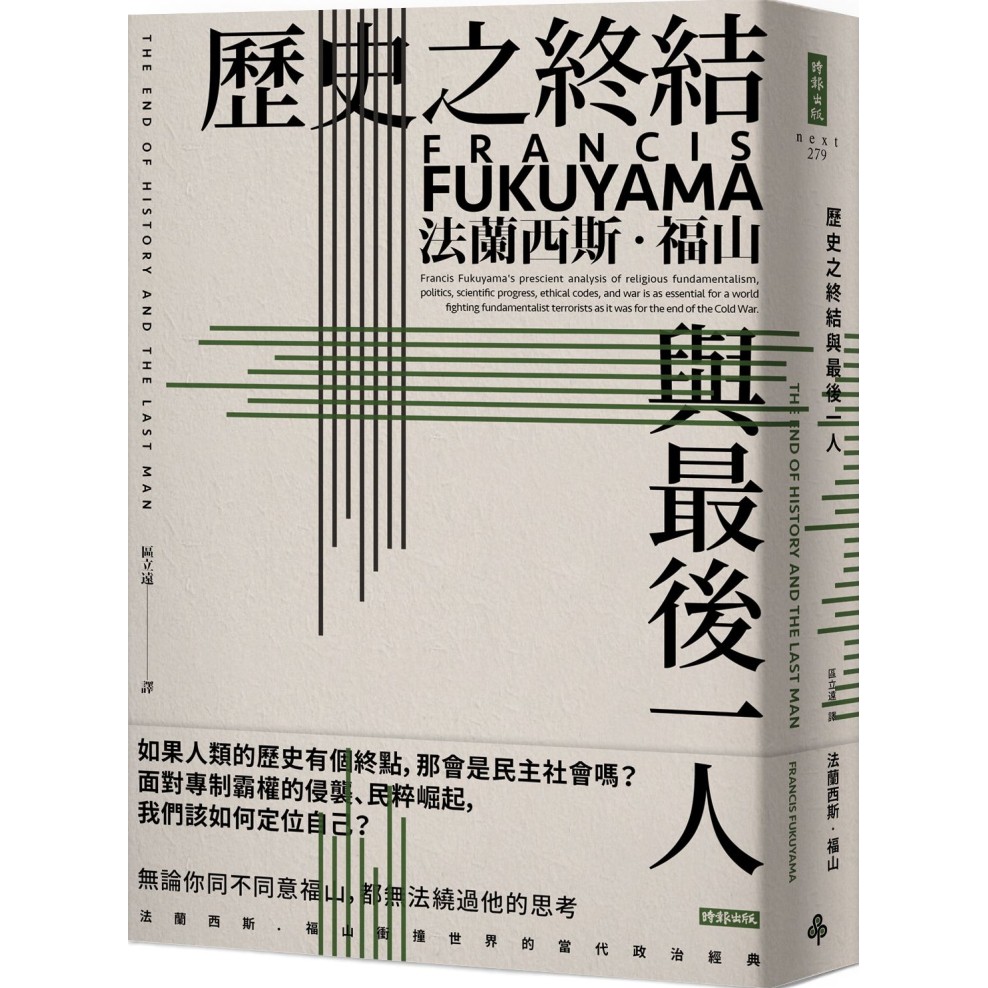
現代的群衆—人已經喪失了自身,而將自己視爲被拋入到一個毫無意義的世界中,在這個世界中,對於更好的未來他們不抱有任何的希望。
《快樂的科學》中的狂人
這一相對主義所產生最後的結果就是「謀殺上帝」。此事件最早的徵兆表現之一是,在1882年出版的《快樂的科學》中(斯賓格勒恰恰代表了一種尼采主義的傳承),在第三卷一開始,尼采就宣稱:「上帝死了」。然後,在關於狂人(the Mad man)的警句125中,他論述到一位白日提着燈籠的狂人,在市集中呼喊,「我找上帝!我找上帝!」遭遇到一群不信上帝的人的譏笑。衆人揶揄他,有人說,上帝失蹤了嗎?迷路了?或者流亡了?逃跑了?在譏笑聲中,狂人在他們中間,狠狠盯着這些人,宣告到:
「上帝哪裡去了? 讓我們告訴你們吧!是我們把他殺了!是你們和我殺的!我們大家都是兇手…我們是否會如同穿過無窮的虛無那樣迷路呢?…上帝死了,永遠死了!是咱們把他殺死的!我們,最殘忍的兇手,如何自慰呢?那個至今擁有整個世界的至聖至強者竟在我們的刀下流血!誰能夠擦拭掉我們身上的血跡?用什麼水可以洗淨我們自身?我們必須發明什麼樣贖罪的慶典和神聖的遊戲呢?這偉大的業績對於我們是否過於偉大呢?我們自己是否必須成爲諸神,以便與這個偉大的業績相稱呢?從未有過比這更偉大的業績,因此,我們的後代將生活在比至今一切歷史都要高尚的歷史中!」(此段文字參考黃明嘉譯本)。
在尼采筆下的狂人所採取的行動是,他在尋找上帝!但是,他對一群不信上帝之人卻問到的關鍵問題是,「上帝哪裡去了?」人如何能夠謀殺掉一位上帝? 尼采藉着狂人之口問圍觀諸人:人是否在虛無中迷失掉?如果是那樣,那麼在狂人的尋找中,他所找到的不是一位死去的上帝,而是活着的諸神。沃格林也問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謀殺上帝何以可能?就如尼采藉着狂人的口所說出的, 那謀殺上帝的就必須稱爲諸神,來和偉大的業績相稱,因此對於尼采而言,狂人所需要找的神,並不是存在的舊神,而是那些了謀殺了這位上帝的人,人必須藉着謀殺成爲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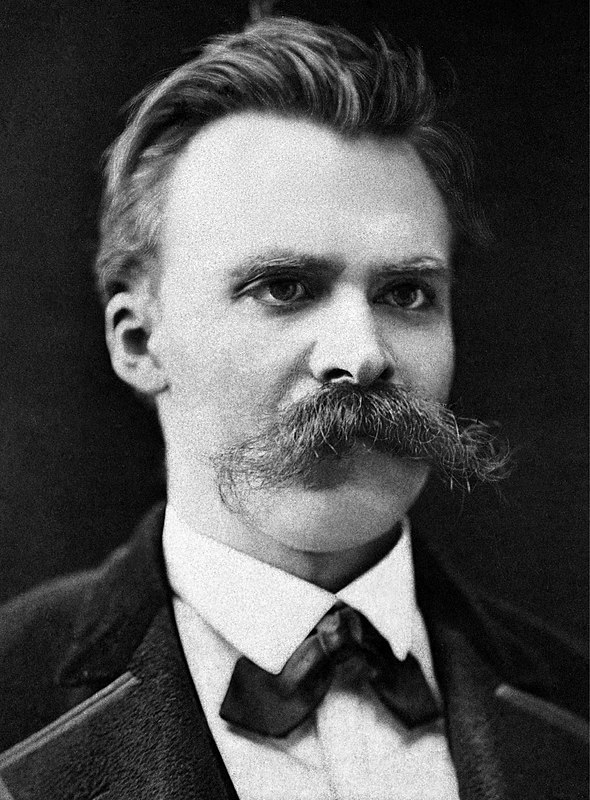
人們通常會膚淺的理解尼采的「上帝之死」。相反,尼采所感受到的卻是歐洲思想所暴露的真正的病癥——「上帝」的概念逐漸在笛卡爾爲開端的現代思想中,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全面被排除;人無法在生活中感受到一位活着的上帝,上帝被徹底排除在人—內在世界的範圍內,人則彷彿被拋在了一個漫無目的的物理宇宙中,需要重新尋找自己的意義。如杜伊維爾對此的總結說,當下,普遍被世俗化的人們已經喪失了對於宗教的真正興趣。他已經陷入了一種靈性的虛無主義的陷阱之中。他否認一切的屬靈的價值。他已經喪失了一切的信仰,除了他自己慾望的滿足之外,拒絕任何高於慾望的理念。甚至連人本主義對於人的信仰,對於人理性的力量來支配世界,企圖將人高舉到一個更崇高的自由和道德的水平上,連這些也不再成爲當下群衆—人的心靈中所要訴求之物。對他而言,上帝死了;兩次世界大戰已經摧毀了人本主義關於人的理念。現代的群衆—人已經喪失了自身,而將自己視爲被拋入到一個毫無意義的世界中,在這個世界中,對於更好的未來他們不抱有任何的希望。
尼采自身並不是一位虛無主義者,而是試圖去克服這種虛無主義。在《道德的譜系》中,他認爲傳統的道德真正的基礎不是善而是仇恨,是生命弱者,是奴隸對於強者,貴族的報復,西方宗教所營造出來的表面的價值,不過是弱者和奴隸的復仇。只有當「上帝之死」這一思想運動才真正構成了西方社會道德偽裝的瓦解,而在這種道德的真空中,需要的是產生出新的超越之人(Ubermensch)。在尼采的歷史哲學中,他重新構建了歷史的論述,第一階段是荷馬史詩般的貴族,而第二階段是弱者和奴隸的代表祭司階層和貴族之間的鬥爭,以祭司所創造的道德掩蓋了真正的權力意志,成爲西方主導的道德,而在上帝之死之後,是虛無主義和道德重構的時代,需要的是超越善和惡,恢復一種真正的權力意志。這在早於尼采的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經表現了出來。對此,政治哲人沃格林對這個象徵進行了分析:
有必要澄清一下這一象徵……因爲它出現在一種魔幻的語境下。必須確定在魔術時,存在秩序真正發生了什麼。一樣事物的本質不能被改變,不論誰試圖「改變」其本質,就毀滅了那樣事物。人不能講自己變成一個超人。要造出一個超人的企圖,就是要謀殺一個人。從歷史上來看,對上帝的謀殺之後,不是出現超人,而是人被謀殺:諾斯替主義理論家們的決定之後,是革命實踐者們的屠殺。(《沒有約束的現代性》英文版284頁)
在《沒有約束的現代性》中,沃格林也再次提出,對上帝的這場謀殺之後,所產生出來的結果不是超人,而是對於人的謀殺。西方世界對於上帝的反叛,所造成的不是超人,而是人的分崩離析;對於宗教的批判,造成的不是宗教的瓦解,而是現代國家取代了上帝,成爲人造宗教(Ersatz religion)。
沃格林談到了各樣極權主義群衆運動的表現根源,都在於本體論上的失序、精神的瓦解。在沃格林給出的諾斯替主義的運動的名單中,我們看到不僅僅包含了實質性的群衆運動、法西斯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還包含了一些思想性的運動,如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 實證主義和心理分析學。正如沃格林所說的,這些大衆運動並非一種自發的現象,每一種都有其思想的根源,儘管一些思想性運動(如實證主義和心理分析)最終並沒有形成政治性的大衆運動。早在聖西門和孔德的「人造宗教」中,在馬克思的思想體系中,我們都看到了通過革命來創造「新人」,建立自由王國的觀念;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中,我們看到其宗教的根源。
在1938年沃格林早期的文章《政治宗教》中,他指出,儘管反對宗教者和無神論的運動者拒絕承認他們的狂熱具有宗教性的根源,他們卻的確是在宗教之外的事物中尋找神聖的依據。上帝之死後發生的,是上帝主權的至高性被排除在世俗領域之外,創造的秩序也被排除在國家之外,從而國家自身取代了上帝。這,就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強調的「可朽的上帝」。沃格林關注到,在霍布斯的利維坦中,這一象徵形式成了極權主義國家,一種諾斯替主義的終極的形式, 排除了超驗神聖的存在。國家自身成爲權力的來源的時候,人就成了非人格化的人,國家則成爲了絕對精神對人的現實體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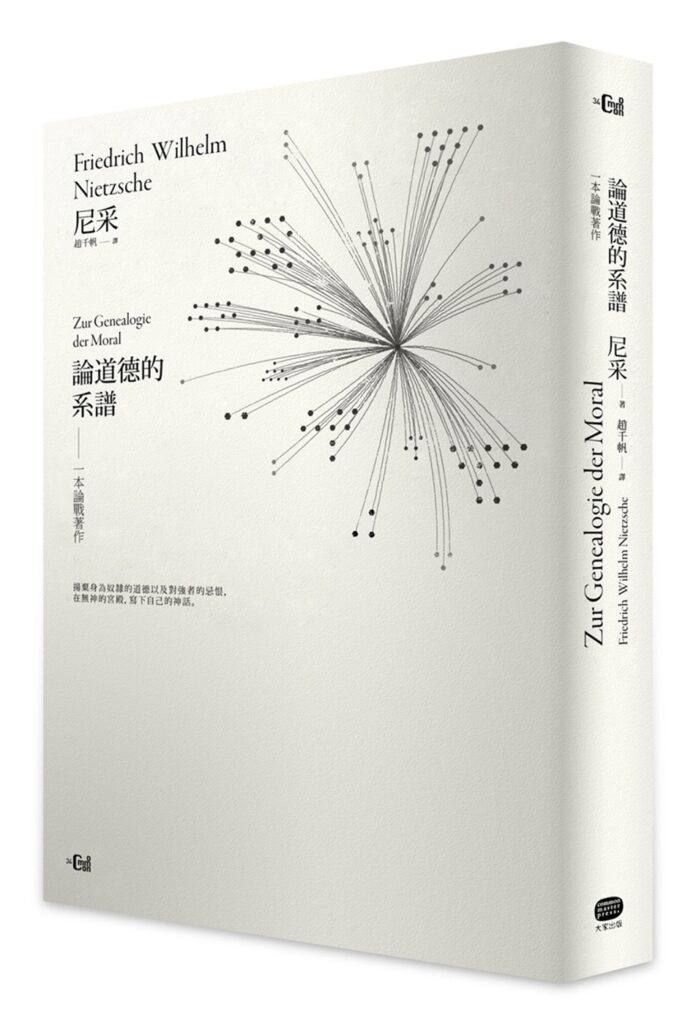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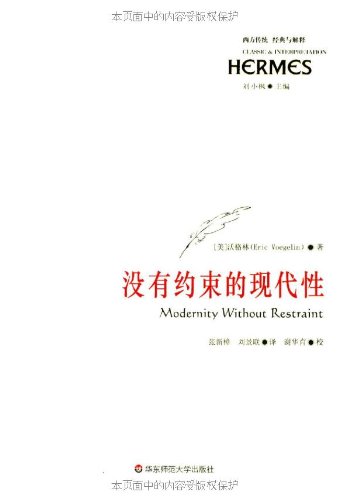
在「喫人的道德」傳統中,人對待人的方式是以物的方式而不是以人的方式來對待,「人」是喫人宴席中的肉,《藥》中的人血饅頭,《祝福》中供他人聽到厭煩的痛苦,以及飯後的談資。
魯迅的「狂人」
1918年魯迅在五四運動前夕發表了極具影響力的小說《狂人日記》。在此前,尼采的學說已經被中國現代的知識分子們所關注。梁啓超和王國維早在1900年代就介紹了尼采的思想和著作。而魯迅在1900年代開始寫作中也展現出了尼采對其文字和思想的影響。這篇魯迅寫於38歲的小說,開篇介紹的是整個背景:「我」和沒有姓名的兄弟兩人曾是中學期間的好友,多年不見,偶然聽到其中一位大病,順道去探訪了他們。然而只見到兄長,他告訴「我」,是他的弟弟生病,曾患「迫害狂」病,現在早就好了,去外地候補差事了,並且讓「我」看了其弟在病中語無倫次的日記。這篇小說的獨特之處就是出現了兩個「我」。一位是作爲外來舊友旁觀者的「我」,而在小說主體的敘述中卻被轉化爲了作爲「狂人」的「我」。
在狂人「我」的眼中,看到了令人懼怕的事情:「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着,這就是喫人的傢伙」。這裡的狂人「我」和尼采的狂人構成了一個共同的意向,就是看到被建構的道德歷史背後另外一種動機。「凡事總需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喫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尼采的狂人是在白日中宣告了「上帝的死亡」。人所做的是需要對過去一切道德價值體系重新思考,過去的價值體系中是弱者的復仇。相比之下,在魯迅筆下的狂人確實是一個弱者,在「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中來反抗一種「喫人」的道德,也就是對於人的謀殺和人格的瓦解。
這種人格的瓦解中分成了三個部分,全部以第一人稱出現在《狂人日記》的拜訪者和記錄者的「我」和狂人的「我」,第三個「我」則是狂人日記所投射出的另一個「我」——「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從這三個「我」恰恰構成了一種歷史哲學的結構:捲入歷史事件中的記錄者,歷史中主體—客體的「我」, 以及構建的歷史本身。這三者的自我意識是彼此轉變的。狂人的「自我」是在曾經無意間喫人和發現喫人的歷史這種矛盾中掙扎,這種矛盾的運動進一步到產生出一個新的意識,就是歷史本身的「我」,四千年的喫人歷史,。狂人的「我」和歷史的「我」最後所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人!」。這種喫人的主體—客體,主奴辯證的運動在魯迅的筆下不經意地流露了出來,他寫到,「自己想喫人,又怕被別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通過馬丁 · 布伯的《我與你》所提供的視角可以幫助理解這點。「我」如果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進行主客體的理解,就只能是一種物化,因此,在「喫人的道德」傳統中,人對待人的方式是以物的方式而不是以人的方式來對待,「人」是喫人宴席中的肉,《藥》中的人血饅頭,《祝福》中供他人聽到厭煩的痛苦,以及飯後的談資。
在《狂人日記》中還暗藏着一條與西方傳統相對應的線索,作爲記錄者和兄弟倆朋友的「我 」 、見證了「狂人」的「我」、和他兄弟三者之間的關係。記錄者並沒有告知外在主體的作者—讀者,那位「狂人」是否活着。究竟是日記中「我」的論述是真實的,還是狂人的兄長告訴記錄者 「我」是真實的?還是存在第三種可能,那就是這位記錄者本身身份的問題。這三方的關係,恰恰是尼采追溯到西方奴隸反抗的道德根源,也就是聖經《創世記》第四章中作爲哥哥的該隱謀殺兄弟亞伯的事件。
在《創世記》這一事件中,有同樣的三者結構。謀殺者該隱被上帝詢問,「你兄弟亞伯在哪裡?」,該隱說到,「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 在上帝—該隱和亞伯之間構成了我—你之間的關係,並且也暗示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的關係是一種看護的關係。然而, 謀殺事件之後,上帝同時作爲見證者和審判者,判罰了該隱「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成爲缺失根的人。人彼此作爲看護者是不能被物化,一旦人不再是人,也無法成爲上帝,而是現代國家運動中的群衆。
但是,我和你之間人的關係,在《狂人日記》中是缺失的。主客體關係對於世界而言,是主奴的關係,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是喫和被喫的關係。一旦將這種關係打破,就等於是將自我意識的第一層徹底的毀滅。因此,在狂人的眼中,他看到了這種物化的關係,在記錄者的記載中,脫離了他者的自我,恰恰開啓了一種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就是:歷史被掩藏在了「喫人的宴席」中。歷史的命運,恰如該隱的命運,是無根的,是流離的。
作爲作者的魯迅是如何解決這個文章中本身所構成的困境呢?竹內好在《近代的超克》中指出,魯迅《狂人日記》不是尼采那樣的虛無,不僅僅是沉默中的爆發,也就是尋找新人,如同尼采試圖尋找新的上帝一樣,重估一切的價值。但是,和尼采所不同、甚至對立的是,《狂人日記》中所尋找的是被喫意義下的弱者,沒有喫過人的人,是沒有被瓦解的人,也是未來之人,然而魯迅依舊錶現了一種對未來的猶疑,「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那麼這個外來的記錄者「我」的身份就成了一個謎,投射在百年中國激盪的變革中,給我們留下了究竟是否是希望呢,這點始終成爲了革命之謎?

不是尼采和魯迅造成了現代世界所產生的危機,而是如同每一個時代危機出現時那些先覺者一樣,他們敏銳地捕捉到了時代問題的徵兆。
西方還是東方?
如開篇所述,如果單純陷入東西方各自的表述中,來構建一個他者,這對於理解中國現代性的展開,還是理解西方現代性的問題,都會陷入一種滑稽悖論。恰恰是在一百年前1918年的時刻,所謂的「東、西方」都感受到一種生存的危機,其表象是外在的政治—經濟的社會運動。東方和西方彼此似乎都在尋找一種可能性的出路。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人類作爲整體的思想動盪時刻。尼采和魯迅所刻畫的兩位狂人構成了整個現代世界的存在結構,也就是在一個無神和無人的世界中。什麼纔是真正的人的問題?在兩次世界大戰後所興起的存在主義和後現代的思潮是這種生存狀況的突出反應。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不是尼采和魯迅造成了現代世界所產生的危機,而是如同每一個時代危機出現時那些先覺者一樣,他們敏銳地捕捉到了時代問題的徵兆。我不認爲他們中的任何一位是虛無主義者。恰恰相反,他們都站在了其對立面,是用一種對即將降臨的絕望和虛無的反抗姿態。然而,他們彼此之間也構成了一種對立,在對人類道德結構的瓦解和重估價值中,他們看到了不同的東西。在過去的道德根基中,尼采看到的是弱者對於強者幽怨的復仇,而魯迅看到的卻是生命中的弱者被擺放在了喫人的宴席之中。不過,在魯迅的意識中,弱者和喫人者是能夠相互轉化爲物化的他者,弱者和喫人者的不同只是因爲宴席中所出的位子。「我」也在幫忙擺着宴席!顯然,百年尼采和魯迅都在召喚一個嶄新世界的來到。此時,「上帝之死」和在喫人之宴席中的「人之死」,構成的結果是現代國家中非人格化的群衆,也就是冷漠的看客、圍觀的人。
在這百年歷史的跌宕起伏中,革命所開啓的不一定是希望,重估的道德未必不是喫人的宴席,新的階級未必就是先進,然而這一切的教訓和代價卻太大了。這一百年來,「人是什麼?」依舊是一個不可逃避的中心問題。我們既不是上帝也無法成爲超人,卻很容易被物化、被奴化。倘若問,現今在看似死水的境況下,人還能做什麼,至多也不過如魯迅所期待的那樣,「自己揹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們依舊沒有逾越過這場持續百年的危機,卻應該意識到「我」對於危機有回應的責任。正如哲人沃格林曾指出的:
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混亂,我們每個人都很願意嘮叨的文明的危機,但這絕對不是命中註定的事情;相反,我們每個人都擁有資深生命之中克服這種精神危機的手段。我們的努力不只是要指明這些手段,更是要指明如何運用這些手段。沒有哪個人是活該陷入到社會的這場精神危機之中的;相反,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 避免這種愚昧,讓自己生活在秩序之中。
延伸閱讀:

撒旦墮落的故事,成為對抗極權的詩文:密爾頓《失樂園》的歷史背景與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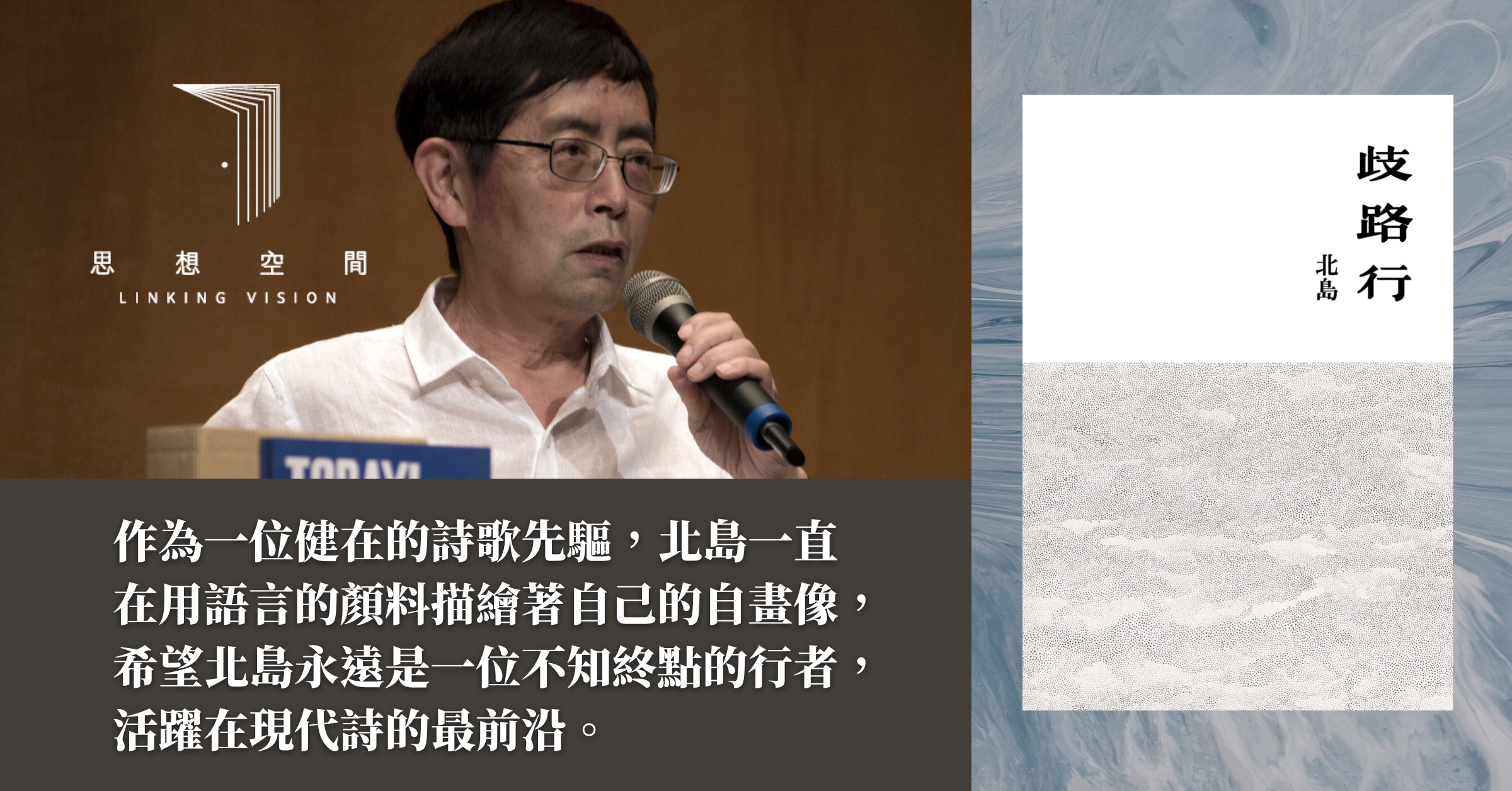
田原:行者的自畫像 ——讀北島《歧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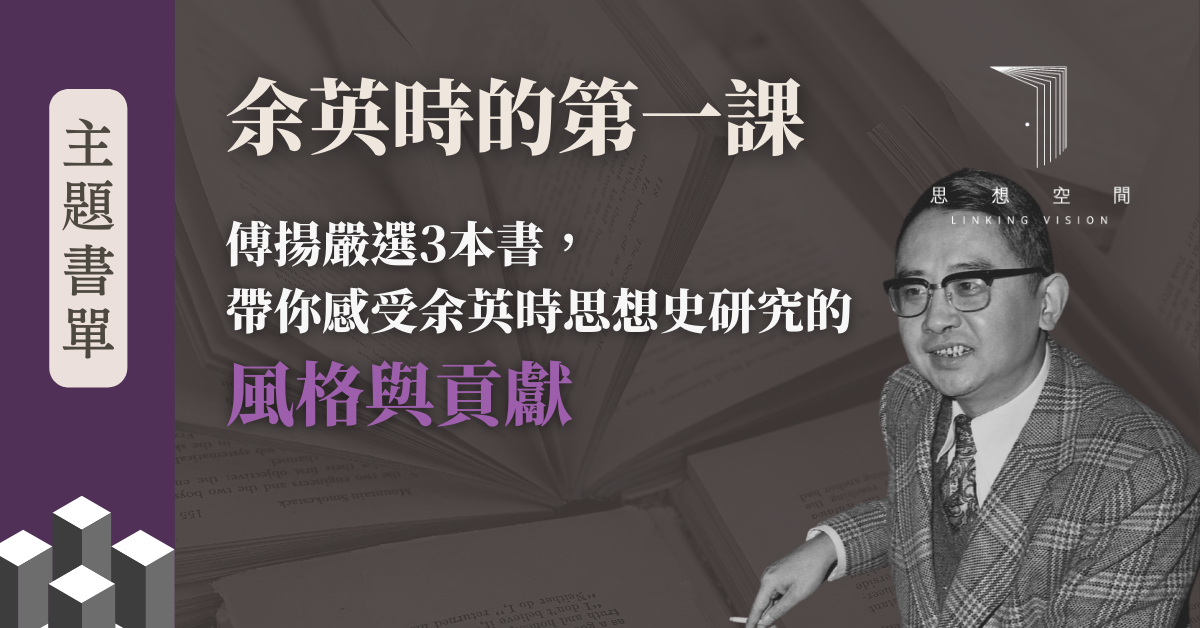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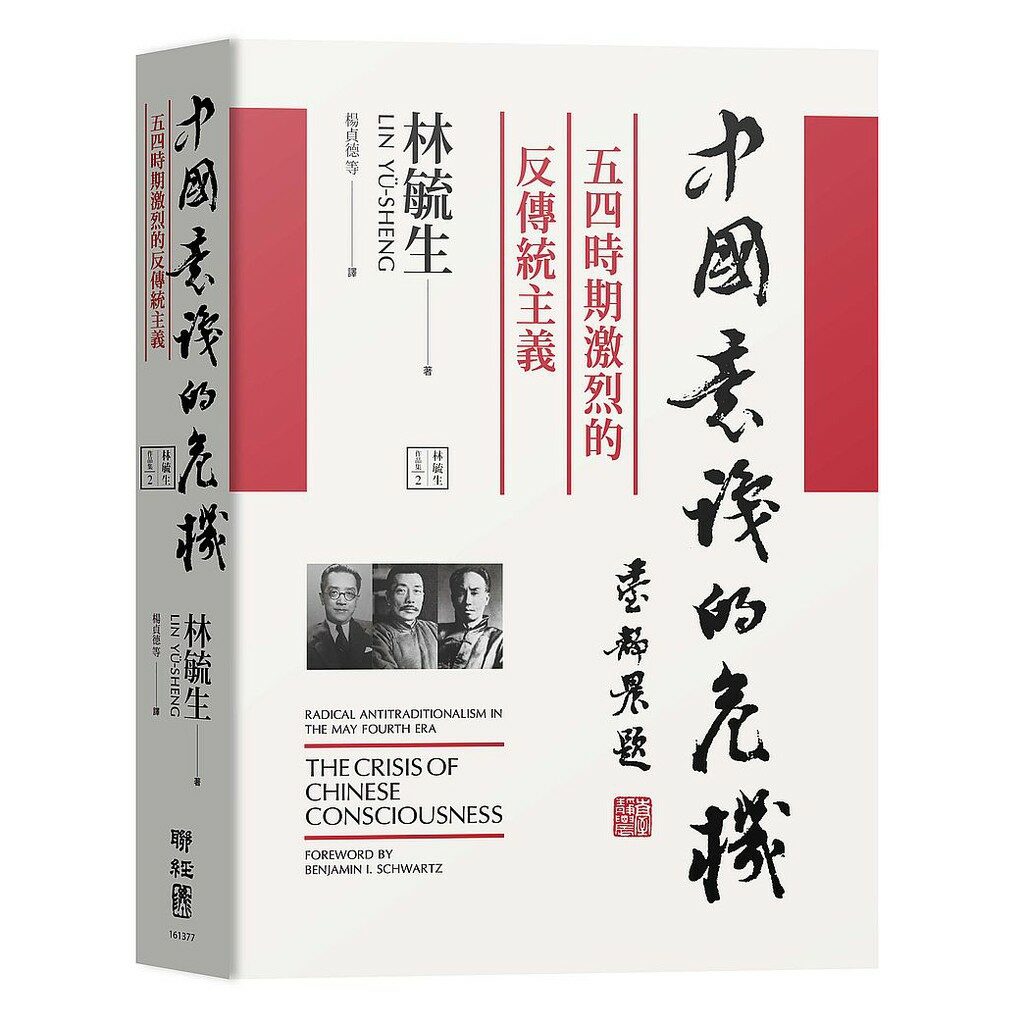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