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里.維斯(Bari Weiss,記者、編輯、專欄作家)
譯/彭依仁(香港詩人、評論人)
編按:2022年3月3日,《政治秩序的起源》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末日: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的啟示》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巴德學院學者華爾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三人共同參與podcast網絡節目,就烏俄戰爭展開深度辯論。本文由香港詩人彭依仁翻譯,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
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已進入第二個星期。烏克蘭首都基輔正響起空襲警報,俄軍正在圍困該國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南部城市赫爾松已經淪陷,接近一百萬烏克蘭人逃離家園。
為何普丁要在這時候入侵烏克蘭?他的終局會怎樣西方的終局又會怎樣?這場戰爭會宣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嗎?也許甚至會掀起一場新冷戰?
昨天,我和三位很敬重的人物坐下來一起談到歷史、外交與美國的實力。
尼爾.弗格森是一位歷史學家,也是史丹福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他最新的著作是《末日: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的啟示》。
華爾特.羅素.米德在巴德學院任教,並在《華爾街日報》撰寫外交政策專欄。他的下一部著作《盟約之弧:美國、以色列與猶太民族的命運》,將於今年七月出版。
法蘭西斯.福山是任教於史丹福大學的政治學家,他的最新著作《自由主義及其不滿》,將於五月面世。



這已釀成一場災難,讓一場大規模戰爭爆發,如果沒有如此明顯的脆弱跡象,這場戰爭本可避免。
關於普丁、澤倫斯基和拜登——這場戰爭中的三位主角
巴里.維斯(下稱:維斯):
根據手上的資料,我覺得我們可以借鑑俄羅斯小說傳統,在我們談到戰爭以前介紹三位主角與及他們的動機。尼爾,不如我們在此先談一談其中一位主角: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他是誰?他怎樣看自己?他怎樣看待自己國家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
尼爾.弗格森(下稱:弗格森):
弗拉迪米爾.普丁長期以來並非渴望恢復蘇聯,而是要恢復沙俄帝國。
自十八、十九世紀,他的偶像是彼得大帝,他把他對1709年波爾塔瓦會戰的想像重新實現——那時候俄羅斯真正走上了歐洲舞台,成為大國之一。
那正是烏克蘭的特殊性。去年七月,普丁發表了一篇奇怪的偽歷史文章:〈論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歷史性統一〉,基本上在說烏克蘭的獨立是歷史的反常。九月份我在基輔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意識到烏克蘭會碰上大麻煩。普丁要徹底破壞烏克蘭的獨立地位,或者更可能地,把她削弱成白羅斯或哈薩克斯坦一類的傀儡國家——明顯地在俄羅斯勢力範圍之內,以免有成為傾向西方或歐盟及北約成員國的成功民主政體之虞,這正是他要發動這場戰爭來避免的。
維斯:華爾特,那弗拉迪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又是誰?
華爾特.羅素.米德(下稱:米德):
他正是剛登上世界舞台的一位最奇怪的人。他起初是一名烏克蘭喜劇演員,實際上也拍了一齣電視連續劇,內容講述一名喜劇演員成為了自己國家的總統。他當選總統在某方面亦意味着,在烏克蘭國內,不少人與現存政治體制疏離。
這個國家正經歷一次真正的撕裂。一方面,爭取民主的公民社會運動主張走向西方;另一方面,他的政黨、經濟機構,與及政府官方部門仍維持着可上溯至蘇聯時代的架構。這個國家由有權勢的寡頭操控政治過程。在這場國族危機中,我們看到一個新烏克蘭正為其誕生而奮鬥。而我認為,這將會改變總統的角色,甚至把他拋進一個他從來沒有想過的位置。烏克蘭人的回應很令人驚訝,普丁或許會成為使烏克蘭成為一國的人物而被載入史冊。

維斯:法蘭克,那麼喬・拜登在這場戲中的觀點和動機又是怎樣?
法蘭西斯.福山(下稱:福山):
嗯,喬・拜登作為中間偏左的候選人當選總統。自從他成為總統以來,他的立場已轉向民主黨內的中間派,或者以後甚至會有一點傾向於黨內進步派。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令美國回歸傳統位置,就是成為民主盟友的國際主義支持者。
我認為他在召集整個北約聯盟反對普丁方面做得相當出色,比如他把液化天然氣供應分給歐洲,讓他們可以在戰爭時承受俄羅斯切斷天然氣的影響。他可能促成了德國外交政策的驚人改變:德國放棄40年來與俄羅斯的聯繫,這是安格拉・默克爾任內的標誌。德國總理奧拉夫・肖爾茨已宣佈加倍提高德國國防預算,並願意運送武器予烏克蘭。這些進展都是戰爭發生前一週內一連串外交活動的成果。整體來說,拜登或許不是一位成功執行外交政策的總統——撤出阿富汗是一場真正的災難——但我真的認為,他很實質地救贖了自己。
弗格森:我可以完全不同意嗎?在俄羅斯文學中,有一部偉大的小說:杜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而拜登就是那個白癡。這次事件發生的理由,是由於拜登政府減緩向烏克蘭輸入軍備的進度,並解除對本來繞過烏克蘭的北溪2號管道的制裁,對俄羅斯發出了美國不會軍援烏克蘭的訊號,所以讓普丁更清楚地以為,他有機會採取軍事行動,而惟一要怕的是制裁。美國政府的策略是威脅要實施最嚴厲的制裁,好像制裁可以阻嚇普丁。然後他們試過做一些甚至更瘋狂的事情,那就是宣稱:「你要去入侵別國,而我們知道入侵的日期。」好像這會以某種方式阻止他入侵別國。他們試過最差的事,就是當普丁以北京奧運後入侵作為條件,換取中國對普丁行動亮起綠燈,他們就讓中國去勸阻普丁。
這已釀成一場災難,讓一場大規模戰爭爆發,如果沒有如此明顯的脆弱跡象,這場戰爭本可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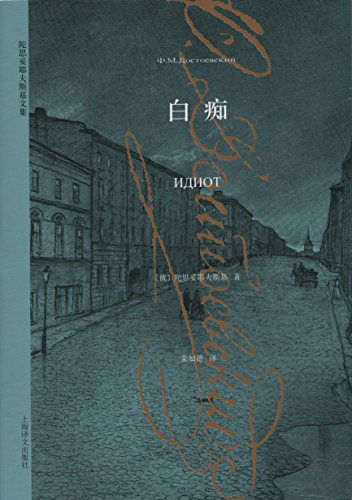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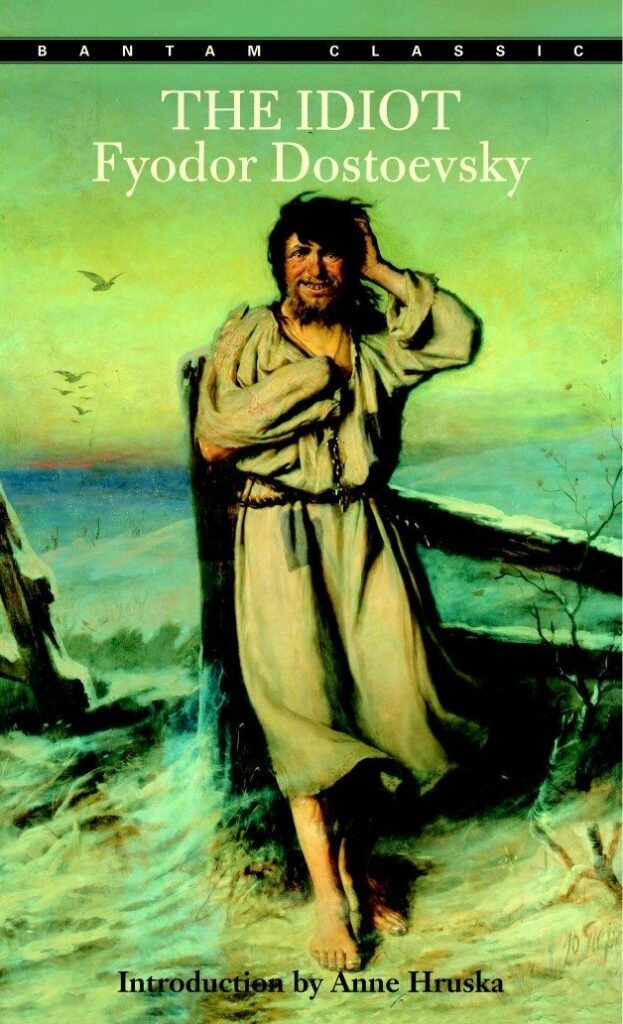
普丁在2021年的經歷就是在贏、贏、贏。我認為他覺得自己正交上好運,這次要做一件大事了。毫無疑問,在俄羅斯鄰國中,烏克蘭一直被普丁視為心腹大患,而其獨立也是他最無法容忍的。
關於戰爭爆發是否不可避免
維斯:讓我們回到2022年2月24日清早。華爾特,為什麼俄羅斯在這個時候入侵烏克蘭?
米德:普丁從根本上誤讀了形勢,但他視此為一個很好的機會。他看見美國政府在阿富汗危機以後失去了很大的信任度,並在反對他介入烏克蘭方面表示出興趣不大。他發現德國新政府總理未經受考驗,而且他所屬的社民黨,是德國最偏左的主流政黨,在歷史上想要維持良好的德俄關係。他發現中國自我感覺很強大,且更加反美。
而在靠近國境的地方,他能夠輕鬆解決在白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的問題。在白羅斯,普丁幫助阿歷山大・盧卡申科(他曾多番嘗試協調俄羅斯與西方關係,像某些烏克蘭政治領袖所做的)粉碎民主。而在哈薩克斯坦,這個最大的中亞共和國暨前蘇聯加盟成員國,該國領袖在國內權力鬥爭受到威脅時,就找上普丁。
所以普丁在2021年的經歷就是在贏、贏、贏。我認為他覺得自己正交上好運,這次要做一件大事了。毫無疑問,在俄羅斯鄰國中,烏克蘭一直被普丁視為心腹大患,而其獨立也是他最無法容忍的。
維斯:法蘭克,為何對他來說無法容忍?
福山:在普丁開戰前夕發表的一篇演說中,他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圖。他要重新統一白羅斯、烏克蘭與俄羅斯,他不認為他們應該分開。還有一篇文章意外地發表於俄羅斯網站,大概是對其勝利作慶祝,這篇文章提到這一點。文章講到1991年蘇聯解體的悲劇,及這場歷史的錯誤現在會被修正。
除此以外,我還認為,如果你看看他們在入侵前的談判中提出的要求,他們也想北約撤回去——不僅不再東擴至烏克蘭,更要回到九十年代的所有狀況。至於所有在1997年後加入北約的國家,他們不想有這些國家,或不想有任何與這些國家的軍事合作。所以我認為那是他的意圖。
不像尼爾一樣,我認為美國決定揭露所有這類情報,並預測入侵發生,事實上是一種絕妙的策略。我們知道俄羅斯人會對他們在烏克蘭做的作出錯誤陳述,而我認為美國政府解密大量情報讓每個人都準備好,以致不會相信從俄羅斯流出的一些東西。它產生了絕妙的作用,沒有人相信從這些東西。這件事引發大規模抗議的部份原因,是由於俄羅斯的陳述完全無法說服任何人,因為我們在事前似乎已獲得情報——而且,部份地挽回伊拉克戰爭的失敗,那時候我們所發報的情報被證實完全錯誤。
維斯:尼爾,你稱之為災難,但法蘭克卻說,美國將他們知道關於這次入侵的真實細節拍發電報甚至誇大是絕妙之計。我承認,作為一介平民,而不是外交政策專家、歷史學家,或政治學家,我所目睹的,是一次極大的示弱。我想:「稍等,如果世上最大的超級霸權都知道目前正在發生什麼事,知道一場戰爭將會展開,而又無法停止它,我會感到很震驚。」你是這樣認為嗎?
弗格森:是的。問題在於我們為烏克蘭加入北約及加入歐盟製造機會。但我們真正的態度就像《紐約人》漫畫中的那個人物,他在電話中說「不,星期四我幹不了。不幹又怎麼樣?」我們無法認真讓他們加入北約或歐盟。我們沒有向他們提供足夠軍備,讓他們抵禦俄羅斯的攻擊。結果,我們釀成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集體地緣政治危機。告別別人你看見那件事發生,並不是戰略上的高明,而是戰略上的庸碌無能。
這場戰爭的結果,當然是深遠的。首先,美國政府為了避免更高通漲而傷腦筋,他們拼命嘗試恢復伊朗石油在國際市場上進行供應,我認為,這會令所有類似的讓步轉過頭來傷害他們。目前在中國,習近平正在觀察着這場慘敗,並告訴自己:「嗯,如果我最該害怕是制裁的威脅,那麼一旦我決定要控制台灣,我的情況還好。」而當普丁拿出他的核子劍讓它嘎嘎作響,我們立即被嚇怕。歐洲人怕得要死,他們立即中止向烏克蘭人提供手上戰鬥機的計劃,在入侵後的較早日子,他們曾提出向烏克蘭提供戰鬥機。
福山:你會做什麼事情?考慮到普丁看到的利害關係,你會做什麼拜登政府沒有做的事情,在你看來可以對俄羅斯人的盤算產生巨大影響?
弗格森:有兩種選擇,而我們沒有選擇任何一項。我們可以遊說烏克蘭接受中立,因為不是這樣的話,俄羅斯人會入侵你們,而我們不會參戰——這就是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2014年提出的建議——或者你必須充份地武裝烏克蘭人,讓他們能抵禦俄羅斯人,而我們沒有那樣做。
福山:他們能拖住俄羅斯人的部份原因是,我們已廣泛地提升該國(烏克蘭)的武器。我們給予他們訓練,我們與他們在情報上合作。我們沒有飛入烏克蘭領空,但我們把靴子放在地上。在你的建議中,沒有一項是現實的,是我們本來可以做到的。
如果你在赫爾辛基說:「與我的情報人員相比,我更相信弗拉迪米爾.普丁」,那是給予幫助和安慰。在我看來,這跡近叛國。
關於美國責任的問題
維斯:尼爾提到季辛吉在2014年說過,西方需要奉行以俄烏修好為目標的政策。六年前,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警告過:「西方正把烏克蘭帶上安逸之路,而最終結果是烏克蘭將會殘破。」在2015年,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說過,烏克蘭想加入北約的意慾「並不是保護烏克蘭,它是用一場大戰來威脅烏克蘭。」
政治上,我和他們三人的看法有很大分別,但他們每一位都會就這件事作出一陣子的警告。華爾特,我要問你的問題是:美國和西方在目前這場戰爭中有多大責任?在過去幾星期或者幾個月以前,我們能否做好某些事情來避免它發生?
米德:看吧,這場危機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幾個方面。自九十年代開始,我就不喜歡北約擴張。我認為更好的構思是嘗試讓雙方在某些方面達成安全安排,包括瑞典、芬蘭和其他國家在內將獲得北約,或許還有俄羅斯的保證。這能否奏效還很難說。
這個大難題自2008年的格魯吉亞危機開始,當時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而我們沒有想出十分有效的回應。那時候宣佈在克里米亞建立美軍基地將是良方妙策,因為正是俄羅斯的行動令局勢不穩。然後在2014年,我們以電報發表回應,說我們會通過制裁,那除了讓我們感覺良好外,根本做不了什麼;我們還發表大量演說,提到我們的團結,還有對民主的貢獻。在好幾年間,我們讓普丁知道我們對抗地緣衝突的方式,是透過強硬的言辭,以及產生邊際影響的制裁。
他十分期待這次發生同樣的事情:他拿到更多領土,我們作出更大制裁。這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我想歷史書最終會這樣寫:歐巴馬被認為是與普丁打交道時最沒成效的美國總統。要說誰讓普丁蔑視西方,那人就是歐巴馬。現在川普的政策比歐巴馬做的還更反對普丁,即使他的言辭並非如此。因為他在通俄門上那種完全瘋狂的防衛方式,讓他陷入各種各樣的糾紛。那就是醜陋得一團糟。我認為普丁從川普那裡認識到西方在一定程度上的軟弱——歐洲聯盟變得更弱,美國正無望地變得兩極化。
弗格森:我同意歐巴馬的對俄政策是一場災難。記得那句話「80年代在呼喚着,現在他們要回他們的外交政策」嗎?他的政策極為失敗,我認為它引發很多趨勢,這些趨勢現在導致了惡劣的後果。
維斯:法蘭克,看來華爾特和尼爾視歐巴馬的軟弱為我們現在見到很多事情的根源。我認為我們是不同意的。
福山:我認為很多美國總統將我們帶到曾經所在的位置發揮了作用。我認為我們應該從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會開始,那時候烏克蘭首次被承諾會得到北約成員資格。當時我認那是個大錯誤,因為實際上我們無法實踐承諾。那是在喬治.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任內。我亦會同意許多人對歐巴馬的批評:我認為他拒絕向烏克蘭售武以及看不見在敍利亞的紅線都是很差的一著。
但我認為你們讓唐納德.川普擺脫責任。他不單被通俄門激怒,他在當選總統之前已經在發表支持普丁的聲明。甚至在入侵以後,他也說普丁是天才並且很精明。幾日前,他在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PAC)發表演說攻擊誰是全球暴君——是賈斯汀.杜魯道,他沒一句話提到普丁。他與他的右翼支持者對強人領導有一種真實的親切感。那就是真實的問題關鍵。如果你在赫爾辛基說:「與我的情報人員相比,我更相信弗拉迪米爾.普丁」,那是給予幫助和安慰。在我看來,這跡近叛國。
普丁有充份理由相信,美國在拜登執政下變得很弱——部份地因為川普在1月6日以後還沒有離開,而共和黨內有相當一部份人相信這個謊話,即選舉成果被竊去。這個國家被嚴重分化,因為共和黨無法承諾和平移交權力。所以如果你是普丁,你會認為可以倚靠你的共和黨朋友軟化任何打擊。
最後,談到拜登,是的,我認為他沒做某些事。當他改變主意,不再嘗試取締北溪二號時,我非常失望。真的,四位總統都有份塑造美國的軟弱形像,並在政策上犯錯。但你知道的,基於那些遺產,我認為,我們現在的位置已是很好的了。
無疑在某個時候,伊朗要成為另一個核子大國的野心會出現危機,台灣亦會出現危機。而我想,步向這些危機時,我們正處於明顯軟弱的處境……
關於戰爭會如何結束
維斯:我們未必未會願意開戰,但普丁很明顯是這樣。他不正比我們更想要主導自己的終局嗎?還有美國與自由世界在這場遊戲裡的終局會如何,如果我仍能那樣形容它?
米德:現在還不可能預言事態如何發展,這正是為何這是一件令人注目的世界大事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明天俄羅斯有可能發生一場宮廷革命,那裡的人民認定這位叫普丁的人真的太過份。但亦有另一種軌跡,就是愈來愈暴力。必須想一想烏克蘭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如何恐怖:一次世界大戰、俄羅斯革命、史太林的壓迫、希特勒的入侵、史太林的重新統治。這是一個被反覆肆暴的社會,而普丁的世界觀正是那種暴虐的運作。
弗格森:西方應該做的是,嘗試(如果還可能的話)維持烏克蘭人的抵抗活動不墜,雖然我覺得現在幾乎是太遲了。如果俄羅斯的勝利不能避免,那麼也應該尋求促成停火。這是季辛吉在1973年的劇本,當時以色列正被埃及、敍利亞與及其他阿拉伯國家攻擊,而且也不是北約成員國。季辛吉的劇本是向以色列提供足夠武器以免他們戰敗,但也不提供過多,以免他們完全壓倒阿拉伯人。
而當下我們做的卻完全相反。我們在提供掌聲、社論和演講的有力武器,而不是烏克蘭人需要的硬件。我們不是真正幫助他們打贏,當然我們也不會用漂亮的話給他們勝利。我們也不管中國政府充當調停人,這是很致命的。這幾乎就像外交史上曾經被遺忘的所有教訓。
我覺得無能為力已經成為日常,那正是為何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景。也許還有更糟的情景——核子戰爭是更糟的——但這已是夠糟的狀態。如果俄羅透過野蠻的手段獲勝,那樣一場將運用在格羅茲尼或阿勒坡的戰術套用在哈爾科夫的常規戰爭,將會殺害大量人命。然後他們坐在那裡,或許會發動一場骯髒的起義,控制烏克蘭並威脅波羅的海國家及波蘭。巴里,這件事最讓我操心的,是一場災難導致另一場災難的瀑布效應:無疑在某個時候,伊朗要成為另一個核子大國的野心會出現危機,台灣亦會出現危機。而我想,步向這些危機時,我們正處於明顯軟弱的處境,我不能回顧然後說拜登政府只是把事情搞砸了。
福山:你對烏克蘭的形勢抱持太失敗主義的看法了,現在烏克蘭的形勢並不像你描繪的那麼差。那種透過19萬人便能控制逾4千萬人口國家的想法實在荒謬可笑,那種只消用不多兵力便能控制基輔的想法亦很難成真。就算他們設法推翻澤倫斯基政權,他們將要面對長期叛亂,因為烏克蘭人從未試過像現在般團結。後勤問題阻碍了烏克蘭人的軍備,因為所有人,由美國閆始,都為了將反坦克武器、毒刺導彈、頭盔、醫療供應品送到基輔而絆倒自己。我們做了很多,而我認為那種我們或許知道普丁最終會勝利的想法是失敗主義的。
弗格森:沒有人在情感上更投入在這件事上:那就是我暴躁的原因。我在烏克蘭有親愛的朋友,現在發生的事對我來說是一種恥辱。但這影響我朋友的前景,首先,在十分野蠻的狂轟濫炸之後是一場兵變,那令我充滿沮喪。在過去十年間,我每年都會過去基輔,每年都會約見年輕的學生。他們一直希望能開展朝向西方的新生活,走出莫斯科的控制。
我不是失敗主義者。我是現實主義者,因為西方媒體報道大肆渲染,說烏克蘭的抗抵有可能維持挺住超過幾星期。你必須看看實際情況。
看來我們正跌跌撞接的進入一個艱難、嚴峻,甚至可能是野蠻的世界——而至少在西方,我們沒有迎接那種挑戰的領袖。
關於美國強權在一個更危險世界中的未來
維斯:這場在美國的討論,揭露了一些令我感到很驚訝的事情。我想,關鍵在於你如何回答兩個問題:第一,在伊拉克與阿富汗以後,你是否相信美國勢力仍否能成為一股向善的力量?第二,你是否信任主事者?你是否信任一個在任何事上曾對我們撒謊的政治階層,會實際地告訴我們現在烏克蘭所發生事情的真相,並且實際地跟進威脅?那些我認識的,又在說類似「我不能信任美國強權,也不能信任美國菁英。」這種話的人數,令我感到震驚——也許我不是那麼震驚。
福山:當然,美國可以成為一股向善的力量。我想,即使在越戰中我們曾作出壞的決定,我們在冷戰中的角色仍然是善的,而它最終得到了回報,民主在那些被共黨獨裁統治過的地方傳播開來。我認為大部份糟透的錯誤都在中東,在那方面我會實際地說,我們在大體上撤出,或者嘗試減少出現在那裡會比較好。我想我們在東歐及在烏克蘭的道德清晰度,比起在譬如敍利亞、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等國的道德清晰度更高。
是的,我也覺得你可以信任美國。如果你相信美國的強權是一股向善的力量,那麼這種對美國的普遍不信任,比如美國的菁英或會向你撤謊,他們不可信任,他們不會兌現他們的承諾等,是有危害的。很老實說,正如我在討論開始時說過,我認為拜登政府已經算很好地兌現承諾。所以我們必須樂觀地期望重建信任,因為我們對世上很多指望我們的民主同盟國家來說,仍然很重要。
弗格森:擁有良好情報並不足夠。問題在於在那些情報的基礎上建立一種連貫的戰略。如果你可以嚇退俄羅斯,又找不到面對衝突的外交替代方案:那麼你擁有的辦法,必須比迄今我們從拜登政府看到的更多。歐洲人在回應方面更能打動人心,他們也推進了制裁議程。但我想,制裁並不能決定戰爭的結果。我感覺我們目前的處境,就是美國對發生的事失去控制。
維斯:華爾特,我知道我們本不該向前望,但至少對我來說,就像我們會走到一個時代的終結,往後退步數十年,甚至幾百年。你有那種感覺嗎?你如何看待美國以及全世界的轉變?
米德:後冷戰時代已經過去。俄羅斯、中國、伊朗,以及其他國家,不單不喜歡後90年代的世界秩序,更付諸行動來與它角力。這是一個不同的世界,充滿了大國競爭。這個世界並不會在聯合國通過決議或者建立多邊論壇。硬實力回歸了。
對於認為那些東西已經結束的那一代人來說,那委實是很恐怖的,但我們沒有能力後退。當你讀到歷史的時候,歷史能夠最強烈地教曉你的,似乎真的是人們不會從歷史中獲得教訓。世世代代總會繼續犯類似的錯誤。在某些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都是特別深刻的教訓。但即使那個教訓也已經開始褪色。所以這或許會造成你認為我們身處另一個地方的感覺。
弗格森:我們正經歷第二次冷戰,而事情有一點不同。在這場冷戰裡,中國是一個主要的角色,俄羅斯只是二把手。將會有一場不結盟運動,但那將會是不同國家變成不結盟國家。我認為更多行動會在跨太平洋而非跨大西洋區域進行。那就是為何我會觀察這片區域——台灣快要來了。但我們仍在這裡,同樣的舊衝突,仍在同一塊舊地方上進行着。
維斯:看來我們正跌跌撞撞地進入一個艱難、嚴峻,甚至可能是野蠻的世界——而至少在西方,我們沒有可以迎接挑戰的領袖。
延伸閱讀:
Derek Hall:在這個特定的時刻,西方左翼必須全力聲援烏克蘭——對David Harvey的幾點回應
烏克蘭哲學家Volodymyr Yermolenko:贏得人心的戰爭,俄羅斯早已失敗
【重磅對話】 史奈德×哈拉瑞:從烏克蘭抵抗行動,看人類未來的可能性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