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 思想空間編輯部
編按:2022年9月24日,Podcast 讀書節目「衣櫥裡的讀者」主持人黃星樺,在台北女書店導讀了奈及利亞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著作《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講座中,黃星樺分享了書中例證、個人經驗,延伸至其他性別文本,與讀者們一同思考女性主義在當代社會所面對的困境與解法。(* 本場講座紀要已獲講者授權撰寫、刊發,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文章部分內容談及性暴力及種族暴力,請酌情閱讀。)
| 講者簡介 |
黃星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Podcast 讀書節目「衣櫥裡的讀者」主持人。
我的人生跟工作(目前)是在花蓮;26歲以前,我是台北市六張犁人,我讀台大,所以大學、研究所時期也經常來女書店。對我來說,女書店是一個很重要的啟蒙場域。所以今天這場演講,從五月份收到邀請,我就很開心地就答應了。可是比起當講者,讓我更開心、也更自在的身分,是女書店的讀者。所以我很期待講座順利結束,很快地大家可以批判我,我就可以重新回到一個女性主義學習者及讀者的角色,也把這個空間還給大家。
我們今天要讀的書叫作《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這本書脫胎自作者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一場30分鐘的演講。阿迪契是來自奈及利亞的黑人女性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演講者。在這場短暫的演講中,阿迪契用她生活中作為一個女性、而且作為一個非洲黑人女性的生活經驗切入構想。她告訴我們:為什麼直到今天,女性主義仍然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講這本書之前,我想狂妄地要求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願意的話,稍微回憶一下──相信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叫作「委屈感」的經驗。我所理解的委屈,就是你明明覺得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但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其妙就接受懲罰。你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是被譴責的人,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千夫所指,好像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傷害、一切的錯誤都是你造成的。回想一下這樣一種委屈的感覺,因為這場講座一路到最後,都會跟委屈感有一點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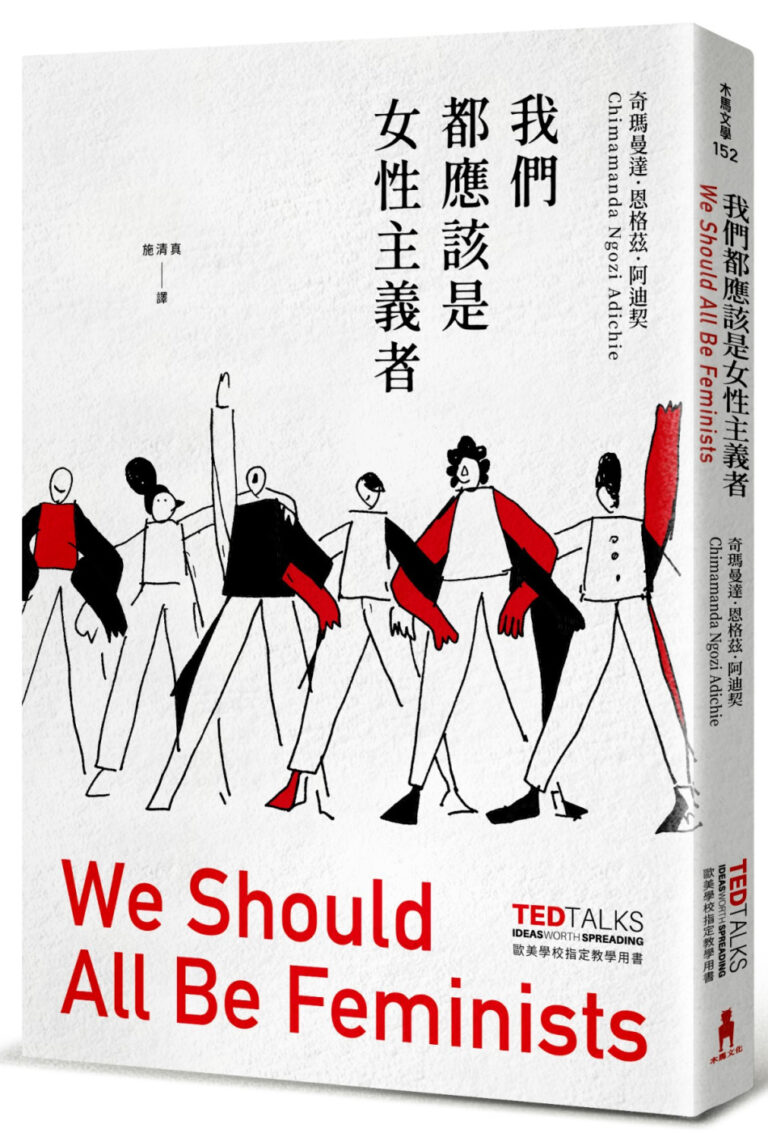
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沒有做錯事,但是所有人都覺得做錯事的人是自己,自己卻有口難言。我想,在每個人的生命經驗裡面,或多或少可能有類似的經驗。
從「阿魯巴」談起
我想分享一個我自己比較委屈的經驗,這個經驗來自於我的童年。我家有四個人:一個大我七歲哥哥,我爸、我媽,還有我。我們四口之家,那時候住在台北市的六張犁。我哥長得跟我很像,只是比胖一點,他是一個很典型的異男──請大家調動一下你對「異男」的刻板印象,想像一下異男想事情、做事情的方式,以及聊天講話的方式──八九不離十,就是我哥的樣子。這樣典型的台式異男,他們經常使用「身體觸碰」的儀式來跟大家打招呼或拉近關係,比如說一個很典型的遊戲叫作「阿魯巴」。
我應該不用解釋阿魯巴是什麼,大家沒玩過也應該知道。之前聽畢恆達老師分享,他的學生有做過關於阿魯巴的研究,期間碰到一個困難:通常研究要做文獻回顧,然而他們發現在外文文獻中並沒有直接與阿魯巴相關的資料,最接近的一種叫作「霸凌」,另一種是高中社團(類似兄弟會)的入會儀式──它有一點折磨你、讓你覺得身體上疼痛,通過儀式之後,你才能成為這個社團的一員。
可是阿魯巴跟霸凌、兄弟會的儀式都有點不一樣,是更具諧謔性的一種遊戲。大部分時候它不是霸凌,因為被「阿」的人可能是群體裡人緣最好的那個。所以這比較像是一種男人之間,尤其台灣的青少男、異男之間,透過身體接觸來維持友誼的遊戲。另一種沒那麼遊戲化的方式,就是很熟的男性朋友間透過觸摸身體部位來打招呼。譬如當兵的時候,大家會互摸奶頭來作為打招呼的方式,更熟的話可能是互摸下體。當然這不是一種情慾性的撫摸,只是透過身體的接觸──尤其是稍微私密一點的部位的接觸──來確認彼此的友誼。
我哥也是這個文化裡的產物,他覺得我也是,所以從小他對我打招呼的方式就是觸碰身體比較隱私的部位。可是我覺得我不太在這個脈絡裡,因此感到不適應、不舒服。所以每次他要碰我的時候,我就會用(當時)很稚嫩的聲音嚴正抗議;然而我愈反抗,他就覺得愈好玩。作為兒童,我最直接想到的是找我的照顧者,於是就問媽媽可不可以制止一下。我媽大概會給我兩種回覆,一種回覆叫作:「哥哥也是男生,你也是男生,男生互摸沒有關係」;第二種回應是:「哥哥就是因為看你反應這麼大,覺得很好玩才會摸你。你下次假裝沒事,他覺得無聊就不會這麼做了。」我知道我媽說的部分是事實,如果我真的這麼做,也許哥哥就會停止那樣的行為,可是我覺得自己沒辦法做到。
當我發現跟媽媽回報卻沒有得到解決辦法時,就決定要把議題升級──我想找一個正式的場合,向所有家人提出問題,希望請我哥不要再這麼做了。大概是國中時,有一次我們家四口聚餐,去了比較高檔的中式餐廳。當吃到剩甜點的時候,我放下餐具,正襟危坐,跟大家說:「爸、媽,我想要講一件很嚴肅的事情」。然後我媽的表情就變了,我猜想那個時候在她的心裡,可能想到也許我會說我的女朋友懷孕了,可是我講出來之後,她就鬆了一口氣;而她鬆了一口氣之後,我就知道事情不會被解決了,同樣的回覆就再輪播一次。講到這都還不是最委屈的部分,委屈的地方是什麼呢?當下我其實很難過、很生氣,很想翻了桌子就走。可即使是才讀國中的我,已經知道如果在那個場合掀翻桌子,事情更加不會被解決,而且很麻煩的是,做錯事情的人就會變作我。
這是我的一個委屈經驗,這個經驗的精髓,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沒有做錯事,但是所有人都覺得做錯事的人是自己,自己卻有口難言。我想,在每個人的生命經驗裡面,或多或少可能有類似的經驗。如果願意的話,請你稍微把這個經驗放在心中,記住那種感覺。

關注性別議題的女性要遠多於男性,可一旦有個稍微願意瞭解性別議題的男人出現,他就變成一個擁有聲量的人,大家會特別關注他。
身為女性的委屈
今天講的這本書叫作《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作者阿迪契曾提到她小學時的故事,是一個關於當班長的故事。這也是跟委屈感有一點關係的故事。
阿迪契在家鄉奈及利亞唸小學,有一天,老師跟大家說「今天要選班長」。怎麼選呢?進行一場考試,最高分的人當班長。當班長可以拿著老師的藤條去巡視全班、管理秩序,阿迪契非常想要當這個角色,所以她非常認真地得了第一名,可是老師卻跟她說:「我忘了講,男生才可以當班長。」在老師的心目當中,男生才可以當班長這件事是不需要明講的。最後,班長職位給了班上一個非常文靜、溫和的男生。
另一個令我覺得很有趣、有共鳴的故事,是關於泊車青年的故事。奈及利亞的大城市拉哥斯有一班人,他們會守在餐廳或者機構外面,看到有人要進去,就幫忙停車、收取小費賺錢。阿迪契每次請人幫她停車的時候,只要身邊有男性友人,泊車青年就會向男性友人道謝,即使車子是她的、付錢給泊車青年的人也是她。在多數人的概念裡,一男一女去餐廳或任何地方,即使女生付了錢,錢的來源應該也是男生的,所以他們要向男生道謝。我身為一個男人,有時候也會觀察到這樣的現象。
另一個讓我特別有共鳴的地方,是阿迪契討論到一個在女性主義、性別研究中經常討論的項目,即「性別分工」議題。例如在主流社會的眼光裡,煮飯通常被認為是女人的工作;然而在烹飪領域中,往往取得最高權威、或是最高薪水的都是男性。也就是說,即使是在煮飯這樣普遍被視為女性範疇的工作中,到了較有權威性的位置時,主要角色仍然是男性。今天我們好像就複製了這樣一種情況──討論一本由女性所寫的有關女性困境的書,現場大部分是女性聽眾,但卻是作為男人的我,在這邊拿麥克風跟大家講解。我很認真在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在台灣,至少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關注性別議題的女性要遠多於男性,可一旦有個稍微願意瞭解性別議題的男人出現,他就變成一個擁有聲量的人,大家會特別關注他。
說回這本書,阿迪契要回答的問題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仍然要談女性主義?為什麼女性主義仍然是重要的?」這本書大致分成兩方面去回答。一方面就是我剛所講的,女性在生活細節中會感受到的被歧視、不被重視的經驗,或是作為附屬品的經驗。另一方面,阿迪契也花了一些篇幅來談男人的經驗──男人在這個社會到底經驗到了什麼?為什麼男人也應該成為女性主義者?
它就是一種我們從小被教養起來的文化,而這個文化的慣性強大到,即使一群男人進入一個純男性的社會時,仍然要用某些機制(其中最極端的可能是強暴)去區分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
有害的男子氣概
書中談到一個重點,就是「男子氣概」。阿迪契說,我們養育男孩的方式其實對男人造成了傷害,因為我們對男子氣概的界定是非常狹隘的。所有男孩都被關在一個叫作「男子氣概」的牢籠裡,他們不懂得如何面對自己的憂慮、怯懦,如何去展現自己的悲傷、哀傷或者是脆弱。這些情感一旦展現,他們會被懲罰,並且失去作為男人的資格、作為人的資格。即使是今天在台灣,應該都有類似的經驗吧。
阿迪契在演講中舉到一個例子,叫作「付錢」。在奈及利亞,通常男、女生出去的時候,永遠是男生付錢,因為這件事牽涉到男子氣概。即使一個超有錢的女生跟一個不怎麼有錢的男性朋友出去吃飯時,也必須讓男性付錢;如果不讓男性付錢,他可能還會生氣,因為這等於傷害了他自尊。這也成為了奈及利亞的一個社會問題──在奈及利亞,男性偷竊者遠多於女性,可能就是出於這種「必須要付錢」的男子氣概施於他們的壓力。
男子氣概不止壓抑男性,同時也傷害女性,因為女性變得要很懂得照顧男性脆弱的自尊。社會鼓勵女人要優秀,但又不能太優秀,平衡點就在於你必須要比身邊的男性伴侶稍微不優秀一點,不然就會傷害他的自尊。
剛好我是作為男性的女性主義者,想特別從一個男性的角度來嘗試回應,或者補充我覺得阿迪契在這本書裡點到為止、還沒有深入展開的議題。我想要講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應阿迪契說的「男子氣概」議題。阿迪契說的沒有錯,但我們可以換一個更讓人不安的議題來切入討論,這當然也是女性主義裡很重要的議題,叫作「強暴」。為什麼會有強暴事件?強暴最根本的動機來源到底是什麼?在主流社會講法中,強暴的動機來源叫作性慾──因為男性對女體有慾望,得不到時就使用強迫手段。可是我相信在座很多人,也聽過另一種在女性主義中很流行的說法:強暴動機不一定來自性慾,更多的時候,最根本的動機是來自權力和支配。
強暴背後的支配結構
1970年代討論強暴議題的書中,有一本很具代表性,叫作《Against Our Will》,作者是Susan Brownmiller。這本書探討了不同情境下的強暴,比如在戰亂中發生的強暴很多是系統性的,它不見得是要滿足強暴者的性慾,而是為了實踐某一種民族侵略的政治目標;對於被強暴的那一方民族來說,受到的往往也不是跟性相關的傷害,而是一種男性的傷害,是覺得民族道德感情被侵犯。
還有一種特殊情境中的強暴,是在監獄裡的強暴。監獄通常是男女分開,而在男子監獄裡也會發生強暴。當這些強暴事件被披露時,公眾往往會直接聯想到同性戀;然而Susan在《Against Our Will》中提出,她發現在男子監獄裡強暴他人的施暴者,入獄前並沒有同性性行為,出獄之後也不會再有,只有在男子監獄才會發生強暴性行為。如果不是同性戀,為什麼男子監獄裡會有強暴發生?
根據Susan的研究,通常當比較嬌小、溫和、沒有男子氣概的男性到監獄時,很容易會碰到強暴的問題。從主流眼光看來,我們或許會說這兩個人都是同性戀;但在監獄裡,強暴人並不會被稱作同性戀。我們知道,在主流社會或男性文化裡,「同性戀」常常是「娘娘腔」的代名詞;可是在監獄裡,強暴者往往可以透過強姦另一個男人,而獲得非常man的地位,被強姦的才會被說是「娘炮」。施暴者其實是透過強暴,去複製從小不斷學習的一種「男子氣概」所構造的「支配與被支配者」的結構。
在一般社會裡,支配者可能是男性,被支配者就是比較陰柔的女性;可是在男子監獄裡,因為沒有生理女性,他們仍然要複製這樣的結構。因此在這樣的處境下,支配者就變成比較勇武、陽剛、有力的男性,被支配者則是比較溫和、陰柔或矮小的男性。透過這些現象你會看到,很多時候所謂「性」或「男子氣概」不見得跟生理性別有關。它就是一種我們從小被教養起來的文化,而這個文化的慣性強大到,即使一群男人進入一個純男性的社會時,仍然要用某些機制(其中最極端的可能是強暴)去區分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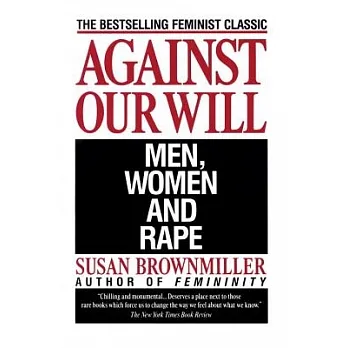
男性跟女性在講性的時候,可能用了同樣的詞彙;但很多時候男人說性與女人說性,兩者所召喚出來的東西,可能是很不一樣的。
男女的「賺賠邏輯」與經驗差異
本書還談到一個問題:社會比較容許、甚至鼓勵男性在各種場合談性,可是女人卻不然,甚至很多時候是被禁止談性的。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阿迪契這段話,是很幽默的表達:
我們告誡女孩,叮囑她們不可以像男孩一樣談性說愛。如果我們有兒子,我們不會介意瞧一瞧兒子的女朋友,可是如果是女兒要帶男朋友,那就千萬不可以。(不過時候到的時候,我們還是希望這些女孩可以帶一個理想的對象回家。)
我們控管女孩、我們誇獎女孩是個處女,卻不稱許男孩是個處男。
我不知道這怎麼說得通,因為失去童貞這件事情,難道不是涉及男女雙方嗎?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奇怪、矛盾的邏輯呢?我覺得至少有兩個回答可以回應這個問題。
第一個回答是,社會上往往帶有一種「男賺女賠」的邏輯。在國中時,有一件事情讓我很困惑:我們是男女混校,班上的男生熱衷於玩一種遊戲,他們會想辦法去看女生裙子裡的內褲;有時真的看不到什麼東西,但是他們看得很high。當時我就產生一個問題:如果性別調換的話會怎麼樣?國中男生們,多看到女生一點肌膚、內衣或內褲就很開心,可是如果性別調換,好像就不是那回事,女生好像沒有這樣的文化。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國中時,我留意台灣女性主義史上很著名的一本書,何春蕤的《豪爽女人》。《豪爽女人》為我解答了這個問題──男生接受一種狩獵者的培訓,於是「看女生內褲、多看一點就贏了」;而女生接受的是被狩獵者的培訓,所以永遠要雙腳併攏、掩嘴笑、遮掩自己的身體部位。我們把女生訓練成一個被狩獵者的角色,所以一旦她多談一點性,就輸了、賠了,這就是「賺賠」邏輯。
針對這個問題,稍微深入一點的話,我還有另外一個可能的答案。這個可能的答案也是我目前為止思索的成果,很有可能是錯的,但我就講講看。
在英語世界裡,有一個禁忌的詞彙,N開頭的。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我把它講出來,叫作「Nigger」。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使用這個詞,或者說,不同人使用這個詞的時候,它所召喚出來的東西是非常不一樣的。Nigger這個字承載了18世紀以來的奴隸貿易歷史,黑人從非洲被運到美洲,被迫要做苦工,他們被閹拔、被強姦,然後被殺害,這是一個兩三百年來的歧視性結構,甚至至今某部分仍然在延續。所以當一個殖民者後代講Nigger時會遭受譴責,可是在某一些情境中,黑人會用Nigger來互相稱呼。為什麼同樣的Nigger,會召喚出不一樣的情感經驗、意識形態?這是語言哲學裡,很多學者在討論的議題。
在性別運動中也有一個很類似的詞彙,叫作「QUEER」,台灣翻譯為「酷兒」。如今很多人直接把酷兒當作同性戀、LGBT的代名詞,可是QUEER最早開始流行的時候,是帶有汙衊性的詞彙──像「娘炮」、「GAY炮」或「死GAY」。可是在性別運動裡有一群人,刻意翻轉這個詞的定義,重新奪取、並且賦予這個詞以顛覆性、結構性或翻轉性的定義。QUEER本身就有一種怪異、格格不入、怪誕的意思,因此他們就站出來說:「我就是這樣的人」。透過現身,他們真的把這個詞成功翻轉。我認為男性跟女性在講性的時候,可能用了同樣的詞彙;但很多時候男人說性與女人說性,兩者所召喚出來的東西,可能是很不一樣的。
作為男人,我不知道大家聽到「強暴」這個詞時,會召喚出怎樣的心理經驗與感受?我所認識的女性中,很多都對強暴這件事有著真實的恐懼感,會憂慮、擔心。可是坦白說,作為一個男人,我從來沒有擔憂過自己會被強暴。因此以「強暴」為例,在女性心中,這個詞可能會召喚出非常不一樣的意識形態或經驗。
以男性觀點講強暴的時候,講的就是身體性的侵入與傷害,可是沒有一種語言或方法,可以讓他理解女性受暴時整個人崩解的過程。
「強暴」的女性經驗
大概在2017年,我看到一個新聞──有個遊戲叫作GTA5,是一個充滿暴力、殺害、可能也牽涉到毒品販賣等各種犯罪行為的遊戲。當時有位美國女直播主玩遊戲給大家看,在直播過程中遇到一群男性角色玩家,他們用外掛程式把角色的褲子脫掉,然後做出交媾動作,同時還有一群男性角色在圍觀。她在虛擬世界裡被強姦了。今年,日本也有一個女玩家在VR遊戲裡被強暴,媒體報導還發明了一個詞彙來描述這種強暴,叫作「VR強姦」,或叫「虛擬強姦」。我發現很多人有疑問:如果GTA5本身就是犯罪類型遊戲,當殺人在遊戲裡都被允許,為什麼角色被強姦時,女主播還是會覺得受到冒犯?這個事件顯示出,當男、女性在討論「強暴」這個詞的時候,所召喚出來的東西可能是非常不一樣的。
基進女性主義法學家麥金儂(Catharine Alice MacKinnon)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很多時候女性被強暴了,但是不是強暴犯做的。」意思是,很多時候女人覺得被強暴了,但以男性為主體的主流社會不認為這叫強暴,例如「婚內強暴」,又比如說有的男人會覺得「女人說『不』就是『要』」,還有某一些更幽微、曖昧的情境,例如師生關係、職場關係,甚至有時候為了要獲得、或是保有一份工作而去陪睡⋯⋯這些叫不叫強暴?在準備講座的時候,我剛好在網路上看到一則很驚悚也很寫實的標語:Why does every woman know another woman that was raped, but no man knows a rapist? 我認識曾經被強暴的女性,而且她願意告訴我她有這樣的經驗;可是我不認識任何一個強暴者,或至少沒有任何一個人曾告訴我,他有過這樣的經驗。
有一篇文章也讓我印象深刻,是台大法律系教授陳昭如所寫的〈基進女性主義的強暴論〉。文章指出了刑法中對強暴的定義,是非常男性中心的定義。舉例來說,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當中,區分「強暴未遂」跟「強暴既遂」的差別在於陰莖有沒有插入陰道。但從一個女性受害者的角度來看,陰莖有或沒有插入有本質上的差別嗎?可是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刑法定義後者不叫作強暴。對此,陳昭如有一個很powerful的表述:「這叫作用男性的爽來定義女性的痛。」這個事情完全可以回到剛講的VR強暴、虛擬強姦,在這些案例中,女性在虛擬世界的受暴經驗不被承認、甚至被質疑,是因為我們今天對於強暴的理解不但是男性中心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體制化的。
我為此寫過一篇回應文章,其中談到:當一個女性有受暴經驗的時侯,身體有可能會受傷;身體的傷在一段時間後可能會痊癒,而心理、或全身心、或她跟世界的關係可能就破滅了,她對於什麼叫作安全的環境、人我之間界線、或是信任感可能就整個崩解。在我的經驗裡,以男性觀點講強暴的時候,講的就是身體性的侵入與傷害,可是沒有一種語言或方法,可以讓他理解女性受暴時整個人崩解的過程。

男性跟女性在講性的時候,可能用了同樣的詞彙;但很多時候男人說性與女人說性,兩者所召喚出來的東西,可能是很不一樣的。
諧謔談性與身體焦慮
我有一個比較粗淺的觀察:很多時候男性要討論「性」的時候,不管是討論強暴還是性慾,往往只有兩種主要方式。其中最常見的,就是我稱之為「A片式的情慾投射」。比如談到性的時候一定會談到女體,很多時候在異男文化裡面,我們講到性跟女體是分不開的。而另外一種談論性的方式,叫作「諧謔式的談論」。
黃克武老師的《言不褻不笑》一書中,有一章專門研究清代笑話集《笑林廣記》如何寫性笑話。如果把《笑林廣記》每一篇看下去,會發現其實很多笑話都不好笑,因為我們已經離開了那個時代;而明清時代流行的性笑話,很多到今天都還會覺得好笑,笑點跟今天流傳的黃色笑話基本上是非常雷同的。
笑話很多時候能夠呈現出社會的一種集體焦慮,或集體對於道德缺陷、缺憾的一種不滿。關於男性陰莖太小的笑話,也是在明清兩代流傳的笑話裡十分常見的主題,所以可以很安全地推論出來一件事:明清兩代男人可能也跟今天很多男人一樣,有陰莖大小的焦慮。有趣的是,雖然在不同笑話集裡都會蒐集到關於陰莖太小的笑話,可是在笑話領域之外,基本上看不到對陰莖大小焦慮的表達。為什麼這種話題就只會出現笑話本當中呢?這其實也反映出一種很強烈、嚴實的、對於男子氣概的要求──一旦不是用諧謔的方式,而是很嚴肅地承認有陰莖太小困擾的時候,就非常容易被嘲笑。
我之前有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女性YouTuber叫作Clara Dao,是一個胸部非常扁平的女生。我們知道,對於胸部大小的焦慮,也是存在在很多女性身上的一種焦慮感。可很有趣的是,在YouTube上就有這樣一位女性專門開了一個頻道,與其他受到胸部太小問題所困擾的女性對話。她拍影片教小胸部女生怎樣打扮、穿搭,也花很多篇幅想辦法面對自己的身材焦慮,去愛自己、愛自己的身體。可是至少在我的經驗中,就比較沒有看過男性YouTuber討論陰莖焦慮。我覺得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當有人這麼做的時候,很容易會收到嘲笑的反應;根據我的猜測,去嘲笑他的人恐怕大部分會是男性。因此,男性表達焦慮的方式,很多時候是相當受限的,這也會讓他更加壓抑。最極端可怕的結果,是它可能會轉化成某一種對於弱勢者、或對女性的暴力。這件事情是非常寫實的,它仍然在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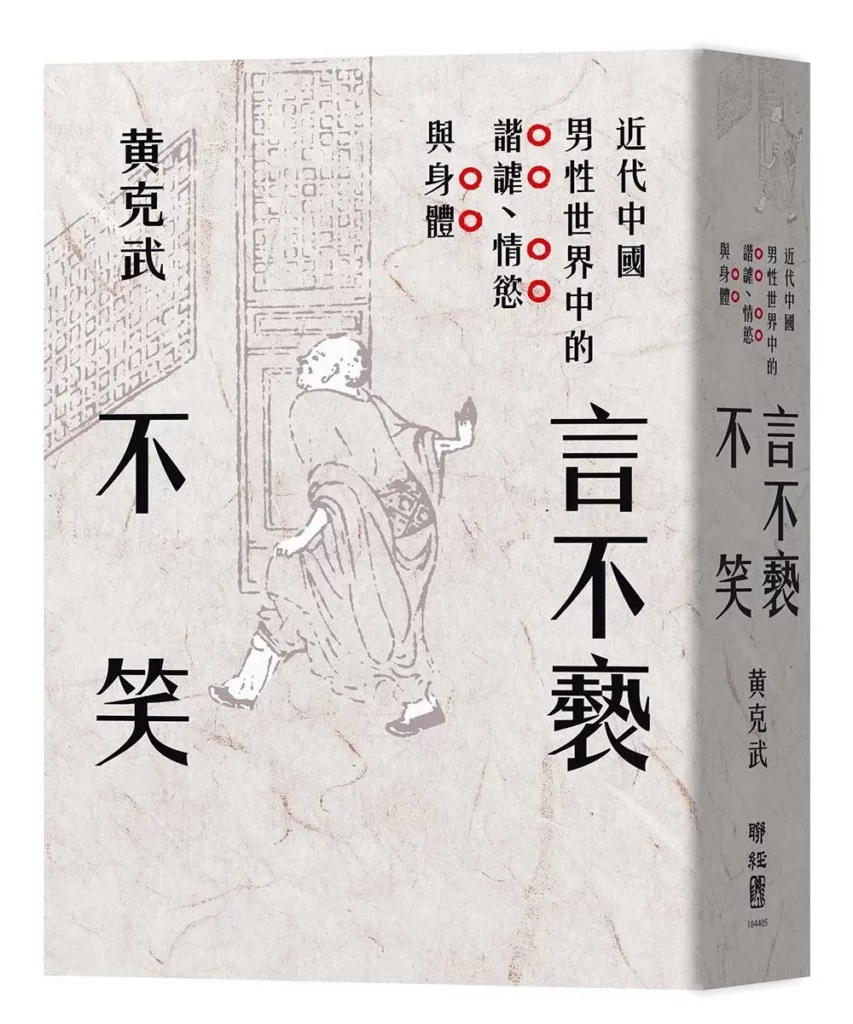
當對於一個地方或一群人,你的故事來源只有一種版本,就很容易對這個世界產生誤解,你會以為這個故事就是他們唯一的故事。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讀到最後,會發現它給出了一個很樂觀正向的結尾;而在準備講座的時候,我把阿迪契另外一本中譯書找回來看,是她的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在《繞頸之物》中,我讀到一個非常不一樣的阿迪契。她的短篇小說裡充滿了無奈、哀傷,讀了會讓你感到憂鬱。書中很多憂鬱來源都是性別,或是因為身為非洲人、黑人。
在讀這兩本書的時候,我心裡產生了一個矛盾:到底作為小說家的、比較悲觀的阿迪契所描述的世界,比較接近真實的世界,還是作為演說者的阿迪契所描述的未來,比較接近現實世界當中可能的未來?我們到底有沒有理由樂觀,還是我們應該要保持悲觀?帶著這樣的問題,我看到阿迪契曾做過的另一場演講,名為《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演講中提到,阿迪契對小說產生興趣,是因為小時候讀了很多來自英國和美國的童書,書中寫的當然都是英美生活經驗。所以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在阿迪契最初寫下的故事裡,角色都會喝薑汁汽水,可是作為一個奈及利亞小孩,她小時候從來沒有喝過、也完全不知道什麼是薑汁汽水;她筆下的角色在雪地玩耍,然而奈及利亞是不太下雪的;角色見面的時候會談論天氣,可奈及利亞人見面的時候並不會。直到後來,阿迪契長大了一點之後,讀到了阿切貝這些偉大的非洲作家的小說,才終於發現原來像她這樣的黑人女孩也可以成為文學作品的角色,她可以把生命當中熟悉的事物寫進小說裡面。因此,講座之所以名為《單一故事的危險性》,是阿迪契在告訴我們:當對於一個地方或一群人,你的故事來源只有一種版本,就很容易對這個世界產生誤解,你會以為這個故事就是他們唯一的故事。
阿迪契在演講中講到另一個很多人會有同感的故事。19歲那年,她第一次離開奈及利亞去美國念大學,當時她的美國室友對一件事感到很驚訝:「你怎麼會講英文?你英文怎麼這麼標準?」阿迪契只好告訴他,因為奈及利亞的官方語言就是英文。室友還問她說:「你是奈及利亞來的,那放一下你的部落音樂好不好,我聽一下你們部落的音樂。」阿迪契拿出瑪麗亞 · 凱莉(Mariah Carey)的CD給他聽,室友就非常失望。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在阿迪契的詮釋裡面,這仍然是單一故事的危險性──室友想像中的非洲,是一個單一故事的非洲,充滿了災難、貧窮、飢餓。於是對於非洲的態度也只剩下一種,叫作憐憫。
阿迪契反省到,很多時候她也會對某一地方、某些人群抱有單一故事的傾向。比如說當她在美國時聽到很多人討論非法移民,最常呈現出的形象就是墨西哥人,他們會從美墨邊境溜進來打黑工。阿迪契第一次去墨西哥的時候覺得非常慚愧,因為她原本以為會看到一大堆美國媒體呈現出來的罪犯形象,可是當她去到的時候,發現大街上有人在做蛋餅,有人在抽菸,有人在談天,有人在笑。她突然意識到,原來她對墨西哥是這麼不了解,對墨西哥人的想法,就是來自美國媒體灌輸給她的單一故事的版本。
阿迪契也講到一個很有趣的經驗:有一次她去美國一所大學演講,結束後有位學生走上來,談到最近讀了一部奈及利亞小說,寫的是一個有家暴傾向的父親,然後他就跟阿迪契說:「我覺得非常憤怒,奈及利亞的男人實在太可惡了,他們怎麼每一個人都這樣對待他們自己的太太。」阿迪契就回他說:「我最近看了一本美國的小說,叫作《美國殺人魔》,但是我沒有因為讀了這個小說而覺得美國每個人都是殺人魔。」單一故事會造成我們對特定人群有一個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問題不是因為不正確,而是因為不完整,它讓一個故事變成了「唯一的故事」。
我非常喜歡這場演講,「單一故事的危險性」所帶出的反思,其實就是多年來女性主義教給我最重要的事情:單一故事永遠不會是完整的版本,是危險的。當我在思考性別問題、乃至任何問題的時候,向內追索自己的生命經驗固然重要,可是我更有機會去探索另一個性別的生命經驗,甚至可以去探索不同世代、族群、文化背景的人的生命經驗,這種探索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
回到剛剛的問題:作為演講者的阿迪契是樂觀的,而作為小說家的阿迪契是悲觀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呢?我覺得完全可以用阿迪契早年演講裡的一句話來回答:「非洲充滿了苦難,非洲有非常可怕的強暴事件,有很令人悲傷的事情,例如說奈及利亞,當一個職缺開出來的時候,有5000個人要搶一個職缺,而其他4000多個人要繼續在失業的狀態裡面徘徊。但是仍然,在非洲、在奈及利亞,我們有很美好的故事,我們可以去訴說它們。訴說這些美好的故事,跟訴說這些充滿苦難的故事,是同等的重要。」
開始的時候,我講了一個自己的故事,關於我哥曾經性騷擾我的故事。這是一個我受委屈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母親看起來好像是失職的,因為她沒有辦法正確辨認出兒子正在遭受的苦難;而背後沒有辦法辯證出來的原因,可能也是因為某一種男子氣概的意識形態。所以在這個故事版本裡,某種意義上,我媽媽變成了性騷擾的「幫助者」。
可是在結束分享之前,我最後想說一件事情。我現在非常肯定一件事:預計兩個小時之後,我會回到台北的家裡,看到我媽,會告訴她我今天去女書店演講,有很多人來聽,我很開心。然後我非常肯定,媽媽會因為我的開心而感到開心,她會稱讚我,然後我會跟她說:「媽,我愛你。」跟媽媽說愛、表達愛這件事情,也是女性主義教給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延伸閱讀:

陳力深:不只是「約砲神器」——交友軟體的政治性

李根芳×伍軒宏×丘延亮:史碧瓦克的異想世界 2/27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