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來西亞華人、臺灣女婿,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約聘助理教授,研究專長是道家思想、先秦儒家、倫理學、政治哲學、書法美學。對文化、宗教、藝術、歷史等有濃厚的興趣,關心臺灣文化、馬來西亞的文化與教育,也關注全球化、跨文化、世界文明衝突等議題。曾與「哲學新媒體」作者群合著:《給哲學家的分手信》,臺北,時報出版,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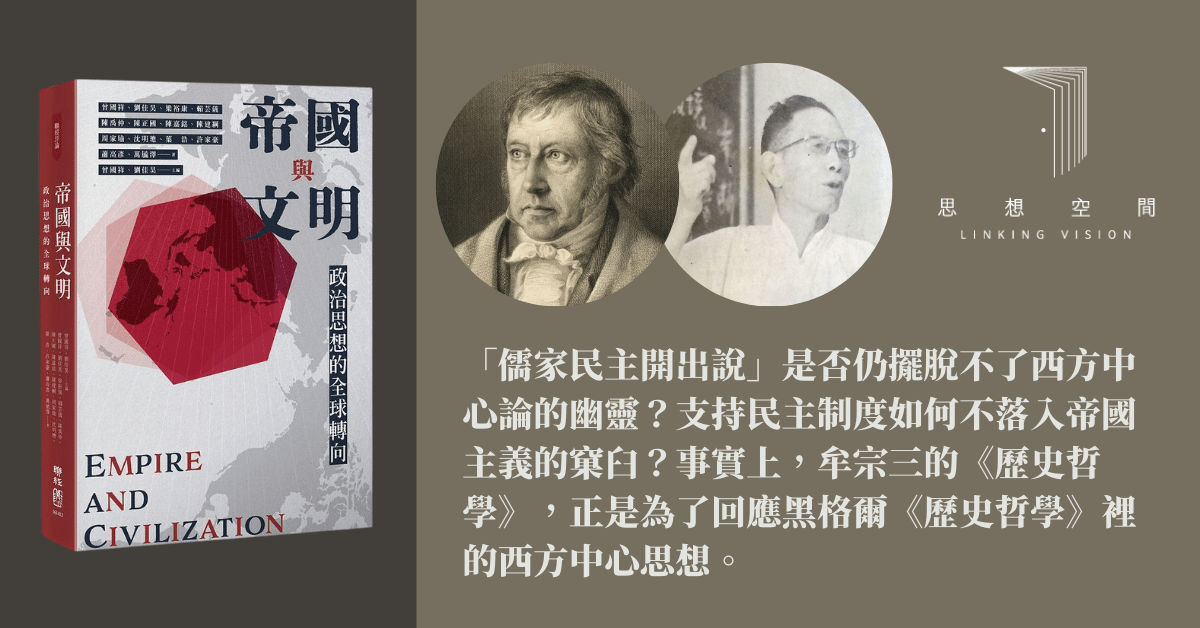
文/陳康寧(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約聘助理教授)
編按:2022年4月,聯經出版新書《帝國與文明:政治思想的全球轉向》,以東亞學者視角為立足點,呼應英美思想界的「全球轉向」,除了意欲重新檢視近代歐洲政治與思想的文化、歷史影響,探尋型塑現代政治與價值的關鍵。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約聘助理教授陳康寧為本書撰評,與讀者一同思考帝國、殖民與文明和思想的發展之間,有著怎樣的辯證互動關係。(* 本文原題為〈如何思考中華文化?——從帝國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的反省到跨文化潛力與文化創造的來源〉,標題為編者擬。)
思想(學術)與政治之間存在各種複雜的關係,一方面思想會被政治型塑,另一方面思想也會試圖影響政治,兩者呈現動態的辯證關係。
帝國文明
今年4月出版的《帝國與文明:政治思想的全球轉向》帶出了一個重要的省思:從全球政治史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熟悉的人權、自由、平等、民主、文明、公民等等概念,往往是隨著帝國的征服與殖民而傳入東亞地區。當東亞社會高舉理性文明、自由平等、普世人權的時候,是否反映了西方文明優越論或中心論,直接把西方的政治文化與模式移植到非西方國家?
近代西方殖民史,一般會追溯到15世紀,當時歐洲國家的航海技術發達、商業資本興起,於是有了開拓海外市場、尋找更多資源的需求。從葡萄牙、西班牙到荷蘭與英國所主宰的海上霸權,宣示了殖民主義時代的來臨。
眾所皆知,思想(學術)與政治之間存在各種複雜的關係,一方面思想會被政治型塑,另一方面思想也會試圖影響政治,兩者呈現動態的辯證關係。身處當時的歐洲哲學家,固然會對殖民、歐洲霸權論提出批判(帶有負面意涵的「帝國主義」是19世紀後才流行的),但也難逃為帝國殖民背書的嫌疑。為人所熟悉的自由主義哲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就曾說:
首先,平常的國際道德規範要求彼此互惠(reciprocity),但野蠻人不會如此行事。我們也沒辦法期待他們會遵守規則。他們的心智尚未發展到足以做這樣困難的事,而他們的意志也尚不能被這麼遙遠的動機所驅使。再者,尚未走出這種野蠻階段的國家,被人征服或受制於外人的管轄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一件好事。(這段話出自於 Essays on Equality, Law, and Education,轉引自《帝國與文明》,頁396)
「文明」與「野蠻」的二分架構,貫穿了彌爾的帝國政治思想,他認為英國作為當時歐洲的文明國家,應該肩負起促進人類文明的重大責任,適當地干預是合理的。「不干預原則」只適用於文明國家之間,不適用於非文明的國家。
當然,學者葉浩也提醒了一點,彌爾的「文明」與「野蠻」之區分,不建立在特定種族的基礎,而是就國家的財富分配、工業水準、知識程度、智力、道德、法律、政府形式、風俗習慣等等來決定(彌爾心目中的理想制度是民主代議制)。同時,對其他國家的干預是有條件的,一些不適當的干預,彌爾依然會採取批判,而干預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國際合作關係來協助飽受戰爭摧毀的國家早日結束戰爭。然而,彌爾卻使用了「成人」與「小孩」來比喻「文明」與「野蠻」的國家,而且認為前者要教導後者,同時也主張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管治,這對當時東印度公司與殖民地的關係而言,多少也合理化了英國的帝國擴張。
「歷史演進一元論」影響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胡適就曾將中國新文化運動比附為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歷史演進一元論
若把焦點放到東亞的中國來看,晚清面對西方的「船堅炮利」和西方文化的衝擊,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放棄封閉的海禁政策,甚至要學習西方的知識與技術。嚴復翻譯史賓塞的《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取名為《羣學肄言》,為中國引入了西方社會學的視野。當時的知識分子擔心中國從此一蹶不振,慢慢被外國瓜分,「圖亡救存」成為他們的時代意識,如何一方面學習西方的現代知識,一方面維繫中國的傳統文化,是重要的課題。然而,中國現代轉型的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全盤西化」的聲浪也不曾中斷。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幾乎都是環繞著這樣的一個重大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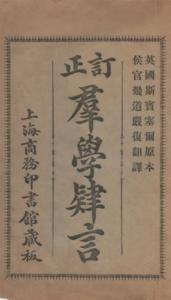
承繼這樣的一個問題意識,現代新儒家(張君邁、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試圖從傳統的中國文化中開展一條通往現代科學與民主的道路,特別是牟宗三先生的「儒家民主開出說」,至今仍影響深遠。然而,一度興起的「大陸新儒家」(蔣慶、康曉光、姚中秋等人)則提出很不一樣的主張(註)。蔣慶批評「儒家民主開出說」乃是西方文化下的產物,不是墊基在傳統的中國文化,強調儒家開展出民主制度,只是變相的「西化論」。然而,「儒家民主開出說」是否仍擺脫不了西方中心論的幽靈?支持民主制度如何不落入帝國主義的窠臼?事實上,牟宗三的《歷史哲學》,正是為了回應黑格爾《歷史哲學》裡的西方中心思想。黑格爾說:「東方從過去一直到現在,只知道『一人』是自由的;希臘與羅馬則知道『一部分』(某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一切』(全體)是自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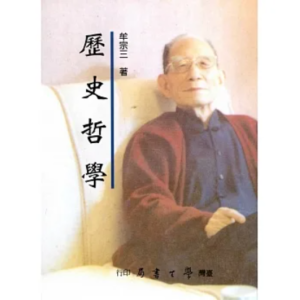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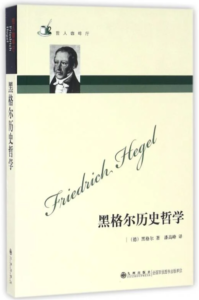
黑格爾主張,亞洲(中國)是世界歷史的起點,而歐洲則是歷史的終點,所謂的「起點」與「終點」,在時間上是從專制到民主的進步發展,在空間上則是從東方到西方。牟先生則認為,黑格爾談世界歷史,應該要承認各民族、各文化有其自身的發展以及未來的前途,而且可以「期得一精神之大匯通,不當以空間上之從東到西之空間次序代替時間次序。」他認為,即使中國過去兩千年都只是重複而無進步,但也不能輕易被忽略、抹殺,黑格爾把世界歷史的起點歸給中國,而終點則在歐洲,那會把中國的未來給抹殺掉。這種「西方代表進步的文明史觀」,往後則發展出歐洲的「歷史演進一元論」,如余英時先生指出:
到了十九世紀,歐洲便出現了不少社會思想家(如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相信自己已發現了人的世界的規律,並據之以進行歷史分期。和自然世界的規律一樣,這些規律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行之百世而不惑」的。因此任何地域的社會(或文明)都在它們的支配之下。用在歷史分期的方面,這是預設所有的社會(或文明)都必然經歷相同的發展階段;或者說:在絕對性規律的支配下,歷史演進只有這一條路,是任何社會(或文明)所不能不遵循的。所以我稱之為「歷史演進一元論」。
「歷史演進一元論」影響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胡適就曾將中國新文化運動比附為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可這樣一來,就意味著中國的歷史發展比歐洲「落後」,現在正要努力「趕上」。不過,牟先生也認為黑格爾的觀點「並非全然無理」。牟先生依循黑格爾的說法,認為中國只有皇帝一人是自由,他並不全然為傳統中國辯護,而是思索為何傳統中國文化「開不出」民主制度?某個程度來說,牟先生也對傳統中國提出了批判,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曾錯失了可以發展出民主制度的時機。至於未來在思想上要如何「開出」,可從「道德主體」和「政治主體」的關係來理解。
參與政治、共議決策,是否能夠真正培養出人民的道德,近年來也受到很多挑戰。
以公民社會作為道德主體的培養場域
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和張君勱合撰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有一段話至為關鍵:
在過去中國之君主制度下,君主固可以德治天下,而人民亦可沐浴於其德化之下,使天下清平。然人民如只沐浴于君主德化之下,則人民仍只是被動的接受德化,人民之道德主體仍未能樹立,而只可說僅君主自樹立其道德主體。……由是而我們可說,從中國歷史文化之重道德主體之樹立,即必當發展為政治上之民主制度,乃能使人真樹立其道德的主體。(粗體為筆者所加)
這一段話或許可以理解為:要讓人人都能夠樹立其「道德主體」,必要先給予人人都有一個「政治主體」,也就是讓每個人有一個自由平等的政治地位,否則只有君王一個人能夠樹立「道德主體」。
若上述的理解是正確的話,那就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為何沒有自由平等的政治地位(政治主體),「道德主體」就無法樹立呢?安靖如(Stephen Angle)在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裡,提供了一個滿清晰的說法,他不是要詮釋牟宗三,但坦言受到牟先生的啟發,他說:
讓民眾擁有有機會參與公共目標的設計與努力實現這些目標的機會對於民眾的德行成長有重要意義。如果國家替民眾做了所有重大決定,只留下一些個人小事讓民眾自己決定,那麼就等於視民眾為嬰兒。換言之,這就等於拒絕給他們重要的修德的機會,而真正的德行的成熟需要民眾參與各種複雜的事務,因為只有通過瞭解每一種特定事務的各種方面我們才能達到和諧的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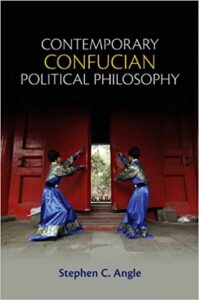
若用安靖如的觀點來幫助理解新儒家的思想,或許可以這麼說,「道德主體」的樹立需要透過修養來一步一步實現,而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參與政治,正是培養道德主體的關鍵。賦予每個人自由平等的政治地位,正是要讓每個人有機會可以實現道德主體。 現實上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實現道德主體,但至少在政治制度上,要讓每個人有這個機會。
不過,參與政治、共議決策,是否能夠真正培養出人民的道德,近年來也受到很多挑戰。布倫南(Jason Brennan)在《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裡用了大量的數據和心理學研究來說明,人民參與政治、討論政策,大部分只會加深原本的偏見,甚至不同立場的人會加深敵對關係,尤其是在敏感的議題上。很多人也經常互罵對方不理性、自私、接受假訊息、受到嚴重誤導等等。參與政治不僅沒有培養到德行,反而惡化了。臺灣之前的公投和總統大選前後,只要聊到政治,家人關係就會變得很僵,甚至關係破裂,朋友之間也在FB上互刪好友,這些現象多少也呼應了布倫南的判斷。
如今面對的一個質疑是,「中華民族」會不會吞噬掉社會的多元族群,忽略掉少數族群的政治地位?
「五族共和」與「中華民族」
不管如何,與其說新儒家思想是一種「西化論」,不如說是在中西會通的過程,吸收西方哲學的優點,重新在中華文化的土壤上開創出新的思想。有意思的是,對楊儒賓教授而言,新儒家的理念,可以再往上追溯到梁啟超與孫文。梁啟超主張的「中華民族」,是為了回應時代挑戰而提出的政治概念,但如今面對的一個質疑是,「中華民族」會不會吞噬掉社會的多元族群,忽略掉少數族群的政治地位?
面對其他族群的問題,孫文曾支持「五族共和」,如他在《討袁宣言》(1916 年)說:「辛亥武昌首義,舉國應之,五族共和,遂深注於四億同胞之心目」,也說:「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國基已定」。不過,對於滿州、新疆、蒙古、西藏的問題,他依然有很大的顧慮,這跟當時的局勢有莫大的關係,包括面對俄羅斯和西方國家勢力的問題。當時外蒙古要獨立,跟俄羅斯的介入多少有一些關係,實際情況可能比想像的還來得複雜。
早在1912年,孫文就表示,蒙、藏不知道共和的真理,以至於在外人的挑撥下,出現「種種背謬行為」,他甚至認為英國、俄國與日本在滿州、新疆、蒙古、西藏的勢力擴張,對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帶來的傷害,比德國與奧地利還要嚴重許多。之後在1919年的《三民主義》手稿中,孫文認為,應該要像美國那樣,強調自身的民族、文化,所以要凸顯「中華民族」的重要,這樣才可以讓中國「駕美迭歐而為世界之冠」。
然而,人是複雜的,尤其孫文是革命家,不完全是思想家,他當時所在的位置要面對很現實的問題,他的思考應該是不斷游移和掙扎,很難看成鐵板一塊。 他或許覺得「五族共和」的理念很不錯,但現實上就遇到困難。而且當時候西方的「現代國家」,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的建構,名義上人人平等,但要真正重視「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也是建國之後仍須努力的事。從美國的南北戰爭到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來看,即使是老牌民主國,種族的課題依然是相當棘手的問題。
「中華民國」做為一個「理念」,有點類似黑格爾的「精神」,包含了政治(民主憲政)、文化、歷史、民族、思想等。
中華民國的理念
目前,「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話語權,掌握在中共手中,立足在臺灣,該如何看待「中華文化」,也成為了當前一個重要且具爭議的問題。楊儒賓教授的《思考中華民國》(尚未出版)試圖提出不同的論述來與中共的論述抗衡,他從梁啟超、孫中山到現代新儒家,為「中華民國」建立了一個歷史與文化傳承的系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華文化與民主憲政的結合。他指出,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不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更早可以追溯到晚明。
換言之,楊教授認為,真正繼承中華文化的命脈,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說,「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繼承了梁啟超與孫中山的理念,到了新儒家的思想,完成了中華文化與民主憲政的結合,而這個結合就體現在「中華民國的理念」,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
從宏觀的歷史文化意義來看,中華民國的理念可以上溯到堯舜,進而發展至先秦的孔孟、宋明理學、明代黃宗羲,再到晚清的梁啟超、孫中山與現代新儒家,形成一個「天下為公」的歷史與文化傳承。楊教授主張的「中華民國與臺灣的一體化」,賦予了臺灣的文明意義,不管是放在兩岸關係或東亞位置,面對世界,都具有提升臺灣地位與價值的意義。楊教授也主張,應該要從兩岸的「關係性」來界定臺灣的特色,若不斷「去中化」,會逐漸讓臺灣失去國際上的優勢。
「中華民國」做為一個「理念」,有點類似黑格爾的「精神」,包含了政治(民主憲政)、文化、歷史、民族、思想等。楊教授是本省人,年輕也參加過黨外運動,曾被某個學者說是「很綠的」,他所提出的「中華民國」論述,很值得關注。
楊照提出的「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前文化部長鄭麗君說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或許都可以有進一步的解讀……
跨文化潛力與文化創造
在臺灣談「中華文化」,已經不純粹是復古、傳統,而是具備了中西方的跨文化潛力,一方面承繼民國初年以來的文化斷裂,一方面又自覺地進行思想重構。何乏筆教授在〈創傷與創造:台灣的文化糾結與中華文化的重構〉一文則清楚表示:
筆者建議在文化斷裂與文化連續性之間加入「批判」的因素,以強調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帝王秩序之後,對中華文化的重構工作應該是一種「批判性的重構」。因為『批判』涉及對文化歷史資源的評斷和選擇性的重估,某些學者以「規範性的重構」取代之。
不管是「批判性的重構」或「規範性的重構」,基本上已經結合了中西方的視野。余英時先生曾以「價值系統」來對比中西文化的不同,特別是在價值源頭的「超越」不一樣,他把西方的超越視為「外向超越」,而中國的超越則是「內向超越」。不過,余先生也強調,他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談兩個文明發展,並不是要做高低優劣的判斷,而且,中國可以吸收西方發展法治與民主的歷史經驗。
臺灣歷經了荷西、明鄭、清領、日治到現在的民國,有人稱臺灣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冷戰之後,陳光興教授也指出,美國文化(帝國文化)已經「內在於」臺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帝國與殖民的足跡,不也同時醞釀出豐富而多元的思想與文化?楊照提出的「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前文化部長鄭麗君說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或許都可以有進一步的解讀,即「中華文化」是臺灣跨文化與文化創造的來源之一。
註:相對之下,牟宗三等人則被歸為「海外新儒家」,不過李明輝教授反對這樣的分法,他建議以「大陸儒學新思潮」來取代「大陸新儒家」。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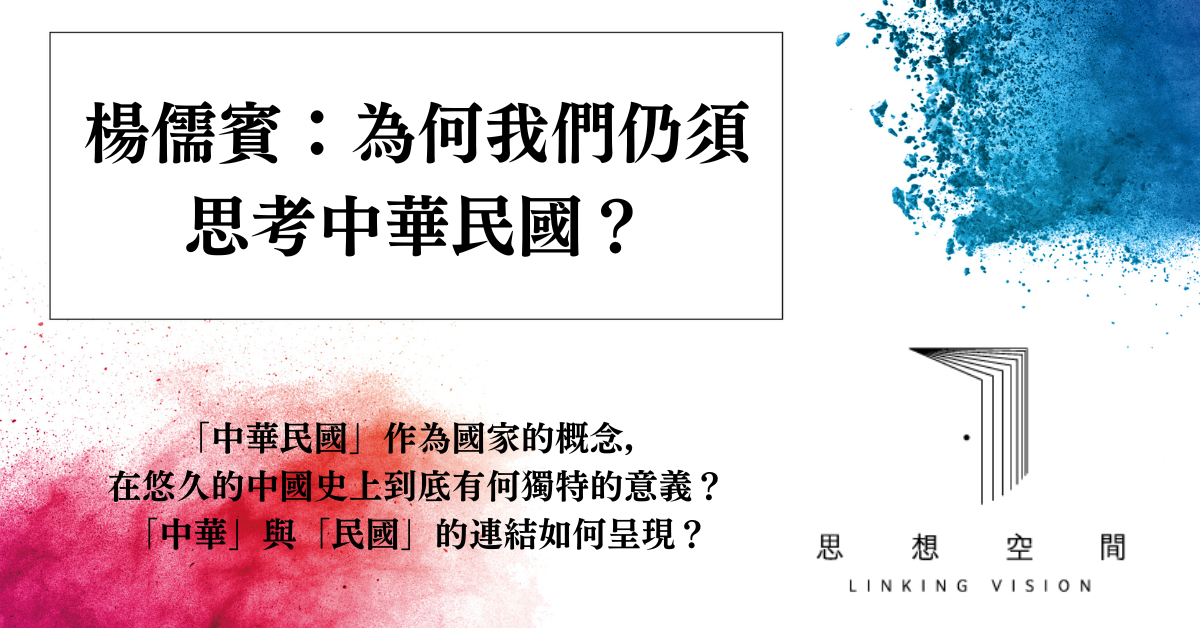

| 閱讀推薦 |

馬來西亞華人、臺灣女婿,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約聘助理教授,研究專長是道家思想、先秦儒家、倫理學、政治哲學、書法美學。對文化、宗教、藝術、歷史等有濃厚的興趣,關心臺灣文化、馬來西亞的文化與教育,也關注全球化、跨文化、世界文明衝突等議題。曾與「哲學新媒體」作者群合著:《給哲學家的分手信》,臺北,時報出版,2020。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