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楊儒賓(二之二):做不討好的研究,追尋更廣闊的歷史時空


文/李雨鍾(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後研究員)、
梁靧(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生)
編按:2022年,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楊儒賓出版了新書《多少蓬萊舊事》,集結近年來在學術工作之餘、補寫學術論證難以消化的情觸內容,為其研究作出另類的學術注腳。身為學者,楊儒賓的思想脈絡為何?內心又有哪些人文關懷?回顧2019年10月,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曾與楊儒賓進行專訪,探討了晚明與現代性、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1949、台灣的民主工程與儒家的關係,並論及其思考理路與治學經驗。(*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者擬。)
當我們身處台灣來進行討論,則對於1949這一節點的歷史功過,更需要訴諸廣大台灣人民的記憶與感知。
從兩邊不討好的《1949禮讚》突圍
在1949年之前,台灣本土固然也有過許多優秀的文學、藝術成果,但畢竟還不是世界級的,而1949年後來到台灣的那些學者,像是胡適之、錢賓四這樣的,哪一個不是當時世界頂尖的學者、知識分子啊!
楊儒賓在訪談中不禁發出感嘆,而類似的話在《1949禮讚》中也屢屢出現。實際上《1949禮讚》的核心宗旨可以說正反映在書中的這段話裡:「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各有他們的1949,1949之於新中國,主要是政治的意義;1949之於新台灣,則是文化的意義。」[1]在楊儒賓看來,相較於從政治(災難)的角度來看待1949,從文化的角度,可以看到更為深層的結構性意義。雖然他並未避諱談及1949所帶來的災難與創傷,但他更想要提醒我們去關注這伴隨著災難而來的重大文化機緣。
楊儒賓固然苦口婆心、反覆陳說,但在本土派的眼中恐怕未必討好,尤其是其中對台灣本土文化成就的評價,實在不免會讓許多人皺眉。正如一些評論所指出的,楊儒賓的評價背後是否預設著從中國文化場域出發的標準呢?而如果1949年國民黨政府沒有來台,再多給台灣知識分子一些時間,難道本土文化就不可能在東亞文化圈扮演重要角色嗎?[2]這樣的批評並不容易回應,尤其是當我們身處台灣來進行討論,則對於1949這一節點的歷史功過,更需要訴諸廣大台灣人民的記憶與感知。不過楊儒賓如今更將1949與四百年前的明鄭王朝進行隔空搭連,將原本單一節點上的局部攻防提升到更為廣闊的歷史時空之中,由此是否有望突破1949之困呢?
正是由於這一更貼近中國本土的面向在歷史進程中被人們忽視,才使得五四的理念後來被唯物史觀所取代,進而讓中國走向另一種命運。
連結晚明與五四的中國現代性
楊儒賓企圖以《1949禮讚》介入公共討論,暫不論觀點允當與否,其精神已是可佩。在訪談的過程中,當1949與明鄭王朝之間的關聯被漸次搭建出來,他看似孤立的公共論述與其專業學術研究之間的隱秘連結,亦冉冉浮現。
這中間有兩個層次。首先是歷史偶然性,明鄭王朝與1949的國民黨政府雖然相隔近四百年,卻同樣是從中國大陸敗退到台灣的政權,為台灣輸入了大批漢人移民。不過這樣的歷史偶然雖稍稍為1949之爭帶來了時間縱深上的支援,卻似乎仍顯單薄,更關鍵的是,與這一歷史偶然對應的是另一個文化內在性的層次。這個層次將明鄭連接上晚明思潮,又將1949連接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楊儒賓強調晚明文學中有一種朝向情慾解放的趨勢,這正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相互呼應,兩者同樣展現出某種內在於中國文化而又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現代性因素。可惜晚明與五四所展現出來的這種可貴發展,都在中國本土被政治力量打斷,不得不遷移到台灣以延續火種。
在土地改革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地主「階層」是否具有發聲的空間,一直是學界論爭的重點。
這樣的想法乍聽起來頗為浪漫,背後卻蘊含著楊儒賓嚴肅而獨特的見解。例如,楊儒賓認為僅僅從西方啟蒙思想的傳入來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充分,他甚至表示西方對個體情感的重視還「不夠偉大」,如果我們不將五四與晚明連接起來看待,就很容易忽視前者原本還具有回歸土地、回到鄉村的根源性追求,而正是由於這一更貼近中國本土的面向在歷史進程中被人們忽視,才使得五四的理念後來被唯物史觀所取代,進而讓中國走向另一種命運。
楊儒賓坦言,他對於中國現代性的思考受到日本學界的很大影響,遠至早期京都學派的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近至島田虔次、溝口雄三對中國近世思維的考察,都促使他不斷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思考中國文化與當代政治的歷史命運。因此,當那串聯起晚明與1949的歷史線索,被放置在中國文化自身發展出的獨特現代性上來思考,則1949為台灣帶來的「中華民國」,被楊儒賓視作一種寶貴的理念,不應輕易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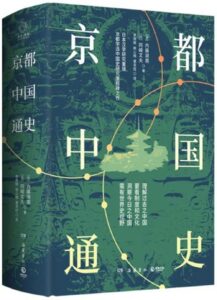

作為一種「理念」的「中華民國」,在歷經明鄭與1949這二度否定與挫敗的辯證中,揚棄出了豐富的文化生命力;而在這歷史進程中的階段性挫敗或災難,也如楊儒賓所言,是為「天假其私而濟其公」,是歷史弔詭地以政治苦難來成就某種文化價值,因此不能輕易片面地妄下斷言。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晚明還是五四所發展出來的另類現代性,最終都遭受壓制,被從原生大陸排除出去,遷移到台灣才得以延續。如果這曾二度重蹈的現象並非偶然,那麼我們就需要去追問,無論是中國內在現代性還是「中華民國」理念,是否本就與其母體土地處在某種緊張關係之中?實際上,在楊儒賓對「中華民國」的界定中,已然包含著答案。
在兩岸形勢雲譎波詭的當下,楊儒賓看似孤獨的身影,不失為一種深具歷史底蘊的聲音。
自我批判還是本土化:歷史宿命的追問
楊儒賓在《儒門內的莊子》一書中對自己的莊學研究的定位,也呈現出與上述「晚明——五四」架構之間的有趣呼應。楊儒賓宣稱,該書實際上是有意要銜接晚明的方以智、王夫之為代表的第二波莊學運動,以及二十世紀以降在西潮衝擊下的第三波莊學運動。[3]這種旨在銜接晚明與現代的莊學研究,恰與連通「晚明——五四」的現代性理念相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認知中,莊子屬於道家,乃是儒家的尖銳批判者,那麼所謂「儒門內的莊子」,是否正意味著一個自我內部的批判性、反叛性因素呢?楊儒賓強調「中華民國」本就扮演著一種批判性的角色,能夠挑戰其母體文化內部不合理的成分。或許正是這種批判性導致它遭受其母體文化的排斥,而台灣二度接納、延續此種理念的意義也就顯得更為重大。
不過遷移後的理念若要活生生地存在下去,而不淪為陳年故紙堆中的遺跡,則必然要遭遇到「在地化」的問題。楊儒賓明確表示,他當然贊同「中華民國」理念的「在地化」,並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1949禮讚》一書亦屢屢論及1949後中華民國——台灣的一體化,如何推動了所謂「新漢華文化」的形成。
楊儒賓的關懷更在一個頗為宏大的文化時空中開展,他強調我們不應停留在明鄭王朝、1949遷台的具體政治事件層次,而是應當關注其背後更為深層的漢文化、乃至東亞文化版圖的位移。這樣宏大的關懷背後,無疑帶有強烈的歷史宿命感與使命感,若與吳叡人在論述台灣主權獨立時,所說的那種由生於台灣之偶然轉為別無選擇之必然相對照,則頗有一種異質交錯的奇特對照感。[4]
在兩岸形勢雲譎波詭的當下,楊儒賓看似孤獨的身影,不失為一種深具歷史底蘊的聲音。有朝一日,若雲開霧散,回首滄桑,則楊儒賓的思考與言說,仍會是台灣文化史上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一份見證。
對於楊儒賓而言……儒學民主化的重點並不是只從制度上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如何支撐制度的存續。
直承晚明儒學:一個與台灣連繫的現代性探詢
對楊儒賓來說,「中華民國」的普選實現,是我們對於民主化與現代性的解答。他認為這可以上溯到晚明儒家對於暴政的反思。他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很大的長處,但是也有很大的弱點,就是它在制度上一直沒有辦法解決專制政權的問題。」他認為從儒家「心性論」的角度來看,心性論的「民主開出說」當中有一種具有超越而內在的自由主體,它意味著新的物論的興起以及民主的醞釀。而民主制度的要求,以晚明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唐甄的《潛書》作為代表。楊儒賓說到: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原臣〉談的是政治體制的問題,〈原法〉牽涉到法律的問題,更高一層就是憲法的問題,〈學校〉則扮演類似議會的功能,這裡談的是立法和監察的問題,我認為他是把中國傳統政治的問題都提出來。
楊儒賓將晚明作為現代性的起源,這是一個蠻特殊的觀點。這不同於中國大陸左派學者汪暉,援引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將現代性起源定位在北宋;這也不同於中國大陸新儒家學者蔣慶所呼籲的「回到康有為」,將現代性起源定位在晚清。


楊儒賓認為晚明最後的承繼,在於台灣的明鄭政權。他談到明鄭二、三十年在台的歷史價值,並不只是意在「保明」,而更是意在「保天下」。明鄭的天下意識,一方面作為漢文化延續的文化總體,一方面又帶有轉化為現代性的內涵存在。「舉凡政權合法性、法令的客觀性、道統與政統在根源性上的分權、中央與地方在制度性上的分權、物的反思、新的主體範式等問題,均在明末出現曙光,然而異族的征服,卻摧毀了敏感的現代性內容。」
在「儒家與當代中國」系列演講時,筆者曾問及楊儒賓對於「大陸新儒家」(與港、臺新儒家有別)的看法。「大陸新儒家」提倡回到晚清公羊學「託古改制」的氛圍下,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所提及的「儒學民主化」多半是一種典章制度上的改革,比如說民主制度並不全盤承接西方,在民選的下議院之上,設立一個具有儒學特色的上議院,以四書五經等科舉考試、或儒家菁英社群內部推舉作為參選資格。上議院可否決下議院的民意主張。在大陸新儒家的觀點裡,臺灣新儒家的「民主開出說」只是一種儒學保守主義、只是保守地跟隨在西方價值之後的「西方民主自由的啦啦隊」而已,缺乏積極的制度變革。
對此,楊儒賓強調台灣新儒家的心性論主張,他認為從台灣新儒家的觀點來看,有清一代兩百年的儒學因為缺乏心性論,顯得並不具有價值,也鮮少被提及,這是他不認同「大陸新儒家」的主因。他認為心性論在1949年之後,於中華民國的民主實踐上具有很重要的思想史意義,這不單單只是典章制度上的問題,文化風土的基磐也是指導民主運作的原則。很顯然地,對於楊儒賓而言,雖然民主作為制度,必有其體制上的存在,但儒學民主化的重點並不是只從制度上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如何支撐制度的存續。
我們在問及這是「誰的現代性」的同時,我們所希望的是保留更多元的發聲在台灣的公民社會,至此,我們也不能免除儒學的參與。
從晚明到1949:一個正視新儒家在台的現代化過程
在訪談時,楊儒賓數次提及他與「自由主義、獨派的朋友」在台灣民主化與現代化的認識差異很大。他雖然不認同國民黨的史觀,但也不將1949年國民黨政府來台視為只是現代化的絆腳石。他說:「1949不完全是只有災難,它為台灣帶來了極大的文化資源。」
我覺得正是1949的那樣一個偶然,台灣史才會出現那樣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是大量的文化資源流注在台灣,把台灣開始放在一個國家與文化的高度,透過這樣的歷史撞擊,使台灣人開始從不同的視野去看待問題。
在楊儒賓的現代化論述裡,在西方思潮以外,儒學扮演了很特殊的位置。1949年的渡台學者是歷經五四運動洗禮的,五四運動的特點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新的主體性呈現」,這種新的主體性「強調人的個性的自由、強調男女情欲的價值、強調從封建倫理之網脫身的解放」,楊儒賓認為這與晚明思潮的演變,有著密切相關,更尤其是晚明儒學突出「情」的概念,將個體自由與男女私情視為是良知在新的歷史情境下的表現,對五四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楊儒賓強調五四運動並不是只有全盤西化下的科學、民主、自由,新儒家的牟宗三當時也身處在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裡,「新儒家也是五四之子」,只是「一個五四,兩個路線」,一個現代性起源是西方的、一個現代性起源是中國的。楊儒賓說:
從我的觀點來看,「中華民國」就是中國現代性和西方現代性所混合的產物」,這個產物雖然在100多年前出現,但我不認為當時它的理念有什麼問題。
楊儒賓正視台灣現代性起源,除了西方現代性之外,還有中國現代性的參雜。這難免迥異於部分獨派人士企圖只以本土化路線所進行的現代性建構,對此,楊儒賓說:「台灣從明鄭以來,我並不相信台灣有哪個時期的發展,是只在台灣內部產生。」他更積極地建議說:「在文化上如何與中國脫鉤,這是一個很不切實際的想法。反而應該要是透過一種互動,取得到更好的發言位置,以尋找對台灣最有利的可能性。」
對於為何不將民主化與現代化的起源全歸諸於西方,楊儒賓在系列演講與《1949禮讚》曾數次提及,我們面對現代性問題必須自問:這是「誰的現代性」?這是「什麼樣的現代性」?關於這樣的自問,他在書中說:
如果現代性只有歐洲一種,其他世界全扁平化了,那麼,這樣的趨勢會帶來如下的問題:歐洲會缺少一塊足以對照、反省的參照者,它無法校正它自己的現代性之盲點或流弊 。[5]
這一段話,或許就回答了儒學之於民主化、現代化的參與意義。我們在問及這是「誰的現代性」的同時,我們所希望的是保留更多元的發聲在台灣的公民社會,至此,我們也不能免除儒學的參與。
在台新儒家在1996年民主普選之後的下一個時代關懷:進入民主開放之後,我們如何在公民社會之中,彼此保有不同的差異性卻又彼此能相互溝通理解。
氣韻生動下的多元民主
在歷經一整個下午的訪談裡,筆者注意到楊儒賓教授在訪談時很有趣的態度。在面對筆者試圖以不同的台灣史與台灣民主化立場質疑時,楊儒賓教授時常先是抱持著理解的態度,重新描述他所理解這些立場背後的成因與情懷,並表達對於不同論述的建構者在努力上的肯定,隨即便又自嘲說:「這我好像又沒回答到你的問題。」又才開始闡述他自己的觀點。
他數次提及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所擁有可貴的言論自由以及人們對於歷史經驗的多元性,他肯定其他立場都是其來有自、各有各的存在價值。彷彿他之所以違反主流政治下藍綠兩黨的史觀,以從獨特的視角去強調晚明的現代性起源以及1949的文化意義,這當中有一份呈顯台灣多元與豐富之處的心意存在。這不免讓我想起楊儒賓在學術上所闡發的「形氣主體」精神:在一氣流轉的變化之中,人的主體總是在氣化流動中不斷躍出,使得我們保持著豐富與多元的面貌,又同時因為氣的同情共感而使我們得以理解不同的他者 。[6]
在訪談時,我們一行人開了楊儒賓玩笑說:「楊老師的論述裡充滿著黑格爾式歷史哲學的味道。」楊儒賓教授對此並未否認。或許筆者在最後對於儒家現代化的這一場接力賽可以有如下遐想。
從歷史辯證的角度來說,宋明新儒家歷經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晚明氣學等不同的歷史階段。如果說,對應於當代,從馮友蘭的新理學、到在台新儒家以心學為主的論述。楊儒賓教授承繼晚明,並將氣論引入現代化的基礎,這恰好猶如晚明劉宗周氣學做為宋明理學之殿軍一樣。這接續了在台新儒家在1996年民主普選之後的下一個時代關懷:進入民主開放之後,我們如何在公民社會之中,彼此保有不同的差異性卻又彼此能相互溝通理解。
對照近年的世代對立、性別平權、同婚爭議、南北差異、課綱問題等公民議題,輿論中常充斥著無法互通的差異與割裂之其中。或許氣韻背後的政治共感,正是楊儒賓教授所試圖帶領我們回歸現代性去重新省思的問題。
[1] 參見楊儒賓,《1949禮讚》。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頁32。
[2] 參見顏訥,〈納中華入臺灣的1949創傷癥候,與發明新臺灣的可能:讀《1949禮讚》〉,《文化研究》第22期,2016年春,頁243。
[3] 參見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頁454-460。
[4] 吳叡人從生在台灣這一偶然性出發,結合台灣所處的國際環境逐步推導出主權獨立的必然命運,參見吳叡人,〈人間的條件—論台灣獨立之必要〉,收於林秀幸,吳叡人主編,《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臺北:經濟民主連合,2020年,頁35-53。
[5] 楊儒賓:《1949禮讚》。臺北:聯經,2015年,頁177。
[6] 楊儒賓:〈遊之主體〉,收錄在,頁12、21。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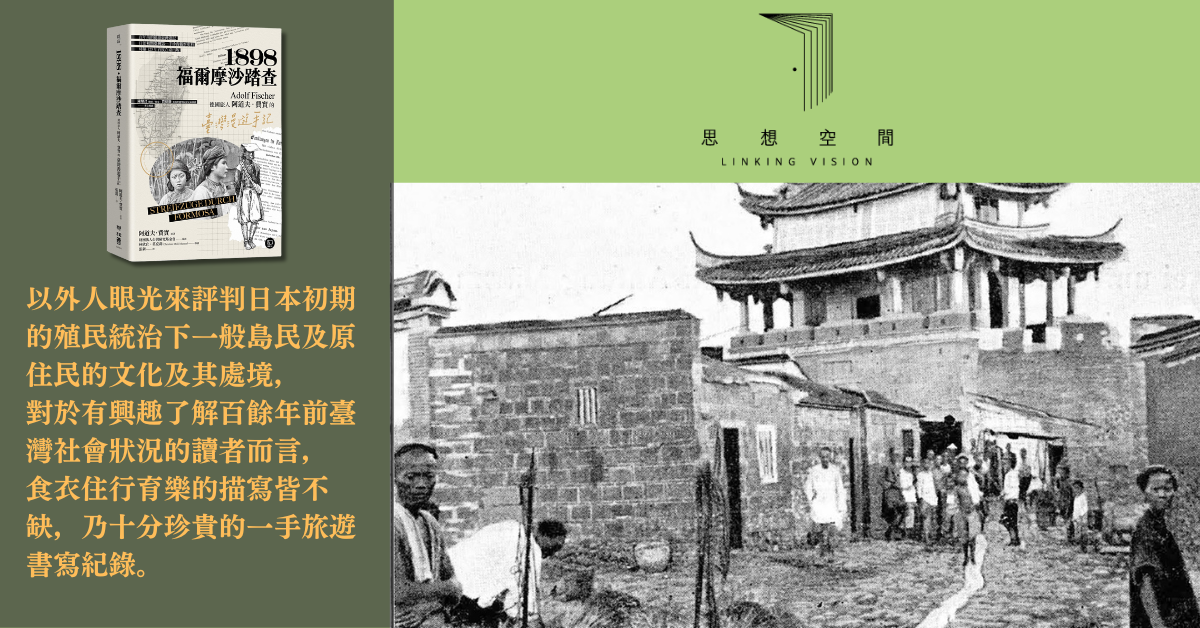


| 新書速遞 |
| 閱讀推薦 |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