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遊
(* 本文原刊於澎湃思想市場,思想空間經授權轉載。)
2022年4月2日,立陶宛紀錄片導演、人類學家曼塔斯 · 克維達拉維丘斯(Mantas Kvedaravicius)在馬里烏波爾遇難,他生前正有一部拍攝馬里烏波爾衝突的紀錄片《馬里烏波爾》(Mariupolis)。起初,媒體報導他意外死亡於汽車爆炸事故,然而不久前隨着曼塔斯的太太冒着炮火到馬里烏波爾尋屍,烏克蘭人權事務專員發布了對曼塔斯死因的調查結果,曼塔斯是被俄軍囚禁,開槍射殺,死後暴屍街頭。
本文作者在最後寫道:曼塔斯致力於研究和拍攝暴力,最終死於暴力,一個離奇的迴環。在《隔離之地》片中的暴行彷彿溢出鏡頭,進入了當下的現實,而導演本人又彷彿成為了自己紀錄片的主人公。這種時空的交錯和耦合不僅賦予了曼塔斯的人生一種藝術化的殉難色彩,還提醒着我們:這個世界的一些惡並沒有被充分地反省和糾正,它們凝固在部分系統內部,還在重複上演。而戰爭本身,就是滋生這類暴力最好的土壤。面對曼塔斯的死,我們是時候再一次大聲呼籲和平。
隨着俄烏戰爭的延續,正在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炮火下的犧牲者,其中也包括藝術家和學者。2022年4月2日,立陶宛電影導演、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曼塔斯·克維達拉維丘斯(Mantas Kvedaravicius)在烏克蘭城市馬里烏波爾遇難,年僅45歲,引起世界範圍的哀悼。他的影像和學術研究致力於探討暴力與情感。
我問烏克蘭朋友有沒有看過曼塔斯的電影,得到的回答是在他死前甚至沒聽過這個名字。曼塔斯確實太「小眾」了,在IMDb上看過他的片子的人都寥寥無幾,遠不及此前勇於直言,不惜與烏克蘭電影學院割席的謝爾蓋 · 洛茲尼察。這真的是一種悲哀——我們只能借這個沉重的契機來認識他,回望他那些同樣不輕鬆的作品,回望他用自己的鏡頭以最大的温情和不忍記錄下的暴虐與殘酷。
曼塔斯的學術研究和影像作品存在一種互文關係。他的人類學視角深刻地影響到藝術創作。他在媒體採訪中說過,他對電影明星不感興趣,打動他的是普通人。
曼塔斯·克維達拉維丘斯1976年生於蘇聯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比爾扎伊。他曾於維爾紐斯大學和牛津大學學習文化人類學,2012年在劍橋大學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2014-2016年任教於維爾紐斯大學傳播學院。他共有三部電影作品。2011年發表首部電影作品紀錄片《隔離之地》(Barzakh),以車臣為題材,在2011年柏林國際電影節斬獲獎項。2016年發表的第二部作品紀錄片《馬里烏波爾》(Mariupolis)聚焦於2014年以來烏克蘭東部戰爭中的這座城市,獲2016年立陶宛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獎和2016維爾紐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據報導,戰爭爆發後他重返馬里烏波爾,就是為了拍攝這部作品的姊妹篇。2019年他的首部故事片《帕台農》(Partenonas)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
曼塔斯的學術研究和影像作品存在一種互文關係。他的人類學視角深刻地影響到藝術創作。他在媒體採訪中說過,他對電影明星不感興趣,打動他的是普通人。他本人也往往將田野研究的內容生產為學術寫作和電影兩種形式。早在2006年曼塔斯就開始關注北高加索地區的人口失蹤和酷刑問題。2006年——2009年他就俄羅斯在車臣反恐行動中的暴力問題進行田野調查和拍攝,在此基礎上創作了紀錄片《隔離之地》並撰寫了博士論文,論文題目為《不存在之結:車臣反恐區法律邊界下的死亡、夢想和失蹤》(Knots of absence: death, dreams, and disappearances at the limits of law in the counter-terrorism zone of Chechnya)。2014年-2015年他又來到了馬里烏波爾做田野並拍攝同名紀錄片。2018年他發表了學術論文《肉身的合法性:反恐行動區的情感生活》(Carnal legalities: affective lives within zones of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進一步探討車臣和烏克蘭東部這些法律意義上的反恐區域是如何依靠權力濫用生成的,日常生活中人們的情感又是如何受到上述權力的影響的。2019年曼塔斯發表題為《永久停火:東烏克蘭戰爭和日常生活的展演》(Eternal Ceasefire: Performing War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Eastern Ukraine)的學術文章,從當地人日常生活的美學與情感的角度探討戰爭及其後果。包括故事片《帕台農》也基於曼塔斯3年來的民族誌研究攝製,主要關注身體與記憶。通過了解曼塔斯的學術研究來理解他的電影作品是一種很好的途徑。
「我的電影並不是關於戰爭的,而是關於戰爭地帶旁的日常生活,關於即便戰爭發生了,日常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
Mariupolis,馬里烏波爾這座城市有一個美麗的希臘名字。黑海和亞速海古時就是希臘人開闢殖民地,商船和探險家往來之地。但這座城市得名馬里烏波爾其實歸功於18世紀下半葉葉卡捷琳娜二世。她野心勃勃地制定過一個希臘計劃,想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建立一個希臘帝國,復興東羅馬的雄風。因此在黑海和亞速海水域出現了一連串擁有希臘名字的城市,比如塞瓦斯托波爾、雅爾塔、敖德薩,等等。用導演本人的話說,馬里烏波爾具有一種特殊的氛圍,既有古希臘神話的印記,又存在於詭異的後蘇聯現實之下。
曼塔斯把鏡頭對準2014年之後位於戰爭前線的馬里烏波爾。昔日俄羅斯帝國的美好願景已經不再,烏克蘭政府軍和俄羅斯支持下的分離主義者的對壘讓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顯得極其脆弱。導演不急不徐地展示這裏普通人的日子,其間充滿了詩意:一個男人逗他的小女兒玩,亞速海的水天一線間一對父女出海捕撈,冶金廠裏令人昏昏欲睡的消防培訓,鞋匠的修修補補。還有動物:野兔在草地上跑過,牛安靜地咀嚼草料,動物園裏的狗熊張大嘴巴,午後的蒼蠅在希臘雕像上爬過。在這座衰落了的工業城市,人們過着真正的慢生活。而戰爭的火藥味就隱現於這派寧靜祥和之中,構成一種背景音似的存在,隱隱地製造出一種緊張感。鞋匠的女兒想要成為戰地記者,在炮轟過的廢墟間學習報導;一個朋克少女學習怎樣使用槍支;軍人們在營地的東正教堂裏祈禱後在胸前劃十字離開;男人弟弟的忌日;前線傳來的爆炸聲。導演並未將主要的鏡頭直接對準硝煙瀰漫的戰場。戰爭浮現於於新聞廣播裏,還有人們不經意的聊天裏。只是不時地,譬如在戰地記者的鏡頭裏,才讓戰爭的全部恐怖面目露出原形。在關於兩部紀錄片的作品的一次訪談中,曼塔斯表示:「我的電影並不是關於戰爭的,而是關於戰爭地帶旁的日常生活,關於即便戰爭發生了,日常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
馬里烏波爾緊鄰烏俄邊境,在烏克蘭國家的最東南角上,也是此次戰爭的前線。導演敏鋭地捕捉到馬里烏波爾的邊界特徵,不管是政治屬性上的過渡性還是日常生活中的微妙矛盾和衝突。烏克蘭東部模糊的身份認同在這裏有時表現為對蘇聯的懷舊情緒,有時表現為一種不同於烏克蘭也不同於俄羅斯的地方性。比較洛茲尼察聚焦於2014年基輔的紀錄片《中央廣場》,這裏幾乎是另一個世界。影片中一個重要情節是慶祝5月9日偉大的「衞國戰爭勝利日」,這是蘇聯人和俄羅斯人對二戰中蘇德戰爭的稱呼。慶祝這個節日在烏克蘭始終是一個爭議話題。2015年烏克蘭國家議會最高拉達立法將5月9日命名為「反對納粹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日」,以和俄羅斯與蘇聯的傳統相區分。人們開始以不同方式慶祝勝利日。有人佩戴烏克蘭官方規定的紅罌粟,有人佩戴象徵俄羅斯軍隊和愛國主義的聖格奧爾基絲帶。片中人物不僅對歷史,而且對當下發生的戰爭也各執一詞,廣場上反對烏克蘭極右分子的人們和認為俄羅斯人在屠殺烏克蘭人的人們吵作一團。烏克蘭語和俄語,基督教徒和無神論者,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和斯大林像。這裏邊陲的特性無處不在。和洛茲尼察明確的親烏立場不同,曼塔斯在這衝突雙方之間並不選邊站。他以一種更為中立的視角温情地記錄下這一切。
消失的受害者們本人無法在片中露面,導演的鏡頭展示了他們的家屬是如何無休止地體驗到這種「無法無天」的暴力的。
如果說《馬里烏波爾》(Mariupolis)這部電影對暴力的描述更為剋制且柔和,那麼關於車臣的紀錄片《隔離之地》(Barzakh)就毫不掩飾其殘忍和恐怖。影片縈繞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圍中。Barzakh來自波斯語,在阿拉伯語和車臣語中的含義是limbo,靈薄獄,是生死的交界之地;在古蘭經中,是死後肉身與靈魂分離之處。曼塔斯講述車臣這座人間地獄發生過的暴行,令人不寒而慄。影片不時地從現實沉入幻想的世界,再回到現實,恍若在生死兩界來回穿梭。曼塔斯生前還曾從事水下考古。那些充滿超現實色彩的水下鏡頭或許正來自這段特殊的經驗。
《隔離之地》這部片子具有懸疑色彩,也是從寧靜而憂愁的日常生活開始。一個車臣女人的丈夫消失了,他究竟去了哪裏?一位老婦的兒子6年前被綁架,全家人至今還在尋找他。一個只有一隻耳朵的男人,他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隨着情節的推進,真相被一層層揭開。許多無辜的車臣平民被執法者以反恐的名義綁架,片中提到在車臣這樣消失的已有6000人。生還者展示曾經的審訊室和當局的酷刑,當時的審訊中他被殘忍割去了一隻耳朵。昏暗的囚室,夜裏的亂墳崗,不知道有多少犧牲者的亡靈遊蕩在這裏。而那些活着回來的人,都曾經進入過生死不明的靈薄地獄。一塊石碑上寫着:我在哪裏?發生了什麼?我究竟是死是活?影片的結尾,導演寫道:獻給娜塔莉亞。記者娜塔莉亞·埃斯蒂米洛娃(Natalya Khusainovna Estemirova)經歷了和片中人物類似的命運:2019年她因揭露當局這些恐怖行徑在車臣家門口被綁架並殘忍殺害。謀殺事件主使直指車臣共和國總統拉姆贊·卡德羅夫。
曼塔斯在學術論文《肉身的合法性:反恐行動區的情感生活》中寫道:車臣和烏克蘭東部都曾經是兩國官方分別界定的反恐行動區域。在這些地方,不僅已有的法律遭到破壞,還產生了新的暴力形式,比如接連發生的人口失蹤和酷刑。為了維持這些地區的「反恐」性質,必須系統性地依靠屈打成招甚至綁架和殺戮來捏造和「生產」出恐怖分子,而且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某種例外狀態。許多人被抓走,遭受折磨,死後屍體被當作所謂「恐怖分子的死屍」示眾。執法者製造出的系統性的例外狀態已經超越了法律界定的例外狀態。曼塔斯用一個俄文詞彙безпредел,「無法無天」,來描述後蘇聯空間這種國家機關日常的權力濫用,以及這種權力濫用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反覆和以多種方式體驗到的。
消失的受害者們本人無法在片中露面,導演的鏡頭展示了他們的家屬是如何無休止地體驗到這種「無法無天」的暴力的。他講述家人們(主要是女人)在檢察院拒絕立案後如何懷着最後一絲希望繼續上訴,一遍遍地講述受害者失蹤當天的經歷,不厭其煩地填寫表格和申請書,在街頭貼上一張又一張尋人啟事,占卜、反覆祈禱和哭泣,不斷地喃喃自語「我在夢中還見到了他」。
這個世界的一些惡並沒有被充分地反省和糾正,它們凝固在部分系統內部,還在重複上演。而戰爭本身,就是滋生這類暴力最好的土壤。面對曼塔斯的死,我們是時候再一次大聲呼籲和平。
曼塔斯的死掀起了一小波紀念他和反對戰爭的浪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Audrey Azoulay就表示「譴責殺害曼塔斯的行為。導演的死提醒人們要保護媒體工作者,尤其是在衝突地區工作的媒體工作者。應當對犯罪者進行追究和審判,以捍衞公正、表達自由和藝術自由。」曼塔斯的電影界同行對他的去世公開表達哀悼。立陶宛電影製片人Giedre Zickyte稱曼塔斯為立陶宛電影工業「真實而獨特的聲音」。Giedre Zickyte 表示:「許多人出於悲痛詢問為什麼曼塔斯要回到馬里烏波爾。我知道曼塔斯和他的拍攝對象之間有着多麼深厚的感情,而且他擁有一顆無比純粹的心靈。所以我能理解他為什麼覺得不能不直面這場戰爭,馬里烏波爾對他來說太珍貴了。而且他向來無所畏懼。當他覺得自己該去的時候就非去不可。」曼塔斯在牛津大學的碩士導師Bob Parkin悼念他說:「他是一名非常有才華的學者,緊跟人類學的前沿,而且不怕去觸碰那些困難的議題。這使得他能夠去參與其他各種形式的工作,包括到局勢複雜的地區拍攝複雜議題的電影,而且為此獻出了生命。」一些民間組織自行發起曼塔斯的電影放映和討論活動,將門票所得捐給逝者家人。
關於曼塔斯的死因,起初的報導是他遭遇火箭炮襲擊。然而不久前烏克蘭人權事務專員發佈對曼塔斯死因的調查結果,說他在馬里烏波爾被俄軍囚禁,然後開槍射殺,死後暴屍街頭。曼塔斯致力於研究和拍攝暴力,最終死於暴力,一個離奇的迴環。在《隔離之地》片中的暴行彷彿溢出鏡頭,進入了當下的現實,而導演本人又彷彿成為了自己紀錄片的主人公。這種時空的交錯和耦合不僅賦予了曼塔斯的人生一種藝術化的殉難色彩,還提醒着我們:這個世界的一些惡並沒有被充分地反省和糾正,它們凝固在部分系統內部,還在重複上演。而戰爭本身,就是滋生這類暴力最好的土壤。面對曼塔斯的死,我們是時候再一次大聲呼籲和平。
延伸閱讀:

【學人專訪】謝爾希.浦洛基:新的烏克蘭社會已經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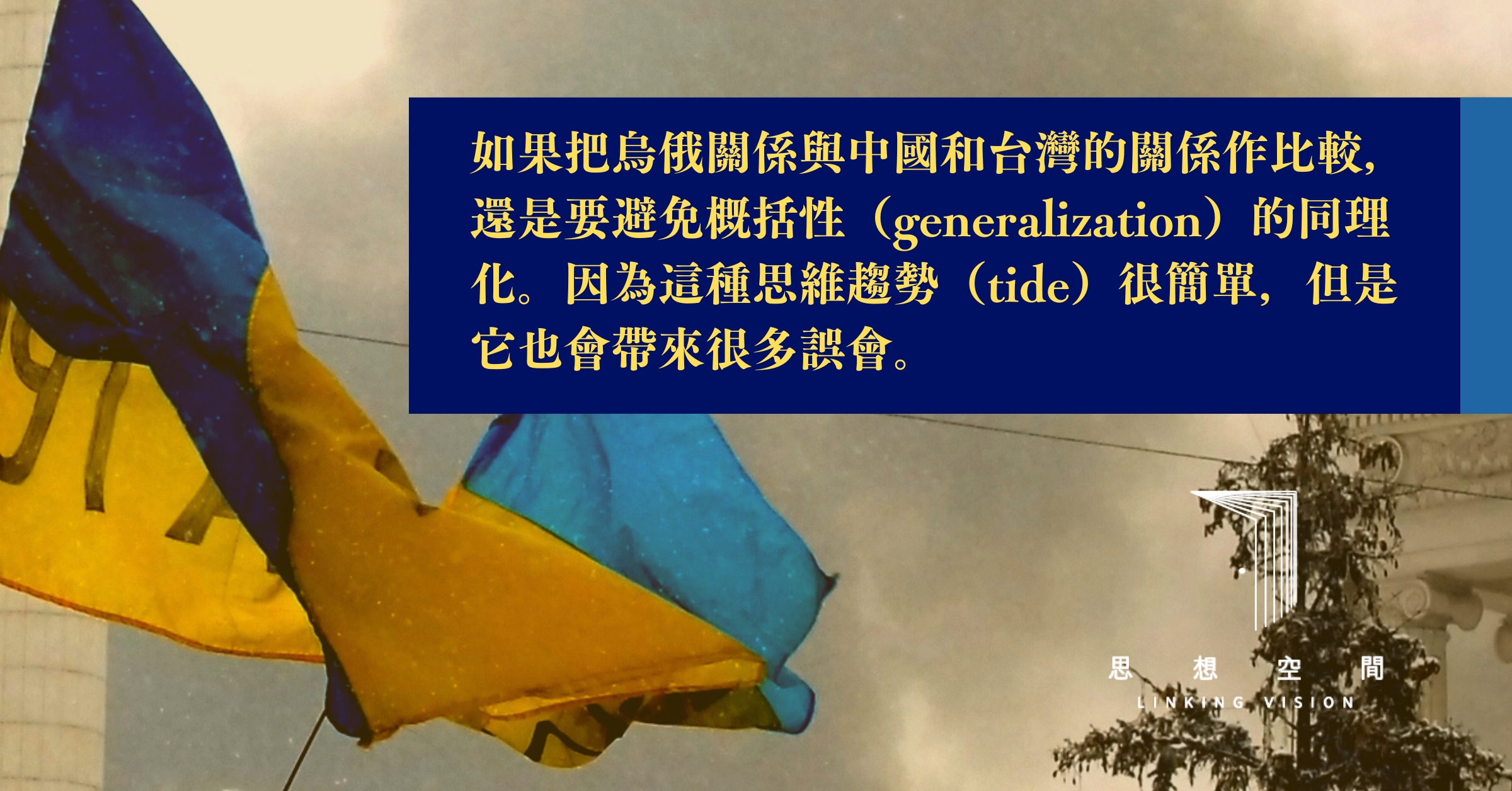
Mariana Savchenko x 涂豐恩:我們為何會低估烏克蘭人的力量與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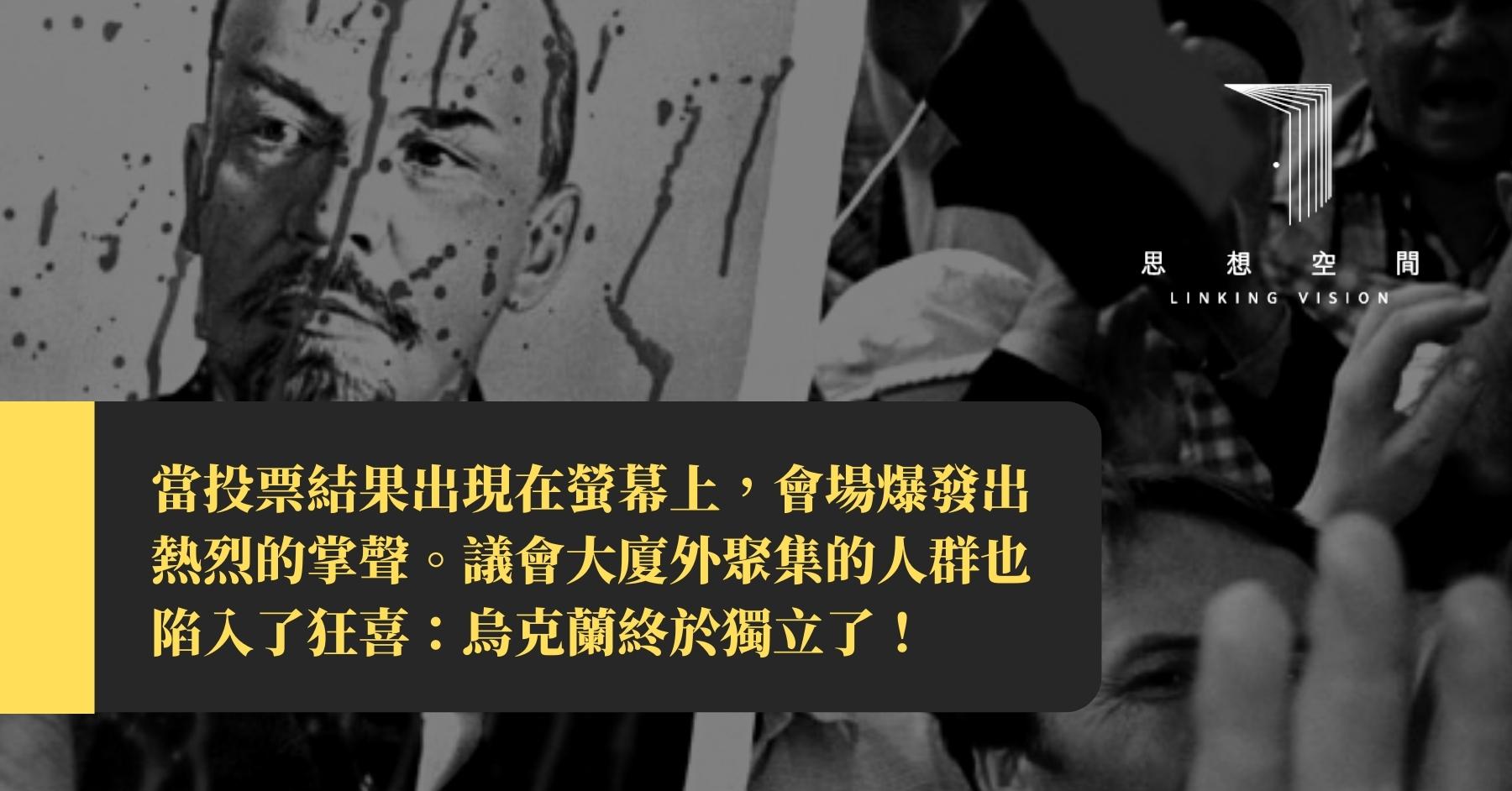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