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撰文 / Mariana Savchenko
編按:自2022年2月24日起,俄烏戰爭爆發至今已近一年;在戰火硝煙之中,世人也更加關注烏克蘭這個國家的歷史與文化。在《烏克蘭》一書中,哈佛大學烏克蘭中心主任謝爾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深度剖析這座「歐洲之門」兩千多年的歷史軌跡,從希羅多德到奧匈帝國,一直到今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聯經思想空間亦邀請了「烏克蘭之聲」的發起人之一瑪驪雅蒳(Mariana Savchenko),與本書作者浦洛基進行專訪,瞭解更多成書脈絡、及其對於烏克蘭歷史與當下的看法。
前言:謝爾希.浦洛基的《烏克蘭》一書的譯作最近(2022年9月)在台灣出版,這使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與世界媒體每日欄目所帶來的震撼相比,它是介紹烏克蘭的寶貴的信息來源。如果深入瞭解烏克蘭數百年歷史——自基輔羅斯時代以來我們文化的持續存在、哥薩克人的現象、在帝國主義幾個世紀和蘇聯幾十年的鎮壓之下的存在、以及在獨立年代社會發展——那麼現代烏克蘭對俄羅斯全面侵略的抵抗,就不會讓人感到意外。我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感激之情,與該書的作者、歷史學家浦洛基教授談論了這種背景對於我們別無選擇、也無法預料的今日的影響。
* 以下為訪談對話
M=瑪驪雅蒳(Mariana Savchenko)
S=謝爾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
M:在今天這個信息社會時代,歷史學家能否與宣傳家競爭?
S:這場戰爭的發生,實際上是一段以柏林牆倒塌為開端的時期的終結。冷戰的結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很顯然的是,冷戰結束後的世界將不復存在;未來會怎樣,則是目前人們正在解決的問題,包括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事實上,這一切都增加了我們對於歷史的興趣;歷史就像是個信息數據庫,通過它,我們可以思考並且想像當刻與未來。這種人類的經驗、烏克蘭的經驗,在今天看來都是非常需要的。與此同時,整個世界對自身歷史、戰爭史、冷戰史也愈來愈感興趣。歷史學家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水平,與更廣泛的聽眾對話。現在幾乎所有人都得從歷史學家和歷史中汲取資訊,而歷史學家面臨的主要挑戰,則是讓這種討論保持一定的學術水平與客觀性水平。這場戰爭也是整個時代的結果——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真相相對性」時期、否認真相本身的「假新聞時期」——因此,這對於史學家而言是一項額外的挑戰。也正如眼前所見,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使自我形象達到均衡評估的水平(the level of well-balanced assessments),讓真實而非虛構的事實重返到世界話語之中。
M:正如您所指出的,今天正在發生的進程是冷戰結束和帝國「半衰期」的必然結果,而它仍在進行中。在這樣一個社會轉型時期,是否有可能逆轉歷史進程,普丁逆轉歷史進程的強迫觀念是否可行?
S:當然,對於普丁來說,和許多人一樣,「理想世界」就是他們年輕時的世界,是他們進入現實生活、並體會周圍世界萬物的時候。普丁的青年時代,身處冷戰環境之中,蘇聯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之一,這也決定了他眼中的常態性。
俄羅斯的帝國歷史對他來說很正常,帝國廢墟上崛起的國家在他看來卻不在歷史之中,它們沒有存在的權利。普丁一方面生活在俄羅斯帝國主義思想中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在蘇聯作為超級大國時期的世界,而且他相信那之後發生的事情是蘇聯領導層犯錯的原因。普丁很討厭蘇聯領導,包括列寧,甚至是斯大林,尤其是在民族問題上,還有西方的各種「陰險行為」;而他的歷史使命,恰恰就是糾正「扭曲的歷史」。也就是說,普丁的思考其實不在 20 世紀帝國崩潰的框架中;而烏克蘭戰場上正在決定的,恰好就是這些歷史的版本,或解讀其中哪一種才是真實的。
普丁的思想也為在烏克蘭進行的所謂「軍事行動」形成了基礎。該行動應該只持續幾週、甚至幾天,以「統一的俄羅斯人民」而告終。然而,好吧,這一切的後果我們都看到了:我們一方面看到了烏克蘭的悲劇,但另一方面也看到西方國家的團結,以及俄羅斯的一系列失敗。從當今世界走向來看,這是一個很好的跡象。
M:那麼,為什麼「戰略家普丁」沒有考慮到過去 30 年來烏克蘭一直在發展一個新社會,尤其是在兩次獨立廣場革命之後,這個社會具有與他不同的價值觀,並且不像他那樣懷念過去?
S:從他的文章和演講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否認烏克蘭人民具有任何主體性(主觀能動性)。在他看來,烏克蘭人是被民族主義者恐嚇、被西方國家賄賂的俄羅斯人,他們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行動和立場。這是從他管理俄羅斯人民的經驗中得出的。實際上俄羅斯社會完全無力,無法保持自治,即使被送入在普丁看來「自相殘殺的戰爭」時也無法抵抗。這就是普丁在俄羅斯以「同一民族」觀念助長的經驗傳播,他相信我們和他們是同一個民族。但為什麼俄羅斯人民的行為如此,烏克蘭人民又有不同的行為呢?因此,普丁是他自己的思想和歷史解讀的受害者。
M:但普丁應該明白,烏克蘭的政治局勢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發展,儘管在他看來是「同一個民族」⋯⋯
S:不,他並不明白。他所寫的、所說的或所做的都表明:他不明白。我們對他所理解的和不理解的過於信任。
M:的確,在某個階段,烏克蘭和我們西方夥伴低估了普丁的野心。在我看來,世界上許多國家對於烏克蘭(以及其他後蘇聯國家)的歷史,仍然沒有從蘇維埃俄羅斯以分散的方式被理解和研究。如果後蘇聯研究向國家研究的範式轉移早點發生,是否有可能避免這場戰爭?
S:首先,學術界的確相當保守,對烏克蘭的過去以及當代歷史的瞭解非常有限。烏克蘭社會在過去 8 年中發生的變化基本上未被留意到,2014年後烏克蘭武裝部隊的出現也被專家界忽視,所有知識都與俄羅斯軍隊有關。
這有幾個原因:一方面,學術專家社群通常是如此形成的,當然其重點是俄羅斯——從俄羅斯文學到俄羅斯政治。另一方面,對於整個世界前往方向和方式存在絕對的幻想。德國認為,如果吸引俄羅斯參與一些聯合經濟項目,會降低其戰鬥的能力或意願。其實這並沒有降低俄羅斯的戰鬥欲望,反而增加對其軍隊的財政支持。因此(學界)犯了很多錯誤,而且一種思維慣性與學術存在的慣性重疊。在美國和加拿大,至少在學術界,由於在烏克蘭僑民的幫助下創建了研究所和教研組,情況還要好一些;但在更傳統的歐洲社會中,實際上與烏克蘭很接近的國家,例如德國或法國的烏克蘭學研究,目前都還處於非常萌芽的階段。當然,我很難從大學校園的專家環境中缺乏關於烏克蘭的知識,與所發生的局勢得出如此直接的聯繫,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事情是相互關聯的。
M:您如何向那些不完全瞭解烏克蘭民族、烏克蘭民族理念以及烏克蘭民族何時形成的地區讀者作出解釋?
S:我認為烏克蘭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一切,都應該放在19、20世紀歐洲發展的背景下來看。歐洲民族(nations)的根基相當深厚,但是近現代民族(nations)的形成卻是19世紀的歷史。這是一個與語言和文化統一標誌相關的歷史。 19世紀中下半葉,統一的德國就是這樣誕生的,統一的意大利也是這樣誕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部分崩潰。正是在它們的廢墟上,在文化統一的基礎上形成了現代民族(nations),烏克蘭就是其中之一。首先,由於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以及俄羅斯強大的帝國主義傳統,烏克蘭與波蘭、匈牙利不同,無法在(1917年的)革命期間以及之後保持獨立。這獨立伴隨著蘇聯解體而來。因此,這就是烏克蘭歷史和今日現實的整體框架,以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它。今天發生的戰爭是俄羅斯帝國崩潰及之後蘇聯崩潰的延續。今天的俄羅斯正試圖作為中國和印度的朋友,以某種反殖民主義的方式團結起來對抗西方,但實際上卻是在發動一場帝國戰爭。中國和印度都需要瞭解這一點,但我認為目前在政治階層或整個社會層面都沒有這種瞭解。
M:那麼如何解釋烏克蘭人不是俄羅斯人這一事實的價值本質呢?如何傳達並解釋這種主體性,我們這種「烏克蘭性」?
S:曾有一段時間,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庫奇馬 (Leonid Kuchma) 出版了一本關於烏克蘭的半回憶半反思的書,書名是《烏克蘭不是俄羅斯》。這本書是在莫斯科首次以俄語出版的,他試圖向俄羅斯領導層傳達這個簡單的事實,尤其是當普丁堅持要他驅散 2004 年的廣場革命(橙色革命)時。
「烏克蘭不是俄羅斯」存在於多種層面,但主要層面基於烏克蘭是一個公民社會非常發達的國家,烏克蘭可以非常有效地動員起來反對一個試圖剝奪一些基本個人自由的國家,即反對自己國家政府,並且可以非常有效地動員起來反對外部侵略,尤其是正如今年發生的情況。
因此,這是一個擁有非常強大的公民社會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任何與領導層達成協議的嘗試,就像與亞努科維奇一樣,都不會產生任何結果。這種嘗試對於任何烏克蘭政治家來說,意味著一張單程票——移民。所以烏克蘭是一個自由人民的國家,我認為這是對「我們是誰」最簡單也可能是最準確的解釋。
M:事實上就是這樣,但從像俄羅斯這樣不承認我們、並強制試圖將我們納入其帝國範式的國家的角度來看,這顯然是不夠的。什麼可以作為承認一個年輕民族 (nation) 獨立和生存權利的證據?
S:一個獨立國家存在的每一天,都是存在權的又一證明。其次,是這個民族 (nation)有多少自我意識、以及它多麼願意保持自我的問題;有一個關於民族(nation)的經典定義,即「一個民族(nation)是每天的人民公決」。所以我們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我們彼此不認識,但我們想像彼此是一體的。只要這個想法和對這個想法的奉獻存在,這個民族(nation)就存在。
有時,這種意識存在在沒有國家 (state) 的情況下。波蘭人創作的國歌,講的內容是關於波蘭國家 (state) 在 18 世紀消失、但他們仍然存在。所以有時這些是很持久的事業。波蘭從歐洲地圖上被消滅,因為分裂它的國家——俄羅斯、普魯士和哈布斯堡王朝同意「波蘭」這個詞不應該出現在該地區的任何實體名稱和地圖上,但波蘭整體上回來了。這些都是長期的事業,我想再次強調,民族 (nation) 在國境 (state) 以內或以外存在的每一天,都是其存在權的另一個論據。我們希望這個問題很快得到解決,但這些都是歷史過程,實際上有時需要比一兩代人的生命更長的時間。
M: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在台灣社會引起了較大的共鳴,烏克蘭被視為動員和抵抗的典範,而台灣也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在您看來,將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係、與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進行比較,是否有意義?
S:相似之處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外部的、更強大的對方都不承認人民或國家獨立存在的權利。這是最明顯的對比。如今烏克蘭非常成功地抵抗,實際上已經讓台灣處於比以前更有利的地位。它首先表明的是,通過武力改變邊界的企圖是無法保證的,可能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和危機。烏克蘭戰爭的發展方式對台灣的安全帶來了很大的好處。這場戰爭做到的第二件事,是動員了西方;而西方是台灣的傳統夥伴和盟友,這是台灣因烏克蘭抵抗而獲得的另一個利益。
所以,一方面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就像您說的:對於台灣人而言有一個榜樣告訴你:捍衛自己的選擇是必要且值得的。第三, 烏克蘭改變了世界的思維方式,而將它改變為有利於台灣和台灣的的主權。由於烏克蘭的抵抗,中國軍事入侵(台灣)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如果烏克蘭沒有提供這種抵抗、並且俄羅斯在2月底或3月初的時候實現了其目標,那麼這種可能性(武力侵台)就會大得多。
M:您如何解釋烏克蘭今天的抵抗機制?與以往的歷史經驗和其他國家的經驗相比,它有何獨特之處?
S:我不認為這對世界經驗而言有任何獨特性,因為烏克蘭正在進行的是一場典型的反帝國戰爭——反對帝國主義力量,社會和國家團結一致,相互支持。這是一場愛國高潮、動員和捍衛獨立的戰爭,也就是經典的「獨立戰爭」。儘管它在蘇聯解體後被推遲,且烏克蘭已經處於國家機構及社會成型的狀態。
所以,就世界歷史的獨特性而言,這場獨立戰爭發生在帝國正式崩潰後的大約30年。
但這對烏克蘭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第一次有烏克蘭國家與人民站在一起,相互支持、加強。這在烏克蘭歷史上才是獨一無二的。
M:全世界,包括台灣的目光,都聚焦在澤連斯基總統的身上。澤連斯基作為政治家的現象是什麼,他在這場戰爭中扮演什麼角色?
S:澤連斯基總統在烏克蘭選民的極大支持聲中上台,大約 73% 的選民投票支持他。他上台是作為和平解決與俄羅斯聯邦所有問題的支持者,也實際上表明他正試圖達成某種共識。當戰爭開始,他呼籲人民抵抗,而且由於這場戰爭不是他的選擇,烏克蘭成為侵略的對象,澤連斯基也得到了極高的信任。
總統留在基輔並領導國家捍衛主權,這成為了非常重要的積極因素,尤其是在戰爭的頭幾天和幾週。並且,這發生在澤連斯基的前任之一、亞努科維奇總統在危機期間逃離的背景之下,發生在阿富汗總統在危機和戰爭開始時從阿富汗領土上消失的背景下。澤連斯基實際上打破了已開始的全球趨勢,也打破了烏克蘭總統在面對國家、個人、家人等受到威脅時的行為方式的模式。
澤連斯基總統的角色,當然應該放在烏克蘭社會情緒的背景下。在戰爭的任何階段,即使是最糟糕的階段,也有不少於 75% 的受訪烏克蘭人相信勝利。這一定程度上,當然可以說是澤連斯基總統的功勞,他的立場反映了整個社會的情緒。而這正顯現出了這場鬥爭中政府和人民的團結,這是烏克蘭最強大的力量,也是最大的驚喜,無論是對侵略者、還是對部分烏克蘭歷史而言。因為在烏克蘭歷史上,政府和人民大多站在對立面;而這種情況在今年發生了變化,並將持續。
M:您如何看待戰後世界秩序?如何看待我們勝利後,烏克蘭和整個世界的變化前景?
S:我認為這場戰爭的後果之一,已經很明顯了,就是歐洲「灰色地帶」的消失。事實上,烏克蘭和摩爾多瓦將從「灰色地帶」走向西方,即融入歐洲和跨大西洋世界的經濟、政治和安全結構。這場戰爭的另一個後果也相當明顯,那就是俄羅斯的顯著削弱。因此,俄羅斯將自己視為多極世界的極點之一的地緣政治野心,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將會終結。
我認為,最終我們會看到中俄之間有更多合作,很可能會出現中國成為世界第二極的趨勢,不僅是從經濟的角度、也是從政治的角度。因此,我認為這是整個世界的重新格式化開始。所以西方的鞏固、俄羅斯的削弱,(世界)可能朝著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兩極之一的方向又邁出一步。當然,預測是一項非常忘恩負義的工作,但這些趨勢在今天已經很明顯了。
M:在您看來,俄羅斯的這種削弱可能會導致俄羅斯在某種程度上解體嗎?
S:如果這種削弱還導致政權危機,而不僅僅是權力更迭,那麼俄羅斯的部分解體是很有可能實現的。比如說車臣,它不僅是自治的,也可以說是俄羅斯聯邦的半獨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聯邦外圍某處(包括亞洲)民族運動的增長,但俄羅斯的骨幹仍將存在。所以至少在今天,我沒有看到任何更徹底解體的跡象,但當然邊界可能會發生變化。
M:如果我們真的發現自己與中國處於戰後世界的不同兩極,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雙方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S:很明顯,中國在這場戰爭中並不是烏克蘭的盟友,它採取了中立的立場。中立好於敵對,當然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應該受到重視的因素。但很顯然中國不是盟友,因此,烏克蘭絕對清楚北約是一個政治、戰略和安全盟友。這並不意味著(至少目前,未來可能會改變)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應該以某種方式停止或對其施加任何限制;也許在未來,但不是今日。但在政治上、地緣戰略上和安全上,烏克蘭已經做出了選擇,這絕對是烏克蘭作為一個國家生存和存在的先決條件。
中國保持中立對烏克蘭極為重要,這是當今烏克蘭政治的主要任務之一。烏克蘭應該在這個意義上採取非常周密考慮的立場,即在這個問題上採取戰略性行動。以色列就是這種行為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以色列也處於幾乎永久的戰爭狀態,顯然是永久的威脅,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並不孤單。我認為朋友和合作夥伴完全理解這種情況並且考慮到烏克蘭所處的戰爭狀態,對於烏克蘭在情感上以及在政治上可以成為盟友的理解是絕對踏實。
M:你認為我們勝利後有可能完全重新一體化歸還的臨時被佔領土嗎?首先,在世界觀和文化意義上,考慮到8年的俄佔和思想工作。
S:當然,隨著烏克蘭不斷被分裂的每一天,重返社會的難度將越來越大。但很明顯,在過去的 8 年裡,與 2014 年之前相比,烏克蘭形成了一個不同的社會,對自身的不同理解,與政府和世界的不同關係。
而相反的過程發生在臨時被佔領土上。這是一個挑戰,但從歷史上看,8 年仍然是相當短的時間。當我們談論帝國的崩潰、國家建設的過程等等時,指的是幾代人,幾十年,有時甚至是幾個世紀,所以這並非不可能。例如,重新一體化的基礎問題——如果在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還不清楚,在2022 年就變得非常清楚了:實際重新一體化只能在這些領土融入新的烏克蘭社會的基礎上進行,而這新的烏克蘭社會已經形成並捍衛了其生存權和生命權。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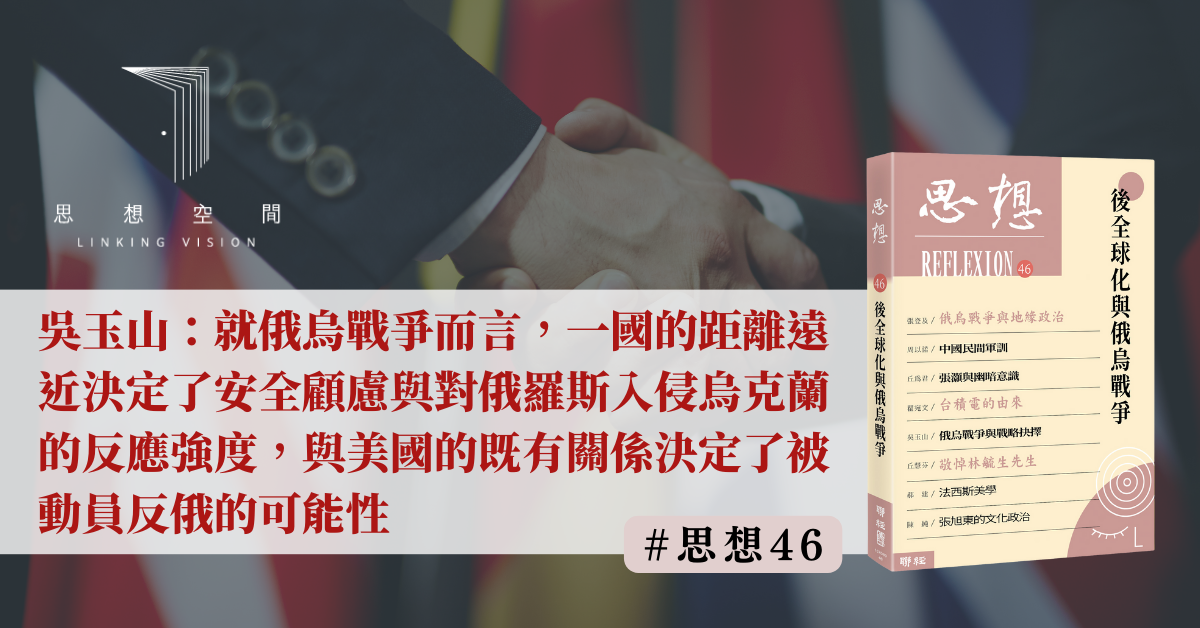
盤點各國在俄烏戰爭中的站位——如何理解戰略抉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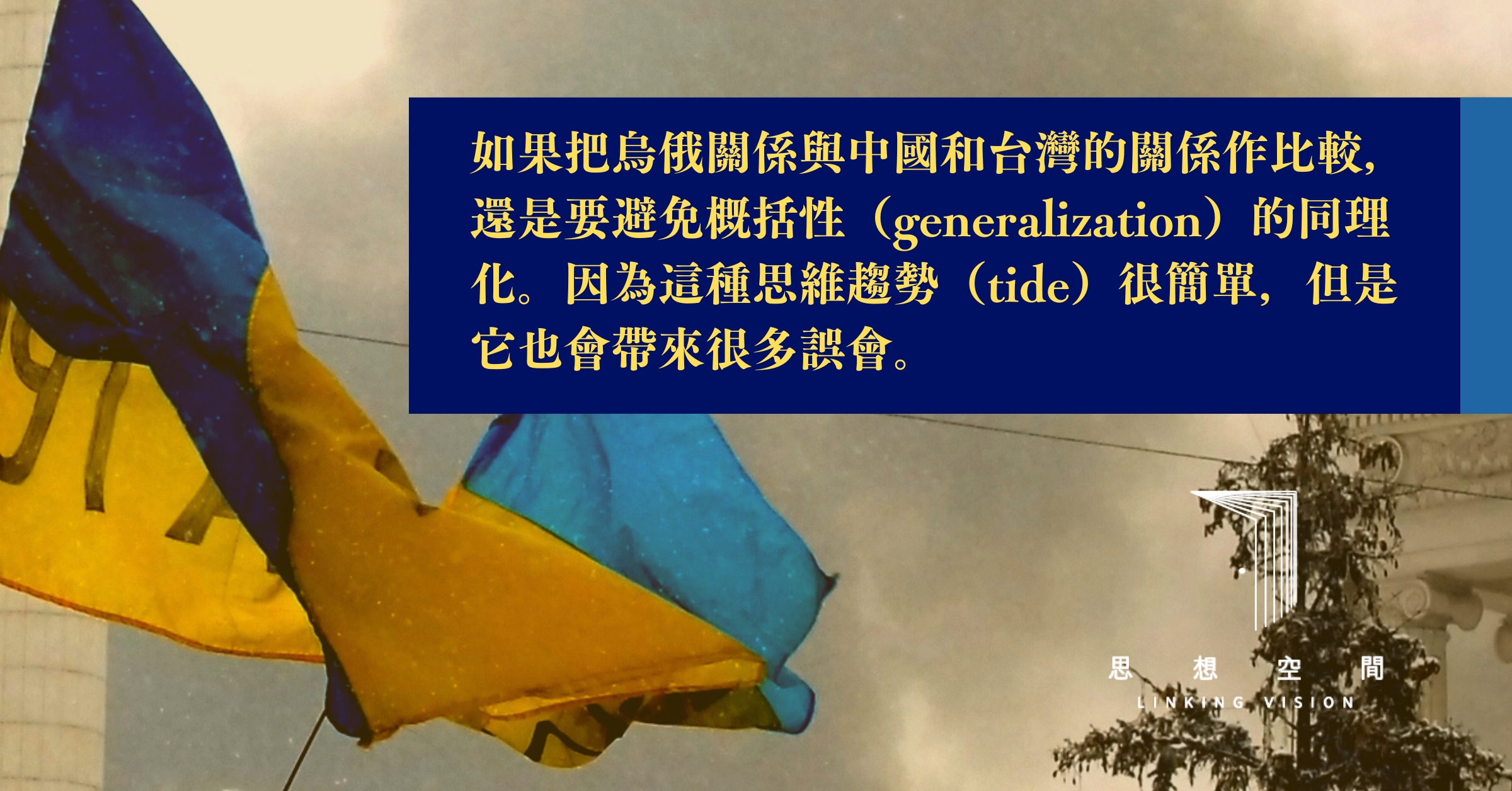
Mariana Savchenko x 涂豐恩:我們為何會低估烏克蘭人的力量與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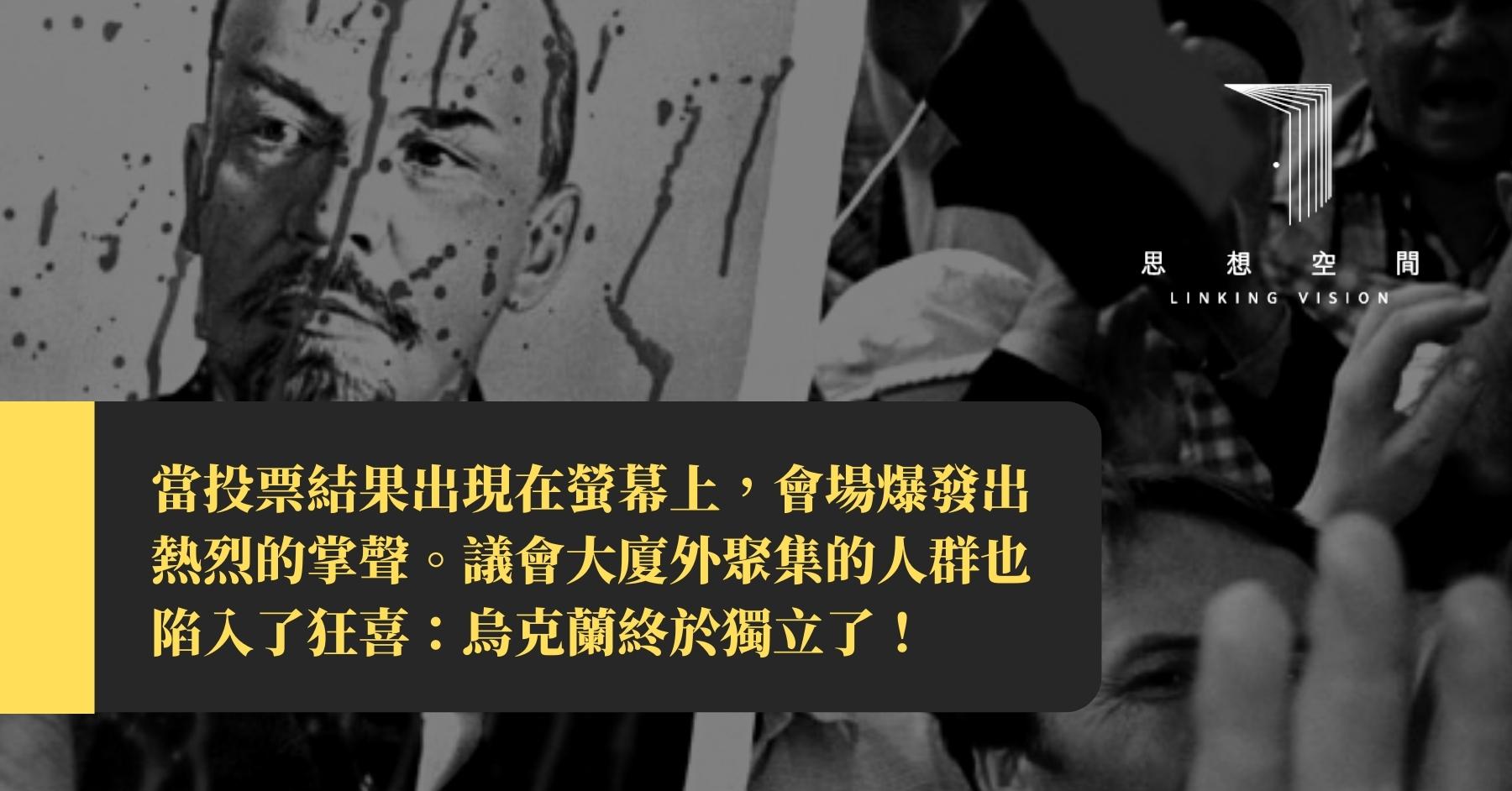
謝爾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帝國煙消雲散時,烏克蘭的誕生(二之二)
| 閱讀推薦 |

瑪驪雅蒳(Mariana Savchenko)是烏克蘭漢學研究員、文學譯者、音樂製作人和聲音藝術家,目前在基輔塔拉斯·舍甫琴科國立大學攻讀中文語言學和民族音樂學博士學位。 瑪驪雅蒳於五月抵達台灣,作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烏克蘭學生和學者獎學金的獲得者,目前在中研院語言所實習。在台灣,瑪驪雅蒳與其他烏克蘭專家一起建立了獨立訊息平台「烏克蘭之聲」,希望幫助台灣朋友更好地了解烏克蘭,其複雜的歷史和動盪不安的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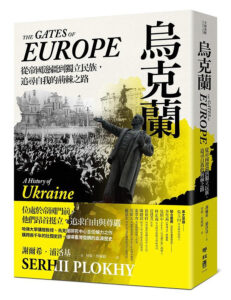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