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在求學的道路上緩慢爬行中。研究興趣為香港、臺灣、馬來西亞三地文學,也在努力開拓其他地方文學的領域。經常陷入自我懷疑的狀態,最喜歡無所事事的日子,因此總是跟不上世界變化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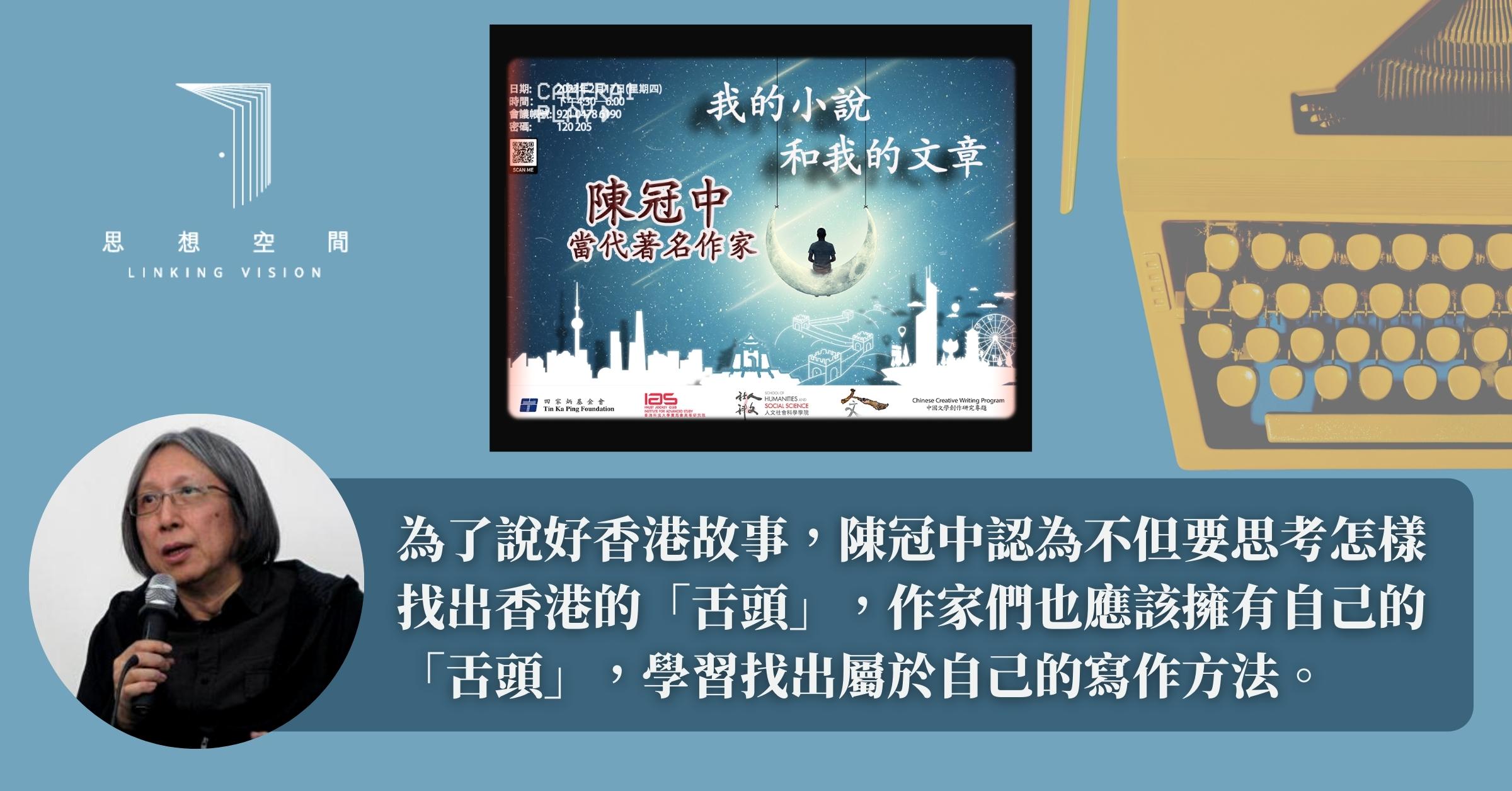
記錄/郭曉琳
編按:2022年2月17日,由香港科技大學創意寫作項目舉辦的「港臺名家系列講座」展開第一講,邀請到華文作家陳冠中,以「我的小說和我的文章」為主題作分享。在演講中,陳冠中分享了自身文學閱讀及三地經驗,提出了「為什麼我寫的小說是華文的?我是香港作家嗎?」的疑問,並試圖提出作家應如何擁有自己的「舌頭」、找出屬於自己的寫作方法。
| 講者簡介 |
陳冠中,華文作家,香港大學榮譽院士,香港浸會大學榮譽院士, 2013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著作有小說《盛世》、《裸命》、《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什麼都沒有發生》、《香港三部曲》、文集《我這一代香港人》、《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或許有用的思想》、《是荒誕又如何》等等。1976年在香港創辦《號外》雜誌,1980年代從事電影編劇,並策劃監製了超過十齣香港電影和三齣美國電影。1995年參與創辦台灣超級電視台,並為北京《讀書》月刊1994年至1997年繁體版的出版人。2008年至2011年出任國際綠色和平理事。現為台灣《思想》季刊編委。
演講一開始,陳冠中就扼要說明了是次分享的三個重點:第一,說明6、70年代的香港,以及華人世界提供了怎樣的條件,使自己走上狹窄的寫作之路。第二,香港寫作者在華文世界寫作的焦慮和問題。第三,找出香港作家「舌頭」的方法。
對陳冠中來說,中學預科的經歷培養了他對中國歷史的興趣,以及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嚮往。
關注文學的起點
陳冠中首先分享自己中學時代的課外讀物,除了《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之外,陳冠中還會租借金庸的武俠小說。
中三(註:國中三年級)的時候,他開始接觸《中國學生週報》。起初是被笑話版「快活谷」所吸引,但隨後注意到電影版介紹很多非商業電影的影評,因而意識到廣闊的世界,並且開始關心文學,更可以說其「文藝青年」的傾向是從《中國學生週報》所介紹的各地藝術電影中培養出來的。
對陳冠中來說,中學預科的經歷培養了他對中國歷史的興趣,以及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嚮往。由於預科選修文科的關係,陳冠中得以讀到錢穆的《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和《秦漢史》,讓他第一次有「看書」的感覺。
除此之外,他也開始閱讀《明報月刊》,裡面關於中國知識份子趣味的文章使他成為一個「知道份子」——甚麼都知道一點,甚麼都想知道。後來陳冠中寫了兩篇年輕人抱怨香港教育制度的文章投稿至《星島晚報》副刊,這是他最早發表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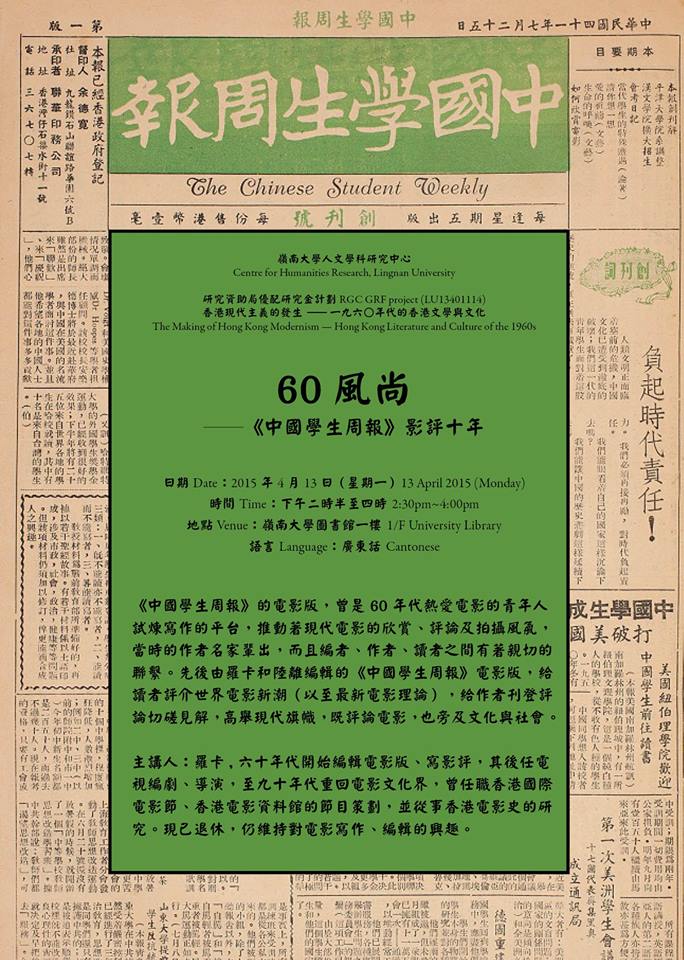
如果說臺灣文學使他建立閱讀華文小說的習慣,留學美國的經歷則迫使他培養出閱讀英文小說的愛好,甚至逐漸注意到不同地方和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
華文文學的「根」來自臺北
直到大學一年級,陳冠中才真正對文學產生興趣。
1971年考入大學後,他經常會去尖沙咀「文藝書屋」。這家書店主要售賣臺灣書籍,書店主人王敬羲是一名去臺灣留學的香港僑生,其小說曾在臺灣文學刊物上發表,後來結集出版《康同的歸來》。陳冠中在那家書店買了不少書籍,比如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余光中的散文集《左手的繆思》、詩集《五陵少年》,李敖《傳統下的獨白》,小說方面則有白先勇《臺北人》、《紐約客》,以及臺灣皇冠出版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臺北的出版物和臺灣作家的創作是他最初接觸的文學作品,是以陳冠中笑言自己「華文文學的根來自臺北」,加上他當時幾乎沒有讀過香港作家和中國大陸作家的作品,所以自言其文學源頭並非魯迅,而是張愛玲。


大學時期的陳冠中斷斷續續寫了許多影評,還有三篇短篇小說,但他並未想過專職寫作。對他們這一代人來說,以寫作維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1974年大學畢業後,陳冠中遠赴美國波士頓大學攻讀新聞學研究生課程,一來出於逃避心理,二來自覺英文欠佳,赴美初期更因此而產生極大的焦慮。
其後,他決定透過大量閱讀來加強自己的英文能力,起初讀海明威(Ernest Miller)、《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 1925)等美國經典文學。6、70年代的美國的嬉皮運動氛圍又使陳冠中接觸到一些反映時代精神的流行讀物,比如《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第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Five, 1969)、吳爾芙(Virginia Woolf)、後現代小說等等。
如果說臺灣文學使他建立閱讀華文小說的習慣,留學美國的經歷則迫使他培養出閱讀英文小說的愛好,甚至逐漸注意到不同地方和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例如是符合知識份子興趣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 1945)、《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一九八四》(1949),歐洲大陸的創作如《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1984)、《瓦解》(Things Fall Apart, 1958)、《白牙》(White Fang, 1906),以及《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 1997)、《雪》(Snow, 2002)、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拉丁美洲小說和印度魔幻寫實小說等歐洲大陸以外的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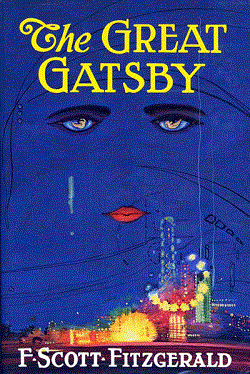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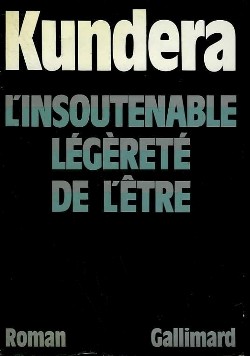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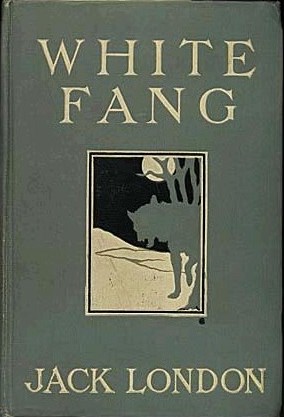
香港的教育環境、文化資源為他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既能找到大量英文書籍,也能在一般書店找到不同政治立場的刊物……
《號外》讓我變成一個文化人
對陳冠中而言,華文世界和英文世界一直是共存關係。回港以後,陳冠中一邊任職英文報紙《星報》(Star)記者,一邊與大學同學在灣仔開了一家樓上書店「一山書屋」,主要出售遠景和遠流兩家臺灣出版社的作品和大陸的盜版書籍。
1976年,他聯同朋友丘世文、鄧小宇及胡君毅創辦《號外》雜誌,最初是想繼承《中國學生週報》、《70年代雙周刊》的概念,配合自己在美國讀到的地下報紙及《紐約》(New York)雜誌的新新媒體,以同代人為目標讀者,寫一些符合這一代年青人趣味的文章。由於《號外》的作者不多,所以每位編輯都要寫大量文章。時任全職編輯的陳冠中認為《號外》讓他重新書寫中文,以不同風格和筆名把讀過的英文作品以標準白話文變成本土的味道,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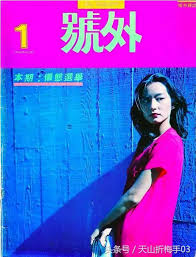
除此之外,香港的教育環境、文化資源為他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既能找到大量英文書籍,也能在一般書店找到不同政治立場的刊物,而其著作《太陽膏的夢》和《半唐番城市筆記》都是出版以《號外》為主的文章。陳冠中認為《號外》不只譯介西方作品,還探問香港本土的意義,使他得以不斷挖掘自己對本土的理解。
陳冠中指自己與同代人共享相同的香港背景,其後因個人決定而走向文化,又在偶然情況下寫了大量文章、短篇小說,直到2009年才下定決心把寫作的主力放在小說上。
三城記:香港—北京—臺北
自80年代起,陳冠中進入香港電影圈工作,先後改編白先勇〈謫仙記〉和張愛玲〈傾城之戀〉,又參與了《上海之夜》、《等待黎明》、《花街時代》等歷史電影的劇本創作。1992年因為投資者有意進入北京文化圈而前往北京工作,期間讀了不少中國知識份子作品。1994年起旅居臺北,陳冠中也在這段時間閱讀大量臺灣作家的作品,比如平路、蘇偉貞、陳玉慧《海神家族》、吳明益《複眼人》、楊牧《水田裡的媽媽》等。除此之外,他也讀了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西西《我城》、趙振開(北島)的《波動》等兩岸三地的作品,這些年的閱讀經驗讓他明白中國、香港、臺灣三地雖同樣使用華文寫作,但大家的路徑卻截然不同,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教育。


那時陳冠中在臺北電視台工作,電視劇劇本《總統的故事》成為他的第一本單行本小說。後來他覺得應該寫一個香港故事,於是在香港九七回歸後交出第二本單行本小說《什麼都沒有發生》。2000年起定居北京,陳冠中才真正下定決定從事寫作工作。他開始大量閱讀中國大陸小說,比如茅盾《虹》、錢鍾書《圍城》、老舍《正紅旗下》、施蟄存的心理小說和魯迅作品。女性作家方面,他則讀了虹影《饑餓的女兒》、葉廣芩《采桑子》、劉索拉《你別無選擇》和藏族作家白瑪娜珍的《復活的度母》。2008年北京奧運後出版小說《盛世》,57歲的陳冠中才真正立志要成為小說家,過去十年間他不但堅持寫文章,也出版了四本以中國為主題的作品:《盛世》、《裸命》、《建豐二年》及《北京零公里》。陳冠中指自己與同代人共享相同的香港背景,其後因個人決定而走向文化,又在偶然情況下寫了大量文章、短篇小說,直到2009年才下定決心把寫作的主力放在小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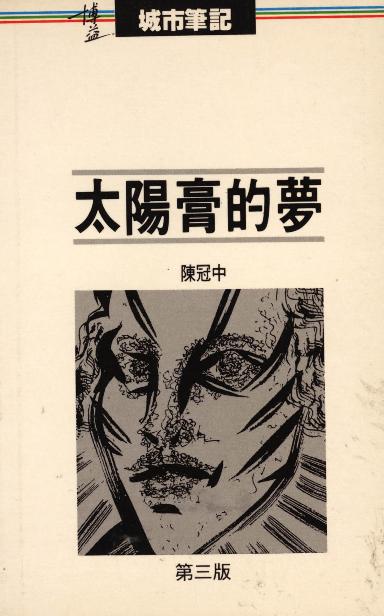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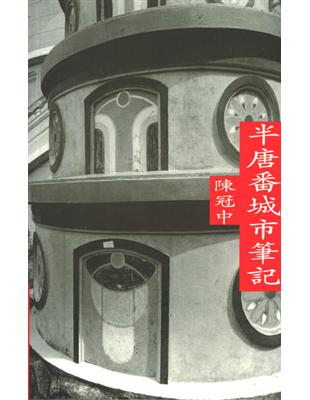

陳冠中認為每個地方的作家都應該有寫作上的限制——怎麼寫?寫給誰看?這些都是必須問的問題,而每個作家都會有自己的解決方法,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
尋找地方作家的「舌頭」
雖然香港為陳冠中提供了寫作的條件,但他也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麼我寫的小說是華文的?我是香港作家嗎?」陳冠中在大陸時總被冠上香港作家的標籤,他表示自己很樂意成為香港作家,但研究者必須講究香港作家的定義。
用陳冠中的話來說,自己移居北京24年,四部小說都是是關於中國大陸的,這種情況下該如何判斷作家的身份?因此,香港作家的身份必須加以論證,畢竟沒有人知道香港作家該怎樣寫作。過去的香港作家習慣以標準書面語寫作,但他發現地方作家往往關注怎樣在標準書面語的情況下加入地方色彩。他舉出香港作家亦舒和上海作家張愛玲的小說為例,她們雖然同樣在香港寫作,但前者的小說對白全是普通話,後者則表明自己寫給上海人看,那麼又該如何理解香港作家的身份?
因此,陳冠中認為每個地方的作家都應該有寫作上的限制——怎麼寫?寫給誰看?這些都是必須問的問題,而每個作家都會有自己的解決方法,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比如他的小說〈金都茶餐廳〉以粵語寫成,每一個字都可以在古漢語中找得到,但非粵語讀者就會覺得自己在讀外星文一樣,很難看得懂。又如臺灣作家的臺語創作,他認為全都是作家各自選擇的結果,也反映了作家意圖。
及後,陳冠中提到「舌頭」的比喻來自巴基斯坦裔英國作家哈尼夫.庫雷西(Hanif Kureishi)的短篇小說〈你的舌頭在我的喉嚨〉(With Your Tongue Down My Throat, 1987),他認為這個比喻很能夠說明「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也斯語)的原因。從人類學家的角度來看,處理自身文化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外部世界理解原始民族,另一種就是原始部落的世界觀。由於外面的人不懂在地語言,於是大家都在借用外來的目光講述自己的本土文化,但這可能是錯誤的決定。為了說好香港故事,陳冠中認為不但要思考怎樣找出香港的「舌頭」,作家們也應該擁有自己的「舌頭」,學習找出屬於自己的寫作方法。可是,當大家都在使用自己的「舌頭」時,如何混合眾人的語言、予以溝通和理解也會形成新的困局。正如陳冠中在〈一種華文:各表、同表、共生〉提到香港、臺灣和北京雖然使用同一種華文,但在用法上越來越不一樣了,而且三地讀者都不太關心對方,因此他認為必須要培養「超級讀者」——能看得懂幾種華文的讀者,畢竟「現在可能是華文最多花樣的時代,恰恰也是互相最不理解對方的時候」。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在求學的道路上緩慢爬行中。研究興趣為香港、臺灣、馬來西亞三地文學,也在努力開拓其他地方文學的領域。經常陷入自我懷疑的狀態,最喜歡無所事事的日子,因此總是跟不上世界變化的速度。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