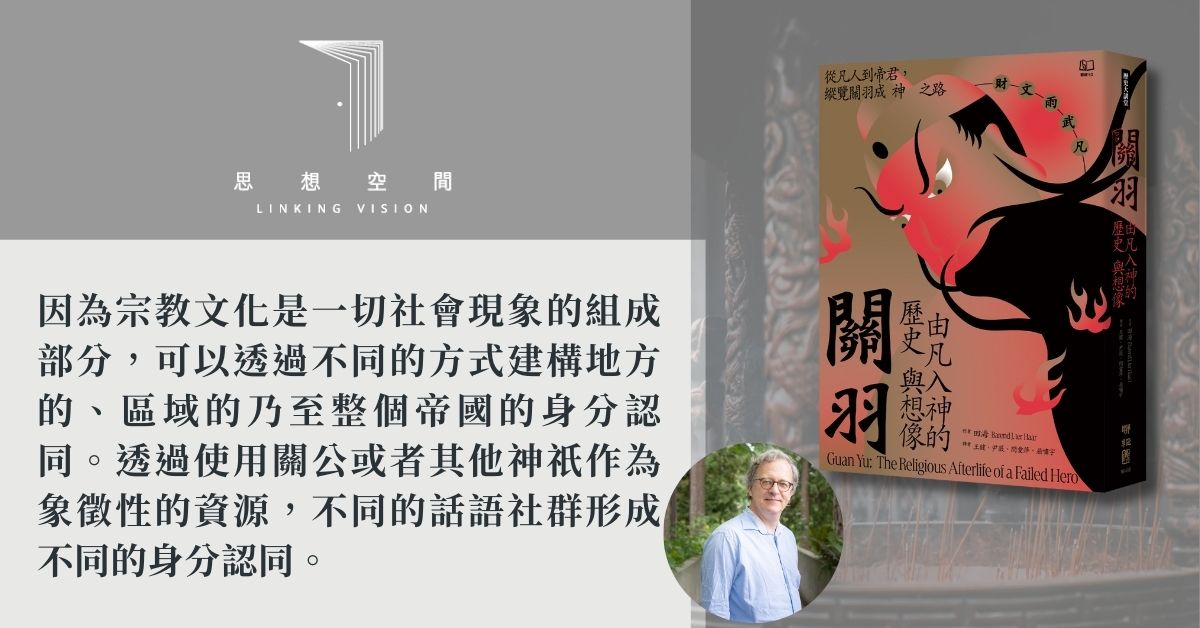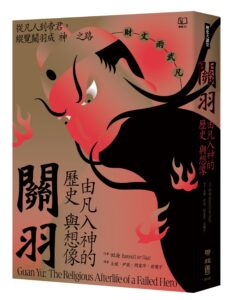文/田海(Barend J. ter Haar)
編按:本文摘自《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像》一書。
儘管我們永遠無法獲知個體對神靈最直接的體驗是怎樣的,因為這些體驗都來自口頭描述,部分甚至無法描述,但那些傳聞確實有助於我們從某些方面,在不同的層次上重構或者理解這些經驗。第一個層次是這些事件的主角和目擊者。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關於這些事件經過的最終版本,在此之前,那些主角和目擊者由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已經對最初的事件內容進行改編,這些因素包括他們此前(或此後)的經歷、其他人對他們經歷的反應,以及那些流傳更廣和神祇相關的故事。特別是到了十六世紀晚期,我們會有相當多由當事人自己記錄內容的翔實描述。只要我們充分認識到那些作者在呈現自身形象時肯定會考慮到其他人的觀感,那麼這些記載便可以視為極其有用而有趣的史料。我認為此類資料與人類學家所使用的田野訪談報告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有些史料是由那些與最初發生的事件或經歷完全無關的人所編寫的,他們和事件的主角身處不同的時空,有著完全不一樣的社會和教育背景。在這裡,和其他任何層面的重構一樣,人們在觀察與講述類似事件時,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出於規範性的考慮決定哪些部分適合講、哪些部分不適合講,再比如經過改編的神蹟故事是在怎樣的情境下被講述的等等。
但正因為我所感興趣的是人們的信仰,換句話說,也就是講述者對這些事件的看法以及他們表述人神互動的方式,所以即使是那些來自不同時空的資料仍然有其價值,它們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是人們覺得可信而有意義的。無論我們的史料是來自事件的發生地附近還是遙遠的他鄉,它們總會被重新改編,在這一過程中,文化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們幾乎無法追溯這一重構發生的過程。很多看似非常個人化的事件都有著類似的文化表達,這本身就是它們經歷改造過程的證據。
在這些被改編的故事中,我們所瞭解到的不僅是作者的個人觀點,同時也是地方社會群體的想法,這些社會群體透過血緣、業緣、地緣等不同紐帶而聯繫在一起。
在任何時代,現存的故事最終都是大大小小的社會群體集體記憶的呈現,它們經過相關文獻作者的編輯,恰巧流傳到我們手中。因此,在這些被改編的故事中,我們所瞭解到的不僅是作者的個人觀點,同時也是地方社會群體的想法,這些社會群體透過血緣、業緣、地緣等不同紐帶而聯繫在一起。真正發生了什麼並不重要,因為史料肯定會告訴我們,人們是如何進行選擇性的記憶,又是希望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將這些故事告訴後人。最後流傳下來的,是現實中人們選擇並接受與之共存的故事版本,我們可以從中瞭解到人們是如何解釋突發事件,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他們又是怎樣為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賦予意義。
在關於歷史和記憶的大量文獻中,「記憶」這個詞彙通常被用於指稱最近的歷史以及人們關於這段歷史的印象,或者也涉及國家、社會群體和個人積極建造紀念物以記住和紀念這段歷史的不同方式。對更久遠的過去來說,它並沒有太多用處,也許是因為如果太久的話,記憶就喪失自身的口頭屬性,轉變成書面文字,之後就感覺不再像是記憶了。在我看來,奇聞逸事類的文獻就是基於類似的久遠記憶而形成,它們從口耳相傳的階段開始就被不斷地重構,但這樣的重構並沒有削弱其價值。在本研究中,我並非僅僅將筆記小說中記載的個人關於神助的記憶看作史料,同時也將這些記載本身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在本書中,我們將個人的主觀體驗看作有效的研究對象。
除了在這些史料中反映出的所謂記憶外,人們還可以透過很多方式建構起關於地方廟宇的記憶文化(memory culture),甚至在國家層面上也可以做到這一點。國家授予關公很多頭銜,以紀念一些特定的事件,有趣的是,關公所擁有的一些最重要的頭銜卻是透過非官方管道獲得。尤其重要的是為了紀念一些重要的事件而立碑的傳統,比如一座寺廟的創建、修復或擴建。通常,面向參觀者的碑陽包括敘述性的碑文,以及相關的日期和落款,碑陰則列出修建所涉及的各類捐助者資訊。石碑可能會放置在一個底座上,碑上的文字會用線條框起來,也可能會在整篇文字的頂部加上龍紋或者其他紋飾。只要我們認識到一方石碑上的內容既包括對神祇的描述,同時也反映製作團體的情形,那麼一塊石碑的正反兩面都是重要的資訊來源。碑文提供廟宇修建和復建的精確日期,對於我們追溯神祇崇拜的歷史有著巨大的價值。它也許會給出對獲得神靈幫助從而修建寺廟的簡要性說明,或者之前廟宇破敗情況的資訊,但它們很少會提供關於當地信仰和地方傳說的可靠資訊,反而幾乎總是在重複關公和他的兩個結義兄弟的官方歷史敘事。儘管如此,當罕見的例外確實突破上述類型的限制時,它們可以提供關於神靈顯應助力寺廟建設的絕對有用的資訊。有時候,這些資訊甚至透過回憶的形式出現在碑文中,例如在一○八○年的一方碑記中顯示,當地士兵總結了他們前往遙遠的南方抵禦外來侵略者的痛苦經歷,以及在他們戰鬥和撤退過程中神祇顯靈護佑的事蹟。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只有當地方上有人能夠記起那些正在被紀念的實際發生的事情時,才能夠提供有價值的碑記內容,而絕大部分的當地人剛開始或許根本不知道碑記中說的是什麼。所以,碑記是可以證明廟宇重要性的第一手實物。
這些材料不保存記憶,也不是在紀念神祇的過程中直接形成的,但是它們確實反映了人們對關公神祇的感知,以及神祇對於人們的生活所具有的潛在重要性。
逸聞筆記和碑刻文獻是我使用的兩個最重要的資料來源,前者在幫助我梳理人們的記憶方面更為重要,而後者在重構神祇如何為地方社區甚至特定的個人提供支持方面扮演著更為關鍵的角色。地方志通常會使用到這兩類資訊,有時會引用碑刻正文中的部分內容,同時還會添加一些口頭故事或逸聞。我們會用到與關公崇拜相關的一些早期詩歌,以確認這一崇拜的某些發展動向,但這些詩歌所包含的意義經常是隱晦不明的,對歷史分析而言用處並不是很大。其他類型的材料是更廣泛意義上的崇拜行為的產物,比如把關羽當作驅邪將軍以對抗惡魔軍隊的儀式,以及講述在成為劉備部下之前關羽經歷的民間傳說等。這些材料不保存記憶,也不是在紀念神祇的過程中直接形成的,但是它們確實反映了人們對關公神祇的感知,以及神祇對於人們的生活所具有的潛在重要性。還有一類印刷出版的書籍,其中有神祇透過道德教化類的文字向世人發出忠告的內容。這些書籍再版時,可能會在開頭提到神祇透過夢境或者扶鸞顯應時所給予的建議。這類書籍既可以視為記憶的產物,同時也可以視為對神祇及其所給予幫助的紀念。
早在十六世紀後期,我們就可以看到人們越來越把關公視為一個識字之人,他可以透過鸞書和文字形式的預言與人溝通。關公現在演變成受過教育的男性精英所崇拜的神靈,該形象也得以在其他受教育群體中傳播開來。這一變化看似和當時人們識字能力的提高有關,但同樣也和識字能力變得越來越重要有關。在第七章中,我將探討這個問題。關公現在把自己變得足夠像一個文人,這樣文人群體才會承認祂,並且繼續崇祀祂。結果,人們就越來越關注到據說作為歷史人物的關羽所具有的閱讀《春秋左氏傳》的能力,到了十七世紀中葉,他擁有一個新的頭銜—關夫子(Master Guan),從而得以與孔子齊名—孔子是歷史上另一位著名的精通《春秋》的專家。在這一章中,關於神靈的祭祀談得很少,但是我們有大量的證據可以說明文人是如何重新塑造關公形象,同時還有很多敘事性文獻,其中記載神靈如何透過不同的形式向文人提供幫助,以及後者關於這些靈異事件的記憶。
在關公發展為文士之神的過程中,祂還逐漸具有道德監督者的角色。人們往往認定是因為崇祀者實踐正確的道德行為,關公才會給他帶來奇蹟般的保護和支持。到了人們通常把關公稱為關聖帝君(Imperial Lord Saint Guan)的十七世紀晚期,開始出現託名為關帝所著的各式各樣的宗教小冊子,這時我們看到關公崇拜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我認為這一發展的趨勢和人們可以越來越輕易地提高自己的識字能力有關,到了十八、十九世紀,這種聯繫會變得更加顯而易見。重要的是,作為道德監督者的關公仍然非常崇尚武力,大量的資料都提到那些惡人是如何受到關公的武力懲戒。長期以來,祂都被視為一位為了幫助地方民眾,勇於站出來挑戰玉帝的神祇,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進一步發展出一種信仰—人們認為他取代玉帝的位置,成了萬神殿中的最高神。第八章的主題就是討論作為道德之神的關公和那些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宗教訓諭的起源。在該章中,我們主要用到兩類文獻。其中逸聞筆記告訴我們,人們往往認為是因為道德良善,才獲得神祇關公的幫助,並呈現了人們建構的過程;而各種宗教道德類的小冊子則向我們表明,在人們的想像中,關公對於社會道德的提升做出貢獻,而為了獲得他的幫助,人們又必須做些什麼。
因為宗教文化是一切社會現象的組成部分,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建構地方的、區域的乃至整個帝國的身分認同。透過使用關公或者其他神祇作為象徵性的資源,不同的話語社群(discourse communities)形成不同的身分認同。他們之間可以透過集體崇拜(collective worship)和互相分享有關神祇的故事來交流。在華北地區,崇拜關公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地方認同的表達,因為祂首先是一位北方的神祇;但是在中國的其他地區,在城市中,祭祀關公也可以被認為是在承擔一種全國性的責任。地方社會中的農民、小店主、商人、儀式專家、軍人及文人在如何看待關公方面稍有不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重構這些差異,但通常對於這些信仰和故事的內容,我們只能作整體上的理解,而無法把它們和特定的社會與教育群體聯繫起來加以考察。整體而言,本研究一方面可以被視為對一種特定宗教崇拜的考察;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看作從社會史(social history)的角度去觀察人們的恐懼與希望、焦慮與不安,以及他們的應對之方的著作。
延伸閱讀:
| 閱讀推薦 |

【穿越時空長河】尋回「人」的精神,面向未來|許倬雲「從歷史看未來」

【穿越時空長河】鐘聲再響,回到那年課堂教室 ── 我的知識嚮導許倬雲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