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義玲(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自出版第一本著作《討海人》(一九九六)來,廖鴻基便以腳跡船痕的切身實踐展開海洋書寫。隨著海洋行旅一波一痕地擴延,從沿岸、近海、遠洋,再復返沿岸;像個海洋浪者,所搭載的船筏從鏢魚船、遠洋漁船、貨櫃船,又復返無動力舟筏的黑潮漂流,承擔臺灣海洋作家使命,廖鴻基波光水影般的書寫,以幾乎一年一本的定量出版,早為讀者的眼目擴延出一方浩瀚深海。
二〇二一年,蓄積了海潮浪湧的能量,廖鴻基再度回到寫作出發點的討海人沿岸,以靜謐之筆拍出一摺驚潮湧浪,近三十年前《討海人》的「少年家」竟再度走到我們面前,不同的是這次的主角有了確切名字:「清水」,而「清水」又將經歷一段從陸地逃亡到海洋的旅程,且被換名為「濁水」,他將在「海湧伯」帶領下,經歷一場場風浪之戰,直至鏢魚臺上與秋風旗魚的正面遭遇,死亡凶險的最深寧靜中,才能以「清水」之名回返陸地。從一九九六到二〇二一年,從「少年家」到「清水」,乃至於「濁水」,廖鴻基在海洋經驗的擴延後又回返書寫原點,《最後的海上獵人》遂如一場直球對決,襯著整個臺灣漁業的興廢歷史,廖鴻基既寫出一則令讀者驚嘆的海洋傳奇,也寫入深藏心底的一處漩渦暗流,一曲在陸地與海洋間探問自我認同之深海詠嘆調。是的,這是臺灣文學期待日久的一本地地道道海洋小說、鏢魚小說,也是廖鴻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最後的海上獵人》。
廖鴻基意圖在《最後的海上獵人》開啟的海洋視角,已是一個帶著特殊問題意識的視角:一個失敗屈辱的人還能怎樣活下來?如何面對世界與他人?
深海詠嘆調: 海有多深
詠嘆音節的發出,始自盤纏在「清水」心裡的屋頂夢與飛翔夢:是否有能力建立一個家?可否開創出一片天地?似是一個男性立足社會與面向自我的驗證題,自成長初期便被種入心底了:十三歲那年,依循著小城出人頭地的慣例,清水被父親送往大城依親就讀,但金錢的困窘,清水始終飽嘗親友及師長譏嘲;不久小城家變,清水心疼母親被欺凌卻無能返回,兼諸父子衝突,清水讓自己變成了一隻縮回內心巢穴的刺蝟。而後少年清水長大了,有鑑於成長經驗,他迅速地掌握了大城市遊戲規則,與閒雜事務保持距離,只一逕埋頭耕耘自己,至覓得安穩工作、娶妻生子買房買車,一路過關斬將終於攀上屋脊;也未料一個錯誤判斷誤入投資圈套,緊接著破產、失去工作,被追債、離婚、喪失兒子撫養權,飛翔墜落一路逃亡,直至島嶼邊陲角落:邊角漁港。那是陸地盡頭了。
從屋頂夢與飛翔夢看清水生命願望的實現與破滅,作為一部長篇小說,我們會發現廖鴻基意圖在《最後的海上獵人》開啟的海洋視角,已是一個帶著特殊問題意識的視角:一個失敗屈辱的人還能怎樣活下來?如何面對世界與他人?可以獲得有尊嚴的自己嗎?當三十出頭的清水在「邊角漁港」蹲下身來,膽怯地向「海湧伯」詢問可否收留自己當學徒?眼前漫漫大海,如此心虛迷茫的探問,海洋才為清水,也為讀者開啟了大門。
飛翔墜落的眼前,如何面對他人評價?或更根本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失敗?可能重新站起來嗎?
「這條路怎麼忽然就走到底了」
事實上,「屋頂夢」與「飛翔夢」作為立足社會的關卡,不僅是清水一個人的考題,也是普遍性的現代人生存課題。小說中,清水的問題也及於另兩位男性:粗勇仔與海湧伯。粗勇仔原是水泥工,因天性稟賦需求更大舞臺,在海湧伯調教下成為一位優異的海上獵人,其傲人的鏢魚成績也讓他獲得佳人愛情且共組家庭。卻在一次追獵大尾旗魚過程中,因為搞怪旗魚使詐糾纏,被海湧伯揮刀斷繩,命保住了,但一個踉蹌腳跛了生命也跛了,從此身體銘刻著失敗者印記,黯然回返陸地。
而海湧伯呢,這位從《討海人》時期便出現在廖鴻基筆下,對海洋有著深刻體悟,且能引領學徒討海技藝與開啟智慧的老討海人,即便曾有過多麼風光的漁獵往事,但一輩子於大海耕耘的結果,便是與親人漸漸疏離,更兼漁業蕭條收入不豐,早已成為陸地家人的陌生人了;而至砍傷親手調教的學徒粗勇仔的腳筋,深刻的內疚更引致自我懷疑,喪失了海腳,何止陸路,連海路都迷霧茫茫了:「這條路怎麼忽然就走到底了。」
從三位男性的現實遭遇來看,他們都曾經懷抱堅定的屋頂與飛翔夢,努力奮發以掙得立足之地;也未料竟有一天,會被原以為能牢牢掌握勝券的人生戰役出局。襯著時間驚濤拍岸不斷,廖鴻基以深入暗流漩渦之筆,寫出擱淺於海陸間的清水、粗勇仔、海湧伯三人的幽暗心事:
「人的世界裡,是否真的有個地方,是真正的邊陲角落?是否真的有個地方,允許潛藏、逃避和重新開始?」
「這場傷後,即使想要繼續討海,恐怕也站不住鏢臺了。」
「是否甘願承認被一條大尾旗魚給打敗了?」
飛翔墜落的眼前,如何面對他人評價?或更根本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失敗?可能重新站起來嗎?生存的危機啟動敘事視角的轉換,小說第二篇,清水踏入海湧伯鏢船,且被粗勇仔譏嘲換名為濁水,然那重新啟程的討海人行旅,可能終結陸地的逃亡?
討海人的生活場域是海洋,迥異於陸地生活的安穩與規律,當船舶航入大海,在風速與流向的時刻變化中,已蘊含了與陸地生活相對的戰鬥之意。
「當我想起鏢旗魚, 我會覺得榮耀」
從窮途末路再往前一躍,濁水的討海之路,是一條怎樣的路?討海人的生活場域是海洋,迥異於陸地生活的安穩與規律,當船舶航入大海,在風速與流向的時刻變化中,已蘊含了與陸地生活相對的戰鬥之意。如小說寫道濁水初入海上,一次次暈船、嘔吐,從苦澀膽汁再到和著腸胃黏液與鼻水淚水的乾嘔,更兼體力透支與晨昏顛倒,已至身體受苦的極限;此外,濁水必須有能力從巨浪、漩渦與險溝的不測海流中發現漁場、尋找魚隻;而當濁水站穩顛晃甲板,且能平衡隨浪而來的左右側翻與上下俯仰時,海湧伯更要他自己找到方法,從那僅有兩只腳套牽連人與船隻的鏢頭站立起來;不僅如此,大海航之不盡,濁水得磨練聽海與看海本事;最後,濁水得從眼前可見的大海,航入與自己生命相應的那一方心海,看到其中的恐懼亂流:可還有機會擁抱日思夜夢的兒子?
何止濁水,《最後的海上獵人》的其他人物也在面對著內心煎熬:粗勇仔雖跛腳了,但返回陸地的他重操水泥舊業,且因緣際會地搭上時代需求,以所累積的海洋經驗與人脈,做起了海洋造景工程,事業發展順利,甚至開了公司。看似圓滿的結局,卻是回應生命困局的開始:既是一位天生的海上獵人,當北風吹起,他身上的鏢手靈魂便甦醒了,輾轉反側坐立難安;更重要的是,他心上有一塊移不走的大石頭,粗勇仔一再一再地對妻子芬怡請求讓他踏上鏢船:
這樣說好了,我過去是鏢手,是鏢旗魚的海上獵人,我一直有這種感覺,簡單說,如果沒有下海去完成剩下的那百分之五,即使岸上發展有再大的成就,我的生命還是會有缺憾。
會有那麼一天,我不會半夜醒來因為鏢旗魚這件事而睡不著;將會有那麼一天,我不會眼睛閉起來,就看見那條害我被砍斷腳筋的大尾旗魚,有一天,我再也不會聽見海上淒涼的呼呼風聲;有一天,當我想起鏢旗魚,我會覺得榮耀,並且自然而然地就會抬頭挺胸。
除非直面那個被打敗且黯然而逃的片刻,且為它再戰一回,否則即使再有岸上成就,也不覺光榮。但問題是粗勇仔跛了,上不了鏢臺,妻子也不允許他再到海上去征戰冒險了,他能怎麼辦?
而海湧伯的煎熬更被烙上了時代印記。作為一位以海為家的老討海人,他眼下已是一個魚不來、船閒著、人走了的漁獵荒落時代,當身旁漁人紛紛轉去和漁業公司合作,利用先進技術輕鬆捕獲大量魚隻,甚至讓鏢手改鏢容易上手的翻車魚獲利時,他卻仍堅持每年組合鏢船獵人,與丁挽旗魚在秋風大海上正面遭遇,而被其他漁人譏為不知變通的「老孤獨」。時代變遷讓海湧伯處境難堪:如何面對漁獲的枯竭,乃至自己理想的終場?當人生的信念已成為他人笑資,還有堅持的必要嗎?他是一位船長,但是否還有能力聚攏海腳出航,在翻騰大海出鏢,為自己搏回生存的光榮感?
所有的問題,都等待解答,也只能在行動中解答。
作為一本地地道道的臺灣鏢魚小說,我們看到了廖鴻基如何以「鏢魚」,這最原始的海上漁獵引領讀者的心思進行最後一搏。
逃亡的、跛的、孤獨的人啊
是以當北風吹起,旗魚季開鑼,三人各自從內心的擱淺暗路出發,來到海湧伯的老鏢船「展福號」,搭上第一波漁季的流水,往雜沓俯仰的浪濤航去,便如一場回應命運的大戲了。而決定這場命運大戲的便是三位獵人必須「遇到一條分量足以改變他們的命運,足以改變他們生命光榮感的旗魚」,若有機會遇見,他們便要迎上前去展開一場生死拉拔的賽局。只因不管三人此刻現實境遇為何,或黯淡或光彩,都有一些絕不能放棄、絕不可讓渡的尊嚴之物,而他們尚未獲得。
為了尋著那條高貴的白肉旗魚,漁季才開鑼,老中青三代組合的獵人比其他漁人更辛勤地出航,專注地往浮漾海面搜尋、安靜等候,但這卻是他們一起面對更嚴苛海洋考驗的開始:即使辛勤出航,但漁季頭一個月只鏢獲一尾雨傘旗魚,連油錢都不夠,引來漁人們訕笑紛紛,但他們得從譏嘲中再度出航;最致命的是漁季的第二個月中段,三人一整天搜尋後,好不容易天光西斜時看到一隻丁挽武士,卻在攻擊節奏響起的高峰崖邊,一個引擎咳嗽船隻顛躓,熄火了。兩年來的蟄伏與等待就這麼隨著船隻摔落浪丘谷底。更糟糕的是,展福號失去動力,海湧伯必須和漁人朋友開口求援;而向來不贊成粗勇仔出航的妻子正焦急地等在岸邊;致命錯誤的造成,又源於努力想要證明自己、重新爬起來的濁水前此的一個船隻保養疏忽。逃亡的、跛的、孤獨的人啊,被打回原形,一切回到挫敗與羞辱的原點,甚且是更破碎的原點。漁季時間點滴流逝,船壞了待修,三人再次面對了茫然的前路,努力是無望的:「何必苦苦堅持?」
正是在這破碎原點、生存的最虛無時刻,作為一本地地道道的臺灣鏢魚小說,我們看到了廖鴻基如何以「鏢魚」,這最原始的海上漁獵引領讀者的心思進行最後一搏。小說後段,當海湧伯看到自覺羞愧的濁水收拾行囊準備離開展福號,只一個警鐘般的提醒:
一走了之,就像是順風逃跑,告訴你一件事,知道嗎,幾乎每次鏢中的旗魚,都是在順風逃跑時露出破綻,而那種時常逆風正向游的旗魚,鏢船往往連接近都很困難。
海湧伯不僅看到濁水的羞愧,更直接看入他內心陰暗、性格中的逃亡本質,以鏢魚經驗,也同時是人生體驗告訴濁水:「這樣子離開,會帶一輩子內傷。」更在濁水開不了口的心虛上回應:「知道沒臉,就重新作一張臉啊。」「當退無可退,就勇敢面對吧。」像師傅,也像父親,斥責之外,還是一種激勵,更是一種寬諒與再接受了;而落難返家後的粗勇仔也是一樣的,即使錯不在己,但若要重返鏢船,他也必須去獲得妻子更大的諒解與支持。
我想那正是《最後的海上獵人》最為生動的「鏢魚」現場:鏢魚所以是一種最原始漁獵,在於它是發生在海上的,一場人與魚之間的糾纏、競技與生死拉拔的賽局。除非船上每個獵人都能撐住自己,且調動全幅之力通過各種阻撓、獲得支持,才能讓這場鏢魚活動發生且延續下來——不正是一場生存戰鬥?是以即便眼下漁季只剩一半,領獎無望了,三人仍必須從所有的不可能處境出發,去赴一場鏢魚之約,因為生命的尊嚴就在那大海上。小說最末一幕,三人乘著展福號再度出航,終於在漁季結束前的五天,他們遇著了,竟是前年那隻讓粗勇仔與海湧伯摔落谷底的搞怪大魚。
北風凜凜、浪濤翻湧,狀況在瞬間變化著,一片肅殺氣氛裡,三人正無言地與那大魚,與自身的命運拉拔著。
才真正地終結逃亡了。
海濤拍岸水霧撲揚,每個人都在恐懼且逃避著飛翔墜落的路上,也都在那不小心從屋脊跌落的瞬間,問著:是否有機會站起來?是否還能重獲生命的光榮?
最後的海上獵人, 一頁漁業興廢變遷史
從開卷到終篇,我們彷彿跟著廖鴻基的帶領,走了一趟從陸地到海洋的旅程,且在「邊角海港」,那窮途末路的命運現場,看到惶惶交錯的人影:有人一路逃亡至無路可走、有人從海上鏢臺踉蹌跌落陸地、有人將船舶孤獨停靠漁港去處茫然。海濤拍岸水霧撲揚,每個人都在恐懼且逃避著飛翔墜落的路上,也都在那不小心從屋脊跌落的瞬間,問著:是否有機會站起來?是否還能重獲生命的光榮?
《最後的海上獵人》中,當三人從所有不可能的處境出發,一起往那北風獵獵的大海展開一場直面恐懼的鏢魚之戰,獵人與獵物的正面遭遇,生命意志的高舉昂揚,海洋,作為承載命運大戲的舞臺,早以其翻湧不息的本質,為所有走到逃亡之路的人們,做了「出路」的回答。
因為出路的答案就在那方翻湧大海中,是以當海湧伯對濁水追憶昔日邊角漁港的鏢魚盛況時,我們會與清水/濁水一同驚訝:何以不過四十年,那曾經興盛繁華的漁業光景,會淪落至今日的蕭條黯淡?從這裡看《最後的海上獵人》的書名,將發現廖鴻基寫作此書的另一重要意圖:為那即將消失、正在消失的鏢魚文化留下紀錄,寫出那一頁臺灣近代傳統漁業的興廢變遷史。因為現實生活中,廖鴻基便是一位曾經在老船長帶領下,參與鏢魚之戰的「最後的海上獵人」。是以一如小說中的清水/濁水必須回返陸地重新開始,在臺灣社會快速朝向現代化的轉型發展中,立基於那魚不來、船閒著、人走了的黯淡漁場,二〇二一年的廖鴻基更要以《最後的海上獵人》再次引領讀者回到沿海,且站上了那北風獵獵的無人鏢魚臺,自那生命深沉的大海,人生的逃亡路上,進行了一場記憶回返的搏鬥——看哪,展福號折身衝下波谷,海湧伯一聲喝喊,出鏢,大尾旗魚一個驚顫扭擺,一坨巨大水花綻開海面⋯⋯。
(本文摘錄自廖鴻基《最後的海上獵人》推薦序)
延伸閱讀:
廖鴻基:致沒有海明威與德布西的台灣海
| 新書速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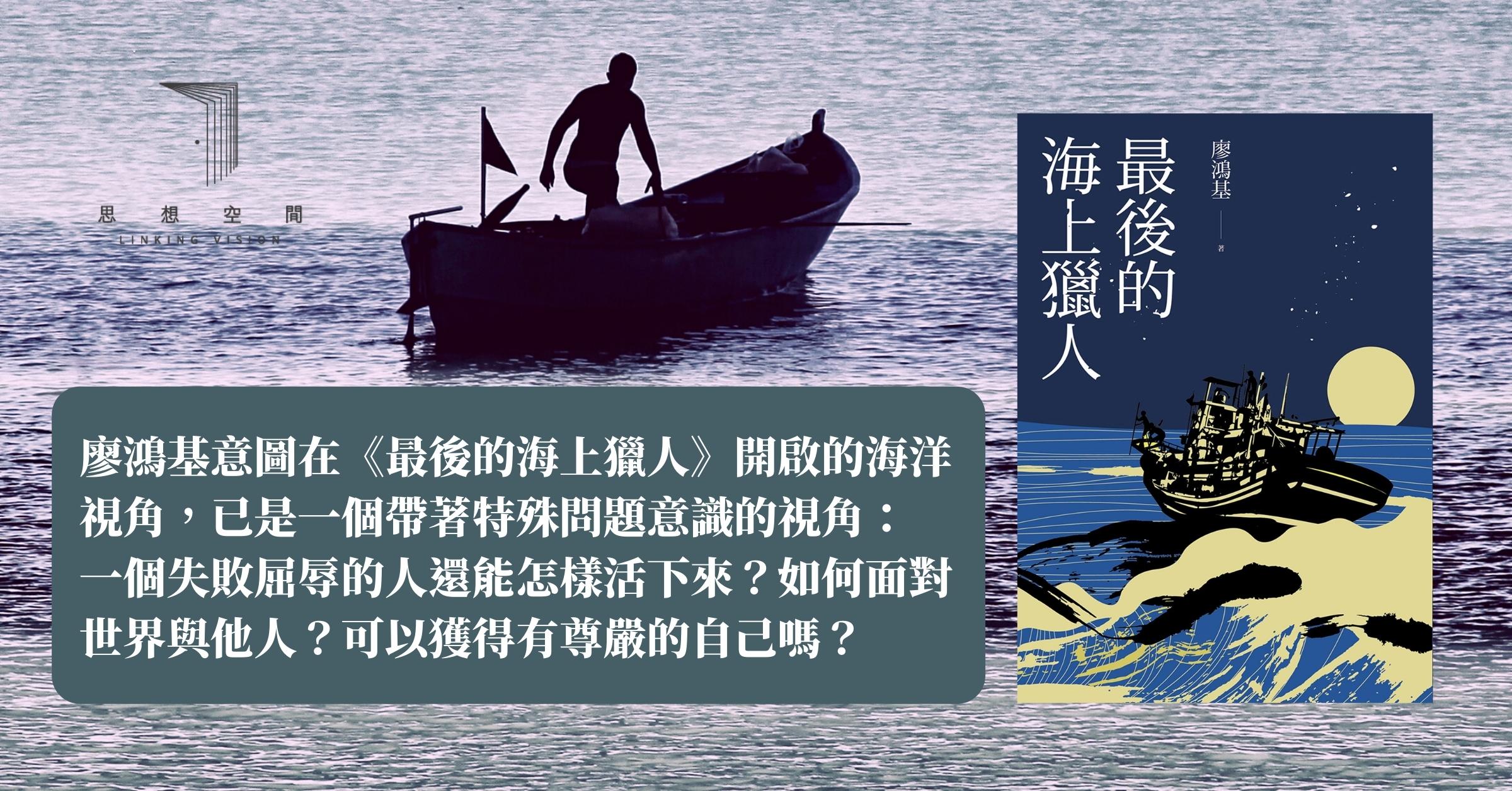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