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1年12月26日,著名歷史學家、中國史學者、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於康乃狄克州家中逝世,享年85歲。史景遷一生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天安門》、《胡若望的疑問》、《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曹寅與康熙》等。1999年,《聯合報》曾促成「東西史學大師跨世紀對談」,邀請余英時與史景遷以1898至1989世紀交替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為題,分別以東、西方視角來探討一百年來中國歷史與文化之路。2021年,史學界痛失兩位重要學者,而他們的學術貢獻卻會長存於世;思想空間也在此與讀者們一同深沉悼念,並回顧兩位珍貴的思想交鋒。
本文轉載自《聯合報》1999年1月7日-1999年1月8日專訪聯載。
余英時(以下簡稱余):過去一百年來,中國多集中於研究西方的科技中國。而史景遷教授數十年來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治學範圍從16世紀到現代中國,都有深入的研究,並出版多本有關中國文化歷史的書籍如《康熙自畫像》、《王氏之死》及《近代中國之追尋》等,極受西方社會歡迎。你的研究及筆下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印象,頗值得我們參考。現在就請你就今天對談的話題「1898年至1989年世紀交替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先起個頭。
史景遷(以下簡稱史):1898年的戊戌變法可以是一個有趣的開始,中國內地及美國的學者都對戊戌變法十分感興趣,耶魯大學最近還特別舉辦了一次研討會。在一股1898年的研究風潮中,西方史學研究者也開始重新思考中國歷史事件,不只是看到戊戌變法的失敗或清朝的滅亡,而開始研究自晚清起中國實際已開始推動的政治結構改革。
20世紀初年,清政府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支持下,開始推動改革,每個省都有類似西方民主的諮議局及有限的地方選舉,其改革的幅度不深亦不廣,因為教育並不普及,但畢竟是一個重要的始點,這個地方選舉的活動,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1913年,中國知識分子甚至比西方人還早就開始討論在議會中選出女性代表的可能性。
清朝當權派的抗拒,是當時改革難以成功的主因。根據西方學者羅傑 · 湯普遜研究中國改革的一個成功個案是,晚清的山西省成功地建立了地方議會(諮議局),並積極從事公共衛生、地下水道及警察制度等建立,這是中國地方士紳明顯脫離中央控制的一個鮮活實例。繼之,不少會館及同鄉會等傳統組織亦各自設立其公共衛生制度。儒家士大夫似乎不願接受一切由中央規劃的統一體制。
而1906年至1914年(編者:按袁世凱稱帝)的這段時期,更有一些正面的發展值得歷史學家好好研究。1912年的全國國會選舉是一個令人鼓舞的進展,但是積極推動建立國民黨組織化及政黨制度的宋教仁卻不幸被人暗殺,其因並未被清楚了解,但與當時國民黨有意限制行政力量、增加立法及司法權力,及有人認為與宋教仁太有野心都有關係。但宋的被暗殺更反映政黨間緊張關係及政府和國會如何共存的問題。

史景遷:「因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及凡爾賽和約引發的五四事件,產生的反日情緒應只是突發事件。五四運動的圖像相當複雜,我們對五四的剖析,不應只強調單一因子。」
袁世凱其實是中國民族主義者
史:另外,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鄧小平思想」這個詞語,是不是也可說有一個「袁世凱思想」?美國學者Ernst Young曾研究袁世凱,並著書稱袁其實是一位「中國民族主義者」,只是,他主張中央化的政府並非正確的方向,他在軍事上及政治上建立一己的抉擇。但袁世凱也自有他一套想法。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中國知識分子是,戊戌變法中的譚嗣同。過去學者研究的對像多為康有為兄弟、梁啟超,其實,譚嗣同是一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在宣揚中國民族主義的同時,把佛教的觀念納入中國價值體系;他注重佛教,並且要求政治改革。
余:談到這裡,我們已經觸及近代中國變革的兩種類型。清末到民初的立憲運動,代表由下而上的逐漸改革;譚嗣同則可列入「革命型」了,他有「革命非流血遍地不可」的說法。譚嗣同是中國近代史上激進主義的先鋒,他在戊戌變法時選擇死亡做一位烈士,其激進思想不只反映他的反清,還與其個人家庭有關:其後母給予他的痛苦,使他對儒家的價值體系進行廣泛的批判。他主張打倒三綱五常,而成為中國近代革命的原型。
譚嗣同自中國傳統中吸收許多非儒家思想——如佛家的慈悲,他的著作《仁學》中的「仁」,即包括了佛教的仁慈,而不只限於儒教的仁。他用「以太」釋仁。梁啟超曾說,譚嗣同早年不知有周公孔子,這種說法不一定正確,但譚的確吸收不少非儒家的思想。
去年2月,我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上發表文章,明白地對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做一類比。在明末,國家面臨危機時,朱家皇室是相當孤立的,沒有什麼支持的力量。但清末除了愛新覺羅皇室外,還有五百萬滿族的八旗等制度在支持它,因此,除了遇到危機,知識分子面臨的是「保清」還是「保中國」的矛盾,這個滿族便類似現代的「黨組織」。
我們要了解清末,就應好好研究慈禧太后,不應把她視為邪惡之人。她行政能力及學習能力都相當強,早在咸豐去世前,就學會如何處理政事。
史學家孟森曾說,從朋友在火車上親眼見聞,慈禧拿筷子,光緒才拿起筷子;慈禧放下筷子,光緒也立刻放下筷子。並據朝鮮實錄中的記載,乾隆退位後,他與嘉慶的關係和慈禧與光緒一樣。乾隆笑,嘉慶才笑,乾隆生氣,嘉慶也跟著生氣。這是太上皇與兒皇帝之間的關係,先後如出一轍。
現在我想請問史教授一個問題,在1911年至1912年的南北和議後,孫中山先生退位,袁世凱出任總統,當地也有人對中國的前途感到相當樂觀,他們欣喜中國可以就此轉變為現代的中國,不需再流更多的血。你對此的看法如何?
史:這個問題相當複雜。我們或可藉幾位知識分子來觀察此一問題,梁啟超和林長民(梁的長媳林徽因之父),他們在這段時期都曾表明對中國未感絕望,但是曾在日本住過許久的梁啟超及在倫敦、紐約都待過的林長民,他們都是具有國際觀的知識分子,究竟會如何看待一個國家元首用暗殺除去最大政黨的政敵,如此國家還有共和政體可言嗎?他們會覺得這個政體有希望嗎?
袁世凱死後的大事件是五四運動,我們談談五四吧。若從1910年往下看,五四運動的意義其實並未如一般人所說的這麼重要。塑造五四運動的因子很多,五四只是歷史演進的一個結果。現在許多學者研究五四都一再往前追溯,有至12年左右的年輕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我們暫且忘卻他後來是一位共產主義的信徒,在他參與的由章士釗創辦的《甲寅》雜誌中,就可發現許多中國年輕知識分子試圖了解中國所處的環境,他們在思想及心靈上的奮鬥多是發生在留學日本期間。另外,日本用漢語鑄造有關現代事務的漢語詞彙,更對中國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因此,從長期的觀點來看,因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及凡爾賽和約引發的五四事件,產生的反日情緒應只是突發事件。五四運動的圖像相當複雜,我們對五四的剖析,不應只強調單一因子。
我年輕時有幸跟隨房兆楹研究胡適。胡適所做的紅學研究,著實令我感到敬佩,他是一位史學分析家,卻能認真地將中國傳統文學與滿洲文化做一完美的連接,可見胡適在五四運動中的反傳統主張只是他的思想的一部分。
五四運動與反傳統說法的掛鉤,其實與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及與五四的淵源有關。但這對五四運動及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都不一定很恰當。
余英時:「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就像共產革命前夕的俄國知識分子,整天在變。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大動蕩的時代為自己關心的問題尋找出路的足跡。」
毛崇拜胡適注意問題少談主義
余:1994年,在蔣經國基金會的讚助下,學界曾在捷克布拉格舉辦五四研討會。
史:這是說蔣經國基金會有意助捷克重振漢學傳統?
余:是的。那個研討會的目的在重新檢視五四運動。我曾為文主張五四「既非文藝復興也非啟蒙運動」。五四運動可以自不同觀點來理解。
若自國內的觀點來研究「五四」,魯迅就比胡適更重要,陳獨秀也是一個重要人物。胡適只能算是右翼。胡適在五四時代最佩服的學者是王國維,1926年他在英國演講時也提到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也應說是五四成果的一部分。
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就像共產革命前夕的俄國知識分子,整天在變。有人指出,當時俄國知識分子早上是自由主義者,中午是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者,一會兒又變成斯拉夫民族主義者。陳獨秀最早崇拜的是俾斯麥統治的德國,後來又崇拜美國的杜威,最後變成共產主義的信徒。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大動蕩的時代為自己關心的問題尋找出路的足跡。
史:毛澤東也是。
余:對的,毛澤東原本最崇拜的是胡適,在胡適與李大釗就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辯論中,毛是站在胡的這邊,認為應注意問題少談主義;而國內史學家卻說毛站在李這邊,最近中國大陸的學者已指出此一錯誤。80年代「開放」以來,一些大陸學者——如李澤厚更認為若戊戌政變能夠成功,中國可以避免日後的所有革命。這似乎顯示五四思想已走完了的第一個循環,又回到戊戌維新前後的改良主義軌道上來了。
大陸知識分子已自激進主義轉變為漸進的改革者,即使在美的人士亦極少提倡「革命」。如史學家王賡武發表的一篇英文文章所說,現在中國的問題是如何去「改革革命」(To reform a revolution)。
史景遷:「因清廷法律禁止大規模集會,中國基督徒便改為小型祈禱會,並將此聚會的觀念轉移到其他用途上。」
基督教傳入近代中國又多了一個國際觀
史:另一個對近代中國有相當大影響的因素是基督教新教的傳入。晚清在福建地區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如福建諮議局代表中有相當多的基督徒,經由基督教建立起的人際網絡,成為繼中國過去傳統同鄉、同族及師生關係後,一個新的個人政治勢力網絡。
近代中國在新起的中國民族主義、地方主義外,又多了一項基督徒的國際觀。當清末改革失敗後,清廷決定限制地方自治的進度,積極自治的省份都極力抗拒,不願將諮議局的角色限於顧問機構。其中排拒最早及反應最為激烈的要屬福建諮議局。
清朝的基督徒經由西方教會,學會傳統中國人缺少的團體討論及公開辯論的技巧,訓練年輕人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成立聚會所,有組織地在公開場所唱歌,從聖歌到愛國歌曲,日後更學會舉旗、遊行等活動與觀念。
基督教的儀式就在這種大規模活動中進行,但因清廷法律禁止大規模集會,中國基督徒便改為小型祈禱會,並將此聚會的觀念轉移到其他用途上。基督教的傳入與臨海的福建和東南亞各地因商務往來有著密切關係。活躍在東南亞的福建生意人,將海外生機活潑的社會訊息帶回中國,他們因為在東南亞及香港的外國帝國殖民地致富,這些經驗使他們認真思考法律及憲政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是近十年來台灣及香港多所辯論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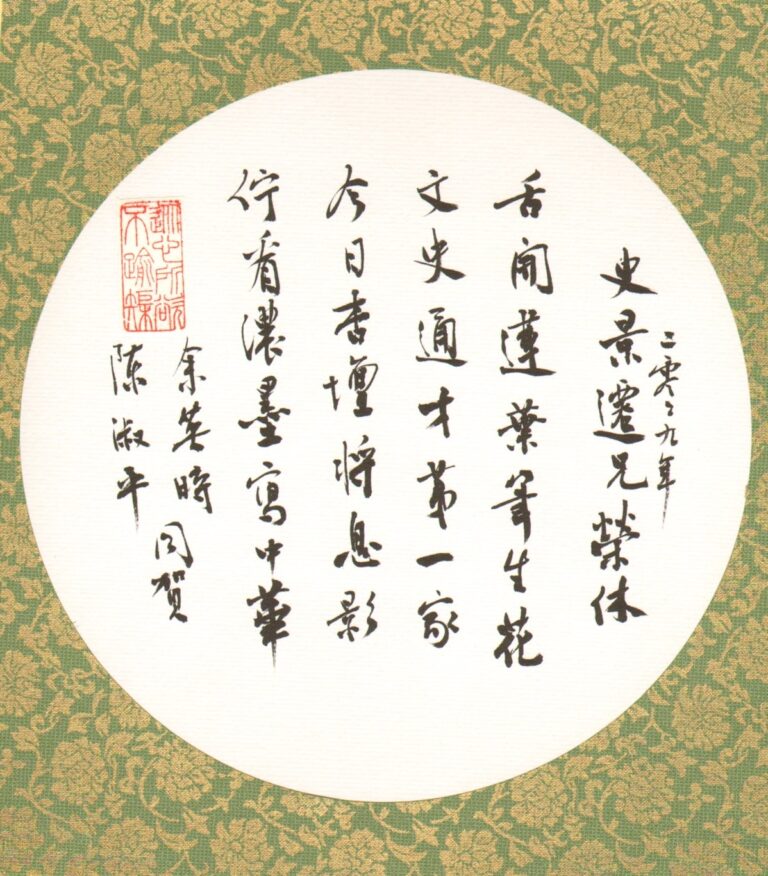
反纏足倡導:清末基督教對社會的重大影響
余:除去史教授對利瑪竇和洪秀全「上帝的中國兒子」所做的研究外,在戊戌變法前後傳教士對中國社會的批評也很重要。基督教影響中國一般知識分子的實例,有上海的西方傳教士如傅蘭雅對譚嗣同的思想影響,他們與基督教接觸而了解世界知識。王國維曾作過分析。清末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最重要的一個影響,要屬在反纏足的宣導上。從譚嗣同到胡適都接受了這一批評。
胡適一再說過,若非外國傳教士指出纏足的殘酷,一般中國人對纏足還是熟識無睹。俞正燮曾寫過關於纏足的史實,我最近在陳亮文集中發現有「女人束腰縛足」的說法。可見南宋已成風氣。今天西方學者批評中國文化不重「人權」仍多引「纏足」為例。更有人以此攻擊宋明理學家。理學家沒有對此抗議過,誠如胡適所指出的。但我又在元朝筆記中發現,二程的後代婦女在元代都不纏足的記載。這一點也很值得注意。
史:其實,在基督教反對纏足外,中國社會內部也有批評之聲,如小說《鏡花緣》中的描述。
余:但是,西方傳教士批評纏足似乎很早,我們今日難以論斷《鏡花緣》這本小說的作者,是否受到基督教觀念的影響。信仰基督教的宗教史家陳垣,似乎認為明清基督教對中國人的思想影響,要比一般的認識為深遠。
史:我記得清朝的滿洲人曾於1645年禁止中國人纏足一年。
余:從知識分子的思想易受海外傳入基督教的影響。這一點可以引申到地區性是另一個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因素。
史:此一地域性的差別在清末民初尤為明顯。毛澤東年輕時極為崇拜曾國藩,其理念實難與他後來的共產主義思想相配,只是毛澤東和曾國藩同為湖南人。
余:以福建地區而言,我想到洪業(煨蓮)先生,他是福州人,一位深受儒家重要價值影響的中國學者,但同時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洪業是一位民族意識很深的知識分子,他贊成孫中山革命,反對清朝的專制,他又崇拜西方文化,參與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和司徒雷登一起創辦燕京大學。還有林語堂,他出身牧師家庭,最後也皈依了基督教,但他在西方宣傳中國文化,影響不小。
史:浙江也有一批獨立性很高的知識分子,如蔡元培、秋瑾、徐錫麟。
余:浙江知識分子在清末民初的活躍狀況,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中記載最詳。廣東也有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不少活躍的知識分子。但我們似乎無法在北方知識分子中找到具有地方特色的社群。也許因為北京是首都,知識分子來自各地。清末提倡北方顏李學派也始於南方學者,如戴望。
而位於內陸的湖南,則有一群保守勢力強大的知識分子如葉德輝、王先謙,公開反對梁啟超。雖然,在戊戌變法前,光緒是因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在湖南推行新政成功才支持改革。
余英時:「沉睡的中國意謂著中國退出歷史的潮流之外。這一觀點在中國也曾流行過,甚至受儒學影響很深的人,也說中國自宋以後只有故事,沒有歷史了。」
另一歷史支流對中國文化正面書寫
史:談及基督教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我們不可忽視一股歷史支流是,基督教對中國文化做負面的書寫。
一位在西方十分有名的史學家明恩溥Arthur Smith,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國人的性格》,強有力地宣揚基督福音,卻十分看不起中國,該書批評中國人的特性與魯迅《阿Q正傳》中對中國人的描述是極為相似。1905年日俄戰爭後,不少西方學者如明恩溥等的著作,都有日文翻譯,不久再轉譯為中文;魯迅等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批判是否受到他們的影響?此例顯示當時文化環境的複雜性。
余:我想請教你,在16、17及18世紀間西方傳教士的著作中,究竟有多少對中國持批評的態度,有多少是稱許中國的?
史:雖然耶穌會教士的著作中提及中國的暴力、多妻制等缺失,但17世紀中葉前,他們大多對中國充滿了誇讚。即使是反對耶穌會的道明會及方濟會,也對中國多所稱許。在現代史學家眼中,有諸多明顯缺失的明朝,在當時天主教神父的描述中卻是一個強大的政府。
外國傳教士對中國的宗教亦特別感興趣,他們嘗試把佛、道教和儒家分開論述,認為佛教與道教是偶像崇拜,儒家能和柏拉圖哲學及基督教、猶太教的傳統一神論思想相聯結。
整體來說,西方人喜愛、崇拜中國文化卻不了解它,尤其是中國的音樂。
18世紀,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雖利用耶穌會教士的書籍稱許中國,其目的卻在批評法國教會。此時,西方世界反中國的氣氛已佔上風。一本著名的小說《魯賓遜漂流記續集》就是明顯的例子。
《魯賓遜漂流記續集》是《魯賓遜漂流記》在市場上暢銷後,應書商要求再寫續集。這回魯賓遜一漂就漂到中國,書中對中國字、中國學術、中國建築、食品、文化及中國人的儀態,都有嚴厲的批評。為何該書作者選擇以批判的態度撰寫他的小說?
這與市場需求有極大的關係,自1715年起,英國的出版商判定反中國的基調會是暢銷書,同時,法國也出現反中國的歷史小說。而造成西方社會對中國產生負面印象的因素有英法當時積極推動和中國的商務關係,但是仍打不開中國的門戶,外交官及商人均備感挫折。
余:乾隆時期英國派來的使節馬卡特尼(Haiiiday MaCartney)在返國後,有何影響?
史:以西方近代的勝利眼光,撰寫對極其輕蔑中國的文章和書籍,認為中國一定要自我改善,否則會在歷史中消失。這就是幾十年後黑格爾的觀點。
余:另外,在史教授新作《可汗的大陸》一書中,指出德國思想家赫爾德(Herder)對中國也有很負面的批評,這讓我感到相當訝異,我以為他是一個以平等眼光看待多元文化的學者,他批評中國的觀點來源何在?
史:商務報告。另一本影響西方人看中國的奇怪書籍是,英國第一位高階海軍軍官Anson撰寫的。他指揮的船艦在中國廣東靠岸,他依國際法要求中國提供給他需要的補給,卻為中國人悍然拒絕。他回到英國後著書對中國極盡嘲諷之能事,廣為當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閱讀。
而另一個西方人對中國負面形象的相關說法是,赫德爾書中提到的沉睡的中國。
余:沉睡的中國意謂著中國退出歷史的潮流之外。這一觀點在中國也曾流行過,甚至受儒學影響很深的人,也說中國自宋以後只有故事,沒有歷史了。80年代大陸上青年知識分子常說中國的「被開除球籍」,也是同一思路。
史景遷:「我不覺得各文化間有明顯的衝突,中國與西方文化有很多複雜的交錯點。利瑪竇對中國文化並未完全理解,卻十分重視……」
先崇拜後批評西方知識分子對中國觀反覆
余:現在我想將問題拉回至近代來討論,何以西方知識分子近來又開始崇拜中國,尤其從1970年代大陸初「開放」的時期。但90年代後又出現了負面的批評,被大陸上說成「妖魔化中國」。你又如何形容這種改變?
史:這是一個逐漸清醒、幻想破滅的過程。美國人需要花長時間去消化分析他拿到的資料。
余:可否讓我們把討論的焦點縮小集中在費正清?他是美國最有影響的學者,他的觀點常有改變,1940年前他十分同情中國共產黨,數十年後又有轉變。我覺得很難對他的主張做一綜合性的論述。你的看法如何?
史:費正清是我老師的老師。他的觀點足以改變一般美國人的看法。他支持中國學者、促成中美學者的交換計劃,並對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形成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二次大戰間的動亂時代中,每個人都有朋友住在重慶、延安、上海、北平,甚至香港、美國,任何人都難以對中國事務有正確的報導,全視哪位朋友誰對他影響大。在那段時間,西方人對重慶政權多持有負面的印象,李約瑟是造成這種印象的一位學者。而延安則有意識地營造好印象。這讓研究近代史的歷史家對新資料的開放及出現都抱持懷疑態度,以免被人操縱。
余:回到基督教在中國影響的問題,我想就最近亨廷頓的「民主的第三波」和「文明衝突」的觀點,請教你關於基督教在中國的整體影響的問題。
史:是的。基督教帶入中國的大型聚會觀念,對中國的政治及社會會發生一定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史中,基督教新教對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其在宗教上的力量,與其教友人數完全不成比例。傳教士李提摩太就大大地影響中國的自強運動。他們強調的教育,正是中國最需要的。
基督教對國民政府有絕對的影響,而共產黨的成員中不少是基督教青年會的會員,他們自社會服務中習得公共體系的概念。
余:據杭亨廷說,基督教與韓國的民主化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那麼基督教在台灣地區是否有如此的影響力?實際上,就我所見,台灣民主化與基督教的關係似乎不如亨氏所說的那樣密切。這讓我們歷史學者覺得很難理解亨廷頓「第三波」和「文明衝突」中提及基督教、伊斯蘭教及儒教間的衝突,你是否覺得世界各不同文化間的確存在著所謂的「衝突」?我們如何自近代中國文化與西方間產生衝突的角度,來解讀中國文化。
史:我不覺得各文化間有明顯的衝突,中國與西方文化有很多複雜的交錯點。利瑪竇對中國文化並未完全理解,卻十分重視;他受中國經典的影響,認為儒學和基督教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對道德問題都有相同的關懷,對人類文明如人口、生態等具有共通性的問題,進行平行的追求。
余:亨廷頓似乎認為儒教與西方文明是互不相容的,儒家文化不能與民主並存。但19世紀末以來,最早擁抱西方「民主」概念的,都恰恰是出身儒家教育的一些知識分子,如今文學派的康有為,古文學派的章炳麟、劉師培等人。這個問題好像尚待深究。
延伸閱讀:
孫康宜:文學偵探余英時
劉再復:我與李澤厚的《告別革命》對話錄緣起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