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90年代初,兩位移居異鄉的學者——李澤厚與劉再復相會於美國,展開了漫長而深入的交流。閒談之中,劉再復留意到了李澤厚的不少未曾發表、但彌足珍貴的洞見,於是有了以兩人對話錄形式發表的《告別革命》的成書機緣。1994年,這部後來引起中國思想界長久論爭的對話錄整理出版時,劉再復撰寫專文,回顧李澤厚之中國思考。
時隔28年,李澤厚先生在美逝世,蒙劉再復先生授權,聯經轉載此文。為摯友的告別,劉再復先生亦在思想空間寫下悼念之辭:
「難兄難弟,一起逃亡,一起告別革命,確認改良才是中國出路;亦師亦友,共同表述共同建構桃源,明了漂流方為世界原則。」
* 感謝劉再復先生授權轉載,原文題為〈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李澤厚和他對中國的思考〉,標題為編輯擬。
李澤厚的這套思想,卻恰恰是「解構」本世紀的革命理論和根深蒂固的正統意識形態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這是飽受苦難的中國人民易於和樂於瞭解和接受的,因此也就具有最大的影響力而成為正統教條主義的真正威脅。
1
1992年1月初李澤厚來到美國,而且來到科羅拉多,他在科羅拉多學院(Colorado College),我在科羅拉多大學(U.of Colorado at BOulder),相距只有兩小時的高速公路。於是,我們見面、打電話很方便,自然就常一起談論。撫今追昔,海問天空,談哲學,談文學,談中國,談美國,談毛澤東的烏托邦悲劇,談鄧小平的「實用理性」、談政治、經濟、文化、情愛的多元。在國內時我們就是好朋友,我一直把李澤厚視為師長,認真讀他的書和他的文章,並深受他的學說的影響。那時我們雖也常見面,但彼此都太忙、從未像此次贏得如此充分的時間進行如此充分的交談,在遙遠的異邦,天長地闊,我們竟能同處一地,這真是天降的學緣。
開始我們只是隨便聊聊,但我很快就發現李澤厚談論的內容許多是他著作中未曾表述過的、他的許多學理性見解非常獨到和寶貴,確實稱得上「真知灼見」。這兩三年,中國社會正處於大轉型的急速變遷中、社會問題極為龐大而複雜,也因此,學界各種似是而非的看法特別多,加上商品潮流的衝擊,人們為了迎合市場的需要也喜歡故作驚人之論和故張怪誕離奇之舉,讓人深受刺激而莫衷一是。在這種狀況下,我特別感到李澤厚的充滿理性的談話,非常難得。我所說的理性,是指揚棄情緒、揚棄道德義憤的思考。李澤厚一再表明,他的思索只對兩者負責:一是對歷史負責,一是對人民負責。有責任感才有理性。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他在國內學術界就遭遇到兩面夾攻:一是極左教條主義攻擊他「自由化」,二是某些年輕朋友抨擊他過於「保守」,但他在眾聲喧嘩中還是堅持「走自己的路」,這條路,就是理性之路。李澤厚已到「耳順之年」,也確實做到「耳順」,即不管來自何方的聲音,不管是批判還是禮讚,是詛咒還是歌吟,都不會影響他理性的思索。他對僵化的教條主義,一直作原則性的理論批評,但他的批評又是隱含於正面的學術建設之中。李澤厚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有一種學術性的信念,特別是對它的唯物史觀;但是,他對唯物史觀又作出自己的闡釋。他的闡釋和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闡釋不同。後者把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解釋為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而李澤厚闡釋和強調的則是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首先是要吃飯,然後才有思想、意識形態這一脈絡,即把生產力(科學技術)看作決定性因素,確認這一因素乃是人類通向自由王國的物質前提和基礎。李澤厚所強調的恰恰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所忽視的。這種忽視便造成對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鬥爭、文化批判、上層建築革命的迷信,而這種迷信又造成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各種社會浩劫,特別是精神浩劫。所以,他一再批評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和所謂「辯證唯物論」(包括《矛盾論》和《實踐論》,而主張「吃飯哲學」和「以經濟為本」。而這正是教條主義者所深惡痛絕的,所以,李澤厚總是被他們作為批判對象。在區別教條主義的同時,李澤厚也與一些年輕朋友的激進思想不同。其不同點一是關於非理性,一是關於徹底「反傳統」。李澤厚在美學、文學上一直強調感性、個體和偶然,早就指出文學的本體乃是情感而不是認識;但在社會歷史思考上則一直認為不能以激情代替歷史分析。在1989年出國前夕,他接受《人民日報》記者祝華新的訪問時說:「目前年輕人中流行一種徹底反傳統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與紅衛兵現象近似。當年的紅衛兵那麼狂熱的『砸四舊』、反傳統,也是認為要產生一種新文化,必須把舊文化徹底剷除掉。這種激烈的非理性的情緒反應衝力很足,有很大鼓動力量。但不能解決什麼問題,是一種破壞的力量。中國需要的是建設,而不是破壞。以前上上下下總講『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但並沒有真正立起什麼來。亂罵一通很容易,要正面作點學術建設卻沒有那麼簡單。中國缺乏的是建設性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他還說,現在的中國需要的是卡爾·巴柏(K.Popper)「你可能對,我可能錯,讓我們共同努力以接近真理」的理性精神,而不是「只有我對,你們都要不得」的非理性態度[1]。李澤厚出國後不久(也正是我們的對話之初),他就把這一次談話寄給我,並在邊上寫道:「讀此恍如隔世也。但我的看法竟毫未改變。當時即認為激情可能危險,不幸而言中也。」他在作此感慨的同時,寫作了《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文章,對20世紀中國的基本道路作了更為宏觀的理性思考,而他這些思考和我在1989年出國後所作的文化反省正好相通。1989年3月,我被李歐梵教授邀請到芝加哥大學參加他主持的「中國文化反省」的專案,就是對20世紀中國的一些基本思路進行理性重評,如文學上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思路、哲學上的心物二元對立思路、歷史學上的革命動力思路等。我在1989年出國之前,就非常注意李澤厚關於理性與感性的區分,注意他的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二律背反的思想,但是,由於我個人帶有更多的文學氣質,因此,在社會歷史分析上總是帶著許多情感,這一點,我在1989年出國之後有所長進,而對社會歷史的思考冷靜得很多。在這樣的時候,我對李澤厚的理性談話,更加有興趣。因此,我開始對談話作些錄音和作些記錄。將近三年之中,從科羅拉多到斯德哥爾摩到溫哥華,都是如此,這樣不斷進行,至今整理出來竟有二十多萬字,可作為一部書籍出版,這真是意外的收穫。
2
這部書稿,我們最初起名為「回望20世紀中國」,後來又加了一個正標題為「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5年版)。這一正標題也可說是整部對話錄的主題。影響20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遽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不包括反對侵略的所謂「民族革命」)。儘管這些行動在當時有其各種主客觀原因或理由,但到今日,是應該予以充份反省、總結和接受其經驗教訓的時候了。對20世紀中國來說,這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反省。在此新舊世紀之交,許多朋友都在展望2l世紀,我們也展望,我們的展望就是要明白地說:我們決心「告別革命」,既告別來自「左」的革命,也告別來自「右」的革命。21世紀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當作聖物那樣憧憬、謳歌、膜拜,從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動群眾情緒,最終又把中國推向互相殘殺的內戰泥潭。當然中國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輸出革命。21世紀應當是中國進行自我調整、自我完善、自我壯大的世紀。
李澤厚一出國就和我談論「革命與改良」,而我在1989年出國之後所寫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自我迷失》,也悟到中國知識份子充當激烈的革命家並非好事,中國只有和平——改良——建設才有出路。應當說,在中國宏觀走向的思考中,我和李澤厚都是溫和派。但是,在1989年出國之後有關方面卻動員和組織力量對我們進行全國性規模的大批判。使我困惑的是,李澤厚二十多年來始終站在經典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立場,思考比我還要溫和冷靜,但仍然報以他上百篇毫無道理的批判文章及幾十頂恐嚇性帽子。為什麼?為什麼左派教條主義如此仇恨李澤厚?為什麼他們不選擇某些遠為激烈的知識份子作為批判物件,而緊緊抓住李澤厚不放?現在我逐步明白,原來那些激進言論倒不見得有深遠影響,倒是李澤厚的這套思想,卻恰恰是「解構」本世紀的革命理論和根深蒂固的正統意識形態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這是飽受苦難的中國人民易於和樂於瞭解和接受的,因此也就具有最大的影響力而成為正統教條主義的真正威脅。這與50年代毛澤東不批蔣介石和陶希聖而大批溫和學者胡適的理由完全相同,因為胡適在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影響最大,從而是心腹大患,不批不行。但百年來的中國思想界,如果沒有康有為、梁啟超、胡適、魯迅,20世紀下半葉如果沒有李澤厚,整個中國現代思想史就是另一種狀況。而上述這些思想家卻幾乎不可避免都遭到兩面夾攻的命運。康、梁、胡無論矣,連魯迅當年不也既受北方的正人君子、又受南方的革命小將(創造社等)的左右夾攻嗎?總之,頑固派視為洪水猛獸,激進派斥為保守倒退、不夠革命,其實,真理也許正在這些既不保守也不革命的思想之中。
寧肯小心翼翼,穩健探索,絕不橫衝直撞、危言欺世;寧肯作鬥實觀察、常識談論,絕不作稀奇古怪的眼睛。我們以為,這才是經過百年暴風驟雨、付出巨大代價的世紀末中國所真正需要的態度。
3
在整部對話錄中,有一小半是靠錄音整理出來的,而大半則是靠記憶而書寫下來的。當然,兩種方式最後都由李澤厚作了仔細校閱和補正。我所以能記下來,一是因為李澤厚的談話思想明晰,便於記憶。我平素讀書就注意讀思想,不太注意讀文采,所以腦子中的思想膠汁比較多;二是我對李澤厚格外尊重。《猶太智慧》中有句悟語:對人心悅誠服可幫助你的記憶。我對李澤厚正是心悅誠服,格外尊重,並覺得,他的寶貴學識,是值得我調動生命的黏液去把它嵌進自己的心靈之中的。無論是在上學的年輕時代還是已當上文學研究所所長的時候,我都這麼想。在當文學所所長期間,我常藉著可坐小車的「特權」、跑到幾十公里之外的皂君廟去聽他「坐而論道」,我的《論文學的主體性》就是在他的影響下形成的。當我讀到他的《康德主體性哲學論綱》之後,我禁不住內心的激動,並隱約地感到,我將要在文學理論領域中進行一次顛覆性和建設性的變革,令機械反映論作霧散雪崩,而《論綱》就是我的起始之點。所以我一再說,大陸主體性理論的始作俑者是李澤厚。關於這一點:文學研究所的兩位優秀的年輕學人陳燕谷和靳大成在《劉再復現象批判》中曾作過精彩的表述。他們說:「必須公正地指出,在我國,主體性問題是李澤厚首先提出來的。當『十年動亂』剛剛結束,很多人還處於思維混亂的情感宣洩狀態時,大部分人還在撫摸昨日的『傷痕』時,李澤厚即以其獨到的洞察力和思想深度為創造成熟的歷史條件進行了寶貴的思想啟蒙工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實際上成為中國人文科學領域中的一個思想綱領的制訂者,他的哲學、美學、思想史著作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包括劉再復在內。《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主體性論綱》以及《思想史論》三部曲,他的著作一再成為當代文學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他對康得、對馬克思的主體理論的創造性闡述與發揮,使這種思想像一股暗流潛伏在每一個熱血的思考人生的人心中。」[2]
這兩位年輕學人要求在我主編的《文學評論》上發表這一意見的時候,我非常興奮。這不僅因為他們對我的「批判」給予我激勵和啟迪,而且因為他們比其他學人都更真實、更正直地指出李澤厚在中國的位置和作用。他們畢竟年輕,胸懷清朗而坦蕩,論述的才華沒有被其他功利算計所淹沒。我讀了這篇文章之後很高興,因為他們說出我想說的話。我一直認為,李澤厚是中國大陸當代人文科學的第一小提琴手,是從艱難和充滿荊棘的環境中硬是站立起來的中國最清醒、最有才華的學者和思想家。像大石重壓下頑強生長的生命奇跡,他竟然在難以生長的隙縫中長成思想的大樹。在我從青年時代走向中年時代的二、三十年中,我親眼看到他的理論啟蒙了許多正在尋找中的中國人,並看到他為中國這場社會轉型開闢了道路。但是,李澤厚不僅沒有被自己的故國充份認識和肯定,而且一再被作為政治打擊的對象(這種打擊從反胡風就開始,他被當作胡風分子整了一年,以後則打擊不斷,直到現在還沒有結束)。對此,我常對朋友感慨:人類的弱點真是「貴耳賤目」、「貴遠賤近」。西方學界的名人權威,離得遠遠,如坐雲端、愈遠愈奇,因此便捧之上天。這種崇奉本來也並非沒有道理,但反過來對自己的土地所孕育的傑出兒子按之入地甚至想置於死地就不免古怪。這除了有人心存卑鄙的動機之外,多數人乃是因為自己的人才離得太近,容易看到他是凡人一個而忘記了他的傑出與卓越。這種現象,與「僕役眼裡無英雄」這一諺語的意思相通。侍僕因為離英雄太近,所以總是看到英雄只是凡人而忘記他是英雄。這種精神現象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就分析過,他說:
諺語說,「侍僕眼裡無英雄」;但這並不是因為侍僕所服侍的那個人不是英雄,而是因為服侍英雄的那個人只是侍僕,當英雄同他的侍僕打交道的時候,他不是作為一位英雄而是作為一個要吃飯、要喝水、要穿衣服的人,總而言之,英雄在他的侍僕面前所表現出來的乃是他的私人需要和私人表像的個別性。[3]
李澤厚也逃不了被「僕役」看輕的命運,他多次被哲學研究所的同事批評「很少去打開水」,要喝水已屬凡人,喝水而少打開水更不能成為英雄。我聽過許多對李澤厚的非議,但這些非議,並不是李澤厚不是哲學家,而是非議者乃是一些混跡哲學界中的哲學庸人和自命不凡的「老子天下第一」者。我喜歡陳燕谷、靳大成對李澤厚的評價,正是他們擺脫了世俗的僕役的眼睛,而用一種學理的,歷史的眼睛。在庸人們看來,這是「吹捧」,其實不對,這是理性評價。就在這兩位年輕學人發表《劉再復現象批判》的幾個月後,著名的法國國際哲學院宣佈李澤厚為正式成員(院士),給予這一榮譽的都是當代國際上最傑出的哲學家。在西方學界享有極高聲譽同時也被中國學人十分崇敬的伽達默爾、哈貝馬斯、利科、斯特勞森、奎因、大衛森等就是被這一學院選出的院士。在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唯有李澤厚一個人得到這一殊榮。這本來是中國應當引為光榮的。一個正常、純潔、沒有嫉妒心的民族,應當為自己能誕生一個這樣傑出的思維腦袋而自豪,但是,很可惜,報以這一榮譽的,先是沉默(新聞界不作報導),後是大舉的批判和討伐。1989年初,在歡迎布希總統的宴會上,我見到香港《文匯報》記者劉紹銳先生,對他感慨說,政治家們天天在報刊扮演主角,但學術上像李澤厚這種事恐怕也得寫上一筆吧。他畢竟正直,這才發了一條消息。我也不是說法國國際哲學院的月亮就比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月亮圓,但在這一事上,它的眼睛確實比中國文化界的眼睛單純。而且它還啟示我們,至少啟示我:要珍惜,要珍惜自己祖國的傑出人才。一個不愛自己的傑出兄弟的人,不是真正的愛國者。我們不要自高自大,但也不要妄自菲薄;我們敬重哈貝馬斯是應當的,但敬重李澤厚也無可非議。大約是著意要對妄自菲薄進行反叛,我的朋友、中國哲學界的後起之秀甘陽,在去年哈佛大學召開的會上說:怎麼就知道哈貝馬斯,但我們的李澤厚比哈貝馬斯還了不起。這不是激憤之辭,早在芝加哥,他就認真地和我說過。我所以著意和李澤厚的對話並認真地把他的思想加以整理,與上述我對他及中國學界的認識自然有關。
4
此時出稿就在面前,在即將發出之時,我從頭到尾又翻閱了一遍,好像在翻閱逝去的歲月。閱完之後,我感到欣慰和踏實。所以欣慰,是因為我以自由的心靈說了該說的而且願意說的話,沒有背叛自己;所以踏實,是我們的談話畢竟是負責而慎重的。談話之初,我們就共同覺得,這個世紀中國的豪言壯語、驚人妙論實在太多了,那種雄赳赳氣昂昂的慷慨激情也實在是夠充份了。今天還是謹慎一些為好。寧肯小心翼翼,穩健探索,絕不橫衝直撞、危言欺世;寧肯作鬥實觀察、常識談論,絕不作稀奇古怪的眼睛。我們以為,這才是經過百年暴風驟雨、付出巨大代價的世紀末中國所真正需要的態度。而我們的談話,採取的正是這種態度。讓我感到踏實的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做的是一件比較切實的、該做的工作,這就是反省20世紀中國的基本思路。這些流行於社會並被我們的心靈接受的思路,除了上文已經提過的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外,還包括歷史決定論思路、辯證唯物論思路、政治倫理宗教三位一體的思路、階級鬥爭與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兩項對立的思路、意識形態崇拜的思路等等。與這種思路不同,對話錄主張以經濟為本,主張階級合作、階級調和,主張多元共生,主張改良漸進,主張開放輿論,主張政治與文學的二元論,主張社會與政府的區分,主張注意歷史發展的二律背反,主張重新確立人的價值等等。我到海外之後,對20世紀中國文化進行反省,覺得能夠給故國以切實幫助就是改變一些在本世紀特別是在本世紀下半葉流行的而且被普遍接受的習慣性思路。現在的中國已開始從這些思路走出來、但作為自覺意識地走出來,還需要知識者的工作。中國是一個充滿潛力的偉大國家,只要打開思路與眼界,它就會贏得光明的將來;反之,如果還陷入20世紀的一些基本思路,那麼,21世紀必將要發生可悲的歷史重複。我們所以要回望20世紀中國,就是為了使故國人民從百年風浪中吸取經驗教訓,避免發生悲劇性的圓圈遊戲。李澤厚很重視英國的經驗哲學,特別是海耶克的政治哲學和巴柏的科學哲學。因此,他認為對20世紀中國極其豐富的經驗教訓給予認識上的提升,意義非常。就以毛澤東來說,他本人是極有才華的,而且很早就想避免發生今天蘇聯的悲劇並從其體系中分離出來,免於同歸於盡,這有功勞;但是,他卻把蘇聯的列寧——史達林意識形態推向極端,把無產階級專政從政治經濟領域推向心靈領域,結果導致自我毀滅性的文化大革命和帶給中國許多痛苦和災難。吸取這種教訓,特別是從宏觀思維的角度上去總結教訓,對於中國是很重要的。總結自身的教訓這比求助於西方學者韋伯、維特根斯坦、福柯的思想和語言更為重要。在我們的對話中,這也僅僅是開始,但是,李澤厚所總結的毛澤東在思維上犯了「迷信意識形態」和「迷信戰爭經驗」這兩條根本性錯誤,無疑是很有價值的。對於前者,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沒有看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本身也是著眼於文化批判(這在西方是有道理的)。他們不可能有中國學者如此痛切的感受:沒有經濟充分發展這一前提,其他什麼都談不上,包括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對於後者,在中國更是極其特殊。中國經歷了這麼長的戰爭,整個革命過程那麼艱難與複雜,這是蘇聯、東歐所沒有的,因此,形成對戰爭經驗的迷信和崇拜並不奇怪,何況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國革命也犯過同樣錯誤;然而,當一個國家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之後,如果還迷信搬用戰時的經驗,就會造成人為的緊張,恐怖和種種畸形的激進狀態,乃至造成在反對資產階級法權名義下取消貨幣、辦全民食堂等「戰時共產主義狀態」,而且使許多領域,包括精神文化領域變成以互相廝殺為樂的現代瘋人院。
整理完這部對話錄,我很高興。在海外漂流的文字生涯中,我又有一次新的完成,而且是非常有意義的完成。歲月沒有虛度,思想未被堵塞,於山明水秀中寄寓情愫,於友人智慧中領悟滄桑,這就是美好人生。時空無窮,個體有限,我沒有更多的期待,但這一次一次的筆墨完成,使我感到在人間很有意思。
1994年11月l5日於科羅拉多大學
[1] 1989年4月8日《人民日報》。
[2] 陳燕谷、靳大成:《劉再復現象批判》,《文學評論》1988年第2期。
[3]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第172頁,賀磷、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出版。
延伸閱讀:
黃克武:該怎樣理解李澤厚?他的思想變遷,與身後一整代人(二之一)
黃克武:李澤厚「告別革命」之後(二之二)
1941年生於福建省南安縣劉林鄉。1963年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新建設》編輯部。1978年轉入中國文學研究所,先後擔任該所的助理研究員、研究員、所長。1989年移居美國,先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科羅拉多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加拿大卑詩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科技大學、臺灣中央大學、東海大學等高等院校裡擔任客座教授、訪問學者和講座教授。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客座教授。
著作甚豐,已出版的中文論著和散文集有《讀滄海》、《性格組合論》等六十多部,一百三十多種(包括不同版本)。著作、文章被譯為英、韓、日、法、德、瑞典、義大利等多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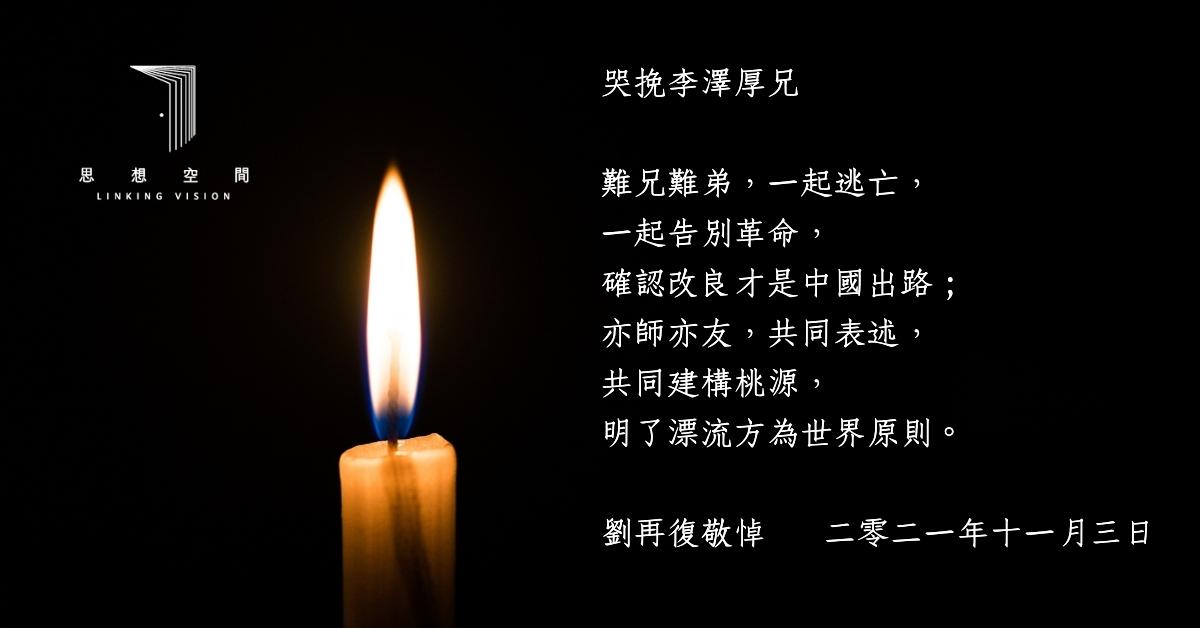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