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1948年出生於匈牙利,英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社會學教授。其學術研究主要圍繞帝國主義問題和發展問題,著有《Culture of Fear》、《Paranoid Parenting》、《Therapy Culture》等書。
Frank Furedi:當代社會知識分子的專業化危機


知識分子的工作一旦職業化,就不再具有獨立性, 也喪失了提出艱難社會問題的潛力。相反的,它也獲得了管理或技術官僚性質的功能。
隨著傳統知識分子衰落而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包括市場對學術生活的影響日增、學術生活制度化和職業化、媒體力量日益增強,以及行使意志自由的公共空間遭到侵蝕。許多討論這個問題的作者宣稱,推動這種學術面貌轉變的主要力量,是學術界的擴張。根據這一看法,學者職業化使知識分子生活的生命力受到重創。雅各比對這一點有很好的論述。[1]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 ,專家(expert) 和專業人員(professional)的興起,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自1950年代以來,這一趨勢逐漸變得清晰可見,現在更有力地影響著人們對權威的看法。那些把知識分子描繪為「新階級」的人常說,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現 已成為支持統治精英權威的意識形態。從這一點來看,可能會得出知識分子比過去更有力量的結論。這種看法由古德納在1970年代系統化地提出來,他聲稱「專業主義潛移默化地使『新階級』榮升為高尚合法的權威典範,他們 運用其專業技能,並關注於整個社會。」[2]
專業權威的提高是否會增加知識分子的影響力,這點讓人存疑。專業人士的心智勞動主要是用來提供服務,而不是促進思想。在專業任務中所含括的思想,不是因其自身價值,而是作為實現的工具而受重視。定義知識分子的並不是從事的學術工作,也不是任何特殊的經濟功能。知識分子是通過他們與社會的關係,以及思想的發展而形成的。不論他們的職業是什麼,都不會直接以他們的工作,來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
與新階級的理論相反,專業主義的擴張效應可能帶來思想活動的新障礙,而專業主義所提倡的價值和行為方式,可能與知識分子的相矛盾。諸如對現狀提出批評、充當社會的良心,或者不計後果追求真理,都不是專業人士的工作。就如卡瑟琳.弗瑞德忠斯多迪所說,職業專家可以是個批評的知識分子,但是「當他作為一個專家時,人們肯定不希望他表現的像批評的知識分子」。[3] 事實上, 職業專家與知識分子的行為方式相距甚遠。這也解釋了許多探討這個問題的作者,相信專業主義成為知識分子所面臨最嚴重的威脅。薩伊德詳細闡述了專業主義與知識分子作風間的差異:
我所謂的專業主義,是指把知識分子的工作理解為謀生手段,從早晨9點到下午5點,一隻眼睛盯著鐘錶,另一隻眼睛轉向所謂合宜的職業行為——不找麻煩,不跨出認可的範式或界限外,使自己暢銷受歡迎,尤其是要體面好看,讓自己不涉爭議、不涉政治,並且要保持「客觀」。[4]
知識分子的工作一旦職業化,就不再具有獨立性, 也喪失了提出艱難社會問題的潛力。相反的,它也獲得了管理或技術官僚性質的功能。
矛盾的是,對心智工作的強大需要,反而給知識分子的活動增添了新障礙。思想市場的繁榮促進了知識型工作的專業化。就如艾爾曼注意到的,在把知識型態的工作從邊緣移向中心,對知識性的生活表現產生前所未見的影響。這種過程的結果,是制度化知識分子的相關活動。
傳統上那些製造知識分子的機構和方式——大學、文化和政治的公共領域,尤其是與文化和階級衝突銜接之處——在現代社會後期越來越制度化、專業化和商業化。作為一個社會批評家,曾是知識分子傳統理想的核心也被加以制度化,其程度之嚴重, 已使「知識分子」僅成為電視談話節目和嚴肅報紙「文化」版中的固定特色單元。[5]
所以,雖然今日的心智工作比過去更明顯,但卻是由機構及其專業人員構成而非知識分子。那些試圖通過媒體傳播思想的知識分子,常變成節目的說話人頭,只有在提供媒體所需的引用和娛樂時,才會被加以容忍。
學術工作的制度化影響思想和社會間的關係至深。作為專業人士和專家,甚至作為學者,知識分子的權威不是建立在他們思想的品質上,而是在具有專業知識的主張上。他們的用語越來越技術和專業化,不再是可被大眾理解的日常用語。學者所使用的新語言反映了一種獻身狹窄專業的生活方式。通過這種做法,知識分子的活動內容本身也發生了變化。弗瑞德忠斯多迪指出,像文學批評幾乎已成「一種專屬學院出身者的專業化行為」。她認為,這已改變批評的形式和內容,因此一個跟不上文化批評新潮流的人,就無法在這行長久立足。[6]
知識分子生活的專業化,促使探討這個問題的人懷疑知識分子的獨立角色是否存在。有人也不斷提出,市場的壓力同樣直接衝擊著思想領域,高度專業化導致知識越來越支離破碎,也逐漸削弱知識分子與整體社會打交道的能力。艾爾曼沿著這一思路指出,「市場經濟的運作具有決定文化產生的內容的力量。」[7]
市場經濟所具有的力量無疑對文化創造內容產生重要的影響,但卻不是市場造成知識分子的潰退。在過去, 知識分子通過反市場而得以茁壯——如今,他們卻可能借助市場來實現其抱負。認為知識分子無知地成為環境的犧牲品,忽視了他們樂意運用學術工作制度化中機會的事實。知識分子在推廣專業化和制定學院規章制度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基的理性主義也讓位給實用主義,這是種顯見的對生活的工具主義態度。
知識分子的獨立感,被要求獲得體制的肯定和承認所取代。在當代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缺席的相關討論中,這一變化尤其顯眼。討論一開始原試圖解釋獨立知識分子數目降低的原因,後來一些發言者卻呼籲機構和公共組織協助營救日漸消失的公共知識分子。某些美國大學把這視為是一種市場機會,推出了培訓公共知識分子的研究生課程。其他人則呼籲公共機構採取行動來推動知識分子的活動。從這一觀點出發,兩位美國學者說:
最後,我們呼籲對這些種 各異的公共知識分子工作,提供更多在制度和物質上的認可,這包括重視和鼓勵公共工作。比如, 對那些從事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的人,機構應提供或要求培訓或資格證照,使所有教職員工都能參與某種服務學習,並對那些認真努力融入社區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外的自由時間或者減少工作量。[8]
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工作要求提供資格證明,正說明了學術獨立的觀念已讓位給專業化潮流。當知識分子的身分需依賴機構加以承認時,顯示與學術自由的傳統追求已毫無關係了。
今天的專業思想家的文憑主義心態,很難解釋為市場經濟作用的直接結果。專業人士和專家市場的擴大,無疑影響了這些變化,但卻無法解釋人們欣然接受與傳統知識分子角色不相稱行為的態度。要想明白前因後果,就必須在影響學術工作結構變化之外去尋找原因。
(本文摘錄於Frank Furedi:《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標題為編者所擬)
[1] 見Jacoby (1987)。
[2] Gouldner (1979), p.19.
[3] Katrin Fridjonsdottir (1987), “ The Modern Intellectual: In Power or Dis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and Intellectual W ork ” , in Eyerman, Svensson and Soderquist (1987), p.121.
[4] Said (1994), p.55.
[5] Eyerman (1994), p.191.
[6] Katrin Fridjonsdottir (1987), “ The Modern Intellectual: In Power or Dis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and Intellectual W ork ” , in Eyerman, Svensson and Soderquist (1987), p.121.
[7] Eyerman (1994), p.92.
[8] Brouwer and Squires (2003), p.212.
| 閱讀推薦 |

| 相關書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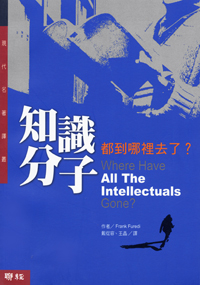
佛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1948年出生於匈牙利,英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社會學教授。其學術研究主要圍繞帝國主義問題和發展問題,著有《Culture of Fear》、《Paranoid Parenting》、《Therapy Culture》等書。
Be First to Comment